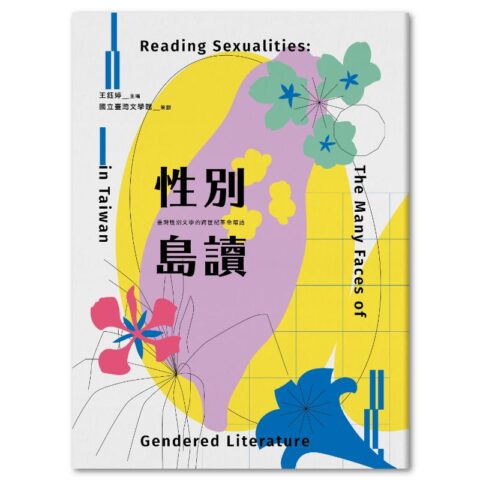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
原書名: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
出版日期:2007-05-11
作者:宇文所安
譯者:陳引馳、陳磊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08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1498
系列:宇文所安系列
尚有庫存
中國的「中世紀」和歐洲意義上的中世紀(the Middle Ages)不同,本書所指的「中世紀」,是指中國的中唐時期,作者使用一個歐洲的詞語,是喚起一種聯想:歐洲從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時期,中國也從唐到宋做一個轉型。「中世紀」的稱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可以從這裡開始討論,八九世紀之交,也就是在唐貞元、元和年間,所產生的文學、文化史上的重大變化。
中唐是中國文學中一個獨一無二的時刻,又是一個新開端。在許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兩百年後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僅僅數十年前的盛唐詩人。中唐文學的特色,有特立獨行的詮釋,有對小型私家空間的迷戀,有優美的園林,也有浪漫的愛情故事和鍾愛的情人。
作者:宇文所安
美國哈佛大學James Bryant Conant特級講座教授,任教於比較文學系和東亞語言文明系。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和比較詩學。研究以中國中古時代(200-1200)的文學為主,目前正在從事杜甫全集的翻譯。主要著作包括《晚唐》(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2006)、《諾頓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論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1996)、《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Ome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1985)、《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等等。
譯者:陳引馳
譯者:陳磊
前言
導論
特性與獨占
自然景觀的解讀
詮釋
機智與私人生活
九世紀初期詩歌與寫作之觀念
浪漫傳奇
《鶯鶯傳》:抵牾的詮釋
附錄
後園居詩(九首之三) 趙 翼
霍小玉傳 蔣 防
鶯鶯傳 元 稹
譯後記
前言 宇文所安
在本書的標題中,「中世紀」這一稱謂是加了引號的。引號的作用是提醒讀者:中國的「中世紀」和歐洲意義上的中世紀(the Middle Ages)不同,用「中世紀」來描述中唐可以說是老子所謂的「強名」。
我使用一個歐洲的詞語,是爲了喚起一種聯想:歐洲從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和中國從唐到宋的轉型,其轉化有很多相似之處,也存在深刻的差別。對英語讀者來說,使用「中世紀」的稱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我們可以從此開始,討論八九世紀之交,也就是在唐貞元、元和年間,初次産生的重大變化。
「中世紀」這一稱謂對英語讀者來說是個有用的切入點,因爲它聽起來很熟悉;那麽,它對中國讀者來說也是個有用的切入點,因爲它的新奇。書的英文標題有兩個「中」字:「中唐」把這一歷史時期放在一個在文學和文化史研究中十分熟悉的範疇(也即唐朝)裡面;而「中世紀」則要求讀者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思考這一歷史階段。當我們改變文學史分期的語境,熟悉的文本也會帶上新的重要性,我們也會注意到我們原本忽視了的東西。
我不是說我們可以任意劃分歷史階段;我希望指出的是,存在著不同的方式(同等有效的方式)來理解一個歷史時期。用朝代的模式來思考文學和文化史當然是可以的,但這一模式已經成爲家常便飯。有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博物館裡的雕像的正面:我們可以看很長時間,可以看很多遍,直到我們認爲我們已經非常了解這一雕像了。但是,假使我們換一個角度||這一角度可能是很不舒服的,不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所設計和期待的,但是,從這一角度,我們卻會看到我們以前從未注意到的因素;我們感到驚異和興奮。假設在這個時候,一位藝術史家向我們解釋說,雕像曾經放置在一座廟宇之內,善男信女們在進入廟宇時只能從某一特定的側面看到雕像,而不能很容易地看到雕像的正面,這時,我們就會意識到:我們已經看習慣的雕像,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由博物館陳列展品的慣例所産生的一種特定形象,如此而已。
按照朝代進行分期的文學史,是文學中的博物館形式。我們已經拜訪了很多這樣的博物館,它們是我們整理閱讀經驗的熟悉模式。這種理解模式並不算壞,但是只有從一個陌生的角度進行觀察,我們才能看到新東西。
學者應該大量閱讀,然後思考所閱讀的材料。這是「學者」最簡單的定義。學者和任何讀者一樣,有對文學作品作出個人化反饋的能力。但是,學者進行評論的權利是通過廣泛的閱讀和思考贏得的。如果學者發現某種現象很新奇,這位學者必須追根究柢,問一個爲什麽。
中唐總是給我帶來驚訝。在中唐之前,當然也有許多新鮮而激動人心的東西,不過,往往要把它們放在一個可以追溯到東漢的傳統中進行理解。如果杜甫是個例外的話,那麽我們要記得,杜甫也是由於中唐文人對他的欣賞才獲得其重要地位的。中唐的主要文人就宇宙萬物、社會、文化等提出問題的頻繁度和激切的程度,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同時,他們也總是游離和遊戲於常規的反應和答案。當然,我們總是可以找到一些先例,但是,如果我們按照歷史順序閱讀唐代文學,中唐是讓人吃驚的。在這一時期,人們和過去的關係改變了;以往通過重複建立權威的文化,現在由一個通過發問建立權威的文化代替了。
比如說中唐的傳奇小說〈任氏傳〉,是以一個傳統的「狐狸精故事」開頭的;這樣的故事應該在鄭生發現自己迷戀的女子原來是狐狸的時候結束。但是,鄭生沒有扮演這樣的傳統角色,相反,他告訴任氏,他不在乎她是異物,還是一如既往地愛她。只有在超越了標準的「狐狸精故事」時,小說才變得真正有意思起來,而我們也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文化世界。
〈任氏傳〉是中唐文化的典型産物。在中唐,有一種智識上的騷動不安,一種人性的騷動不安,人們不再滿足於舊有的答案。譬如說韓愈,「文學史博物館」裡的一座典型的「雕像」,當我們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看待他,就會發現他不再是儒家價值觀念的虔誠代言人,而是一個非常不安於傳統的思想家,一個不得其平而鳴的人物。
盛唐文學仍然代表了唐代文學的典範,但是我們應該記得,是中唐首次把盛唐變成了這樣的典範。中唐以盛唐爲基準和思想背景,來理解自己的知性文化。我們不能脫離中唐來孤立地看待盛唐。
這裡需要提到,這些文章所沒有涉及到的一個方面,是十一世紀後期商業印刷的發展。這是定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以及衡量中國文學文化之重大轉折的另一種方式。這一變化也是在中唐初見端倪的。
導論
這部論文集的問世,已是在我上一部討論盛唐的唐詩史的寫作十五年之後了。在這期間我常被問起是否有意在繼《初唐詩》和《盛唐詩》的寫作之後,再出一部中唐詩歌史。收在這部集子裡的論文,可以說是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同時表示了寫作這樣一部中唐詩史之不可能性。
這裡的論文是具有文學史性質的,然而它們本身卻不能構成一部文學史。它們不是要描述一個變化的過程,或是給出一幅大小作家的全景圖,而是要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和文體來探討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問題。這些具體的問題就其本身的性質而言,與文化史或社會史等更大的領域息息相關。在一個層面上,這裡所討論的文本本身就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對於占有或領屬權的公開描述,對於微型園林的誇大而富於諧趣的詮釋,以及有關男女間風流韻事的討論,本身就是具有社會性的行爲表現,而它們所體現的價值也必定是在某種程度上爲傳抄這些文本的讀者物件所認同的。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些話語現象是如何與更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相聯結的||如土地所有權的模式、園林建構及納妾制度||則不在本論文集的討論範圍之內。
稱它作一部「中唐詩史」是不恰當的,因爲從七九一年到八二五年這一期間的詩歌,較之於初唐和盛唐詩,更難以體裁分類。在風格上、在主題上,以及在處理的範式上,中唐詩遠比盛唐詩紛繁複雜,而且其詩歌範圍擴大與變化的方式與其他話語形式中發生的變化緊密相關。詩歌、古典傳奇及非虛構性的散文享有共通的旨趣,這樣的情形在初唐與盛唐則並不如此常見。可能也正是對中唐詩這一側面的直覺印象才使得自十三世紀以降諸多有影響的批評家指責這一時期的詩歌較之於盛唐詩,少了一份「詩味」。然而中唐詩歌的廣度,超越先前詩歌局限的態勢,也恰好成爲其長處。
現代文學理論在宣稱文體的自成系統(每一話語形式都以其專擅而它種形式又不能替代爲榮)與宣稱某一時期所有文化再現樣式都享有共同的歷史淵源這兩極之間搖擺。前者確信詩歌、小說或戲劇是相當獨特的,它主要關注的是拓展其自身的文體潛能,回應其自身的文體發展歷史;後者將所有同時代的話語形式都看成是分享著超越了文體形式的某種歷史決定因素。
文學理論要求我們在這些相互對立的可能性之間做出抉擇,或是試圖調和它們。這些可供選擇的可能性被視作「研究門徑」而不是存在於研究對象之中的歷史差別;相反,從一種具有歷史性的觀點我們也許會說:「有時候這一種占上風,有時候則那一種占上風。」在某些時期,縱覽全局,呈現出強勁的文體系統;初唐與盛唐便大致是如此,於是在這種情形中「詩歌史」成爲可能。然而中唐詩打破了文體的統轄與局限;這樣一些深刻地改變了中唐詩的關注在中唐作品中隨處可見,而中唐詩的歷史也不再僅僅屬於詩歌。
第一篇論文,〈特性與獨占〉,將中唐文學對身分的再現視作對他人或爲他人所排斥。在個人身分的層面上,這樣的一種特立獨行可以表現爲宣稱自己優於他人,不過它也可以是一種異化感,而這種異化感造成了他人對自己的排斥。在中唐時代的作品中,特立獨行表現爲一種獨特而易於辨識的風格,它可以爲他人所襲用,但它卻總是與一個個體作家掛鈎。在那篇著名的︿答李翊書﹀一文中,韓愈也同樣將自己散文的境界趨於精純的過程歸結爲摒除屬於(或取悅於)他人的雜質。在群體身分的層面上,特立獨行也以同樣的形式表述出來,比如一個文學集團將自身與大的作家群體區分開來;又比如對韓愈而言,華夏文化的景觀取決於對外來成分(佛教)的排除。這一類型的獨特性在形式上與一種新的領屬權話語相通,也就是說,二者都排斥他人的獲得或占有。
接下去的一篇論文,︿自然景觀的解讀﹀,討論各種不同的再現風景的方式,顯示自然的潛在秩序如何在中唐成爲一個問題。一方面是文本對於自然的井然有序的表述和品評;這樣的風景具有建築性,這在先前的詩歌是罕見的。另一方面是對於缺乏潛在秩序的風景的再現,是美麗卻不連貫的細節的堆砌。這就引發了柳宗元在一篇著名的散文中所提出來卻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否存在一個造物主,在大千世界種種現象的背後,是否存在目的與靈性。
這第二篇論文僅限於物理世界秩序的再現問題,然而同樣的問題也在人倫世界的事件中生成。︿詮釋﹀這第三篇論文探討中唐時代的一種傾向,它對現象所給出的推測性解釋,要麽就是與常識相乖違,要麽就對通常認爲無需解釋的境況做出解釋。如此獨特的詮釋,缺乏任何證據或文本章句的支撐,常常沾染上一層富於反諷甚或瘋狂的意味。這樣一來詮釋便被看成了一種主觀的行爲,不是取決於有待詮釋的現象,而是取決於詮釋者的動機與處境。中唐時代對於這一新的、更具主觀性的詮釋的自覺意識,可以在白居易作於幼女夭折後自寬自慰的兩首詩中窺見一斑:他知道他只是在自寬自解,他作爲認識主體爲滿足其他動機而使用的道理不足以容納感情現實。
主觀詮釋行爲在純粹遊戲的層面實施時,便成爲機智的戲謔。︿機智與私人生活﹀審視對私人空間和閒暇活動的遊戲性的誇大詮釋,作爲抗拒常規價值的一種私人價值觀的話語。這樣的價值和意義,遊戲性地奉獻給讀者,屬於詩人一個人,構成了一個有效的私人界域,迥異於中國道德和社會哲學專橫的一面,這一面甚至將個體的或家庭中的行爲都納入公衆價值的一部分。舉例來說,當五世紀的一位官吏辭官歸田,成爲一名隱士棲居在山林間時,這表面上是屬於個人的抉擇有可能被而且確實通常被理解爲一項政治宣言;而當一位中唐詩人戲謔地聲稱自己在公事之餘全身心地爲松林或寵鶴所迷時,他那戲謔性的誇示已從公衆和政治的意味中擺脫出來。當我們發現這個遊戲世界通常和詩人的擁有物相關時,我們並不感到驚訝。這些文本糅合了領屬權的問題、主觀詮釋以及對他人的拒斥,因爲他人常規性的觀點使他們無法看到詩人所採取的價值觀。
詩人在他的微型園林裡上演適意自娛的小戲,在詩中吟詠這樣的時光,此刻他已經對有關詩歌是如何創作出來的假設做了重大修正:不是詩直接對經驗做出回應,而是經驗被策劃,爲了作詩而將空間做了規劃經營。︿九世紀初期詩歌與寫作之觀念﹀探討中唐時期對寫作,尤其是對詩歌寫作進行再現時發生的某些根本性的變化。
在八世紀討論技巧的詩學中我們已經發現了一種論調,承認在誘發詩興的經驗和詩歌的寫作之間有一段間隔。詩歌創作與經驗之間的關係被描繪成事情過後的重新回味。到了九世紀初期,原先所設定的詩外的經驗與創作間的有機聯絡已不再是想當然的了。詩的基本材料是對句,被視作「意外的收穫」;對句是由深思熟慮的匠心精雕細琢而成,鑲嵌入詩。這樣的詩歌創作觀,不管在西方詩學史的架構中看來是多麽的司空見慣,在一個將自然本色奉爲圭臬,且原先是靠對經驗的敏捷回應(如果不是完全的即興)來保證的中國詩學系統內,它代表了一個重要的轉型。到了九世紀,詩可以被視爲某樣被構築出來的東西,而不是一種自然的表達,且詩中所再現的是藝術情境而不是經驗世界的情景。這個在骨子裡「富於詩意」的情境常被形容爲「……外」或「不盡……」||語詞或普通人感受到的意象是難以窮盡的。而在一段有關中唐詩人李賀作詩過程的膾炙人口的描繪中,我們又看到詩作爲有待鍛造和擁有之物,作爲想像出來的而又是具體可感的構造,毫不遜色於微型園林:每日詩人騎驢而出,靠詩興靈感偶得一聯半句,記下來投入囊中;每晚傾囊而出,將其綴成詩篇。
最後兩篇文章探討八世紀晚期成形的新的浪漫文化。題名︿浪漫傳奇﹀的文章以︿機智與私人生活﹀中提出的問題爲前提,探討︿霍小玉傳﹀。這篇有關情愛和背叛的故事作爲一個例證,顯示了私性的價值觀是如何試圖爲這份體驗開闢一個空間,使得它免受外界社會的強制。與機智的詩人吟詠他的微型園林有所不同的是,定情不是純粹的遊戲;它的私性疆域難免會和社會之間産生牴牾,受到社會的干擾。然而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觀衆的存在,他們觀摩、評判並最終介入顯然是屬於私生活的情愛故事。最終浪漫文化不是屬於情人,而是屬於閱讀這些故事的社群,而且在他們當中得到文字表現。在浪漫故事中,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社群,雖說這一社群明顯是由屬於公衆社會價值世界的人們所組成,卻支援浪漫愛情的私性價值。
︿︿鶯鶯傳﹀:牴牾的詮釋﹀探討的對象是所有唐傳奇中最著名的一篇。女主角鶯鶯和她的情人張生是姻戚,本可以明媒正娶,卻捲入了中唐時期熾烈而犯禁的浪漫文化,其結局正如大多數浪漫故事那樣,以鶯鶯遭張生遺棄而告終。男女情人都是一名詮釋者,試圖將敍說的故事遵循他或她自己的意向來引導,且每一位都要求觀衆站在對他或她有利的立場上來評判。可是兩位情人對於事件的詮釋相互抵消,於是我們所面對的是唐代敍事文中這樣一幅獨特的情景,其中公衆的評判成爲訴求的對象,然而卻又沒有固定的評判。情愛故事又再度納入社群的框架中,社群製造流言,就這段風流韻事創作詩篇,並忖度該如何評判張生的行爲。
中唐既是中國文學中一個獨一無二的時刻,又是一個新開端。自宋以降所滋生出來的諸多現象,都是在中唐嶄露頭角的。在許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兩百年後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僅數十年前的盛唐詩人。以特立獨行的詮釋而自恃,而非對於傳統知識的重述,貫穿於此後的思想文化。對於壺中天地和小型私家空間的迷戀而做機智戲謔的詮釋,成了在宋代定形的以閒暇爲特徵的私人文化複合體的基礎。浪漫文化不但繼續流傳,而且唐代浪漫愛情故事不斷地被複述和擴充,而後代的作家還在試圖處理浪漫文化所提出來的問題。當宋代大作家蘇軾觀賞一幅美麗的風景畫時,他的反應不是尋訪該地實景去直接體驗一番;在︿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一詩中,具有審美意味的田園牧歌變成了想像中的購買:
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
作家以大小巨細各種方式宣稱他們對一系列對象和活動的領屬權:我的田地,我的風格,我的詮釋,我的園林,我所鍾愛的情人。
像中唐這樣的時代應當有確切繋年的界定。這裡的論文所集中討論的大多是七九一年至八二五年間的作品,儘管也有先前和此後的作品收羅在內的。我們知道時代實際上是沒有清晰邊線的模糊中心,然而我們要劃定疆界,要排拒不受保護的空間這樣一種地緣習性,本能性地轉化爲我們爲歷史繪製的地緣圖。要講述好一個歷史「故事」,我們至少需要一個開端。
任何有關中唐的描述都追溯到韓愈這位講故事的能手,他的文學和文化史敍述造就了所有後來的敍述。韓愈最著名的文化史敍述集中在韓愈自己身上,作爲儒學復興運動的前鋒,他的致力於道德的文章,即「古文」,旨在成爲承擔儒學價值復興的載體。爲了在一個關於「開端」的敍事裡給韓愈的敍述定位,就讓我們把中唐確定爲從七九一|七九二年開始,在此期間韓愈、孟郊、李觀及其他一些書生匯聚在長安,趕赴進士考試。韓愈和李觀七九二年進士及第;另外兩位重要的中唐作家,柳宗元和劉禹錫於翌年及第。
如若我們將此視作中唐的「開端」的話,這並非出於對韓愈的權威性的過分尊重,而是鑑於他對於一個重要文化時刻的卓絕的策劃最終成爲促成變革的強勁的原動力。我說「最終」是因爲,即便韓愈有再大的雄心,他也無從知道他自己會是一個叫作什麽「中唐」的開端,或這一事件意味著什麽。開端只有在事後的反省當中才會呈現出它的全部意義;你首先必須知道所開始的究竟是什麽。儘管年齡差異懸殊||孟郊生於七五一年,李賀生於七九○年||然而此後三十五年文人社團的形成,構成了非常獨特的一代,這在此前三十五年的作家群中是看不到的。
中唐文學所顯示的深刻變化和韓愈對歷史延續性的重大揚棄同時發生:韓愈聲稱他自己和他那個時代是華夏文化的轉捩點,跨越上千年直接賡續自孟子以降便已廢弛的儒學傳統。不管這一聲稱在儒學史上有多麽重要,這樣一種自封的與往昔的關係在形式上體現了與衆多傳統的新關係。對屬於變化創新的一代人的自覺意識,帶來了各式各樣的新變和新興趣,已不是振興儒學文化的初衷所能夠包羅的了。
在七世紀九十年代初會集長安的年輕人,表達了緊迫感和危機感,主張必須做出一番事業來振興文學,並通過振興文學來復興文化價值。這些書生慷慨地讚頌彼此的作品,並深信他們能爲千瘡百孔的蒼茫大地找到良方。韓愈、孟郊及李觀的復古主題和道德緊迫感並不代表整個中唐;事實上他們只是複雜整體的一小部分。他們的意義似乎正在於打造一代新人、宣告變革和劃分歷史時代這一行爲本身。
許多人試圖說明是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獨特性導致了這些作家的緊迫意識。這樣一個因果律論點的問題是,唐代還有遠比這更糟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卻沒有激發起作家同樣的迫切感。無論是武則天的改朝換代,她死後王朝的腐化,安祿山叛亂的浩劫,還是自此後一個半世紀的朝廷的風雨飄搖,都未能激發起作家這樣的危機感(只有少數例外,杜甫是其中之一)。我們可以說韓愈及其朋伴感受到了當時的緊迫性,然而這並沒有告訴我們爲什麽他們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走到了一起。
比較明智的做法是給出歷史背景而不是因果解釋。德宗臨朝的初期(七八○|八○四)似乎別有一番幻滅感。這一朝起初在平叛後的廢墟上顯露出重振中央政府權威的生機,這線生機很快隨著德宗於七八三年在節度使手中遭受的羞辱而宣告破滅。德宗的雄心受到打擊,他成了一個沒有什麽吸引力的帝王,而道士李密及其後任竇申的內閣,對於解決朝廷的財政和政治危機一籌莫展。七九二年,著名的政治家陸贄出任宰相,似乎暫時又有了一線轉機。
古代中國不乏政治和經濟上的現實主義者,然而操縱歷史敍述的史官向來對他們的著作不感興趣。傳統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唐代,傾向於將政治、社會和經濟危機視作文化危機的症候,而文化危機通常被認爲是語言和文章的危機。雖說這並非德宗朝所絕無僅有的,在那段期間確實存在著帝王話語權威的貶值;比方說,帝王話語巧妙地被陸贄操縱使用,通過斡旋使王朝在七八三年得以苟延殘喘。在皇家足以憑恃的權力貨幣(軍隊和現金)匱乏時,陸贄便揮霍起帝國象徵系統的貨幣來;他出賣頭銜及可以說是王朝的前途||薪水及特權,而這些本來只能是通過王朝的安定來實現。對於那些恪守孔子「正名」古訓的人來說,這段時期簡直就是夢魘,到處靠鬻售空頭銜虛爵位來安撫豪強勢力,並在要挾之下默許地方官吏的任命世襲化。我們要記住貶值的權力通貨這一僵死的隱喻:當時産生了語言的通貨膨脹。儒家藉以治國平天下的「言文」變成了空文。
中唐的嬗變是在感受到語言和文章危機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對於這一危機的回應各式各樣卻彼此相關,由一些在當時反覆出現的、在下面論文中將要討論的話題貫串起來。也許關於文明史進程中這樣一些時刻,我們所能說的最多是「什麽事情發生過了」。歷史事件總是要比我們所能敍說的要浩瀚廣袤得多;然而有限的敍述也是我們貼近這更紛繁複雜的現象的唯一可行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