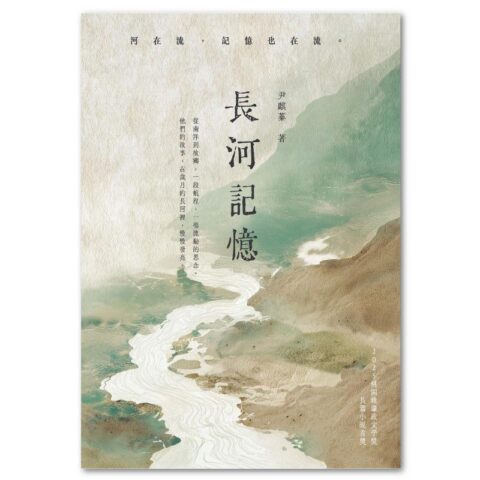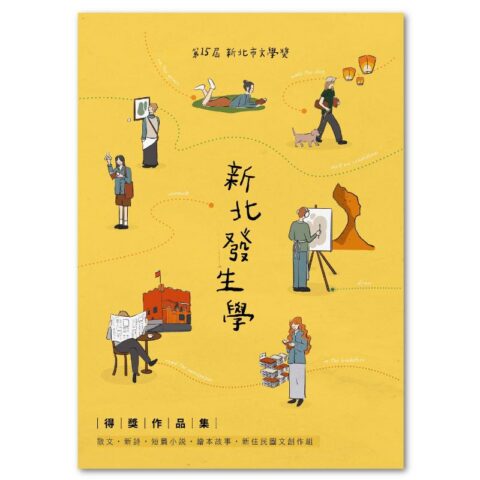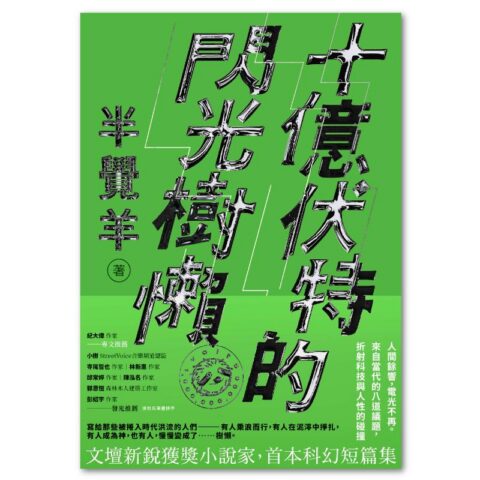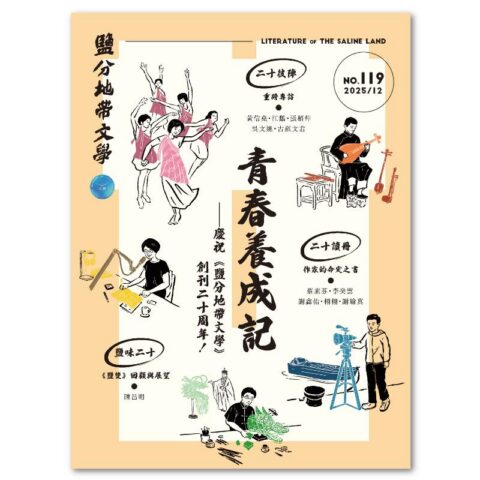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出版日期:2011-01-19
作者:董啟章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632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7445
系列:董啟章作品集
已售完
對董啟章而言:
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這是他到現時為止,所能抱有的最大的寫下去的理由。
我不想說寫作是一條孤單的道路。它是,也不是。
它是,因為就寫作的本質而言,
過程中只得作者自己一人面對,結果也只得一人負責。
它不是,因為無論環境條件如何惡劣,
我們身邊還存在一個寫作共同體,一群理念和實踐的同路人。
再者,寫作絕對不是一個人的事。
寫作必然在世界中發生,在世界中進行,在世界中結果,在世界中重生。
寫作為世界所塑造,但寫作也反過來塑造世界。
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紅樓夢獎決審團獎、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得主 董啟章
從 安卓珍尼 到 雙身 到 天工開物 到 學習年代
20年有成,他堅持走自己的路,在平凡中寫出最不平凡的故事。
這是當代世界華文文學重要的發聲
在學習年代,與同代人對談,論寫作、論行動
致同代人,致後新人,我們是為世界而寫作的
寫出我們這一代!
出道近20年創作思考之集大成
看香港當代重要小說家董啟章如何談文學、論創作、說藝文、品大師
甚至通過文字的力量為弱勢者發聲,同時思考言說和行動、文學與世界的關係
打造華文世界「如何文學,怎樣寫作」的典範
在香港當代重要小說家董啟章的召集下,當代世界文學、文藝、文化創作等各路人馬齊聚一堂。累積豐富的小說創作經驗和舞台戲劇表演的董啟章,以不同於一般文評家的跨領域角度自剖寫作心得,點評各種文學概念和形式術語,與同代的知識分子、文藝創作者、愛好者、讀者、出版人隔空對話,追溯文學創作的本質、文學內蘊的歷史進程,一路談到當代的薩拉馬戈、村上春樹、黎紫書……董啟章精闢的個人見解,反映了新一代創作人的文藝觀念。全書文采飛揚、思路通達,展卷之間,有如親臨其身,親聽其聲,令讀者嘆服。
董啟章的小說素以結構巧妙著稱,每一出手都是重量級巨作,看董啟章如何親述自己的創作過程以及概念形成的每個關鍵,無論是董啟章迷、文學愛好者、研究者,還是有意投入寫作的人,都絕對不能錯過!
本書第一部分「同代人」中的短文,寫於1997年3月至12月,刊於《明報》世紀版專欄「七日心情」的雜論。第二部分「致同代人」是於《自由時報》發表的隔週專欄,時間是2005年5月至2006年11月。第三部分「學習年代」是在寫作長篇小說《學習年代》期間的片段反思,從2009年5月至2010年3月,分6期刊載於文學雜誌《字花》。第四部分「論寫作」,大體上總結了董啟章到目前為止對文學和寫作的看法。第五部分「論行動」是環繞著「行動」的觀念、因為時勢的需要而寫成的文章,幫助欠缺公共渠道的弱勢者發聲,同時思考言說和行動、文學與世界的關係。第六部分「對談」,除了是指狹義的對談形式,也指向文學的對話特質。第七部分「序言」,是董啟章近年給幾位年輕香港作家的作品集所寫的評介文章。最後一部分「自序」,收入的是幾篇較能代表董啟章不同時期的寫作觀念的自序。
作者:董啟章
1967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1994年以〈安卓珍尼〉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同時以〈少年神農〉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1995年以《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1997年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2005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出版後,榮獲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誠品好讀雜誌年度之最/最佳封面設計、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2006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榮獲第一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審團獎。2008年再以《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獲第二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2009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發展獎2007/2008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文學藝術)。2010年《學習年代》榮獲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2011年《學習年代》榮獲「第四屆香港書獎」。2011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簡體版)榮獲第一屆惠生 施耐庵文學獎。2014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2017年《心》榮獲「第十屆香港書獎」。2018年《神》榮獲「第十一屆香港書獎」。2019年以《愛妻》獲2019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
著有《安卓珍尼: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紀念冊》、《小冬校園》、《家課冊》、《說書人》、《講話文章:訪問、閱讀十位香港作家》、《講話文章II:香港青年作家訪談與評介》、《同代人》、《貝貝的文字冒險》、《練習簿》、《第一千零二夜》、《體育時期》、《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對角藝術》、《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學習年代》、《致同代人》、《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博物誌》、《美德》、《名字的玫瑰: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I》、《衣魚簡史: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II》、《董啟章卷》、《心》、《神》、《愛妻》、《命子》等。
前言/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一、同代人
給同代人(序)
文類與秩序
文類與書寫形式
「文類小說」的可能性
人類的家畜化
人類中心的動物書寫
殘障文學‧文學化的殘障
「得獎文學」的測試作用
傳媒觀察與觀察「傳媒」
詞典是誰的工具?
工具‧技術‧意識
多種歷史/histories
歷史的物質製作
古物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如何用古物製造歷史?
延續性史觀的偏差
香港史的斷裂性
衝突與共融
香港神話的雙向論述
為鏡頭加上嘴巴
香港製造
製造香港
心靈是由什麼材料做成的?(上)
心靈是由什麼材料做成的?(下)
EQ的偽心理修辭學
「文化現場」在哪裡?
謊言的真理
同其異
異其同
「紀念」的價值
設計的發現與期盼
書是不是商品?
圖書館與文化空間
圖書館賣的是什麼菜?
假「私」濟「公」
「生活」的迷思
「生活」在何方?
成己達人
獨善與兼濟
文學的邊界
「嚴肅」與「通俗」的區分
殿堂在他方
文學千年
文學歧路
文學書寫
造作的藝術
極端的藝術
節制的藝術
書的拯救
評論之罪(兼談博物館)
評論的欲望(兼談欲望肚臍眼)
拯救還是幫助‧九七年‧玫瑰念珠
附錄:想像之版圖──寫在九七之前、《地圖集》之後
二、致同代人
首先讓我們承認,我們都是獨裁者
分別只是,大獨白和小獨白
真對話和假對話
前衛就等於反權威嗎?
不是一句回歸現實就可以
當戰鬥已經變成虛無
開放的遊戲與封閉的遊戲
寫實主義如何失喪真實
想像力就是同情的同義詞
理念和情感的二分法
理智與情感的共融,還是參差對位?
除非你比通俗走得更通俗
分別就只是文學和非文學
在無邊宇宙裡的招呼
我們還可以做新人嗎?
「知識人」的夢與實踐
小說家與小說寫作者
虛度的咖啡時光
要錢的嗎?這些東西!
你知道我是誰嗎?知道!當然知道!
瘋人船上的同行者
用左手學寫字的前輩
在語言的國度裡逃亡
在藝術形式之間逃亡
生活的質與微小的創造
「字之花」開得還要再野一點
你們每一個也是獨特的
站在門檻上的永恆發問
彼此之間的同在感
怪物化的自畫像
在寫作太少也太多的時代
作為生活演出的寫作
在自己的城市被離棄
在劇場裡尋找人生
只要你還未曾失去熱情
在作家和父親的身分之間
兒子絕不是筆下的人物
眾數的我跟眾數的你的傾訴
苦行與美好生活
三、學習年代
比整個宇宙還要大一點點
我是單,我是雙
我是我,我不是我
物種源始‧人類承傳
世界‧無世界
比太遲更遲的重新開始
四、論寫作
私語寫作
新櫃桶底主義──一本書的完成
一本書的完成‧一個人的完成
內向的擴散模式──個人的文學與世界的文學
在小說和音樂之間
劇本的未完成性
青年作為方法
文學副刊的天方夜譚
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文學是所有人的事
文學是要「館」的!──創設香港文學館的想像
空中樓閣,在地文學──想像香港文學館
理想的香港文學館──香港人的故事館
九問九答西九香港文學館
要「館」不要「管」──再問再答香港文學館
香港文學@愛荷華
吹冷又吹暖的嘴巴
跟死神開玩笑的薩拉馬戈──一個小說家的善終方式
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
飢餓、斷食與藝術
最後之後的新飢餓藝術家
還文學一個位置,還藝術一個真貌──香港文學館與西九概念
末日教主村上春樹──作為空氣蛹的《1Q84》
只有這個世界可能還不夠──從1Q84逃出來之後
為什麼要寫長篇小說?──答黎紫書《告別的年代》
五、論行動
當一個女子站在推土機前面──給廈門街甘霍麗貞女士的信
從紀錄到創作──《黃幡翻飛處》如何構造利東街
為了確認那不再可能實現的美麗圖景──利東街居民的規畫方案上訴
保留與開展──捍衛天星行動之雙重意義
「以人為本」的「人」字何解?
一個好人馮炳德
我們的唐吉訶德──黃乃忠
作為「行動」的八九學生抗爭
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
《清明上河圖》的反諷──民間社會如何被偷龍轉鳳?
六、對談
對「真實」的永恆追尋與創造整理:鄒文律
跨界閱讀董啟章許維賢訪問及整理
我們能不能為未來懺悔?駘蕩誌整理
社會議題與創作──陳炳釗與董啟章對談潘詩韻筆錄/整理
小說是建構世界的一種方法祝雅妍整理
七、序言
不妨偷聽的私人密談
「自然懼怕真空」──寫作的虛無和充實
回家的路
失蹤的孤草‧失蹤的陳志華
寫也難,不寫也難
愛意要是沒迴響,世界與我又何干?
日落星提,殘紅孕綠──一代青年藝術家自畫像
在變與不變中建構存在畛域──俗物與圖鑑的互證
八、自序
模擬自己
作家的起步點
類之想像
幸災樂禍──《雙身》的性別變向
作為小說家,我……
附錄/董啟章創作年表(1992─)
從天工到開物── 一座城市的建成(節錄)
從考古學到語源學
城市盛衰的循環觀深深地影響著我的寫作。寫於一九九五年的短篇〈永盛街興衰史〉也許就是一次夢華錄式的嘗試。跟宋朝城市雜記不同的是,我們已經很難再單純地相信事實的紀錄能夠保存真實,以及史料的閱讀能夠還原過去。當中總有一種SimCity式的虛擬性作祟,讓我們忍不住用想像的方法對待歷史。而在真實不斷地被虛構的後世,歷史已經變得很可疑。歷史真相的種種缺漏或不能消解的矛盾,讓當代的夢華錄更像一場噩夢。追本溯源變成一個不得不進行但又不可能實現的任務,最後唯一肯定的卻只有一條街(以至一個城市)的逝滅。所謂「尋根」只是一場往自我的內部挖掘的遊戲,而揭示出來的就只有自身的欲望。由於「不得已而又不可能」的雙重困境,到了《地圖集》(一九九七)、《V城繁勝錄》(一九九八)和《The Catalog》(《V城夢華錄》)(一九九九),城市的歷史探源便被開宗明義地納入「想像的考古學」的裝置裡了。
「想像的考古學」的虛擬性不單在它的考古對象V城,更加在於它的考古者角度設定。那是一個(或多個)存在於不特定的未來時空中的不知名敘述者的觀點。由於時空的挪移和置換,從寫作當下的立場來說,這三部小說便成為了悖論式的「對現在的考古」了。而三者中,只有《地圖集》延續了〈永盛街興衰史〉的(不得已而又不可能的)歷史溯源,其餘兩者則只能成為繁盛的遺物和毀滅的見證了。「夢華」的本義就是逝去,而SimCity的終極意象就是廢墟。如此這般的一個永遠只能回望過去的頹垣敗瓦的考古學者,不就是班雅明筆下的背向未來面向廢墟的歷史天使嗎?問題是,對考古學者來說,廢墟就是樂園。這三本小說建構的都是紙上的廢墟,文字的廢墟,符號的廢墟,由是散發著虛擬的氣息。每一個面向這些廢墟的讀者,也自動跟作者一樣,成為目睹災難而束手無策的天使。也許災難並不單純見諸城市的衰落,而是關於知識、文學、語言的崩壞和失傳。短篇〈衣魚簡史〉(二○○一)似乎就是這系列「想像的考古學」的虛無總結──被窒礙的欲望、從後面進入而無法完成的性交、荒廢的圖書館、被蟲洞穿透的紙頁、以建築物或者墓碑的姿態沉入海底的滿架的書本。
很難否定這種廢墟意識和末日詛咒跟九七的關係,但也許它並不完全是個政治問題,而同時是個文學問題。又或者,在政治和文學兩端,危機更為迫在眉睫的是文學。當然文學問題又不是純文學的問題,而同時是政治問題。廣義來說,是人為社會的建造和維繫,以及文學如何參與其中的問題。狹義來說,是九七回歸對香港文學造成的身分認同的衝擊。在這個時代的轉折或者斷裂上,「想像的考古學」有其適切性甚至是必要性,但卻未必能成為過渡的橋梁,或者面向未來的基礎。「想像的考古學」建基於「終結」,而我們同時需要關於「開始」或「起源」的探究。這樣的探究有助於我們發現「新生」的可能性。「想像的考古學」在這方面無能為力,只能陷入先前所說的「不得已而又不可能」的困局裡。我們需要由「考古學」到「語源學」的轉向,尋找意義的起點和流變,在歷史建築不斷倒塌的現場,通過文學予以不斷重建。
從自然史到文明史
自然史對文學具有雙重意義。其一是作為意義的追本溯源和系譜承傳的借鑑。其二是人之為人的定義,以及人為世界的根源、起點和邊界的探索。信奉大一統理論的當代生物學家一致認為,人類的社會行為和文化習俗(包括宗教)也屬於生物學的研究範疇,也即是都服從於生物學的演化法則。在決定個人構造和行為的基因(genes)之外,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創造出memes(文化基因)這個詞,來解釋人類社會文化模式的演化。換句話說,人類社會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類文明史只屬自然史的一個分支,兩者在本質上沒有分別。我更信服的卻是赫胥黎對於自然進程和人為進程的經典區分。赫胥黎在發表於一八九四年的鴻文《演化論與道德倫理》裡指出,人類雖然產生自生物演化,但人類組成的社會卻自成一體,其運行法則跟自然演化截然相反。赫胥黎以「園藝進程」作為人為世界的比喻,說明人類社會為了確保個體的生存和整體的穩定,必須遏止「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鬥爭,採取互相合作和保護弱者的措施,並且建立公平和公義的法規。天地不仁,自然界無善惡可言,唯獨人類社會講究道德倫理。自然界的法則也因此並不適用於人為世界。這很明顯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粗暴挪用演化論所做的撥亂反正的一擊。從「天工」到「開物」,兩者雖然有所聯繫,但卻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有趣的是,達爾文的忠實追隨者、演化論的勇猛守護者赫胥黎,相信的卻是一套循環時間觀。赫胥黎認為天演的宇宙進程無始無終,而當中的人類文明很可能只是一瞬。就正如園丁必須時刻努力防止圍牆外的大自然入侵井井有條的花園,人類社會只要稍一鬆懈,文明就會在宇宙進程的巨大力量下崩潰,世界於是又回到蠻荒狀態。所謂盛衰有時,這本身不就是自然界的規律嗎?這跟十九世紀末備受崇尚的線性發展觀是如何地大相逕庭!不過,雖然循環往復,自然史和文明史始終是截然二分的。於是,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去界定兩者之間的邊界。文學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大創造物,本身就一直在刻畫著這條界線,探究著人之為人的根源,以區別於非人的事物。
香港文學作為城市文學,似乎一直缺少對自然的關注,或者是對自然的自覺性。這原本也無可厚非,因為在現代性的全面擴張下,城市幾乎等同世界,而農村和鄉郊已經在現代想像中消失,更不要說未開發的原生地區。我們生活在一個以SimCity為世界模式的時代。以城市為世界的香港文學的一個特例是吳煦斌。她是非常罕有地看到城市的邊界、並且以寫作為冒險探進邊界以外的香港作家。可是,吳煦斌尊敬自然和回歸自然的立場,以及對城市文明一面倒的批判,卻似乎是反過來以人類的價值築構出一個過於富有意義和善意的自然了。我主張發掘自然史的文學意義,並不是要恢復或提倡浪漫主義或環保主義的那種自然書寫,而是嘗試把城市模式的文明史往上推移,直至它的源頭或者邊界,讓人類在當代世界中的生存條件外露出來。在這樣的條件考察中,我們能了解到自己的局限和可能。換句話說,城市作為最巨型的人為築構物,它所賴以存在的根基是什麼?而在它高速甚至是過度發展的情況下,它所面臨的危機又是什麼?這樣的危機跟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什麼關係?而面對著這樣的危機,人又應該對自身的(城市模式的)社會做出怎樣的調整,而非單純地相信「回歸自然」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普遍而基礎層次的探討,又必然結合香港的獨特歷史時空,以達至本土與世界互相映照。這就是為什麼我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開始的三部曲並不叫做「香港三部曲」而叫做「自然史三部曲」的其中一個原因。
從達爾文到阿倫特
達爾文的《物種源始》和霍金的《時間簡史》也是關於起源的書。兩者的差別不在於時間的跨度、證據的多寡或者進程的先後。後者所探究的宇宙起源看似比物種起源更為根本,但在人類事務的層面卻不及前者迫切和震撼。宇宙起源的問題雖然關乎神或精神世界的存在與否,以及人在宇宙中的角色,但卻跟人類世界的構成和運行關係不大。物種起源的問題卻直接涉及人類社會所遵從的法則,究竟是歷史文化的產物,還是人類的生物本性所決定。這對於人類事務的理解和實踐有根本性的影響。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種族優劣論,都是演化論涉入人類事務的明顯例子。在科學上我相信演化論的合理性,我懷疑的只是以演化論解釋人類文化的做法。這方面我認同赫胥黎的主張,也即是把宇宙進程和人為進程歸因於兩套性質截然不同的法則。
阿倫特對人類政治史的考察,同樣採用了追本溯源的方法。阿倫特賦予「起源」或「開始」或「誕生」特殊的意義,認為它是人類事務之所以能產生改變甚或是製造「奇蹟」的根基。而人類行動的本質,就是製造新的可能性。阿倫特徹底懷疑生物學上的「人類本性」(human nature)的存在,也因此堅決反對任何物質決定論。對她來說,人類不是一個物種,又或者,當我們處理人類事務的時候,我們不能採用「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角度,因為物種代表的是一種抽象的、非人的、先設的特質的總合。然而,人之為人,是因為每一個人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這些獨立的個體以眾數對等的方式聯繫在一起,組成了一個人為的共同世界。這就是阿倫特思想中「政治」的本義。阿倫特對於人類活動的三分法──勞動(labor)、製造(work)和行動(action)──很微妙地跟赫胥黎關於自然進程、人為進程和社會進程的三分法相似。當中跟文學有關係的,是第二範疇,也即是物的製造。
文學作為製造物(work/fabrication)當然不是說文學就像一個箱子一樣,用來保存一些東西。但文學又的確有點像一個箱子,它的確發揮了保存的作用。又或者,文學像一件工具,可以用來製作別的事物。又或者,文學更像一個工場,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工具,用來打造各種各樣的事物。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我把這稱為「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不過,我並不是說文學只有工具性,例如作為觀念或意識形態的宣傳機器。不。文學作為一種工具,它的製作物就是文學世界本身。它既是手法(means)也是目的(end)。文化層面的創作物跟物質層面的製造物,在性質和功能上當然有所差別,但也有共通之處。兩者都是在變幻易逝、毫無意義的自然進程中,為人提供恆常持久的、具意義的存在居所。它是人類的共同世界的基礎。有了這樣的聯繫,世界才得以形成。所謂「世界」,從根本意義上說,就是人為的,或者是從人的角度體驗的。石頭沒有世界,動物也沒有世界。人類所建造的世界,一種具有意義的存在,是自然進程當中所沒有的。這是人與非人的差別,也是人之為人的根本。這個世界既建基於物質製造物,從用具到建築到城市,也同時建基於文化創作物,諸如文學、音樂、繪畫等藝術形式。前者賦予這個世界穩定持久的形態,後者賦予這個世界可知可感的意義。是以文學乃創造世界、維繫世界和改變世界的方法之一種。
在文學之中,小說是最具規模或最接近世界模式的建築物。所謂小說世界,是一個介乎於真實與虛幻之間的想像世界、可能世界。小說跟真實世界的關係,不是單純的反映或模仿,也包含逆反、改造和創新,是對真實世界的回應,也因此能成為真實世界的參照。當我們把這個小說世界設定為香港,寫小說就等於建築一座城市。我的意思不是「以香港這個城市作為小說題材」,而是「以小說來建造香港這個城市」。而這個以小說建築起來的城市,並不只是一堆建築或景觀的集合,也不只是由一些事件串連起來的故事,而是一個由眾數的人所組成和分享的共同世界。是以自從《體育時期》(二○○三)開始,我就著意探索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感的問題。所謂共同感並不是一模一樣的思想和行為,也絕對不是什麼和諧社會,而是在縱使充滿差別甚至對立的情況下,人和人依然能站在共同的基礎上,擁有共同的關注,並就這些關注展開對話和互動。我發現長篇小說是特別適宜建構這樣的世界進程的形式。
小說建構離不開人物,這好像是無須多說的事情,但世界建構的關鍵其實就在於「人」和「物」的關係。雖然阿倫特不相信人類本性,反對運用自然規律來理解人為世界的事務,但我認為人無法完全擺脫自身的生物/物質條件限制。自然與人為、生物與文化、身體與思想並不是毫無關係的。就算前者不完全決定後者,而後者也不是前者的延伸,兩者還是處於互相作用的關係。我認為人類的生存鬥爭,很大程度發生於這兩者之間,而不單單發生於個體與個體,或者物種與物種之間。換句話說,它發生於每一個人的身心之間。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人物世界」的部分,構思了「人物」這種存在。「人物」在此一語雙關,一方面指小說或故事中的角色,從而探究人物及其作者的關係,或者寫作倫理的問題;另一方面指字面上的「人+物」的想像式存在,也即是人體和物件的結合。這其實就是現代人和器物的不可分割的依存關係的寫照──我們通過物(諸如種種科技產品)來定義自己、延伸自己,但也限制自己。同理,我們也通過物來促進或妨礙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城市作為一個龐大的「人物」集合體,自然成為以小說處理人類存活問題的當然場所;反過來說,小說也成為城市營造的理想形式。阿倫特給我更大的啟發,在於把小說實踐從「製造」的層面延伸到「行動」的層面。從《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到第二部曲《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的「溜冰場作為宇宙運行模式」、「圖書館作為時空交錯場域」和「神功戲作為社會抗爭方法」,以至於第三部曲《物種源始‧貝貝重生》的「劇場作為行動空間」和「虛擬世界作為政治領域」的探究,是從文學作為建築到文學作為行動的轉向。當然作為行動的文學並沒有脫離城市這個場所。相反,當下最迫切的行動正正在城市過度發展的情境下發生。與此同時,在最大化的、充滿壓迫性和排斥性的城市想像當中,一種極端的SimCity模式會否成為開放式政治參與的出路?換句話說,一個稱為「平行世界」的網路虛擬遊戲──「人為世界中的人為世界」或「第三自然」──能否成為新的政治實踐的空間?這些也是我在第三部曲裡要處理的問題。
史達林把文學家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樣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立意去建構人的靈魂,是一件極其可怕而且危險的事情。況且靈魂這回事是沒法建構的,它是絕對地內在也因而無從證實更遑論製作和操作的。跟個體內部的靈魂工程相反,文學家應該是「世界的建築師」。在文學這座建築裡,人的精神找到棲居之所。(當然這並非找到精神安慰的意思,文學不應成為安眠藥、止痛藥或鎮靜劑。相反文學往往會造成精神激盪,令人經歷痛苦和困惑,但在種種掙扎和衝擊之中,文學卻同時給我們搭建意義的房子,讓我們不致在虛無中流離失所。)當代文學往往以城市為世界建築的模式,香港文學尤其如是。而這樣的一座文學之城,必然要經歷無數次的拆毀與重建。種種人為災難的碎片堆積在面向過去的歷史天使的跟前,但畢竟文學不是歷史,文學的建築不會都化為廢墟,又或者在文學裡縱使存在廢墟,也依然是完整的、可棲居的廢墟。只要文學的建築能夠屹立不倒,天使也許就有半晌喘息的空間,回過頭去,看到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