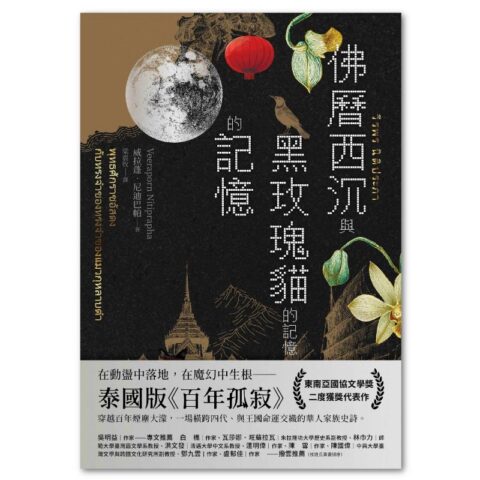燃盡的地圖(全新翻譯本)
原書名:燃えつきた地図
出版日期:2016-05-13
作者:安部公房
譯者:邱振瑞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20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7307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這是一場不存在的人相互尋找彼此的遊戲,
但始料未及的是,我竟然把自己也弄丟了……
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經典,安部公房小說,全新中譯本
若非猝逝,他必定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 佩爾・韋斯特伯格(Per Wästberg)
‧日本已故知名作家 大佛次郎、小說家 三島由紀夫 為之讚嘆驚豔
‧作家/著名翻譯家 邱振瑞 專文導讀
「他」行蹤不明、下屬自殺、委託人的弟弟遇害、「我」則成了他人的跟蹤目標……他們在玩捉迷藏嗎?
當「他」失蹤下落不明,妻子請求徵信社協尋。但徵信社人員手中的線索,僅有一個舊火柴盒和一張相片──假如這就是尋人地圖的指引方向,那麼空白之處也太多了。尋人過程中,徵信社發現委託人的弟弟屢屢出現在訪查地點,彷彿也正在尋找失蹤者,或是追蹤某件事物……
然而一場街頭幫派火併中,委託人之弟意外身亡,委託人與「弟弟」的真正關係才因此揭露:徵信社職員開始思索:「失蹤者」的離開或許有其苦衷。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其實也算是暫時的失蹤者吧,與真正的失聯者相較,對比也不過就是一輩子和幾小時的差別,為何社會自以為有權追蹤他人?出於自由意志出走之人該被抓回來嗎?而被拋棄者是否認為失蹤者沒有出走的權利……
徵信社職員驟然失去座標:如此存在的我,也等同不存在了吧。這竟成了一場不存在的人相互尋找彼此的遊戲……
隨著一次尋人行動開展,帶來更多謎團:當城市中的人際關係一一離散消失,便猶如在日曆上沒有的某日、在地圖上沒有的地點突然醒來,或是身為海盜在陌生的大海上揚帆,身為盜賊躲藏在無人的沙漠……所謂的「逃走」,其實必定是完成了某種意義──猶如一張看似完成的地圖,行進路線只有箇中人物才能體會。
作者:安部公房
日本知名小說家、劇作家。1924年出生於東京,幼時舉家搬遷至滿洲國的奉天(今中國東北瀋陽市),1940年進入東京成城高中就讀,該年被診斷出肺結核,休學返回奉天療養。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就讀,二次大戰末期一度偽造診斷書返回奉天,直到1946年底方被遣返回日本。1948年自醫學系畢業,但最終放棄實習。
少年時期喜讀愛倫‧坡、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亦曾受德國詩人里爾克吸引。思想上則逐漸傾向馬克思主義,曾加入日本共產黨,之後又被開除黨籍。
1951年以小說《牆壁──S‧卡爾瑪的犯行》獲得第25屆芥川獎,1962年以《沙丘之女》獲得讀賣文學獎,後者於1964年改編成電影,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獎,享譽國際。其作品往往著眼架空的背景與虛構的人物,著重人性的疏離與異化,呈現強烈的前衛色彩,近似卡夫卡等存在主義作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韋斯特伯格(Per Wastberg)在2012年受訪時曾提到:「若非猝逝,安部必定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距離得獎非常非常地近。」
除了小說創作,他也是位才華洋溢的劇作家。曾以劇作《幽靈在此》獲得1958年的岸田演劇獎,1967年以《朋友》一劇獲得谷崎潤一郎獎,1974年則以《綠色絲襪》獲得讀賣文學獎。此外,在《沙丘之女》、《別人的臉》、《燃盡的地圖》等作品改編電影時,亦親自擔綱撰寫劇本。
1992年年底,他在寫作時因腦溢血緊急送醫,於隔年1月22日病逝。
譯者:邱振瑞
日本現代文學翻譯家與作家,目前任教於文化大學中日筆譯班。譯著作品豐富,譯有三島由紀夫《太陽與鐵》、《不道德教育講座》(大牌);大澤在昌《暢銷作家全技巧》(野人),與山崎豐子、宮本輝、松本清張等名家小說。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商周)及《來信》(允晨)。
那高貴的異端/作家‧著名翻譯家 邱振瑞
安部公房(一九二四~一九九三)的小說向來以前衛、晦澀、深奧和抽象概念的構思著稱。在他的作品中,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幾乎是架空出來的,人物多半沒有具體姓名,乍看下情節有些怪誕突兀,當你鼓起勇氣試圖往下讀,他卻倏然在你面前撒落漫天的迷霧和沙塵,這似乎給他的讀者和研究者帶來困難。然而,對某些人而言,這種晦澀卻是不可思議的,又充滿奇妙的魅力,它可以激發研究和工作,亦可增加閱讀的趣味。雖然有些晦澀需要歷經艱苦努力才能揭示出來,但破譯出其精神特有的複雜性即是最大的回饋。從這個意義上說,為了充分探析安部公房的文學底蘊,或許有必要把他與同世代的作家三島由紀夫的生涯稍加對照,因為從他們迥然而異的文學風格,我們可以更理解二戰前後日本知識人的精神危機和內在生活。他們在小說呈現出來的愛憎與惶惑不安,都與那個翻天覆地的時代緊密相連著。
以世界文壇的知名度而言,在日本作家中,以三島由紀夫與安部公房的作品(《沙丘之女》、《別人的臉》、《燃盡的地圖》、《第四冰河時期》、《朋友》、《幽靈在此》,有俄語版、捷克語版、羅馬尼亞語版、丹麥語版、比利時語版、芬蘭語版、英語版、墨西哥語版、法語版、德語版、義大利語版、葡萄牙語版等)獲得最多國外讀者的閱讀。他們兩人都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二戰前,三島進入了學習院的初、高等科就讀,之後考上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安部的生活道路卻轉折得多,父親奔赴當時日本的殖民地「滿洲國」的奉天(今中國東北瀋陽市)當執業醫師,基於這個家庭因素,安部就讀該地的小、中學,高中時期才回到東京。是年冬天,他患了肺結核休學,一九四○年回到奉天的自家休養。一九四二年四月,他的病情已恢復過來,因此返回東京。一九四三年十月,他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這時日本可能戰敗的消息甚囂塵上,他出於某種莫名的情感召喚,偽造了「重度肺結核」的診斷書,以此病由返回奉天的家裡。一九四五年,日本和滿洲兩地爆發了嚴重的傷寒。翌年,蘇聯軍隊入侵了中國東北,並接管所有的醫院,其父親遵從命令製作傷寒的疫苗,不幸受到感染而過世。之後,來了國民黨政府,整個體制改弦易張,但旋即又被八路軍擊退,短短兩三個月內,政策和市容為之改變。這些無疑給安部造成巨大的衝擊。同樣地,三島在入伍前的體檢,由於軍醫的誤診,認為他疑似患有肺結核,得以免除兵役。同年十月,三島的妹妹美津子罹染傷寒死亡。簡單地說,這兩個同世代的作家,三島在「內地」接受傳統教育,安部在「外地」度過青少年時期,但是他們有個共同點:兩人都經歷過「日本帝國的崩解」與時代疾病的威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震盪。而在文學道路上,三島於日本傳統文學中大放異彩,安部則堅決地站在「異端」(反傳統)立場上,持續思索故鄉存在的定義和被荒漠化的靈魂。可以看出,在安部的生命裡,他自始至終直視「做為場所的悲哀」(Realms of Memory)的困境。順便一提,阿爾及利亞出身的法國作家卡謬的《異鄉人》、前總統李登輝在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的篇末對談,皆為絕佳的例證。換言之,滿洲這個空間上的場域,既是真切的實在,同時還包含場所、位置和身分的認同,卻由於政權的更替,又把它丟入流變的漩渦中,致使日本移民者不知何去何從。而這個二律背反的問題,又成為安部的精神原鄉,從文學上的啟蒙,到小說的場景描繪,都圍繞著滿洲的經驗。
正如他在創作經驗談中提及的:「……滿洲的冬天嚴寒,儘管到了午休時間,同學們仍很少到教室外面走動。我讀完數天前剛買的《愛倫.坡短篇小說集》,把故事內容口述給同學聽,他們大為讚賞。坦白說,我不但擅自加料,還編造了許多情節,而這卻意外地催生出我向壁虛構的才能……。」此外,他在《道路盡頭的路標》描寫的就是「我」與「故鄉」的關係的反思。他這樣寫道:「我的確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在忍耐周遭的圍逼,又像物體般存在著。可是故鄉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之間到底有多大的距離呢?」這個投給讀者的詰問,其背景即是他深切生活過的滿洲。而出現在《道路盡頭的路標》的「我」,以及長篇小說《野獸們尋找故鄉》中,通曉各國語言的中國籍高姓通訊口譯員(當時標榜五族共和),同樣被關入了土牢,這正道出日本戰敗、滿洲國解體後的混亂局面:日本移民不但沒有國籍,也無法通過立法保障自身財產與安全,連生活在滿洲的中國人也不例外。或許如同安部自述的那樣:「從本質上來說,我是個沒有故鄉的人,或許正是因為這樣,使得我本能地憎惡故鄉的存在,總是不敢輕易對它做出定義。」的確,當滿洲國皇帝退位的同時,整個滿洲就土崩瓦解了。安部居住的城鎮每次遇到沙塵暴的侵襲,便陷入一片灰濛境地。他的隨筆集《沙漠般的思想》,經常提及「荒涼的土地」和「沙漠」,感嘆與日本的田園風景無緣,正是源於這樣的地理環境。他似乎在展示一種基本立場:所有界限都是人劃定出來的。縱然是在半沙漠和沒有界線的地方,終究只是人在自我設限而已。
隨著戰局的結束,安部這個清醒的漫遊者,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遣返回祖國日本。在那之後的三年間,他發表了幾部小說。此外,他久別的祖國和自己的文學生涯以及文壇亦出現重大的變化:日本國憲法正式實施。東京大審判做出了判決。椎名麟三《深夜的酒宴》、太宰治《斜陽》、田村泰次郎《肉體之門》、原民喜《夏之花》、大岡昇平《俘虜記》、島尾敏雄《在島嶼盡頭》、木下順二《夕鶴》等,都是這個時期的文學成果。翌年二月,安部在《近代文學》雜誌上,發表了小說《牆壁──S.卡爾瑪的犯行》,他就是以此作品獲頒第二十五屆芥川文學獎。同年六月,他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十一月,在《新潮》文學月刊刊載中篇小說《闖入者》。從其文學思想來看,這時期確實較沒有出現早期以滿洲的沙漠為背景的描繪,而視域慢慢朝都市的「被封閉的空間」移動,這看似修辭學上的變化,其實仍是這種思想的延續。畢竟,這個曾經給予多達二十餘萬日本僑民希望又使之幻滅的城市──滿洲經驗,早已長驅直入到他的靈魂深處了。而《箱裡的男子》和《密會》以及《櫻花號方舟》所設置的場所與情節,幾乎全是在被封閉在某個空間裡,任憑故事的主角如何尋求脫困,最終只能回到茫然的原點。
沿著這個思想,我們就可更明白,在《沙丘之女》中,那名為了採集日本虎甲標本的學校教師,不慎跌陷在沙丘的圍困中,歷經多次的挫敗,終於逃出了生天,但最後他卻出於某種入魅(enchanted)的回音,選擇了留在把他重重圍困的沙丘,像被封堵出路那樣,繼續日常的生活。然而,這裡有個弔詭的插曲,就在安部發表這部作品的同時,他被日本共產黨開除了黨籍。理由是他與所屬該黨的「新日本文學會」的作家意見對立,尤其在小說《飢餓同盟》裡,顯露個人主義的傾向,並語帶嘲諷似地要與所屬的共同體訣別。事實上,安部的筆尖批判的不只共同體與個人衝突的問題,還包括了日本的政治體制。這部看似帶有推理色彩的《沙丘之女》,又多了些社會批判與政治寓意的縱深,經過這個轉折,我們或許可更真切看到其桀驁不馴的思想的姿態了。如果說,這些充滿前衛性的作品和劇本反映出安部的思想光芒,那麼《燃盡的地圖》就是其集大成之作了。在這部作品的場景中,同樣出現廣漠無垠的地理空間,同樣使人難以辨認方向,但其宏旨更具普遍性,他呈現的場域已超出滿洲國和日本國界,進而深刻指出人類在現代化社會裡的共同困境。當我們生活在自己不能成為自己的指路明燈的地方,你依靠的地圖又被燒毀,大概沒有比這惶惑不安更沉重的吧?現在,我們有機會走進安部的小說世界,只要你有足夠的勇氣和慧識,必定能找到輕安妙樂的出路。
打從水銀燈那裡下坡約莫十步的地方,在草坪旁有個下水道孔蓋。那天,「他」避開爭先恐後趕路上班的人群,略有所思在人行道邊上慢慢地踱著……假設附近有人看見「他」,那就是「他」留給世間的最後身影了。但話說回來,就算事實如此,這究竟又有多少意義呢?
「既然公共汽車的班次不定,而且又是下坡路,何不腦筋靈活點,一開始就搭地鐵去,豈不來得省事嗎?何況那天早上,他還跟某人約在S車站碰面,如果是直接去公司,倒是坐公共汽車方便……」
「不過,他卻失約不見了。」
「所謂的失約意味存心撂下不管呢。」
「事情不是這樣。我換個說法。哎,我該怎麼說呢……」
「三天以前,他還是一直開車上下班的嗎?」
「是啊。聽說是車子出了問題,送廠維修了。」
「現在這輛車呢?」
「嗯……情況到底如何呢……」她顯得有些驚愕,睜大眼睛,露出純真的眼神,「我弟弟應該知道情況吧……」
「又提到令弟啦。可是,妳說令弟未必想跟我碰面呀。」
「見不見面都無所謂。我弟弟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就是他叫我找您來幫忙的。請您要相信他。這是我弟弟的為人……」說到這裡,她的聲音忽然高昂起來,「哎呀,他並沒有失約……這是千真萬確的,我有證據……我可想起來啦。那天早上,他出門後又馬上折回,我猜那必定是很重要的事。他下了樓梯,還不到一分鐘……取了迴紋針……他意識到要在S車站交給對方的那份資料,應該事先用迴紋針別起來……」
「這件事您已經向我說過了。」
「哎呀,是嗎?」她嘴唇微張,牙齒淺露,但眼睛仍掩不住驚恐惶惑的神色。「我經常自言自語……對不起,我竟然有這種毛病呢,如果是自言自語,說多少遍也不會有人罵我,我真像個傻瓜似的,說什麼迴紋針……我時常這樣想……而且,他回來取迴紋針豈不證明他還想去赴約嗎?大家都這樣問起,所以不知不覺間,我就染上絮絮叨叨的習慣了……」
我緩緩走過去,停下腳步,轉過身子,再走回來。荒涼破敗的柏油路人行道……我以平常的步伐,從三號樓角往前走了三十二步左右,抬頭望去,全是些不會眨眼的假眼般的水銀燈,它們如咒語呼喚著永遠不會到來的節日遊行隊伍;所有從長方形窗戶映射出的淡淡燈光,恰如對這類節日意興闌珊的背影。風彷彿濕濡的抹布抽打臉頰,我豎起外套的領子,繼續往前走……
如果我相信她的願望抑或自言自語……真有此事的話,那麼在這短短的三十幾步裡,必然潛藏和埋伏著荒唐又令人束手無策的異常情況。這樣一來,他不僅失信無法前去赴約,也等同於背棄社會本身,最後踏上了別無退路的斷層……
「我理解您的意思。如果可以只憑想像的話,不妨多加設想一下。比如……請您別生氣啊。有人握有不利於您丈夫的把柄,進而脅迫他什麼的。例如,他以前的情人啦,或者跟這個舊情人生下的孩子啦……這是常有的事。有些人年輕時犯過大錯,死後不能上天堂,淪為鬼魂四處遊蕩,這可沒什麼稀奇的。現在又恰好是八月份,正是幽魂出來閒逛的好季節。當然,鬼魂不全然是女的。以前因盜領公款後來身敗名裂的他的同夥也很可能與此案有關。另外,比如前幾天剛從監獄放出的慣犯,因為您丈夫密告被當成勒索的慣犯而向他報復……您有沒有這方面的線索?當然囉,這也可能是不相識的人設下的圈套。這些年來,智慧型犯罪的手法愈來愈高超了呢。例如,他們偷偷用自己的名義為不相關的第三者投保巨額死亡意外險,然後再以假車禍撞死對方,這種傷天害理的手法似乎很流行呢。然而,像這種情況,如果沒有找到屍體或查明身分,他們一毛錢也拿不到。因此,您丈夫遭人暗算的可能不大。對啦,既然警方沒有通知您去辨認死者的身分,至少可以排除他是意外死亡或者其他的謀殺案。若是他殺的話,他可能早已被灌成水泥桶塊沉在海底了。不過,這樣一來,事情可就棘手了。他可能跟黑道幫派搭上了關係而惹來殺身之禍……好比參與走私集團或者印製偽鈔……」
她把第二杯啤酒約莫喝了大半後,沒再喝下去。她一動不動地盯著杯中逐個破滅的氣泡,看著啤酒的色澤漸漸變深。她是在思索呢?抑或在生氣?或者只是單純的茫然若失?她的下唇比上唇微微突出,如同還沒完全斷奶的嬰兒嘴唇。儘管她得稍微俯下臉孔,才能完全掩住上翹的鼻孔,但她的鼻子仍顯露出某些傲氣。
「不過,真正棘手的或許不是幫派組織,而是像微不足道隨手扔在地上的菸蒂般的對手。那種邪門的反常行為最可怕了。我給您講個真實案例。銀行職員原本都很循規蹈矩,其中有個分行經理特別安分守己。但就在他屆齡退休那天,跑去看脫衣舞表演,卻鬼使神差似地迷上某個脫衣舞孃。嚴格說來,那個舞孃沒什麼真本事,只是跟著其他舞孃徒具形式地一起跳罷了。可是那個退休的分行經理,對她咬指甲的動作為之著迷,一連三天,每天都去捧場,還寫信對她訴說情意。第四天,他便設法帶著舞孃外出用餐,看似打得火熱時,第五天事態卻急轉直下,舞孃在自己的房間逼著他一同殉情自殺,鬧得沸沸揚揚。您不認為人就如同刮鬍刀的刀片,愈是堅硬愈容易折斷嗎?」
她的表情依然沒有任何變化。杯中的啤酒泡沫消化了大半。從側面看起來,泡沫表面會使人聯想成從空中俯拍的熱帶叢林表層。她正在看著什麼?驀然,或許是光線映照的緣故,我看見她的下眼皮有個透明般的鼓泡,那是淚珠嗎?我有些慌張,因為我不是故意的啊……
「不過,在我看來,他回來取走迴紋針的事……正如您所說,或許這可以作為有力的證據。然而,他是否真的按照約定把資料送到S車站去,這又另當別論。當然囉,這要看那些資料的內容而定……」
「聽說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呢。」
她這冷不防的回答,如同皮球般輕快地彈回來,而且她說話的聲調與沉默的態度都沒有變化。
「這應該是公司的業務吧?」
「我覺得絕對不是重要大事。」
「我需要的是事實根據,不是您的自行推論。他是否去送資料給客戶,明天我可以到他公司查問。只是我想不透,您說沒有線索,這是主觀上的問題,我無能為力。不過,比如備忘錄啦、日記啦、客戶的名片啦、通訊錄啦,這類可當線索的東西,居然一件也沒留下來,這對於一個擅於整理資料的人來說,實在令人想不通,這未免不合常理啊。您始終想不出什麼線索來,並認為他是突然失蹤的,可是我覺得情況恰好相反。有道是:鳥去不留痕。我認為這才是真實情況。」
「可是,他回來找迴紋針的事又怎麼解釋呢?而且,我們的銀行存款也沒短少呢……」
「您別這麼固執嘛,恕我有話直說,難道您敢百分之百保證,他這樣做是故作姿態,目的是要您信以為真?我說得有道理吧。說不定他想偷偷向您說聲再見呢……」
「我不相信。我在找迴紋針時,他還用刷子擦著皮鞋,吹著怪里怪氣的口哨呢。」
「怪里怪氣的口哨?」
「好像是電視的廣告歌……」
「不行這樣啦!您找什麼理由蒙騙自己都隨您,但用這種說法,對我可不管用。」
「這麼說,又好像有點什麼相關的,說不定就在電話簿裡……」
說完,她才有些倉皇地轉向放著電話的屋角,彷彿咬拇指指甲般連忙把緊握的拳頭貼在自己的嘴唇上。她這個怪癖是藏不住的。從她那塗滿厚厚指甲油的指甲邊上的白色痕跡,正顯示出她向來就有這個惡習。她略帶歉意地微笑。
「應該還找得到備忘錄吧?」
「你這麼一說,我似乎有點印象。那個架子上的確有個黑漆的盒子,大概這麼大……把按鈕對準第一個大寫字母,輕輕一按,盒蓋就會應聲打開。」
「這盒子是跟您丈夫一齊失蹤的嗎?」
「不。假如被人拿走,那就是我弟弟拿的。他總不能什麼也不做,只教我枯等啊。而且,他查來查去,也沒查出有用的線索,就這樣擱置下來。況且,那盒子只要一直擺在那裡,我每次看到一定會坐立不安。我弟弟反對我做危險的事……」
「什麼危險的事?」
「他說,人生在世只要一張地圖就夠了。這是我弟弟的口頭禪。他常說這社會如同猛獸毒蟲出沒的森林和草叢那樣,只能沿著大家走過的安全無虞的路徑走……」
「這種說法好比洗手之前,先把肥皂消毒一番呢。」
「是啊,我弟弟就是這種性格。他每次來我家裡,總要花好久時間,又是洗手,又是漱口的折騰半天……」
「不管怎樣,我求求您,現在就請您打電話給他。」
女子的神情突然為之黯然。也許是她卸下彩妝,露出了肌膚本色。她用並排的雙手指頭,輕輕摩挲著桌面的邊布,然後悄聲站起來,繞到狹窄的椅子後面,用手指在檸檬色的布幕上捅出淺淺的凹窩。這與黑色很搭配的女子……那拒絕重力的腰身曲線……拿起話筒,也沒看電話簿就撥起號碼來。這個動作結束後,她揪住布幕的皺褶……細細的指頭彷彿沒有關節……她似乎像是出於某種習慣看到什麼就抓住什麼。莫非這是為了戒除咬指甲的習慣而養成的新習慣嗎?她輕輕搖晃那片布幕,像是帶著幾分醉意。話說回來,黑色和黃色原本就是「危險」的標誌……
「簡直是胡搞嘛!」她用嘶啞的聲音像是對眼裡的某人說,「總不能讓她習慣性地自言自語嘛,最好直接問她本人吧。我原本也不敢相信,他悠閒吹著口哨,但是馬上就………這令人害怕極了。噢,這怎麼回事,沒人接電話……是不在家嗎……」
「您打電話給誰啊?」
「後面那個……」
「是那個最後的目擊者嗎?算了吧,他一定不想接您的電話。而且,我又不是請您打電話給他。」
她怔了一下,用像不慎抓住毛毛蟲似的動作,擱下話筒,
「那麼我要打給誰呢?」
「當然是打給您弟弟啊!」
「這恐怕不行呀。因為……」
「反正我非要地圖不可,哪怕十張二十張都行。您只給我一張相片和舊火柴盒,叫我到哪裡找人呀。我們幹的是出生入死的危險行業。我出示給您的委託書上,寫得非常明白,您有義務提供各種資料。我覺得這種要求並不過分。」
「我弟弟知道情況。他說,任何人都派不上用場,他要自行調查……」
「他倒很有自信呢。既然這樣,您為什麼委託我調查呢?」
「因為我已經等不及了。」
沒錯,等待是焦灼痛苦的。然而,我還在繼續等待。我信步而行,停下來,轉過身。又再起步……偶爾有公共汽車到站,稀稀落落的腳步聲,但就是看不到人影,不僅看不見任何人影,連斷層、地裂、魔圈、祕密地道的入口,類似這些東西的痕跡絲毫也辨別不出來。
尤其在清晨七點半,那是所有時刻中最令人情緒低落的時候,人們無論遇到什麼特殊狀況都不予搭理的如蒸餾水般的時刻。我不禁想像:這個燃料貿易公司的課長身上究竟能發生什麼樣的突發事件呢?是我不被看在眼裡呢?或是我遇上了愚蠢的委託人?不管是哪種情況,我都無所謂,因為看不見的東西終究無法看見,而且一開始,我就不打算看。
我想看的東西已經看到。我的目光始終盯著那裡。那映出淡淡長方形的光亮、檸檬色的窗戶……我剛剛才從那裡告辭出來。那檸檬色布簾似乎在阻擋黑暗入侵她的房間,與此同時,它還向站在暗夜中顫抖的我發出陣陣冷笑。然而,必然就是你,到頭來要背叛她。我就等著呢,繼續等到你的出現。
就在這時,有個似乎用腳跟走路的腳步聲倉皇挨近,於是,我這才收回眺望的視線。那個女子的腳步聲顯得有些膽怯。踩著高跟鞋的步伐急促,似乎在趕時間,腋下挾著紙袋……儘管在黑暗中,仍可看見白色大衣的領子和袖口都鑲著毛皮。她佯裝沒看見我的樣子,但表情瞞不過我的眼睛,因為她看向我這邊時,上半身僵硬得有如穿著鎧甲;我突發異想,這時我若猛然把她按倒在草坪上,會是怎樣的情況呢?她一定駭然地叫不出聲來,如同雕像般咚地倒下,佯裝昏迷。她那白色大衣過顯眼了,我應該往她身上撒些枯草敗葉……埋在枯葉中的女子沒有動彈……她突然脫得全身赤裸,只有手腳伸展開來,一陣風吹來,把臉上的草屑帶走……這時候,那張面孔忽然變成檸檬色布簾那邊的女人……強勁的陣風吹來,吹散她身上的枯葉……然而,顯現出的並非我預料的裸身,而只是個黑洞……那個穿著白色大衣的女子,就在水銀燈下輕盈地一轉身,迅速膨脹的身形漸漸消融在暗夜中……我也看不見她的手腳,只留下深邃水井般的空洞……
我覺得穿在腳上的不是鞋子,而是冰凍的魚肚。不過,我打算再等三十分鐘看看。如果我料得沒錯……我只能相信自己料得沒錯……她彎腰的身影一定會映在窗簾上。因為她和覆在枯葉下的女子的情況不同。這不是我在選擇,而是她自己在抉擇啊!
從剛才的情況即已得知,她若想打電話,椅子礙手礙腳,因此她只能採取那樣的姿勢。她側著身子朝向窗戶,加上光線的緣故,頭部可能無法完全映現。窗簾布料很厚,但織得很稀疏,所以毋需擔心看不見她的身影。我只要抓住那個場面,稍稍挨寒受凍,這等待就算值得了。她要打電話給誰呢?毋庸置疑,就是所謂向來行為奇特的弟弟了。據她所說,她弟弟是個親切聰明奮不顧身又過於深思熟慮因此居無定所的奇怪男子……這個特地擔任徵信調查的委託者,在緊要關頭,卻把洽談事宜全扔給整天沉浸白日夢中、幻想被丈夫逗笑得前仰後合、動輒自言自語、快要酒精中毒的女子,而且始終不願露面,這種作法太不負責了……
不過,這倒無所謂。我原本就無意推論委託者提供的資料是否屬實。我們吃這行飯的,只要客戶給錢,明知他們謊話連篇,我都照樣承接。然而,我們還得掌握案情的來龍去脈,否則連傻瓜的角色也扮演不來呢。實際上,要把傻瓜扮演得恰如其分並不容易啊!況且,這還不能損及自尊心呢。要我佯裝笨蛋尚能接受,但若把我看成愚蠢透頂的傻瓜我可不奉陪!我只收下三萬圓的調查費用,它絕不能超出這個範圍。
我把皮箱放在腳下,兩手放進大衣口袋,一面輕揉著側腹,繼續盯著檸檬色窗簾那邊的動靜。一輛計程車發出尖銳響聲爬坡上來,劃破黑暗的夜幕,往社區公寓深處駛去。我決定在那輛計程車折返之前繼續等下去。但我旋即心想,萬一那輛計程車就此不再出現呢?這不可能,我總覺得她所說的弟弟或許根本不存在……智慧的車輪這種東西,有時候按圖組裝比拆卸來得簡單自然呢。
遠處傳來粗暴關閉鐵門的聲音,彷彿在縱橫交錯的管道間迴響不已。它如大地的嘆息般傳進耳中。微弱的狗吠聲在空中盤旋遠去。我突然升起一股尿意。我渾身不由自主地顫抖,似乎快憋不住了。我原本以為是雪花飄落,看來可能是凝視黑暗過久產生的錯覺。儘管我閉上眼,雪花仍在我眼底紛揚而下。然而,比這雪花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剛才那輛計程車居然亮著「空車」的紅燈折返回來。你說不可置信什麼呢?一切都難以置信。因此我不知道要懷疑什麼,我似乎連思考能力都被凍僵了。檸檬黃的窗戶那邊沒有任何變化……我原本想吃顆糖,卻誤將玻璃珠塞進嘴裡。幸好,我沒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我忍著冷顫,終於解完尿,從地上拿起皮箱回到車裡。計程車的引擎聲很刺耳,倘若事情像我所預料的,這「音響效果」應該是送給委託者的,但如今在我聽來卻覺得憤恨和鬱悶。哎,如果這斷然就是事實的話,我只好從這個事實著手調查了。
一個舊火柴盒和一張相片。設若這就是地圖(線索),那麼空白的地方未免太多。儘管如此,我認為自己沒有義務非得把空白全部填滿,因為我終究不是法律的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