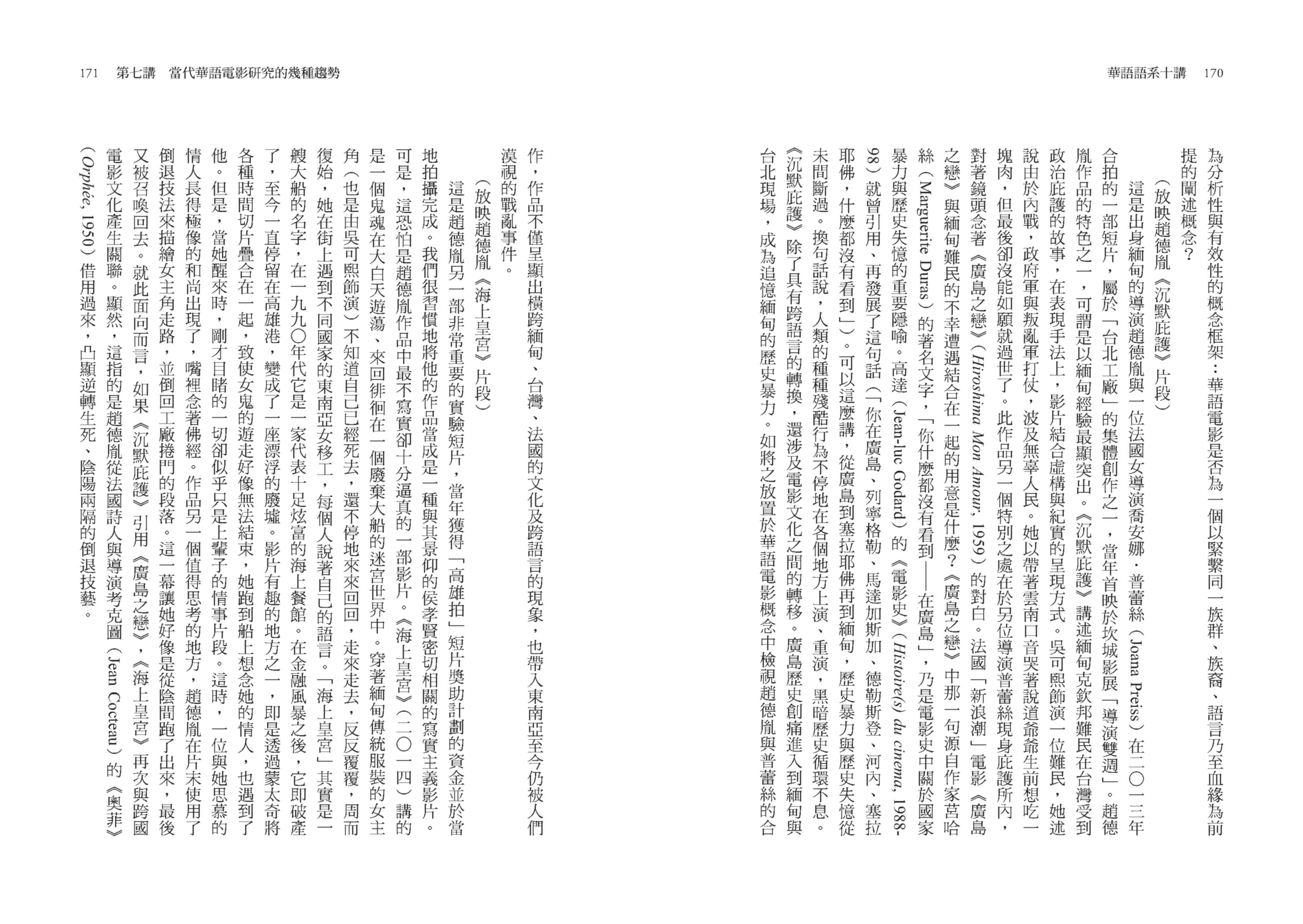華語語系十講
出版日期:2020-04-08
作者:王德威、史書美、李育霖、姜學豪、孫松榮、陳榮強、黃亞歷、黃淑嫻、楊翠、羅鵬
編者:李育霖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96
開數:25開,長21×寬14.8cm×高1.8
EAN:9789570854992
系列:聯經評論
已售完
探索華語語系理論的內在張力與學術動能
發掘跨領域、跨學科對話的可能契機
Sinophone(華語語系、華夷風或其他翻譯)一詞已成為當前華人/華語文學及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關鍵字之一。《華語語系十講》的內容,是以「第二屆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習營」的十個講座為基礎編輯而成,主題包括華語語系理論論述、文學批評、語言與文化政治、酷兒論述、電影與紀錄片研究、少數族裔文學、原住民文學論述等重要議題。一方面希望介紹這一概念並嘗試將其引介進入台灣學界,特別針對年輕學者,期待他們對該議題有更深度的認識,以擴大其研究視野;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機會能對這一概念提出在地的批判性理解,而非全盤地接受。
《華語語系十講》呈現了華語語系的論述跨越既有學科領域疆界的可能性,無論語言、族裔、政治、社會、區域、歷史、性別、國家與文化層面等等,在華語語系的話語與框架中都得以重新取得新的視域。透過這十講,除了具體體現華語語系研究對於地域、語言、歷史脈絡、文化媒介等差異的強調,同時也期許能進一步帶動國內人文領域學門跨領域的對談,並促進與國際人文研究社群的對話與交流。
作者:王德威、史書美、李育霖、姜學豪、孫松榮、陳榮強、黃亞歷、黃淑嫻、楊翠、羅鵬
(依姓氏筆劃排序)
王德威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長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書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系、比較文學系、亞美研究系合聘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兼任陳漢賢伉儷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文系榮譽講座教授
李育霖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姜學豪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專任副教授
孫松榮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
陳榮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文化研究與比較文學副教授
黃亞歷
台灣獨立製片工作者,以《日曜日式散步者》榮獲第五十三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黃淑嫻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中文碩士課程主任
楊翠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
羅鵬
美國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系教授
編者:李育霖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台灣文學、電影研究、生態批評、翻譯研究與德勒茲研究等。近期著作包括《台灣理論關鍵詞》(合著)、《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擬造新地球》,另編有《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帝國在臺灣》與Deleuze and Asia等書,並翻譯《德勒茲論文學》與《德勒茲論音樂、繪畫與藝術》等。目前除聚焦華語語系研究外,也探索數位科技帶來的後人文狀況。
編者序╱李育霖
第一講 什麼是華夷風?╱王德威
第二講 何謂華語語系研究?╱史書美
第三講 酷兒論述與華語語系研究╱姜學豪
第四講 華語語系‧南洋——多元文化和語言╱陳榮強
第五講 回顧香港的回歸╱羅鵬
第六講 國族、殖民與本土——香港六〇年代文學與電影中的香港身分╱黃淑嫻
第七講 當代華語電影研究的幾種趨勢(兼論跨藝術研究)╱孫松榮
第八講 當代紀錄片與文學的交會╱黃亞歷
第九講 少數說話——兩位少數民族華語女作家的歷史敘寫╱楊翠
第十講 華語語系的前沿地帶——幾個台灣文學的案例╱李育霖
編者序(節錄)
本書的講座內容主要是以二○一七年國立中興大學舉辦的「第二屆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習營」為基礎編輯而成。華語語系研習營由教育部與蔣經國文教基金會補助,自二○一五年開始舉辦。Sinophone(華語語系、華夷風或其他翻譯)一詞開始於北美學術圈,但幾年下來,儼然已成為當前華人/華語文學及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關鍵字之一。而研習營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希望介紹這一概念,並嘗試將其引介進入台灣學界,特別針對年輕學者,期待他們對該議題有更深入的理解,以擴大其研究視野;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機會能對這一概念提出在地的批判性理解,而非全盤地接受。因此,研習營在這一構想下做了一些設計。首先,研習營邀請國內外華語語系研究的重要學者前來講座,就此一研究概念與趨勢做深入的講解與剖析,期待能深化研究議題的面向與深度。其次,研習營遴選兩岸及海外研究生與新進年輕學者參與,這些學員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甚至加拿大等不同地區。值得欣慰的是,這些來自不同區域與不同人文領域的年輕學者,透過研習營期間彼此熱情的相互詰問,的確成就了一次美好的跨學科、跨領域的深度交流與廣泛對話。
本書匯集的正是此次研習營的十個講座。研習營結束之後,我們決定將講座編輯成書,以饗未能參與研習營的先進同好。這些講座聚集了國內外華語語系研究的重要學者,包括王德威教授(哈佛大學)、史書美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陳榮強教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羅鵬教授(杜克大學)、姜學豪教授(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黃淑嫻教授(香港嶺南大學)、孫松榮教授(臺北藝術大學)、黃亞歷先生(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導演)、楊翠教授(東華大學)以及李育霖教授(中研院)等人的講座。這些講者來自不同區域,且具有相異的文化背景,也帶著各自的學術視角與對特定區域的關懷。此外,講座的主題也相當豐富,包括華語語系理論論述、文學批評、語言與文化政治、酷兒論述、電影與紀錄片研究、少數族裔文學、原住民文學論述等重要議題。我們這樣設計,一方面固然希望能盡可能地涵蓋不同區域與多重面向,以期更廣泛地理解華語語系研究;同時,我們也要求講者針對其專業領域做出更深入的剖析,希冀在深化華語研究論述深度的同時,也在各自的領域中做出示範性的操演。
眾所皆知,所謂華語語系研究並非定於一尊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典範,甚至連「華語語系」一詞也引來諸多議論。然而我們認為,這正是華語語系作為概念或作為關鍵字的內在張力與學術動能。事實上,我們在研習營學員熱烈的發問與辯論中,目睹這一充滿活力的論述能量。除了在課堂上與講師熱切互動外,在晚間的討論時間,甚至在課程之外,學員間仍持續相互詰辯,令人印象深刻。更值得一提的是,華語語系的論述也隱含了跨越既有學科領域疆界的可能,包含語言、族裔、政治、社會、區域、歷史、性別、國家與文化層面的疆界,在華語語系的話語與框架中,重新取得新的視域。學員來自於不同學門、不同地區,而本次研習營的內容與組成,除了具體體現華語語系研究對於地域、語言、歷史脈絡、文化媒介等差異的強調之外,同時也展望了跨學科學術探討的可能契機。
第一講 什麼是華夷風?╱王德威
二○一四年六月末前往馬來西亞參加會議期間,同行馬華同事建議我可在馬來西亞或東南亞其他華語地區進行在地考察。因此,便藉機安排一趟馬來西亞行程,從北向南,從檳城到怡保、吉隆坡、芙蓉、文丁、波德申到最南端的麻六甲。見證了不同時期的華人聚落和文化生態,以及華語使用者眾聲喧譁、南腔北調的現象,這是一次親臨「現場」的難得震撼經驗。
麻六甲是具有上千年歷史的港口,是東西不同宗教、種族、政治,以及商務集散地。旅程中和幾位同事經過老城區的一家古玩店,門上的對聯「庶室珍藏今古寶 藝壇大展華夷風」,引起高雄中山大學張錦忠教授的注意。古玩店對聯上的「華夷風」三字,則促使我深思。「華夷雜處」是麻六甲存在的歷史現象,也是文化語言本色。當時張教授靈感忽至,提議Sinophone的對稱詞可以是「華夷風」。原來「華語語系」的譯法稍嫌呆板,也容易引起語音中心主義的聯想,對此語言學家早已提出批評—認為「語系」這兩個字另有所本,不應輕易挪用。相對於此,「華夷風」正好代表今天我們面對廣大的華語世界,尤其海外華語社會,所要面臨的各種各樣中西夾雜薈萃的語言文化和生活形式。這是「華夷風」的緣起。
什麼是華語語系文學?如果以大中華地區視角來看,不論是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或是台灣的「國語」,都行之有年;而白話文教育早自一九二○年開始推動。在這樣的國家語言體制下,往往易於忽略在標準的、官方的語言表述下,各種不同華語的聲音。聲音是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的開端。
過去對於以中文(或漢語)寫作的文學,我們一般以「中國文學」稱之。從中國大陸視角來看,「中國文學」的指稱似乎無庸置疑:中國文學就是中國文學。但我們必須思考「中國」文學這個標誌下的辯證性和複雜歷史的延伸性。相應於一個以國家領土疆界以及主權為定位的設置,例如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都是「國家」概念。這一國家概念和實體源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民族主義。就此延伸,我們總是認為一個國家的論述裡必須要有代表性的國家文學。所以中國必須要有中國文學,馬來西亞要有馬來西亞文學,這些看起來都是明確且清楚的概念。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華語語系所衍生的思考下,我們對於這些看似無庸置疑、約定俗成的標誌,應該要有辯證和問難的好奇心:什麼是中國文學?
過去七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理所當然地以「中國文學」為境內文學命名。但這樣定義下的「中國文學」要如何安置「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中文(或漢文)書寫文學?我們一方面理解它的國家代表性,但另外一方面,就文學論文學,對於這樣的「中國文學」,在地理劃分上——不論是政治地理、文學地理、甚至是想像地理——可以發揮不同的想法。
在過去,中國文學聚焦於廣大國家領土上形形色色的文學發展。像同心圓般延伸出去,海外第一圈是港澳台文學,然後是華僑文學,世界華文學……從大陸中國文學史的內容可以得知,這些地區的文學通常是邊緣的、附屬的,過去都是夾雜在文學史的片段裡聊備一格,甚至是置於附錄裡。後來才逐漸受到重視,有了專章;較有心的學者將不同的區域融合在不同的主題或現象下,如介紹寫實/現實主義文學,內容涉及北京、上海、台北、香港等地,做出綜合論述。但相對於主流的、正宗的中國文學,海外華僑文學、世界華文文學、漢語文學等畢竟是一種從屬的、次要的概念。
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及許多海外華語社群歷經政治洗禮和思辨,使得這個話題逐漸複雜。因此,中國文學這個詞需要重新給予定義。這裡最有意思的標誌是世界華文文學,通常我們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理解,以為無所不包:「世界華文文學」難道不包含中國嗎?中國人不是也說華文華語嗎?但此種用法的分別是有階序的,「中國」(中文)與「世界華文」其實涇渭分明。這在早期中華民國時代也是如法炮製。所謂葉落歸根、四海歸心、血濃於水的修辭常被用為唯我獨尊的潛台詞。但時至今日,台灣的中華民國早已罹患精神分裂,對世界、中國、華僑或是漢語等用詞特別敏感,不斷辯證什麼是中國、什麼是華僑、什麼是華文等。這些現象說明我們需要有新的名詞來說明新的現象;每一種新的命名方式,代表介入問題的新方法,甚至代表觀看世界的方法。
有些台灣文學研究者疑惑:我們已經有台灣文學了,為什麼還要再有華語語系文學呢?同樣的話題也出現在中國大陸的研究者:我們好好地做中國文學不就好了,為什麼還要華語語系文學呢?這恰是問題的開始。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正是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責任;我們的能耐就是經由文辭不斷創造層層思辨。
第二是關於華語語系命名的爭執,這牽扯到我和史書美教授間的爭辯。我先簡述我們意見相同的部分,再說明我們不同之處。
Sinophone這個字是有淵源的,來自西方學院從事第二、第三世界研究,尤其是後殖民學派。十九、二十世紀歐美強權在第二、第三世界殖民;不論是法國、德國或是英國、美國、西班牙,宗主國將政教模式、語言文化、教育機制,強加於在地的、被殖民的土著身上,年深日久,逐漸改變在地的文化生態,以至於到了某一時間點,宗主國強勢的語言文化制度凌駕、甚至抹消在地原有一切。於是有了英語語系、法語語系、西班牙語系、德語語系、葡萄牙語系等殖民文化。這是一個不得已的歷史情境。所以後殖民論述興起後,不論是第一世界學院的學者,或是被殖民地區的學者,都對於這樣的現象做出反思。而Sinophone是延續這樣的論述出現的。
在台灣,我們可以談日語語系(Nipponophone)環境。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將台灣化為殖民地,以強勢的語言及政教模式改變台灣屬性。到了一九三○、四○年代,台灣人已經在邁向新日本人或是準日本人的過程了。在這個意義上,語言不再只是透明的表意工具而已;語言承載過多政治符號及歷史創傷。對於殖民地的子民,如何找回失去的聲音,如何在殖民的經驗之後,重新認識自己身分,這是後殖民論述對於華語語系研究或是其他語系研究很大的貢獻。
但我認為在華語(中文)語境裡,華語語系不能完全以西方的後殖民論述作為唯一的方法學,它並不完全適合華語語境或中國語境,所以如何在這樣的差異裡,找到一個屬於華語語系的,相當不同的理論範式,這是我想致力的目標,以下會進一步說明。
接下來是另一個話題:我們使用華語語系,並不是只承認漢語是唯一的語種,或是我們唯一關注的對象。我們承認漢語在今天是(廣義)華族語言的大宗,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使用者。但當我們把這個領域擴大,我們了解在中國大陸(官方認定的)五十六個民族所使用的語言超過八十種。回看台灣,除了標準國語外,有閩南話、客家話等;而閩南話如果細分,又有南北差異。更不用說原住民所屬南島語系的不同語言。我們要特別注意在「華語」的「華」之下,「眾聲喧『華』」的現象。中國大陸的語言學家也提出,在目前廣義的中國語言裡,漢語之外,我們至少有阿爾泰語、通古斯語、南島語、南亞語不同語系。所謂「華語語系」因此不僅牽涉政治、文化、族群地理,同時更是一個時間流程裡不斷分合律動的現象。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把它歸因為廣義的眾聲喧「華」現象。
華語語系研究出現之前,對於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性,學界已經有許多思辨和不同論述方法。簡而言之,「何為中國」從來都是一個歷史漫長的問題,華夷之辨一直存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所謂「中國性」的問題有了新一波的討論,討論的興起時間恰好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天安門廣場上,上百萬學生及不同階級的代表示威罷工,最後導致官方流血鎮壓。面對這樣的歷史危機時刻,一群海外知識分子提出應對中國重新定義。當時任教於哈佛大學的儒學研究者杜維明認為,中國的政治可以千變萬化,文化源遠流長;所謂「文化中國」於焉而起。新加坡學者王賡武認為中國性永遠是在地的,而且必須不斷在實踐的過程裡體會、定義、重建。他的「中國性」帶有實證主義色彩。當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李歐梵強調「遊走的中國性」,認為「中國」不必由政治地理空間作為唯一判準;只要懷抱中國想像,人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加州柏克萊大學美國華裔王靈智教授則強調雙重統合,認為海外華裔必須在中國性和異(美)國性間來回思考,協調自己身分。
九○年代中期以來,更具批判力度的聲音出現。任教美國,來自香港的學者周蕾強調「反血緣的中國性」。對周蕾來說,所謂「血濃於水」、「葉落歸根」、「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些以倫理、血緣為訴求的中國性論述,已經過時。「中國性」必須重新去思考。周蕾的香港背景也許說明了她的立場,但她並非只是簡單的反中主義者。對她而言,中國性仍然是我們論述的槓桿,需要左思右想,達到論述的高度和張力,不能輕言廢棄。洪美恩(Ien Ang)教授出身印尼的Peranakan背景,即土著和中國移民所形成的混血文化,在荷蘭接受教育,於澳洲教書。不論是在中國或是台灣旅行,她都遇到類似的質疑:既然有中國血統,為什麼不認同祖國,為什麼不會說中文?這種對中文/中國性愛恨交織的結果,產生「On not speaking Chinese」的弔詭辯論。最後還有一種選項,對於像哈金這樣的作家,留美英語系博士,六四之後,他理解哪怕是創作,也不能再用中文恰當地表達他的複雜感情;他反而在英語世界裡找到表達方式。這樣的作家算不算華語語系作家呢?他關懷的還是中國問題,他在語言策略上的選擇卻是非中文表述。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更多聲浪出現,以史書美教授《視覺與認同》(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2007)一書最具辯證性。史教授認為,必須要強調華語語系的原因基本是地理政治的:我們所面對的中國如此壯大,無所不在,幾乎有帝國架式。因此她特別強調華語語系的研究範疇是海外的華語社群,還有法理中國以內、被迫臣服於國家勢力的少數民族。華語語系必須有一個抵抗的力道、批判的訴求,這樣才能夠展現論述的強度。
史教授以三個論述支撐她的立場。第一,大陸殖民主義。她提醒我們,雖然一般以為在中國境內從來沒有殖民與被殖民的情況,事實上清朝就是帝國式統治。中國也許沒有歐洲的海上殖民經驗,但內陸殖民行動從來未曾停歇。第二,定居殖民主義。從十九世紀歷經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再到一九四九,中國至少有四次大規模移民潮。大批的華人,尤其是東南沿海華人,來到東南亞、港澳、台灣,甚至遍及歐美。這些華人以移民或難民身分來到異鄉,但落地之後,運用語言文化以及商貿優勢,展現他們在地生存力,有的時候甚至喧賓奪主,壓抑了當地的土著。
我理解這一論述對華人移民的批判。但在誇大華人的殖民共犯身分之餘,史教授沒有對當地土著原本可能存在的政治瓜葛,以及不同移民殖民勢力在不同的移居時間點上與其他勢力,無論是帝國的、土著的、殖民的勢力,此起彼落的鬥爭過程。比方說,東南亞華人一方面是定居殖民者,一方面也是歐西勢力下的被殖民者。這都可以做出更複雜的論述。刻意強調土著受到外來勢力的壓迫固然有人道精神,但也容易墜入「高貴的野蠻人」的浪漫迷思,是為另類的「外來」思維霸權。
史書美教授的第三點是「反離散」。她認為離散帶有回望故國故土的寓意,意味移民者對移居地不願有安身立命的承諾。她強調移民者到了不同移居地後,應該力求落地生根,而非葉落歸根:所謂離散終有盡時。這樣的反離散觀點完全是在理想(多元一體)空間定義下做出,忽略時間的縱深發展和種種歷史偶然性。反離散固然有深耕在地的理想,但人類的遷徙居留豈能局限於想當然耳的邏輯預設?沒有一個族群願意永遠在離散的路上。離散的現象一方面顯示歷史狀況無可奈何,但另一方面也同時投射歷史的無限可能。比如,馬來西亞的華人力求落地生根,但在貌似多元、實則並不公平的族群政策之下,又如何要求華人委曲求全地融入未必友善的多元社會?離散成為不得已的選項。而在後現代世界裡,離散的路徑不必然導向回歸故土,也可能只是行程的下一站。
和史教授主張幾乎針鋒相對的是耶魯大學石靜遠教授。她的專書《中國離散境遇裡的聲音和書寫》(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2010)除了點明語言的眾聲喧譁外,更強調書寫表述才是另外一塊戰場。言說有賴廣義的書寫、銘刻或紀錄為媒介,才能散播流傳,才不至於成為浪漫的語音中心主義。另外她提出一個關鍵詞,「Sinophone Governance」,也就是綜合治理。她認為在歷史的脈絡裡,各種的華語表述、傳布每每受制於特定歷史狀況,而使用者必須做出因地、因時制宜的決定。語言不是完全透明無礙的東西,總是各種考慮,包括意識形態、政治訴求、經貿動機下合縱連橫的網絡。例如曾經為因應中國正在崛起,東南亞各國嚴防左派滲透的政策早已因為時過境遷,而有了修訂。華語成為熱點。所謂合縱連橫意味每一個使用華語的個人、社群或地區時時刻刻地在調度、選擇華語如何表述的理由與方法。
石靜遠教授也強調無所謂天生的、本然的「母語」;每一個人都在既定的社會環境裡形成語言的習性。她的方法一方面具有後現代解構性,一方面具有英美實證主義的特色。
我們再把討論版圖擴大。有些學者雖然不一定是自覺的華語語系研究者,但卻有殊途同歸的成績。上海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的「宅茲中國」研究,概念語帶雙關。「中國」有其歷史淵源,可以上溯到西周;到宋代「中國」二字開始具有國家、政治領土的涵義。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才指涉現代語境中的國家主權的政體。「中國」在葛兆光的敘事裡完全被歷史化了。宅茲中國的「宅」本來的意思是在這裡;這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但葛教授也有言外之意,影射今天的中國雖然家大業大,但還是很「宅」的,局限在民族主義裡。
相對於此,葛教授提倡「從周邊看中國」。意味中國之所以如是,不僅是一個自覺主題而已,更是一個被觀看、詮釋的客體而存在。中國不能每天只說自己是中國,需要有一個被指陳、對話的對象。所以他的研究轉到漢字文化圈。他從越南、高麗、朝鮮、日本的書寫,如遊記、詩文、使節紀錄等對中國的描述,拼湊不同中國圖景,就是外國人看中國。這結果非常精彩,因為所謂中國有了倒影,既是他者,也是我者。我們在談華語語系常常可以強調聲音的政治,忽略漢字漢文這一塊。秦漢之際漢字就傳到越南,在漢代傳到高麗,在晉朝到了日本,整個東(南)亞的漢字圈有悠久的歷史。到了今天,作為一個中國學的研究者,我們不得不注意如何從周邊往裡看中國的方法。
最後來到我所提出的「後遺民論述」。這個詞容易引起誤解和爭議。我其實刻意用後遺民對應史老師的後殖民,希望把問題的張力拉開。事實上,殖民或後殖民不足以說明華語語系的問題。關鍵點在於,第一是年深日久的文化傳承,但我所謂的文化傳承,不是指簡單的連續性,不只是一以貫之的傳統(great chain of being),也是無數分合裂變的傳統(tradition of breakups),因為歷史也是無數的斷裂所構成的脈絡。我們太多時候在全然反中的情緒裡看待中國,其實不知不覺落入大中、一統的結構中。如果我們同時注意中國歷史也是無數的斷裂,我們在每一個斷裂都可以找到橫生歧出的可能性。這樣定義的中國沒有必要被一個政權,一種歷史,或被一種文化想像所局限。
第二,「後遺民」特別著重解構主義的「後」(post)的說法,因此與遺民有所區隔。如果遺民代表難以割捨的鄉愁,前朝故國的憂思,後遺民的「後」意味「完了」、「過後」,一切對時間、正統的思念都已經煙消雲散。但遺民既已是時過境遷,一種對往事故國錯位的追懷嚮往;後遺民是錯位的錯位,對追懷的追懷。因此,「後」又意味「完而不了」。過去似乎總是幽靈般的縈繞不去。這幽靈其實滲透到現代定義的國家論述裡。我們要問,二十世紀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理論早已擺脫封建王朝的體制,不應該有遺民的孤臣孽子之思,但何以忠君愛國的遺民心態仍然是想像國家共同體的要素,甚至成為預設邏輯?又比如說,以台灣為名的建國論述其實是投向未來的想像,但卻往往被操作為先驗的必然,彷彿未來潛藏在過去。如此歷史法統的幽靈必須憑空製造,以便作為未來國家的「歷史」的一部分。
我認為遺民的幽靈無所不在,我們必須批判性地對待。這樣的幽靈事實上也降臨在這個空間裡,在你和我的身上。畢竟過去的傳統,無論是有意的排斥或無意的接受,總是徘徊不去。欲潔未曾潔,云空未必空。自以為是重新開始,卻往往有意無意因襲了過往包袱。在這意義下,後遺民的觀點其實是批判遺民的立場。如前述,「後」,不只是暗示一個時代的完了,又暗示一個時代的完而未了。就算沒有源頭傳統,但是為了未來的政治目的,也必須發明一個源頭,一個傳統,以作為「想像的過去」的未來繼承者。所以我認為「後」字有強烈批判意思。而「遺」這個字,在這裡我認為不只是失去、遺失而已,也是剩下的、殘遺的意思;而這個「遺」字,在字源學裡,還有餽贈、遺留的意思。
我特別想說,在面對一個龐大的名為「中國」的歷史包袱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權陳述自己的立場和政見,但不要忘記,最反抗的姿態裡可能已經不知不覺沿襲原本要反抗或是唾棄的思維邏輯,甚至言說方式。這是不請自來的遺民幽靈。從遺民到後遺民,我們大家必須思考我們如何面對歷史的方式,越是正本清源、獨立自主的姿態,越應該警覺自己作為後遺民的可能。在台灣目前的政治語境裡,史書美老師的後殖民理論無疑具有更多的市場優勢。但在一個論述場域裡面,後殖民論述難以說明台灣歷史千絲萬縷的關係;後遺民立場不僅批判遺民論述、也同時批判後殖民論述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