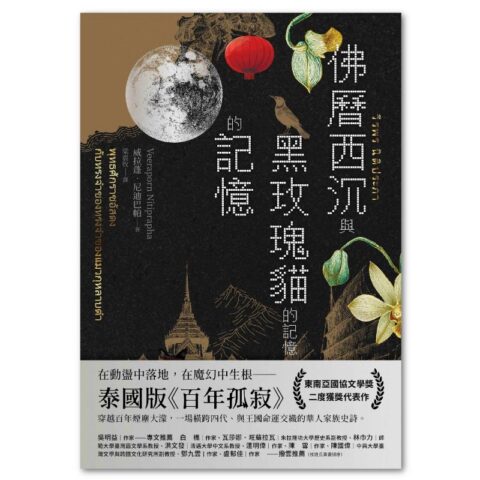四重奏(禮讚書盒紀念版)【首刷特贈神思音律紀念書票】
出版日期:2023-02-09
作者:T.S.艾略特
譯者:杜國清
裝訂:精裝
EAN:4711132389777
尚有庫存
★ 首刷特附神思音律紀念書票。
★ 特別設計典雅禮讚書盒,值得收藏與餽贈。
★ 封面採用高級墨黑書皮紙 + 綠灰花漾紙,以三接式裝裱,呼應《四重奏》中的信仰探索、時間和人的關係,自然呈現廣袤又幽微的議題。由外在到內容,一體呈現詩作的核心價值。
字謎般深奧難解的詩作,訴諸深邃的思辨而非純粹情感的共鳴;
突破固定的格律,自有獨特的節奏感與音樂性……
艾略特以一己之精神世界,撼動歐美以至華文世界詩歌的創作,
自成一座劃時代的里程碑。
然而其語言的冰山顯露出的尖角之下,
往往藏著他對時間、生死、哲學、現世、宗教等深奧概念的思索與探尋;
藏著他對歷史意識與古典傳統的承載、藝術的經營、詩之本質的探究……
令希冀追溯其影響,或僅為一窺其面目的船隻難以近身。
本書收錄詩人創作史上的壓軸之作四首〈四重奏〉。
由既是艾略特文學理論的研究學者、翻譯家,同時也是詩人的杜國清譯詩,
在字句意義的傳達之外,兼重其語言藝術、詩意、節奏和音樂性之重現及再創造,
並針對冰山之下龐大的隱喻、象徵、典故……輔以譯註與解說,
如同踏入艾略特曲折紛繁之思想世界的路標。
本書並為目前唯一採中英對照之版本,
更便於細品詩人精密細緻的文字表達安排、文句特有的音樂性。
力求完整呈現詩歌此一無法離開語言存在的藝術原有的面貌,
與曲盡全意後再創造的表現力,兩相對照之魅力所在。
作者:T.S.艾略特
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詩人、劇作家、評論家,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家族為英格蘭裔。
艾略特詩作的產量不算豐碩;1922年發表的〈荒原〉,卻是二十世紀最受矚目的名篇,加上其後出版的高峰作品〈四重奏〉和諾貝爾獎效應的推動,艾略特成為現代詩的代表人物之一。1999年更獲《時代》雜誌選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世紀詩人」。除了詩歌,艾略特還創作了多部詩劇,包括《大教堂謀殺案》、《家庭團聚》、《雞尾酒會》、《機要文員》、《政界元老》等。
艾略特能成為「世紀詩人」,固然有賴於他的詩作;但與詩作同樣重要,是他的評論,能教無數詩人、學者、評論家著迷,不知不覺間按照他的詩觀讀詩、寫詩、評詩,為他建立一個輝煌的「艾略特時代」。
譯者:杜國清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日本文學碩士,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教授、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暨台灣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創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Series),致力於臺灣文學的英譯出版。
杜國清專攻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理論、中西詩論和臺灣文學。曾任《現代文學》編輯,為1963年臺灣《笠》詩刊發起人之一。著有詩集《蛙鳴集》、《島與湖》、《雪崩》、《望月》、《心雲集》、《殉美的憂魂》、《情劫》、《勿忘草》、《對我 你是危險的存在》、《愛染五夢》、《愛的祕圖》、《山河掠影》、《玉煙集 錦瑟無端五十絃》等;散文集《推窗望月》;評論集《詩論.詩評.詩論詩》等;翻譯有艾略特《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波特萊爾《惡之華》、劉若愚《中國詩學》、《中國文學理論》等。曾獲中興文藝獎、詩笠社翻譯獎,1993年漢城亞洲詩人大會頒與功勞獎,1994年獲文建會翻譯成就獎。
四重奏(1936)FOUR QUARTETS (1936)
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 )
東科克(EAST COKER)
岬岸礁岩(THE DRY SALVAGES)
小吉丁(LITTLE GIDDING)
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
No.1 of ‘Four Quartets’
〈四重奏〉之一
雖說「道」是萬人共通的原則,大多數人活著似乎都有
自我的理解力。
上行道與下行道同是一條路。
──Diels 編:《蘇格拉底時代哲學者的片斷》
τοῦ λόγου δὲ ἐόντος ξυνοῦ ζώουσιν οἱ πολλοί
ὡς ἰδίαν ἔχοντες φρόνησιν.
ὁδὸς ἄνω κάτω μία καὶ ὡυτή.
─—Diel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Herakleitos).
I
時間現在與時間過去
二者或許存在於時間未來,
而時間未來包含在時間過去中。
假如一切時間永遠存在
一切時間都無可贖回。
可能曾經有過的是一種抽象
留下永遠的可能性,
只存在於思索的世界中。
可能曾經有過的,以及曾經有過的
指向一個終點,那永遠是現在。
足音在記憶中迴響
沿著我們沒走過的通道
向著我們沒開過的門
進入玫瑰花園。我的話
如此,回響在你的心中。
但是為了什麼目的
騷擾一盆玫瑰葉上的塵埃
我不知道。
其他種種回響
棲息在這花園裡。我們跟著去嗎?
快快,小鳥說,把它們找出來,把它們找出來,
就在那拐角兒。穿過第一道門,
進入我們的最初世界,我們要跟隨
那隻畫眉的欺矇嗎?進入我們的最初世界。
就在那兒,顯得高貴,但看不見,
沒有壓力地移動,越過枯葉
在秋暖中,穿過顫動的空氣,
於是小鳥叫了,應和著
灌木中隱然聽不見的音樂
而看不見的眼神交叉,因為玫瑰
具有引人觀賞的花容。
就在那裡,像我們的客人,招待也被招待。
於是我們行動,他們也一樣,以正式的模樣,
沿著無人的小路,走進黃楊樹的圓圈,
向下望著沒有水的池塘。
乾涸的池塘,乾涸的水泥,褐色的邊緣,
而池塘充滿陽光照射的水,
而水蓮升起,靜靜地,靜靜地,
池面在陽光的中心閃耀著,
這些都在我們背後,映照在池塘裡。
然後一片雲飄過,而池塘空空。
去吧,小鳥說,到那邊,葉蔭下滿是小孩,
興奮地隱藏著,忍住笑聲。
去吧,去吧,去吧,小鳥說,人類
不堪忍受太多的現實。
時間過去與時間未來
可能曾經有過的以及曾經有過的
指向一個終點,那永遠是現在。
I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Into the rose-garden. My words echo
Thus, in your mind.
But to what purpose
Disturbing the dust on a bowl of rose-leaves
I do not know.
Other echoes
Inhabit the garden. Shall we follow?
Quick, said the bird, find them, find them,
Round the corner. Through the first gate,
Into our first world, shall we follow
The deception of the thrush? Into our first world.
There they were, dignified, invisible,
Moving without pressure, over the dead leaves,
In the autumn heat, through the vibrant air,
And the bird called, in response to
The unheard music hidden in the shrubbery,
And the unseen eyebeam crossed, for the roses
Had the look of flowers that are looked at.
There they were as our guests, accepted and accepting.
So we moved, and they, in a formal pattern,
Along the empty alley, into the box circle,
To look down into the drained pool.
Dry the pool, dry concrete, brown edged,
And the pool was filled with water out of sunlight,
And the lotos rose, quietly, quietly,
The surface glittered out of heart of light,
And they were behind us, reflected in the pool.
Then a cloud passed, and the pool was empty.
Go, said the bird, for the leaves were full of children,
Hidden excitedly, containing laughter.
Go, go, go, said the bird: human kind
Cannot bear very much reality.
Time past and time future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