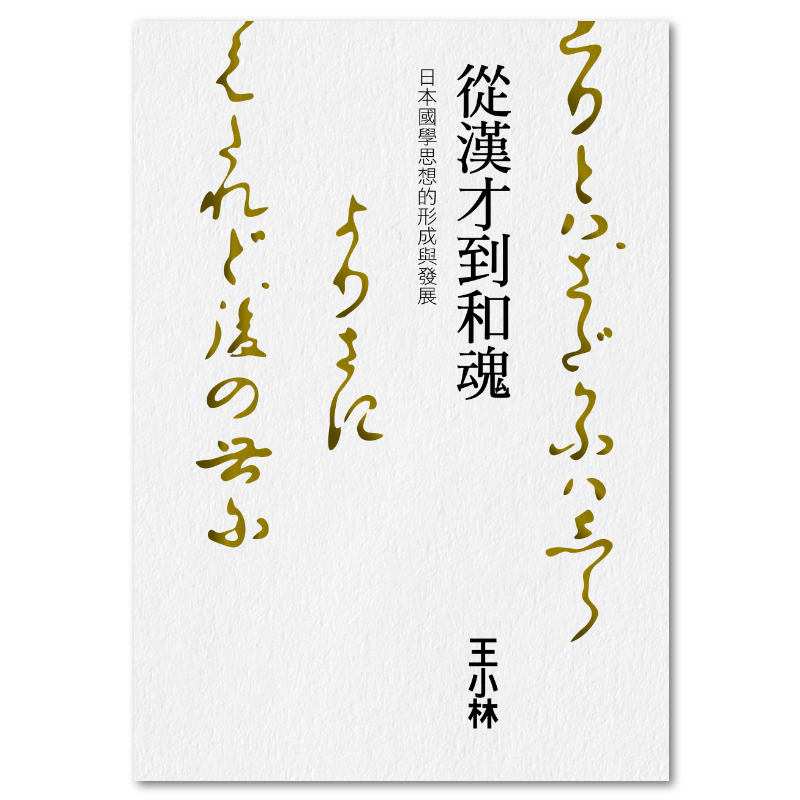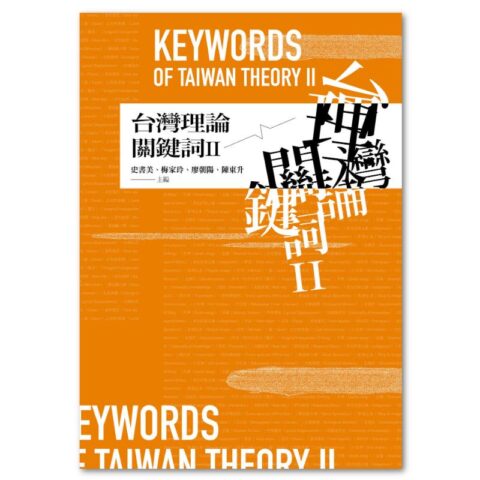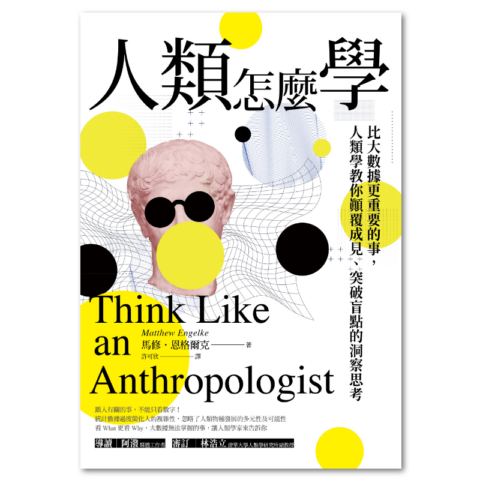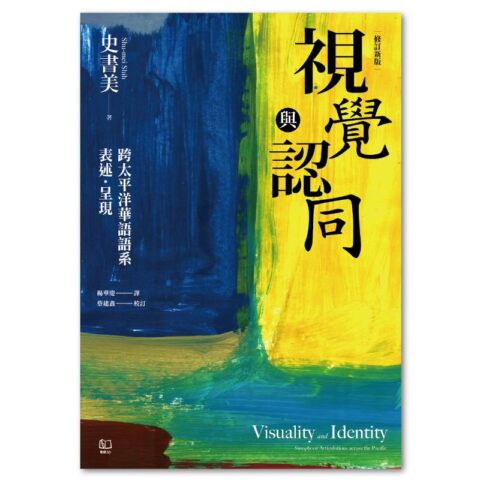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出版日期:2013-01-14
作者:王小林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41251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不了解日本國學,就無法了解日本社會及文化,更遑論了解日本人
日本國學產生的歷史和背景漫長且複雜,
為了對日本國學的形成、發展、特點及其影響,有較為清晰的把握,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王小林
以漢字、名實觀、朱子學、疑古思潮等作為觀察對象,
多元檢視日本國學思想的要素,
為讀者提供了相對全面理解日本國學之內在精神結構的可能。
本書作者王小林以「從漢才到和魂」作為日本國學思想之形成與發展的研究、觀察視角,分別從不同議題、現象與學說主張來考察日本國學思想的發展流變。
《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第一章與第二章主要從「漢字」與「言靈」;「名」與「言」,探討了漢字與「和魂」、「國語(日語)」之關係,以及名、言與「實事」、「體魂」之間的演繹詮釋,如何神聖化日語同時強化日本之神國意識。第三、四、五章則以朱子學為江戶儒學之代表,將之視為日本國學之對照學問,闡述了日本國學之文論、宇宙觀與不可測度之神。第六章則從江戶儒者富永仲基之「加上說」與顧頡剛之層累說之間的關聯,爬梳了中日兩國之「中國學」背後的日本國學之成份。最後一章的第七章,則闡明了決定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職分」、「世間」這兩個精神關鍵概念,其宗教理論根據其實來自近世日本之國學家。
如上所述,《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以漢字、名實觀、朱子學、疑古思潮作為「漢才」與「和魂」比較的觀察對象,多元檢視了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要素,本書所涉及之議題內容,提供了讀者數個面向以思考形構日本國學之要素有何?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相對全面理解日本國學之內在精神結構的可能。
作者:王小林
1999年獲日本國立京都大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日本古典文學,特別是上代(奈良時代)文學與中國文學及宗教思想的比較研究。近年亦著力研究儒學的日本化與日本國學的各種問題。著有《日本古代文獻の漢籍受容に關する研究》(日本和泉書院‧研究叢書420),另有多種相關論文在日本、台灣、香港等地的學術刊物和學術機構發表出版。
序章
第一章 漢字與「言靈」:日本傳統漢字論中的「執拗低音」
1. 什麼是「執拗低音」
2. 漢字與「言靈」
3. 漢字與「和魂」
4. 「古言」與「和魂」
5. 漢字與「國語」
6. 結語
第二章 「名」與「言」:中日語言哲學的演繹及啟示
1. 前言
2. 「名」與「實」
3. 「言」與「事」
4. 「名」與「體」
5. 「言」與「魂」
6. 結語
第三章 從朱子學到「古道論」:近代日本國學文論的形成及其影響
1. 「政治性」與「非政治性」:圍繞中日文學的偏見
2. 江戶學者的朱子學闡釋與「古道論」的產生
3. 「古道論」與山崎闇齋的神儒混合說
4. 「古道論」與近代日本的反智識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5. 走出「日本文化特殊論」的誤區
第四章 日本近世國學宇宙觀的形成及其影響
1. 序言
2. 國學宇宙觀與西方天文學的關係
3. 日本古代宇宙觀中的自我定位
4. 從「神佛習合」到「神儒習合」
5. 國學宇宙觀的確立及其意義
6. 結語
第五章 日本近世國學宇宙觀與宋學的關係
1. 序言
2. 「三大考爭論」的焦點
3. 《三大考》的表述與《朱子語類》
4. 「理」與「神」的對立
5. 「理」與「神」的結合
6. 《三大考》與「中國論」
7. 結語
第六章 「加上說」與「層累說」:中國學背後的日本國學
1. 《中國上古史》與「加上說」
2. 「加上說」的形成背景與近代日本學術思潮
3. 「加上說」與「層累說」的關係
4. 關於「層累說」形成之幾個疑問
5. 結語
第七章 國學與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1. 序言
2. 有關日本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不同論點
3. 「職分」「世間」與日本資本主義精神研究的關係
4. 「職分」「世間」的宗教性與禁欲傾向
5. 「職分」「世間」與日本資本主義精神的基本特徵
6. 結語
參考文獻目錄
序章(節錄)
一
十多年前,在京都的舊書店偶然購得一冊滿是灰塵的文庫本,題為《玉勝間と初山踏》。作者是二戰前後享譽日本古典文學領域的東京大學教授久松潛一(1894-1976)。這本總數不超過一百頁、出版於1943年二戰期間的小冊子,以介紹和闡釋近代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1730-1801)的兩篇學術隨筆為主。在當時,作為《日本精神叢書》中的一冊,與眾多的學者、文學家的著作一道,從文化思想的角度為國家機器所發起的戰爭提供理論依據和精神支援,特別強調「國學」對鞏固發展日本文化的作用和重要性。由於當時我的研究主要關注日本的上代文學,而這個領域的相關文獻大都被視作日本「國學」的經典,所以,這本小冊子的內容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
時過境遷,戰前風靡日本的「國學」概念,已經淡出日本學術界。《日本精神叢書》這一類的小冊子,也似乎已經被塵封和遺忘。然而,仔細閱讀其中的內容,卻仍然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現代性。因為,雖然「國學」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日本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概念,但只要生活在日本,無論是從電視中的時事辯論中,還是在日本學者的言談舉止中,都可以感受到與這本小冊子一脈相通的某種氣息。我至今還記得,在碩士指導教師研究室的門上,赫然貼著一張大大的海報,中間是國學家本居宣長的自畫像,旁邊則是本居宣長手書的歌頌日本精神的自創和歌,大意是:
若問何為大和魂,芬芳櫻花映朝暉。
這種情景,時常令我聯想到曾經裝點中國學者書齋牆壁的宋明理學家的詩句或語錄。諸如魯迅在《祝福》裡描述的魯四老爺客廳裡的「事理通達心氣和平」之類。
1997年深秋,我所屬的研究室組織了一次赴三重縣的伊勢松阪參觀本居宣長故居及墓地之旅。看完本居的墓地,在夜幕徐徐降臨的下山途中,走在我旁邊的導師猛不丁地對我說:「如果本居宣長知道你對寶貴無比的《古事記》所做的解讀,真不知道會作何感想呢!」我不記得當時回答了什麼,也可能只是敷衍地笑了笑。但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隱隱地意識到,自己每天所做的日本古典文獻考證與文字訓詁,是不能作為遊離於日本社會現實的純粹的學術來看待的。我預感到,在自己所從事的日本文獻研究與古日語訓詁學的另一端,遲早要與某種無法回避的意識形態遭遇。幾乎同時,我開始注意到了一個研究界甚少有人觸及的現象,即:本居宣長的古典研究方法論在近三百年的歷史中,一直左右著上代文學中被視作「國學」經典的文獻的解釋和訓詁,而向來被學者們看作定論的本居宣長的有關解釋和訓詁,大多是基於某種信念的臆測。但正因為這種信念和臆測與其類似神學體系的「國學」思想密切相關,所以,很少有學者對此進行挑戰。這一點,不僅從反面證明了我的預感沒有錯,同時也令我強烈地意識到,日本古典研究,特別是「國學」經典與意識形態的關聯性,是一個尚未過時的課題。
二
有趣的是,幾乎與購買久松這本小冊子同時,中國大陸的「國學熱」開始出現在大眾的視野。至今依然如火如荼的這一現象,不時地逼迫我去關注「國學」在日本和中國各自歷史進程中的意義。什麼是「國學」?其起源與定義究竟如何?炙手可熱的中國「國學」與曾經在近代日本國家主義浪潮中獨佔學術鼇頭的「國學」究竟有何異同?
回答上述問題並非那麼容易。數年前,朱維錚教授就曾對「國學」的定義與範圍提出過質疑,也指出了「國學」在近代中國政治文化中引起的一系列弊病。劉夢溪教授也從學術史的角度,對近代以來「國學」一詞在中國的衍生、發展、影響及其局限性等作了詳細的梳理和分析。兩位先生均對「國學」內涵的複雜性保持了審慎批判的看法。而我認為,針對這種複雜性的分析和批判,不能單從中國學術史一個方面來看。中國之所謂「國學」,與近代以來中日的政治、文化的發展歷史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時至今日,有關「國學」這個概念,在中國學者之間尚未達成共識。
一般來說,中國的學者們似乎都瞭解到,「國學」一詞是日本的「舶來品」,後來成為「中國學術」的簡稱。例如,近人張岱年在《國學今論》的序文中,曾就「國學」的定義作過如下的詮釋:
國學是中國學術的簡稱。二十世紀初年,國內一些研治經史的學者編印《國粹學報》,其後章太炎著《國故論衡》,又作了《國學概論》的講演,於是國學的名稱逐漸流行起來。稱中國學術為國學,所謂國是本國之義,這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了。……國學是本國學術之意,這是我們所用的名詞,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學術,就不能稱之為國學了。西方稱研究中國的學問為Sinology,一般譯為漢學,現在亦譯為中國學。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謂Sinology不過是對於中國歷史陳跡的研究,把中國學術看作歷史博物館中的陳列品。事實上,中國學術源遠流長,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經過時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國學術是人類的精神財富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中具有歷久常新的精湛內容。
另外,余英時教授在最近一次與陳致教授的學術對話中,就「國學」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也作了如下的闡述:
國學原是說日本國的學術,是用來反對日本的儒學的。所以,有一批人講日本的神道,日本的文學,這就是他們的國學。日語讀法叫Koku-gaku-sha,就是「國學者」的意思,在18、19世紀非常活躍地反中國的思潮。那時因為日本人的本土意識起來了清末中國學者遊日本者很多,不知不覺地就借用過來了。
較余英時的推論更為具體細緻的考察,當推桑兵教授的近著《國學與漢學》。桑著第八章〈梁啟超的國學研究與日本〉中,就日本「國學」如何在近代被借用作如下分析。在考察梁啟超與日本學者古城貞吉的關係時,桑著指出梁啟超擔任主筆的《時務報》第22冊載有古城貞吉譯自《東華雜誌》的〈漢學再興論〉:
明治以前,漢學最盛,士人所謂學問者,皆漢學耳,除漢學則無有學問也。及政法一變,求智識於西洋,學問之道亦一變,貶漢學為固陋之學,如論孟子史之書,一委諸廢紙之中,無複顧問者。然其衰既極,意將複變也。比年以來,國學勃然大興,其勢殆欲壓倒西學,而漢學亦於是乎將復興也。
此外,桑著還留意到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之際,古城曾明確勸吳以如下之語:
勿廢經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
桑著由此推論:「可見國學一詞,源自日本,本意在與西學、漢學相區別。日本人士在向中國人鼓吹保存既有文化時,不能稱漢學,而以國學為替代。中國遂借指本國學術。因而東亞三國,各有其國學。」
從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瞭解到「國學」雖然是指中國本身的學術,但概念產自日本,於清末傳入中國後逐漸普及的基本事實。然而,僅僅澄清這一點,並不能解決中日圍繞「國學」這一概念的差異性及其所引起的問題。如後所述,日本「國學」產生於漫長的與外來文化對抗的歷史之中,在強調日本民族單一性與優越性的同時,也為日本國民提供了類似「終極關懷」的宗教性學說。事實上,日本「國學」以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為近代日本推行的一系列國家主義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依據。其理論雖然以古典文獻解讀為基礎,但基本上如同其他宗教教義的詮釋,具有倫理大於學理,信仰高於學術的性質。故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簡單地借用這一概念,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例如,中國「國學」的「國」是否以近代「民族國家」為前提?其二,是中國「國學」所涵蓋的範圍,是否僅僅限於「儒學」?其三,是中國「國學」的使命,要建立和推行什麼樣的精神或信仰?在我看來,這三個疑問一日不澄清,我們就沒有理由來消費「國學」這個看似萬能的學術概念。而這種弊端,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顯現出來。曹聚仁曾經在〈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一文中,就「國學」這一概念導致的學界混亂景象描述如下:
國學二字,浮動於吾人之腦際者經年矣,聞有一二博學者不察,用以為中國舊文化之總攝名詞,逐流者乃交相引用。今則國學如麻,略識「之無」,能連綴成篇,謂為精通「國學」;咿唔詩賦,以推敲詞句自豪者,謂為保存「國粹」。他則大學設科,研究中國文學,乃以國學名其系;開館教授四書五經,乃以國學名其院,人莫解國學之實質,而皆以國學鳴其高,勢之所趨,國學將為國故學之致命傷。國學一日不去,國故學一日不安,斬釘斷鐵,惟有轟之一法。今名之曰國學,即中國學術之簡稱,將與日本學術,英國學術,法國學術同為類名,吾不知其所以表獨立不相混之點何在?既無以表獨立不相混之性,則國學一名,即難成立。
曹聚仁文中所描述的現象,幾乎是當前國內圍繞「國學」所出現的各種現象的翻版。據我瞭解,中國大陸的某大學在設立「國學院」的時候,就曾經為「國學」究竟單指「儒學」,還是應該包括佛教、道教以及敦煌學等等發生過爭論。此外,成仿吾也曾經將熱衷「國學」者分為三類加以批判。1923年,成氏在《創造週刊》發表〈國學運動的我見〉一文中論道:
從事這種(國學)運動的人,約略可以分為下列的三種:
1.學者名人而所學有限,乃不得不據國學為孤城者。
2.老儒宿學及除國學外別無能事乃乘機倡和者。
3.盲從派,這是一切運動所必需之物。
這三種人性質雖稍不同,然而他們純襲古人的非科學的舊法,思用以顯耀一時,卻是一樣的。要想取科學的方法為真切的研究,他們都欠少科學的素養。他們的方法與態度,不外是承襲清時的考據家。所以他們縱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過增加一些從前那種無益的考據。這樣的研究不僅與我們的生活毫不相干,即於國學的研究,亦無何等的益處。
文中對考據學的微詞以及對「科學」的強調,自然是作者新文化運動立場的一個表明。但是,即便如此,成氏對「國學」作為學科的非科學性以及利用「國學」來掩飾學識的淺陋,視野的狹隘以及趨炎附勢的功利的批判,在今天看來依然有其現實意義。除了上述二位針對宣導「國學」,推行「國學運動」的「國學家」的批判之外,鄭振鐸對所謂「國學家」的本質也做了犀利的剖析:
他們是研究中國的事物名理的,然而卻沒有關於事物名理的一般的,正確的,基本的知識;他們是討論一切關於中國的大小問題的,然而他們卻沒有對於這一切問題有過一番普遍的,精密的考察;他們會講上古期的中國哲學,中古期的中國文學,近百年來的中國史,然而他們對於所謂「哲學」,「文學」,「歷史」的根本要點卻沒有握捉到手;他們談治水開河,他們談制禮作樂,他們談「立法三章」的事,他們談中國教育的問題,然而他們卻不是水道工程的技師,卻不是音樂家,制譜家,卻不是法律家,卻不是教育家。總之,他們是無所不能的國學家,卻不是專精一家言的專門學者。他們是認識世界最難認識的中國文字者。他們的唯一工具是中國文字,他們的唯一寶庫是古舊的書本,他們的唯一能事是名物訓詁,是章解句釋,是尋章摘句,是闡發古聖賢之道。他們逃脫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之外,這只手掌心便是書本古舊──的書本。
鄭氏文中所言「國學」混同「哲學」、「文學」、「歷史」各個學科概念的非「普遍性」與「非科學性」,與當今流行的「國學」概念有著相似之處。
事實上,自從「國學」這個概念使用之日開始,就陷入將意識形態與學術研究混為一談的狀況。觀察近來中國學界和媒體上流行的「國學班」、「國學大師」、「國學講壇」等等,不僅給人以百鬼夜行之感,更多的則是錯愕和茫然。
坦率地講,在尚未確認「國學」的內涵與範圍的狀況之下侈談「國學」,並不能令人由衷產生自信心和自豪感。相反,一位本來在人文學研究的某個領域積累了一些經驗,發現了某種原理的學者,一頂「國學大師」的桂冠,完全有可能將原本樸素的學術真理變作神秘莫測的文化圖騰。這頂桂冠甚至有可能被當作欺世盜名的工具,對文化發展產生完全負面的影響。而這一切,似乎都源自「國學」概念的神秘性和模糊性。所以,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將這個概念產生和發展的環節一一進行剖析的話,至少就不會被「國學班」、「國學大師」、「國學講壇」這一類的名稱搞得眼花繚亂、暈頭轉向,喪失追求學術真理的樸素熱情。
第一章 漢字與「言靈」:日本傳統漢字論中的「執拗低音」
一、什麼是「執拗低音」
日本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曾先後在〈歷史意識的古層〉與〈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研究的個人歷程〉兩篇文章中,對日本傳統思想和信仰在近代化過程中的體現方式做了詳細的分析,並使用「古層」、「執拗低音」就其特點進行描述。「古層」與「執拗低音」這兩個概念分別來自地質學和音樂學。丸山在此文中將「古層」――日本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即神道教與儒教、佛教、天主教、自由民主等外來思想區分開來,指出在近代日本,雖然歐美近代思想居於壓倒主旋律,但也常常被「古層」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低音部修飾。這種低音時而成為背景,時而壓倒主旋律,時而也被主旋律覆蓋。
那麼,丸山所說的「古層」與「執拗低音」究竟指的是什麼?就這一點,丸山並始終沒有具體說明,而是以日本最古的兩部文獻《古事記》、《日本書紀》所記載的神話體系為例,將這兩部文獻中的神道宇宙觀看作是構成「古層」與」執拗低音」的重要因素。針對這一點,筆者認為,透過歷史性地考察漢字與日本本土語言信仰的關係,可以清晰地認識和把握丸山所說的「古層」與「執拗低音」的具體形態。而且,這種形態並非僅僅局限於丸山所關注的近代,而是自漢字東漸伊始,就已經呈現在日本思想史中。本文的目的,就是嘗試從上述角度為丸山所提出的「古層」、「執拗低音」論提供新的詮釋。
二、漢字與「言靈」
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文獻《古事記》中卷應神天皇段,記載了中國古典最早傳入日本的狀況。
天皇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貢上。故,受命以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此和邇吉師者文首等祖。
與這段文字記載相似的內容,也可以在另一部史書《日本書紀》中看到: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達。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
《古事記》所言《千字文》是中國六朝梁(六世紀)時的文獻,而這兩段文字所描述的應神天皇時期為西元四世紀至五世紀初,所以在史實上顯然有誤。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年代的真偽。這裡我們應注意的是兩部文獻所具有的象徵性。因為,考古發掘的結果已經證明,中國文字文獻在應神天皇朝之前就已被日本人廣泛運用。雖然這兩部文獻被《古事記》記錄的原委和意圖不得而知,但這兩部文獻幾乎代表了日本在最初接觸和吸收中國文化時的基本姿態。對此,日本歷史學家東野治之做過如下論述︰
《論語》與《千字文》被《古事記》列舉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二者已經普及。也有可能因為二者是初學者所用的基本文獻。當我們離開歷史事實講述學術的起源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敘述當時的初級課本何時、由誰開始傳播。所以,這個記載,應該看做是由歸化系氏族繼承和傳播的初級讀書方法,被當作學問傳播的形式體現出來的結果。《古事記》編纂開始的七世紀後半葉,是我國在大化前期以來發展的官司制度的基礎上正式步入律令官人制的成熟期。即使是在官司制度之下,要做官人的人們毫無疑問必須懂得讀寫的技巧。而天武朝以後律令制度的迅速完善,在依靠檔案處理事務以及表面奉行的儒教理念方面,也需要更多具備一定程度識字能力的有教養的官人。上述學問的形式之所以被廣泛接受的原因,正在於這種實際狀況。這一點我們絕不能忘記。
東野治之的這段文章注意到七世紀日本人的中國觀。東野認為,儘管日本在建立最初的政治體制時大量地汲取了中國文獻所傳播的思想和技術,然而這並不意味日本就是在全面、無條件地吸收中國文化。雖然在表面上尊崇儒教理念,實質上卻偏重於實用。那麼,東野的論述究竟有無依據呢?這一點,似乎有必要從古代日本的對外意識角度進行考察。
迄今為止,在有關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研究中,學者們多著墨于中國文化如何東漸,如何影響日本文化。與此同時卻很少注意到,日本文化自與漢字接觸伊始,就萌生了強烈的本土意識。這種意識的集中體現,就是針對以漢字為表像的中國文化,不斷建構和鞏固本土語言信仰。在眾多的現象和事例中,八世紀著名詩人山上憶良(660-773?)的文學作品可作為一例。
山上是一位曾經以遣唐少錄身份留學長安,歸國後歷任築前守等要職的官僚。《萬葉集》所保留的漢文作品,顯示出山上嫺熟的漢文寫作技巧與深厚的漢學修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上在用漢文漢詩抒發情懷的同時,也用日文寫了大量的作品。其內容反映出山上對本土語言所持有的信仰。例如,《萬葉集》所收作品的內容如下:
原文:神代欲理,雲傳久良久,虛見通,倭國者,皇神能,伊都久志吉國,言靈能,佐吉播布國等,加多利繼,伊比都賀比計理。(卷5‧894)
譯文:從神代口口相傳至今的是,我們大和國,是天皇神威之國,言靈昌盛之國。
同樣,另一位同時代的宮廷詩人柿本人麻呂,也就「言靈」有如下的表達:
原文:事靈八十衢夕占問占正謂妹相依。(卷11‧2506)
譯文:我在言靈多驗的八十街口問蔔,結果理想,阿妹定會與我相依。
原文:志賀島倭國者事靈之所佐國敘真福在與具。(卷13‧3254)
譯文:我們大和國是言靈保佑之國,願其長久平安。
對上述作品中出現的「事靈=言靈」一詞,十八世紀日本國學家契沖曾作過如下的詮釋:
言靈者,謂詞之有靈驗也。
言靈乃目不可見之神靈也。
古登(ことkoto,筆者注)者與事字訓義並通。蓋至理具事翼輪相雙。有事必有言,有言必有事。故《古事記》常多通用,……言即心也。
作為被後世所譽為「國學五大人」之一,契沖在學術領域的主要建樹,在於扭轉了江戶以前漢學主導的學術潮流,從日本本土語言的角度重新詮釋日本古典。也正因為如此,契沖的語言文字論中不時地出現貶低漢字、褒揚日語的言論。例如,在《倭字正濫抄》序中,契沖為了突出「言靈」的優越性,特意以古代中國稱日本為「倭奴國」為例,指出「倭奴」二字只為表音,因為「中華人為奴僕之奴,未知方言也」的緣故,才使用了這兩個漢字。接著,契沖就針對漢字所發明的日語假名的意義作了如下的論述:
雖然如此,上世淳樸,而無文字。蓋待中華耶。譽田天皇馭宇之世,百濟國奉詔供博士王仁。從是浸親紙墨假字記和語。後及通中華逾究精奧。然和字之學闃無所聞。學書黃口者,寫難波津之什,摹安積山之唫。才為始步,暨於我埜山准竺墳字母有四十七言,裁以呂波歌。世人溥學至今則之。以有限字,述無窮心。可謂千古絕妙百世依憑。
契沖這種重視「言靈」信仰而貶低漢字功效的觀念被後來的國學家賀茂真淵(1697-1769)所繼承。例如,賀茂就「言靈」的意義首先做了如下解釋:
因我皇國不使用文字,是言的國度,故尊稱其語中有魂也。
言靈者,謂言中有神之禦靈相助也。
事即言也,靈即神之禦靈也。
繼而在《祝詞考》一書中強調「言事相通」這一原理,同時還在語言哲學論著《語意》中將「言」作為優於漢字的存在來看待:
《古事記》、《日本書紀》及其他古典,因其傳承了古語,雖使用漢字,只要得其旨意,文字之違無須介意。字雖違而古意傳也。……吾邦之古典,雖以喧嘩浮飾之漢字記錄,但因其所記為吾邦之事,如不以吾邦古代之「意言」讀之,如何可以瞭解。
這裡,賀茂將「意言」即「言」=「ことkoto」與漢字對立起來,認為漢字是「喧嘩浮飾」與「古意」相違的東西,只有「意言=言」才是古代的事實。賀茂在文中使用的「意言」,日文訓作「こころことkokorokoto」。如前所述,「こころkokoro」一詞在古日語中作為「意」、「心」、「情」等漢字的和訓被廣泛使用。
上述的二者對「言靈」的解釋,並非獨創之見。其根源來自日本傳統的語言觀。古代日本人視語言「言」與精神「意」、「情」、「心」為一體,而且這種意識同時也可以與具體事物「事」被等量齊觀。契沖「言即心也」與賀茂「事即言也」的觀點,正是基於上古日本的「言靈」信仰的,視「精神」與「物質」為等同之物的古代思想的再發掘。
賀茂也是在承襲「言靈」信仰的基礎上試圖建立日本獨特學問體系的首位人物。賀茂在《語意》中開卷伊始就將日本描述為:
吾日出之國,以五十聯音為言,以口述傳承萬事之國。
緊接著,又以「言」、「字」(漢字)對立的形式來強調中日文化的差異:
或問:吾國為言之國度,然如若未用他國(=中國,筆者注,以下同)文字記載,則何以知遠古以來代代傳承之事?答曰:此乃汲末流之濁水而不知本源之清澄也。吾國人心正直,事言並寡。所言必無惑,聞之必無遺。言而無惑則聞者悉得,聞而無遺則世代相傳。民心正直則君主之旨令鮮少,苟有旨令,則如春風遍及全國,如春雨滋潤全民。故此吾國天意人願以言語相傳而無所違背,世世代代共為一體。于漢字有何用焉?有何益焉?
賀茂在論及漢字的功用時,特意以「汲末流之濁水而不知本源之清澄」的比喻來否定依循漢字撰寫的日本史書瞭解歷史的態度。而這個比喻,與章太炎批評日本人缺乏漢字的素養時所用的比喻恰恰相反:
或言日本雖用漢字,淩雜無紀,支絀亦可睹矣。漢人守之,其不利亦將等於日本。此未辨清濁之原也。日本語言,故與漢語有別,強用其文以為表識,稱名既異,其發聲又才及漢音之半,由是音讀、訓讀,所在紛猱。及空海作假名,至今承用,和、漢二書,又相羼廁。夫語言文字出於一本,獨日本則為二本,欲無淩雜,其可得乎。漢人所用,顧獨有漢字耳。古今語雖少不同,名物猶無大變。……若循《法言》、《切韻》之例,一字數音,區其正變,則雖謂周、漢舊言,猶存今世可也。況其文字本出一途,不以假名相雜,與日本之淩雜無紀者,阡陌有殊。憂其同病,所謂比擬失倫者哉。
一位將依附漢字稱為「汲末流之濁水而不知本源之清澄」,一位卻將漢字使用的不規範性稱為「未辨清濁之原」。兩個例子,極具代表性地顯示了中日知識份子對待漢字的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
三、漢字與「和魂」
契沖與賀茂視「言」與「心」、「意」、「情」為等同之物的語言觀,為日本近代學術思想竭力排斥漢字,向宗教色彩濃厚的,「古言」=「和魂」的方向發展奠定了基礎。將這種語言觀與民族主義思想相結合並理論體系化的,就是賀茂的弟子本居宣長。
在本居宣長的著作中,學術隨筆《葛花》主要以問答的形式,闡述本居對中國思想的觀點。「葛花」意為醒酒的草藥,本居就書名定為《葛花》,在卷首有如下的說明:
天下學者,飲千年漢籍之毒酒,且沉湎其文辭之甘美,眾皆醉亂無一醒者。偶有依直毘神之靈而醒之人,吾欲促其猛醒,然其猶言吾非醉,而愈發狂言。稍醒者又更飲毒酒,愈益沉醉。因不堪入目,故采來葛花,令其嘗之以醒毒酒。
這裡所說的「漢籍之毒酒」,本居明言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的「聖人」之書。在本居看來,這些中國的書籍,無異于「甘美的毒酒」,愈飲愈醉,最終會導致自我意志及意識的喪失。所以,重要的是不被中國書籍文辭之「甘美」所迷惑,而是要追求作為日本人的自我認同(identity)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包含了「和魂」的日語。例如,在《葛花》上卷中,本居就漢字與日語口語的關係表達了如下的看法:
以言語之傳較之文字之傳,二者互有短長,難分高下。自古及今既慣於文字
之用,故以今世之心觀之,若僅以言傳,萬事難得其確切之情,文字之傳或
優於言語之傳遠矣,持此見者亦必多矣。然觀之上古,其世雖無文字,僅以
言傳,而萬事莫不畢現也。非唯文字,種種器物,古亦無之。經時愈久,新
物愈增。既慣於新物之便,經年曆月,遂生昔無此物則必不便之感。然若本
無之,更無所謂欠缺也。文字之理亦同。皇國有漢字,有片假名,有平假名,
三者若缺其一,則或生不便之感。然漢國本無平假名及片假名,故無之亦可。
欲致意于遠方,因言傳多違本意,故特以文字傳之,此文字之德也。然又有
文字之所難表者,則示之以物,並口述原委以達其意。此亦非言傳之德耶?
以此觀之,上古之事若悉以言傳,則其精詳之狀亦必悉傳至今也。且漢人亦
歎書不盡言,故知文字之傳,所失者亦不可謂不多耶!……無文字之世,乃
為無文字世之心,故雖以言傳,與有文字世之言傳亦大不同也,此絕非空虛
浮華之言。在今之世,識文字者,萬事托於文字,而不記其事;不識文字者,
反詳記其事,此其理也。況古語有言,皇國乃言靈保佑之國,言靈昌盛之國。
是故吾國言語之神妙,冠絕萬邦也。
前半部分,本居似乎是在公正地評價「言語」與「文字」的不同功能,且不吝於讚賞「文字」之功德。然而,當話題涉及到「皇國古語」這一神聖的領域時,「言靈」信仰支配的語言觀,很自然地發出了「吾國言語之神妙,冠絕萬邦也」的讚歎。本居的這種「皇國古語」觀,貫穿於其所有的國學語言論之中。
「言靈」信仰與日本民族主義思想的結合,是隨著「和魂」這一概念而產生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據傳由十二世紀日本政治家兼學者菅原道真所撰《菅家遺誡》中如下一段論述,被作為日本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理念來看待:
凡神國一世無窮之玄妙者,不可瞰而窺知。雖學漢土三代周孔之聖經,革命之國風,必深加思慮也。凡國學之大要,其論雖涉古今,究天人,自非和魂漢才,不能聞其閫奧矣。
在這裡,菅原強調,日本人雖然可以學習「漢土=中國」的三代周孔的經典,但是,日本的政治體制卻應該慎重對待諸如孟子「易姓革命」類的思想。所以,作為日本人一定要首先擁有和保持「和魂」,將中國的學問作為「才」即可。菅原道真著作中的這段文字,後來被證實是由江戶學者在編篡菅原道真著作時加入的。其動機是因為菅原道真在歷史上曾經反復強調日本文化的主體性,並主張廢除遣唐使,中止與中國往來。
這裡要注意的是如何解釋「和魂」這一概念。在古代日語中,「魂」與「靈」同義,均訓讀為「たまtama」。所謂「和魂」,可釋作「日本精神」或「日本心、日本靈魂」。最初使用「和魂」這一概念的,是小說家紫式部。紫式部在小說《源氏物語》中,曾經通過主人公的口說出「只有以中國的學問為工具,方可使大和魂有用於世」的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和魂」這一概念早在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其內涵一直較為含蓄模糊。而本居宣長對「和魂」的解釋,卻擯棄了前人所使用的抽象含義,而是具體地將「和魂」與日語本身結合在一起。例如,在其國學指南著作《初山踏》中,本居強調初學國學的日本人,要通過仔細閱讀和研究《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二書來鞏固「大和魂」:
潛心閱讀此二書,則可令大和魂堅固不破,以防漢意之侵襲。有志於學道者,第一之要務乃清除漢意儒意,堅固大和之魂。
這裡,本居非常具體地指出,「和魂」是蘊藏在《古事記》與《日本書紀》這兩部經典中的,必須拋棄一切外來思想的先入觀,以平常心去潛心閱讀才能獲得的東西。
那麼,究竟如何來獲得「和魂」呢?對此,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本居指出隱藏在《古事記》與《日本書紀》漢字漢文之中的「古言」就是「和魂」。而且他又將「古言」與「古道」相連接,強調獲得了「古言」就等於獲得了「和魂」,同時也就掌握了「古道」。此外,別無他物可以替代:
欲知古道必先學古歌,讀古歌然後習古文。欲作古文,知古言,則需細讀《古事記》、《日本書紀》二書。不知古言則不知古意,不知古意則難知古道。(中略)言、事、心三者近同一之物也。蓋賢者所言之言,所行之事相應而賢;拙者所言之言,所行之事拙也。又男子所思、所言、所行之事為男子也,女子所思、所言、所行之事為女子也。而時代之別,亦與之相似。上古之人有上古之事,中古之人有中古之事,後世之人有後世之事。唯其所言之言、所行之事及所懷之心同一也。在今之世,如欲知上古之人之言、事、心者,其言可求諸於歌,其事可求諸于史。其史亦由言記,其心亦應由歌而知,故唯言矣。則言、事、心三者乃同一之物,故後世之人,如欲知古人之心、古人之事,求諸古言、古事可也。所謂古道者,具在二典(《古事記》、《日本書紀》,筆者注)之中,得古言、古歌而讀之,其道自明也。
這裡,我們已看不到有關「和魂」的任何曖昧及形而上的解釋。按照本居的邏輯,《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古言」和「古歌」,因為記錄了古代日本人的「言」,所以也就保留了日本人的精神「和魂」。既然「言、事、心三者乃同一之物也」,那麼,掌握了這些古典中的「言」,自然也就擁有了「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