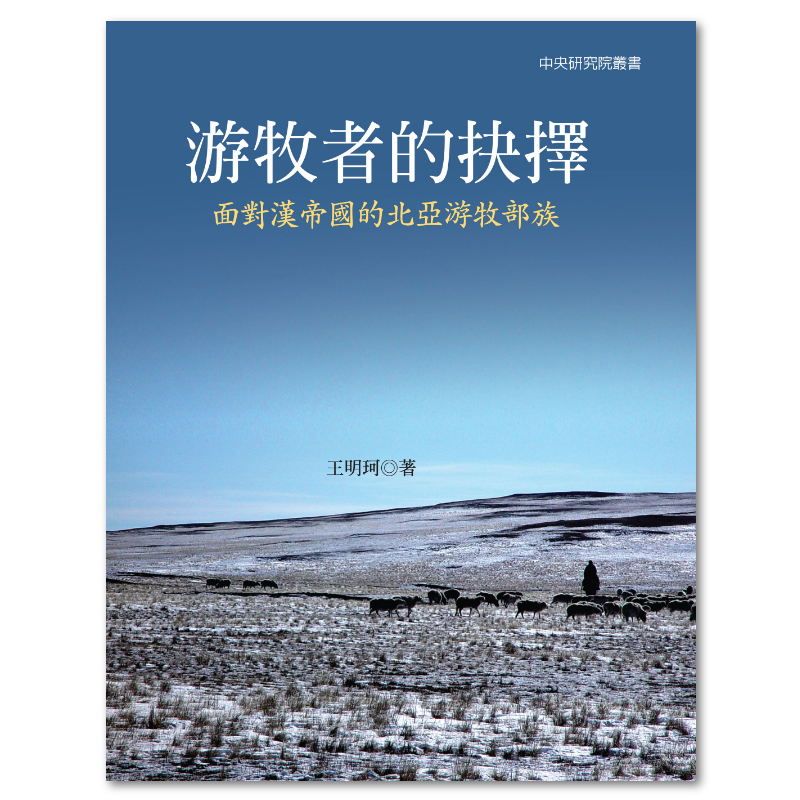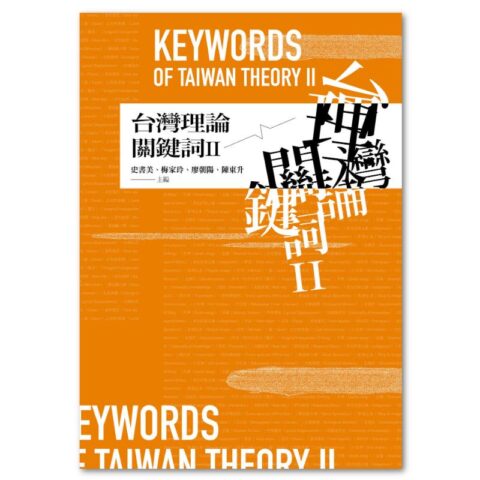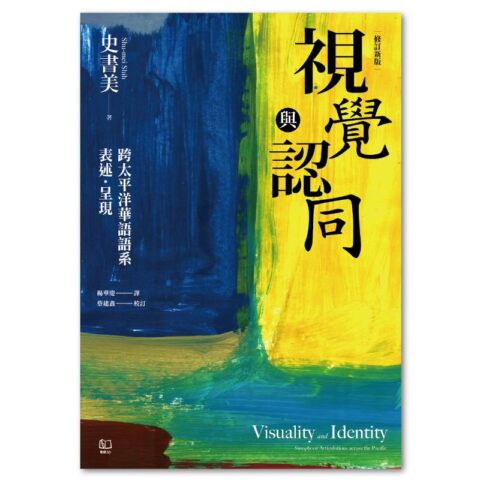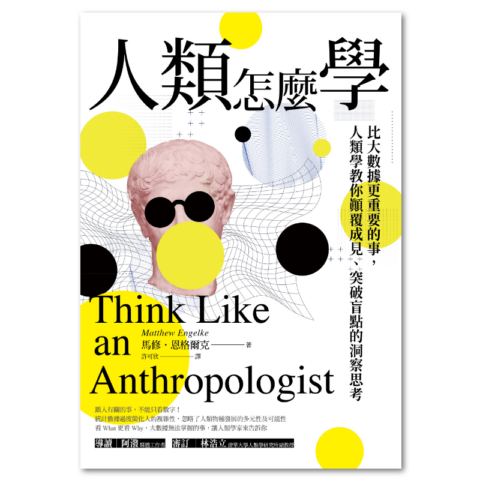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
出版日期:2009-01-06
作者:王明珂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04
開數:18開西式橫排
EAN:9789860170054
系列:中央研究院叢書
已售完
本書以人類學的游牧社會研究為基礎﹐重新詮釋考古與文獻所見的漢代中國北方三種游牧人群社會――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與森林草原游牧的鮮卑與烏桓――以及他們與漢帝國間的互動。本書說明這些游牧人群﹐為了適存於華夏邊緣形成所造成的新情境﹐而發展各自的專化游牧生計﹐並形成特定社會政治組織﹐西羌的「部落」﹐匈奴的「國家」﹐以及烏桓﹑鮮卑的「部落聯盟」。他們藉此與漢帝國互動﹐在漢代形成不同的北方華夏邊緣﹔後來這三種北方華夏邊緣﹐又不同程度的延續至明清時期。
作者:王明珂
王明珂,1952年生於台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92)。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範圍是中國民族─羌族與中國西南民族,北方遊牧社會之歷史與人類學研究;研究主旨在於人類生態,社會認同與區分,及相關之歷史記憶與文化表徵等問題。1994年以來,多次到川西羌族地區進行田野研究。曾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與東吳大學等校教授歷史與人類學相關課程。
自序與謝詞
前言
第一章 序論:游牧經濟與游牧社會
自然環境
畜產種類及其動物性
畜產構成
游牧與其移動模式
游牧生產﹑分工與消費
輔助性生業:狩獵、採集、農作、貿易、掠奪
游牧社會組織:家庭與牧團
游牧社會組織:家族、氏族與部落
分枝性社會結構、領袖威權與外在世界
第二章 中國北方游牧經濟的萌芽
有關歐亞大陸游牧起源的一些問題
考古學有關中國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討論
西元前15至前3世紀中國北方的人類生態與社會變遷
內蒙古中南部與晉陜之北
西遼河流域與燕山地區
甘青之河湟地區
環境﹑經濟生態與人類社會
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
游牧「國家」問題
地理與自然環境
牧區與畜產
季節移牧活動
匈奴牧民的輔助性生計活動
游牧經濟下的匈奴國家與社會
匈奴牧民在國家與部落間的生存抉擇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河湟地理環境與人類生態
河湟羌人的游牧經濟
畜產構成
季節移牧
輔助性生計活動
羌人部落及其社會
羌人之種號與豪酋之名
部落結構
部落領袖之決策權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擇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烏桓與鮮卑
秦漢時期遼西的地理環境
烏桓、鮮卑的游牧經濟
畜產構成
季節移牧與狩獵﹑農作
貿易與掠奪
烏桓、鮮卑的部落社會
第六章 游牧部族與中原北疆歷史
魏晉隋唐的中原王朝與炎黃子孫
漢代以後游牧部族與中原帝國的互動
長城邊緣地帶
河湟與西北邊郡
游牧國家興衰﹕歷史循環論
歷史本相與表相
游牧國家﹑部落與部落聯盟
歷史本相的延續與變遷
結語 邊界‧移動‧抉擇
參考書目
索引
表目次
表一 阿穆拉貝都因人各氏族所宣稱的祖源關係
表二 布里雅特蒙古各氏族部落祖源關係
表三 漢軍與匈奴戰爭中擄獲匈奴畜牲記錄
表四 史籍所見匈奴入寇漢帝國之發生季節
表五 漢羌戰爭中漢軍擄獲羌人畜牲記錄
表六 史籍所見羌入寇漢帝國之發生季節
表七 史籍所見鮮卑與烏桓入寇漢帝國之發生季節
我從前寫過幾篇有關中國早期游牧社會的文章﹐多年來一直希望能在此主題上完成一更整體的研究。然而從1995年開始進行羌族田野研究以來﹐我一直關注的是歷史記憶﹑族群認同﹑邊緣研究﹑文本分析﹑歷史心性等問題。近三年來﹐我又較積極的從事中國早期游牧社會研究﹐主要是為了履行兩個承諾﹕一是﹐我在10餘年前修習游牧社會人類學時﹐對自己許下的將以此研究中國游牧社會的承諾﹔二是﹐對我的蒙古朋友參普拉敖力布教授的承諾。
1992年我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回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先是不能免俗的花了兩年升等為副研究員。隨後在1994年我第一次進入中國﹐迫不急待的希望能進行一些田野研究﹐使得我在哈佛所習的人類學知識更為完整。在北京﹐我認識了中央民族大學的參普拉敖力布﹐一位與我同年歲的蒙古學者。我們一見如故﹐我與他談了許多關於人類學游牧社會研究之情況﹐他十分感興趣﹐我們也相約合作進行有關蒙古游牧的研究。那一年離開北京後﹐我又到西安與青海西寧﹐最後進入川西的汶川。在汶川﹐我決定以川西羌族作為往後研究的重心﹐就這樣開始了將近十年的羌族田野調查與研究。隨後幾年我與參普拉還有些書信往來﹐路過北京還到他家中喝馬奶酒﹐後來因工作繁忙便中斷了聯絡。
2002年有關羌族的研究即將完成時﹐我再與參普拉教授聯繫﹐但卻從他夫人的來信中得知他已在一年前去世。據說是有一天他結束田野研究返回家中﹐晚上感到不舒服﹐經緊急送醫後第二天便去世了﹔醫生說是過於勞累。近幾年我獨自進行些簡單的游牧田野觀察﹐並完成這本書﹐從某一角度來說也是為了完成和朋友間的許諾。促使我進行此研究的﹐不只是因為我與參普拉間的朋友感情﹐更因為我深深感受他以及其他蒙古朋友們對蒙古族人及其游牧文化的關懷。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以人類學的游牧社會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徑﹐對中國早期游牧社會――漢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鮮卑與烏桓――作一些新考察。這個研究有多重目的。第一﹐提倡一種結合人類學游牧社會知識的游牧民族史研究﹔第二﹐藉著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來增進我們對人類早期游牧社會的認識﹔第三﹐促進游牧及定居農業文化人群對彼此的了解﹐並期望因此對中華民族內的漢蒙﹑漢藏關係有些貢獻。由最後這一點來說﹐此與我多年來所從事的羌族以及其它有關華夏邊緣的研究要旨是一致的。
在研究過程中﹐我曾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我的學生蘇布德及她在呼倫貝爾草原上的哥哥們﹐特別是布仁特古斯先生﹐曾幫助我在新巴爾虎右旗進行草原游牧觀察。內蒙古克什克騰旗的寶音特古斯先生﹑朵日娜女士等人﹐以及參普拉的夫人斯琴格日勒女士﹐曾協助我在此的田野訪談與考察工作。川西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草原上的資深獸醫鄭文興先生﹐曾陪伴我在紅原﹑若爾蓋進行藏族游牧考察﹐並授我許多有關當地牲畜生物性與疾疫方面的知識。我的朋友考古學者羅豐教授以及王欣教授﹐曾陪同我在寧夏﹑新疆﹑內蒙古等地造訪各個博物館及考古遺址﹐穿越準葛爾盆地﹑毛烏素沙地與長城﹐觀察賀蘭山﹑陰山﹑天山與巴里坤等地的自然環境生態與古人類活動遺跡。對於以上這些朋友﹐我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本書有關的田野﹐受歷史語言研究所撰寫專書計劃經費的支持﹐我在此向該機構及相關人士致謝。本書主要內容完成於2006-2007年我在哈佛燕京學社任Research Associate的期間﹐部分內容曾在該校人類學系之演講中發表﹐在此我對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杜維明教授﹑Peter Kelley教授與人類學系Rowan Flad教授等表達謝意。
前言
當1980年代末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之時﹐曾在人類學系修習湯瑪斯.巴費爾德(Thomas J. Barfield)教授講授之 “游牧社會之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Nomadism)。從那時起﹐我便深深為這門學問所涉及的一些問題所吸引﹐後來我更廣泛閱讀相關民族誌與理論著作。這些閱讀與問題思考﹐當時對於我在人類學各領域的學習﹑體悟都有相當幫助與啟發﹐因此最後游牧社會人類學研究也是我博士資格考的三個主題學科之一。
我與許多人一樣﹐對 “游牧民族” 最初的興趣來自於一些浪漫想像。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過著自由不拘的生活――“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中國文人對這種無羈無束生活的浪漫寫照。然而﹐人類學所見的游牧社會首先便讓我們擺脫這些浪漫想像﹐強調這是人們利用邊緣﹑不穩定自然資源的一種經濟﹑社會生態體系――生活中處處充滿危機與不確定﹐毫無浪漫可言。人們對游牧社會的另一個誤解為﹐“游牧” 相對於農業而言是一種原始的人類經濟生產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屬於由 “漁獵” 到 “農耕” 的中間進化階段。事實上﹐正因為游牧所利用的是邊緣﹑不穩定的自然資源﹐因此它需要人們高度技術性的對自然(地理環境與生物)的理解與掌握﹐並配合經濟﹑社會各方面之種種精巧設計――此遠非8000年前或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農民所能企及。因此在人類歷史上﹐世界幾種主要類型的專化游牧都大約出現在公元前1000至前400年之間﹐遠較原始農業的出現為晚。人們對游牧的第三個誤解是﹐似乎 “游牧生活”﹑“游牧經濟” 代表一些同質性的經濟生產與生活方式。事實上﹐游牧是人類對於環境的一種精巧利用與適應﹐因此各種不同緯度﹑地形與植被環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樣性(nomadic altenatives)是人類學游牧研究的重點之一。最後也是最普遍的﹐人們對游牧人群有一種刻版意象﹐表現在西方卡通電影 “花木蘭” 中匈奴人猙獰如野獸般的造型﹐表現在將他們描述如 “狼” 的通俗著作之中。在本書中我將說明﹐由於游牧經濟及相關的社會組織特質﹐面對定居敵手時游牧者亦有其脆弱的一面。
人們對游牧社會的不了解或誤解﹐主要是由於身處於世界主要文明圈的人大多是定居農業文明及相關文化下的產物。以此而言﹐游牧社會研究更大的意義在於它可以挑戰﹑刺激我們的知識理性﹔因於這樣的刺激﹐我們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對於熟悉定居文明社會價值體系的 “我們” 來說﹐游牧社會及其文化所造成的 “異例”(anomaly)或 “陌生感”﹐挑戰我們許多既有的信念﹕如群體的團結與社會穩固﹐財富的爭奪與累積﹐對領袖的忠誠﹐勇敢奮進的戰場道德﹐尊重社會階序權力等等。因此人類學游牧社會研究的相關議題探討――如領袖威權與脅迫性政治權力(coesive powers)的由來﹐平等自主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的人類經濟生態背景﹐分散性社會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及其功能等等――皆為一般性人類社會研究提供另類民族誌資料﹐以及可能產生反思性新知。
譬如人類學者費德瑞克.巴斯(Fredrik Barth)最為人所知的是其在 “族群研究”(ethnicity study)上的開創性見解﹐表現在他1969年所編廣為學界引用的《族群與其邊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書及他為本書所寫的導論上 。而巴斯也是游牧社會研究者。在他1961年發表的《南波斯的游牧人群》(Nomads of South Persia)一書中﹐巴斯已注意到這些游牧人群在族群認同上的分歧與多樣性﹐以及注意到其族稱﹑語言與認同的變易性 。這些﹐顯然對後來他所提出的族群研究新方向――強調族群認同的主觀建構性﹐以及族群邊緣之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與因時變易的(situational)本質――有一定的影響。另一個例子是﹐西爾弗曼(Marilyn Silverman)與古立弗(P. H. Gulliver)在1992年共同編著《探索過去﹕以愛爾蘭研究為例的歷史人類學》(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在這本書的導論中﹐兩位編者對 “歷史人類學” (historical anthropology)有很精采的論述 。而古立弗這位資深英國人類學者﹐過去也是游牧社會的研究者。早在其1955年發表的《家庭牧群》(The Family Herds)一書中﹐古立弗已注意到一游牧家庭的家族譜系記憶在父子兩代之間便有相當差別。他指出﹐在那父親死後﹐他兒子的家族史版本將成為 “正確的” 家族歷史記憶――他稱之為 “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 。這種思考――將 “過去的事實” 視為在現實下被爭辯及可被遺忘﹑改變的記憶――無疑是歷史人類學的先聲。而我自己﹐近十餘年來一直從事於有歷史人類學或社會記憶研究傾向的族群認同研究﹐除了受巴斯與古立弗等人之相關研究影響外﹐多少也與此二位學者相同的受到游牧社會研究的啟發。
在這一本書中﹐我將以結合多項學科的游牧社會研究為輔﹐探討漢代中國北方的多元游牧社會。這樣的研究有多重意義。首先﹐我希望藉著中國北方早期游牧社會的例子﹐介紹人類學游牧社會研究的一些問題旨趣與方法。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整體人類學中﹐游牧社會研究從未得到主流地位。甚至在1970年代以後﹐由於游牧世界之變遷與戰亂﹐人類學家在此失了大多數的田野﹐因而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並不豐盛。可以說﹐這是一個日薄西山的學術專題。然而有許多的理由使我相信 “游牧” 仍是一個重要議題﹔不僅因為在新的社會環境與科技下﹐有些人群仍努力調適﹑修正並踐行這種經濟模式﹐也不僅因為這些當代游牧被視為破壞環境的元兇而受到許多爭議與指責﹐更因為世界各傳統游牧地區近代以來大多在戰爭﹑饑饉﹑貧困與政治紛擾之中。此顯示﹐近代以來的世界政局﹑科技與相關意識形態變化﹐皆不利於游牧經濟及其人群的存在與獨立發展。而人們對於游牧社會的認識不足﹐常使得許多對傳統牧區的救濟﹑補助﹑改良徒勞無功﹐許多對游牧的指責﹑怪罪也經常是無的放矢。
本書所提及的游牧社會人類學研究﹐事實上並不限於狹義的 “人類學”――除了人類學傳統的民族誌(ethnography)調查研究外﹐它還包括環境生態﹐動物性與動物行為﹐以及相關的考古與歷史等研究。也就是說﹐這個研究傳統不僅強調綜合各種學科知識以了解當代游牧社會﹐也關心游牧社會在人類歷史上的起源﹑發展與其近代變遷。便是這樣的整體性與歷史性﹐使得它很適於被應用在中國北方游牧社會的研究上――這兒不但有多元的游牧社會﹐歷史上本地各種游牧政治體與中原王朝間又有長期的緊密互動﹐因此漢籍文獻對他們的活動留有大量文字記憶。早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漢代﹐幾種不同類型的游牧社會便已出現在北亞歷史舞台上﹐並從此與南方中原王朝展開模式化之互動。因此﹐透過研究漢帝國北方游牧社會之形成及其與帝國間的互動﹐最能表現人類學游牧社會研究對環境生態﹑草食動物之動物性﹑人類經濟活動與社會組織﹑游牧與定居人群關係﹐以及相關歷史等等之整體研究旨趣。
其次﹐我希望藉著本書之作﹐使得中國關於古代游牧社會之豐富文獻記載﹐特別是其所呈現的多元游牧社會類型與豐富的 “史事”﹐對於我們了解世界早期游牧社會有些貢獻。我對此稍作說明。如前所言﹐許多學者都對特定形式(如駱駝游牧)﹑特定地區(如東非)之游牧社會起源﹑形成與發展變遷等問題很感興趣――這是一個涉及多種學科的探索。運用比較動物學﹑考古學及古氣象學等知識﹐學者探討世界各地游牧經濟的起源背景與過程。然而由於文獻記錄缺乏﹐游牧生產活動之特質――所需工具少﹐居住遺痕也極少――又使得其考古遺存難以被發掘﹑呈現﹐學者們對於早期游牧社會情況所知十分有限。甚至由於游牧考古遺存多為墓葬﹐藉此片面資料以認識古代游牧社會也可能失之偏頗。然而﹐漢晉時期之中國文獻不僅對北方游牧人群有豐富的記載﹐且這些文獻描述幾種不同游牧生態下的人群――其中最主要的三種類型為鮮卑﹑匈奴與西羌。這雖不是世界最早有關游牧人群的史料﹐但其內涵之豐富﹐描述對象之多元性﹑差異性﹐卻是十分罕見的。這些文獻資料﹐可以填補我們對早期游牧社會認識之不足。藉著古文獻與考古資料﹐以及人類學對游牧社會之研究成果﹐在本書中我將說明 “游牧” 不只是一種生產﹑消費與交換之經濟手段﹐它還需要特定的社會組織﹑社會價值觀來與之配合。在這些社會組織與價值體系下﹐人們基於種種情感﹑動機﹐與一層層外在世界人群互動而產生種種言行與事件表徵﹔這些表徵強化原有的社會體系﹐或導致社會變遷。
最後﹐我希望本書能對中國境內之游牧與定居農業兩種文化人群之彼此了解有些幫助。我所期望的了解﹐建立在情境化的(contexturalized)與具反思性的歷史與人類生態知識基礎上﹐也是對當前中華民族體制下漢﹑滿﹑蒙﹑藏等民族歷史關係的一種新體認。我期盼此知識與理解﹐能有助於促進公平﹑和諧與合作共生的民族關係。我在1997年出版的《華夏邊緣》﹐2003年的《羌在漢藏之間》﹐以及2006年所著《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可說都是這一系列的研究 。在《華夏邊緣》一書中我提出一種邊緣研究法﹐探索發生在華夏邊緣的人類生態與歷史記憶變遷﹐以此了解華夏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羌在漢藏之間》是以羌人與羌族為具體例證﹐說明華夏西部族群邊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變遷﹐以及相關人類生態與社會權力關係背景。《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則是由歷史文本與情境的互映﹐建立一種對華夏及其邊緣――也就是 “炎黃子孫” 與其 “兄弟民族”――之反思性歷史新知。
在這本書中﹐我探討的對象是華夏最古老的一個邊緣﹐華夏北方邊緣。在《華夏邊緣》中我曾提及﹐形成華夏認同最主要因素便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左右發生在黃土高原之北的人類生態變化。也就是說﹐華夏的形成與黃土高原北方邊緣人群之游牧化二者相生相成。這樣的歷史背景與人群分化﹐造成兩千餘年來帝制中國社會上層人群根深柢固的定居文明偏見﹐乃至今日主體社會對 “游牧” 的認識仍相當不足。認知不足﹐多少也使得各種政策之制定與推行可能難以深入考量北方﹑西方游牧世界的特殊社會情境。相對的﹐傳統上華夏周邊游牧文化人群對於 “華夏” 以及中原王朝也缺乏深切認識。強調事件與事實的歷史書寫傳統﹐也造成並強化農牧人群間的區分與對立。在這本書中﹐我將歷史事件當作表相(表徵)﹐以探索造成歷史上一連串 “單于南下牧馬” 與 “漢將直搗黃龍” 事件的人類生態本相。我將說明﹐漢代中原王朝與其北方游牧部族之互動曾造成三種不同的華夏邊緣﹐也是三種人類生態本相――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蒙古草原的匈奴﹑東北森林草原的鮮卑與烏桓。後來在歷史上發生的一些模式化歷史事件﹐許多都可溯及形成於漢代的此三種華夏邊緣。我希望如此藉由人類經濟生態角度所理解的過去﹐可以讓不同地域﹑文化﹑經濟模式之人群能更深入的了解彼此﹑體認現在﹐因而能規劃﹑期盼更好的未來。
研究文獻回顧
世界一般性游牧社會的人類學或民族學研究﹐除了中國以外﹐主要有兩個學術傳統。一是﹐歐美人類學界的游牧社會研究﹐另一則是前蘇聯民族學者的游牧社會研究。兩者在田野﹑研究方法與問題旨趣等方面都有些差異﹐也有相同之處。東非﹑西北非﹑阿拉伯世界﹑西亞﹑中亞等地是歐美人類學游牧研究的主要田野。前蘇聯學者的田野﹐則主要是其境內與邊緣的游牧人群。前蘇聯民族學者的研究較宏觀﹐長於結合多學科﹐進行具歷史深度的理論探討。歐美人類學者則在其民族誌研究傳統下﹐長於深入參與觀察﹐作細膩的民族誌描述及相關社會理論探討。他們共同之處則是﹐強調游牧是一種環境資源﹑動物與人之相互依存﹑社會組織與結構﹐以及牧民與外在世界之關係﹐四方面緊密結合的人類生態。
雖然我的學術傳承主要來自歐美人類學的游牧研究﹐由於本書探索的主要田野――蒙古草原及其周邊森林草原﹑高山河谷草原的早期游牧人群――與前蘇聯學者研究的區域﹑人群有相當重疊或接近﹐後者的研究成果自然是我在研究及寫作本書時的重要參考資源。更重要的因素是﹐前蘇聯學者的歷史研究傾向也與本書的主題相合。除了一些考古文獻外﹐與本書關係最深的是兩本已譯成英文的俄文著作――安納托利・卡扎諾夫(Anatoly M. Khazanov)所著的《游牧人群與外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以及塞伏晏・凡虛坦因(Sevyan Vainshtein)所著之《南西伯利亞的游牧人群﹕突伐人的牧業經濟》(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卡扎諾夫這本結合前蘇聯與歐美游牧社會研究的鉅著﹐除了討論一般性的游牧社會特質外﹐主要探索不同地區﹑類型之游牧社會與其外在世界(主要為定居人群國家)之互動關係。他最主要的觀點是﹕游牧是一種不能自己自足的(non-autarchy)經濟生產模式﹐因此游牧社會人群與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種的互動模式﹐以獲得外來資源。在以下本書中﹐我將說明鮮卑﹑匈奴﹑西羌的游牧經濟﹐他們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他們與漢帝國間不同的互動關係﹔可以說本書許多論述﹐都是在卡扎諾夫與其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所作的進一步探討。凡虛坦因的著作﹐除了北亞游牧經濟的歷史背景外﹐對我而言最珍貴的是這本著作的田野地區 “圖瓦” (Tuva﹔中國文獻所稱的薩彥嶺地區)﹐其地理環境包含森林﹑森林草原﹑高地草原等不同的游牧生態區﹐因此對於探索﹑比較不同生態環境中的游牧經濟有相當大的助益。
有關戰國至漢代中國北方游牧人群的歷史﹑考古﹑藝術之研究﹐中﹑西方及日本學者之著作卷帙浩繁。這其中﹐許多都是本書的重要參考文獻﹐但是以游牧經濟生態觀點探討此一時期游牧社會的著作卻不多。1940左右出版的兩本鉅著﹐日內・格魯塞(Rene Grousset)所著的《草原帝國﹕中亞歷史》(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與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所著的《中國的內亞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仍為非常值得參考的文獻 。尤其是﹐拉鐵摩爾之書中許多問題的探討及見解――如他強調經濟生態與歷史的關係﹐如他分別探討蒙古草原﹑滿洲﹑西藏等地不同的人類經濟生態﹐如他注意華夏之擴張與北方游牧世界相生相成的關係等等――都對我有相當的啟發。在本書中我將延續拉鐵摩爾的相關研究討論。1950年代漢學家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所著的《征服者與統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 ﹐該書將中國周邊游牧社會以其牧養動物種類不同而區分為三種類型﹕藏系(Tibetan)﹑蒙古系(Mongol)與突厥系(Turkish)。他說明此三者社會結構之差異﹐如以牧馬為主的突厥系民族較進步﹐社會分化程度高﹐也最有能力建立游牧國家等等。雖然這樣的分型過於簡化﹐但他注意牧畜種類﹑游牧移動類型與游牧社會組織的關係﹐並以此探討游牧國家的形成﹐這也是我在本書中將進一步探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