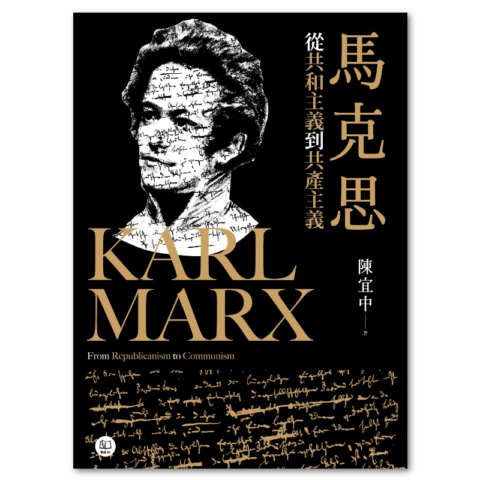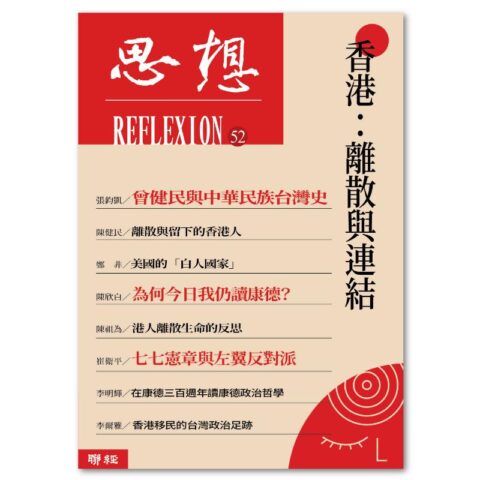韋伯方法論文集(精裝)
出版日期:2013-03-14
作者:馬克斯‧韋伯
譯注者:張旺山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728
開數:18開(高23×寬16.8cm)
EAN:9789570841466
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已售完
韋伯──近代社會學之父
西方現代社會學及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
本書對於瞭解韋伯在「哲學」與「宗教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的概念,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韋伯對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與邏輯學的反省,值得關心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領域中哲學概念的讀者費心細讀。更重要的是,韋伯探討的主題不侷限於一般所說的「方法論」問題,而是擴展到了知識理論與邏輯學的分析、乃至更根本的「知識」或「科學」的意義問題。
在〈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一文中,韋伯使用直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實例探討許多相關連的「基本的邏輯-方法學的問題」。〈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則討論「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對於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探討的主體:「資本主義的“精神”」,是如何被建構及研究的議題,可自〈「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一文中一窺端倪。。對於如何掌握「歷史學的對象是什麼」及「歷史學之邏輯上的本質」這類與研究工作息息相關的問題,韋伯也在本書中作了詳細討論。
本書另外收錄韋伯對當時新康德主義法哲學家史坦樂(Rudolf Stammler, 1856-1938)及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 1844-1931)著作的評論。其中論及韋伯的方法論思想中最重要的側面,包括如何在文化研究中對「經驗上的詮釋」或「釋義學上的詮釋」這二條進路做出區分、「事實」與「價值」的區別、「價值關連」學說、研究客體之建構,以及「理想典型」的概念等。
最後,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一文中,韋伯提出對於「價值中立」這個概念提出最深入、細膩、且完整的分析與論述。韋伯認為知性、倫理與心的判斷各有其必須遵守的法則,不能以知性的認知結果去譴責心的感受或倫理判斷。心和倫理判斷是不受指揮、也不能被指揮的,也由此可知,知性的法則的侷限。這種「知、情、意」三分而各有其「固有法則性」的想法,可以說是韋伯的思想的「人學基礎」。
作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德國國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法學家。儘管是法學出身,一生從事的正式教職都是國民經濟學的教職,且在1903-1918的長達15年間,韋伯還是一個學院外的學者,但韋伯的學術興趣與成就卻幾乎涵蓋了整個的文化與社會科學,其著作對後世的影響既深且廣,難以歸類。韋伯生前著作多以文章形式發表,直到過世前不久才開始集結成書,死後由其遺孀與學者陸續集結出版。韋伯不僅是在學術上多方面具有原創性的學者,也是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他除了是「理解的社會學」的建立者,並在許多社會學分殊領域(如: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支配社會學、音樂社會學等等)有重大的貢獻之外,在經濟史、社會史乃至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等方面也都有重要的成果;除此之外,他對當時德國的政治體制、政策以及俄國革命的分析與論述,也都是不可忽視的精神遺產。韋伯最著名的著作,乃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本書翻譯的文章,則主要收錄於《科學學說文集》。新編的《韋伯全集》分三部分(「著作與演說」、「書信」與「講演與筆記」),預計出版47冊,1984-2012已出版33冊。
譯注者:張旺山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1956年生於台北縣烏來鄉。台大哲學系、哲學研究所畢業後,先後獲教育部公費及德國自由民主黨Friedrich-Naumann-Stiftung獎學金,於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 Bochum)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副修政治學與社會學,博士論文為《文化實在與文化科學:韋伯的方法論與價值學說》(德文)。1993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一年的約聘助研究員,1994年8月起在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任教迄今。主要興趣是政治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哲學、十九世紀德國哲學以及韋伯研究等。
譯者序
中譯本導讀
壹、本書與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
貳、關於本書之翻譯
參、韋伯與國民經濟學
肆、個別文章導論:
〈羅謝與肯尼士〉
〈弁言〉、〈客觀性〉與〈文化科學的邏輯〉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一文及其〈補遺〉
〈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
〈“能量學的”文化理論〉
〈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
參考書目
凡例
〈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
文前說明
I.羅謝的“歷史的方法”
羅謝對科學的分類
羅謝的「發展」概念與實在的非理性
羅謝的心理學和他與古典理論的關係
知解性認識的限制與羅謝論有機體之形上學式的因果
羅謝與「實踐性的規範與理想」的問題。
II.肯尼士與「非理性」問題
行動的非理性。肯尼士著作的性格
肯尼士的“意志自由”和“自然制約性”與現代理論的關係
馮德的“創造性綜合”範疇
具體的行動之非理性與具體的自然事變之非理性
“詮釋”這個“範疇”
對這些“範疇”之各種知識理論上的探討:
(1)敏施特柏格的「“主觀化的”科學」概念
(2)西美爾的“理解”與“詮釋”
(3)歌陀的科學理論
III.肯尼士與「非理性」問題(續)
(4)李普士的“投入感受”與克羅齊的“直觀”
“顯明性”與“效力”
啟發性的“感受”與歷史學家之“暗示性”的描述
“合理”的詮釋
「因果性」範疇的雙重用法與「非理性」和「非決定論」之間的關係
肯尼士的「個體」概念;人學式的流出說
〈弁言〉
〈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
引言
I.「對理想與價值判斷進行科學的批判」的意義
「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之原則性的區分
II.「文化科學的認知興趣」之構成性意義
文化科學中「理論的」與「歷史的」考察方式的關係
「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之邏輯結構
經驗性的社會知識之“客觀性”的意義
「文化價值觀念」與「文化科學的興趣」之會變遷性
〈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
I.與愛德華‧麥耶的論辯
引言
各種「偶然」概念
“自由”與“必然”
歷史學的對象。
II.歷史的因果考察中的「客觀的可能性」與「適當的起因造成」
對實在之歷史上的形塑
“客觀的可能性”理論
客觀的“可能性判斷”之“效力”的模態
「“適當的”起因造成」這個範疇
“適當的”與“偶然的”「起因造成」作為思想上的抽象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
1.文前說明
2.史坦樂對歷史唯物論的陳述
3.史坦樂的“知識理論”
4. 「規則」概念之分析:
「規則」作為“規律”與作為“規範”
“準則”概念。
遊戲規則
法規則
法學的與經驗的概念。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一文之補遺〉
史坦樂的“因果性與目的”
史坦樂的“社會性生活”的概念
〈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
〈“能量學的”文化理論〉
〈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
I. 學院課堂上的實踐性評價
專業訓練與講壇評價
II.「純邏輯的或經驗的知識」與「評價性判斷」作為「異質的問題領域」之原則上的分離
“價值判斷”概念
由“目的”和由「手段」所做的批判
實踐性的令式與經驗性的事實確定之異質的效力領域
倫理的規範與文化理想。「倫理」的“界限”
倫理與其他價值領域之間的緊張
「價值秩序」之間的鬥爭。經驗真理、價值理論與個人的抉擇
價值討論與價值解釋
“發展傾向”與“適應”
“進步”概念
理性的進步
「規範性事物」在經驗學科中的地位
經濟的科學性學說的課題
國家的角色
人名譯註
韋伯年表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中譯導讀(節錄)/本書與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
本書翻譯的,基本上都是收錄於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以下簡稱WL)中的文章。但是,這本書無論是書名還是其中收錄的文章,卻都不是韋伯親自決定的。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對這部著作形成的歷史做些交代。
在1919年11月間寫給他的出版商Paul Siebeck的一封信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到了自己想要出版一本「方法論-邏輯學文集」(eine Sammlung der methodologisch-logischen Aufsätze)的想法,並說他認為可以考慮收錄進該文集的文章包括:
《文庫》中所有這類的東西(導論文章、與E. Meyer, Brentano, Stammler等人的論辯)、《邏各斯》諸文章(‘Logos’-Aufsätze)、以及一篇為社會政策協會寫的關於「勞動的心理技術」(Psychotechnik der Arbeit)的文章。
信中所提到的《文庫》,指的自然是韋伯與宋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和雅飛(Edgar Jaffé, 1866-1921)於1904年接手主編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以下簡稱《文庫》),而「導論文章」指的則是韋伯為該刊物新系列定調的重要文章〈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至於「與E. Meyer, Brentano, Stammler等人的論辯」,則是指分別於1906、1907、1908年發表於《文庫》中的三篇文章:〈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以及〈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邏各斯》諸文章」指的是分別於1913與1917年發表於《邏各斯》上的二篇文章:〈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和〈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而那篇「為社會政策協會寫的關於勞動的心理技術的文章」,則是指在1908-1909年間分四期發表於《文庫》的長文〈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Zur Psychophysik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
但是,一直到韋伯於1920年6月14日辭世為止,這本構想中的《文集》並未出版。韋伯辭世後,韋伯的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870-1954)才將韋伯的一些性質相近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並定名為《科學學說文集》。WL的第一版出版於1922年,但內容與韋伯的構想並不完全相同:韋伯提到的〈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一文並未收錄其中,反倒是收錄了幾篇韋伯並未提到的文章,包括:(1)韋伯於1903-1906年間,分三次發表於施莫樂(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主編的《德意志帝國的立法、行政與國民經濟年鑑》(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以下簡稱《年鑑》)的一篇論文:〈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以下簡稱〈羅謝與肯尼士〉);(2)1909年發表於《文庫》中的文章〈“能量學的”文化理論〉;(3)一篇選自《經濟與社會》第一部份第一章的前六節的文章,並冠以〈社會學的方法學基礎〉的篇名;(4)韋伯於1917年於慕尼黑演講、1919年修改付梓的講稿〈科學作為職業〉;以及(5)由遺稿整理付梓的〈〈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一文之補遺〉。但這本文集為何會定名為《科學學說文集》,而瑪莉安娜又是根據什麼觀點或想法選定這些文章的,則毫無說明。1951年,WL發行第二版,除了將〈社會學的方法學基礎〉這個篇名改成〈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並通讀一遍、做了一些小幅度的註解與說明並附加「索引」之外,文本上並無改變。
瑪莉安娜過世後,Johannes Winckelmann(1900-1985)才在他1868年編輯出版的WL第三版中,加入了二個新文本:(1)瑪莉安娜於韋伯遺稿中整理出來、並於1922年發表於《普魯士年鑑》的文章〈正當的支配之三種純粹的典型〉;(2)將〈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文擴充到第七節。Winckelmann在第三版的〈前言〉中說,加入前者的理由是:〈正當的支配之三種純粹的典型〉乃是1913年的〈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一文之思想上的直接延續;而加入後者的理由則是:第七節乃是為使「正當秩序的學說完善」所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Winckelmann還放棄了第二版所加的註解、說明與索引,恢復第一版的「純文本版本」型態(原先的構想是要另外出版一本《說明卷》,但始終未見完成)。此後的各個版本(1973, 1982, 1985, 1988等版本),書名與收錄文章基本上都沒有改變。這就是今日多數學者研究韋伯的方法論所依據WL的文本的由來。
在新編的《韋伯全集》(Max-Weber-Gesamtausgabe,以下簡稱MWG)中,規劃將收錄韋伯有關邏輯學-方法論問題的文章、編輯評註、書評、討論稿、意見書等等文字的,共有二卷:第7卷與第12卷。第7卷定名為《關於文化-與社會科學之邏輯學與方法論》(Zur Logik und Methodologie de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第12卷原先定名為《關於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與價值判斷討論》(Zur Methodologie und Werturteilsdiskussion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1984年改為《理解的社會學與價值判斷中立:1908-1920著作與發言》(Verstehende Soziologie und Werturteilsfreiheit. Schriften und Reden 1908-1920)。事實上,這二卷收入的文字,除了原已收入韋伯著作《社會學與社會政策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中的討論發言稿、1913年為在「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內部討論「價值判斷」問題所提出的意見書、以及一些編輯評註和書評之外,基本上與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並沒有什麼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MWG中,〈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一文獨立成冊(MWGI/11),並未列入上述二卷中。至於〈科學作為職業〉一文,則與〈政治做為職業〉合為一卷出版(MWGI/17)。
我基本上同意Friedrich Tenbruck(1989: 102)的說法: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應被視為韋伯授權的、表達其方法論思想的版本,並且其中所收錄的文章不只是一些零散的「沒有深刻的統一性與意義的爭論與機緣之作」,而是貫穿著一個「涉及了所有科學的整體之種種基本問題」之「相連屬且統一的提問」;換言之,其中事實上包含著一套有系統的「科學學說」,只是沒有有系統的解說而已。
由於韋伯夫人瑪莉安娜曾經研究過費希特──她第一本出版的著作是《費希特的社會主義及其與馬克思的學說的關係》(Fichtes Sozialismus und sein Verhältnis zur Marx’schen Doktrin)──,也許有人會認為她將韋伯的這本文集命名為“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多少與費希特的 “Wissenschaftslehre”(中文一般譯為「知識學」,事實上就是費希特心目中的「哲學」)概念有關。其實不然。“Wissenschaftslehre” 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流行的語詞,可用以泛指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說。例如本書頁[111]註1中所提到的W. Hellpach的Zur Wissenschaftslehre der Psychopathologie(《論心理病理學的科學學說》)一書的書名,就是在相同的意義下使用“Wissenschaftslehre”一詞的。也因此瑪莉安娜會將韋伯信中所沒有提到的那些文章也收入論文中。相反的,溫克曼所加的部分,便顯得與「科學學說」不太相干了。
因此,本書基本上將以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所收錄的文章為準進行翻譯。惟其中1913年的〈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一文,因與方法論的關係不是那麼密切,比較適合與1921年的〈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文放在一起對照著讀,以掌握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的概念的發展,因此不收入本書中。至於的溫克曼所加的部分,跟「方法論」更不相關,我就不翻譯了。但由於瑪莉安娜編輯的版本已不易找到,且學術界長久以來都以溫克曼編輯的版本為引註根據,因此本書亦採用之,以方便讀者查考。我根據的版本是1982年出版的WL第五版。另外,〈科學作為職業〉這篇文章,由於已有不錯的譯本可讀,我就不再重譯了。其他所有收入WL中的文章,則將依照時間順序安排,一一譯出。這樣一來,由於本書所譯的文章,都是韋伯較為扣緊方法論主題的著作,將本書命名為《韋伯方法論文集》,就顯得更為恰當了。為了方便懂德文的讀者查考原文,本書將以“[]”標示譯文所根據的德文版本的頁數。
但若嚴格依照文章發表的編年順序安排,分別於1903、1905與1906年分成三篇文章發表的〈羅謝與肯尼士〉一文,卻又將被分隔開成二個部分。因此,為顧及文章的完整性,本書將把〈羅謝與肯尼士〉一文的三篇文章放在一起。除此之外,本書還收錄了一篇韋伯於1904年與宋巴特、雅飛接手主編《文庫》時,以編輯群的名義所寫的期刊新系列發刊詞〈弁言〉(Geleitwort)。這篇短文為WL所無,收入本書的理由詳後。
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 (1906)
I.與愛德華‧麥耶(Eduard Meyer)的論辯
當我們的第一流歷史學家中的一個,覺得有必要對自己和他的專業同僚說明他的研究工作的目標與途徑的時候,則這一點一定會引起某種超出專業範圍的興趣,因為,他這樣做已超出了他的個別學科的範圍而進入「知識理論的考察」的領域(das Gebiet erkenntnistheoretischer Betrachtungen)了。這樣做當然首先會有一些負面的結果。邏輯學就其今日的發展而言,已然和其他專業學科一樣是一門專業學科,因此,就像任何一門其他學科的範疇一樣,要能真正熟練地操作邏輯學的種種範疇(Kategorien der Logik),也必須經常運用這些範疇;然而,本文的作者和愛德華‧麥耶(本文要談的就是他的著作《論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學》(Zur Theorie und Methodik der Geschichte, Halle 1902)一書)一樣,顯然都不能、也不想主張自己對邏輯學問題有這樣的一種經常性的精神上的交往。因此,本文中對該著作所做的知識批判方面的論述(erkenntniskritische Ausführungen),可以說並非醫生的、而是病人自己的病情診斷報告,也希望讀者能如此看待並理解這些論述。因此,專業的邏輯學家和知識理論家或許會對麥耶的許多表述感到反感,而對其目的而言,也可能無法由這部著作中獲得真正新穎的東西。但這一點對於該著作對相鄰的個別學科的意義卻毫無損害。恰恰由於專業的知識理論之種種最重要的成就,都是運用“理想典型”的方式(idealtypisch)去形成關於個別科學之知識目標與途徑的種種圖像而進行研究的,因而高高飛越後者的頭上,以致於這些個別科學往往難以用未經武裝的雙眼,在那些論述中再辨認出自己來。因此,若要達到自省(Selbstbesinnung)的目的,反倒是那些在這些個別科學當中的方法論論述,儘管從知識理論的觀點看來這些論述的表述並不完備,卻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正因為這種不完備的表述,而往往更容易對這些個別學科有所幫助。恰恰是麥耶的陳述之清晰易解,為鄰近學科的專家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讓他們有可能以一整個系列的點為出發點,去解決某些他們和那些較狹義的“歷史學家”們共同的邏輯問題。
這正是以下的種種討論的目的:這些討論首先以麥耶為出發點,依序將許多邏輯上的個別問題給弄清楚,然後再由如此獲致的觀點出發,進一步去評論一些有關「文化科學的邏輯」方面的新近著作。由於已有許多人嘗試過透過跟“自然科學”劃定界線的方法去規定社會科學的獨特性,本文的論述將特意從一些純歷史的問題出發,而在較後面的論述中才去處理那些尋求社會生活之「規則」與“法則”的學科。過去的做法基本上總帶有一項未加明說的預設,即認為:“歷史”乃是一門純收集材料的、或甚至只是純“描述性”的學科,頂多只能將“事實”揪出來,作為現在才開始的“真正”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建築石材。並且令人遺憾的是,正是專業歷史學家在試圖建立專業意義下的“歷史學”之獨特性(Eigenheit)時,他們所採取的方式也大大地加強了下述成見,即認為:“歷史的”研究工作是某種性質上不同於“科學的”研究工作的東 西,因為“概念”與「規則」和歷史“毫不相干”。由於(在“歷史學派”的深遠影響下)人們到今天都還習慣於以“歷史的方式”為我們的學科奠基,也由於與“理論”的關係一直到今天都還跟二十五年前一樣曖昧不明,因此正確的做法似乎是:首先去問「邏輯意義下的“歷史的”研究工作究竟可以被理解為什麼」,並將這個問題首先在毫無疑問並受到公認的“歷史的”研究工作——此處首先要加以批判的著作所從事的就是這種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加以解決。
愛德華‧麥耶一開始就警告人們,不要高估方法論的研究對於歷史學的實踐(Praxis)的意義:最廣博的方法論知識並不會使任何人成為歷史學家,錯誤的方法論觀點也不必然導致錯誤的科學實踐,而是只不過證明了歷史學家對自己的正確的「研究工作的準則」(Arbeitsmaximen)作了錯誤的表述或詮釋。我基本上同意這種說法:方法論畢竟只能是對那些在實踐中通過考驗的手段之自省,而「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手段」這一點也不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的前提,正如解剖學的知識並非“正確地”走路的前提一樣。的確,正如不斷想要以解剖學知識控制走路的方式的人將會有跌跤的危險一樣,專業學者如果硬是要以方法論上的考量為基礎去決定其研究工作的目標,也會遭遇到相同的情況。如果方法論的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一點上直接服務於歷史學家的實踐(這一點當然也是方法論研究工作的意圖),則這恰恰是因為這種研究工作使得歷史學家得以因此絕不會被拿哲學妝點門面的半瓶醋說法所蒙蔽。唯有指出並解決實質的問題,各種科學才得以建立,其方法才得以進展;相反的,純知識理論的或方法論的考量則從未在此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對科學的經營(Betrieb der Wissenschaft)本身而言,這樣的種種探討往往唯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是重要的,即:由於人們觀察某一材料、使之成為陳述的對象的那些“觀點”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以致於產生了一種想法,認為這些新的“觀點”勢必也要求我們對向來的“經營”在其中運轉的那些邏輯形式(logische Formen)進行某種修正,從而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本質”產生了不確定感時。目前的歷史學無疑就處於這種情況之中,也因此雖然麥耶認為方法論對於“實踐”而言原則上是無意義的,他還是有理由在今日親自從事於方法論。
麥耶首先致力於陳述最近出現的一些試圖由方法論的觀點出發去改造歷史科學的理論,並將他特別想與之進行批判性論辯的觀點表述為:
下列各項對歷史學而言是無意義的、因而也不應該被納入科學的陳述中:
(a)“偶然性事物”(das “Zufällige”),
(b)具體人格之“自由的”意志決定,
(c)“觀念”對於人的行動之影響;
相反的,
(a)科學性的認識之真正的對象則是:
(b)相對於個別行動之“群眾現象”,
(c)相對於“個殊物”之“典型物”(das “Typische”),
相對於個別的人的政治行動之種種“共同體”、尤其是種種社會性的“階級”或“國族”的發展;最後,因為歷史的發展在科學上只能以因果的方式加以理解,亦即只能理解為某種以“法則”的方式進行的過程,因此,歷史學的研究工作之真正目的,乃是要找出種種「人的共同體」之必然以“典型”的方式前後相續的各種“發展階段”,並將歷史上的雜多(geschichtliche Mannigfaltigkeit)安排進它們之中。
以下,我將暫時完全撇下麥耶的論述中專為與蘭佩雷希特論辯而發的所有論點,並且同樣的,我也將不揣冒昧,依照對以下的一些研究——這些研究的目的畢竟並非只是要對麥耶的著作進行某種批判——的需要有利的方式,將麥耶的種種論證加以重新編排,並從這些論證中挑出某些個別的論證出來,放在在稍後接著的一些段落加以特別討論。
針對他所要辯駁的觀點,麥耶首先指出:“自由意志”與“偶然”(根據他的觀點,這二者乃是“完全確定且清晰的概念”)無論在歷史或在人生中都扮演著重大的角色。
首先,就“偶然”的討論而言,麥耶當然不會將這個概念理解為客觀的“無原因性”(在形上學的意義下之“絕對”的偶然)或主觀的、但在相關種類(如:擲骰子)的每一個個別事例中都必然一再出現之對「原因上的條件」的認識之絕對不可能性(在知識理論的意義下之“絕對”的偶然),而是將這個概念理解為在「許多分別被想出來的原因複合體之間的某種邏輯關係」的意義下之“相對”的偶然,並且整體而言——當然難免並非處處都做了“正確”的表述——是合乎專業邏輯學的學說(這學說即使在今日,儘管在個別論點上有許多進步,但基本上還是承續著溫德爾班的處女作的)所接受的「偶然」概念的。麥耶也大體上正確地區分開了(1)這種因果概念的“偶然”(所謂的“相對的偶然”):──在此,與「“偶然”的結果」相對的,乃是那種我們可以根據一事件之那些我們綜合為一個概念的統一體的因果成分而加以“期望”的結果,“偶然的事物”即是我們無法根據現象的一般規則由那些我們納入考察的條件因果地導出、而是由“外在於”這些條件之外的一個條件之加入所造成的東西,——和(2)與此不同的目的論概念的“偶然性事物”:其對立物乃是“具有本質性的事物”(das “Wesentliche”),無論涉及的是我們為了知識目的而進行一個概念的建構時所排除的實在中的那些對知識而言“非本質性的”(“偶然的”、“個別的”)組成部分,還是我們對於某些實在的或被設想出來的客體作為達到某一“目的”之「手段」所做的判斷:這時候,某些性質(Eigenschaften)唯有作為「手段」才是在實踐上相干的,而其餘的性質則是在實踐上“無關緊要”的。誠然,麥耶的表述(尤其在第20頁下面將這種對立理解為一種“過程”與“對象”之對立的地方)尚有可以改進之處,而我們稍後對麥耶對「發展」概念的態度的討論也將顯示,他對這問題的種種邏輯上的結果並沒有透徹地想過。但他所說的,畢竟一般而言滿足了歷史學實踐的種種需要。——然而,我們在這裡感到興趣的,卻是該著作在稍後的地方回過頭來再論偶然概念的方式。麥耶在該處說道:「自然科學固然能夠 … 說:如果點燃火藥,就必定會發生爆炸。但自然科學卻不可能預言:在一個個別情況中,這爆炸是否會發生以及何時會發生,發生爆炸時某個特定的人是否會受傷、被殺死或獲救,因為這一點是依賴於偶然和自由意志的,自然科學不知有自由意志,但歷史學卻知道。」在這裡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偶然”與“自由意志”的緊密綰結。這種緊密的綰結透過麥耶所舉的下述第二個例子而更加明確地凸顯了出來,他說:我們一方面有可能運用天文學的手段“確定地”——亦即在沒有受到任何“干擾”(例如:陌生星體之誤入太陽系)的情況下——“計算出”某一星座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不可能”預言該被計算出來的星座位置是否也將會“被觀察到”。第一:根據麥耶的前提,該陌生星體之“誤入”一定也是“無法計算”的——從而不僅歷史學、就連天文學也知道有這種意義的“偶然”了,——第二:我們其實通常很容易就“可以算到”:將會有某個天文學家試圖去“觀察”那被計算出來的星座位置,並且在沒有任何“偶然”的干擾出現的情況下,事實上也將會觀察到該星座的位置。這讓我們產生一種印象:儘管麥耶對“偶然”作出了完全決定論式的解釋,但他卻未將這一點明白地說出來,反而想像著“偶然”與某種“意志自由”之間具有一種特別緊密的選擇親和性(Wahlverwandtschaft),使得歷史的事變具有某種特有的非理性。就讓我們進一步看看吧。
麥耶稱之為“自由的意志”的東西,根據他的說法,卻又絕不包含任何與“具有公理性質的”、並且根據他的觀點同時也是無條件地、對人的行動也有效的“充足理由律”(Satz vom zureichenden Grunde)的矛盾。而是:行動之「“自由”與“必然”」此一對立,轉化成了某種僅僅是考察方式的區別:在後一情況中,我們考察的是「已然生成了的東西」(das Gewordene),而這東西——包括曾經事實上做出過的決定——對我們而言算是“必然的”,——在第一種情況中,我們則是將過程當作是“正在生成著”、亦即尚未存在著、亦即也尚非“必然的”,而是當作無限多的可能性之一而加以考察的。但是,由某種“正在生成著”的發展的立場出發,我們卻絕對無法主張:一項人的決定,只會是(後來)事實上做出的那項決定,而不會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決定。「在任何關於人的行動的情況中,我們都無法超越於“我想要”(das “ich will”)之外。」
於是首先便產生了一個問題:麥耶是否認為,上述二種考察方式的對立(“正在生成著的”、並因而被設想為“自由的”的“發展”——“已然生成了的”、並因而可以被當作是“必然的”去加以設想的“事實”),僅僅適用於「人的動機」的領域,而不適用於「“死的”自然」的領域?由於他說:「認識某一人格及其境況的人」,有可能「也許以極高的或然率」預見結果:——“正在生成著的”決定,因而看起來他似乎不會接受這樣的一種對立。因為,由給定的種種條件出發,對一個個體性的過程所做的某種真正精確的預先“計算”,即使在「“死的”自然」的領域裡,也有賴於以下二個預設:(1)所涉及的,僅僅是給定的事物之“可以計算的”、可以在量上加以陳述的組成部分;(2)“所有”對該進程而言相干的條件,都的確為我們所知並精確地加以測量了。在另一種情況中——而只要事關事件之具體的個體性(如:未來特定的某一天之天氣的型態),這種情況就完全是規則——我們在那裡也無法超越種種具有極為不同等級的確定性之或然性判斷(Wahrscheinlichkeitsurt eile)。在這種情況中,“自由的”意志或許不再有任何特殊地位,而該“我想要”也許不過就是詹姆士(James)所說的那種形式性的「意識的“命令”」(“fiat” des Bewußtseins),這種“命令”就連諸如決定論的刑法學者們都可以接受,而不會有損於他們的種種「歸因-理論」的結論。但如此一來,“自由的意志”將不過意味著:賦予那事實上由也許永遠都無法完全找出來的、但無論如何都是“充足的”原因所產生的“決定”以因果上的意義,而這一點就連一個嚴格的決定論者也將不會認真地爭辯。如果除此之外就不涉及任何其他問題了,則我就實在看不出來,我們有時候會拿來說明“偶然”的「歷史事變之非理性」這個概念有什麼不能接受的。
然而,對麥耶的觀點所做的這樣一種詮釋,首先必定會讓人感到奇怪的一點是:他在這個脈絡中,竟然會覺得有必要去強調「作為“內在經驗的事實”之“自由的意志”,對於個別的人對其“意志的活動”(Willensbetätigung)的責任乃是不可或缺的」。他之所以會這麼想,唯一的動機也許是因為他覺得歷史學應該負起擔任其主人公之“法官”的任務。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麥耶的確站在這立場上。他說:「我們嘗試去揭露 … 導致他們」——亦即例如:俾斯麥1866年——「做出他們的那些決定的種種動機,並據此判斷這些決定的正確性以及他們的人格的價值(請注意!)」。根據此一表述,也許我們可以相信:麥耶將「獲得對“在歷史上行動著的”人格之種種價值判斷」視為歷史學的最高任務。但是,不僅我們稍後還會提及的麥耶對“傳記”的態度(見該文結尾處),而是還包括他對歷史上的人格之“固有價值”(Eigenwert)與他們的「因果上的意義」的不一致(Inkongruenz)所做的那些極為中肯的評論,卻都讓人覺得:麥耶在上引的那句話中所說的「人格的“價值”」,無可置疑地就是指(或為求前後一致就只能指)那些具體的人物之某些特定的行動或某些特定的——對某一各自採取的價值判斷而言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如:在威廉四世的情況中)是負面的——品質之因果上的“意義”。然而,就「對那些決定的“正確性”之“判斷”」而言,卻又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理解:要嘛理解為(1)又是對作為該決定之基礎的目的(如:基於德意志愛國者的立場而想要「將奧國排除於德國之外」的目的)的某種判斷,——或者理解為(2)藉由問「是否、或者——由於歷史畢竟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無寧說:為何『決定發動戰爭』這項決定,恰恰在當時那個時刻中,乃是達到該目的(德國的統一)之恰當的手段」這個問題,而對該決定進行某種分析。麥耶主觀上是否事實上清楚地將這二種提問區分開來了,我們就暫置不論了:適合用來論證歷史的因果性的,顯然將只有第二種提問。因為,這種在“手段與目的”這二個範疇下對歷史處境所做的、就形式而言為“目的論式”的判斷,在某種並非作為「外交官的處方書」、而是作為“歷史”而出現的陳述的內部中,顯然只有一個意義(Sinn),那就是:使我們得以對種種事實之因果上的、歷史上的意義進行某種判斷,亦即去確定:恰恰在當時的那個時刻,做出該決定的一個“時機”並未被“錯過”了,因為該決定的“承擔者”——麥耶是這麼說的:——擁有一種抗拒一切阻力而堅持該決定之“心靈的力量”(seelische Kraft):藉此便可以確定,在因果上有多少是“取決於”該決定及其性格學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先決條件的,換句話說,(例如)那些“性格品質”(Charakterqualitäten)之存在,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麼意義下,曾經是一個具有歷史的“效力範圍”(Tragweite)的“環節”(Moment)。但這樣的一些由某一特定的歷史的事變回溯到某些具體的人之種種行動的「因果上的回溯」(kausale Zurückführung)的問題,當然應該跟探討「倫理上的“責任”之意義」的問題(Frage nach Sinn und Bedeutung der ethischen “Verantwortlichkeit”)嚴格地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