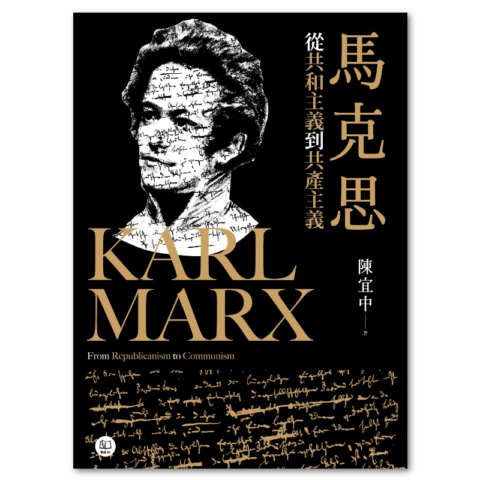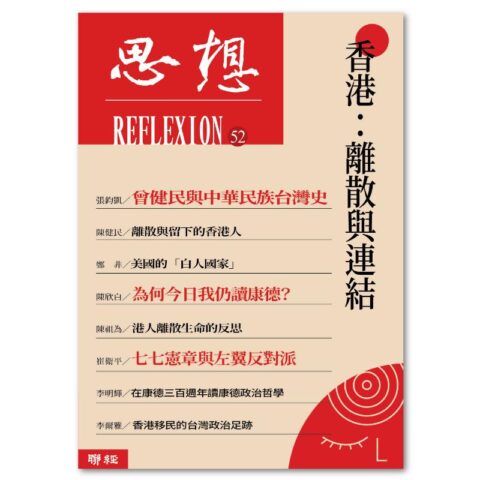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23)
出版日期:2013-05-31
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1886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思想23》的專輯是「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
本期收錄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為何不支持女權主義?〉、〈女性主義vs.多元文化論?──反思兩者間的「緊張關係」〉、〈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認識女性主義〉、〈女權運動與自由主義思潮的對話〉等文章。
訪談的專欄,則訪問了朱天心女士,談信念的必須承受之重,也訪問了周瑞金教授談權錢之間的改革。
其他還有〈委內瑞拉查維茲的激進民主傳奇〉、〈日本右翼思想的四個源流〉等精選文章。
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錢理群
試論當代儒家之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李雅明
殖民地統治與大量虐殺: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新視野╱楊海英
■思想訪談
信念的必須承受之重:朱天心女士訪談錄╱李 琳
權錢之間:周瑞金先生談改革╱李宗陶
■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
女權運動與自由主義思潮的對話╱黃長玲、顏厥安、蘇芊玲、陳昭如
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為何不支持女權主義?╱李思磐
女性主義vs.多元文化論?——反思兩者間的「緊張關係」╱范芯華
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 ╱陳昭如
認識女性主義╱陸品妃
■思想評論
日本右翼源流:尊王攘夷、天皇主權、排西蔑中、愛鄉主義 ╱邵軒磊
查維茲的激進民主傳奇╱廖 美
倖存者的批判與重構:讀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杜應國
■思想人生
王元化 反思歷史╱李懷宇
致讀者
致讀者
思想不喜歡絕緣的無菌室:它是一種說理與反思的活動,因此不可能在同質的環境之中進行;它渴望跟異議者對話,互相解惑、攻錯、取長補短。一個思想傳統如果閉關自守,堅持純正本色,很快便會枯竭;但如果它積極迎向其他思潮,不怕比較彼此的價值觀點與理知資源,它便有機會成長發展、與時俱進。
自由主義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久而彌堅的思想傳統,仰仗的正是對於來自其他思潮的挑戰保持開放與吸納。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生機盎然的新生理論兼實踐模式,幾十年來衝撞滲透到各個思想傳統中,企圖改變各種理論的男性中心視野。在西方,自由主義與女性主義的關係既親近又緊張:親近來自追求平等的共同歷史動力,緊張則來自對平等的迥異理解。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的爭辯與學習,是促進雙方繼續進步的重要動因。
可是在中文世界,這兩種思想取向之間很少對話。對台灣或者香港來說,兩套理論的爭論已經在西方發生,在地的對話便顯得多餘。而在中國大陸,兩種思潮都還處於艱困求生存的狀態,顯然缺乏對話的客觀條件。何況如本期李思磐女士的文章所示,某些中國自由主義者受到階段論或者傳統思路的影響,主觀上也缺乏正視女權主義的動機。
《思想》早就有意探討自由主義與女性主義的關係,但直到如今方組成專輯。當然,無論自由主義還是女性主義,所涵蓋的範圍之遼闊,涉及的議題之雜多,既非幾篇文章所能窮盡,也都有必要繼續跟包括左派在內的其他思想取向互相學習。本刊會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儒家與基督教的關係,是一個很老的話題,不過爭論多年,並沒有找到什麼深刻的結論。然而,近些年來的整個思想氛圍大有改變。多元文化主義成為主流,科學知識的典範地位已遭顛覆,基督教對於其他文明與世界觀的態度也變得更為正面積極,在在有助於重新檢討儒家與基督教的關係。本期李雅明先生的文章,雖然爭議性強,卻也正適合引發各方的批評與反省。
在當前世界上,遠方的拉丁美洲是左派的地盤,近處的東亞則日益右傾,尤以日本的發展引人擔憂。拉美左派的支柱查維茲甫去世,身後的遺產如何評價,廖美女士的及時文章有全面的探討。日本的右派正在抬頭,並且可能改變戰後的日本國家性質。邵軒磊先生清楚整理出了日本右派源遠流長的系譜,對讀者會大有幫助。
前期(第22期)《思想》的「走過八十年代」專輯,係由中研院社會學所蕭阿勤先生與編委汪宏倫先生二位合作規劃促成。由於編者疏忽,在該期沒有向蕭先生致謝,謹在此說明並致歉。
此外,本刊編委王超華女士因為長居歐美,多次請辭編委職務;幾經挽留未成,我們不敢再勉強。超華女士對本刊的貢獻很大,我們在此向她致謝,並且盼望她繼續幫這份刊物籌劃、寫稿。
從2012年5月開始,經李琳女士的倡議與實際操作,《思想》在新浪微博開通帳號,定期貼出本刊發表過的文章,很受各方讀者歡迎。目前該帳號的關注者已經達六千餘位,並穩定增加中。感謝李琳的熱心,也希望本刊能在網路上接觸到更多的讀者。
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在某大學的一次演講)/錢理群
最近我編選了一本《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入門讀本》;今天就以此作為我的演講的題目。
熟悉我的朋友,很容易就注意到,我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要從魯迅出發;因此,有人說:「錢理群走在魯迅陰影下」。這或許是我的一個弱點或局限吧。但這樣做,是有我的三個考慮的。
首先,這是應對我的一個矛盾的一種言說策略:我的專業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研究魯迅;但又對國際、國內的重大政治、思想、文化、社會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今天我就是來和諸位討論這些問題的。這樣的對非專業的問題的發言,是有很大的危險性的:魯迅早就警告過,專家要對他不熟悉的問題發言,很容易發謬論,是不足為信的。因此,我每次作這樣的發言,都要預先聲明:我不是以專家的身分,而是作為關心這些公共問題的普通公民來發表個人意見,姑妄言之,大家也就姑妄聽之。──今天,我也照例要先作這樣的交代,希望大家對我下面要說的話,當作是朋友間的聊天,隨意聽聽罷了。但另一方面,為了對聽眾負責,我也不能隨便亂說,總要有點依據。於是,就儘量利用專業方面的知識來支撐我的言說,這就是我不斷引述魯迅的論說的原因。
但這又會遭到一種質疑和責難:你這樣引述魯迅的話,是不是「過度闡釋」,違背了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呢?坦白說,多年來,我的魯迅研究與言說,一直受到這樣的批評,我總是說,自己在學術界是一個有爭議的學者,指的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對這樣的批評、爭議,我的態度有二:一是吸取其合理部分,時刻警戒自己:不可遠離魯迅思想實際和實質,把他的言說當做一種自我言說的包裝,那是對魯迅的利用和褻瀆,是我自己對魯迅的感情也不允許的。但同時,我始終固執地堅持一點:創造性的學術研究對研究對象的思想,既要有闡釋,而且要有所發揮,有時候闡釋本身就是一種發揮。因此,我可以毫不掩飾地公開宣佈:我對自己的魯迅研究的要求是:「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如果有可能,還要「接著魯迅往下做」。這絕不是狂妄自大,而是一種學術責任和使命。事實上,學術研究就是一個對研究對象的創造不斷添加、引申、發揮,再創造的過程,絕不能否認研究者的主觀能動作用;最後的成果,當然是以原創者的原著為基礎,但已經包含研究者的創造。就以「儒學」為例,它以孔丘的《論語》為基礎,但已經積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者在注經過程中的創造、發揮,它就成了一個集體創造的產物。我想,「魯學」也是如此。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裡的發揮就很多,有的經不住考驗,被否定了;但有的就作為「魯學」的重要成果被積澱下來。——我在這裡也不妨作一個聲明:我今天的演講,是從魯迅的觀點出發的,但也有被當今中國和世界現實所激發的我的理解和發揮。這些理解與發揮,當然不一定準確、適當,是可以而且歡迎批評、討論的,但它也絕不是沒有意義的。
魯迅的觀點在今天所以有發揮的可能與餘地,是和魯迅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有關的。這就談到了今天演講的主題:魯迅活在當下的中國。我多次說過,魯迅的作品,特別是他的雜文,是有兩個層面的:一方面是對現實的直接回應,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他總是把現實的批判深入到歷史、文化的深處,人性、國民性的深處,因而具有普遍性和超前性。我經常說魯迅的思想絕不是「過去式」的,而是「正在進行式」的;有人曾嘗試把魯迅對1930年代文壇的批判文章重新發表,加上一個標題:「魯迅論當代中國文壇」,大家都覺得非常合適,彷彿魯迅就在對當下發言。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驗: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問題,都會去重新閱讀魯迅的有關論述,而且總能從他那裡得到啟發。我說魯迅的思想,不僅具有原創性,而且是源泉性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社會大危機、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空前活躍、也空前混亂的時代。每一個關心時事、喜歡思考的人,都充滿了焦慮、困惑和迷茫。如何認識當下中國社會,怎樣把握中國的未來發展,即「中國往何處去」,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辦?」這都成了迴避不了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限於空談,也不能一味發牢騷,在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對歷史與現實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論資源。魯迅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要求下,顯示出它的特殊意義和價值。這些年我一直帶著這些現實問題,去重讀魯迅著作,突然發現魯迅的許多精彩論述,讓我眼睛一亮,茅塞頓開,引發了許多思考。下面就具體地談談我的學習心得,和諸位分享。大概有七個問題。
一、什麼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魯迅在《隨感錄。五十四〉(收《魯迅全集》1卷《熱風》)裡,有這樣一個概括:「中國社會的狀況,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松油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當下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將「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幾十世紀縮在一時」了。具體地說,中國的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處於「前現代社會」;西部地區的許多地方,中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大部分都進入了「現代社會」;而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就已經是「後現代社會」了。這是就整體而言,在每一個地區內部,又都存在著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差異。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地區差異巨大、發展不平衡,各種社會形態「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國,這構成了我們的基本國情。
我由此而聯想到三個問題。
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我經常對關心中國的外國朋友說:僅僅從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發展,來認識中國,是片面的,它會遮蔽許多中國的真實問題;你們必須深入到中國的社會底層,窮鄉僻壤。那裡才有更真實的中國。我也對中國的大學生們說,你們必須要到農村去,到還在點松油片、推獨輪車的地方去,當你親身體會到,中國的農民,老百姓,他們是「多麼的苦,又多麼的好」時,你就真正懂得中國了,而且也會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怎樣確定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以社會發展不平衡這樣一個基本國情,作為前提,針對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不同問題,尋求不同的發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窩蜂」,而這恰恰是當下中國發展的最大問題。這不僅是中國各級政府的問題,也關係到民間志願者支農運動的發展方向,我經常對他們說,不要以為你們去支農就一定給農民帶來好處,如果脫離當地農村發展的實際,亂來一氣,說不定會幫倒忙。
也許是更重要的,我們在思考中國問題時,也必須以其發展不平衡性為前提,採取更為複雜的態度。我多次講到自己的一次尷尬遭遇:我在北京書房裡,站在後現代的立場,對貴州發展中少數民族語言的喪失問題,憂心如焚,於是特地跑到貴州各專州,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發出「拯救民族語言」的呼籲。結果收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現在最關心的,是畢業以後的就業問題。懂得民族語言,並不能幫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漢語,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語。因此,我想請教錢教授:要如何才能學好英語?我的尷尬並不在我的呼籲不正確,而是我把問題簡單化了,沒有充分考慮少數民族在尋求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的複雜性;更成問題的是,我的那種想當然的居高臨下的「拯救」姿態,而不是和少數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面對真實存在的問題。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啟示是,我們在處理中國的思想問題,宣導各種思潮時,也必須考慮到這種不平衡性,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是會遇到不同問題的。我自己就發現,我的具有強烈的啟蒙主義色彩的演講,在不同地區的聽眾中,是會有不同的反響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方講「五四」科學、民主傳統,受到了空前的歡迎,現場氣氛之熱烈,讓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類似場景。但我在北京講科學、民主,聽眾的反應就要冷靜得多,他們常常會從後現代的問題出發,對科學主義、民主萬能,以至啟蒙主義本身提出質疑。在我看來,西北和北京地區的學生的不同反應,都真實地反映了他們所面對的不同問題和思想欲求,這就要求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在思考、言說、處理啟蒙主義,及與之相關的科學、民主之類的命題時,必須採取更為複雜的態度,我後來選擇了「既堅持又質疑啟蒙主義」的立場,就和這樣的中國國情有關。
二、中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魯迅於上一世紀初的1907年,也即一百零五年前,在〈文化偏至論〉裡,對現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往者為本體發展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役,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嗚呼,眷念方來,亦已焉哉!」(文收《魯迅全集》1卷《墳》)。
魯迅作出這樣的判斷,是自有針對性的。他所說的「本體發展之偏枯」,是針對「自尊」而「抱守殘闋」的保守派、頑固派,提醒人們必須正視中國本體的專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傳統的弊端,強調中國必須變革;「以交通傳來之新役」,是針對「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的維新派,提醒人們必須注意「歐洲19世紀之文明」即西方工業文明,包括其科學、民主、平等的觀念可能及已經導致的弊端。在他看來,本體的東方專制主義和
交通傳來的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危險,甚至可能導致「中國之沉淪」。
我對此曾有過一個分析:這反映了魯迅和他們那一代人在尋找、開創中國的發展道路時,所遇到的兩難選擇:作為一個變革者,當然要反對、批判國內的東方專制主義,為此就必須引入和學習西方工業文明;但此時在西方社會,工業文明已經出現了問題,形成了西方文明病。既要反對東方專制主義,又對西方文明病心存疑慮,這就成了兩難,於是出現了四種選擇。一是所謂「全盤西化」派,即不否認西方文明病的存在,但認為西方文明病和東方專制主義有「小壞」和「大壞」之別,當務之急是用西方文明來取代東方專制,以後再來解決西方文明病的問題。二是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派,反過來認為還是中國文明最好,甚至希望用中國文明來解決西方文明病的問題。其三是「馬克思主義」派。他們試圖用馬克思主義來同時解決東方專制主義和西方文明病的問題。這在理論上自然是一個最理想的、合理的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這是後來許多知識分子都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因。其四,是魯迅的立場,即堅持對「二患」的警惕,既用西方工業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學,民主,平等等)來批判東方專制主義,同時又對這些基本理念及其實踐保持警惕,並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價值理想和現代化目標,對東方專制主義、西方文明病同時採取批判態度。魯迅的這一思想和態度,顯然具有超前性,對今天也還有啟發意義;但只限於思想、文化領域,並沒有涉及具體的社會實踐及制度的建設,他的理想也多少帶有烏托邦的性質。
問題是,中國後來的歷史發展,是選擇了一條所謂「中國特色的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是陷入了空想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為了強行實現,也就必然借助於東方專制主義,走上了「極權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改革開放後,又在堅持極權社會主義基本體制的前提下,引入西方市場經濟,其結果是導致了西方文明病(消費主義,實利主義,實用主義,等等)的氾濫。如果說,一百年前魯迅說的「二患交伐」尚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危險,那麼,到上一世紀的1990年代,以至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就成了活生生的現實。這就是我經常提到的,今天中國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最壞的社會主義和最壞的資本主義的惡性嫁接」。
在我看來,如何對待這樣的「二患交伐」的中國問題,是每一個關心中國發展的人,都無法迴避的。記得在1990年代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論爭中,他們各執一端:自由主義堅持批判極權社會主義,但對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向和西方文明病則儘量迴避,或將其作為「未來的禍害」而擱置起來;新左派則以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作為主要危險,對極權社會主義的問題卻態度曖昧。在觀察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動向時,我們再一次遇到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全盤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義」派,而當年的新左派對極權社會主義的態度,也由曖昧轉向極力理想化,提出了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經驗」論,在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上和文化保守主義合流了。
客觀的說,所有這些不同思想派別的分歧和論爭,都是魯迅那一代先驅者面臨的兩難選擇的延續。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切發展中的國家的知識分子在尋找國家現代發展道路時,所面臨的困惑。坦白地說,我自己至今也還沒有擺脫這樣的焦慮:儘管在理論上我完全認同魯迅式的雙重質疑的態度,但在找到具體的實踐之路前,這依然只是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與實驗的問題,但其前提卻是要敢於像魯迅那樣,正視這「二患交伐」的現實:我們需要面對與解決的是兩個問題,既有帶有東方專制主義色彩的極權社會主義的問題,也有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西方文明病的問題。
在今天,明確提出這樣的問題,還有一個全球的背景。觀察2011年以來的世界局勢,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全球性的危機:用2011年英國首相「英國病了」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全球都病了:美國病了,日本病了,中國病了,印度病了,歐洲病了,北非病了……。這就意味著,現行的所有的社會制度,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的社會發展模式,無論是美國模式,北歐模式,中國模式……,都暴露了」自身的矛盾,弊端,都陷入了困境。這就給我們的選擇帶來了新的困惑:過去我們不滿意中國的極權社會主義,可以選擇美式資本主義,或者北歐式民主社會主義,事實上中國的一些思想派別就是這麼選擇的,在目睹了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與北歐經濟社會危機以後,我們的選擇至少不會那麼簡單、明快,而是要更複雜化了。當然,也有人因此全盤美化所謂「中國道路,中國模式」,那是一種自欺欺人,不足為訓。或許現在到了這樣的時候:在經歷了國內和國際的種種危機以後,我們可以站在更高的層面,來思考和探索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發展道路。這樣,危機就會變成轉機。作為魯迅的後代,我們有責任繼續思考與探索他們所提出卻未能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