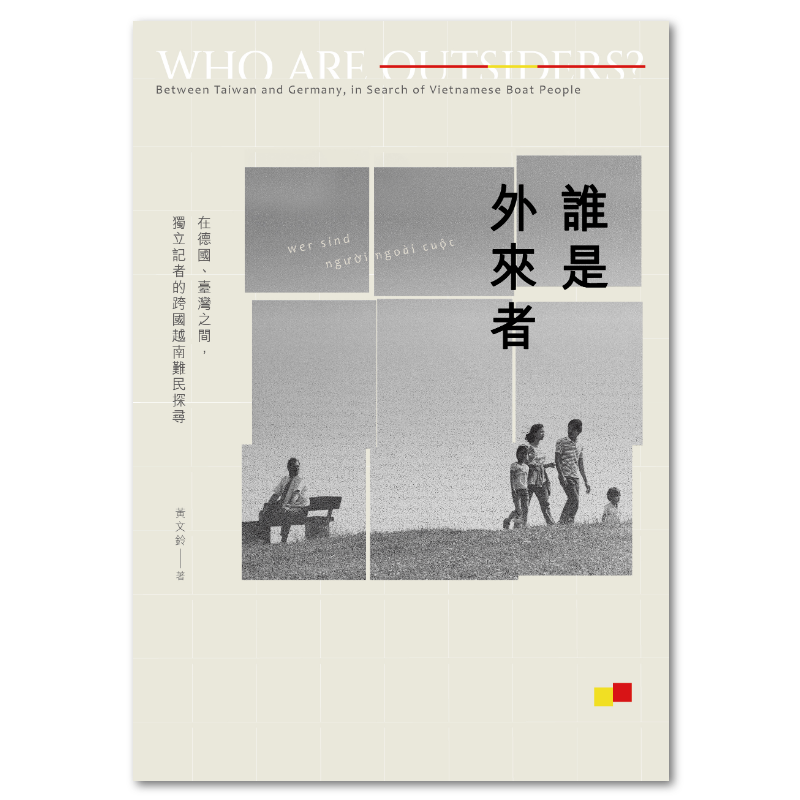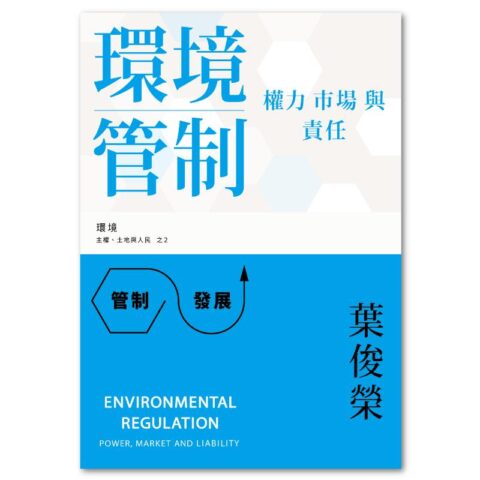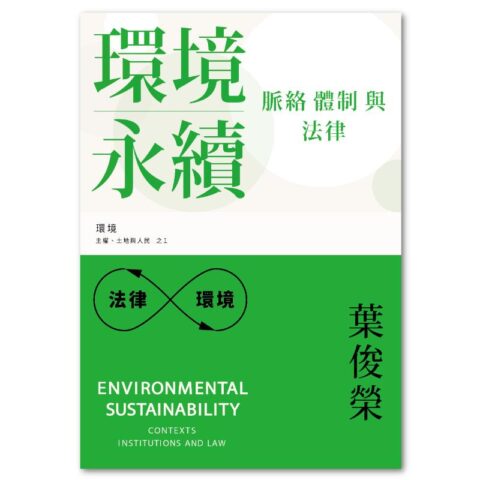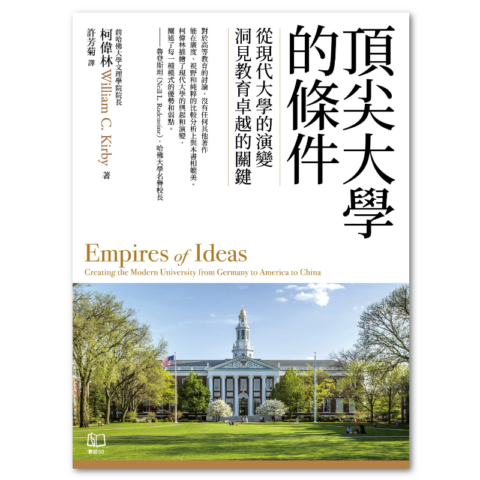誰是外來者:在德國、臺灣之間,獨立記者的跨國越南難民探尋
出版日期:2022-08-04
作者:黃文鈴
印刷:16彩頁+黑白內文
裝訂:平裝
頁數:384
開數:25開,21長*14.8寬*2.1高
EAN:9789570864342
系列:眾聲
尚有庫存
訪問逾50人、越洋串聯德國與臺灣,獨立記者從心而發的萬里追尋。
他們以肉身化作橋樑,來到島嶼,
帶著記憶、文化與語言,從此他鄉變故鄉。
「當我們面對移民或難民,不再是以面對特定外來族群的態度,而是以同為人的身分,在同一塊土地上,往『我們未來如何共同生活』的目標邁進,這個社會是不是就不會這麼分歧了?」
你知道,臺灣曾經接收過難民嗎?
他們在高雄、木柵、澎湖……在你我身邊生活超過40載。
為什麼我們幾乎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
賭上生死的「船民」
1975年4月,越南共產黨拿下西貢,內戰長達20年的南北越就此統一,然而戰爭結束並未帶來和平,反而讓載滿難民的船飄蕩海上。這些「船民」逃難異國,他們的移居擴大了人們對民族與國家的想像。
映照德國與臺灣,不一樣的族群融合之路
《誰是外來者》作者黃文鈴往返德國與臺灣,採訪超過50位越南移民,聽他們述說驚心動魄的親身經歷,書中並陳西德、東德、臺灣三地接收越南移民的方式、政策,探討理想的族群融合可能之道。
● 西德-70年代末,西德因納粹歷史而對越南難民產生共感,民間出資買下救難船,多次出航營救,接納德國史上首批大規模的亞洲難民。
● 東德-80年代,越南政府派數萬契約工至同為共產政權的東德,卻意外遭遇兩德統一,在無融合政策之下,他們與西德船民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 臺灣-越南華僑在越戰結束前後搭乘中華民國政府的軍艦、專機來臺,散居各地的他們自身即是歷史,但我們為何遺忘了這段活生生的逃難史實?
40年了,他們還是「外來者」嗎?
記者黃文鈴以移民身分發出探問:當膚色與文化截然不同,「外來移民要做到成功融入一個新的國家,我們能給出哪些答案?」越南移民已定居德國、臺灣社會逾40年,我們可曾真正探究他們的歷史?是否還片面狹隘地以外貌、膚色、口音區分「你」與「我」?
我們可能在保有彼此相異處的情況下,仍視彼此為一個群體嗎?
各界推薦
【注目推薦】
白曉紅(記者/作家)
李岳軒(獨立媒體《移人》總編輯)
林育立(駐德國記者)
黃雋慧(《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作者)
劉吉雄(澎湖難民營三部曲導演)
【書店推薦】
孩好書屋
苑裡掀海風
飛地書店
晃晃書店
烏邦圖書店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作者:黃文鈴
菜市場長大的孩子。35歲那一年決定離開熟悉的臺灣,目前定居柏林邁入第五年。喜歡這裡的自由跟可能性,但常常想念臺灣各種好吃的美食。
曾獲柏林政府文學研究補助、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文化部青年創作等補助計畫;曾任國內報社記者、《報導者》特約記者,因為想第一線採訪難民,選擇出走臺灣。目前定位自己是寫作者與記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到達很遠的地方,讓更多人聽見受訪者的故事。
推薦序 帶給當下社會啟發的越洋追尋/林育立
推薦序 在困逼與關懷中闖出新天地/黃雋慧
自序 尋找社會融合的最佳答案
主要名詞釋義&越南移民大事記
地圖
序章 我們與他們
第一部 前往異國
第一章 去了西德的越南船民
前言
從遠東來
全體動員
終航
非政府的力量
來到西德之後:船民的真實故事
第二章 飄洋過海的越南移工
前言
時代巨變
不再安靜的越南移民
非法的生活、合法的生活
第二部 前往中華民國
第三章 坐船來臺的越南華僑
前言
越南華僑是怎麼來的?
中華民國政府派艦救僑胞
海漂來臺
越棉寮歸僑
第四章 中華民國政府的仁德專案
前言
從啟航到降落
木柵的越南家鄉味:蘇英葉與阿荷的雜貨店
依親來臺
越南歸僑協會
第三部 抵達
第五章 越南移民第二代
前言
自我認同的糾結
亞洲來的家庭關係
阮氏瓊:被丟來火星的孩子
第六章 北方的小鎮
前言
拿撒勒之家
船民會所
結語 如果我們不把自己隔離起來
後記
致謝
注釋
附錄 受訪人物表
自序(節錄)
二○一七年九月,我隻身離開臺灣來到德國。
當時我辭去任職近三年的報社記者工作,身懷近十年的新聞採訪經驗,我想掂掂自己的斤兩,挑戰擔任獨立記者,目的地就是自二○一五年因敘利亞戰爭而收容百萬名中東難民的德國。
我想第一手採訪那些在戰火中離開家園、在異鄉重建人生的難民們,面對面聽他們說話,寫他們的人生故事。
就因為這麼簡單的起心動念,我開始著手申請簽證、找房子,最後在一期德文課都還沒上完的情況下,落腳柏林,這個先前我只旅行過一週的城市。
至於為什麼是德國?在我離開正職工作不久後,因緣際會透過網路聯繫上一名敘利亞難民阿里,他原本在首都大馬士革是名專業的工程師,但因為拒絕好友邀請加入塔利班,遭到多次暗殺,只好逃離家鄉。我在電腦的這一頭,聽著他鉅細靡遺述說著逃難的經歷,多次千鈞一髮,甚至在匈牙利的監獄遭獄警脫光衣服羞辱。
那通電話是在臺灣的半夜兩點,整整兩個小時過去,我的手心直冒汗,隨著他講到自己終於踏上德國土地,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他在電話那頭笑說,逃來德國的那一天,他在火車上累到睡著、忘了車票放在哪裡,查票員竟然悄悄在他耳邊說:「你是難民嗎?剛到這裡嗎?不要緊,下一站你先下車,但不要出站,避免遇上警察。」這個新國度對難民的友善,讓他至今仍深懷感激。
這是我鑽研難民議題的開端。等我自己也到了德國,陸陸續續寫了多篇關於難民的專題,難民這個詞,不再只有戰火、需要人們施捨的刻板印象。他們有血有肉,許多人雖然背負著逃離家園的創傷,但仍為自己的未來努力打拚,就像你我一樣。
隨著獨立記者的生涯展開,在德國以異鄉人的身分生活,我在難民受訪的話語裡看見自己,聽他們說失語的困境、談人生道路的不確定性。他們不知道多年的等待後是否能得到一紙合法留在德國的居留許可,我當時則是掙扎著在德國只靠寫報導要養活自己究竟可不可行,雖然兩者的命運無法比擬,但同樣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很能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我是出了國之後才深刻感受何謂移民。在西方人的主流社會裡,亞裔族群始終是少數,加上臺灣是個多數國家都不承認的小國。因為這樣,我將關注的視野放諸移難民在德國的發展。我想知道,這個社會怎麼看待龐大的移民群體。我們移民,會一直都是德國社會的外來者嗎?我們和他們,有沒有可能擁有相同分量的話語權?有沒有可能彼此的界線,因為彼此多一點努力,淡去一些些?
因為身為這個社會的少數族群,我很自然在路上特別留意亞洲人的身影。在柏林這個大城市裡,不消長駐,就會察覺到越南人的普遍存在。在這裡,越南菜幾乎與亞洲菜畫上等號,越南餐廳、小吃店遍布,甚至有許多店家兼賣越南河粉與壽司,是這裡的有趣特色。
幾乎每個地鐵站轉角的花店都由越南人經營,尤其是東柏林的花店、雜貨店、衣服修改店、美甲店,一進到店裡,店員們彼此都以越南話交談。我自己也好幾次走在路上被亞裔臉孔的路人以越南話搭話,或被亞洲雜貨店老闆詢問是不是來自越南?
同為亞裔的好感,加上龐大的好奇心,我開始查閱越南移民來到德國的歷史。從「為什麼這裡越南人這麼多?」這個疑問出發,我更好奇,為什麼明明街上隨處可見越南人的身影,但新聞或政治討論裡,卻聽不見他們的聲音?
這本書即是從這個疑問出發延伸出的訪談研究。本書分成三條軸線:七○年代末被西德政府收容的越南船民,以及八○年代透過短期工作契約,來到東德的越南契約工(Contract Workers)。這兩大族群是目前德國的越南移民最主要的來源。我在第一、第二章會分別深究探討他們來到德國的歷程,帶給德國的影響,與這個國家的關係。
第三條軸線與臺灣人民切身相關,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前後,以海軍軍艦、專機等方式,從淪陷的南越接收了數千名越南華僑;一九七七年,由於海漂來臺的越南難民人數逐漸增加,基於人道立場,我國政府在澎湖更興建難民營,成立中南半島難民臨時接待所。
這段史實是中華民國歷史上重要的一頁,記錄著我國曾在援救越南難民上不遺餘力。一般談到難民,會覺得距離臺灣很遙遠,但其實早在四十年前,我們就已經憑一己之力搭了一座橋梁,讓戰火中的人民來到安全的國度。這當中的脈絡會在本書的第三、第四章詳加闡述,並將場景拉回越南華僑最早在越南落地生根的過往古今。
我在開始書寫這本書之前,對於越南移民的認識僅停留在臺灣人一般熟悉的外籍配偶,一直到了柏林才發現這個族群的複雜性,越南因為曾經分裂成南、北越,各自被民主、共產政權統治,和曾經分裂成東、西德的德國,在歷史的軌跡上意外地交會,撞出命運的火花,也是本書一大關注重點……
推薦序2(節錄)/在困逼與關懷中闖出新天地/黃雋慧/《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作者
和文鈴是在二○一九年透過網路認識,當時她正在籌劃寫作本書,蒐集資料的時候接觸到敝作《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之後收到她的來信,希望我能引介一些受訪者。記得在全球新冠疫情前,我每年都收到私信提出類似的請求。做過相關專題的人,都能體會尋人過程的艱難,而且很多當事人未必信任陌生採訪者,文鈴能贏得眾多受訪者信任,成功走完整個書寫過程,實在難能可貴。
處理移民問題有如踏平衡木
《誰是外來者》以一九七八年越南人蛇貨輪「海鴻號」」事件作起點,回顧德國朝野應對一路惡化的印支(中南半島)難民潮。當年難民潮震撼西方媒體的程度,從美國CBS(當時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長壽新聞雜誌節目《六十分鐘》可見一斑。《六十分鐘 》每集一般分成四個單元,每單元一個專題。一九七九年,《六十分鐘 》採訪隊特地飛到馬來西亞探訪比東島難民營,製作越南船民特輯,整個特輯就占盡四個單元。
在這段時間,聯合國開過兩次會議,協調國際社會聯手化解危機。
西德是其中一個積極伸出援手接收越南難民的國家,政府會依據他們的背景提供相關的德語和技能訓練,盡可能協助重拾故業,令我印象深刻。西德政策背後的核心價值是尊重新移民的過往,而新移民愈快適應和投入社會,對國家的貢獻自然更大,少有國家能如此細心。大部分國家的現實,是新移民都做本地人不願做的工種。民間方面,大報《時代週報》,和美國CBS一樣,派人去馬來西亞比東島實地採訪,更大膽承擔安置難民的交通和語言服務的經費。然而要數德國最突出的舉措,就是募款組織人道救援船阿納穆爾角號,在南海搜救遇險的難民船,發揮強大的行動力和人道精神。
阿納穆爾角號出動以來救治的難民上以萬計,數目可觀,但遠在西德,安置難民的配套很難追上速度,而幾年後,阿納穆爾角號一度要緊急煞停。我們一方面會出於惻隱之心,同情逃難的人,但同時也會矛盾:這收容的門會不會開得太大?興許一些富裕國家有足夠資源安置難民,卻未必充份考慮接納的速率;比如配額十萬人,是一年內全入境?還是分十年接納?接納的速度對醫療等各項社會資源的衝擊大有分別。再者,偷渡往往牽涉到蛇頭、人口販賣這些錯綜複雜、黑暗的操作,很多偷渡客都無證件,或用假證件,有很多令人頭痛的現象要克服。作者再指出,面對持久的難民問題,收容國的政府和民間都要拿出無比的勇氣、行動力和智慧去承擔。我更認為,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每個有能力的國家都需要預備一些預建樓房(Prefabricated homes),應付突如其來的危機,除了臨時救濟難民,更可用作安置災民或檢疫。
《誰是外來者》其後的章節也不時刺激思考。第二章涵蓋東德在一九八○年代引進的越南移工,越南統一後,因不事生產以及受到多國制裁、經濟蕭條,故透過輸出勞工賺取外匯,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近日的俄羅斯,因攻打烏克蘭而受到制裁,日後整個局面的布局發展有何異同?
作者也訪問在德國和臺灣的越南移民和下一代,分享種族歧視的經驗及身分認同的看法,移民為免被排擠、被邊緣化,會有意識地尋求主流社會的認可,不時要在不同文化間的夾縫處掙扎。書中的訪問令我想起一個在香港難民營出生的越南青年,他回憶小時候獲得香港居留權後,行動自由了,但母親一下子要在一個語言不通的陌生環境自力更生,深受壓抑,經常抱著他哭,再加上屋內正播放著淒怨的越南歌曲,令情緒更加膨湃,故有段時間他非常抗拒越南歌曲,每次家人一播他就發脾氣,有客人來他就出門,而他就在這樣不時的陣痛中,一步一步成為香港講粵語的一分子……
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一艘原應被銷毀的老舊貨船,卻超載著兩千多名越南船民,在越南政府默許下,逃離祖國。這艘名為「海鴻號」的難民船,意外帶起西德一陣援救船民的熱潮,西德政府甚至史上首度大規模收容亞洲來的難民,掀起七○、八○年代四萬多名船民橫越數千公里來到德國的開端。
這一切全起因於一名德國記者的全民號召。當年四十歲的諾伊德克(Rupert Neudeck),原本只是一名平凡的廣播記者,在聽聞「海鴻號」的慘況後,他決心投入拯救船民的行列。
在普遍民眾還不了解這群船民為何逃離家鄉的情況下,他上電視節目發表演說募款,觸動德國人民曾袖手納粹惡行,最後導致猶太大屠殺慘劇的罪惡感,彌補心態加上對於船民為逃離越共、追求自由不惜離家千里的同情,全民以鉅額捐款熱情響應,共同買下「阿納穆爾角號」。這艘德籍搜救船,拯救了許多漂流在南中國海的難民,帶他們駛向安全的未來。
從遠東來
──────────
英州的回憶 (1)
我們走在荒蕪的海岸邊,腳踩著泥濘,等著來接我們的船,已經過了五個小時。天氣好冷,夜晚的強風呼呼地吹,沒有外套或斗篷得以蔽體。當我們的船終於在清晨四點現身時(它應該要在半夜兩點到,但花了很多時間在躲警察),我以為那只是艘接駁船,會把我們帶到更大的船上。但我錯了,那就是我們要搭的船,長九公尺,寬三公尺,載滿一百二十七人要逃離越南!
我進到船艙,發現最溫暖的地方是引擎室,決定待在這裡,但這是我最大的錯誤,因為其他人跟我想的一樣。引擎室很快就擠滿了人,機器散發出的熱氣加上過多的人,讓裡頭又熱又悶。船總算啟航了,躺在地上的人們像沙丁魚般擁擠,動彈不得。
數小時過後我覺得奇怪,船怎麼還在開?這時旁邊的人告訴我,這一艘船就是我們要搭的逃難船,而不是接駁船。我暈船了,愈來愈虛弱,總算能入睡(感謝老天)。
昏睡間,我聽到一聲吼叫,一名男子試圖在引擎室隔出空位、往裡頭加柴油。突然,引擎噴火了,冒出好大的火焰,我以為自己死定了。所有人都被濃煙嗆到,但大家都保持冷靜。此時船長走來引擎室,發現他的助手添加的不是柴油,竟然是水!船長把水倒掉,重新加滿柴油,我們的旅程終於得以繼續。
外頭很黑,有人尿在船艙裡。甲板上沒有廁所。我好渴,但沒有人給我東西喝。在黑暗中我爬至一處夾縫,這裡有新鮮的空氣進來。突然間,我發現角落放著一罐大瓶的檸檬汁。我不知道那是誰的,仰頭一飲而盡喝個精光,再把空瓶放回原處。我決定待在這裡,因為這裡才有新鮮的風。
後來船長拿起那個空瓶,大聲咒罵,因為裡頭是空的,我這才發現,其實自己待的地方是船長站著控制船的地方。
隔天早晨我上了甲板,仍可以看見頭頓的山,表示船開得還不遠。我很怕被海巡抓到,但另一方面卻又想被逮捕,因為這樣才有存活的機會。我坐在船尾,可以摸得到海水,這個位置離水面大概才二十公分。海豚隨著船揚起的波濤玩鬧著,因為牠們想和船玩。在我心裡,前方等著我的只有死亡。很奇怪,那時我對死亡再無恐懼,也許是因為當下的死亡太過真實。
有人給我幾塊北越士兵戰時吃的乾糧,我只吃了一小塊,因為太硬太乾了,我口好渴,用手盛了海水來喝。一開始覺得好多了,後來嘴巴好乾,讓我覺得更渴,身體又虛弱不已,便陷入沉睡。直到一位爸媽的朋友找到我,把我帶到他在船上的位置,給我水跟乾酪。因為暈船,我只喝了幾湯匙的水就吐了。
隔天下午,暴風雨襲擊海面,大海的顏色由藍轉墨,船長決定停航、挺過這場風暴。坐在甲板上,我可以看見波濤洶湧的浪如何包圍小船,我們就像一葉扁舟,載浮載沉。我很確定,一道巨浪將擊中我們的船,將我們帶到死亡的深海底。海水逐漸滲進船內,船長於是命令一些人拿桶子將水舀出去。漁船通常都是木船,用樹脂黏合而成,水自然會滲漏進來,但如果引擎還啟動著,水會自動排出。而此時我們的引擎是關著的。
這是逃難途中第二次我覺得自己應該逃不過死劫。船上的人們此時依著各自的信仰喃喃祈禱著。我不記得這場暴風雨持續了多久。
後來有人大喊:「有船!」我們看到前方有艘大船,以為已經到了公海。那艘船朝我們駛近,船長拿著望遠鏡,趴在甲板上,試圖想找出那艘船的所屬國,但徒勞無功。他命令婦女跟小孩上到甲板,男人則藏在船艙(婦孺的畫面能引起憐憫)。船長問有誰會說英文?可以和那艘大船的人溝通。一個男人自願前往,他提議,上到大船甲板時,他會用繩索將我們的船綁在大船上,如果那船來自東方國家,他會大聲地哭,我們得立刻切斷繩索逃離(當然他會因此被犧牲留在大船上)。
那艘外國船愈來愈靠近,船長關掉引擎,以船槳控制船隻。
時間彷彿停止了。四周靜悄悄的,只聽得見胸膛底下心臟跳動的聲音。
當兩艘船近距離靠近時,我們突然聽見對面的擴音器傳來越南話:「這是德國船隻阿納穆爾角號。我們是來拯救你們的。請保持冷靜,我們會把梯子放下。婦女跟小孩會用起重機將人帶到船上……。」
我們得救了,我們活了下來。一些人開始哭泣、交叉著雙臂仰望天空。
我們的船倚靠著大船,相比之下我們的船好小,從引擎室走出來我只看見大船的船身,其他什麼也看不到。所有的人都被撤離到大船上,難民船則被船員用大船的錨砸爛(怕引起其他船的事故)。這一刻我覺得有點心痛,因為這艘小船保護我們度過暴風雨,帶領我們邁向自由,現在它則孤單地被遺留在大海底。
阿納穆爾角號開始動了,這次全速前進,因為這時船隻還在越南水域!不久,暴風雨來了,即使巨大如阿納穆爾角號也開始劇烈搖晃。我又開始暈船。
在船上的越南籍助手(有些是已經逃到德國的越南難民,志願擔任阿納穆爾角號的助手)向我們解釋,阿納穆爾角號的船長已經在雷達上發現我們一段時間,他持續觀察我們,預備我們到達公海就會來搭救,但他同時也發現一場颶風就要來臨,如果他不在越南海域出手救我們,我們永遠也到達不了公海。
我們的船是該船拯救的第十二艘船,也是該次行程獲救的最後一艘。現在船隻得航向新加坡,阿納穆爾角號要將難民們交給難民營,補充新的糧食與飲水,更換執勤的船員。
我不知道阿納穆爾角號停靠在新加坡時,那些還在海面上的難民船會發生什麼事,希望他們找到其他能救援的船隻。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多達二十萬到四十萬的船民死在海裡。
──────────────
海鴻號
十月底的天氣仍然炎熱,海象不甚穩定,越南頭頓港卻停留了一艘船身五十公尺長、重達一千五百八十噸的貨船。港口前大排長龍,人們帶著簡單行囊、攜家帶眷,搶著擠上這艘船。
距離南北越統一已過三年,南越人民逐漸認知衰敗的經濟看不見復甦的可能,種種迫害、驅逐境內華僑的政策,讓他們忍無可忍,決定踏上征途。
搭上這艘「海鴻號」的多是越南華人,越南政府剛實施針對華僑「公開」的放行偷渡。許多有管道、家裡還有一些錢的,紛紛趁這個機會搭船逃難。「海鴻號」也是其中一艘政府默許得以出海的大型船隻,先前早就打點好了,每人上繳的船費十六塊金條(當時等值約三千兩百美元),其中有十條進了越南官員的口袋。
貪心的越南政府不顧船長反對,原本預計僅收一千兩百名乘客,最後卻強加一千三百餘人,全船乘客因而多達兩千五百六十四人,遠遠超過船隻能承受的載重。
逾三十年船齡的「海鴻號」自湄公河三角洲啟航,一路駛向印尼,卻被強風吹離了航道,途中更遭遇麗妲颱風侵襲,引擎因此故障。糧食與水耗盡後,船隻試圖靠岸印尼卻遭拒絕,僅答應補給水與糧食。
十一月九日,船長在無奈下,只好下錨於馬來西亞巴生港三海里處,尋求馬國庇護,但馬來西亞政府聲稱船上乘客因付錢給越南政府才得以離境,拒絕承認其難民身分。不僅如此,更派遣軍船日夜巡迴,嚴禁船民偷渡上岸。停泊在馬來西亞外海的「海鴻號」糧食逐漸耗盡,長達近兩個月的征途,人們飽受酷熱天氣曝晒折磨、疲憊不堪。在醫療衛生條件極差的狀況下,疾病逐漸在船上蔓延。
馬來西亞並未援助「海鴻號」糧食或水,反倒任由擠滿甲板與船艙的難民在破爛的防水油布下勉強抵擋烈日曝晒,其他鄰近國家也不顧這艘超載的貨船在海上與命運搏鬥。「海鴻號」在漫長航行期間已有兩名船民死亡,停錨馬國外海時又有一人因病過世。船上的人長期無法沐浴,加上過度擁擠,許多人身上長滿紅疹,皮膚病爬滿全身。
獲准上船採訪的記者如此形容眼見的驚人景象:
我們真的就是踩在人的身上,其中有男有女、有小孩跟老人,躺平的或是蜷縮在一起的,他們明顯非常疲累、全身發抖。
.東方的猶太人
當時越南難民雖前仆後繼逃往鄰國,西方國家卻鮮少聽聞他們的處境。直到國際媒體揭露「海鴻號」的慘狀,許多人透過電視看見奄奄一息的難民,才知道他們的存在,國際社會隨即掀起討伐馬國的輿論巨浪。
馬來西亞當時已收容約三萬五千名難民,難民營早已人滿為患。為了遏止助長人蛇集團公開偷渡的歪風,馬國原堅稱這些人非法入境,最後在強大輿論壓力下,開出條件讓難民登岸:船民須先獲得第三國收容保證,船則拖出公海暫時擱置,由各國協商安置。
這波人道救援聲浪也在德國逐漸沸騰。看到船民冒著生命危險渡海只為逃離越共,勾起德國人傷痛回憶。許多人認為這些越南難民的處境如同二戰後一千萬名逃往西德的東德居民,不顧一切只求脫離共產黨統治。恰好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迷你影集《納粹大屠殺》(Holocaust)於西德上映,披露一九四○年代猶太人大規模逃亡的劇情更是推波助瀾,讓人聯想到舉家逃難的越南船民,後者甚至被視為「東方的猶太人」或「亞洲的猶太人」。如今向這些船民伸出援手,猶如幫助納粹時期遭受苦難的猶太人,對於西德人而言是種遲來的彌補。
當時,一名十五歲的中學生甚至親筆寫信給西德政府:
越南難民的困境如同當初的猶太人大屠殺……在希特勒時期沒人敢言,敢說話的人都被毒氣毒死了,沒有人能幫他們。但現在我們必須幫助他們。
這些中了樂透的人
下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總理阿爾布雷希特(Ernst Albrecht)也透過電視報導看到海鴻號難民的慘況。再過一個月就是耶誕節了,西德街上洋溢著歡樂氣息,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此情此景與瘦得皮包骨的船民相比,彷彿平行世界。
他隨即做了明快的決定:下薩克森邦無條件、並率全德之先,接收一千名越南船民,自此拉開德國接收越南難民的序幕。
這些下薩克森邦接收的難民當中,有多達六百四十四人、兩百零八個家庭都來自海鴻號。西德媒體形容,這些人就像「中了樂透」。海鴻號難民被不同國家收容,其中西德收容人數在西方國家中,僅次於美國。
十二月三日早上七點,首批越南船民搭乘波音七○七客機,飛越一萬兩千公里,終於降落在漢諾威朗根哈根機場,結束長達四十五天的海上惡途,踏上西德國土。
這些遠道而來的亞洲難民,提著塑膠袋,裡頭裝著所有家當,身上還穿著夏季衣服,腳上踩著涼鞋,一下機冷得直打哆嗦,醫護人員趕緊為他們披上棕色的羊毛毯子。候機室備好了熱茶、雞肉湯跟米飯。大批媒體早已等候多時,一見船民出來,對著他們不停按下快門。
親自來接機的阿爾布雷希特鼓舞難民們:「我們知道你們所遭遇的劫難,也感同身受。」
「你們已經到了一個能自由生活的國家,不會再受任何人欺壓。你們不需感到害怕,儘管帶著勇氣與樂觀開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