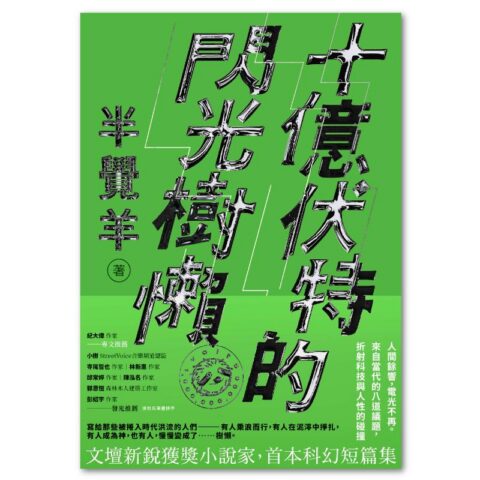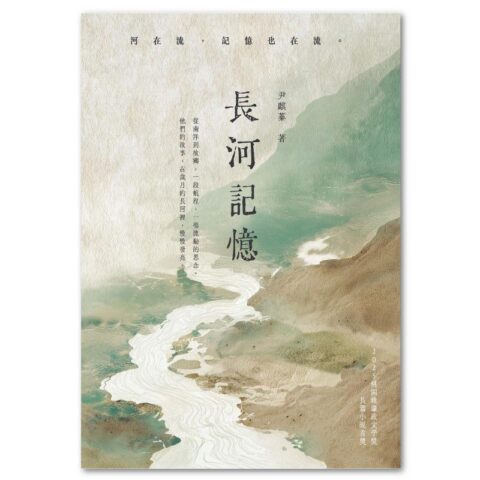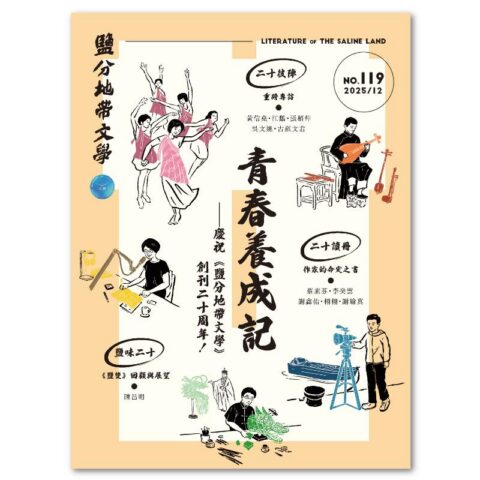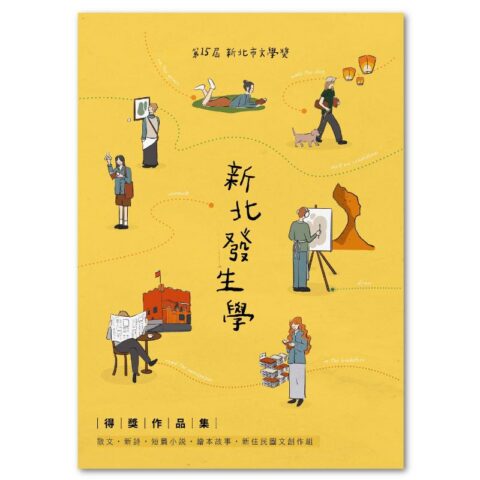風景線上那一抹鮮亮的紅
出版日期:2021-01-28
作者:韓秀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04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1.8cm
EAN:9789570856903
系列:當代名家‧韓秀作品集
尚有庫存
2020年美國總統國家與社會貢獻獎得主
唯美的字句饗宴.雋永的篇章盛會
日常的每一個瞬間都是雍容美善的風景
我心底裡的光焰是對人性至美的無懈追求。
──韓秀
王爾德說:「我們都在陰溝裡,但是,仍然有人會仰望星空。」在沒有戰亂的承平歲月裡,我們依然時時被許多煩惱攪得六神無主方寸大亂。韓秀的書寫撥開似雲似霧的迷茫,讓我們看到璀璨的星空。在這些溫煦、明亮的星辰照耀下,眼前豁然開朗,腳下也堅實起來。
韓秀把生活過成美的樣子,於人,於事,於物,在在脫不了美的核心。從深度積累的古老文明,到親切美麗的嶄新世界,有豐美若普羅旺斯或曼哈頓,也有一道貧瘠而荒蕪的地平線,無論叱吒風雲的拿破崙,又或縫紉百衲被的平凡母親,韓秀都能發現其不為人知的隱密之處,進而彰顯出其絕非尋常的魅力,以文字輝映出迷人的嫵媚姿態。
對世間美好的無比珍惜,是韓秀源源不絕的筆耕動力,她以不計生死的帝王蝶自喻,要將吉光片羽好好留下,成為不褪流行的永恆。
作者:韓秀
出生於紐約市,在臺海兩岸居住過三十七年,現居美東華盛頓近郊北維州維也納小鎮。讀書、寫作,時不時歡喜遊走在世界各地的書展、書店、博物館、畫廊。
曾經任教於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研究所。1983年開始華文文學寫作,為海內外華文報刊撰寫近四十個專欄,為美國《漢新月刊》撰寫的書介專欄至今已經是第十四年。兩度擔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長,2020年榮獲美國總統國家與社會貢獻獎。
著有自傳性長篇小說《亞果號的返航》(《折射》之新版)、《團扇》、《多餘的人》;短篇小說集《親戚》、《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散文集《雪落哈德遜河》、《尋回失落的美感》、《文學的滋味》;文林憶述《尚未塵封的過往》;書話《翻動書頁的聲音》、《永遠的情人:46篇藏書札記》、《喜歡,是一粒種籽》;藝術家傳記《林布蘭特》、《塞尚》、《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神的兒子:埃爾.格雷考》等四十餘種。《多餘的人》英文版The Unwanted於2020年8月問世。
自序 獲獎理由
輯一
當美學教育成為唯一的目的
從一張菜單說起
多年如一日
在托斯卡尼尋訪卡拉瓦喬
溫柔的霞光
小鎮盛景
美麗的藝術家們
唯美的世界
明淨的世界
風從莫拉諾吹來
秋的旋律
走近現代藝術
那一個下午,白浪如練
永遠的風景
古蹟捍衛者
當代英雄
一部電影的意義
輯二
酒神的微笑
庫司庫司—特法伊阿
次颶風時速八十英哩
風景線上那一抹鮮亮的紅
親密的接觸
花事
偶遇
琵琶玓的黃家老宅
密林深處一小屋
問候塞尚先生
何須道別
尋找良醫
正當瘟疫蔓延時
二○一五年三月下旬的世界
誰是紅石頭先生?
誠信無價
選票的聲音
歷史上的這一天
馬爾商與拿破崙
輯三
遙望遠天之上那溫煦的星辰
老師,您瀟灑如昔
痛悼太乙姐
魏子雲教授與海內外金學研究
山水靜好
距離在消失中
雨,終於落下來了
填平十一年的溝壑
如果生活不是這般難耐
下坡路,慢行
人情之常
灰色的背影—回憶梅蘭芳先生
脾氣
那雙藍眼睛不再明亮
當星星殞落的時候
海神波塞東的指紋
奔向普林斯頓
活的紀念碑
地標○英哩
百分之三十俱樂部
一個離我們很近的地方,叫做索契
當一條河變成了毒龍
自序/獲獎理由
二○二○年十一月一日,週日,寒風蕭瑟,樹葉即將落盡。我寫完這一天要寫的段落來到後園將這一年最後的鮮花剪下來插瓶,大捧的桔梗便用輕柔的淡紫色、冰藍色妝點了前廳。然後,走出前門,用小掃把清掃簷下懸吊著的暗綠色的「小燈籠」,帝王蝶的蛹。
鄰家的五歲小女孩瑪芮帶著小狗貝貝正站在人行道旁我家郵箱下那一叢普羅旺斯薰衣草前。她喜歡用手輕撫這香草,不但放到鼻子下面聞個不停,還伸手讓貝貝聞香,狗兒搖搖尾巴,並不領情。
瑪芮常來,曾經親眼看著帝王蝶在花叢中飛舞,在乳草馬利筋上產卵;卵變成幼蟲,拚命加餐,將乳草青翠的葉子吃得乾乾淨淨;然後,這些毛毛蟲就沿著植株、牆壁爬上我家門廊,僅憑著一根細絲懸吊在簷下。瑪芮常常驚恐地指給我看,說是蟲兒要掉下來了,怎麼幫牠們一把才好。我總是安慰她,帝王蝶絕頂聰明,牠們能夠克服任何艱難險阻。果真,成排的小燈籠順利地懸掛起來了。兩週之後,從那小燈籠裡面成功脫身出來的帝王蝶只有一位。我和瑪芮親眼看著牠從比牠小得多的蛹裡掙扎出來,舒展一下身體,然後就振翅飛走了,飛向三千英里之外的墨西哥。瑪芮淚眼模糊地問我:「牠什麼時候回來?」我跟她說,只要我門前的乳草健康茁壯,帝王蝶就會回來,只不過,不是現在飛走的這一位,而是牠的孫兒們。瑪芮的眼淚流下來了,她跟我說:「帝王蝶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勇敢的物種。」何止如此,大自然以怎樣柔韌、堅定的力量造就了這麼偉大的物種。
這一天,瑪芮親眼看著我把那些已經乾癟的小燈籠收拾乾淨,沒有掉淚,只是很嚴肅地跟我點頭問好,帶著貝貝回家去了。我知道,帝王蝶的壯麗行程感動了這女孩,她在這幾個月裡長大了。
回到房裡,電話鈴響,老友的聲音:「下午一點鐘,你方便嗎?要送個東西給你。」非常時期,友人送東西不是放在門外就是塞在郵箱裡,哪裡還需要打電話約時間?除非是善本書。老友不但是政治家、經濟學家也是藏書家,難不成機緣湊巧遇到了珍本書要跟我分享?於是喜孜孜答應了老友,回書房查核資料,準備第二天的寫作,完全忘記了老友在白宮任職這回事。
準時,門鈴響,手裡提著白宮的大紙袋,眼睛裡滿是疲憊的老友到。原來,疫情煎逼、選情緊張,日理萬機的白宮主人卻還掛念著默默耕耘的文化人,要頒個獎給我。週日,老友為了這件事竟然親自開車來。似乎讀懂了我的心思,未等我開口,老友已經摘下口罩:「你哪裡有什麼週日?還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這倒是實話。
沒有隔著六英尺遠的距離,老友從紙袋裡取出已經裝裱好的大獎狀送到我手裡,打開手機讓我看到總統為獎項簽名的照片,把一枚沉甸甸的金質獎章掛到我胸前,拍照存檔。最後是一頂白宮的棒球帽,充分展現白宮主人的幽默感。我從來沒有過這麼一頂舒適、漂亮的帽子,忍不住笑了起來。老友也笑了。
正事辦完,我問:「我可不可以請你喝杯茶?」老友搓搓手:「太好了。」半年多來,這可是第一次,有人走進家門,不僅摘掉了口罩而且樂意坐下來喝杯茶。
捧著熱騰騰、香噴噴的天仁蔘茶,我們坐在書房外的陽光屋,遠離了殘酷的政治,遠離了艱難的經濟,我們談文學、談文藝復興,從義大利談到西班牙談到克里特談到德意志。看著方桌上有關杜勒的一大堆書,老友問:「下一個不眠不休的旅程?」我脫口而出:「不計生死,就像帝王蝶。」老友點點頭:「國家與社會對你這樣的人表達禮敬是應當的。」告別時,精神已經大好,疲憊已經一掃而空,老友又說:「文藝復興當然非常重要,也絕對值得你全力以赴;不過,你有多久沒有出版散文集了?你的散文很好看的,海闊天空驚喜連連,就像跳躍著的光焰。人需要光焰照亮內心,順便照亮腳下的路。」可不是,我的出版雖然從未間斷,卻真的有足足十二年沒有出版散文集了,那種飄逸不定自說自話的肺腑之言,我心裡想。老友點點頭說:「我等著看。」
幾天以後,地方報紙記者來電:「恭喜獲得總統獎,請問獲獎理由是?」
獲獎需要理由嗎?我一時怔住。對方說:「寫一條消息,獲獎理由是需要的。」
我同老友的相知相惜自然是不方便暴露的,於是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不了了之。
夜深人靜,捫心自問,支撐著自己耕耘文字三十八年的動力究竟來自何處?說到底,是對世間美好的無比珍惜。神說,要有光。我心底裡的光焰便是對人性至美的無懈追求。我相信,口罩、六英尺間隔、鎖國、封城都不是最終戰勝邪魔的利器。歐洲文藝復興的輝煌粉碎了瘟疫、戰爭帶來的漫長暗夜,給我們留下了豐沛的文化遺產。我們能不能像帝王蝶那樣不畏任何艱難困苦,將吉光片羽留在世上呢?念及此,豪氣頓生。
將五十幾篇文字挪到電郵窗口,按傳送鍵。我知道,臺北無所不能的編者定能將其化作一本美麗之書。這本書大概也就可以成為「獲獎理由」的最佳詮釋。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寫於美國北維州維也納小鎮
當美學教育成為唯一的目的
金秋十月,大家都往新英格蘭方向去賞楓,我卻決定要往南走,不是十哩八哩的路程而是整整一千英里的距離。那地方在哪裡?朋友問我。在佛羅里達,東邊還是西邊?東邊,靠近奧蘭多。那個鳥兒不下蛋的地方,除了迪士尼遊樂園之外還有什麼?朋友嗤之以鼻。那地方最近來了大量的紐約客,咦,你不是也要在那裡買房子吧?朋友露出高深莫測的表情,盯著我不放。
噢, 當然不是。我只不過要向一對夫婦表達我的敬意而已。他們姓McKean,在奧蘭多北邊的Winter Park 建造了一家博物館,真正承擔起美學教育的重責大任。朋友支吾說,從來沒有聽說過。
雖然是資訊氾濫的二十一世紀,少為人知的人間至美依然多著呢。
十九世紀中葉,十七歲的少年Charles Hosmer Morse 進入一家機械製造公司,年薪五十枚銀質美元,七年之後,二十四歲的莫爾斯進入公司高層。之後,他有膽有識地買下公司,並且逐步成為十九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機械製造業鉅子,富甲一方。巨大的財力使得熱愛藝術的莫爾斯成為美國藝術的大收藏家。他不喜終日喧騰的芝加哥,雖然他在那裡揚名立萬,他卻珍愛佛羅里達的氣候宜人,尤其喜歡冬之苑的靜好。於是,他在那裡廣為置產,並且在那裡退休。
莫爾斯夫婦育有一個女兒,女兒熱愛藝術,婚後也生了一個女兒,名字叫做Jeannette Genius Morse。乖巧的小婕涅特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外祖父與母親的大量藝術藏品使她在幼年時期已經等於是生活在博物館裡,而她對第凡尼玻璃的認識更是與生俱來,因為家裡的長窗、桌上的花瓶與檯燈正是第凡尼的作品。幼年時代與外祖父在冬之苑的生活也奠定了她日後為此地奉獻一生的感情依據。外祖父在她十二歲的時候故去了,母親在她十九歲的時候也故去了,那時候,正在求學的婕涅特已經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藝術家,她離開了人去樓空的芝加哥大宅,轉向冬之苑,她在那裡的Rollins College 求學,並且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七五年在校董會裡為這所大學服務了三十三年,為大學提供了豐沛的資金,從美國名校延聘知名學者、作家來到羅琳斯學院執教,成為大學最可靠的支持者。
婕涅特與羅琳斯學院藝術系教授Hugh Ferguson McKean 的結識也是緣於外祖父藝術藏品的收藏與展示方面的技術性問題。沒想到,兩人一見鍾情,結為連理,攜手為美學教育的推廣努力。兩袖清風的教授修在婚後更擔任了羅琳斯學院的校長長達十八年之久。權勢與財富沒有改變這位學者的人生態度,他只是更加努力地將人文的藝術的創意付諸實施而已,最偉大的建樹自然是 Th¬e Charles Hosmer Morse Museum of American Art 在冬之苑的建立以及第凡尼藝術品的搶救工程。
一九五七年,位於紐約長島的第凡尼故居拉瑞爾頓莊園遭到大火。那時候,整個莊園已經賣出且被閒置,完全無人居住。空屋遭到祝融之災成為廢墟。第凡尼基金會沒有財力買回更沒有財力修復,第凡尼的女兒給修寫信,希望馬崁夫婦「也許有興趣買一扇窗戶」。因為兩年之前,正是由於馬崁夫婦的大力促成,第凡尼藝術品在羅琳斯藝廊得以盛大展出。我們可以想像,當修與婕涅特抵達長島,站立在殘窗與斷壁之間面對那一片焦黑的時候,他們是怎樣地震驚與心痛。
馬崁夫婦當下做出了決定,他們將買下這全部的廢墟,搶救所有的殘片,盡一切可能修復之。這個決定使得這對夫婦在美國藝術史上留下了永遠的輝煌。這對默默付出的夫婦所付出的不止是無法計量的金錢,更是他們的生命與心血。全部的修復工作在半個世紀之後的一九九九年才完成,那時候,婕涅特已經辭世十年,而修也故去五年了!每念及此,我總是忍不住熱淚盈眶。
現在,我走進了莫爾斯博物館,面對著一扇樸實無華的木頭大門,上面有一個浮雕十字,在這扇門的後面就是曾經曇花一現然後「消失」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第凡尼重要作品,第凡尼禮拜堂(Ti any Chapel)。今天的人們不知世界上有這件珍品的不知凡幾。從拉瑞爾頓莊園移來的這扇木門是鑲嵌在影壁上的,繞過影壁,我們面對的是歷史的、藝術的、文化的整體結晶。禮拜堂以莊嚴、浪漫、輝煌烘托出的質樸懾人心魄。四層半圓形穹頂十二根廊柱呵護著祭壇。祭壇後方的壁上,冠冕之下,兩隻正在開屏的孔雀成為華麗的極致。所有的一切都是用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彩色玻璃鑲嵌而成的巨大馬賽克建築。如此的登峰造極卻不給人難以趨近的感覺,層層臺階以平實的大理石鋪就,立面近大遠小,彩色馬賽克裝飾成活潑的圖案,似乎在召喚著人們的親近。有著拜占庭風格的禮拜堂卻沒有拜占庭的森冷與清臞。大堂正中的天花板上懸吊著三度空間的巨大十字燈飾,巨大的鮮嫩綠色的玻璃與無色透明鑽石般的水晶玻璃交相生輝,那種一覽無遺的瑰麗是典型的第凡尼風格了。雖然,在禮拜堂裡宗教故事不可或缺,但是第凡尼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圓窗上的人物豐滿、圓潤,甚至有些喜氣洋洋。走進這裡的人們不會心生戒懼,反而會滿心歡喜。禮拜堂側殿的受洗之處是一個美麗的球體,那是一個受洗盆,不舉行儀式的時候,半圓形的蓋子是闔攏的,它讓我想到古希臘阿波羅神殿中那世界的「肚臍」,是那樣的自然而風趣,人與神之間大約可以那樣親如兄弟的罷?而這受洗之處的後壁則是巨大的第凡尼長窗,水之濱,白色百合花盛開著,這是對生命的禮讚了。
博物館的設計善解人意,知道我們是多麼希望親近這美麗之所,所以允許觀者直接走進受洗側殿,沐浴在花影之下,享受美麗的球狀「受洗盆」帶給每一個人的無限慰藉。
但是,親愛的來訪者啊!你們能相信嗎,這樣純淨的美好竟然曾經深陷地底
不見天光!而且曾經遠離塵世達百年之久!
一八九三年,盛大的哥倫布世界博覽會在芝加哥舉行,第凡尼禮拜堂堂皇展出,吸引數十萬人參觀、讚歎,報紙上的評論更是花團錦簇。博覽會結束,一位教友將禮拜堂買下,捐贈給正在創建中的紐約聖若望大教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哪裡想得到,這個教堂的建築師與主教根本不欣賞第凡尼更不喜歡這個禮拜堂,認為這「新拜占庭」風格的作品不適合聖若望,並且堅決地表示,這個禮拜堂應當永遠不見天光。第凡尼公司忍辱負重,將禮拜堂的穹頂拆掉一半以適應聖若望大教堂地下室的高度。整個禮拜堂縮在黑暗的角落裡,完全失去了在博覽會中的光彩。
一九一六年,聖若望教堂的地下室水深盈尺,禮拜堂完全成為「棄物」浸泡在水中。第凡尼寫信給主教,他在信中說,禮拜堂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積水對這件作品絕對不利,既然現在教堂棄之若廢物,不如讓第凡尼公司給禮拜堂換個地方。那一年,那位捐贈者也故去了,主教完全無所謂,就讓第凡尼將禮拜堂拆遷了。拆遷過程痛苦不已,禮拜堂不但被砍頭削腳,那巨大的懸吊燈飾也不翼而飛了。第凡尼公司將這幾十萬片玻璃運到長島,在拉瑞爾頓莊園裡,與主體建築有一小段距離,蓋了一所房子,將其成為一個完整的禮拜堂。如此這般,又經過幾年的努力,這美麗、祥和的禮拜堂才恢復了在博覽會上曾有的輝煌。修復工作也苦澀不堪,因為產權還屬於聖若望教堂。直到一九三五年,路易斯.第凡尼去世兩年之後,主教大人才高抬貴手將產權還給第凡尼公司。
一九五七年的大火將拉瑞爾頓莊園的主體建築破壞殆盡,禮拜堂的損失不是太大。經過第凡尼親手修復的禮拜堂與拉瑞爾頓的其他殘片一道被再次搬運,抵達冬之苑。馬崁夫婦的大力援助對於困窘不堪的第凡尼公司而言是巨大的鼓舞。藝術家們紛紛熱情投身這一漫長的修復工程。那最後一次的搬遷也是笑中有淚。一家名譽極佳的搬運公司接受了馬崁夫婦的要求,將這些「廢物」從紐約運到佛羅里達,那時候州際高速公路尚未通車,那搬運工作是比較漫長而辛苦的。抵達之時才發現,所有的殘片只是胡亂與廢舊輪胎等等一道堆放著。「因為,這實在都是廢物呀。」搬運公司坦言。藝術家們不再多說,小心地將全部殘片放進預先準備好的巨大工作間,自此開始,每一片玻璃才真正回到專家們手裡,清理與修復的巨大工程於焉展開。
現實現刻,我坐在博物館對面軒暢的咖啡館裡,從人聲鼎沸色彩斑斕的遮陽棚下看著對面這座鋼筋水泥的堡壘。她與周遭浪漫的西班牙建築完全不同,窄小的窗戶完全沒有採光的作用。但是,水、火不侵,固若金湯。馬崁夫婦給基金會最後的指示:「這所博物館不能成為冬之苑的負擔,而應當為此地帶來繁榮。」我們周遭的一片欣欣向榮正好是最貼切的佐證。
在二○○七年,這個為第凡尼作品以及玻璃藝術量身打造的博物館一日門票三元美金,可以多次出入。外子與我從咖啡館站起身來再次走進這家完全靠燈光照明的博物館,設計高明的燈光會使得玻璃如同寶石、如同飛瀑、如同花瓣與飛旋的樹葉、如同佳人細緻的肌膚,給人不同的「觸覺」與感受。我長久站在整個展覽空間第一幅作品前面,那是一百一十年以前,路易斯.第凡尼為英國商人Joseph Briggs 所創作的一扇彩窗,黝暗的背景中心是異常明亮、歡快、鮮豔、怒放著的一束玫瑰。外子站在一間展室的中心,長久凝視那些雖然不能再修復但是依然是玻璃工藝極品的「片段」,它們被仔細地鑲嵌在透明的裝置裡,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欣賞它們,想像它們在原來的創作中所擁有過的燦爛。當我們終於在博物館即將關門的時分緩緩步向出口的時候,一件作品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歸來。工作人員大大方方在我們面前將作品取出,仔細懸掛回它原來的位置。眼前一亮,正是那幅《飼火鶴》。
當美學教育成為唯一目的的時候,美好與祥和的實現便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