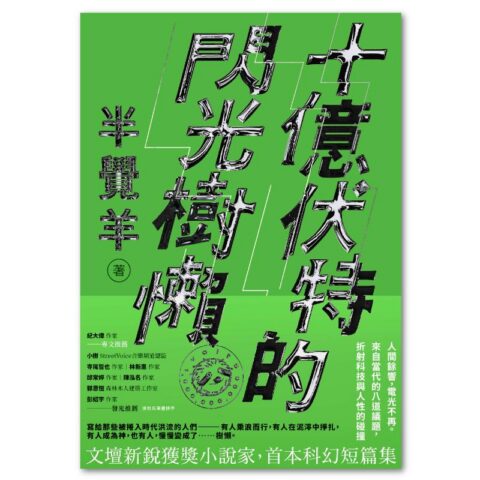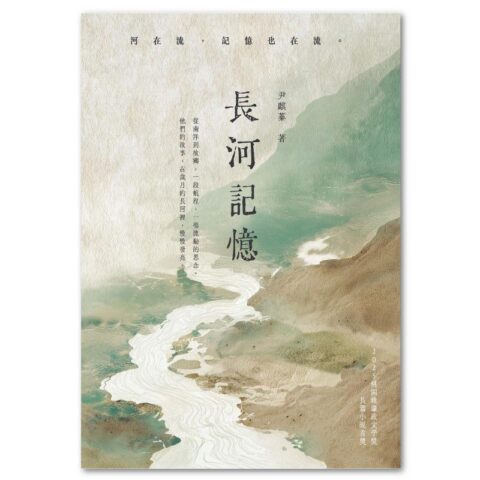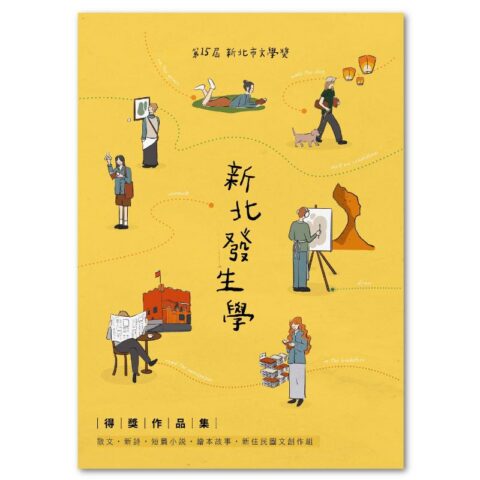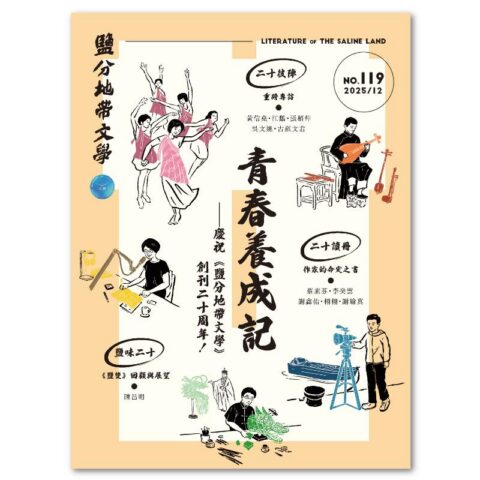高空三萬呎的人間報告:一位空少的魔幻飛行時刻
出版日期:2020-07-08
作者:柯嘉瑋
印刷:黑白印刷+部分彩頁
裝訂:平裝
頁數:296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1.9cm
EAN:9789570855449
系列:聯經文庫
尚有庫存
飛行,作為一種逃逸路線!
31則飛行記事和隨拍,為渴望飛行、嚮往暫離的人們,
體現不存在於地面的想像和哲思。
空服員上下班最為空白的時間,是往返機場和市區的時間,以及待在外站的時間。
我既是填補空白的人,也是被空白填補的人。
從地面到空中,從研究生到空服員,曾考取飛行證照,後接受航管員訓練中。身分的轉換,空間的移動,飛行狀態的思索,柯嘉瑋為那些渴望飛行、嚮往空中的人們,提供不同於地面的故事和插曲。
近三年的空服員工作經驗,曾透過部落格抒發些許對飛行生活的感觸,將在空中和地面的魔幻時刻下了最好的註解。包括:
空服員的日常工作、下機後的輪班生活、遇到的乘客百態、與同事間若即若離的夥伴關係……等。
除了空服員的日常隨筆,他也試圖就身分轉換的視角與空間移動的變化,輔以哲學家思想,試圖替讀者和他自己提出另一種──關於飛行的想像和哲思;更捕捉了長期有飛行時差的人們獨有的瑣碎樣貌,以及專屬飛行生活的人才能體認到的渺小瞬間。
專業好評
原來空服員可以看到如此之多怪形怪狀(比惡形惡狀更有趣)的乘客,而空服員作為一組觀察與被觀察的服務團體,自身的怪形怪狀亦不遑多讓。……如此魔幻卻又無比寫實的場景,永遠有著超穩定秩序中最不可預期的場景調度。
───張小虹|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
本書不會告訴你如何成為一位專業且稱職的空服員,但如果你正同處在一樣的天空裡飛翔,亦是嚮往、好奇著這片藍天裡可能發生的一切事物。那麼,這本書你絕對不能錯過!
───艾迪摳|人氣旅遊部落客
高空推薦
Emily|千萬人氣部落客&空姐報報EmilyPost版主
艾迪摳Eddie Ko|人氣旅遊部落客
張小虹|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
蕭如萍|華航看板空姐
(依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柯嘉瑋
高雄人。大學就讀政大英文系、雙修廣電系。臺大外文所碩士畢業。原本已經申請到博士班的獎學金,卻因緣際會踏入航空業,目前打算在航空業逗留。有時候寫點字、有時候寫點歌,倒不自認是創作人;有時候喜歡望著機場看飛機起降,倒也稱不上是航空迷。曾任空服員,手上有還不知道可以做何用的飛行執照。正在往成為一位合格航管員的路上前進,試圖看到天空的另一種模樣。
推薦序 天空作為一種逃逸路線/張小虹
推薦序 飛翔,亦是嚮往/艾迪摳
飛行線・序
空少・地面
「空少」
表單上的我們
巧遇
班表
待命
交換
文明禮節
飛行線・1
空少・天空
家
妳是一陣令人驚厥的狂風
外籍
水的模樣
熱
「小時候」
輪休的技巧
輪休睡不著的時候
飛行線・2
她的美麗故事
空少・天空
輪休睡不著的時候
瘋子
布蘭琪
傲慢與偏見
登機證
拿督
Just a Normal Flight
飛行線・3
空少・地面
縫線的生活
樑柱下
窗外
公車站旁
房間裡
病床上
點餐檯邊
下次
飛行線・結論
空少們(筆記)
作者的話
這是一本「半」自傳文集。
所謂「半」,包含了兩種模式。
首先,文章內容包含了「半自傳」的成分。空服員和研究生的所思所為某種程度上都是基於自己過往的經驗所寫出來的。特別是空服員的部分。
再者,這是一個在身分上把自己切成「一半」的書寫。這一半是那個曾經身為空服員,而那一半是那個曾經身為研究生的自己:都是已經回不去的自己。我將他們召喚回到同一個平面上,以書寫呈現在大家眼前。
論及寫作時間軸的話,所有歸在「空少」章節的文章都是「事」發當下寫出來的,而所有「飛行線」章節的文章則是「事」(不論是研究生、不論是空服員)隔許久後,寫出來的文字。看起來像是以身分做基準,把兩個篇章切割得壁壘分明。但是現在仔細想想,曾經是「空服員」這一半和「外文所研究生」那一半的自己早就彼此交織在每個文字裡。
我便是從這一半和那一半之間的互動出發,產出這本文集。
這裡不會有任何人生態度的啟示,也不會有任何成為空服員或外文所研究生的教戰守則。但是我希望可以展現出來的,是以不同光源照射這些身分的生活切片,讓這些切片投影在文字裡頭,分享給大家。
推薦序文/天空作為一種逃逸路線|張小虹
總喜歡在課堂上一講再講,那個有關「雨傘」與「蒼穹」的意象。
人們慣於撐起雨傘做自我保護,還在雨傘的內面精心畫上一整片蒼穹,然後開心地在蒼穹之上寫下自以為是的信念與意見。但詩人和藝術家則不同,她/他們要做的不是自欺欺人,蜷曲在保護傘裡安全度日,而是勇敢割裂那畫在雨傘內面的蒼穹,讓宇宙混沌的自由之風吹入,讓透過裂縫乍現的一絲光亮啟動靈感。
這個文學意象最早出自二十世紀英國作家勞倫斯(D. H. Lawrence),而後被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希(Pierre-Félix Guattari)寫入兩人最後一本的合著專書《何謂哲學?》。雖然兩位作者在書中已竭盡全力,一心想要將複雜的哲學概念,以較為簡易平直的語言加以表述,但仍無法避免理解上的難度,故偶爾出現的文學意象,就顯得特別生動近人。每回在課堂上提及,總會瞥見學生眼中閃動的會意眼光,只是不記得,嘉瑋是不是也在其中。
總以為當嘉瑋再次跟我連絡時,應該就是博士論文已順利完成,躍躍欲試申請教職的時刻。沒想到嘉瑋交出來的不是談論英美文學的博士論文,而是一本在三萬英呎高空思考生命的文學創作,驚喜之餘,推薦信也就如此這般變成了推薦序。
《高空三萬呎的人間報告》不是散文,不是小說、也不是論文,而是一個大膽打破文類分界的創作實驗。在敘事結構上以「他」和「我」的分裂與雙重展開,「他」是一位男性空服員,在飛機客艙的「生活劇場」裡見證人生百態,「我」則是一位埋首桌前趕寫論文的研究生,一心想要從德勒茲與瓜達希的哲學理論中,鑽研出一整套有關身體-客艙作為「解域烏托邦」(deterritopia)的新思考與新倫理。「他」和「我」像是一對最親密的友人,但也三不五時鬥鬥嘴、吵吵架;「他」和「我」不斷演繹著從身分認同到生活形態的差異與斷裂,但也如攣生子一般交錯共存在不同的時區,或天上地下相互映照。
但若妳/你以為《高空三萬呎的人間報告》就只是這樣一本充滿深奧抽象思考的書,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對於常常搭乘飛機的我而言,本書讓我大開眼界,也大飽眼福,原來空服員可以看到如此之多怪形怪狀(比惡形惡狀更有趣)的乘客,而空服員作為一組觀察與被觀察的服務團體,自身的怪形怪狀亦不遑多讓。本書讓我了解到空服員的職業特性、工作場所的辛勞與危險,可怕的待命室,有趣的交換機,複雜的班表,甚至那永遠不知從何而來的客艙積水,突然之間飛機客艙變成了如此魔幻卻又無比寫實的場景,永遠有著超穩定秩序中最不可預期的場景調度。本書也是一本最實用、最溫柔的搭機手冊,讀完之後讓我悄悄立下心願,下次搭飛機若非必要,絕對不點特別餐,免得忙壞廚房組員,絕對不在飛機降落前購買免稅商品,免得讓空服員手忙腳亂,而客艙有如萬花筒般的小宇宙中,充滿了太多我們可以因了解而體諒的細節之處,可待再次體驗。本書徹底改變了我習以為常的搭機經驗,一切變得如此有趣,像迷宮,也像推理小說。
所以我喜歡書中對「沒有-時間」的哲學分析,從線性到強度,我也喜歡那跳接在Tori Amos歌聲與印度德里馬路安全島上揮舞著螢光綠塑膠球棒的小女孩之間的敘事技巧;喜歡書中以平針縫線談網際網路,也喜歡將印度文比做突然起霧的早晨丘陵地之幽默巧妙;喜歡書中對階級意識的反思(商務艙與經濟艙,高等國國民與低等國國民,資深與資淺空服員),更喜歡那在七月的雅加達撞見《百年孤寂》馬康多的感性。而這些來自閱讀的歡喜讚嘆,讓我終於放下心中的一大困惑,為何嘉瑋沒有依循既定計畫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原來他想成為寫作者的不安靈魂,遠遠強大過成為學者的循規蹈矩。
或許這一切只是一個美麗的意外。嘉瑋是臺大外文研究所難得一見的奇才,碩士就學期間就已發表英文學術期刊論文,並積極飛到世界各地參與學術會議的論文發表,而別人至少花三年時間才得以完成的研究所學業,他破天荒地以兩年時間完成,並交出一本精彩的碩士論文,以「解域烏托邦」的自創理論概念,解讀加拿大女作家艾特伍(Margaret Atwood)的小說。就在我滿心期盼這位難得一見的奇才,能早日完成博士學業的同時,我似乎忘了嘉瑋在大學時期曾是劇場導演,拍過短片,會作曲,愛寫作。直到拜讀完《高空三萬呎的人間報告》的初稿後,我才恍然大悟,雨傘裡虛假繪飾的蒼穹,如何滿足得了他要探勘宇宙星雲的那股強大能量。
他逃了,逃到三萬英呎的高空去思考何謂哲學、何謂人生、何謂文學書寫。他逃了,他勇敢割裂了雨傘,讓混沌宇宙的自由之風,直灌而下。《高空三萬呎的人間報告》是他風塵僕僕、歷劫歸來的書寫報告,也會是他前往下一個未知浩瀚宇宙的出發預告,飛行即逃逸,有風有雨也有陰晴,但對書寫者而言,回家最近的路永遠是離去。
我有個空少朋友,後來我們不聯絡了。
他是個奇怪的傢伙。好比說,他下班後常常不開手機。他的說法是,他喜歡待在天空的感覺。不開機可以延長待在天空的時間,只要誰都找不到他,他就可以宣稱自己還在飛。
我說,你這不就是駝鳥心態嗎。他說,鴕鳥心態是逃避的心態,但是他沒有逃避任何事情。「我可是積極正面的在天空逗留呢」,他笑著說。視訊那頭幾乎看不清楚他的臉,因為他剛下班,在大巴上。深夜車裡只有外頭路燈打進的光線夠我看到他模糊的輪廓。「姐們都在睡覺,我不能講太大聲,下次再聊。」我心想,你總是有那麼多詭論,在天空逗留什麼的。似是而非又新奇有趣,卻又那麼單純。他是個奇怪而簡單的傢伙,不知道他積極正面的逃避著什麼呢?
■
吉爾・德勒茲與菲力・瓜達希,既是各自發展哲學概念的哲學家,也是同時合力著作的哲學組合。當兩人合著時,我們除了知道作者是「德勒茲與瓜達希」之外,著作內容完全不會提及哪個段落出自哪位之手。雖然許多人已經習慣把兩人合著作品裡頭的思想統稱作德勒茲的思想,但我總覺得,若我是瓜達希,大概難免對德勒茲產生一點瑜亮情節吧。即使自己心裡明確知道是「德勒茲與瓜達希」,口中講著的,始終是「德勒茲」。
我也不知道,每次提及「德勒茲」的我,心裡是不是總有把兩個人,或是兩個人作為一個人的「德勒茲與瓜達希」,或是,這一組刻意的、不願意被區分的「德勒茲—瓜達希」作者連結,給確確實實地放在心裡。兩個人連寫作行為本身都不離自身的哲學,致力在一種「連結」形成的瞬間,在那瞬間可能會產生的一種高張的強度,致使更多可能性得以創生。或許每次只提及「德勒茲」的我,也可以這樣替自己辯解:身為哲學家的德勒茲與瓜達希,兩人在合著時,德勒茲不是德勒茲、瓜達希也不是瓜達希;當然兩人也不是「德勒茲與瓜達希」的「加法」組合。當「德勒茲—瓜達希」這個哲學組合在闡述哲學概念時,他們儼然成為一個外於「德勒茲」或「瓜達希」,也外於「德勒茲與瓜達希」的一種連結。這種連結,是一種強度、一種創造哲學概念的強度,一種得以「解畛域」故有束縛、讓創意得以逃離無形枷鎖的能量。也因為這種外於姓名的哲學組合無法被語言給圈限住,因此我只好稱這個「德勒茲—瓜達希」連結作「德勒茲」。懷著一點偷懶被抓到那般的罪惡感,也懷著幾分面對未知力量的崇畏。
■
他總是分享許多大大小小飛行相關的事。聽多了,總覺得好像我也是個空服員那樣,知道空服員工作大概是怎麼一回事。他的故事對我而言說不上身歷其境,反而像是絮叨聽多了,自然而然就理出一套頭緒。也或許因為我不是個太常搭飛機的人,對於客艙的印象總是模模糊糊,經過他(總是稍嫌繁冗的)敘述之後,對於客艙好像因此產生了更明確的理解,也能更加自在的從他的敘事(抑或是碎念)裡頭抽絲剝繭。
「反正,這份工作就是這樣。」這是他最常下的結論。
反正,有哪份工作不就是這樣?曾有一回我這樣回應他,但是他很快就繼續抱怨在飛機上遇到的某一個,他覺得不斷在刁難組員的客人。我跟他說,下飛機就忘了吧,反正出了機門各自的生活就彼此無關。生活還是要過不是嗎?
但是我無法想像的是,當我說「生活還是要過」的時候,他是怎麼理解「生活」的呢?
是不是因為我自己的生活太過微不足道、太過平凡,所以才開始對別人的生活產生好奇呢?又特別因為,他的生活有好大一部份發生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在天空裡的生活——,所以我才會思考這種叫人難以面對的問題——「空中的生活是什麼呢?」我知道他從來沒有想過這種問題,所以我也從來沒有問出口過。我可以猜想他的回答又會回到那套,「不過是工作」之類的說法。
「但至少,」我像是替自己辯解那般(但是辯解什麼呢),「你們可以暫時逃開一些煩人的事,飛出去就沒人能管你。」煩人。凡人。我以為飛上天空之後的人就不是凡人,也不會煩人。他總是沒好氣地回答,「你不懂啦。」因為在天空中發生的事情不會因為重力而掉到地面上,既然不會掉到地面上,自然就不是我們這些在地面上的人可以理解的事。
從他的單眼皮裡頭我解讀不出任何線索。關於他的生活的線索。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討厭單眼皮的傢伙。
■
一九六零年代尾聲的法國。德勒茲在哲學界已經展露頭角,瓜達希在精神分析學界也開始發展起色。但是兩人彼此不認識,連學術上的對話都未曾發生過。即便兩人的共通點大抵是各自採取激進的姿態發展哲學或是臨床思想。彼時德勒茲已經出版了至今依然為人稱道的哲學著作《差異與重複》和《意義的邏輯》等,並且在里昂大學授課;而瓜達希也是個頗具地位的精神病理學家,在著名的La Borde精神病院為病人看診,同時也參與許多激進的政治活動——當時的精神分析學界哪裡能想像後來瓜達希以反叛的姿態發展出「精神分裂分析」呢?
德勒茲與瓜達希透過共同好友認識,兩人在第一次見面後一拍即合。當時德勒茲正積極投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雖然很弔詭的是,德勒茲對於精神疾病的臨床一點興趣都沒有,他甚至直接表明自己無法與精神疾病患者共處一室——大概也是為什麼德勒茲對瓜達希始終保有一種崇敬。而對於擁有豐富臨床經驗的瓜達希而言,德勒茲的哲學概念發展既創新又具革命性,再加上兩人在思想上的一致頻率,為兩人提供了強大的力場,透過頻繁的書信往來,兩人交換彼此對於精神分析、對於「欲望」作為一種思想機器等等的概念,他們的第一本合著《反伊底帕斯》不久後將要席捲哲學界以及精神分析學界。
當德勒茲談及兩人的這種特殊寫作關係時,他也描述到,兩人都是把自己置放在某種狀態,在這種共有的狀態裡頭產出的文字,自然無法辨識出哪個段落出自誰的筆下。若真的要對這種狀態給予一種形容,莫不如說是兩人早已具備一種得以釋放出哲學概念的頻率,當哲學概念藉由兩人的交談與書信往來越發成形時,他們便會將概念用文字鋪展開來。於是在書寫的當下德勒茲不是德勒茲,瓜達希也不是瓜達希。而是透過哲學概念的創造而貼擠出來的「德勒茲-瓜達希」。
但是實際上的稿子到底由誰下筆,又由誰審稿定稿呢?我們大可猜想德勒茲或瓜達希都會說——你問錯問題了。
■
或許因為他太把一切當做稀鬆平常,讓我更想知道這些在天空中工作——抑或是「生活在空中」——的人,過的是怎樣的日子。我曾經問過,你們在飛機上都吃些什麼,長程飛行的時候在哪裡休息,通常會飛什麼地方——他有一回在語言中透露了輕蔑,「我超討厭別人問我是飛國內線還是國際線。」——,一架飛機通常會有幾個空少,打算一直飛下去嗎,最喜歡去哪個國家,休假都在做什麼……。每當我提出一個明確的問題,他便以最草率的態度回答(「我們有組員休息區」、「飛哪裡都差不多」、「休假都在睡覺」,諸如此類)。雖然知道這種輕率不真的來自他的個性,他大概也只是懶得回答問題而已。
我並不著迷,只是好奇。希望這聽起來不像是辯解。
而當我轉向其他話題,好比說,問到他休假沒有在睡覺時的生活是什麼,他又會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起他的工作。說他討厭飛大陸班、哪個經理又在發神經、覺得哪個客人很可憐、一起飛的某個「大哥」同事又在騷擾他,覺得好累不想做了。一開始我還會好好的聽他抱怨,試圖要他不要隨便放棄這份聽起來很不錯的工作,但是到後來,「那就離職吧」似乎才是最理想的答案。
每當他聽到我說「那就離職吧」,他會立刻回答「我不要」。再過兩秒,「但是又有點想。」我說,你就是口嫌體正直。「你這是什麼意思?」他無辜地問。雖然他曾經說過,想要在離職的時候把所有在公司遇到的事情寫起來。我說,「很好,看來這些東西永遠都不會被寫成了。」想當然爾,他沒有聽出裡頭的諷刺,也只是反問:「為什麼?」
也或許,這些東西的確都沒什麼好寫的。一旦開始仔細思考,他的工作對我——或是像我這樣的一般人——而言,大部分都是可以想像的。或許,把地面生活的一部份像是影片那樣剪下來、貼到空中的客艙裡,幾乎可以完全貼合也不一定。而兩者之間無法密合的部分,造成的疊影會不會類似光暈、貼擠出來若有似無的映像讓人無法直視,因為越想要看清,只會越看越迷離。飛機上的飲食是怎樣的飲食,飛機上的人際關係是怎樣的人際關係,地面上的東西在飛機上會變成什麼樣子(為什麼我直接假設飛機上的任何東西都會變得有點不一樣呢)?我好奇的,關於他的空中生活,是否正是這種疊影?
這種疊影,是謂一種「生活的變體」。我擅自這樣定義,不管他同意與否。
我一邊望向圖書館外坐在石梯上的情侶對著日暮天光彼此摟抱,一邊想著,不知道他落地後會不會立刻傳訊息給我。這次不知道是不是又會遇到怎樣奇怪的同事或是客人。
■
一般所提的「飛行」,大抵意指帶有「行」功能的「飛」。本文意圖打破「飛」與「行」的附屬關係,將「飛」與「行」進行創意連結為「飛-行」,並且以空服員作為「飛-行」展現之場域,探討空服員在客艙裡頭與空間和時間之關係。客艙作為空中之生活環境,其結構和運作模式幾可比擬一種烏托邦之建構,然而此「烏托邦」實為一種「去歷史、去經濟結構」的烏托邦,而空服員作為在此烏托邦內移動之身體,確實打開了一種身體與客艙空間、客艙時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將探討客艙空間如何作為一種特殊的「解域烏托邦」,透過德勒茲-瓜達希發展之「逃逸路線」和「解畛域化」理論,討論空服人員如何與此空間和時間/時差之關聯發展出一種「第三」時間與空間,藉以思考空服員與客艙之間的創意連結如何創造而生。
■
我們的生活,到底哪裡不一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