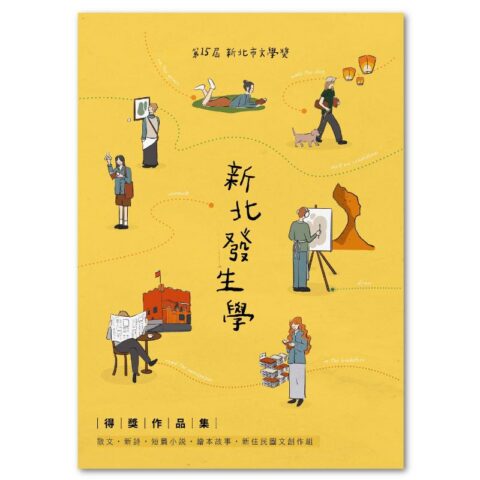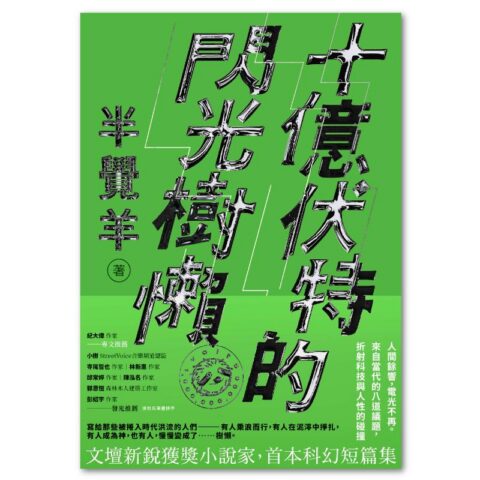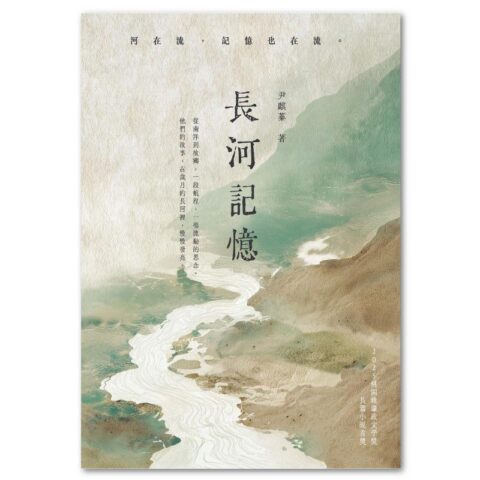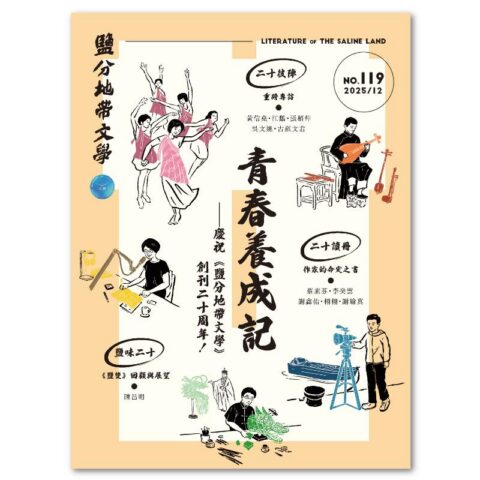初生的白
出版日期:2017-10-20
作者:羅任玲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96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50161
系列:當代名家
尚有庫存
詩是密碼,是飛行,是海洋。
詩是至大,是極微。
詩穿越一切。
一切都將過去,唯有詩會留下來。
首刷隨書附贈羅任玲攝影作品暨親筆書寫書籤一張
一共三款,隨機出貨
全書攝影作品均由羅任玲拍攝,圖文並表,譜出生之初與詩之初。
早慧的羅任玲,從十一歲起開始創作新詩,迄今詩齡已超過四十年。她的創作主題多元,以充滿感性的語句,書寫理性的世界,從個人情感記憶,到宇宙無常生死,藉由筆下反思,深刻地探索與追求至美的境地。羅任玲表示:「詩必須是藝術,反過來說,任何的藝術形式也都是詩的變貌,詩意的延伸。當不同形式的詩通過藝術被記錄下來,自會產生力量。」
《初生的白》是羅任玲自2012年以來的總結。在這五年中,羅任玲經歷了最沉重的生命淬鍊,然後一步一步由混沌陰滯,行至明亮潔白。如同她所說的:
見證殘酷,並非為了恨,是因為有情。
為了記住美好。
※ 名家推薦
白靈:
她冷眼看世界飛舞和飛滅,心再波瀾卻自能定靜,如俯身下看的海,如深藏地底數丈的井,其中隱藏的眼,深不可測。
孫維民:
她的詩最精華之處,在我看來,仍在於呈現某些核心的、亙古不變的主題:生命和死亡,時間及永恆,人的苦難與可能的救贖。她以風格獨殊的詩行描述現象,對於答案則保持機警,時常存而不論。時常以奇特的角度切入主題,某些看來並不特別困難的詩,卻有其複雜深刻的一面。
楊佳嫻:
羅任玲的詩講究顏色,氣氛,意象優雅精確,透露對於人間的求索與悲憫,結尾往往提升到精神、哲思的層次。換句話說,她的詩滿足了愛文學藝術的人對於美的渴望,並試圖往餘韻、境界的方向探求。她承繼詩既言志又抒情的傳統,重新提醒我們,美乃一種偉力,是人身人心在一時空針尖點上的飛揚與凝縮。
作者:羅任玲
喜歡秋夜。老樹。星空。荒野。大海。幽深之境。
台師大文學碩士,著有詩集《密碼》、《逆光飛行》、《一整座海洋的靜寂》、《初生的白》,散文集《光之留顏》,評論集《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2020年出版散文集《穿越銀夜的靈魂》。
自序 穿越那片廣大的祕密花園
輯一/紀念
櫻樹
野地
旅行時帶回來的一朵雲
陌生人
湖畔
微悟
紀念
也有
葉子
寒露之後
祕境
回憶錄
致某蝴蝶
後巷
沙
雨中庭院
秋天的世界
巨大的養雞場
眠夢
那時候
時間的塗鴉
妄念西雅圖
午夜的瓶子
蝶影
彩色的回憶
往事吃剩的星星
時光之廊
輯二/在命運幽暗的走廊
渡口
時空的切面
化武兒童
天空與釘子
夜
無止盡的
繭
童工
一張照片
片縷
遊行
鳥街
致貝拉塔爾
虛空
綿長
顫藍
小強
細微
再見小強
飛行袋
小倩
夢中餐桌
殊途
聖靈們來過了
墳
彩葉芋
龍門遇雨
勝
故事
銅像
少年樹
平安夜
吻
港口
輯三/圓滿之歌
海角之甍
在島上
黑暗之歌
觸鍵之歌
星窗
巴爾蒂斯
冬至
月光緩緩照在岩壁上
圓滿之歌
輯四/初生的白
今晨
沒有
蓮
春晨
冰上
清明
曬衣場
夏日的回憶
在秋天安靜的早晨
鉛筆盒裡的馬
收穫
但願
比砂礫更小的
不存在的梳子
孩子們
奔跑的雲
我要送出遠方
通霄火車站小女生
山行者
早春
因為美
秋夜三帖
初生的白
就在昨天
森林小屋
四季的目光
渡船
後記 並非虛無——致「多出來的一生」
穿越那片廣大的祕密花園
0.
至今我還清楚記得,帶著母親轉搭許多趟地鐵,穿越那片廣大的祕密花園,來到遙遠陌生的修道院博物館。寧靜美好的午後,像夢一樣。
那是二○一三年的夏末,為了帶二姊「回家」。
中世紀的修道院博物館,幽靜無人的下午,我和母親在沁涼的石造建築裡走著,沉默地看著那些中世紀的人像、傢俱、祈禱室。陽光從高高的窗子透進來,那些製作人像的手、祈禱的人,早就不在了。而我想著,剛剛才離開不久的二姊和哥哥,現在都去了哪裡?光影迷離交錯,母親在一旁靜默不語,我始終看不清楚她的表情。那個下午,我拍了很多照片。
兩年後,母親也離開了。
被時光封存的,永恆的夏日,永晝般的祕密花園。
隱喻一般的夏日花園。腐屍,蛇蛻,蚊蚋,豔麗至極的奇異花卉。
邪惡,美善,歡愉,眼淚,疼痛……
沒有母親帶我穿越無始無終的暗黑,
穿越時空邊際,來到這個世界——
這一切根本不會發生。
而詩是那,點亮一切的關鍵嗎?
1.
更往前呢?
一家人都還安然的二○一二年立冬。
從車站出來,天色將暗未暗,依稀見得一絲天光。L問我,接下來要去哪裡?我說,要去一個地方。總是這樣,每當別人問我要去哪裡時,我總這麼回答,其實這地方從來不曾存在,但我無法跟別人解釋我要前往的是一個抽象的地方。
更多時候,是心的穿越……
走上木棧道不久,一隻黃犬跟了過來,是流浪狗,從牠下垂的尾巴和隱隱露出的排骨就知道牠流浪很久了。我停下來,牠也站定了,用細長而尾梢吊起的眼睛看我。那樣狐疑。
同樣是生存,牠的存在對這世界有任何意義嗎?
那麼多卑微的命運。
放眼這幾無人蹤的冬日深林,落日,遠方不明人家的炊煙。
裊裊升起的,生之欲望。無常之跡。
那些破碎的,生之片斷。
2.
詩是穿越那無常之跡的拼圖。
當我穿越那些無人知曉的時刻,像穿越一片荒蕪的神祕野地,困難的沼澤。有時暴雨有時天晴,更多時候是濃霧。我必須自己撥開那些荊棘。生命從來不曾應允簡單。心的旅程只能自己前往。
一直到很晚,我才體會到,死亡(之暴力)是生命最大的禮物。
不曾穿越死蔭的幽谷,如何知曉生之可貴?(雖然這個「生」常常看來如此荒謬。)
萬物皆然。
赫拉巴爾說的:「我們都是掘墓者,帶著准假單來到這個世界。」
一切擁有都是暫時,豈只我們最心愛的人事物,還包括我們自己的肉身。
肉身短暫,唯詩永恆。
3.
詩是穿越。
從十一歲被學校派去參加全國兒童作文比賽,寫下那首不成熟的現代詩算起,我的詩齡已超過四十年了(可惜是即席創作,沒帶回原稿,只記得也是描寫夏日花園)。當年由父母陪同到師大領獎,且在校園留影。那個愛詩的孩子。每次我回到師大,彷彿都能在校園裡遇見她。那個青澀又倔強的,不喜規範,不愛上課,總往大自然裡跑的孩子。穿越這麼多年的時光,來到現在,依然視詩為一切。
我與她,那麼遙遠又那麼近。
是詩,讓那些消逝的雲煙歲月又重聚了。
早就不再有人派我去參加什麼比賽。繼續寫詩,是為了和靈魂在一起。為了讓離開的成為永遠。為了萬物有情。
莫忘初心。
生之初與詩之初。
詩是密碼,是飛行,是海洋。
詩是至大,是極微。
詩穿越一切。
一切都將過去,唯有詩會留下來。
並非虛無——致「多出來的一生」
1.
二○一五年初夏,我常常陪母親搭社區小巴去醫院。盛夏日午,蟬鳴聲中,我們經過一排超市前的綠蔭。從前母親爬完山後,總喜歡坐在這片綠蔭下看報紙吃早點,有時候小橘貓會從背後拍她肩膀,母親就分牠一點吃的。母親一直很有動物緣,但凡她遇見的動物都愛她。牠們一點也不糊塗,知道誰善良誰不能靠近。
就在盛夏的某一天,那片綠蔭的肢幹全部被鋸斷了。剩下一截截光禿的樹身,難堪可憐地曝曬在烈日之下。我和母親從醫院回來,走在失去遮蔭的烈陽下,我惋惜地看著那些不再有遮蔽能力的樹,像看著受重傷的家人,想流淚。母親沉默地經過那些樹,並沒有抬頭。
母親後來不再去爬山了。沒有綠蔭,也沒有了蔭涼的野餐。
記憶中的那個盛夏,幾乎沒有蟬鳴。或許因為無處棲身。我卻在那炎熱盛暑,繼續和母親往返在醫院的路上,路旁是光禿的樹影,我們截了肢的家人。如果可以,我願意繼續陪伴母親,這樣長長久久地。直到那些受了傷的家人重新長出綠葉,母親重回它們的懷抱。
可是沒有,盛夏很快就過完。秋天來了,我最愛的秋天。從高遠的晴空到雨絲漸漸飄落,日影幽暗下來。
秋天剛過完不久,母親也離開了。
母親這一生,恬淡低調而自足。我從沒見她大聲罵過誰,再困難的事也沒聽她抱怨過。就算在生命最後遭到那樣殘忍的對待,她也只是悲傷而非恨。
不只是母親,我很小就知道,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在對岸一個名為「三反五反」的鬥爭運動中,被加諸莫虛有罪名,活活遭凌虐至死的。屍骨丟棄在荒野。鄉里都清楚他們是大善人,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全部捐去造橋蓋學校,辛苦種田的米當作薪餉,自掏腰包請老師來小學堂教書。那麼善良的人,生命卻結束得如此悲慘。
我始終記得小時候因為這件事,內心深處的憤怒、悲傷和不解。或許為了抹去過早的暗影,這件事我幾乎不曾行諸文字,雖然它的確比我經歷過的中壢事件,更早成為我質疑人性的源頭。如今母親痛苦離世,記憶中的那抹陰影再度從暗黑中醒來。
鬥爭是什麼?人體試驗(或各種活體動物的試驗)是什麼?這些我全無興趣。我只知道,一個人或一個動物一株植物,如果是「非自願的原因」被迫死亡,那就是不可原諒的殘忍。
肉食動物殘暴,絕大部分是因為不那麼做牠們會餓死。人類的殘酷,卻可以有種種理由或根本不需要理由。不只是我的母親、祖父、曾祖父。還有更多我不識的人,更多我不識的動物和植物,在這人類主導的殘酷劇場中活著或死去。
究竟是什麼原因可以讓一個柔軟嬰孩,離棄最初的空白,逐漸向黑暗靠近,終於長成一把鋒利的屠刀或嗜血的斧頭?我不知道,過去沒有答案,將來也不會有答案。
做為一個誠實的書寫者,不可能略過這些。
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詩也不能只是控訴,否則它與「一日壽命」的新聞報導何異?詩必須是藝術,反過來說,任何的藝術形式也都是詩的變貌,詩意的延伸。當不同形式的詩通過藝術被記錄下來,自會產生力量。
我不知那力量會有多大,但只要詩與藝術存在一天,那力量就會綿延無盡。我始終相信著。
我不免也想起攝影家克里思多.史托翰,他鏡頭下的「陰影世界」:在籠中用大手緊抓柵欄的黑猩猩,牠絕望的眼神;患了傳染病,在柴堆中即將被燒死的小男孩,他絕望的眼神;廣島原子彈受難者的臉孔標本,他無聲吶喊的嘴;破了一個大窟窿的,野地裡的墓碑……我久久凝視這些照片,久久,感受到一種刨心的痛,和震撼。我想起了母親臨終前,絕望的眼神。
我想起「在命運幽暗的走廊」裡,那些「天上/地下/幽幽前行的隊伍」。這世界的瘋狂和殘忍遠超過我的想像。
這世界的美也遠超過我的想像。
美麗星空下的荒蕪人世。只要還有呼吸,倖存者的日記就該繼續寫下去。
見證殘酷,並非為了恨,是因為有情。
為了記住美好。
2.
母親離世之前,我一直以為,活著,而且呼吸,是多麼天經地義的一件事。年少時,我因厭煩這殺戮爭鬥不斷的人世,常怨怪母親為何要把我生下來。
母親聽著我的抱怨,從沒說過一句話。
母親走後半年,我才知道她當初並不打算生下我。這一生是多出來的。
有段時間,我坐在母親空了的房間裡。看日影掠過窗檯,陽台上的植物漸漸變得黯淡,天地模糊起來。她鍾愛的小貓鬧鐘,在黑暗中還滴滴答答辛勤走著……。我還找到一個她珍藏的小獨角馬音樂盒,像靜靜秋光熟睡在櫥櫃一角。小獨角馬長著一對透明羽翼,瑩白的盒面彷彿夢中之雪。打開盒蓋,上緊發條,那音樂清揚悠遠,一如旅人的歌,漸歇漸止。這一切,真的都只是幻象嗎?如果我沒有來到這一世。
我翻開櫥櫃中的老相簿。想像當年被困難生活鎖住了的,疲憊的父母。三個女兒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兒子。每天被生計追著跑被四個孩子追著跑,他們有一千個理由可以不要這個多出來的我。尤其是母親,父親常年在外辛苦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她幾乎一人扛起照顧全家的責任。我無法想像她是如何做到的。
櫥櫃裡還有當年她寫給父親的一封信:「……我希望能努力維持一個家的溫馨……」
她終於決定留下我。從來,我只是任性的小女兒,擁有絕對的寬容和自由。如果沒有這些,我不可能拿起天馬行空的詩筆。
後來我變成母親的朋友,母親的姊姊。更後來,她變成我的小女兒。我帶她去很多地方。母親安靜、不多話,喜歡美好的事物,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旅伴……
思念母親時,父親也會來到這裡,坐在母親常坐的小椅上,轉動那只秋光音樂盒。
父親說,還好母親當年把我生下來,否則這個家現在怎麼辦?
離開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守著這個漸漸變得冷清的家,覺得離開的人都並未離去。這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的沙堡。
我漸漸明白了,什麼是值得的,需要在乎的。什麼是可以捨棄的。
詩是那不可能的夢中雪。純粹。透明。瑩白。
詩是最美麗的結晶體。
我但願能向那純粹更靠近一點。向靈魂,向真實,更趨近一點。
那必然是我多出來的一生,最大的意義。
詩集命名為「初生的白」,無非也因為此。
這本詩集,是五年來複雜心境的總結。(當然,還有一些更早的,例如〈黑暗之歌〉、〈星窗〉、〈巴爾蒂斯〉、〈妄念西雅圖〉、〈一張照片〉、〈繭〉。)在編排上,我特意將沉鬱近黑的放在前面,而逐漸趨向輕盈趨近白,無疑也是對自己的期待:我不希望在黑暗中停留太久。
從前我不喜歡談自己的事,但現在我想開始寫曾祖父、祖父、父母,更多人,甚至更多動物植物的故事。用詩用散文用我能記得的眼睛耳朵和心。我想讓這個世界知道,真實活過的生命,不會永遠被拋棄在荒野。
在一朵雲的奔跑裡,一棵樹的年輪裡。如果可以,我願意安靜地,用多出來的剩下的後半生。看秋夜裡的月亮升起,看大海映照星空,寫下我記得的。
這個淚中帶笑的世界。
一切都並非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