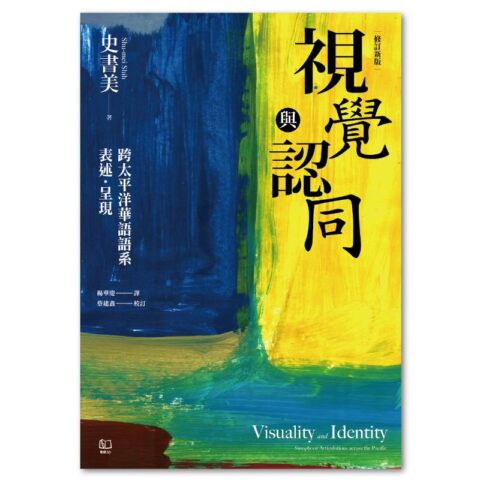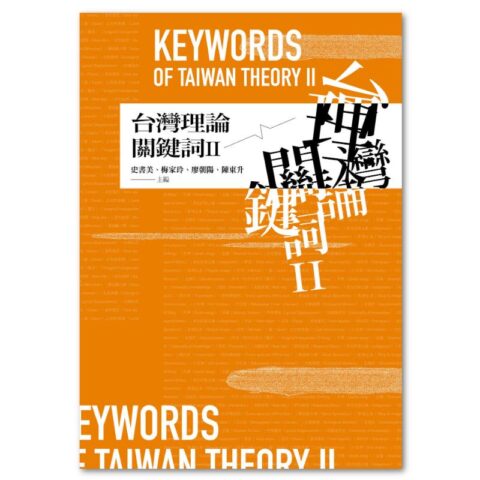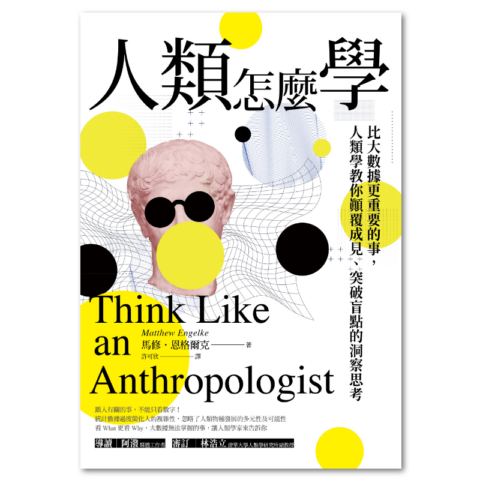排灣文化的詮釋
出版日期:2011-07-27
作者:胡台麗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288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8336
系列:臺灣研究叢刊
已售完
傳說、情感與美感;儀式、文本與影像
胡台麗以細膩的觀察
詮釋了排灣族的文化核心與表徵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胡台麗在晚近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思辨中,以特殊的田野敏感度與感性觸角,對台灣排灣族文化作出有別於以往的探索與詮釋。本書細緻地描述、分析田野實例,顯現排灣族重要的文化表徵例如百步蛇、熊鷹、鼻笛等與排灣傳說中情感元素的關聯。作者並發現「哀思」是排灣族高度認知的情感與美感,是排灣文化的核心概念。此書還從排灣巫師的祭儀經語、祭歌等,探討排灣族最盛大的「五年祭」和極為重要的「家」與「村」等較深層的文化意涵。作者更透過民族誌影片的攝製,體悟到排灣族對於「影像」的獨特在地文化認知,進而挑戰觀察性紀錄片的「真實」。
作者:胡台麗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博士。現職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教授,並擔任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理事長。著作有:《媳婦入門》、《婆家村落》、《性與死》、《燃燒憂鬱》、《排灣族的鼻笛與口笛》等。編導製作十六釐米紀錄片:《神祖之靈歸來》、《矮人祭之歌》、《蘭嶼觀點》、《穿過婆家村》、《愛戀排灣笛》等。
排灣文化之另類探索(代序)
【上篇】傳說、情感與美感
百步蛇與熊鷹:排灣族的文化表徵與詮釋
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
排灣族虛構傳說的真實
【下篇】儀式、文本與影像
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
儀式與影像研究的新面向:排灣古樓祭儀活化文本的啟示
排灣族的影像展演與在地美感
代序
排灣文化之另類探索
一、
和一些立意研究排灣族的人類學者不同,我早先並沒有被那些為數眾多的以排灣族階層社會、長嗣繼承等社會結構為探討重點的文獻所導引,而是在偶然的的機緣下,與排灣文化發生了接觸,受到排灣田野中一些特殊聲音與影像的挑動,激起研究的興趣,逐步走上一條比較另類的排灣文化探索之路。
「偶然的機緣」起於1983年。因為想拍攝民族誌紀錄片,在中研院民族所研究排灣族的同事蔣斌通報協助下,進入台東達仁鄉土坂村參加難得一見的排灣族五年祭。我在田野中為排灣族繁複的祭儀及巫師以快速高亢的音調唸唱的祭儀禱詞、經語所震懾,很想多瞭解一些,但發現那是非常艱困的工作,一時間無法突破,便只集中心力完成了紀錄片《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胡台麗 1984)。
拍攝五年祭紀錄片時,我為了追溯神祖之靈的歸返路線,便前往可清晰望到大武山的村落獵取鏡頭。在泰武鄉泰武村得知有一位老人gilgilau Amulil(郭榮長)會吹奏雙管鼻笛,就請他以大武山為背景作展演。那奇特的吹奏法與低沈而哀淒的音調令我驚訝、著迷,可是未受過民族音樂學訓練的我,那時完全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研究排灣笛。1995年行政院文建會為籌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而展開保存研究計畫。我當時是諮詢委員,在原住民樂器方面建議研究鼻笛和口笛、口簧琴和弓琴。其他委員知道我對排灣族有興趣,便建議由我擔任排灣族鼻笛和口笛委託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我原先還有些猶豫,但在遇到有排灣血統,從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不久的年秀玲(tjuplang Ruvaniao)後,便決定接這個案子。秀玲說她平和村的家隔壁便住了一位會吹鼻笛和口笛的老人,她很樂意擔任此計畫的助理,協助排灣笛吹奏者的訪談與聯繫。1995年我們先作地毯式的現況調查訪問(胡台麗 1995),1997年再邀請有民族音樂學訓練的錢善華教授與排灣族傳道人賴朝財(vuluk Zingerur)加入,展開第二階段的排灣笛藝人生命史、曲譜與製作法記錄(胡台麗 1997)。在這樣超越單一村落的廣泛調查基礎上,我才有可能從比較另類,但遍存於排灣各地區的笛聲、笛子表面的雕刻圖紋和相關連的傳說著手,觸探到排灣族情感與美感的世界。
在拍攝《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過程中,因土坂村有一部分居民是日據時在政府安排下由舊古樓村遷入土坂,我便到西排灣來義鄉的古樓村訪問,並觀看了1984年的古樓五年祭。我發現古樓的五年祭較土坂保存得更完整,內容更豐富。心想:如要對五年祭儀式與巫師祭儀經語有較深入的理解,古樓村應該是一個很理想的田野地點。1989年我再度參加古樓村的五年祭,並邀請之前在土坂拍片時結識的古樓後裔tjinuai Kaleradan(柯惠譯)加入田野採集工作。tjinuai曾協助語言學者Raleigh Ferrell(費羅禮)和Han Egli(艾格理)神父記錄整理排灣族的語料,有很好的排灣語記音基礎,並有追索祖先文化的高度熱忱,而她的母親又擅長講述古樓傳說,可以從旁輔導。不過tjinuai在接觸到古樓的祭儀和巫師的祭儀唸經與唱經時還是遭遇很大挫折,感覺很難理解、記音、和翻譯。幸好晚近輕便錄影機發展神速,能夠將繁複冗長的祭儀語言與動作完整地攝錄下來,可供反覆閱聽記錄;我們又幸運地遇到有能力也願意作詳盡講解的古樓女巫師laelep Pasasaev,讓我們有機會透過以往研究者所疏忽或無法突破的祭儀文本的記錄分析,開啟排灣研究的另一扇門。
二、
受到Clifford Geertz在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一書中論點的影響,1970年代以後的當代人類學者越來越有興趣將文化象徵與行為當成文本來閱讀。閱讀時除了發抒自己的閱讀觀點,更注重當地人對自身文化表徵與活動的詮釋。研究者在民族誌中提出的文化詮釋,是與當地人的詮釋對話後被喚起的詮釋,是對文化象徵體系意義的追尋與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
《排灣文化的詮釋》這本書分為「上篇」和「下篇」,各包括三個章節。在以「傳說、情感與美感」為題的「上篇」中,我從排灣族流傳久遠、極具代表性的圖像文飾、聲音模式與口語傳說的田野資料中,找尋排灣族高度認知的情感及美感,並據以支持和凸顯意圖以「情感/情緒」詮釋文化現象的理論取向,進入過去被忽視而在近期逐漸受到重視的情感/情緒人類學範疇。
第一章「百步蛇與熊鷹:排灣族的文化表徵與詮釋」是以排灣族最鮮明、最為外界熟知的百步蛇與人頭圖紋表徵為切入點,在「泰武式」和「來義式」人頭圖樣差異的分類基礎上,我很想突破以往研究者對此表徵所作的表象描述,以及某些屬於臆測而欠缺當地人觀點的簡單詮釋。我在泰武鄉平和村與來義鄉古樓村收集當地排灣族人的說法,確認「來義式」人頭上端的紋樣不是獸牙而是熊鷹羽毛,而呈三角形的「泰武式」人頭圖像強調的是百步蛇頭部尖突的吻端。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我從村人講述的傳說中發現支持Durkheim與Mauss(1963) 談以圖騰動物作為原始分類時所提出的「情感甚於理智」的論據,也對Levi-Strass的動植物被選為圖騰是因為「適於思考」之說提出修正。排灣族的口語傳說蘊含著許多哀思(tarimuza /mapaura)與驚奇(samali)情感/情緒訊息,顯示百步蛇和熊鷹的形象、聲音與紋樣不僅「適於思考」(“good to think”),而且「適於感受」(“good to feel”),是情感與思考的匯集。排灣各村落雖然在情感上有共通性,但不同村落傳說的情思內容有差異,並在文化表徵的紋樣中表現出來。
我在第二章「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文中,從視覺圖像移轉到對排灣族人非常喜愛並能激起深刻感情的聲音模式(笛聲)之探討。排灣族分佈的地區雖然存在四類不同形制的笛子,但各地的吹笛者都認為笛聲似哭聲,讓人聽了產生哀思的情感與美感。根據排灣當地人的說法,情感是由包含心、肺、肝的「胸」(varhung)發動,而「胸」與很會「想」的「頭」密切互動。排灣族的例子可用以破除西方「情感」與「思想」二元對立的迷思。此外,排灣族高度認知的「哀思」情感還進入了美感層次。在這篇文章中我並提出情感不只是為文化所建構,更有可能形塑排灣文化,成為最具解釋力與涵蓋性最大的概念的新思考方向。
「上篇」裡面的第三章「排灣族虛構傳說的真實」一文特別關注排灣族口述傳說中另一類內容神奇、可用吟唱方式表現的虛構傳說(mirimiringan),以與真實傳說(tjautsiker)類別相對應。我以田野採集到的兩則虛構傳說為例,除了讓大家欣賞極富文學戲劇意味、高潮起伏、異象頻生的情節(像人死復活、會講話的蜘蛛織絲為橋、石頭轉眼變華廈、一夜間造物者將村落遷移、百步蛇變成美男子、鳥變成會發光的美女、吟唱時嬰兒立即長大等),並發現其中蘊含了豐富的驚奇、愛戀、美麗、哀思等排灣族強調的情感和美感。歷代傳述的虛構傳說雖然是人編造的,但反映且塑模了排灣族人的真實情感與美感。
三、
悠悠時光之流中,雕刻圖像、口鼻笛聲和口語傳說都是排灣族文化象徵體系裡相當固定、偏向靜態呈現的「文本」,置於本書「上篇」討論。本書「下篇」以「儀式、文本與影像」為題,包含的三個章節聚焦於排灣文化中較動態的「文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祭儀文本。排灣祭儀中有一類不易變動的固定文本便是女巫師唸唱的經語和男祭司唱的神聖祭歌。
我在「下篇」的首章「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一文中,嚐試記錄並分析古樓村五年祭期間巫師和祭師所展演的經語和唱詞,以及與祭儀緣起相關的真實傳說,以期挖掘出更多排灣文化的深層意義。女巫師在古樓最盛大的五年祭中唸唱的祭儀專屬經語凸顯了「村」(qinalan)的重要性和到「村」的各部位分送祭品的男祭師的角色。為「村」的重要部位做祭儀、獻祭品是為了增強「村」的靈力,以抵禦五年祭期間歸來的惡祖靈(意外死亡者之靈)的侵害。排灣族人期望五年祭時與善祖靈在同一條路(ta jaranan)上相逢,得到他們帶來的福運。五年祭經語中不斷地向善祖靈祈求賜予獵物(qimang),因他們相信若求得獵物,其他的福運會伴隨而來。五年祭的儀式活動中充斥著與獵獸和獵首、男祭司與勇士、象徵「矛」的祭竿與代表獵物首級的祭球、獵首祭屋等意象。這篇文章並借用Paul Ricoeur(1991/1971)將固定化言談和行動視為「文本」的論述,來拓展意義詮釋的領域,將人間「村」溯源時與頭目家族聯結的「同一條路」延伸到人間與神靈界的「同一條路」,對生命的源頭作意義的探尋。
「下篇」第二章「儀式與影像研究的新面向:排灣古樓祭儀活化文本的啟示」除了繼續將固定化的古樓祭儀語言視為「文本」進行探索,還注意此文本展演時整體的動態情境,包括身體動作、祭品擺置、主事者與旁觀者的反應等。在研究方法上我特別提出研究者如能借重新近發展迅速的輕便錄影機,將整套動態儀式「活化文本」作詳盡的影音紀錄,有可能突破前人研究的困境,獲得前所未有的成果。我以自身運用錄影紀錄作研究為例,從古樓祭儀經語「文本」,發現排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家」(umaq/qumaqan)和「村」(qinalan)是人/神格化、有生命、有力量的「活的」存在,而祭儀中女巫師輕微地對手中豬骨哈一有氣,更有將豬骨化為祭獻「活豬」的神奇效用,超越了「物」的物質性限制,為文化詮釋指引新的方向。
「下篇」的最後一章是「排灣族的影像展演與在地美感」。我在前章提到以錄影機所作的實況錄影對文化的記錄和理解有促進和提升之效。這章則是述說我在攝製民族誌紀錄片《愛戀排灣笛》(胡台麗 2000)過程中,發現了排灣族特有的在地美感與視覺詮釋。排灣族人在面對攝影機時刻意地穿戴有傳統象徵紋飾的盛裝,因為他們希望藉照片或影片留給後代哀思的紀念物。我並透過民族誌影片的攝製,反省紀錄片的呈現形式。排灣族人在攝影機前盛裝展露的在地美感與情感,挑戰了西方標榜的真實與自然的「觀察性紀錄片」美學觀。「下篇」的最後章節再度回到「上篇」第一章中關於排灣族傳統百步蛇紋與人頭紋的討論,只不過此時由石版、木板上的雕刻紋飾轉到服飾上,再被攝入靜照和動態影片中,產生一脈相承、延續性的意義。
本書的文字也是一種紋飾(vetsik),從不同面向刻畫、展現排灣文化並作出詮釋。在靜態文本和動態文本、「傳說、情感與美感」和「儀式、文本與影像」的交相呼應與辯證中,同時反映了我個人的情感與美感傾向,以及身為人類學探索者的反思。對於一路上相伴的排灣族人與豐美的排灣文化,謹致上深深的敬意和感謝。
第一章 百步蛇與熊鷹
如果問:台灣原住民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表徵是什麼?無論是台灣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恐怕都會從記憶中鮮明地浮現排灣族群最常運用的百步蛇與人頭紋。尤其是在所謂的原始藝術研究層面,排灣族群木雕、石雕、織繡等採用的紋樣一向是研究者焦點之所聚,其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陳奇祿先生的著作《台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1961)。陳奇祿先生在該書的導言中便指出,日據時代學者的論著中雖然對排灣群諸族的木雕和織繡藝術屢予報導,但是「或因文字簡短,意有未盡;或則偏重於藝術學理論之探討,對標本本身不作充分說明。」因此陳先生的研究一方面根據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和收藏家的藏品,另方面展開實地田野調查,進行繪圖、照相與描述的工作,經過有系統的比對研究,完成了這本極有價值的著作。這本書豐富而多樣的圖文更加確認了一個現象:排灣群諸族木雕所採用的主要紋樣為百步蛇、人頭與人像。但是為什麼排灣族群會以百步蛇與人頭、人像為主要的紋樣呢?陳奇祿先生與他之前的研究者一樣只提出寥寥數句說明:「排灣語稱百步蛇為vorovorong,為長老之意,因為排灣群視百步蛇為蛇之長老。他們信以為百步蛇是貴族的祖先,對百步蛇有很多禁忌,且相當重視和敬畏。所以百步蛇在排灣群木雕的紋樣中出現是具有宗教和社會的意義的,與具有圖騰的民族對圖騰的敬畏頗為類似。百步蛇與人這兩種紋樣均可說是因代表祖先而被尊重,亦是貴族階級的無形體財產(同上引:160-61)。」相較於該書對紋樣外觀的詳細描繪敘述,陳奇祿先生對於紋樣的內在意義詮釋顯得過於簡略,令人產生意猶未盡之感。
近些年我在排灣族村落中做祭儀以及鼻笛與口笛的研究,無意中收集到一些與百步蛇相關的田野資料。當我翻閱陳奇祿先生書中(同上引:21-24)並置的家屋立柱雕刻紋樣時,有兩類紋樣形式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其中一類是陳奇祿先生主要在泰武鄉村落中發現的「泰武式」人頭紋樣,重要特徵為人像的頭部呈尖形,與有尖凸吻端的百步蛇頭部類似,有的尖形人頭紋邊上還加了一對百步蛇(圖1);另一類是在來義鄉村落中發現的「來義式」,「特徵為頭部作橢圓形,頭上戴帽,帽上有牙狀飾物,似為表示常見於該族之豹牙或豬牙帽飾」(圖2)。看到這兩類紋樣,我在田野所累積的一些零散印象與訊息在霎那間凝聚了起來。沒錯,我做鼻笛調查時,在泰武鄉的平和村看到尖頭的人像刻紋;做五年祭調查時,在來義鄉古樓村看到的人頭都是橢圓形,而根據古樓人相當一致的說法,人頭上面的飾物是熊鷹羽毛而非陳奇祿先生猜測的豹牙或山豬牙。關於這一點,伊能嘉矩很早便在一篇描述排灣族雕刻紋樣的短文(1907)中提及:人頭上的裝飾是鷹羽。
泰武鄉的平和村與來義鄉的古樓村同樣屬於排灣族的Vutsul系統,可是二者的人頭紋樣卻有如此不同的呈現方式。前者的紋樣強調的是百步蛇頭與人頭的疊合,百步蛇的形象特別突出,連人的頭像造型也類似具有突起吻端的百步蛇的頭部;後者的紋樣中並沒有凸顯百步蛇頭部,但卻強調人頭上插著熊鷹羽毛。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紋樣差異?紋樣如果是文化的表徵,百步蛇在不同的排灣地區是否有不一樣的文化意涵?熊鷹和熊鷹羽毛又代表了什麼?本文將以平和村與古樓村為例,從紋樣開始,探討排灣族的文化表徵並試圖提出融合「情感」因素的詮釋。
平和村的百步蛇意象
我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一再強調:排灣族的口述傳統若按照他們自己的分類,包含了代代相傳的tjautsiker(真實傳說)與mirimiringan(虛構傳說)這兩類性質不同的傳說,但不少研究者常含混地以「傳說或神話」稱之,而不加以區辨。排灣族人傳述tjautsiker時,接近口述歷史的概念,基本上相信tjautsiker中的人物事件是真實的存在,是前輩或自身確曾發生的經歷,如同部落、家族、與個人歷史的傳述,不敢隨意編造,我將之譯為「真實傳說」;而mirimiringan則接近故事的概念,是人用才智虛構、編造出來的人事物,其中人名多以重複音節表示,有別於現實生活中的名字,故事內容常出現不可思議的情節,具寓言性與教育性,我將之譯為「虛構傳說」(胡台麗1997、1998)。其實,小林保祥早在1930年代的西、南排灣便注意到「人們把不可思議的事情、異常美麗的東西稱為mirimiringan,民間傳說由於其內容多奇妙而不可思議而挪用了這個詞義。mirimiringan裡出現的人名或神名通常採用重疊稱呼,日常生活裡則不存在這種情況」(松澤原子編1998:90);吳燕和也於1960年代在東排灣收集田野資料時注意到tjautsiker與mirimiringan的區分,tjautsiker「有歷史的性質,沒有超乎尋常的事情,聽與講的人都很認真,而相信這些都是真的」,而mirimiringan「最大的特性是大家知道這是人造的故事,是假的,內容的人物常可做超乎尋常的變化」(1993:99)。從以下平和村的例子可以看出tjautsiker(真實傳說)對於排灣族紋樣的形塑有極大的影響。
泰武鄉平和村(Piuma)有非常貼近村人現實生活的關於百步蛇的tjautsiker(真實傳說)。排灣語的蛇叫做qatjuvi,而平和村人稱百步蛇為kamavanan,字根mavan的意思是「真實的」,kamavanan可譯為「就是那個最真實的」。平和村的村長vikung(家名Pasasav)說:我們平和村沒有直接與百步蛇相關的mirimiringan(虛構傳說),可是有百步蛇的tjautsiker(真實傳說)。除了平和村年長者皆能引述的有關平和村Mavaliv頭目家祖先是百步蛇(卵)所生的傳說,大家也都熟知另一則關於百步蛇的真實傳說。以下村長敘述的版本極具有代表性:
在我們遷下來之前居住的舊平和村附近有一條百步蛇(kamavanan),祂是我們平和村人生命的守護者,從創始就在那裡。祂所在的地方叫做salalumegan,在村落下面,距離道路很近,有的時候我們在路上會突然遇到祂,便會對祂說:「你快離開這裡吧,村落的敵人要來了,你如果不小心就會被殺害!」祂聽了我們的話就會返回他住的地方。我們平和村人都很尊敬祂,相信祂是保護我們生命的神(tsemas),從古至今,從來沒有平和村人被這隻百步蛇咬過。
我們平和村沒有竹竿刺球的五年祭(maleveq),可是我們有祭拜百步蛇的祭儀。每隔五年我們輪流到兩個地方祭拜(每一處要隔十年才祭拜一次),一個地方是置放敵人頭顱的男子聚會所tsakar,男子前往那裡祈求維護村人的生命,以避免遭到被別村人獵首的惡運;另一個地點就是百步蛇居住的地方salalumegan。那裡有一棵叫做kalavas的大樹,百步蛇就盤踞在樹的根部。祭拜前祭師會先去對百步蛇說:我們要做祭儀,請你暫時離開一下。祂離開之後祭師會叫村中的男子到salalumegan百步蛇曾棲息的地方摸一摸,會發現還存留著熱氣。男子進入祭拜的場所,女子則在較遠處圍觀。村中代表做祭儀的老前輩說:「我們很感謝kamavanan保佑我們的生命,並防衛我們的村落,祈求祂繼續護衛我們。」等我們做完祭儀離開後,百步蛇會再返回樹的根部。
大約在民國三十九年底,有一個美國來的基督教醫療團到我們這裡傳福音,他們一直唱著:「來信耶穌」。醫療團離開後的次年(民國四十年),那隻百步蛇突然很奇異地經常性地發出叫聲。老人家聽到了就很驚訝地說:「為什麼發出這樣的叫聲呢?」又過了一段時間,百步蛇棲息的那棵樹居然被雷電擊中枯死了,祂居住的地方沒有任何東西存活,令我們全村的人非常驚奇(samali)。在雷電擊中那棵樹之前,傳來百步蛇發出的聲音,大家對這事都有記憶,都很驚訝,事後才知道原來那是要被雷擊的預兆。那時我們全村的人都這樣想:「已經死了!」民國四十一年,平和村的tsemeresai(家名Patjalinuk)娶了筏灣村的女子tsemadas(家名Zengerhurh)。婚前她已經信了耶穌基督,婚後便在平和村傳教。民國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之間村中大部份人都信了教,大約在民國四十五年全村歸信耶穌。我們想我們現在信的上帝比那個百步蛇偉大,因為百步蛇住的地方居然被雷擊中枯死了。醫療團來之後百步蛇一直吹一直吹,大概是預知我們村子的人會變,要離開祂了,祂會感到很寂寞。
我們信了耶穌後就再也沒有聽到百步蛇發出聲音,也沒有再看見祂。不過有一天,tsemeresai牧師要去Tsalisi(射鹿村)主持禮拜,在路上突然遇到這隻百步蛇。他一邊說:「你這個魔鬼!」一邊拿起石頭想把祂打死,可是一轉身,那隻百步蛇就不見了。雷擊之後我們以為百步蛇死了,沒想到祂還活著,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再信從祂了。
在基督教傳入之前曾經擔任平和村Mavaliv頭目家最後一任司祭(parhakalai)並擅長吹奏雙管鼻笛的rhemaliz(家名Tjuvelerem)根據祖輩的tjautsiker(真實傳說),對於百步蛇與頭目家、村落祭儀和鼻笛的關係作如下的傳述:
百步蛇是Mavaliv頭目家的創始者。當我們在Mavaliv頭目家做小米豐收祭儀時,若發生衝突或犯了過失,百步蛇會出現,對我們施以懲罰。只有女祭師(marada)才可以對百步蛇說:「請退回去吧!我們感到很羞恥。」祭儀若有錯失,必須重新再做,做對之後百步蛇才會離開。在Mavaliv頭目家出現的這隻百步蛇就是平時居住在salalumegan那裡的那隻百步蛇。
據說Mavaliv家有一位女祖先名叫muni擅長刺繡。有一天發現百步蛇在她放置刺繡色線的竹籃中盤踞。muni便用木棒觸動百步蛇。百步蛇於是託夢給一位祖輩名叫lavaus,並說:「muni打了我,而我確實是你們的祖先(vuvu)」。那隻百步蛇其實就是Mavaliv家的成員(tsemekemekel),我們不可以侵擾、阻礙祂。只有很有靈性的人像女祭師(marada)才可以對百步蛇說:「請你走吧」,也可以用祭儀請百步蛇離開原先的位置。
平和村五年一次輪到前往百步蛇居住的salalumegan做祭儀(mati salalumegan)時,那些會唱唸經語的女祭師會對盤捲在kalavas樹根的百步蛇說話,請祂離開,然後手中拿著麻(rekrek)做祭儀,祈求神保護大家的生命。我們到那裡一路上要很小心,如果有一點割傷而堅持要去,這個傷就永遠不會好。
我們認為百步蛇kamavanan是神靈(tsemas),不能殺祂,尤其是頭目絕對不會殺祂。如果遇到祂時不能說那是kamavana,是禁忌。我們要說那個vaud(籐類)過去了。我有聽說我們貴族是百步蛇生的,kamavanan是我們的祖先。我沒有看過平和村的百步蛇,但是祂真的存在著,我的父輩曾看過祂。
根據過去老前輩所說的tjautsiker,百步蛇會從翹起的鼻子吹出聲音,通常要下大雨時、天近黃昏時、暴風雨將臨時,百步蛇都會吹出聲音,是預兆和警示的聲音。我們吹的鼻笛聲和百步蛇從鼻子吹出的聲音是一樣的。我們平和村很注重鼻笛(rharingetan),流傳著鼻笛是學百步蛇聲音的真實傳說。以前唯有頭目階級男子才能吹鼻笛,也只有在頭目的鼻笛上才適合雕刻百步蛇紋。日據末期,有些平民開始吹鼻笛和口笛,但是他們絕對不敢在笛子上刻百步蛇紋。吹鼻笛時我們要非常專心,柔和細緻地送氣,輕輕開闔手指,這樣就能吹出令人哀傷思念(temarimuzau)的笛聲。我們的哀思情感是是從「胸」(varhung)產生的,如同為喪家吟唱的哀調,引人落淚。村中頭目過世時不能隨便唱歌、說話,只能夠吹奏鼻笛配合著婦女吟唱的哭調以表達哀傷。
rhemaliz告知,平和村舊聚落的Mavaliv頭目家屋中有四根柱子,每根上面都雕刻著類似的人像。人像的頭頂是尖形的,而眼睛和嘴則呈菱形。Mavaliv頭目家屋外部簷下的橫條木柱(sasuaian)上也刻著連續的尖頭人像。rhemaliz的兒子根據以往Mavaliv頭目家屋內主柱的人像造形在父親的竹製鼻笛上雕刻紋樣,我因此看到了尖形的人頭像。平和村的老人表示尖形人頭是仿百步蛇頭,而上端尖的部份是百步蛇翹起的鼻子。
此外,平和村的老人家也會講述有關百步蛇長大以後會變短再蛻變為熊鷹(qadris)的真實傳說。熊鷹的兩邊翅膀中各有一根斜長形且三角紋樣明晰的羽毛叫做parits,平民獵到熊鷹後要將一對parits羽毛抽出來給頭目做貢賦(vadis)。平和村最看重的parits熊鷹羽毛只有頭目(不分男女)才能夠插在頭上做飾物。但是無可置疑地,平和村有關頭目是百步蛇所生、百步蛇是村落守護神以及百步蛇頭部具有突起的吻端並會吹出聲音的真實傳說,才是深深縷刻在歷代村人心中無法磨滅的記憶。吻端突起的百步蛇頭因此與人頭疊和,成為平和村最凸顯的紋樣與最重要的文化表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