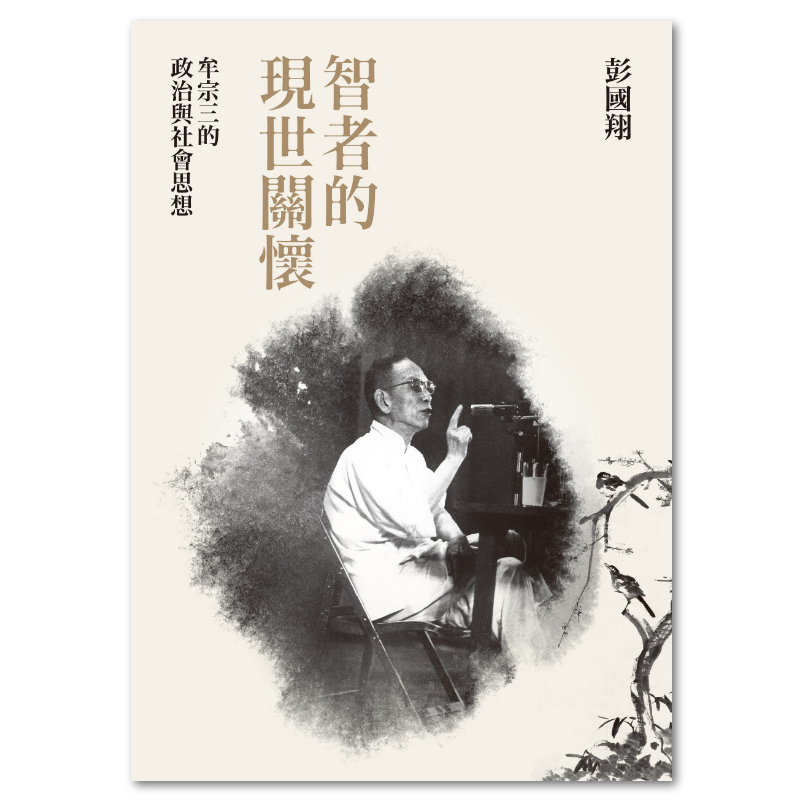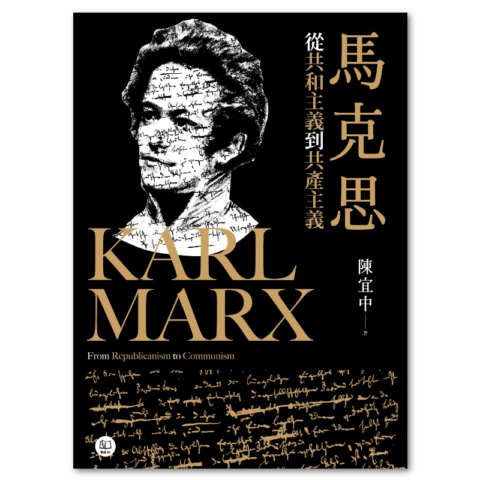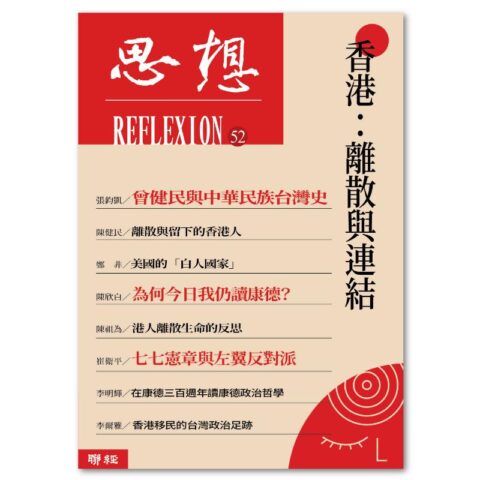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
出版日期:2016-03-11
作者:彭國翔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480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6959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余英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推薦!
《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
遍檢《牟宗三先生全集》相關文獻
利用新發現的佚著和《全集》未收的通信
將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
置於其所在社會、歷史與思想的整體脈絡中,
予以全面與深入的梳理和考察
探討牟宗三的「現世關懷」
作為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牟宗三(1909-1995)不僅有其心性之學的詮釋與建構,同時有其政治與社會的關懷與思考。從20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其政治與社會思想一直都有表達。從早年對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對中國社會史和中國農村問題的探究,到晚年對兩岸關係與臺灣認同的申論,以及一生批判共產主義,在反省與檢討的基礎上提倡自由、民主,都是力圖要為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實踐提供一個正確的思想基礎。
彭國翔透過本書遍檢《牟宗三先生全集》相關文獻,利用新發現的佚著和《全集》未收的通信,將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置於其所在社會、歷史與思想的整體脈絡之中,予以了全面與深入的梳理和考察。本書採取了微觀分析和宏觀綜合交互為用的研究方式,依據具體內涵,將牟宗三的「現世關懷」分成七章,一一詳加論述;通過概念的分析和澄清,微觀的功效在全書中獲得了充分的發揮。但著者並不是為分析而分析,把每一章當作一種孤立現象來處理。相反的,他的目的是展現牟宗三的「現世關懷」的全貌。因此,各章之間都互相關聯,合而讀之,即成一宏觀的整體。本書的另一重大特色是網羅牟宗三的著作鉅細不遺,從佚文到未刊書信,凡是和「現世關懷」相關的文獻,已搜集到應有盡有的地步。
本書第一章是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第二章是牟宗三關於中國社會史發展階段和形態的主張。第三章是牟宗三關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看法。第四章是牟宗三一生對於共產主義的批判。第五章是牟宗三關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看法。第六章是牟宗三對於民主政治的肯定和反省。第七章是牟宗三關於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岸關係的見解。
《智者的現世關懷》既從結構上展現了牟宗三政治與社會思想的各個方面,也大體照顧了牟宗三政治與社會思想在時間發展上的順序。此外,如果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反映牟宗三政治與社會思想中「破」的方面,第五至第七章則主要反映他政治與社會思想中「立」的方面。
總的來說,本書顧及牟宗三一生政治與社會思想的各個方面,同時力求對每一個方面都予以徹底的把握和分析。其二、以盡可能全面掌握牟宗三的各種原始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其三,對牟宗三政治與社會思想的處理方式。
作者:彭國翔
彭國翔,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兼任國際中西比較哲學學會(ISCWP)會長、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Comparative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編委等。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並擔任世界多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訪問學者,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法蘭克福大學、馬普研究院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等。曾獲德國洪堡基金會與教育部頒授的“Friedrich Wilhelm Bessel Research Award”等。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中國哲學、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學和宗教的比較。
著有《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學生書局,2003;北京三聯書店,2005)、《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儒家傳統與中國哲學:新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從先秦儒學、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3;北京中華書局,2015)、《重建斯文:儒學與當今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及中英文論文近百篇。
序 《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 余英時
導言
第一章 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批判
一、引言
二、唯物辯證法批判
(一)以維護形式邏輯的方式批判唯物辯證法
(二)直接批判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則
三、唯物史觀批判
(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理解
(二)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不能相通
(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是「抽象的區分」而非「具體的事實」
(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並非辯證法的矛盾關係
(五)階級鬥爭並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
第二章 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論
一、引言
二、中國歷史的分期與各期社會的性質
(一)上古:現物交換的古代共產社會
(二)周代:現物租稅的封建主義社會
(三)秦漢以降:專制主義下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三、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幾個問題的駁論
(一)中國有無奴隸社會和奴隸制的問題
(二)亞細亞生產方式與社會的問題
(三)中國「封建社會」的問題
(四)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的問題
(五)中國歷史的「反復循環」問題
(六)駁論的關鍵:中國歷史與社會的特殊性
四、中國社會的未來展望: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
(一)非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
(二)有別於歐美式的民主政治
(三)非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第三章 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
一、引言
二、對三○年代中國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判斷
(一)土地分配與人口分配
(二)生產方式
(三)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
三、解決三○年代中國農村問題的方案
(一)批評:針對當時流行的四種方案
(二)方式:從經濟方面著手,從經濟關係來組織農民
(三)目標: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四、結語
第四章 共產主義批判──以《全集》未收之《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為中心
一、引言
二、對共產主義「家庭」、「國家」和「大同」觀念的批判
三、對於「唯物論」的批判及其「人文主義的理想主義」
四、批判共產主義的一生軌跡
五、批判共產主義的根源
六、結語
第五章 自由主義的追求與檢討
一、引言
二、道德自由與政治自由:中國傳統自由觀與西方近代以來的自由觀
三、道德自由與政治自由之間的關係
四、自由主義的根本精神與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第六章 民主政治的肯定與反省
一、引言
二、傳統中國政治的觀察與判斷
(一)君、士、民的結構
(二)政治人物的三種類型與命命相革(人治)的循環史
(三)政道與治道
(四)君主專制的三大癥結
三、民主政治的肯定
(一)民主政治的「本義」與必要
(二)民主政治的普遍性
(三)民主政治是科學和法治的保障
(四)民主政治是事功的保障
(五)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多元的政黨政治
四、民主政治的局限與反省
(一)民主政治無法負責社會風氣的改善
(二)民主政治需要文化教養和道德理性的支撐
五、結語
六、附:對大陸民主運動的看法
第七章 兩岸關係與台灣認同
一、引言
二、論兩岸關係
三、論台灣認同
四、結語
附錄:「出」「處」之際見儒家
後記《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
《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余英時
牟宗三先生是現代中國最具原創力的哲學家之一。他所創建的哲學系統既廣大又精微,因此數十年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分析與闡釋之作不計其數,而且仍在不斷增添之中,彭國翔先生的《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則是這一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的最新貢獻。
本書之所以「別開生面」便在於它的探討對象不是牟宗三的哲學系統,而是他的「現世關懷」,這是以往研究者極少觸及的一面。但這並不是因為國翔不重視牟的哲學。恰恰相反,哲學是國翔的專業,而且早在大學生時期,即八十年代後期,便已對牟的哲學發生了深厚的興趣,並因而在研究生時期即已獲得了「牟宗三專家」的雅號。三十年來他讀遍了牟的一切論著,對於牟的哲學系統有著很透澈的認識。關於這一點,祇要一讀他對於牟氏哲學的「基本架構」與「核心概念」所作的分析便完全清楚了。那麼國翔為什麼從牟的哲學(「內聖」)轉向牟的「現世關懷」(「外王」)呢?原因很簡單:由於牟深信「解決外王問題」必須「本內聖之學」,他的哲學體系「可以說是其現實政治與社會關懷的產物。」國翔因此一針見血地告訴我們:
要想對牟宗三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就不能僅僅局限於其哲學思想,不能僅僅以「經虛涉曠」的哲學家視之。只有對其一生強烈的政治社會關懷有深刻的把握,才能真正了解其精神與思想世界的全貌。
這也是國翔對於他「別開生面」的最明確的解答。
國翔寫此書的主旨是「對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做一全面與深入的梳理」,通覽全書,我覺得他確實取得了高度的成功。限於篇幅,下面讓我揭示本書兩個最顯著的特色。
第一,本書採取了微觀分析和宏觀綜合交互為用的研究方式。著者依據具體內涵,將牟先生的「現世關懷」分成七章,一一詳加論述;通過概念的分析和澄清,微觀的功效在全書中獲得了充分的發揮。但著者並不是為分析而分析,把每一章當作一種孤立現象來處理。相反的,他的目的是展現牟的「現世關懷」的全貌。因此,各章之間都互相關聯,合而讀之,即成一宏觀的整體。不僅如此,本書的宏觀綜合並不止於「現世關懷」這一層次,據我所見,另有兩個層次的宏觀也應該特別指出:其一,「現世關懷」屬於「外王」範圍,但著者隨時不忘怎樣將「外王」和「內聖」聯繫起來。所以他一方面一再引牟的自述,強調一九四九年以後專心尋求「內聖」如何開出「外王」的途徑,另一方面則鄭重地揭出牟晚年一個重要論斷:新時代所要開出的「新外王」便是民主政治的實現。這是著者在牟氏政治思想和哲學系統之間所作的宏觀綜合。其二,著者說:
本書對牟宗三政治與社會思想的探討,儘管在概念的分析與澄清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覺和運用,但絕不將討論和辨析局限於抽象的觀念推演,而是盡可能將其置於牟宗三所在的社會歷史與思想的整體世界和脈絡之中來加以考察。
這是孟子「知人論世」的研究方式,後世所謂「即事以言理」也是此意。(現代西方“contextualism”一派也大旨相近。)可見本書的宏觀已超出牟宗三「內聖外王」的思維之上,而進一步與他的整個時代融合為一體了。
第二,本書的另一重大特色是網羅牟宗三的著作鉅細不遺,從佚文到未刊書信,凡是和「現世關懷」相關的文獻,已搜集到應有盡有的地步。不用說,在這樣堅實而廣闊的文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種種論斷是很難動搖的。對於任何題旨進行學術研究都必須始於全面搜尋第一手的原始資料,這本來是學術界公認的一種工作程序,不足為異。但國翔在本書文獻方面的貢獻則遠非一般情況可以相提並論。他發現了一部久佚的著作,而恰恰是牟宗三「現世關懷」的一個核心部分:牟宗三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了一部《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原為台北招商訓練委員會的一種教材。但此一冊小書流行不廣,從未見有人提及,今天已無人知其存在,以致《牟宗三先生全集》也未能收入。二○○四年國翔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發現了它,並且立即看出它的重要性。本書第四章〈共產主義批判〉便是以它為中心而寫成的專論。
以上兩大特色保證了本書論述的全面性和客觀性。我從一九五○年代初便開始接觸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一九七三─七五兩年又在新亞書院和他共事,時相過從。但是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是在讀完本書之後才對他的「現世關懷」有了深一層的認識。讓我在這裡回憶一下有關的往事。
從一九五○年元旦到一九五五年十月初,我在香港住了五年零九個月之久,這恰好是我在學術和思想上逐步走向定型的時期。在這幾年中,我一方面在學校聽課,另一方面到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閱覽室和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圖書館,選讀有興趣的書刊。(因為那時新亞書院尚無藏書。)但同時我也受到當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界期刊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國》和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限於篇幅,這裡祇能極其簡略地介紹一下它們的背景。
《自由中國》是胡適一九四九年初在上海和國民黨內自由派人士如王世杰、杭立武、雷震等籌劃創辦的,同年十一月在台北刊行了創刊號。自由中國月刊社成立後,胡適在美國遙領「發行人」名義,實際領導的責任由雷震承擔,經費最初則由教育部及其他黨政機構提供。但到了一九五三年,它已能自給自足,成為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民間刊物,不再接受官方的資助了。
《民主評論》是徐復觀創辦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在奉化溪口,取得了蔣介石的同意,五月便到香港籌辦《民主評論》半月刊。當時蔣告假下野,處境相當困難,深感有必要爭取自由知識人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共。刊物取名「民主」即透露了此中消息。蔣一向信任徐,讓他放手去辦,不加干涉;經費則來自遷台後的總統府。《民主評論》社成立後,徐以「發行人」的身分往來於台北與香港之間,編輯事務則完全由香港新亞書院三位創始人負責:張丕介擔任主編,錢穆、唐君毅則「從旁贊助」。這樣的安排出於歷史背景之順理成章。原來徐先生曾師從熊十力大師,與君毅師為同門,他對賓四師一向甚為尊敬,與丕介師則是多年深交。
兩相對照,《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恰好分別代表了當時大陸以外中國兩個主要的思想流派:前者可以稱之為「五四」新文化(或新思潮)派,後者不妨稱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派。(一九五八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民主評論》上發表以後,此派則獲得了「當代新儒家」的通稱。)這兩大刊物同樣認同於「自由」、「民主」的政治社會秩序,也同樣反對共產黨的極權體制,但由於文化觀點的分歧,不但雙方很快便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而且爭論竟長期持續了下去。爭論所涉及的範圍很廣,這裡不必也不能詳說,但其核心所在則可以簡括如下。據胡適在創刊號所寫的「宗旨」,《自由中國》「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但在實踐中,其主要撰稿人(以殷海光為首)則強調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兩千年君主專制的護身符,因此必須首先予以摧毀。另一方面,《民主評論》則嚴厲譴責以胡適為領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打倒孔家店」,走向全面否定傳統文化,最後「以懷疑的虛無主義告終」,以致連他們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也全部落空了。因此他們斷定當時第一要務是在西方文化對照下重建中國文化精神。而且根據「內聖」開出「外王」的邏輯,祇有在中國文化精神獲得新生之後,「科學」和「民主」才能在中國落地生根。如果用牟宗三的概念來表達,便是「道統」開出「學統」和「政統」。
這兩大期刊是我當時每期必讀的,而它們之間的反覆爭議,都出之以鋒銳的言辭,更激起我的興趣。大體上說,由於《自由中國》的啟發,我開始接觸和民主自由相關的政治思想論著,逐漸摸索到一點門徑。《民主評論》則引導我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理解日益加深。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自由中國》的重點在宣揚現代普世價值。對比之下,《民主評論》則全力以赴地展示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特形態,對於民主自由方面卻著墨不多。(其中祇有徐復觀一人時時肯定民主政治並為「自由主義」作有力的辯護。)所以我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確實受益於這兩大期刊。
導言
余英時先生曾經深刻地指出,理學家致力於心性之學的「內聖」方面,並不是要放棄經世致用的「外王」方面,而恰恰是要為「外王」實踐建立一個正確和牢固的「內聖」基礎。宋代道學家群體對於王安石的批評,根本並不在於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政治取向本身,而在於對道學群體來說,王安石的「外王」實踐建立在錯誤的「內聖」之學之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對理學家的理解局限於「內聖」一面是不夠全面的,只有從「內聖外王連續體」的意義上理解理學家,才能得其精神之全。我認為,余先生這一「內聖外王連續體」的觀察和判斷,不僅適用於宋明的理學家,也同樣適用於現當代的新儒家以及整個儒家傳統。作為現代新儒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牟宗三(一九○九─一九九五)不僅有其心性之學的詮釋與建構,同時還有其政治與社會的關懷與思考。從二十世紀三○年代到九○年代,六十年間,其政治與社會思想一直都有表達。從早年對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對中國社會史和中國農村問題的探究,到晚年對兩岸關係與台灣認同的申論,以及一生批判共產主義,在反省與檢討的基礎上提倡自由、民主,都是力圖要為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實踐提供一個正確的思想基礎。這和宋代理學家批判王安石新學是頗為類似的。只不過在宋代理學家的心目中,作為「邪說」危害政治社會的是王安石的新學;而在牟宗三的心目中,「邪說害道」的則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不僅占據大部分中國知識人心靈甚至一度風行全球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
對於這種「內聖外王連續體」,或者說本內聖之學而求解決外王問題的思路,在一九五五年台北的人文友會第十九次聚會時,牟宗三已經有所交代。他說:
我們費了好大力氣講中國過去的種種道理,其目的,即在想把中國的現代化接上去,現代化是由內聖之學向外開的問題。這方面看起來很容易、實則無論實現或了解皆極難。因為懂「理」易、懂「事」難。做書生、做翰林學士易,做政治家、做宰相難。現在要做一個哲學家、科學家容易,而要做一個建國的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就很難。
而在人文友會的第二十一次聚會開始時,牟宗三講得更清楚:
我們現在講內聖是為了什麼,這一點必須知道。過去講內聖,即在通外王。事功,即外王的表現。所謂事功、事業、政治、經濟、典章、制度,通同是外王。現在的建國,即根據內聖之學向外開,亦即是外王。
因此,對於自己五十歲之後為什麼會集中心力於中國的內聖之學,牟宗三一九六二年元旦於香港在其《歷史哲學》的〈增訂版自序〉中有明確的說明。他說:
五十以前,自民國三十八年起,遭逢巨變,乃發憤寫成:
一、《道德的理想主義》
二、《政道與治道》
三、《歷史哲學》
三書。夫此三書既欲本中國內聖之學解決外王問題,則所本之內聖之學實不可不予以全部展露。
由此可見,牟宗三五十歲以後一系列似乎是純粹關乎「內聖之學」、「心性之學」的著作,包括《才性與玄理》(一九六三)、《心體與性體》(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佛性與般若》(一九七七)以及《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一九七九),其實都不是單純理智思辨的結果,而可以說是其現實政治與社會關懷的產物,所謂「欲本中國內聖之學解決外王問題」。換言之,至少在發生學的意義上,正是解決外王問題的現實促動,導致了其內聖之學的最終建立。用牟宗三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今天重視哲學是因為共產黨的問題」。因此,要想對牟宗三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就不能僅僅局限於其哲學思想,不能僅僅以「經虛涉曠」的哲學家視之。只有對其一生強烈的政治社會關懷有深刻的把握,才能真正了解其精神與思想世界的全貌。
以往對於牟宗三的研究,基本上限於他有關中西哲學的思想。即使為數不多的關於其政治思想的研究,也都是囿於哲學的取徑,而且幾乎都是圍繞其通過「良知坎陷」而「開出」民主政治這一個方面。對於其「良知坎陷」基於誤解的諸多無的放矢的所謂批判,自然不足與論。即便對於「良知坎陷」能有相應了解的研究,也往往都是僅僅論及有關民主政治的問題。至於牟宗三政治思想的其他多個方面,包括他早年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晚年對於兩岸關係與台灣認同的觀察、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看法、以及一生對於共產主義的批判,都是以往的牟宗三研究未嘗措意的。至於牟宗三的社會思想,包括他在二十世紀三○年代對於中國社會發展史的獨特看法,以及對於中國農村問題全面與深入的探討,更是以往的研究絲毫未嘗觸及的。本書之作,就是希望對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做一全面與深入的梳理。
牟宗三一九二七年十八歲(虛歲十九)時,由山東棲霞中學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二九年升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在當時的北京(時稱「北平」)恰好是「顯學」。因此,剛入大學並開始接觸新思想的牟宗三,首先面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擊。正如他自己回憶時所說:「一個混沌的青年在當時是被爭取的對象」,他甚至一度成為當時沾染了共產主義意識的國民黨的「預備黨員」。不過,牟宗三並未像一般人那樣往往為潮流所裹挾而人云亦云。他在一度為當時的左傾思潮所聳動和吸引的同時,自始就覺得「不對勁」、「異樣」,於是迅速擺脫了那股迷思狂潮的吞噬。這一段經驗,在其《五十自述》中有清楚的交代:
一個混沌的青年在當時是被爭取的對象,黨人大肆活動。我感覺他們的意識、他們的觀念、他們的行動以及生活形態好像很異樣。其中有足以吸引我的地方,使我有從未有的開闊、解放、向上的感覺。但另一方面也總使我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們那時的意識大體是共產黨的意識;以唯物論為真理,什麼是唯物論他們也不懂,只是那現實的、實際的意識之唯物論。這是共產黨對政治經濟社會全革命的唯物論。這意識沾染了那時的國民黨,而且沾染得很深。有一次,一位黨人同學和另一人討論什麼問題,我只聽他說你的觀點是唯心論的,所以你還是錯的。我當時,就有異樣的感覺,為什麼唯心論就是先天地錯誤呢?這使我有個不能像他們那樣斷然肯定的疑惑。
我當時也沾染了那氾濫浪漫的精神,但我沒有仇恨的心理,我也沒有仇恨的對象。我前面已說,他們有足以吸引我的地方,使我有從未有的開闊、解放、向上的感覺。這是由我那在鄉村的自然生活所蘊蓄的混沌而開放。他們吸引了我,我也接近了他們那一點。他們把我列為預備黨員。我暑假回家,團聚農民,成立農民協會,每夜召集他們開會講習,訓練民權初步。在夜間也跑到十幾里外的別村去開會。夜深了,人都關門了。我隨便找個什麼地方也可以睡一夜。我本我那鄉村中所養成的潑皮精神去作這種活動。我發覺我很有鼓舞的力量,也有團聚人的能力。這原因很簡單,誠樸、潑皮、肝膽,沒有矜持的架子,還有,那是因為我讀了幾句書,畢竟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從北京大學回鄉,鄉下人心中也是另眼相看的。但我迅速地感到在父老兄弟面前,在親友面前,於開會時,很嚴肅地擺起面孔稱同志,那意味總不對。那是太客觀了,太政治了,太形式化了。頓然覺得我自己的生命被吊在半空裡,抽離而乾枯了。我也覺得父老兄弟親友的生命也吊在半空裡,抽離而乾枯了,那太冷酷、太無情。事後,我有說不出的難過。直到如今,我一想起便有無限的慚愧,疚仄,好像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汙點,好像是我做了極端罪惡的事情。我迅速地撤退。我讓那預備黨員永遠停留在預備中吧!我不要這黨員。再加上他們從上到下一起在迅速地轉向,我和他們的距離愈來愈遠。他們那氣味我受不了。那些不對勁的感覺一起發作。
牟宗三這裡所謂的「黨人」,還是國民黨,尚非共產黨。但如他所說,當時的國民黨受到了共產黨很深的滲透,共產主義的意識非常普遍。他的這段經驗,應該是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剛剛升入北京大學不久的事情。而他從一開始就覺得「不對勁」、「異樣」而「迅速地撤退」,應該是非常短暫的一段經驗。因為在一九三一年時,他已經在當時的《北平晨報》上正式發表了批判唯物辯證法的文章:〈辯證法是真理嗎?〉這與他在這裡的自述恰好可以相互印證。由此可見,牟宗三獨立運思的開始,正是起於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省。
第一章、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批判
一、引言
晚清以降,在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中,影響最大並切實改造了中國社會與國家的學說,莫過於馬克思主義。現代新儒學的產生自然有儒學傳統內部的原因,但無疑也是對西方思想的回應。事實上,作為當代新儒學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牟宗三一開始就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自覺地回應。這也是研究當代新儒家與西方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牟宗三與馬克思主義的專題研究。本章即專門考察牟宗三對於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牟宗三一生對於共產主義的批判,也正是建立在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理解之上。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迅速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有勢力的社會思潮。那些嚮往通過革命來使中國迅速步入現代國家的知識青年,尤其是不以純粹學術研究為然而熱中於投身社會運動者,幾乎無不對馬克思主義趨之若鶩。正如當時中國思想界的親歷者郭湛波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所謂:「近五十年中國思想之第三階段,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主要思潮,以辯證法為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同樣是見證人的孫道升(一九○八─一九五五)將當時的哲學界分為兩系八派,他在論述「新唯物論」(即辯證唯物論)時也指出:「這派哲學,一入中國,馬上就風靡全國,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實在不小,就連二十四分的老頑固受了他的薰染,馬上都會變為老時髦。平心而論,西洋各派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為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肩的。」身在時代思潮之中的牟宗三,自然也免不了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在北平念書的時候,坊間的書店,滿坑滿谷都是左傾的書。北平在當時是最左傾的。從那個時候,共產黨那一套ideology就征服了中國。」「照我個人講,當我在學校讀書時,左傾的思想滿天下。那一套ideology,我通通都讀。……那時候我把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通通都拿來讀,它有一定的講法,我也很清楚。」對於馬克思主義,牟宗三可以說是有相當深入的了解。
但是,牟宗三並未像當時大部分的知識青年一樣被馬克思主義裹挾而去,而自始即對馬克思主義從學理上進行了分析考察。他生平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七、八日刊登於《北平晨報》第一六二、一六三期的〈辯證法是真理嗎?〉當時二十二歲的牟宗三正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而牟宗三在二十世紀三○年代發表的一系列批判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文章,都是他純粹從學理本身立論的嚴肅的學術論文。正如他後來回憶所說:
這些我通通讀,可是我卻沒有受它的影響,讀哲學系的人多得很,比我聰明的人多得很,但是沒有人好好考慮馬克思這些話站得住站不住。我沒有偏見,我不是資本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官僚,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也沒有身分。我只是把它們一個個衡量,就發現沒有一個站得住的。你馬克思批評邏輯,我就把邏輯仔細地讀一讀,law of contradiction(矛盾律)、law of identity(同一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排中律)這三個思想律是什麼?你唯物辯證法怎樣來批駁這三個思想律?是不是相應?三個思想律能不能反駁?你的批駁對不對?
仔細考察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之後,我們就會發現,牟宗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生拒斥,實在是基於其三○年代即已形成的理性認知和判斷。他一生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對於共產主義許多情見乎詞的批判,首先和根本的並不是一種情感性的反應,而是基於他自己對共產主義基本觀念的理解和判斷。在其離開大陸之後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幾乎隨處可見的對於共產主義的頗具情感色彩的批判,不過是他自己理性認識的感性表達而已。這一點,在本書第四章關於牟宗三批判共產主義的部分,會有進一步專門的討論。
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系統批判主要見於其二十世紀三○年代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之中。除了上述〈辯證法是真理嗎?〉這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字之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哲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牟宗三發表了〈矛盾與類型說〉。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北平民有書局出版的張東蓀主編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上卷中,牟宗三發表了兩篇文章:〈邏輯與辯證邏輯〉和〈辯證唯物論的制限〉。這幾篇文章主要都是批判唯物辯證法的。而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發表於《再生》半月刊的〈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則是牟宗三針對唯物史觀的系統和集中批判。至於張東蓀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下卷中所收牟宗三的〈唯物史觀與經濟結構〉,其實是〈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一文的前五部分。大概由於〈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最後部分是牟宗三提出了自己解析社會轉變的原則,所以〈唯物史觀與經濟結構〉一文未收。以下,我們就根據這些文字,並結合其他相關文獻,分別探討牟宗三從學理上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
二、唯物辯證法批判
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自我理解還是從牟宗三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的理解來看,唯物史觀都是內在地包涵了唯物辯證法。即便是對唯物史觀的考察,也不能脫離對唯物辯證法的分析。因此,我們首先考察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的批判,再探討他對唯物史觀的批判。
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來看,唯物史觀是先於唯物辯證法的。不過,唯物辯證法被認為是超越並否定了形式邏輯的新的思想方法,同時也是貫穿於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謂:「辯證法突破了形式邏輯的狹隘界限,所以它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唯物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的批判,正是首先從邏輯的角度著手。當然,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在二十世紀三○、四○年代的中國,牟宗三在邏輯學方面的造詣堪稱一流,較金岳霖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牟宗三發表於三○年代的有關邏輯的一系列文章,都代表當時中國邏輯學者的最高水準,絕對值得在邏輯研究自身的脈絡中予以探討。不過,我們還必須看到,對於牟宗三撰寫的這些有關邏輯的文章,最重要的諸如前文提及的〈邏輯與辯證邏輯〉和〈辯證唯物論的制限〉,其目的和用意除了澄清邏輯本身的問題之外,正在於批判唯物辯證法這一當時所謂的「辯證邏輯」或「新邏輯」。
(一)以維護形式邏輯的方式批判唯物辯證法
首先,牟宗三從邏輯方面維護傳統形式邏輯的三個基本法則,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指出所謂辯證邏輯對於形式邏輯三大法則的顛覆不能成立。當時宣導唯物辯證法的陳啟修(一八八六─一九六○,又名陳豹隱)曾經在其所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一書中對形式邏輯的三大法則逐一批評,牟宗三則在其〈邏輯與辯證邏輯〉一文中逐一進行了回應。
對於同一律,陳啟修有兩點批評。他說:
從表面上看來,自同律的要求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但是他有兩種缺點。第一點,與實際上的事實不合〔……〕如說農民是農民,這一自同律的命題,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內容。農民中有地主、富農、中農、小農、佃農、貧農等〔……〕同是農民,隨時代的不同,而其性質也大有變動。又如說,我是我這一命題,我有幼年、壯年、中年、老年、衰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身體及知識都有了改變了。所以對於一個對象所反映的概念,要求永遠同一的內容,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點,依自同律,標識的總計就是概念。概念既要求永遠同一的內容,就是要求標識的不變;如此,則根本否認了發展,否認新的事像的出現。但是事實上,新的事像是常常發生的。自同律只能認識外部的標識,不能深探內部的關聯;只能認識表面的虛象,不能把握真正的本質。
針對這兩點批評,牟宗三分別予以反駁。他說:
你須知同一律並不反對農民中有富農、有中農、有小農佃農等,它也不反對同一農民可以隨時空而不同,它也不反對他有多種性質。我之有壯年老年,同一律也並非不承認,今日之我非昔日之我,同一律也決不否認,它也不否認知識自體之變化。你幾曾見過有人強不同以為同來?你幾曾見過有人這樣施用同一律來?照你這樣說,好像以前的人都不知道有富農、中農、佃農、小農、幼年、壯年、老年、衰年,等你辯證邏輯家出來才發見了這個真理似的。照你這樣反對,則物理、化學一切其他的學問皆可來反對邏輯,皆可來反對同一律。何其謬也!對象之變化與思想之進行尚且分不開,還談什麼邏輯?
同一律與標識的總計所得的概念有什麼關係?他何曾要求概念的內容永遠不變?他何曾要求對象的標識不變?他也何曾否認事物的發展與新事象的出現?你須知對象的發展與性質和同一律是兩回事,你須知解析對象的發展與性質的理論或學問與同一律也是兩回事的。你就忘記了「說話要合邏輯」這句普通的話嗎?就是你主張唯物辯證法,你作這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不也是有條有理的嗎?你如果真正能否認了邏輯否認了同一律,則不但我,就是全體人類,也早就不知你之所云了。
當然,牟宗三上述的反駁看起來還只是反問。除此之外,對於什麼是同一律,牟宗三還從正面進行了申論。他說:
同一律決不是指兩件具體東西之相似而言,它是要確定一個東西之自身同一。
同一律決不是對象本身各分子間的同一與否,也不是對象本身各時代各地方間的同一與否,它決不禁止事物的變遷與發展,它也決不禁止一個東西有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從這方面來反對同一律,完全不明白什麼是邏輯,什麼是同一律。……同一律不是解析對象諸性質諸關係的命題,它乃是理性開始發展之先在運用(antecedent function),它乃是理性的開荒之先鋒隊。
它是「是」這個概念的確定,不是對象本身的性質之是此是彼、是紅是白的確定。
同一律是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證的東西,這就是他的根本處。你不能拿著事物的變化與性質來否定它。
對於矛盾律,陳啟修的批評如下:
矛盾律是自同律向反面表示,他的公式是「甲非非甲」或「甲不能同是乙又是非乙」。這個原則要求同一主辭不能有兩個相矛盾的賓辭;反過來說,他要求同一的賓辭,對於同一的主辭不能同時又被肯定又被否定。矛盾律表面上很合理,仍是不合事實。譬如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方反對帝國主義,進行世界革命,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各國相依存,如通商關係。這種事實上矛盾的存在,是形式論理所無力處理的。
針對這一點批評,牟宗三反駁說:
矛盾律何曾要求同一主辭不能有兩個相矛盾的賓辭?(其實在此所謂矛盾就是不通的,辯證邏輯家每以一物之具有數種性質、數種關係為矛盾,真是不明白矛盾為何物,不通已極!)它又何曾要求同一的賓辭?矛盾律與物體之多種性質有什麼關係?它何曾禁止物體之多種性質、多種關係?以物體之多種性質同時存在來反對矛盾律,真是荒謬絕倫。……蘇聯一方反對帝國主義,一方與帝國主義相依存,這正是它的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這與矛盾律有什麼關係?矛盾律何曾否認了它的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矛盾律是兩個命題的矛盾的禁止,並不是命題所指示的對象之多種性質的同時存在的禁止。你總不能說它是社會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吧!矛盾律就在這裡。如果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含著非社會主義的成分,這也只表示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就含有多種成分、多種性質在其內,也仍不能否認了矛盾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