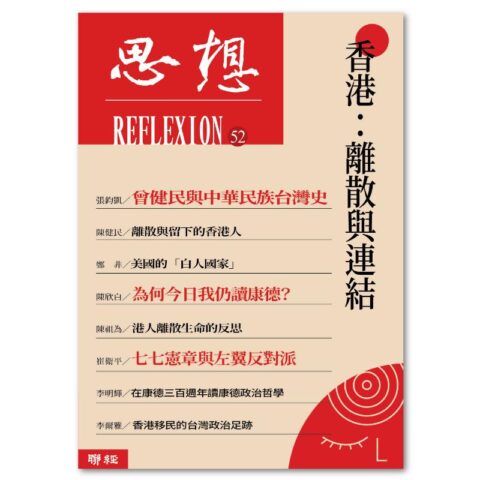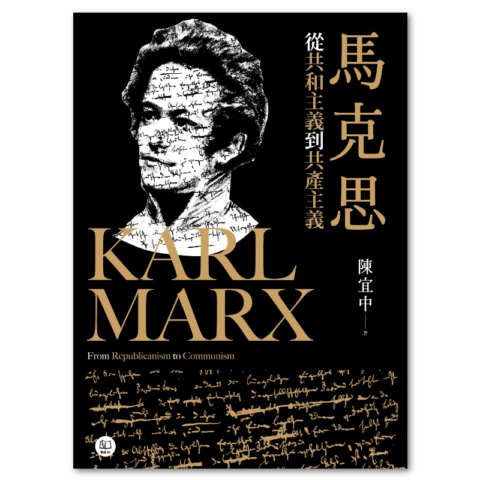情動於「中」:當代中國的思想爭鳴與情感政治
出版日期:2023-07-20
作者:涂航
裝訂:精裝
EAN:9789570869682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以來,儘管中國已從無產階級革命轉向發展主義,有關毛澤東時代的文化與思想論爭,仍未平息。《情動於「中」:當代中國的思想爭鳴與情感政治》聚焦當代中國的思想鳴放與情動政治,追溯兩岸三地知識界近數十年來關於紅色遺產所展開的爭鳴,包括新啟蒙運動的起伏、左翼與自由派學人的激辯、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崛起所激發的「新天下主義」想像。藉著四篇專論,作者涂航回顧李澤厚、劉再復、余英時、陳映真、王安憶、劉小楓等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心路歷程,討論有關「對證歷史」的辯論如何引發了迥異的感覺結構,進而揭示「主義」之爭背後的情感悸動,重塑我們對當代中國知識界思想分化的認知。
與傳統的觀念史研究不同,本書關注的問題是:情感如何參與「思想體系」的構築、影響各種「學理」的闡發、乃至塑造形形色色的「政治立場」?換言之,思想不只是綱舉目張的思辨過程,也牽涉思維主體的癡嗔與愛憎。全書以一九四九為「情動於『中』」開端,講述一段又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陳寅恪五○年代的「心史」寫作成為世紀末自由主義者的懷想對象;李澤厚歷盡文革創傷,力求從廢墟中重建美學價值、塑造情本體;陳映真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嚮往紅色天堂,終必須面對後革命時代的「左翼憂鬱」;劉小楓八十年代從基督神學找尋救贖,遍尋「拯救與逍遙」而不得後,發現殺伐果斷的「政治神學」才是他的歸宿……。這些學者作家的思想根植生命,原是有血有肉的。作者不僅意在描摹個人的歌哭與悲歡,更要觀察他們字裡行間所生的情感如何凝為一種信號,一種召喚與回應,引導讀者體會一個時代「思」與「信」與「感」的取捨。
專業推薦
《情動於「中」》從情感政治角度,勾勒當代中國思想版圖:啟蒙者從「罪」與「樂」重探現代人學與仁學譜系;自由主義者重讀陳寅恪的悲情以見證獨立與自由之必要;左翼作家藉由憂鬱敘事反思革命成敗是非;保守主義者結合政治與神學召喚深不可測的聖寵。這些線索相互鏈接,不僅著眼當代,而且回應了近三百年來情理之辨的大問題,在在可見此一課題的深度和廣度。
——王德威(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這本書是探究中國當代思想複雜圖景的力作。涂航以「情動」做為切入的分析範疇,深入討論了幾個代表人物的論述,展現出的是這個思想圖景的分歧與複雜,也顯示理性言說的驅動力和個人的情感記憶與生活經驗緊密相連而難以切割。作者揭示出當代中國在經歷改革開放之後,革命幽靈為什麼仍然徘徊不去,並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哉問提供了繼續追索的可能路徑。
——丘慧芬(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教授)
本書試圖回答過去一個世紀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何為(中國)革命?從陳獨秀到李澤厚的幾代仁人志士都以「感時憂國」情懷介入有關革命與啟蒙的思想論戰。九十年代以來海內外學界眾聲喧嘩,王德威、汪暉等學者心憂「未完成的啟蒙」議題,發掘革命的唯情向度以及「向下超越」的政治潛能。涂航承前啟後,通過細膩的文本分析討論近百年來激盪中國的各色「主義」如何同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現實發生碰撞,從而產生廣泛、持久的影響。
——柏右銘 (華盛頓大學人文學學系洛克伍德講座教授.電影與媒體研究系教授)
作者:涂航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思想與文學,中英論文散見於《思想雜誌》、《南方文壇》、Critical Inqui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MCLC等刊,另為《明報月刊》等雜誌撰寫文化時評。長於中國南方的九零後,先後求學於中山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自小好讀閒書,酷愛小說,嘗試過創意寫作,未果,而後遊走於學術與生活之間,亦能怡然自得。
序 情動而辭發/王德威
導論 思想的「情動力」
一、革命之後
二、思想的「情動力」
三、對證革命/與過去和解
四、章節概要
第一章 「樂」與「罪」的隱秘對話
一、前言
二、樂感文化:由巫到禮,釋禮歸仁
三、罪與文學:從「性格組合論」到「罪感文學」
四、結語:樂與罪的交匯:告別革命
第二章 自由主義的記憶政治:民國熱視野下的陳寅恪
一、「情動」陳寅恪
二、文化遺民說
三、凸顯的學問家
四、自由主義的殉道者
五、結語:後世相知或有緣
第三章 左翼的憂鬱
一、世紀末的社會主義
二、市鎮小知識分子
三、烏托邦詩篇
四、結語:(後)馬克思主義的幽靈
第四章 從漢語神學到政治神學:劉小楓與保守主義的革命
一、偶像的黃昏
二、拯救與逍遙
三、人神之間
四、革命的微言大義
五、結語:信仰之躍
尾聲 昨日的世界
一、總結
二、中國向何處去
三、多餘的話
書成後記
參考書目
導論/思想的「情動力」
一、革命之後
中國大陸在過去四十年所經歷的引人矚目的市場經濟轉向引發了學界對中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重估」。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以空前之姿重塑知識場域和政治想像的同時,毛澤東革命的幽靈卻徘徊不去,以文學敘述、思想爭鳴和記憶政治等諸多形式魂兮歸來,甚至變本加厲地挑戰和嘲弄啟蒙的共識和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本書試圖深入梳理中國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期間的諸多重要思想與文學脈絡:新啟蒙運動的起伏、左派與自由主義者的激辯、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崛起所激發的大國想像。我認為,改革時代文壇與思想界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即革命遺產為當代中國所提供的價值與靈感: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究竟應該以徹底否思社會主義實踐的方式「告別革命」,還是應該從「革命的回歸」中喚起新的替代性方案和烏托邦圖景?換言之,這是與毛澤東革命「遺骸」(the remainder and reminder of Mao’s Revolution)的對話。1976年以後,雖然革命激進主義政治實踐土崩瓦解,革命的慾望仍然以話語、符號、和想像為載體延展播散,生生不息,引起公眾討論和學術爭鳴。我將論證:有關如何「對證革命」的辯論引發了迥異的政治情感和嶄新的敘述歷史的框架—從左翼知識人的憂鬱、自由主義學人的言說到政治神學家的想像力,進而展現、更新和重釋中國(後)現代性的可能。
時至今日,兩岸三地的知識分子圍繞中國革命的歷史與記憶展開了不絕如縷的思想論戰,而與此相關的學術論述更是汗牛充棟。與傳統的觀念史研究不同,我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情感與思想之間的辯證關係:作為情感結構、道德激情和倫理判斷的「情動力」(affect)如何塑造了關於革命的文化和政治辯論?簡而言之,情感(emotion)如何參與「思想體系」的構築、影響各種「主義」、「學理」的闡發、乃至塑造形形色色的「政治立場」。
誠然,聲稱當代中國知識界仍然被革命的幽靈所困擾,最初聽起來可能有悖常理。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已從宣揚世界革命轉向「發展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說法幾乎成為西方學界的共識。在西方觀察家看來,1981年由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試圖對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做最後的歷史裁決,否定極左政治,推動形成發展市場經濟、參與資本主義全球生產的共識。 九十年代以降,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大陸思想界眾聲喧嘩,支持文化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呼聲層出不窮,使得整個學界呈顯出告別革命、拒斥烏托邦空想、走向「漸進改良」和「現實主義」的趨勢。
即便世界共產革命大勢已去,正如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有革命的「魂在論」(hauntology)一說,看似抹卻的社會主義「情感結構」有如彷徨鬼魅,難以抹消,暗中解構著右翼福音主義的「歷史終結論」。與江澤民時代的放任自由不同,胡、溫政府(2002-2012)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採取了一系列帶有左翼民粹主義色彩的改革舉措來應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平等所滋生的合法性危機。其宣傳口徑也不再一味強調經濟發展,而是多管齊下,在公眾輿論界掀起一陣陣重溫紅色遺產的文化熱潮。社會主義正朔的回歸與自八十年代以來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的資本主義倫理相互激盪,使得思想場域呈現出百舸爭流的姿態。由於蘇東劇變的國際局勢、全球資本主義浪潮的席捲、以及日漸商業化的文化生活,不少大陸學者開始反思八十年代知識界的改革共識,認為必須建立一套新的話語體系和政治理想來矯正「啟蒙狂熱」。1997年,新左派領軍人物汪暉在《天涯》雜誌發表長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認為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代表了自康有為、章太炎以降愈演愈烈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在新左引領的知識潮流中,除了人文學者呼籲從思想脈絡層面闡發五四運動與共產革命的連續性之外,也有不少政治學者和經濟學家從制度層面深入考察毛時代的各種大眾經濟民主和法制實踐,宣揚以黨國體制的「自動糾錯」機制來抵禦私有化引發的社會腐敗和價值的混亂失序。這些標新立異的理論言說隨即引來堅守啟蒙理念和市場經濟的自由派學者的口誅筆伐。出於個人的經歷和現實的挫敗感,不少自由派學人對於任何復興「大鳴大放」式的政治民主嘗試深惡痛絕,他們強調經濟自由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來逐漸形成一個保衛公民權利和政治民主的憲政體制。
時至今日,官方意識形態回潮和學術論戰造成的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在網絡時代的公眾輿論界更是呈現出有增無減之勢頭。2014年,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師們道歉,引發軒然大波,以至於一時間「群情洶洶,議論蜂起,唇槍舌劍,派別林立」。讚成者認為鑒於往昔歷史創傷尚未撫平,多有作惡者逍遙法外而道歉者寥寥無幾,宋氏之舉無疑對反思文革暴力、對證歷史、追求轉型正義具有促進作用。反之,譴責派認為革命摧枯拉朽的詩學正義高於人道主義的膚淺正義,而「道歉」與「寬恕」話語所蘊含的道德主義姿態將一切罪惡歸咎於毛澤東的激進政治實踐,實在是用心險惡。這些此起彼伏的思想論戰和洶湧輿情提醒我們,關於革命往昔的是非之爭,遠遠沒有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平息,反而藉著瞬息萬變的時勢去而復返,幽幽歸來。
為了進一步闡明情感在當代中國思想爭鳴中的關鍵作用,我需要先簡略介紹後毛澤東時代四種主流思潮的形成。從文革結束後到千禧年前後,中國大陸知識界基本上形成了四種立場鮮明卻又相互滲透的「主義」:(1)譴責「救亡壓倒啟蒙」、要求告別革命、恢復五四一代「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之啟蒙訴求的自由主義言說;(2)認為「新啟蒙」話語已無力回應全球資本主義的病症、並藉此推崇毛時代平等主義精神和黨國體制優勢的新左派理論;(3)提出揚棄「啟蒙」與「革命」、重建儒家政教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4)延續官方「百年國恥」的歷史敘事、迎合民間高漲的「民族復興」情懷的大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話語。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分化、理念碰撞的背後,每一種主義的言說都蘊含了獨特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慾望。在自由派看來,從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到群眾運動氾濫的「十年浩劫」,三十年的極左實踐不啻於一連串的人道主義災難,凸顯極權政治的暴虐,因而告別革命、擁抱自由民主乃是歷史正義使然。新左派卻認為,需要區分作為歷史性悲劇的文革和作為解放性理念的文革:激進民主實踐的歷史性失敗並不意味著左翼平等理念的破產。相反,只要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宰制仍四下蔓延,左翼的鬥爭總是未有盡時。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眼中,五四以降的左右之爭凸顯世俗主義(secularism)之濫觴。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都是誤入歧途、積重難返的西洋現代性之產物,而唯有回到靈韻猶存的儒家政教傳統方能重鑄共識,以超越性的文明理念來維護政治共同體之存有。最後,民族主義的旗手們將毛澤東的革命大業看做是結束屈辱歷史、重建國威、復興天朝榮光的里程碑。將「大國崛起」奉為圭臬的民族主義者因此極力淡化中國革命中有關階級鬥爭、國際共運、以及反傳統主義的激進左翼元素,轉而宣揚社會主義實踐的反帝反殖民色彩。
那麼,如何解釋當代中國思想界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對革命的評價如此兩極分化,以至於一部分將「國父」毛澤東奉若神明,另一部分則將革命的遺產視為洪水猛獸?究竟是什麼導致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共識崩塌、內部分化、派系林立、最終走向政治極化?多有學者將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歸咎於不同派系的知識分子所持的基本學理立場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許紀霖、張旭東和汪暉等學者認為,九十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根源在於當新啟蒙運動所持「態度的同一性」瓦解之後,不同學者對於現代性的基本價值「自由、民主、市場、公正、平等」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堅持個人權利優先的自由派希望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來推進自由和法治進程,而左派則更為強調激進民主和經濟平等,認為毛時代的政治遺產有助遏制跨國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和體制性腐敗。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義者關心的則是現代性的倫理規範虧空(the normative deficit of modernity):失去了宗教靈韻庇佑的世俗國家無法以超越性的價值來塑造國民認同和政治共識。簡而言之,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共識崩塌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思想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道不同不相為謀」。
學者和批評家們熱衷於從觀念史學(history of ideas)的角度將思想論爭闡釋為抽象的政治哲學話語、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之間的碰撞:「自由」與「平等」之爭、「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爭、以及「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之爭。我認為,觀念史的理路承自西方思想史家對古希臘以降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學」傳統的細緻分梳,其方法精髓在於把「思想」看做獨立於生活世界以及歷史變遷的「物自體」的存在,其起承轉合遵循著內在的邏輯。因此,注重哲學思辨的觀念史家雖然細緻地釐清了「主義」之爭所折射的價值衝突(the clash of values),卻往往把「思想」的過程化約為抽象哲學理論體系的構築,從而忽略了思想與「生活世界」(lifeworld)之間的互動。此外,與西方語境中恪守某種理論傳統的思想流派(例如法蘭克福學派)不同的是,當代中國思想家常常以「拿來主義」的心態在幾種相互矛盾的中西學術傳統中來回切換,以令傳統學院派難以想像的方式創造性闡釋(或者歪曲)各種西洋哲學概念,將不同的理論言說糅合在一起為我所用。單從某一抽象概念入手梳理當代中國思想的譜系,難免會感覺「亂花漸欲迷人眼」,陷入時空錯亂之迷障。如果不了解抽象思想背後的「生活世界」—由思想者的情緒、記憶、生活經歷、政治信仰等構成的實相世界,我們便很難理解為何對革命遺產的理性思辨會導致強烈的情緒化反應和兩極分化的政治立場。
為了彌合這一缺失,本論題注重思想和「生活世界」之間的互動,既關注情緒、私人記憶、和政治慾望如何創生抽象的哲學概念,又注重從實相世界抽離之後的思想活動如何詮釋包括情緒、感覺和慾望在內的生命書寫。王汎森在對近代中國思想「生活性」的研究中提議,廣義的思想活動「Intellection」是「一切『思』之事物,是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個社會的現象」。如果思想如毛細管一般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那麼反過來說,生活世界的百態—思想家置身於凡塵之中所經歷的生活起伏、慾望、情緒—是否會反過來影響高度抽象性、概念性的哲學思想的生成?由此,我所謂之「思想的情動力」並非僅指形而上學傳統下的哲學反思,而指的是將歷史意識、倫理關切和內在「情動」(affect)轉化成各色「主義」、「理念」和「信仰」的由情入理的思維過程。
以 「思想的情動力」為切入點,這項研究旨在探討當代兩岸三地(大陸、台灣、華語世界)文學想像和思想論戰中對毛澤東革命的「遺骸」的追蹤、指認和敘述。在革命「正統」被質疑、革命慾望卻完而不了的曖昧歷史時期,烏托邦熱情喚起的情感、記憶和理念如彷徨鬼魅,構成當代思想文化界眾聲喧嘩背後三條隱而不彰的線索:一為對毛時代摧枯拉朽之暴力和破壞的沉痛批判,二為因左翼理念幻滅和歷史斷裂所觸發的耽溺憂鬱之哀思,三為革命崇高意象所激發的天啟想像和政治神學。我認為,解答後毛澤東時代文學與思想的激烈轉化的關鍵便在於處理「革命已逝」與「革命猶存」之間的辯證性。同樣面對烏托邦的塌陷,前者以超越和揚棄的方式同革命的經驗和理想決裂,而後者則藉著革命遺骸魂兮歸來之勢尋找使左翼政治「綻出」的另類可能。誠然,如此「類型學」式的解讀雖有以偏概全之虞,然而我無意從社會思想史或是觀念史學的角度梳理出一套全盤敘述。我的目的是細緻地描繪革命的情感結構、政治慾望和文學想像以嬗變的「文」與「思」為媒介,生生不息乃至愈演愈烈的能動過程。
第一章 「樂」與「罪」的隱秘對話
一、前言
1981年,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行世,隨即在校園和文化界掀起一陣「美學熱」。李著以迷人的筆觸描繪了中華文明起源之初的諸多美學意象:從遠古圖騰的「龍飛鳳舞」,到殷商青銅藝術中的抽象紋飾,再到百家爭鳴時期的理性與抒情,這幅綿長的歷史畫卷如暖流般撫慰著飽受創傷與離亂之苦的莘莘學子的心靈。李澤厚早先以其獨樹一幟的「回到康德」論述著稱,然而啟蒙思辨不僅關乎繁複的哲學論證,也得負起終極價值的使命。康德人性論的提綱掣領背後,是幾代中國美學家的關於審美與宗教的深思與求索。五四運動之初,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首倡用美學陶冶性靈以代宗教教化之說。相形之下,李著異彩紛呈的美學意象背後,隱約流動著其對儒學情感倫理學的重新闡釋。在李澤厚隨後描繪的「由巫到禮,釋禮歸仁」的儒學情理結構中,先秦儒學以此世之情為本體,孕育了與西方救贖文化截然不同的「樂感文化」。這種既具有民族本位主義又內含終極價值維度的審美主義試圖為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提供一種安身立命的根基。
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以美學的朦朧想像,重新啟動了五四時期的美育論,以感性詩意的方式呼喚文化和政治新命。面對新的政治想像,批評家劉再復以「文化反思」為出發點,將李著的啟蒙理念闡釋為一種高揚「文學主體」與「人性」的文藝理論,為重思現代中國文學打開了一個嶄新的視野。然而劉說並非僅僅局限於簡單的控訴暴政和直覺式的人道主義,更旨在叩問已發生的歷史浩劫中「我個人的道德責任」。換言之,文化反思並非以高揚個人主義為旨,而必須審判晦暗不明的個體在政治暴力中的共謀。受巴金《隨想錄》之啟發,劉再復以「懺悔」與「審判」為線索反思中國文學中罪感的缺失。劉著受到西洋啟示宗教的原罪意識啟發,卻並非意在推崇一種新的信仰體系。他希望另闢蹊徑,思考文學如何對證歷史,傷悼死者,追尋一種詩學的正義。罪感文學實質上是一種懺悔的倫理行為,通過勾勒靈魂深處的掙扎和彷徨來反思劫後餘生之後生者的職責。
本章以李澤厚的「樂感文化」和劉再復的「罪感文學」為題,通過重構兩者之間的隱秘對話,來勾勒新時期文化反思的兩種路徑。李澤厚在大力頌揚華夏美學的生存意趣和人間情懷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拒斥神的恩寵以及救贖的可能。而劉再復則將現代中國文學對世俗政治的屈從歸咎於超越性宗教的缺失。二者凸顯的共同問題是: 新啟蒙運動為何需要以情感倫理的宗教維度為鑒來反思毛澤東革命的神聖性(sacrality)?簡而言之,對威權政治的批判,為何要以儒學之「樂」與基督教之「罪」這兩種道德—宗教情感為切入點?
在這裡,我需要引入「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這一理論框架,來解釋政治神聖性(the sacralization of politics)與啟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之間的複雜張力。在其始作俑者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看來,理性化進程在驅逐宗教幻象的同時,也導致了「規範性價值的缺失」(normative deficit of modernity)。以技術理性為內驅力的自由民主制不僅無法掩飾其內在的道德缺失,而且在危急時刻不得不求助於高懸於政治程序之上的主權者以神裁之名降下決斷,以維護其根本存在。施密特的決斷論不乏將政治美學化的非理性衝動,然其學說要義並非推崇回歸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而在於借用神學要素來維護世俗政治之存有。由此可見,「政治神學」一詞內含無法調和的矛盾:它既喻指重新引入超越性的宗教價值來將現代政治「再魅化」,又意味著將神學「去魅化」為工具性的世俗政治。不同於施密特對政治「再魅化」的偏愛,二戰後的德國思想家往往以神學的政治化為出發點反思現代政治對宗教的濫用。在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等人的論述中,極權主義往往祭起宗教的術語、儀式、和情感來神聖化其世俗統治。現代政治權威不僅借用宗教的組織和符號,也從基督教的救贖理念和末世論中汲取靈感。在沃格林的筆下,現代全能政治源於靈知論(Gnosticism)對正統基督教救贖觀的顛覆:靈知主義者憑藉獲取一種超凡的真知在此岸世界建立完美的天國。洛維特則更進一步探討了共產主義理念和基督末世論的親和性:暴力革命的進步觀、烏托邦的理念和社會主義新人的三位一體均是基督救世思想的世俗形式。誠然,這種闡釋學的局限性顯而易見:現代政治進步觀與基督末世論之間的概念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並不等同於歷史因果關係(historical causality),把神學理念直接推衍到對現代革命思想和社會運動的闡釋,其解釋效力值得懷疑。例如,中國政治學者雖然注意到毛澤東崇拜與宗教儀式之間的類似性,卻更傾向於強調世俗政治對於宗教符號的「策略性借用」(strategic deployment)。換言之,政治的神化僅僅是一種對宗教元素的功能主義利用。
我以為,這種功能主義的判斷無法解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宏大敘事賦予世俗政治的一種富於宗教情懷的「海洋性感覺」(oceanic feeling)。革命的神聖化本身蘊含了一種相互矛盾的雙向運動:在以世俗政治對宗教信仰的「去魅化」的同時,試圖將宗教的神聖性注入以「革命」、「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為圖騰的世俗變革中。此文旨在以政治神學為切入點來重構李澤厚的「樂」與劉再復的「罪」之間的隱秘對話。我將論證,兩者的論述均以一種隱喻的方式構築宗教意識和政治專制的聯繫,並提出了相應的啟蒙路徑。李澤厚在大力頌揚華夏美學的生存意趣和人間情懷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拒斥神的恩寵以及救贖的可能,而劉再復則將現代中國文學對世俗政治的屈從歸咎於宗教性的缺失。對於基督教超驗上帝(transcendental God)的文化想像導向了兩種看似截然不同卻隱隱相合的啟蒙路徑:以此岸世界的審美主義來消解共產革命的彼岸神話,或是以超驗世界的本真維度來放逐世俗國家對寫作的控制與奴役。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指的「隱喻」並非狹義的修辭策略,而是以錯綜複雜的文辭、審美和想像力生成哲學論述的獨特路徑。不論是德里達等後結構主義者關於文字與思之「再現」(representation)的立論,還是Hans Blumenberg 以哲學人類學為出發點梳理概念性邏輯背後根深蒂固的「絕對性隱喻」(absolute metaphor)的嘗試,這些論述均將流動性的言說和星羅棋布的審美意象看做創生性哲學話語的源泉。更不必說,中國傳統中的「文」與「政」的相繫相依,早已超出了西學語境下的模仿論,而蘊含著道之「蔽」(concealment)與「現」(manifestation)的複雜律動。正因如此,單單從觀念史學或是從文學史的角度梳理李與劉的論述,都無法細緻地追蹤和指認政治—宗教批判與文學/文化批評之間看似毫無關聯,但卻以嬗變的「文」為媒介相互闡發的能動過程。因此,八十年代的啟蒙話語「荊軻刺孔子」式的隱喻政治正是我們闡釋李澤厚之「樂」與劉再復之「罪」的起點。
從另一方面來看,隱喻政治也凸顯「文」的歧義性:與狹義的(現代)文學之「文」不同,四處流串的「文」似乎缺乏有機統一,四處彌散,消解了「文化」、「文理」或「文統」本來具有的批判意義。在這裡,我關心的並不是是大而化之、無所不包的「文」的概念演化,而是重在討論新啟蒙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從李澤厚糅雜中西的美學、哲學實踐到劉再復天馬行空的文化批評—彰顯「情」的倫理教化之功。「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一詞源自十八世紀的西歐啟蒙運動。與高揚理性主體的康德不同,大衛‧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極為強調感性教育的維度,提出培育「同情心」之必要。同一時期的法國啟蒙作家亦把小說作為熏陶情感、塑造道德激情、進而傳播啟蒙理念的重要媒介。與此類似,晚清以來的中國啟蒙知識分子將「文」視為情感教育、聯通啟蒙人性論的關鍵性媒介。例如,陳建華認為,《玉梨魂》這樣的「傷情—艷情」小說旨在「祛除暴力及其情感創傷」,通過「情教」來「重建一種現代國民主體與家庭倫理」。同理,在從「革命」到「啟蒙」的轉型語境中思考情感教育,意味著理解李澤厚與劉再復如何以文學和美學實踐批判毛時代的「階級仇恨」教育,為後革命時代提供普世人性的基礎,進而重塑後革命時代的公民主體性與感覺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