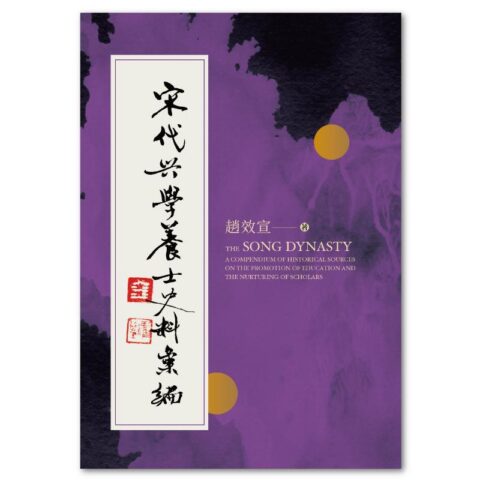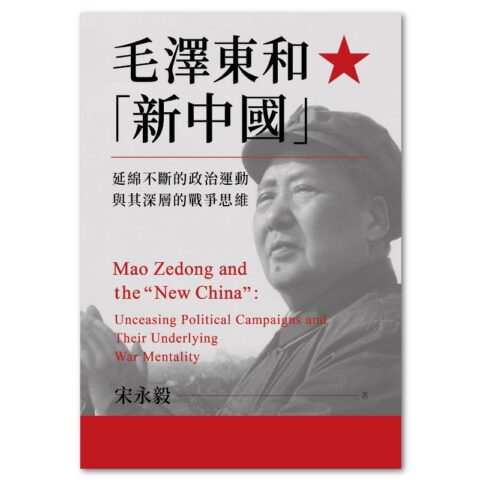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再訪古代中國】卷二 城邦說:國家形態與禮制
出版日期:2026-01-29
作者:杜正勝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68
開數:大18開,24長 × 16.3寬 × 2.6高cm
EAN:9789570878714
系列:杜正勝作品集
尚有庫存
杜正勝院士六十年治史結晶
以宏觀視角重新理解古代中國
從政治、社會、經濟到文化的全景展開
人人心中都有一幅「歷史圖像」──它可能來自書本、來自講述、來自影像或戲劇;卻從不單純等同於歷史的真實。歷史家既追尋事實,又必須在有限的史料間運用理解與想像,於是每一代都在重建屬於自己的「古代中國」。杜正勝院士以深厚學養與縱橫視野,帶領我們重新檢視歷史的表裡內外、制度的生成、家族的運作、文化的傳承,以及非漢世界的遺跡,進入多層次的古代中國。不僅是對古代中國的「再訪」,更是對歷史書寫方法與史學意義的深刻追問。
《再訪古代中國》共五卷
★ 卷一《歷史的內裡:史學傳承與思想》 探討史學方法、考古證據與歷史書寫的界限。
★ 卷二《城邦說:國家形態與禮制》 追索中國古代城邦與禮制秩序的形塑。
★ 卷三《齊民論:政治經濟與家族》 闡明齊民、法制、商業與家族倫理的交織。
★ 卷四《文化基因:先秦古典的根源》 探究思想、倫理與文化想像的歷史基因。
★ 卷五《非漢世界:草原西陲與東海》 聚焦草原、族群與邊疆互動的歷史遺產。
▍卷二 《城邦說:國家形態與禮制》
中國古代城邦的全景剖析,重構三代國家格局
從城與城邦到禮制與身分,揭示社會運作的深層邏輯
中國古代政治起源,是由多樣的城邦形態與禮制秩序交錯而來。本卷聚焦中國古代城邦國家形態,探討早期城邦如何構築社會與權力基礎,闡述其政治、社會與經濟特徵,對比中央地方權力關係,並強調地方自主的重要性,論述中國歷史中殊相與共相並存的張力。透過齊魯故城與商頌文獻考察,揭示考古與文獻如何還原城邦競爭的面貌,論證城邦國家的實際運作模式。卷中亦深入探討中原禮制的如何規範社會秩序,並逐步構築國家形態,以及結合大量墓葬與出土文物分析,呈現貴族與平民生活的差異。不僅兼顧考古與文獻,同時建構中國古典時期國家與社會的完整理解框架。
作者:杜正勝
專研古代中國史,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古代社會與國家》等專著。其他論述如提倡生命醫療史而有《從眉壽到長生》,研究物怪而著《物怪故事解》,探索何謂中國而作《中國是怎麼形成的》。
1990年開始提倡新的歷史研究,與同儕創辦《新史學》,主張開發新課題,拓展新領域,相關討論集為《新史學之路》。
他的新史學思想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增添歷史研究的內容,以下層人民補上層菁英,以社會文化補政治經濟。第二階段超越中國疆界的歷史研究,倡議同心圓史觀,建構臺灣、中國、亞洲與世界的歷史視野。
杜正勝對當前臺灣社會、政治與文化亦多所論述,建立臺灣主體性,論述見諸《臺灣心•臺灣魂》、《走過關鍵十年》。
總序
序
中國古代城邦說
古代中國的城與城邦
齊國建都與齊魯故城小論
商頌透露的城邦爭霸戰
中國古代的殊相與共相
中原禮制的傳承與創新
周禮身分制之確立與流變
文章出處
索 引
再訪古代中國各卷篇目
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自序(節錄)
城邦是一種國家形態,用以概括一國之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的綜合樣貌,和帝國(empire)、王國(kingdom)或酋邦(chiefdom)等國家形態有所區別。
這些國家形態不僅只字面上顯現的政治意涵,其成員的階級性或身分制也會有不同的形式,呈現不同的社會性質,所以政治與社會不可分。上世紀七○年代初始,我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就提出中國古代國家形態是城邦的主張,完成的碩士論文題作「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四年後整理出版為《周代城邦》。周人建國,傳統史學謂之封建,其實即征服殖民,殖民者建立城邦,當時舊族的國家形態也是城邦。不過我更側重的是國家組成的社會基礎,故討論統治貴族、城內國人和城外野人三大階級。
當時我拈出城邦國家形態的一體兩面含攝政治與社會,固帶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猛志,而九○年代我在比較成熟後,有意識地突破樊籬,走出過去政經社會的歷史研究,提倡探索人群之生活、禮俗、心態、情志。剛性的國家形態我比喻作歷史的「骨幹」,而生活禮俗等柔性方面即如歷史的「血肉」,遂謂之新歷史或新社會史。不過,在我人生晚年,經歷比較多世事,也敢說比較了解歷史之後,深深覺得政治還是歷史的核心,重新肯定「骨幹」的部分。本卷的觀點和論述雖然不全是新近之作,但現今的整理條貫則體現我最近二十多年史學思維的新轉折,即使不必然作為晚年定論,猶如古語所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也。
本卷七篇,前四篇關於國家形態的城邦,後三篇偏於社會性質的禮制,相輔相成以認識中國古典時期歷史。解釋夏商周三代的中國古代國家「城邦說」,不像關涉秦漢以下兩千年的「齊民論」之通行,但仍能概括中國先秦兩三千年政治社會的大架構。城邦說的論證俱詳於本卷第一篇的綜合論述和第二篇著重考古出土古城遺址的資料,證據理路應可以禁得起檢驗,所以我也沒有針對一度有人提出的古代帝國或「雛型帝國」的說法提出辨駁。至於第三篇齊魯故城兼具考古與文獻,第四篇說史以解經,從《商頌》的「景員維河」一語證成當時的國家形態是城邦。
歷史上王國或帝國與城邦的大差別在於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前兩者中央對地方如臂使指,城邦則地方自主,諸邦對共主城邦都是獨立的,而邦國內貴族采邑對國君也是獨立的。歷史發展有其趨勢,在特定時空或許產生短暫逆流,長遠看,大勢潮流不會逆轉。如果三代就已經是統一帝國的形態,史料比較充分的春秋時期何以各地還殘存許多小邦,甚至如早期城邦的一城即一國?先秦文獻那麼多遠古萬國的通說,商周之際經過推證知道至少有千餘國,而春秋史籍可考者則一兩百國。這些數據正顯示歷史潮流的大勢,反映大邦吞併小國是城邦時代的通相。可見進入國家階段後,年代愈早,城邦愈多,而非帝國。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各地考古文物出土紛繁,某種文物或文化類型會在相隔遙遠的異地出土,遂為帝國或雛型帝國之說增添證據。不過,同一文物出現在不同地方的原因非常複雜,反映的意義亦截然有異,不一定表示互有隸屬關係。譬如考古所見二里岡期文物分布的範圍遠比殷虛時期遼濶,我們能因此就說二里岡期商人的勢力比殷虛期還強大嗎?有什麼有力證據可以支撐這種認識?相反的,根據《尚書.盤庚》三篇和史書記載,我們有理由推斷盤庚之所以遷殷,是為擺脫先前「九世亂政,諸侯莫朝」的困境而另造新局,於是才有今天從甲骨卜辭和出土文物看到的殷商輝煌文化。怎麼會「九世亂政」時國家影響力還大於二百七十三年不再徙都的殷。在我的城邦分期,殷屬於發展型的封建城邦,而非更早的林立城邦;共主的威權與影響力的確增大了,不過,殷王與方國之間和戰無常,其為國家形態仍然是城邦,不是帝國。
研究比較城邦史的學者羅伯特.格里弗恩(Robert Griffern)和卡羅.湯瑪斯(Carol G. Thomas)指出,世界史範圍內,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多能提供以城市為核心、小而獨立或半獨立政治體的證據,即所謂的城邦(city-states),如西元前第四千紀下半期的蘇美(Sumer),始於西元前 1500 年、盛於前九至三世紀的希臘,中古後期至近世的義大利、瑞士和日耳曼,以及十五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初西非奈及利亞(Nigeria)西北部及尼日(Niger)南部的豪薩(Hausa)等地。然而不同時空文化的城邦可真相似?
格里弗恩和湯瑪斯所編輯的《五種文化的城邦》(The City-state in Five Cultures),歸納上述五種城邦共有的基本特質如下:
(1)以城市為核心,有城牆和護城河環繞,經濟能夠自給自足。
(2)掠奪可以立即生產的腹地,以供應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
(3)基本上有共通的語言、文字、文化和歷史。
(4)尤其重要者,自己認定是一個獨立、自治的政治體,不論它宣稱的政治自治有無更高的合法權威(legal authority)的爭議。(頁 xiii)
若以格里弗恩等的考察來核對中國古典城邦,有同也有異,城牆固然必備,護城河便不一定。城邦經濟自給,但城內的國人亦出城耕種,不是以城外的「野」為掠奪或剝削對象。《周禮》六官序言都說:「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體國經野的「國」指首都城牆內的範圍,「野」則是城外的農莊;城及其腹地結合為一,乃為城邦。至於共通語文、文化、歷史則更難說,如考古顯示魯國城內人口至少可分為周族及商族,衛國分明是殷之舊地;齊國除征服殖民的姜姓西土之人外,還有爽鳩氏苗裔的東土舊族。我們很難說,關中來的周人和東土的商人或更古老的土著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
不過,格里弗恩指出城邦的關鍵特質乃認定自己是一個獨立自治的政治體,(頁 xiv)倒是正確的。以中國古代城邦來說,即使有更高的共主,即《史記.五帝本紀》的五帝及夏商周三代的國君,也無礙於它們內政的獨立自主。至於他說城邦公民擁有實質的能力以獨立地治理他們自己,不同歷史文化條件的城邦恐怕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本卷的〈城邦說〉和〈城與城邦〉二文都指出中國城邦自由民(國人)預政的限度。
作為國家形態的「城邦」,歷經征服併吞,成員來源多樣,即使外表呈現一些共通現象,其社會性質的特異性是很複雜的,只因史料殘闕,難以追究其底蘊罷了。中國古代城邦即使只限於黃淮之間的中原這個不算太大的範圍,如《周代城邦》討論的範圍,今日考古發掘的城牆、建築基址或有限的出土文物並不能道盡其真相。
語言有限,史實無窮,歷史上共名而異實的例證比比皆是。我們所說的城邦時代,傳統史學謂之「封建」,所謂分封親戚,「選建明德,以蕃屏周」也。(《左傳》定公四年)近代日本漢字或中文以傳統「封建」一詞對譯西歐中古的 feudalism,歷史情境明顯地錯置。事實上,即使西歐「封建」,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的差別亦甚大,我在《周代城邦》的〈自序〉對於其中的歧異頗有論述,可以參看。
⏹︎ 城邦說的提出
「城邦」(city-state)是一種國家形態,古今各地文明的發展頗多可見,中國也有過這種形態,而且歷時甚久,大概從傳統歷史所謂的五帝時代到春秋戰國之際,將近兩千年;籠統地說,與「三代」相始終,所以中國古典的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形態基本上屬於「城邦時代」。
這種提法的學者至今還不太多。向來中國史學界討論古史偏重社會性質,對國家形態比較忽略,雖然這兩個層次的問題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只有早年侯外廬提出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的理論,後來研究西方古代史的日知(林志純)也楬櫫類似的意見。日本的東洋史家宮崎市定和貝塚茂樹幾乎同時論述中國古代的「都市國家」。以上四家說法都可以算作「城邦論」,不過我認為用「城市」或「都市」來標識中國古代國家的特質與事實頗有距離,而且會產生誤導作用,其中道理下文將有所說明。自 1974 年我撰寫〈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1979 年題作《周代城邦》出版)以來,陸續發表一些關係中國古代國家形態的論文,我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整體認識也是「城邦論」。
不過由於「城邦」一詞的表面意義只能說明某種國家形態的外緣狀況,無法點出其形態內涵的精神,歷來對於城邦論的討論往往喜歡援引希臘城邦的經驗互相辯駁。其實可以稱得上「城邦」的國家形態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皆出現過,兩河蘇美(Sumer)的城邦固不同於希臘,古代的羅馬與中古的威尼斯雖同為城邦,內容則截然有別,即使同屬於古代兩河流域南部地區,異時異地的城邦也不能一律的。討論中國古代城邦,如果以彼準此,恐怕不容易獲得真相。本文根據個人以往的研究,撮述要義,首要任務在於掌握中國古代城邦的特性,至於古代世界泛城邦的比較,則是另一課題,本文無法申論。
⏹︎ 城邦說的根據
「城邦」這個名詞現在還找不到中國古書的典據,何以見得中國古代的國家形態是城邦呢?恐怕是城邦論者應先回答的問題。
城邦,顧名思義是以「城」作為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國家的重心,不論人力、資源或權力多集中在築有圍牆的聚落,所以討論城離不開最具體的城牆。我們掌握的資料,從文字學、考古學和歷史文獻都證明古國多有城牆。
城,金文作,从庸从成。左邊的「庸」甲骨文和金文同形,今寫作墉,从□从亭,□是圍牆,亭乃圍牆上瞭望用的建築,今日謂之城樓。甲骨金文通常作前後二亭,但也有城周四亭的。右邊的「成」,本字是戉,今寫作鉞,表示防衛力量。單就字形來看,一圈圍牆,牆上二或四亭;圍牆象徵群居聚落,亭代表瞭望,寫實和寓意兼而有之。再加上一把大斧頭象徵武備,那麼一座具有防衛力的大聚落就是「城」了。
「城」首見於西周金文,是比較晚起的文字,較早的「邑」字和「城」共同具備一個要素,即是那圈圍牆。不論甲骨文或金文,邑字皆寫作,象人坐在圍牆下或內。雖然西周以後「邑」逐漸專指小的聚落,但在殷商或周初,大聚落也多稱作邑,如盤庚遷殷,述說他的祖先「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告誡人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尚書.盤庚》)這個新邑就是國都。甲骨卜辭有「天邑商」、「大邑商」,不論指商丘或安陽,商王朝最大、最重要的聚落都可以稱作邑。《尚書.康誥》敘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新大邑當時只通稱邑而已,如《尚書.召誥》周公「達觀于新邑營」,臣卿鼎「公違省自東,在新邑」,及士卿尊「王在新邑」,皆指東都成周。「邑」的字形也顯示大聚落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圍牆。
出土的周初銅器何尊追述周武王
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
或,甲骨文作,金文作、,後者即今日的「國」。「國」(或)字所從的□,即是城字、邑字的圍牆,旁邊的戈一如城字的鉞,顯然圍牆也是「國」的一項必要因素。另外和「國」相近的「邦」,上引《尚書.盤庚》說「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漢代人所謂的「前八後五」,指成湯以後商王五次遷都,所以「邦」的本義亦近於「邑」。金文「邦」字寫作或,从丰从邑。丰即封,下文再談;無邑則不成邦,可見在古人觀念中這圈圍牆對國家的構成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圈圍牆就是考古學上的城牆。中原發現的城牆一般多是夯土,有的挖掘基槽,有的在生土面上直接版築。中國北方山岳地帶的古城牆除纍土之外也堆築石頭,中原城牆除了地層和文化堆積,往往有城牆夯土層或城內探方出土的木炭,依碳十四數據,年代可以比較確定。
今知較早城牆當推河南登封告成鎮的王城崗、淮陽的平糧臺和山東歷城龍山鎮的城子崖。王城崗分東西兩城,東城只剩南垣西段和西垣南段,呈直角相交,其餘多被山洪沖毀,無跡可尋。西城之東垣即東城之西垣,其南、西兩垣在地表下,鑽探得知城角亦接近 90 度。每邊長約百公尺,呈正方形。發掘者推測東城毀後再築西城。平糧臺古城地表猶存,頂寬 8-10 公尺、下部 13 公尺、殘高 3 公尺餘,城垣長度東西、南北各 185 公尺。城子崖,1928 年、1930 年兩次發掘,六十年後重新開挖,認識更清楚,平面近乎方形,東、南、西三垣比較規整,北垣彎曲,城內東西寬約 430 餘公尺,南北最長處 530 公尺。根據城牆地層疊壓及夯土層中的文化堆積,王城崗和平糧臺皆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按碳十四斷代,王城崗兩個數據皆西元前 2455 年,平糧臺一個西元前 2450 年、一個 2280 年,屬於山東龍山文化偏早階段。城子崖的新認識雖然確定是山東龍山文化的城址,但還未見確切的年代估測。同屬於山東龍山文化的古城,見諸簡報者還有壽光邊線王,東垣長 175 公尺、西垣長 220 公尺、中部寬 225 公尺,和鄒平丁公城址,城內南北長 350 公尺、東西寬 310 公尺。可見最遲到山東龍山文化時期,即西元前第三個千年後半,城堡在中原地區已成為聚落的普遍景觀。
總趨勢來看,時代愈後,城邑愈擴大,如河南偃師尸鄉溝商初古城南北超過 1,700 公尺,東西最寬處 1,215 公尺,總計城周約五千餘公尺。可能稍後的鄭州商城,城圈周長則達到 6,960 公尺。到西周晚期或春秋時代,大城如曲阜魯城,周長 11,771 公尺,臨淄齊城 21,433 公尺。但同時也有小城並存,與鄭州商城同時的湖北黃陂盤龍城城牆南北 290 公尺、東西 260 公尺,論面積只有商城的 1/25。西周或春秋時期的小城如河南焦作府城村的商周古城每邊不及 300 公尺,考古發掘雖然不多,但根據文獻所述,周代小城是不少的,大小城的差距也很可觀,這反映城邦大小秩序的現象,下文即將討論。
據目前考古資料,偃師二里頭發現宮殿(或宗廟),未發現城牆,殷墟發掘前後歷六十年,未見城牆;岐山、扶風的周原和長安的灃鎬也有類似的現象,故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國家不必有城牆,或說天子守在四夷,其都城是沒有城牆的。我對這類說法比較保留,考古發掘包含極大的機遇性,二里頭有宮殿無城牆,其附近的尸鄉溝商城則二者兼備。周原舊京據《水經注.渭水注》云,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則漢魏時代周城猶有殘存。灃鎬之地,《大雅.文王有聲》明言,文王破崇,「作邑于豐」;武王纘緒,「宅是鎬京」。準以《尚書》作邑成周及何尊「遷宅」成周之例,當不只是建築宗廟宮室而已,也修城牆的。至於殷墟,解釋比較分歧,或者根本否定這裡是國都(如宮崎市定),或者以為考古發現壕溝,以溝作防。我認為聚落只挖壕溝,不築城牆是早期的現象,如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半坡和姜寨,殷墟早已脫離那個階段,從殷商國力或文化力之廣被程度來推測,其都城的範圍可能超出今日考古工作設定的範圍。觀察中國城邑發展史,單單這些不算充分的證據並不能否定古代城邦存在的事實。
城邦即是國,嚴格定義是一城一國,古書常說「萬邦」、「萬國」或「庶邦」,都形容邦國林立的狀態。如果說從今山東西部到河南西部,包含山西與河北的中南部以及安徽湖北北部有萬國,那麼一國與今日一個中等村莊是差不多的。這種國家雖然和我們的成見極不相同,但晚到春秋仍然殘存有這種小邦。《左傳》記載西元前 524 年邾國乘鄅國國君到城外督導人民種稻,偷襲鄅城,城門關閉不及,被邾人侵入,全國盡遭俘虜,連鄅君本人及其妻、女皆不得倖免。(昭公十八年)鄅國在今山東沂縣北,一戰盡俘,其國之大小可以想見。第二個例子在今河北晉縣,西元前 527 年晉軍圍鼓,「克鼓而反(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昭公十五年)不殺一人而可俘其國君,國家之小不言可喻。既而釋放鼓君,但鼓國再叛,七年後晉國軍隊喬裝糴米者等候在城門外,門一開就發動攻擊,把鼓國滅掉,改為晉國中央統治的行政單位。(昭公二十二年)第三個例子在湖北北部,楚國攻打絞國,坐守北門,伏兵於山下,一戰而絞國投降,訂定城下之盟,可見絞國的確「小而輕」,(桓公十二年)與鄅、鼓不相上下。第四個例子是《論語》所載季氏所伐的顓臾,按照周之禮制,顓臾在魯國境內,是魯的附庸,不能直達於天子,也沒有資格參加會盟,但仍不失為一個國家。季氏的考慮是「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必為後世子孫憂」,不但有城,而且也具備相當的戰鬥力量。這種輕小的城池,《左傳》有一則故事非常形象地反映。莒國有個寡婦,其夫為莒君所殺,年老後住在莒國一個城邑紀鄣,平昔紡繩索,計量城牆高度。西元前 523 年齊國伐莒,莒君逃到紀鄣,齊師隨之追到城外。老婦把握復仇時機,將儲藏的繩索投掛到城外,齊師乘夜緣繩而登,登城者六十人,繩斷,城下的齊國軍隊鼓譟,登上城的軍隊亦鼓譟,莒君打開西門,倉皇逃走。(昭公十九年)
鄅、鼓、絞或紀鄣之類的城邦,一如考古發掘的王城崗、平糧臺、邊線王或城子崖,時代愈早必然愈多,即使經過將近兩千年的吞併,到春秋晚期猶有不少遺存,可以證明中國古代有過一國一城的城邦時代,這種國家一城即一國之所寄,一城破而全國亡。關於他們的興亡存滅,中原國家的史官是很少記載的。然而一般所謂城邦的國家形態當然不限於一國一城而已,包含多個城邑,《周禮.大宰》鄭玄注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大的國家叫做「邦」,小的國家叫做「國」,而邦君或國君所在的城邑也叫做「國」,即今日習稱的國都或首都,正是《左傳》「國」之通義,也是我們理解古代國家形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