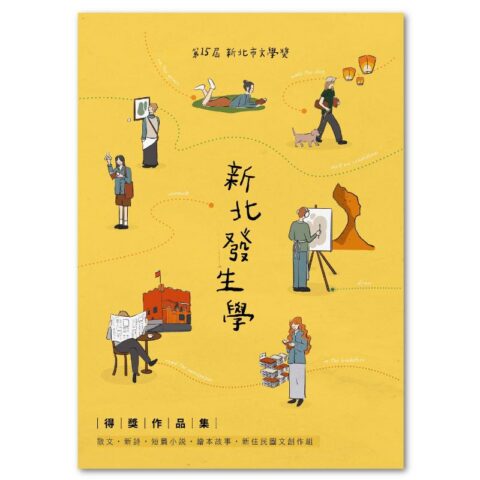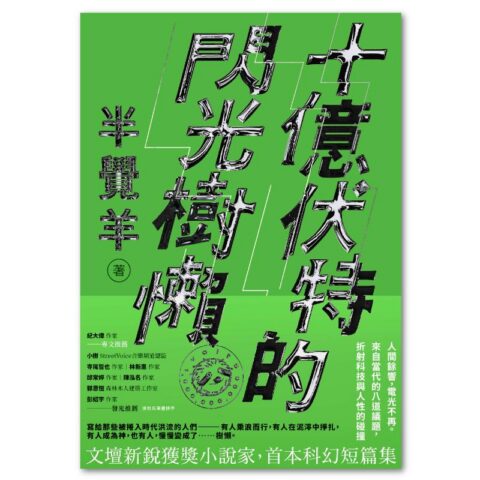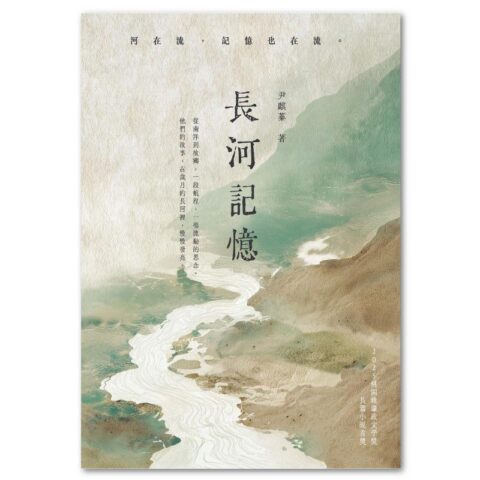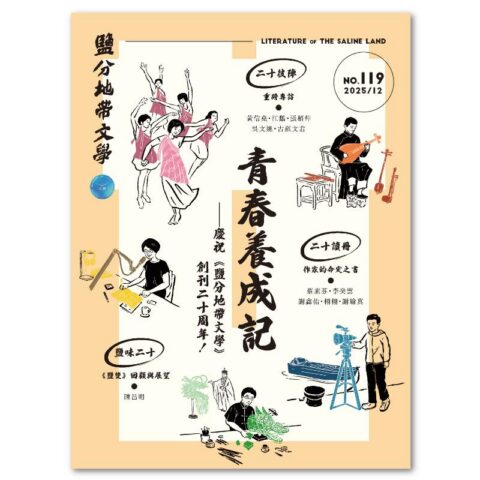書寫青春19:第十九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
出版日期:2022-10-20
編者:聯經編輯部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65974
系列:聯副文叢
尚有庫存
你們的時代回憶,我們的青春提案!
對初試啼聲的新秀來說,文學獎儼然如一紙通行證。證件到手,大門驀地敞開,面對全新陌生景觀,喜悅有之,徬徨亦有之。此時最需要一份地圖,而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除了提供實質上的肯定,更提供如此機會,讓評審前輩們以其生命、創作與閱讀經驗為學子們導覽前路,撥除迷霧,或者無畏地向那迷霧逼近。
羅智成分享,風格之營造,或借重特定主題,或為態度,乃至於語法腔調──箇中竅門,無非是堅持感受。不屈就於陳詞美句,相反地,要更尊敬、更努力探索自我的感覺,如同他在《光之書》後記所寫,「我要為我的性格,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詩。」
何致和認為,觀點才是決勝負的關鍵。然而,題材的選擇其實也反映了寫作者的偏向,個人的感動和喜好難道不會左右選題嗎?當寫作者思索題材或風格時,他建議,不妨將個人放前面一點,技巧總有追上來的一天,只有透過寫作獲得的觸動,才能讓寫作之路走得長遠。
閱讀可博可專精,至於寫,房慧真概略將之分為兩種狀況:一種是作者比作品聰明,作者利用作品傳教;另一種是作品比作者聰明,作者邊寫邊摸索答案,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最終會抵達何處。寫作者的終極關懷是否從中浮現,因人而異。正因為寫作者與其取徑充滿未知性,所以寫作如此迷人,那繁複與豐美,恰恰便如一座熱帶花園。
小說決審:甘耀明、胡淑雯、黃錦樹、鍾文音、駱以軍
散文決審:柯裕棻、張惠菁、須文蔚、楊 渡、簡 媜
新詩決審:李進文、陳克華、零 雨、顏艾琳、羅智成
==============
第十九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得獎作者與作品
短篇小說獎
首獎 〈去當貓吧〉余依潔
二獎 〈若蓮〉陳禹翔
三獎 〈未成功的物品展覽會〉陳映筑
優勝獎〈無聲〉林鈺喬
〈水塔〉顧瑛棋
〈爐火〉林心慧
〈時間的流光〉游耘如
〈白花阿嬤〉林欣妤
散文獎
首獎 〈我們這一代〉羅心怡
二獎 〈二二春〉劉子新
三獎 〈應許之地〉李鈺甯
優勝獎〈籠〉王以安
〈指彩〉黃楊琪
〈青氈〉林子微
〈無人知曉〉張逢恩
〈相忘於江湖〉郭松明
新詩獎
首獎 〈蛇〉古君亮
二獎 〈潛藏〉袁清鋆
〈起霧的鏡〉林鈺喬
優勝獎〈鎖〉張晉誠
〈水星日記〉洪誼哲
〈睡前活動〉程俊嘉
〈誰盲〉陳文昀
〈春日身體說〉林可婕
編者:聯經編輯部
聯經編輯部
序:願小舟航向世界/曾繁城
第十九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金榜
第十九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散文獎金榜
第十九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新詩獎金榜
短篇小說獎
首獎 〈去當貓吧〉余依潔
二獎 〈若蓮〉陳禹翔
三獎 〈未成功的物品展覽會〉陳映筑
優勝獎〈無聲〉林鈺喬
〈水塔〉顧瑛棋
〈爐火〉林心慧
〈時間的流光〉游耘如
〈白花阿嬤〉林欣妤
短篇小說獎決審紀要
散文獎
首獎 〈我們這一代〉羅心怡
二獎 〈二二春〉劉子新
三獎 〈應許之地〉李鈺甯
優勝獎〈籠〉王以安
〈指彩〉黃楊琪
〈青氈〉林子微
〈無人知曉〉張逢恩
〈相忘於江湖〉郭松明
散文獎決審紀要
新詩獎
首獎 〈蛇〉古君亮
二獎 〈潛藏〉袁清鋆
〈起霧的鏡〉林鈺喬
優勝獎〈鎖〉張晉誠
〈水星日記〉洪誼哲
〈睡前活動〉程俊嘉
〈誰盲〉陳文昀
〈春日身體說〉林可婕
新詩獎決審紀要
二○二二 高中生最愛十大好書
選手與裁判:
附錄
作家巡迴校園講座
徵文辦法
二○二二第十九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徵文辦法
文學專刊:台積電文學之星 我的迷戀小史
特別收錄:文學大小事.第2彈 部落格徵文
【文學大小事】「寫給情敵」徵文辦法
文學大小事「寫給情敵」──示範作
文學大小事「寫給情敵」──駐站觀察/夏夏
文學大小事「寫給情敵」──優勝作品十首
創作者的青春提案/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曾繁城
人生中有許多追尋。追尋的背後來自生命的騷動,來自外界的呼喚,也有來自他人的期待。人生的風景非是一鏡到底的順路旅程,更多時候像是剪接室中一段又一段的膠片,每一段的追尋既是終點也是起點。正如小說家何致和獲得聯合報文學獎時的宣言:「我自由了!不用再寫給評審看了!」得獎的瞬間,便是創作自由路的起點。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金榜在每年的夏季公布,創作的種子在盛夏破土萌芽,旺盛的文學生命力燦爛耀眼。自短篇小說、散文到新詩,甚是網路徵文「寫給情敵」的短文與詩作中,皆可看見這群深具天賦的青年朋友對於情感及生活周遭的細膩觀察,以文字的藝術雕塑出心靈意象,撞擊外部世界引發共鳴。這些優秀的作品是創作者的青春提案,更是跨越世代的時空膠囊。
文學培育需要多方的滋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由衷感謝聯合報副刊及文學先進多年的支持與陪伴,除了舉辦徵文競賽,更於高中校園安排文學講座,邀請知名作家與學子交流創作觀點。在影像串流盛行的今日,聯合副刊仍如一盞明燈,引航喜愛文學的大眾及青年世代。
創作的路上無比開闊,亦十分孤單,有其喜悅,有時也帶來憂傷。所有生命的傷痕必是另一次勇敢追尋的滋養。願青年朋友勇敢邁步,為自己剪輯出最精采的人生大片。
【短篇小說獎 首獎】
去當貓吧
余依潔
貓的背毛和尾巴很刺,扳直的四肢飽滿筆直,耳朵像機翼嗡嗡作響,細窄眼眶中誰肥胖的軀體也沒了厚度;貓看起來都討厭我,欠腳也是。
那是外婆取的名,她住在三貂半山腰裡,夜半常摸黑上山路遊蕩,也沒人詢問原因,只當是年老後的副作用;老婦人垂下的胸脯劃過濕冷寒氣,微微反著光的白色衛生衣鬆垮垮蓋在失去彈性的肌膚上,後頭看去凸起變形的肩胛骨,像個迷路的幼童捲縮慢行,野狗呻吟,四周響起山羌喘息般的叫聲,冗長陰鬱的公路合著野林細細將她吞嚥,哼赤哼赤……
「她就這樣騰空出現在車燈前」卡車司機抖著雙手在我面前上下筆劃,雙唇故作堅定,生怕流露一絲心虛。舅舅最先趕到,他從同事得知外婆的消息後急忙跑來看了一眼,擺出長兄架子碎念幾個妹妹沒看緊老人,便又一陣慌亂的離開。
遲來的母親辦完住院手續後在櫃檯前的塑膠椅上坐了下來,乾冷的酒精味蓋過女人招展的香水,我曾質疑過母親和那刺鼻氣味的相容性,她說那像乳溝再平的身版也想擠出一點來,一聞上這味男人就知道該掏出紅包,我不懂並非不是男人,只是班上不會有哪個人這麼做,也不需要;院內各式患者,長的幼的,吊著點滴坐著輪椅的,無一例外臉上都毫無情緒,母親邊環視著大廳邊感嘆鄉裡阿博師老早算到外婆命裡帶福,偏偏上輩子業障未消全,容易受氣場影響,為此當初還花了一筆消災費。
「也算沒花冤枉錢了。」母親長舒了一口氣。
「收白包比較賺吧。」
「呸呸呸,怎麼會賺,也不看看她陰陽怪氣的脾性,兄弟姊妹走得差不多,剩下的年輕人又能有甚麼錢。」
就這樣卡車前大難不死的七十歲老婦人成了鄉裡著名的妖女,有人因此刻意避諱也有人試圖親近,認為佛祖顯靈想撈點陰陽庇護,看著來來往往的街訪鄰居,不知外婆的因果業報是否才正當開始。
過幾周後鄉公所特別編了一支清潔隊,專門提供獨居老人工作和社交機會,外婆也是其中一員,天還未亮就得出門掃馬路,多數人嚮往的興趣即職業,竟在這年過半百的老人身上成功印證,黃色背心鮮亮地映著滿地落葉,隨著人群低語湧動,老婦人從妖女成了樹葉精,彷彿大家都相信那些收在麻袋裡枯黃的屍體全都被精怪私藏囊中回去煲湯喝了修行,外婆倒是對旁人見怪不怪,每日披著發亮小衣,叨唸衣比廟裡求來的護身符還管用,一路上沒人理的野貓多,外婆更樂意和他們打交道。「看,彼個是胖仔,閣有哭夭……咪、咪,一日到晚哭夭,沒有一天飽。」觀察山上野貓,偶爾扔些隔夜的餐食給他們成了外婆日常消遣,獨眼龍、胖仔、餓死鬼……當然沒了左腿的欠角也是,好像只要瞥一眼,就能訂出這些貓如何生,如何死。
「妹妹阿,拄放學喔?」
「黑阿,欲趕緊轉去寫功課拉。」
傍晚巷口擠滿人,多半是隻身前來,然後依著誰的是非聚成小圈高聲細語,住隔壁透天厝的陳姨正好脫離八卦小圈朝我走來,兩顆眼珠直勾勾盯著我的眉眼「是喔……你愛較認真,你媽媽一个人帶你實在辛苦。」
「我知影,多謝你時常關心阮。」
陳姨見我點了點頭,嘴角饜足的抿了幾下,轉身重新跳入小圈
「你佮伊熟似喔?」
「無拉,著是彼个單親拉,單親囡仔!」
「彼個歌廳小姐的查某囡!」
婦人一邊用食指狠狠抵住自己的唇示意對方,不時掃視周圍,憋不住的優越漏滿地,指頭拉皺了制服,我往裡深吸一口氣,昨天剛洗完的花果味襯衫混著賀爾蒙發酵的味道散發出微妙的酸臭,開了口的素色布鞋緩緩向前挪動,空氣有些燙,頸上汗珠艱難的下滑,那群婦人打得熱絡,臉上乾巴的摺子又重新豐盈了一些。
「你以後考個公務員,準時上下班,還能回家吃飯。」
「蛤?雨太大了拉。」
「我說……公務員拉!」
東北雨一盆緊接一盆倒下,沖刷人聲,匯集車流,雨珠順著擋風鏡染身母親的衣領,正想張口,口罩濕漉的內裡憋得胸腔喘不過氣。
「你那醫生舅舅,兒子今年也要去醫院實習,醫生世家阿,他老婆就只剩享福了。」
「還有兩個阿姨,一個頭腦不怎麼樣,學了美容美髮,在那時美髮學徒根本是想餓死自己,幸好嫁了蔬果批發,算不上富貴,起碼也是聽別人老闆娘來老闆娘去;小的說要自己創業,上次見她一頓飯電話接不完,小名牌包掛在椅背多顯眼。」
母親將雨衣掛在牆上,塑料上的皺摺累積好幾漥雨水。
「那種都是機運,你去考個公家機關,實在就好。」
我伸出食指輕碰附著在牆面的小水珠一碰便是一場大遷徙,一遍遍刷新磚牆,無聲向下滑動。
「等明天潮氣過了,自然會乾。」母親說道。
再次看到欠腳是在季風特別旺盛的那年寒冬,外婆出殯隊伍上;前一天公祭,鄉里幾乎無人缺席,彷彿颱風時的里民會堂,擠滿有家卻不可歸的人們,他們都憋紅了或生或熟的面孔,小心揣看家屬神情,不時問上幾句瑣事,打定主意要親自確認老妖婦確實駕鶴西歸,黃色布幕下外婆容貌鮮明,卻比任何時候都還要蒼老,上妝後的大體都強過那張過分老態的彩色照片,外婆一死所有的名都在那哭天搶地的捻香儀式上消散,我曾堅信不移鄉裡人都會在每個獨居老人的葬禮前一晚開會,將亡者的訊息從腦海中抹滅,祂曾有甚麼名,子子孫孫關聯,通通用某種巫術消除,山上地區有幾樣超自然現象也實屬正常吧,其中主辦人大概是阿博師,他就是這樣保住自己名聲的。算命師的清白還未解開,外婆所有的好與壞都隨著這些程序迅速逝去。欠腳在旁一路跟著出殯隊伍走完全程,我想他大概沒參加那場聚會,在他的右耳上隱隱約約能看到一塊缺口滲著血,欠腳缺失地方越來越多,半走半跳的姿態從未停下。
夜裡醫生舅舅、主婦阿姨和她那蔬果商丈夫、賣網拍的小阿姨……全都聚在古厝,神桌下疲憊感和燭光交疊晃蕩,交談聲近乎其微,不過是個山間小鄉,誰家夜半打呼特別大聲,家禽多了幾隻,牲口賣了多少又足夠撐幾個日子……諸如此類芝麻蒜皮傳遍鄉里,赤裸裸攤在眾多炙熱耳目下只是時間長短,即便如此母親他們幾個孩子仍然刻意不做聲響,我才知道外婆的名連著爐子燒盡了,落下的塵覆在留下的人身上,先是舅舅,母親,阿姨…..過了我後知曉外婆那輩的鄉里人也死了大半了吧,隔日所有人匆匆下山,深怕那幾克重的塵灰引來更多口舌;臨走前我看到了那隻三腳貓,瞇起眼捲縮在石子路上,雪白毛皮有層晨霧,耳上的三角口子還不斷沁出一點血。
「帶牠走吧。」不知道貓的記憶有多好,這座山沒剩什麼人能證明外婆不拿枯葉熬湯了,母親沒說什麼,靠著電線桿抽上第二根菸,我將牠套進大塑料袋裡,放在後座為牠繫上安全帶,欠腳只是喵喵叫著,轉過幾個彎後只剩嚶嚶聲,山路的顛簸似乎也把牠轉暈了。
欠腳搬下山後,總是在四十坪大的公寓到處找尋什麼寶藏似,靠著牆能搜上一整天,牠從不理會我的叫喚,自顧自地吃喝撒睡,尋覓這麼久,也總算給牠嗅出沒人拿自己有辦法的氣魄,野性跟著牠的眼一起下山,幾隻麻雀終究遇害於白貓嘴下,一陣尖叫慌亂後母親擺起正色,在陽台出入口架上鐵網,奈何困不住這老貓寥寥無幾的慾望,從鐵網高處跳下時,欠腳僅剩的前肢會連帶胸部重摔在地,耳上傷口順勢漸出血珠,母親看了還是決定作罷。
「缺鐵補鐵,讓牠吃些野味也沒什麼不好。」她邊收起鐵網一邊說服面子,那些光有五臟看起來不長什麼腦的麻雀對輸給一隻三腳貓似乎憤恨不平,每隔幾周討債般吱吱喳喳地不請自來,陽台上伸著懶腰的白貓轉著裂縫般的眼眶,有時滑過我的顱頂,消耗大部分時間。
「乖一點,我很輕……」「這樣才會快點好……不要……再亂動了。」
夜鷺啼叫,高架橋上零星呼嘯行駛的車輛將氣流掃進了廳室,白貓蹬著三隻腳發狂扭動肥嫩的軀體,像顆陀螺不停反覆前後自轉,我捏緊吸飽優碘的紗布直盯那團毛絨風暴,抓緊間隙往牠耳上大開的口下手,一人一貓如此相互對峙已有好一段日子。
「叮拎拎——」
盛滿生理鹽水的瓷碗碰倒,磁磚地一股清冷攀上腿腹,鮮紅的酥麻順著汗毛游下,黏上掌心,動物血混進苦澀碘液摻入這灘泥沼,我伸出拇指劃出幾片深啡色花瓣,一瓣 兩瓣……嗡嗡耳鳴朝向白貓的眼,真空的窒息,欠腳滿臉不在乎,左耳口子上噗簌噗簌又結出了幾顆紅果,紅得安靜腥得鮮明,一股子屍臭味衝上,我能嗅到前前後後死去的麻雀怨靈在牠耳上不停自我繁殖,那刻我為將牠們葬入有蓋垃圾桶感到自責,只當是沒了幫忙的入殮,總歸都是要燒成灰的。
手掌那道開口一呼起氣來密麻麻的刺痛感一把將我拉回小室,雜亂掌紋中觸目的血盆大口撞進腦內,淚水洩洪似地爆發,我對著那團毛絨大罵。
「欠腳!老番顛!討厭鬼!缺角!惡魔!撒旦!沒人要的三腳貓!」
牠停下動作回罵一連串嗷嗷喵喵,走在自己的頻率,絲毫對不上我的回應
「嗷嗷嗷嗷—喵—喵嗷」
清早欠腳頂著朵大王花,花身重得牠抬不起頭,走起路來遲緩,一路停停蹭蹭,一點點拈下深紅的肥厚花瓣,腐敗味鑽進每個犄角,我張開所有孔隙等待它將其補滿,仍未散去的潮氣在腳下積累,柏油似盤上腳踝稠軟而黑亮,死死定住雙腿,白貓俯地長號,排泄了滿地,尿糞拖出蜿蜒的迴旋畫作,圈起牠滿腹血水,喚回失走的名。
外婆在古厝塗上的點仔膠沒有這股腥臭,我又向下摸了一把。
「嘔,好腥。」
是經血,臀部浸在變了色的點仔膠中,床單因吸了過多經血變得浮腫。
「醒了?」我扶著牆走出房門,母親坐在皮質沙發滿臉倦容撥著電話,嬌豔的服飾還未褪下,我走進廚房開了盒新鮮的罐頭兌上一些溫水和魚油,細長的筷子順時針攪動,走過母親身邊她皺起眉指了指我通紅的睡褲,右手繼續和著食糧 ,經血味還緊黏褲底,欠腳睡在儲藏室角落,體液泡濕牠大半毛髮,窗外天光大亮,清黃正陽下白貓耳上靡爛的腐肉枯萎捲縮,瘦骨嶙峋,竹筷在鋁箔盒裡斷了半截,木屑插入指肉,那半截直挺挺地插在了鮭魚肉絲上。
「骨灰……骨灰不用留。」
「集體五千阿?牌位……」
「樹葬嗎,額外費用……」
母親撥著紙鈔,仔細搓揉後交付了五張藍紙給門外帶著一頂藍色鴨舌帽,身穿印有狗掌印休閒衫的男人,欠腳僵直四肢被抱進紙箱內,瞪大的雙眼彷彿只是剛受驚嚇還未緩和過來,我們雙手合十聽著誦經聲,鮮黃的往生被嚴實蓋在欠腳身上,理所當然地,素未謀面的男人帶著裝了箱的白貓和五千大鈔,鄭重行了禮後匆匆離去,我才想起身下乾硬的血漬還留存在那。
牠的牌位安排在藥師佛像旁,大悲咒從不間斷地朗誦,到處都是鮮黃色,欠腳兩字也寫在黃色卡紙上,那隻白貓陌生的名,看過樹葬地點,墓園最深處一塊看似荒廢的草坪,一顆委靡小樹插在那層層疊覆的厚重骨灰中,牠輕薄的骨也混在這片灰濁。
「公共行政系好像不錯。」
從靈園回程路上,母親駛著休旅車試探性問了幾句。
「不太適合我。」
「我們不是說好了。」樹影沿著車窗交錯擺盪,車身搖晃彎過幾個大彎,晚風挔過樹梢,天暗得越來越晚。
「那你要做什麼。」
「我想要……我 我要當隻貓吧。」一個下坡,慣性帶著我前傾,拉近了唇畔和駕駛後腦杓距離,小小氣音也能毫不費力傳達清楚。
「是喔……我打算過幾年辭掉工作,回去古厝。」
「他們全都知道你是誰。」夕陽拉長了我們的影子,眼看要溢出這狹小空間時又將兩個個體的虛影揉捻,一圈暈黃繞著母親,瞇起眼看像有一層薄灰色的粉塵壟罩著她。
「看,斷尾。」母親搖下車窗指著遠處一隻少了半條尾巴的大黑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