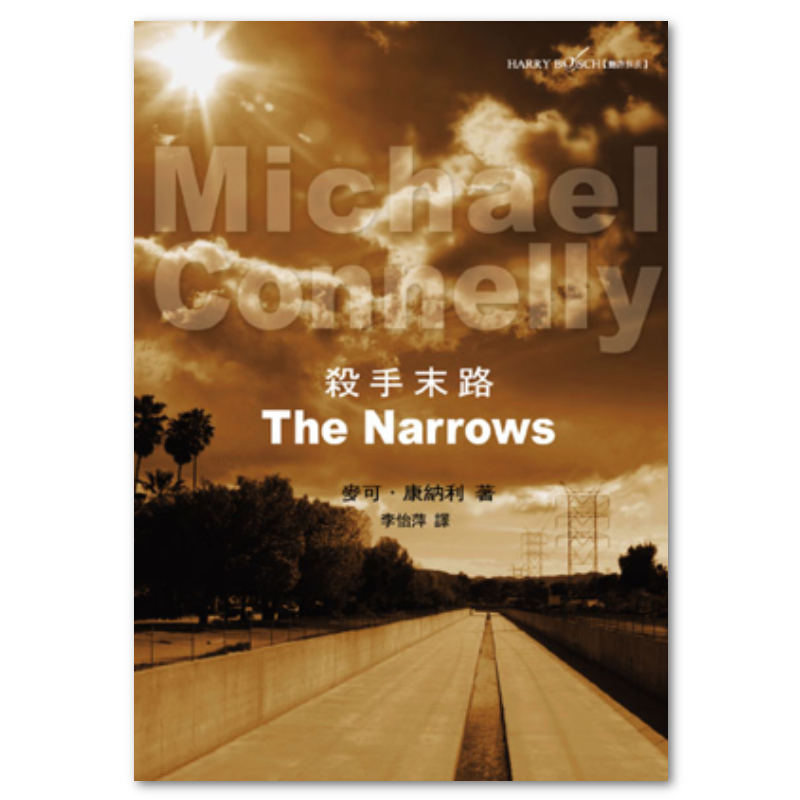殺手末路
原書名:The Narrows
出版日期:2014-10-17
作者:麥可‧康納利
譯者:李怡萍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68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4689
系列:康納利系列
已售完
他是她最恐怖的夢魘,卻也是重獲救贖的唯一機會!
美國推理天王麥可•康納利最新中文版作品《殺手末路》
榮登《洛杉磯時報》排行榜冠軍,
空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舊金山紀事報》等十大暢銷排行榜!
書迷期待多年的續集,
《鮑許系列》、《詩人》、《血型拼圖》三大名作主角大會串,
洛城史上最恐怖殺人魔,「詩人」重現江湖!
作品全球發行超過兩千四百萬冊,翻譯超過31種語言
多年後,聯邦調查局探員瑞秋•沃林終於等到這通電話,電話中她聽到:「詩人」回來了!多年前她投入追查這個用詩句串起一連串令人髮指謀殺案的連環殺手。她從未忘記這個自稱「詩人」的殺人魔──顯然「詩人」也沒忘記她。
哈瑞•鮑許也接到一通電話,致電這位前洛城警探的,是他最近去世的老友泰瑞•麥克凱勒柏(見《血型拼圖》)的妻子。但隨著追查這位老友看似再自然不過的死因,卻一步步將他帶往「詩人」身邊的恐怖未知世界。
在《殺手末路》中,兩大系列主角哈瑞•鮑許與瑞秋•沃林攜手合作,追緝洛城史上最殘忍無情也最機智狡猾的殺人兇手。兩人一路從內華州的沙漠到繁華的賭城大街,再追至洛城的陰暗死角。這次「詩人」會否再次脫逃,他們能否終結這一連串恐怖惡夢,鮑許又能否讓泰瑞的死因真相大白?
〈國際媒體一致推薦〉
GQ雜誌譽為「全球最佳偵探小說家」的麥可•康納利,在第十部鮑許警探系列作《殺手末路》中再登巔峰。他在此證明,這稱號絕非雜誌的誇張過譽。
──《達拉斯晨報》
《殺手末路》情節豐富、迂迴曲折,但即使沒讀過之前多部鮑許警探系列作也絕不難讀……《殺手末路》是他繼《暗甚黑夜》(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後再創新高之作。本作將令舊書迷欣喜若狂,並開拓許多新書迷。他絕對當得起如此盛讚。
──《聖彼得堡時報》
續集常令人失望,但《殺手末路》絕對是個例外。本書將是康納利截至目前的最佳作品……從各種層面來說,《殺手末路》都擔得起所得讚譽,甚至猶有過之。
──報書人書評網站(Bookreporter.com)
作者:麥可‧康納利
1957年生於美國費城附近,1980年自佛羅里達大學畢業,主修新聞學,副修文學創作,之後於《洛杉磯時報》主跑犯罪新聞。於洛杉磯工作三年後,康納利決定著手創作,從新聞記者搖身變為推理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說《黑暗回聲》(The Black Echo)發表於1992年,故事根據洛杉磯一宗罪案改寫而成,不但贏得美國推理小說界最高榮譽愛倫坡獎(Edgar Awards),更奠定其文壇地位,此外也帶出一系列以警探哈瑞‧鮑許(Harry Bosch)為主角的作品。鮑許警探系列之外,康納利另著有以律師米奇‧海勒為主角的法律推理系列,以及《詩人》與《血型拼圖》等多部獨立推理作品,他曾陸續獲頒美國安東尼獎、尼洛‧吳爾夫獎、麥卡維帝獎等。康納利至今創作不輟,作品風行全球、已翻譯超過三十種語言,並分別有《血型拼圖》與《林肯律師》(中文片名:下流正義)於2002及2011年改編為電影。他曾任美國推理作家協會2003、2004年主席,現居佛州。
譯者:李怡萍
政治大學英語系畢業,從事編輯、翻譯多年。譯作有:《別再為小事抓狂之二》、《放鬆解壓全書》、《關於靈魂的21個秘密》、《我是人,所以我說謊》等書籍,以及多部電影翻譯。
1
她身處黑暗,在一片闃黑的大洋中漂浮,天空全無星斗,她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到。在此絕然漆黑的時刻,瑞秋•沃林睜開眼睛,從夢中醒來。
她盯著天花板,聆聽屋外的風聲,聽到杜鵑花枝葉摩娑窗戶的聲音。她不知吵醒她的究竟是枝葉摩娑玻璃的聲音,還是屋內的其他聲響。然後她的手機響起,她沒受到驚嚇,從容地伸手至床頭櫃,把手機拿到耳邊,完全清醒地回答,聲音沒有絲毫睡意。
「我是沃林探員。」她說。
「瑞秋?我是雪莉•黛伊。」
瑞秋立刻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勤務電話,雪莉•黛伊代表寬提科,瑞秋已經四年沒接到寬提科的消息了,她一直在等待。
「瑞秋,妳人在哪兒?」
「我在家,不然還會在哪兒?」
「妳負責的區域很大,我還以為妳會──」
「我在急流市,雪莉。什麼事?」
她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回答。
「他浮出水面,他回來了。」
瑞秋感覺一隻無形的拳頭重捶胸口,然後攫住她。她的腦海開始出現回憶與畫面,不好的回憶。她閉上眼睛。雪莉•黛伊不需要說出名字,瑞秋知道她說的是巴克斯。「詩人」重出江湖了,正如他們預料。像個感染全身的惡疾,停止肆虐幾年之後,再度冒出皮膚,提醒世人它的醜惡。
「告訴我。」
「三天前,我們在寬提科收到一樣東西,是個包裹,裡面有──」
「三天前?你們就這樣放著三天不管──」
「我們沒有放著不管,我們是慎重處理。收件人是妳,是寄到『行為科學部門』,收發室交給我們,我們用X光機掃瞄過,然後小心地打開它。」
「裡面是什麼?」
「一個GPS儀器。」
一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儀器。有經緯度座標。去年的一個案子裡瑞秋也碰過這東西,那是發生在惡地國家公園(Badlands National Park)的一樁綁架案,那位露營失蹤的女士有個掌上型全球衛星定位儀,她將行經路程標記在上面,警方在她的背包發現的,他們根據衛星定位儀追蹤她的路徑,來到一個營地,她就是在這裡遇到一名男子,然後被尾隨跟蹤。警方晚了一步,沒救回她的性命,但要是沒有GPS,他們根本找不到那個地點。
「上面有什麼?」
瑞秋坐正起來,雙腿在床沿擺盪。她另一隻空出的手放在腹部緊握,像朵枯萎的花,她等著雪莉•黛伊繼續往下說。瑞秋記得她還很菜的時候,當時她參加調查局的實習計畫,只是行動小組中的觀察員兼學員,瑞秋被指派為她的導師。十年過了,一個案子接著一個案子,這些案子都在她的聲音裡畫下深深的刻痕。雪莉•黛伊現在可一點兒都不菜,她也不需要跟著師傅了。
「上面標示了一個路徑點:『莫哈維』,就在加州靠近內華達州邊界。我們昨天搭機去了那裡,我們用熱像儀和氣體探測儀,昨天稍晚發現了第一具屍體,瑞秋。」
「死者是誰?」
「我們還不知道,不是新的,已經埋在那裡好一段時間,我們剛要開始,挖掘工程很緩慢。」
「妳說第一具屍體,到底還挖出幾具?」
「我離開現場的時候,已經有四具了,我們認為再挖下去還有。」
「死因?」
「還未確認。」
瑞秋停下思考。她過濾後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何會在那裡,又為何在這時候。
「瑞秋,我打來不只是要告訴妳這件事,重點是『詩人』又開始出沒,我們需要妳過來。」
瑞秋點點頭,她當然非去不可。
「雪莉?」
「什麼事?」
「你們為什麼認為包裹是他寄的?」
「我們不是認為,我們知道就是他,不久前我們取得GPS上的指紋,拿來比對,完全吻合,那是他換電池時留下的,我們取得一枚姆指。鮑伯•巴克斯,是他,他又出現了。」
瑞秋緩緩鬆開拳頭,仔細端詳著手,她的手如雕像靜止不動。適才的懼怕情緒已經轉換,這是無法對其他人坦承的感受。她感覺到血液中再度充滿活力,她的血液變成更暗的紅色,幾近黑色。她一直在等這通電話,每晚睡覺時都把手機放在耳邊,是的,接到任務電話,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但這通是她一直以來真正在等的唯一一通電話。
「在GPS上,路徑點可以命名,」黛伊在寂靜中說:「最多十二個含空格的字元。他把這個路徑點命名為『Hello Rachel』(哈囉瑞秋),剛好十二個字元。我猜他還沒把妳放下,看起來像是他準備好一個計畫,然後把妳召喚出來。」
瑞秋憶起一個男人向後跌倒,撞破玻璃墜入黑暗,消失在下方那片闃黑虛無中的景象。
「我立刻上路。」她說。
「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分部,從那裡進行地毯式搜索容易一點。小心點,瑞秋,我們不知道他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明白嗎?務必小心。」
「我會的,我一向如此。」
「再打電話告訴我班機細節,我去接妳。」
「我會的。」她再說一遍。
然後她就掛斷電話,手伸向床頭櫃,把燈打開。在某一刻,她想起那個夢,死寂的闃黑大洋和天空,像是兩面彼此相對的黑色鏡子,而她就在中間,就這樣飄浮在那裡。
2
當我抵達洛杉磯的家,葛瑞西拉•麥克凱勒柏已停好車,站在我家外頭等著。她準時赴約,但我遲到了,我迅速將車停進車棚,然後趕緊下車迎接她。她看起來並不生氣,反倒一付氣定神閒的樣子。
「葛瑞西拉,抱歉遲到了,今天早上路上很塞,我被堵在十號公路上。」
「沒關係,我挺自得其樂,這裡很安靜。」
我拿出鑰匙開了門,要推開門時,卻發覺門被屋內堆在地上的信件卡住,只得彎身將手伸進門裡把信件拉出來,才能把門打開。
我站起身,轉向葛瑞西拉,手往屋內一比,她從我身邊走過進了門,這時候我沒有微笑。我最近一次見到她是在葬禮上,她現在的氣色只比當時好一點點,憂傷依然停駐在她的眼神中,留在嘴角上。
她在狹窄的門廳跟我錯身而過時,我聞到一股甜甜的橙香,我記得在葬禮上也聞過這個香味,當時我兩手緊緊包覆她的雙手,說我非常遺憾她痛失親人,她若有任何需要,我都願意幫忙。她那時身穿黑色服飾,今天她穿碎花夏裝,在香氣的襯托下更加迷人。我手比向客廳,請她到沙發上坐,問她要不要喝什麼,儘管我知道家裡沒什麼能招待人,大概只有冰箱裡的幾瓶啤酒和水龍頭的自來水。
「不用了,鮑許先生,謝謝你。」
「拜託,叫我哈瑞就好,沒人叫我鮑許先生。」
現在我努力露出微笑,但對她不管用,真不知我怎會認為微笑會對她管用,她的人生歷經風霜,我看過那部電影,而現在又遭遇這樣的不幸。我坐在沙發對面的椅子上等著,她清清喉嚨,開口說話。
「我猜你一定在納悶我為什麼得來找你談,抱歉電話中不便明說。」
「沒關係,」我說:「但我確實開始好奇了。出了什麼事嗎?有什麼我能幫得上忙的?」
她點點頭,望著自己的手,她的手拿著擱在腿上的黑色珠包,看起來應該是為了葬禮而買的。
「出了很大的事,我不知道該找誰求助,我從泰瑞那裡聽得太多──我是說關於他們的處理方式──所以我知道不能去找警察,現在還不是時候;而且,他們也會來找我,我想應該很快。但在那之前,我需要找個能信任的人,一個可以幫我的人,我可以付你錢。」
我把手肘放在膝上,雙手合握,身體前傾。我只見過她那麼一次,就是在葬禮上,她丈夫和我曾是很好的朋友,但最後幾年沒那麼親近,而現在已經太遲,我不知她所謂的信任從何而來。
「葛瑞西拉,泰瑞跟妳提過我什麼,讓妳覺得能信任我,讓妳選擇我?妳跟我幾乎完全不了解彼此。」
她點點頭,似乎覺得這問題和判斷還算公允。
「我們還在一起時,有次泰瑞把所有事情都告訴我,他說的是你們合作的最後一案,他告訴我事情經過,在船上時你們如何救了彼此的性命。所以我覺得能夠信任你。」
我點點頭。
「我永遠記得有次他跟我說了一件關於你的事。」她繼續說:「他告訴我,你有些地方他不喜歡、不能苟同,我猜他指的是你做事的方法。但當天晚上他說,所有認識和合作過的警察和探員中,如果要挑一位共同偵辦命案,他會選你,就這麼簡單,他說他會選你,因為你不會放棄。」
我感覺眼眶周圍緊繃,彷彿真的聽到泰瑞•麥克凱勒柏這樣說。我問了個問題,雖然早已知道答案。
「妳要我幫什麼忙?」
「我要你調查他的死因。」
3
葛瑞西拉•麥克凱勒柏要請我幫的忙,雖然我心裡早已有數,但她提出時我還是愣了一下。泰瑞•麥克凱勒柏一個月前死在自己的船上,這是我在《拉斯維加斯太陽報》上看到的消息,他的死訊會上報是因為那部電影。一位聯邦調查局幹員接受心臟移植手術,然後追查殺害捐心者的兇手。這故事經過好萊塢改編,由克林•伊斯威特主演,雖然他比泰瑞老了二十歲。這部片的票房只能算差強人意,但讓泰瑞變得小有名氣,訃聞有資格刊登上全國報紙。有天早上我剛回到拉斯維加斯大道附近的公寓,買了份《太陽報》,就看到泰瑞死訊的短文刊在A版背面。
當我閱讀時,內心深處開始顫抖,我很訝異,但又沒那麼訝異。泰瑞一直以來活得就像隨時會走的樣子。但我從報導所見,以及之後到卡特林納島參加葬禮聽聞的,都沒什麼可疑之處,都說是心臟──他接受移植的那顆新心臟衰竭。這顆心臟已經讓他多活了六年時光,比全國心臟移植患者的平均壽命長,但最後還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心臟衰竭。
「我不明白,」我對葛瑞西拉說:「他當時是在他的包船上昏倒,他們說……是他的心臟。」
「對,是心臟的關係。」她說:「但有新發現,我需要你去調查。我知道你已經退休,但泰瑞和我在新聞上看到了去年在你這裡發生的事。」
她環顧屋內,用手比畫著。她說的是一年前發生在我家的事,那是我退休後接的第一樁調查案件,結果以流血悲劇收場。
「我知道你仍在辦案,」她說:「你跟泰瑞一樣,他就是沒辦法丟下事情不管,某些層面上你也一樣。我們看到你家出事的新聞那時候,泰瑞就說,他若要找人合作就會挑你。我想他會這麼說,意思就是萬一他出事的話,我應該去找你。」
我點點頭,盯著地板。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我會跟妳說我能做什麼。」
「你跟他有種深厚的關係,你知道嗎?」
我再次點頭。
「說吧。」
她清清喉嚨,身子挪至沙發邊緣,開始說話。
「我是護士,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電影裡把我改成服務生,那樣不對,我是護士,我有醫藥常識,我了解醫院的一切。」
我點頭,沒有開口打斷。
「法醫為泰瑞解剖相驗。不是因為有什麼異常跡象,他們是依泰瑞的心臟科主治醫師漢森醫生的要求進行的,因為想看看能否發現是哪裡出了問題。」
「好。」我說:「那有什麼發現?」
「沒有。我的意思是,沒有任何不法問題,就是單純的心臟停止跳動……然後,他就死了。這很常見。相驗結果顯示心臟壁肌肉變薄,越來越窄。心肌症。身體在排斥這顆心臟。他們只做了一般的血液檢驗,就把他的遺體交給我領回。泰瑞不想土葬,他以前老是這樣告訴我,所以我讓他在葛瑞芬與里夫葬儀社火化。葬禮後,巴迪帶我和孩子搭船出海,我們按照泰瑞的遺願把骨灰灑入海中,讓他離開。那是很私密的儀式,感覺還不錯。」
「誰是巴迪?」
「喔,他和泰瑞一起合作包船生意,是他的合夥人。」
「對,我想起來了。」
我點點頭,琢磨著她的話,試著找出緣由,找出她來見我的原因。
「驗屍的血液檢查,」我說:「驗出什麼了嗎?」
她搖搖頭。
「沒有,就是因為沒驗出什麼。」
「什麼?」
「你要知道,泰瑞每天吃一大堆藥,瓶瓶罐罐的各種藥,他靠那些藥活命,所以血液報告洋洋灑灑有一頁半之長。」
「他們寄給妳了?」
「不是,是韓森醫生收到,他再告訴我的。他打來是因為發現血液檢驗中少了兩樣東西:山喜多和普樂可復,他死時血液中竟然沒有這兩種藥物。」
「而這兩樣東西很重要。」
她點點頭。
「沒錯,他一天要吃七顆普樂可復膠囊,兩次山喜多,那些藥對他很重要,讓他的心臟能正常運作。」
「要是沒有這些藥他就會死?」
「大概只能撐三、四天,很快就會發生鬱血性心臟衰竭,這正是發生在他身上的症狀。」
「他為什麼停止服藥?」
「他沒有停止服藥,這就是我需要你幫忙的地方,有人對他的藥動手腳,害死了他。」
我再次仔細咀嚼她提出的所有訊息。
「首先,妳怎麼知道他真的服藥了?」
「因為我親眼看到,巴迪也看到,甚至那位最後一趟跟他們同行的租船的人也看到他吃了藥,我問過他們。我說過我是護士,要是他沒吃藥,我一定會發現。」
「好,所以妳的意思是,他吃了藥,但那些不是他的藥,藥被人動過手腳。妳為什麼這樣認為?」
她的身體語言透露出洩氣,她認為我沒按正常邏輯思考。
「我補充一下,」她說:「葬禮過後一星期,還不知道這些事之前,我準備讓生活回歸正軌,便開始整理泰瑞放藥的櫃子。你知道,那些藥非常非常貴,我不想白白浪費,有些病人根本買不起這些藥,我們自己也買不起,泰瑞的保險給付已經用完,我們是靠政府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畫才能負擔他的藥。」
「所以妳把藥捐出去?」
「對,這是移植病患的傳統,每當有人……」
她往下看著自己的手。
「我了解。」我說:「你們會把所有的藥捐出去。」
「對,好幫助其他人,那些藥太貴了。泰瑞至少還有九週的藥量,可以幫別人省下好幾千塊。」
「是。」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藥帶著,搭渡輪到醫院。每個人都很感謝我,我想也該塵埃落定了,我有兩個孩子,鮑許先生,不管多艱苦,為了他們著想,我都得繼續往前走。」
我想到他的女兒,我從沒見過她,但泰瑞跟我提過她,把她的名字告訴我,以及命名的由來。我納悶葛瑞西拉是否知道這件事。
「妳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韓森醫生?」我問。「要是有人動手腳,妳應該警告他們……」
她搖搖頭。
「醫院有一套標準程序,所有容器都檢查過了,你知道,瓶子上的封條檢查過,使用期限檢查過,回收批號等等都檢查過了,沒發現任何問題,沒有篡改的痕跡,至少我給他們的沒有。」
「那問題出在哪兒?」
她再往沙發邊緣挪一點,現在要進入重點了。
「在船上。打開過的藥瓶我沒捐出去,因為醫院規定不收已開封的。」
「妳發現有動手腳的痕跡。」
「藥瓶裡還有一天份的普樂可復和兩天份的山喜多,我把那些藥放在塑膠袋裡,拿到以前上班的阿瓦隆診所,我隨便編個故事,說我一個朋友在洗衣服時,在兒子口袋發現這些膠囊,她想知道他到底在吃什麼藥。於是他們把藥拿去檢驗,發現那些藥全都是假的,膠囊裡被放入一種白色粉末,實際上是鯊魚軟骨粉,這種東西專賣店和網路都有販賣,主要是癌症的順勢療法之用,它易於消化又溫和,裝在膠囊裡,對泰瑞來說完全一樣,他不會察覺異狀。」
她從小皮包裡拿出一個摺好的信封,然後交給我。裡面裝了兩顆膠囊,兩顆都是白色但邊緣略有粉紅色痕跡。
「這些就是剩下的藥?」
「對,我留下這兩顆,然後把其他四顆交給診所的朋友。」
我用信封墊著,用手指把膠囊拉開,兩個膠囊外殼毫髮無傷地輕易拉開,裡面的白色粉末落在信封上。我當時就明白,要把膠囊裡的藥物倒掉,再換上無用的粉末並不困難。
「葛瑞西拉,妳的意思是,泰瑞在最後一次為客人開船出海時,吃了以為能救他性命的藥,但其實是毫無效果的東西,從某方面來說,吃了這藥反而害他喪命。」
「一點也沒錯。」
「那些藥是哪來的?」
「那些藥瓶是從醫院的藥局拿的,不過它可能在任何地方被調包。」
她停下來,讓我有時間消化。
「韓森醫生打算怎麼做?」我問。
「他說別無選擇,如果是在醫院被人動手腳,那他有權知道,因為其他病人可能也有危險。」
「這不太可能,妳說過有兩種不同的藥被調包,這表示不可能發生在醫院,一定是發生在藥交給泰瑞之後。」
「我知道,他也這樣說。他說他不得不向有關單位報告,但我不知道是向誰報告,也不知道他們會如何處置。醫院在洛杉磯,但泰瑞死在聖地牙哥外海二十五哩的船上,我不知道是哪個單位……」
「應該會先交由海岸巡防隊處理,然後最終轉到聯邦調查局手上,但那要花上好幾天,妳若直接打給調查局就能馬上處理,我不明白妳為何不找他們而來找我?」
「我不能找他們,還不到時候。」
「為什麼不能?當然可以,妳不該來找我,帶這些證據去調查局,告訴他以前合作的夥伴,他們會立刻調查,葛瑞西拉,我知道他們一定會的。」
她站起來,走向拉門,望著道路。這幾天霧霾很濃,感覺像天空就快著火似的。
「你是警探,你想想看。有人殺了泰瑞,這不是隨意作的手腳──不可能兩個不同瓶子裡兩種不同的藥同時被換,這是刻意的。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誰能接觸到藥?誰有動機?他們一定先想到我,然後就不會再追下去。我有兩個孩子,我不能冒這個險。」
她轉過身看著我。
「不是我幹的。」
「什麼動機?」
「一個是錢,他在調查局的時候有保險。」
「一個?所以還有另外的動機?」
她望著地面。
「我愛我丈夫,但我們的婚姻出現問題,最後這幾星期他都睡在船上,這或許也是他接下那一連好幾天包船生意的原因,通常他只做一天來回的生意。」
「出了什麼問題呢,葛瑞西拉?如果我要著手調查,我就得知道。」
她聳聳肩,彷彿也不知道答案,但後來又回答:
「我們住在島上,但我後來已經不喜歡住島上了,我希望我們搬回大陸也不是什麼祕密。但問題是,他在調查局的工作讓他很擔心孩子的安危,他很害怕外面的世界,他想讓孩子與世隔絕,但我不想,我希望他們能見識這個世界,並做好準備。」
「就這樣?」
「還有別的問題。我不喜歡他繼續辦案。」
我起身跟她一起站在門邊。我把拉門拉開,讓屋內通風一點,我發現應該一進門就立刻打開才對,外出兩星期不在,屋裡已經有酸腐味了。
「辦什麼案子?」
「他跟你一樣,老是執著沒破的案子。他在船底有一箱箱檔案。」
很久以前我也到過他的船上,船頭有間臥艙,麥克凱勒柏把它改裝成辦公室,我記得在上鋪看到好幾箱檔案。
「他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讓我知道,但後來越來越明顯,最後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最近幾個月,只要他沒出船,就經常往大陸跑,我們為此吵過架,他只說有些事他不能就這樣放掉。」
「是一個案子還是不只一個?」
「我不知道,他從來沒說他到底在查哪個案子,我也從來沒過問,我不在乎,我只希望他罷手,希望他多花時間陪陪孩子,而不是把時間花在那些人身上。」
「那些人?」
「那些讓他一直執著的人,殺人犯和受害者、他們的家人等等,他無法忘懷,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對他來說,那些人比我們更重要。」
她說這些話時望著道路。門打開了,路上的喧囂也進來了。下方高速公路的噪音就像遠處競技場之類的地方傳來的群眾喝采聲,而這競技場上的比賽永不結束。我把門整個打開,然後走到外面的露台,我向下望著矮樹叢,回想起一年前發生在此的那場生死纏鬥。我撿回一命,然後發現,就跟麥克凱勒柏一樣,我是個父親。從那時候起的幾個月,我學會在我女兒眼中尋找某種事物,那是泰瑞告訴我,他已在女兒眼神中發現的事物;就是因為他告訴我,我才知道要去尋覓,這點我得感謝他。
葛瑞西拉跟在我後面出來。
「你願意幫我這個忙嗎?我相信我丈夫對你的看法,我相信你能幫我,也能幫他。」
或許是幫我自己吧,我心裡這樣想,但沒說出口,我只是望著高速公路,看到路上車輛的擋風玻璃反光,感覺就像上千隻盯著我的閃亮銀色眼睛。
「好,」我說:「我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