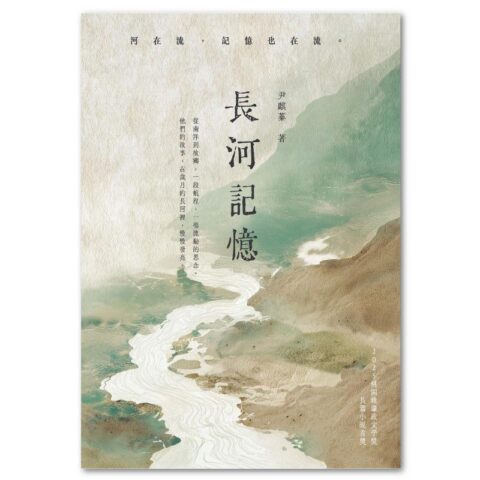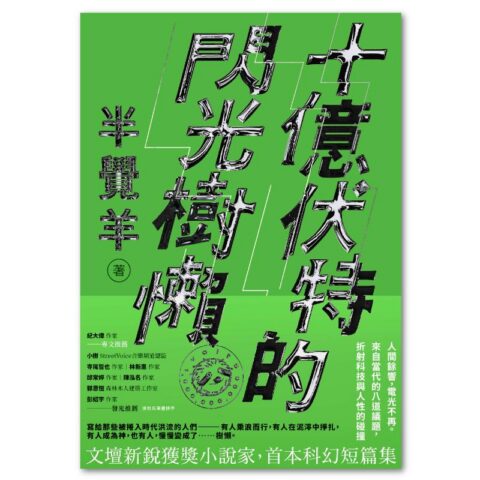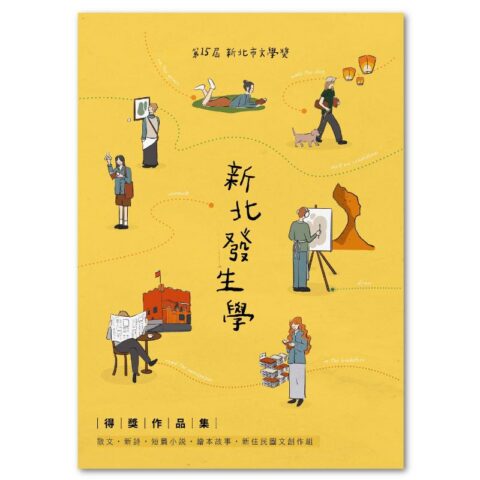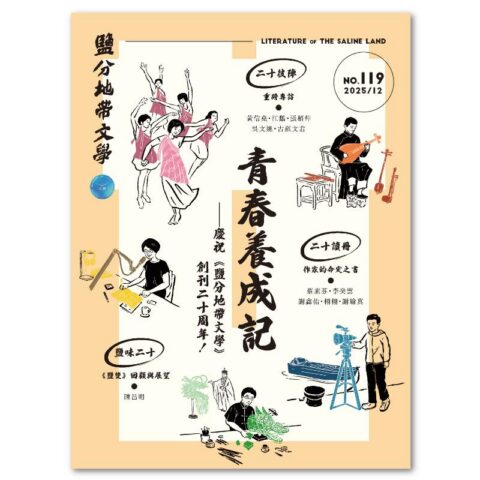恍惚,靜止卻又浮現──威士忌飲者的緩慢一瞬
原書名:Emerging in Trance and Stillness- The Slow Motion Moment of the Whisky Experience
出版日期:2017-09-27
作者:高翊峰
印刷:全彩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08
開數:18開,高20×寬17cm
EAN:9789570850000
系列:當代名家
尚有庫存
你不必善飲威士忌,卻何妨試著調和普通時光,
安靜、堅強、緩慢度日,默默蒸餾人生的橫征暴斂。
然後,懂得他人不懂的哀愁。
小說名家高翊峰琥珀色調的深夜書寫,一本讀兩頁就微醺的重度散文。
或許,你的人生只是少了一杯威士忌。
曾是老派酒保的小說家高翊峰,如同站在無數深夜站過的熟悉吧台後方,
傾聽世界的聲囂,並以他慣有的詩意筆觸回應:
所有記憶的提問、妻子的擁抱、時間的故事、語境的塑造、
旅行的意義、感官的哲學、愛情的真諦與孩子的疑惑。
那麼,在天使分享太多之前,讓我們喚他來一杯威士忌,
慢慢讀,慢慢於煙燻芬芳中恍惚,靜悄悄落一滴淚……
一瞬間,一瞬間想起了什麼。
作者:高翊峰
小說家、編劇、導演。
2012年由《聯合文學》雜誌評選為「20位四十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
文學作品曾獲: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等等。
戲劇作品曾獲:金鐘獎電視電影編劇獎。
十八年時尚雜誌工作,曾擔任《COSMOPOLITAN》台灣版雜誌副總編輯,《MAXIM》中國版雜誌編輯總監,《GQ》台灣版雜誌副總編輯,《FHM》男人幫雜誌總編輯。
個人出版品:《家,這個牢籠》、《肉身蛾》、《傷疤引子》、《奔馳在美麗的光裡》、《一公克的憂傷》、《烏鴉燒》等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出版:《幻艙》、《泡沫戰爭》。小說作品已翻譯成英文、法文。最新出版:《恍惚,靜止卻又浮現——威士忌飲者的緩慢一瞬》(聯經出版)。
記事:
2002年,偶像劇《雪地裡的星星》原著編劇、原著電視劇小說。
2004年,短篇故事〈失格後錯位〉與金曲獎作曲家彭靖合作改編為協奏曲,由台灣絃樂團巡迴德國Castle Wachenheim 、瑞士蘇黎士藝術博物館,以及法國巴黎文化中心進行演奏。
2006年,改編原著小說的同名影像編劇作品《肉身蛾》,獲金鐘獎,電視電影編劇獎。
2006年,短篇小說〈好轉屋家哩!〉改編電視電影《兩個銀角兒》。
2011年,長篇小說《幻艙》,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推薦、評論家南方朔專文推薦;被譽為華文版《白噪音》,同時入圍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決選。
2012年,出版《烏鴉燒》,文學評論家陳芳明教授讚譽:「高翊峰小說出現時,一個新的文學時代於焉展開。」
2014年,長篇小說《泡沫戰爭》,同時入圍2014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決選、入圍2015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決選。
2016年,獲邀擔任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駐館作家。
2017年,擔任客家電視台《暗香風華》訪談節目主持人。
2017年,《煙起的地方》電視電影導演、編劇。
如果天使分享語言
如果艾雷,值得敘事
初戀風土初心
凝視,威士忌哲學家!
散落天堂的憂傷島嶼
琥珀光譜與愛
柯羅諾斯的提問:等於記憶?
面對這樣的威士忌語境,不知為何,我總有一種介於遲疑與猶豫之間的念頭,無法說明清楚,就像過去那些急躁混亂的日子。
在開始寫威士忌語境之前,我懷疑過,是因為村上春樹寫下了《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所以再試著寫威士忌,都會是辛苦的?就像因為村上春樹聽見了《爵士群像》,之於使用文字思考日常的隱者,面對爵士樂最理想姿態,可能就只剩下雨天的陽台、黑啤酒和手捲菸⋯⋯當然,如此描述,對村上春樹的作品,是不公允也不適切的。但確實有過一段迷途時光,我的心底釀著這份辛辣,就像單一麥芽威士忌裡的那種木辣。
我記錄了:飲者,應該是日常的癮者。
我也寫下:寫者,也該是日常的隱者。
我翻開二○○四年在島嶼出版的《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在某一處空白的書頁上,還住著二○○四年十月十八號的自己。當時的我,還困擾於,如何完成一片葉子落地之前的詩意。於是在讀完村上的這本小書,寫下了令自己感到稚拙的文字:
有很久一段時間沒有讀村上春樹的作品了。這次閱讀,又再度勾起對村上式生活的眷戀。威士忌、音樂、旅行,之於一個人,一直都重要得無法被取代吧。回想起來,自從認真接觸小說創作之後,日常似乎被「過度矯正」到另一個美好的虛構世界了。就像一個曾經尚未長大的孩子,從一場寂寞的遊戲裡,躲入發燒的水溝,再游移到住滿羅漢石像的境域池裡。
—-
我一直知道,一切事物必然都會被時間損壞,但只要那瓶波特酒沒有被誰開瓶,我就還能記憶著一位朋友。偶而在心底對他發發脾氣,讓他就那樣靜靜地、靜靜地,在固定的低溫下,躺成液態的活者。在某些時刻,比如經過某個現代化的酒窖,或者喝著某瓶在波特酒桶裡,過桶熟成多年的威士忌,我才又會哀矜地想起——對了,還有那樣的一瓶酒,平躺著等待著我。
─節錄自〈如果天使分享語言〉
—-
我還沒有找到靠近的解答,解讀可能生出胡椒與其他偽裝成Spices氣味的考據。那麼影響更為顯著的橡木桶內熟成期間,這類胡椒辛香風味的討論點又該落在哪裡?這些推想,還有許多值得靠近的。
這確實是我個人一廂情願的靠近。重讀語境,另一層次的校對目的是,試著探究造成威士忌風味可變因素的內在。這與我偏執愛上的小說,都存有神諭。兩者在釀造的過程中,有技藝,有美學限制,也都透過異質發酵、多次蒸餾、收集回流,萃取出酒體與小說——這兩種從模糊框架中誕生的實體。放寬看,在一瓶單一麥芽威士忌與一篇短篇小說之間,都在看似極小卻有無限詮釋可能的空間裡,面對著無名的認識焦慮。
在重讀與校對威士忌及其語境的同時,觸感,也在液態中發生。在思流的岸邊,以文字記錄描繪——這與沉睡於橡木桶中的威士忌一樣,是看似靜止的一種釀製,以逼近那恍惚卻又浮現的意象。
關於泰斯卡的辛香性格討論,多半在蒸餾出新酒之前的製程上,較少聚焦在熟成期間的橡木桶。我在岸上躊躇,持續想像關於「嗅幻覺」這個介於科學又不科學的奇妙辭彙。每每往這個詞彙去解讀威士忌風味,討論有如洄游鮭魚,在產卵之後,死於主觀的溪流淺灘。雖然如此,但這也是「Single Malt」如此饒富著趣味、如此引人的地方:一杯一次,捕捉抽象的單一。
這些淌流而出的威士忌語境,對日常飲者與普通讀者來說,都帶有距離感吧。我無法反駁。但溝通日常生活本身,一直都不是輕鬆的課題。威士忌語境也是一次非主流的局外人嘗試。對我來說,喝威士忌可以慵懶輕鬆,但嘗試溝通威士忌語境,探究威士忌書寫在文字上的敘事實驗,如同體驗爵士樂的即興搖擺(Swing),並不一定適合笑出聲音。
─節錄自〈散落天堂的憂傷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