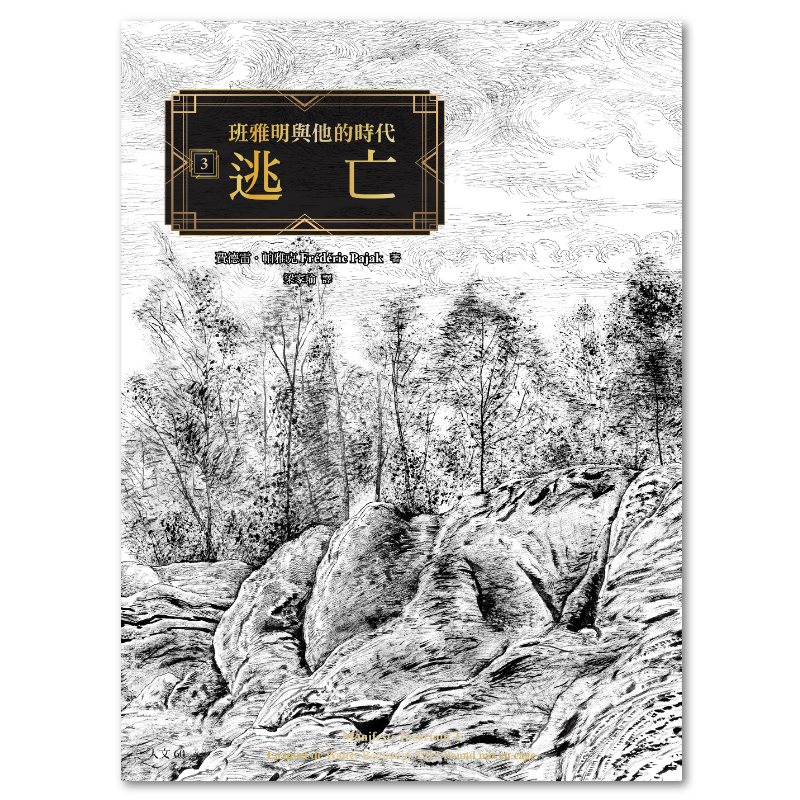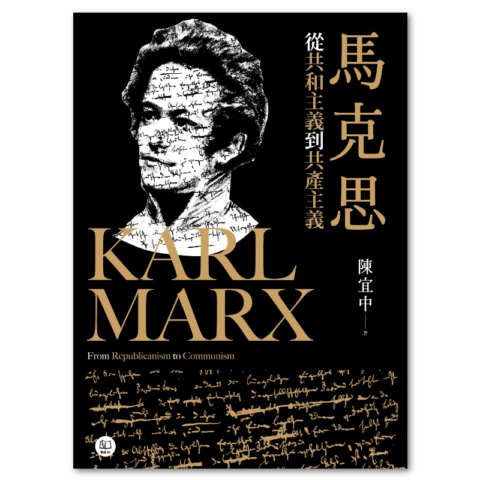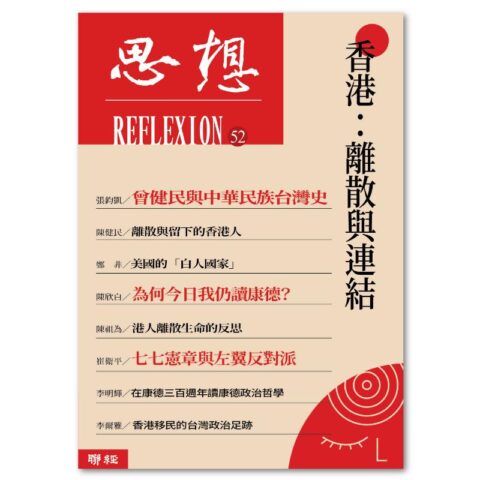班雅明與他的時代 3:逃亡
原書名:Manifeste Incertain volume3: La mort de Walter Benjamin. Ezra Pound mis en cage
出版日期:2019-04-02
作者:費德雷‧帕雅克
導讀者:蔡士瑋
繪者:費德雷‧帕雅克
譯者:梁家瑜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32
開數:長23×寬17.6cm×高1.7cm
EAN:9789570852608
系列:聯經文庫
已售完
2014年梅迪西散文獎、2015瑞士文學獎得主,透過精緻、深刻、動人的圖像與文字,記錄下班雅明的生平、安德烈‧布勒東、伊茲拉‧龐德、薩繆爾‧貝克特等人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
蔡士瑋(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這本書不只是關於班雅明,而是關於時代、關於存在,關於生命的憂鬱以及政治,甚至關於回返。
《科克斯評論》:呈現出敘事之本質與力量的複雜肖像。
德國思想家、哲學家華特‧班雅明,曾被譽為歐洲真正的知識分子、二十世紀最後的精神貴族與最偉大的文學心靈。
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班雅明離開德國柏林,四處流浪,足跡遍及了西班牙伊維薩島、丹麥、義大利、法國。1940年,德軍攻陷巴黎,在納粹追捕下,他逃亡至法、西邊界,最終服毒自殺。
法國知名圖像散文作家帕雅克,以風格獨具的繪畫和詩意的文字,在三冊《班雅明與他的時代:流浪‧孤寂‧逃亡》中描述了班雅明八年間的流浪、逃亡生涯。
其中並穿插描述了幾位同時代活躍於巴黎的重要文人、思想家,如:法國作家及詩人、超現實主義的創始人安德烈‧布勒東;美國著名詩人、文學家,意象主義詩歌代表人物伊茲拉‧龐德;僑居法國的愛爾蘭劇作家,薩繆爾‧貝克特等人。
第三部 逃亡
班雅明在巴黎居住了幾年,直到1939,如同所有的德國公民一樣,他被安置到位於尼維爾的志願勞工營,而所有的行李,就是裝滿一皮箱的書和手稿。兩個多月後,在眾多朋友的奔走幫忙下終獲釋放,返回巴黎,直到納粹軍隊到來。班雅明開始逃亡,先到法國南部,再到馬賽,其間還試圖坐船前住美國,但沒能成功。1940年,來到法西邊界的波爾特沃,病弱的班雅明終究不敵被蓋世太保追捕的恐懼,決定吞藥自殺。
在此同時,另一位深受時局影響的美國詩人,伊茲拉‧龐德,因其狂熱的政治理念,而因判國罪被捕入獄。班雅明和龐德,兩個時空交錯卻不曾相遇的人,彼此在各個方面都截然相反,卻同樣都成為這動盪的時代下的犧牲者。
作者:費德雷‧帕雅克
1955年生,瑞士、法國作家、畫家、出版商,擔任多本藝文諷刺雜誌總編。1987年出版第一本小說《懺悔的囚犯》,1999年~2004年陸續出版了《廣袤的孤寂》、《愛情悲歌》、《幽默與哀愁》,也出版一些詩集以及哲學相關的圖畫散文集,如《尼采與父親》以及作者的二十一幅素描。2012年至2018年陸續出版《不確定宣言系列》(Manifeste Incertain)七部(一至三部為中文版《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3》)。其中第三部《班雅明與他的時代 3:逃亡》獲得2014年梅迪西散文獎與2015瑞士文學獎。
導讀者:蔡士瑋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及多所高中哲學教師,研究領域為政治與文化哲學中身分認同及語言問題。博士後研究則是關於德希達猶太身分認同和彌賽亞政治神學問題。回國之後同時兼任屏東南州「水林藝術空間」策畫及策展人,並著手台灣美術史和藝術美學的相關研究。
繪者:費德雷‧帕雅克
1955年生,瑞士、法國作家、畫家、出版商,擔任多本藝文諷刺雜誌總編。1987年出版第一本小說《懺悔的囚犯》,1999年~2004年陸續出版了《廣袤的孤寂》、《愛情悲歌》、《幽默與哀愁》,也出版一些詩集以及哲學相關的圖畫散文集,如《尼采與父親》以及作者的二十一幅素描。2012年至2018年陸續出版《不確定宣言系列》(Manifeste Incertain)七部(一至三部為中文版《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3》)。其中第三部《班雅明與他的時代 3:逃亡》獲得2014年梅迪西散文獎與2015瑞士文學獎。
譯者:梁家瑜
英國艾賽克斯大學文學暨電影碩士,法國高等電影研究院助理導演文憑,譯者,專欄作家,熱愛音樂。
譯有:《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2:人能自主選擇而負擔道德責任嗎?──思考道德的哲學之路》、《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3:我能夠認識並主宰自己嗎?──建構自我的哲學之路》、《東村女巫》、《論特權》、《社會心理學》。
第三部
進一步報告
維爾努許
信任
夜晚忘記了白天
低語的禾草
最後的最後
為我畫一幅親愛的上帝
風也爭訟
均質而空洞的時間
逃離法國
低語的禾草
華特‧班雅明左右遲疑:是要離開法國還是待下來?在 1940年1月初,路過巴黎途中,他的前妻朵拉懇求他和她一起前往英國。他拒絕了。
儘管如此,他還是和美國大使館接觸,以取得緊急的特許簽證。他們給了他一張用途問卷,其中的第十四點,問到:「您是否是任何某個教派的牧師,或是某個學院、神學院、研究院或是大學的教授?」
1939年冬天與1940年春天之間,他寫了他的十八點《歷史哲學論綱》。其中他詳述了七月革命的第一天夜裡發生的情節,在巴黎的不同地點,在同一時刻並且互無交流的情況下,起義者朝時鐘開槍,「好讓這天停止」。
在將這分論綱寄給格瑞特時,他坦承:「戰爭及其所帶來的燦爛群星,讓我寫下這些我可以說已經被我封閉了,沒錯,封閉在我裡面二十年的思緒。〔⋯⋯〕我將它們委託給你,像是一束低語的禾草,在沉思的散步途中採集而來,一如一列論綱。」
他知道這些論綱提出了某種高度實驗性的特性。它們讓他假設,記憶與遺忘的問題將繼續吸引他好一段時間。但沒有什麼想法比將之付梓更令他感到奇怪了,因為「它們將為曖昧的興奮者打開大門」。接著,他用下述話語結束他的信:
「我們應警醒,要將最好的我們放在我們的書信中,因為沒有什麼跡象指出我們重逢的時刻已然靠近。
你年老且繼續年老的
德特列夫」
班雅明是進步的警醒的反對者。他看進步,正如同人們看著啟示錄的騎士(cavaliers de l’Apocalypse)的衝鋒,任意地進發到古老世界的領土上蹂躪其風俗、景緻、靈魂、一切。樹立起鐵的大教堂和裹著玻璃的水泥。吃汽油的汽車嘶吼著。現代性的喧囂表現令他擔憂,折磨著他。他變得憂鬱,知道事情不會倒退回頭,技術專家的囂張、科學與政治的近親結合、毀滅著並將毀滅一切,直到過往生命的最小的角落。
因為被判為不適合兵役,他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中作戰過。如果他不能很好地衡量人類災難的強度,或是只能從遠處衡量,他卻是景觀與毀壞城市之重建的見證人──因此也就是其現代化的見證人。戰爭是進步的獨裁統治的藉口。隨著自來水與電力而來的,是和平與消費者的馴化。舒適呼籲著一個全新的政府。如果資產家是進步的先驅,那共產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就是它最熱情的清談家。在所有人的物質福址之外,他們還要求速度,新社會的代名詞。而速度不可避免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死敵。這表示所有現代政權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徹底的暴政:必須要快,永遠要更快。如果說納粹發明了閃電戰,那公民社會也將成功地加以模仿。全球商務採納的方法是:轉瞬即逝的訊息、即時的通訊。一切出現的都得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即時性彷若宗教。
伴隨著工業革命,人們對緩慢──以及,此外,還有閒逛──宣戰。班雅明指出,大約在1840年的時候,巴黎廊道裡的漫遊者,帶著烏龜散步,以動物的步伐行走。他還反諷地說,可惜進步並未放慢腳步。但漫遊者是社會的消極敵人:他閒逛著,凝視商家,卻不消費。
在一句話、一段演說的迂迴處,班雅明發現了即將到來的不幸。他和所有人一樣,沒掌握住群眾盲目的程度。面對事件的加速,他顯得逆來順受,表現得越來越像是個宿命論者。他是否相信會有較好的出路,良心的覺醒?很難說。
無論如何,箝制日益緊縮。八個月來,同盟國,法國人、英國人與比利時人,都以馬奇諾防線為掩護,等著德國發動攻勢,後者則以齊格飛防線為掩護。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結束了這場「搞笑的戰事」,德國人所謂的「坐著打的戰爭」。德意志國防軍在閃電戰中入侵了荷蘭、比利時與法國。
在巴黎,警察大肆搜捕。每個人都得隨身帶著身分證,就連法國人也是。
安德烈‧布考夫斯基在筆記中寫道:「在勞動部的入口前,沃日拉爾路(rue de Vaugirard)上,在草坪上,兩名警察幹員來回走動,彎腰,起身,走幾步又彎腰。」
「是的,先生,我們在三葉草中找四葉草。您要一根嗎?」
「說著,其中一位笑著遞給我一個極佳的樣本,我接了過來並放到我的筆記本裡。我也笑了。路易十六,在巴士底被攻陷那天,在日記中寫的是:『什麼都沒有。』」
……
儘管他的居住與生活條件都很悲慘,儘管空襲警報讓他緊張,班雅明還是待在巴黎直到德意志國防軍來臨,在6月14日。他在最後一刻逃離,15日,在前往盧爾德(Lourdes)的最後幾班火車之一上,帶著的行李有兩只大皮箱、一副防毒面具、盥洗用品、手稿以及他作品的影本、以及一幅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名為《新天使》(Angelus Novus ),他從框裡拆下來的──這幅畫將抵達美國,而提奧多‧阿多諾將在戰後帶回法蘭克福,以歸還給遺產接受者舒勒姆,這是根據班雅明在 1932 年試圖自殺時立的遺囑。
班雅明在他的《歷史哲學論綱》這篇文章中描述了這幅畫,然而,詭異的是,人們可能以為他說的是另一幅畫:「它表現的是一名天使,似乎正要遠離某個祂凝神注視的東西。祂雙眼圓睜,張開了嘴,展開雙翼。歷史的天使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祂的臉面向過去。」
然而,這名天使卻凝然不動。祂的翅膀太過瘦弱,無法讓祂飛翔。祂的臉並未轉向過去,而是面向當下。祂看向一旁,神色憂慮,近乎害怕。
張開的嘴表達著害怕。祂說出了麼字嗎?或至少是一聲哭喊?如果得為這幅影像加上什麼解釋,我會說,與班雅明相反,這畫的是當下的天使,孱弱而困惑。
祂並未將背轉向未來,而是轉向過去,像畫的裝飾一樣空洞的過去。
天使是孤獨而迷途的,固定在被稱為當下的懸置的時間裡,無法凝視天空或是大地:天空與大地都不存在。
6月17日──貝當被任命為最高戰爭委員會主席。他簽了休戰協議。停火協議的第十九條表示:「法國政府保證釋放所有德國政府指名的在法德國人,以及法國所屬之領地、殖民地、領土與地區。法國政府保證避免德國戰俘與德國平民囚犯轉移到法國領地與其他國家。」
里歐陀預言:「在讀老報紙的時候,人們對我們說戰爭將會十分艱困。戰爭並不艱困。和平才會是艱困的。」
布考夫斯基指出:「〔法國人〕能夠花好幾個小時討論日常瑣事,這對他們而言是唯一真正重要的問題。今天,您愛他們;明天您會厭惡他們;後天,他們會再次以他們的浮誇和隨和來誘惑您,他們正是以此處理您視為問題的事情。他們有將靈魂物質化的天分,而或許正是這天份構成了他們的靈魂。」
「他們讓我不得安寧,他們令我無法思考,他們讓我無法擺脫壓在我嘴唇上的陳腔濫調。我想鄙視他們,但我不行。我難道不該有這權利嗎?法國是個宗教嗎?」
接著:「人們已經剝奪了法國人他們最依戀的東西:國會裡的混亂。這並不嚴重,他們只是更加依戀⋯⋯但現在他們被剝奪了另一樣東西,他們存在的本質目的:食物。配給卡開始實施,新鮮麵包的販售被禁止了。」
班雅明將他的手稿和信件都留在他巴黎的公寓裡──這些都將落到蓋世太保手裡,後來將被保存在東柏林科學研究院的檔案中。至於進行中的那本關於拱廊街的書,他則委託給了喬治‧巴塔耶。這些手稿將被保存在國家圖書館中。
儘管他不懈的要求,美國領事館還是拒絕給予他入境簽證。研究所方面則試圖邀請班雅明作為演講者到哈瓦那大學。他也試著要通過聖多明尼各到美國去。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