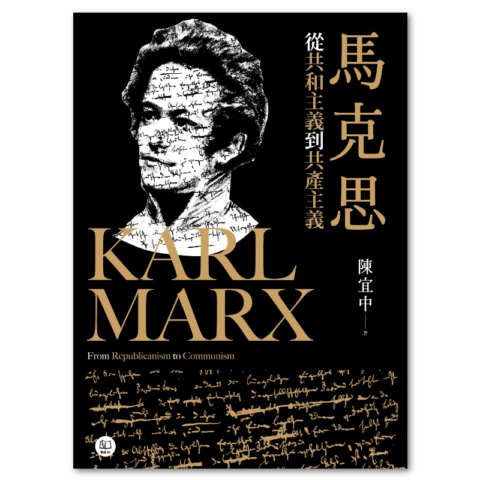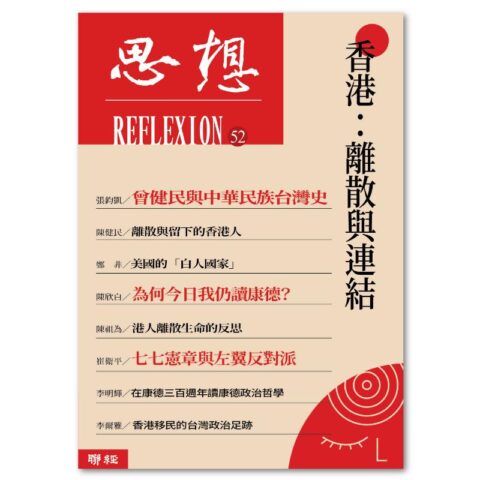久等了,韋伯先生!〈儒教(與道教)〉的前世、今生與轉世
出版日期:2019-03-22
作者:孫中興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68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2.15c
EAN:9789570852790
系列:當代名家
尚有庫存
孫中興教授首度完整詮釋自己的「韋伯大夢」
久等了,韋伯先生!
韋伯的〈儒教(與道教)〉究竟歷經了什麼樣的前世、今生與轉世?沉浸於韋伯理論四十年的孫中興回歸文本自身,從韋伯的幾個「脈絡」和「四本」的角度出發,引領讀者深入認識韋伯學說。「脈絡」包括大我脈絡、小我脈絡、思想脈絡和出版脈絡;「四本」則是指韋伯〈儒教(與道教)〉的版本、文本、譯本、所本。
在《久等了,韋伯先生!〈儒教(與道教)〉的前世、今生與轉世》第一章,孫中興將先借用現代人申請工作的「履歷表」概念來重新整理韋伯的生平、著作等相關資料,讓讀者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看出一個更為立體的韋伯。接著從韋伯的主要著作、思想脈絡、出版脈絡以及相關版本與譯本等進入討論,呈現完整的韋伯理論。最後針對〈儒教(與道教)〉的文本進行深度解析,一舉進入韋伯思想的核心。
作者:孫中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75年拜於儒學大師愛新覺羅毓鋆門下,成為「天德黌舍」門生,從《論語.學而》開啟與孔子的緣分。近年來日日於網路發表一篇「論語日記」,至今已累積503篇。著有《論語365:越古而來的薰風,徐迎人生四季好修養》、《穿越時空,與孔子對話》、《學著,好好分》、《學著,好好愛》、《令我討厭的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理論旅人之涂爾幹自殺論之霧裡學》、《馬克思「異化勞動」的異話》、《馬/恩歷史唯物論的歷史與誤論》、《愛.秩序.進步:社會學之父:孔德》。主要開設課程為社會學理論、知識社會學、幽默社會學、聖哲社會學及愛情社會學。
代序:我三、四十年來一場未止息的「韋伯大夢」
第一章 韋伯的時代和生平
第二章 韋伯的主要著作
第三章 思想脈絡和出版脈絡以及相關版本和譯本
第四章 文本和所本(一):〈(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之)導論〉
第五章 文本和所本(二):〈(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之)儒教(與道教)〉
第六章 文本和所本(三):算是文本還是闌尾的間論
第七章 整理與重建
第八章 文獻回顧
附錄一 韋伯的時代、生平與著作年表
附錄二 韋伯的著作目錄及其中英文譯本
附錄三 韋伯〈儒教〉(1915)與〈儒教與道教〉(1920)目錄對照表
附錄四 韋伯《儒教與道教》(1920)英、中譯本目錄比較
附錄五 《經濟與社會》中〈宗教社會學〉原版和譯本章節區分的比較及其與《中間考察》相關章節的對照
附錄六 韋伯《儒教與道教》徵引書目現有的中譯本(2017年8月)
參考書目
代序:我三、四十年來一場未止息的「韋伯大夢」
從1993年出版《愛.秩序.進步:社會學之父:孔德》以來,我陸續寫了各兩本有關涂爾幹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小書,終於按當初的想法,要寫到我的「理論初戀」—韋伯〔或者,套個學生間流行的說法,畢竟我還是有著難以控制的「韋伯控」(Weber complex)〕。
我在大四(1979年秋季開始)葉啟政老師的社會學理論課上「初識」韋伯的理論,當下「一見鍾情」。那時候喜歡的是他的純理論,或者其實只是他清楚的(適合考試背誦的)幾種分類:社會行動、理性、支配或宰制。那時候能入門的途徑就是老師指定的阿隆(Raymond Aron)的《社會學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1968)以及柯塞(Lewis A. Coser)的《社會學思想的大師》(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1977年第二版)兩本書中的相關章節。當時只有柯塞的書有原文翻印本,阿隆的書是我好不容易才託友人從美國買回來兩冊平裝本。當時的英文程度閱讀起來十分吃力,理解上更是困難。雖然如此,還是立志遠大地買了虹橋書店翻印的葛斯(Hans H. Gerth)和米爾斯(C. Wright Mills)編譯的《韋伯文選》(From Max Weber),但是沒讀多少就知難而退;儘管如此,還是憧憬著有朝一日能買到《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的英譯本來好好攻讀一番。「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就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不過,這真是我的「韋伯理論霧裡學」的時期。
1981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書,馬上就先到學校書店買了一套用盒子裝好的平裝本《經濟與社會》回家「供奉」在書架上。當時為了上課繁重的閱讀材料而忙得焦頭爛額,想讀的書連打開盒子的時間都沒有。
那時候我覺得哥大社會學的理論課不合我意,剛好因緣際會認識了幾位在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念社會學的友人(其中一位就是相交至今的群學出版社總編劉鈐佑兄),和他們聊天的結果,發現他們的理論課很有意思,就儘量去他們學校聽課。哥大的課都在白天,新學院的課則多在晚上,所以我常常兩邊跑(後來課業日益繁重就只好作罷)。當時海德堡大學的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教授剛好在他們學校客座,我去聽過他講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一堂課,很欣賞他從出版脈絡來研究社會學理論。我到美國之前也拿到海德堡大學社會學系的入學許可,但是權衡輕重的結果,還是選擇了美國。剛到美國念書挫折多,甚至覺得到美國念社會學是個錯誤的決定,所以就和施路赫特教授約時間討論轉往海德堡念社會學的可能性。他非常詳盡地問了我在美國的狀況,並且詢問了我到德國求學的動機,最後強調:除非是為了研究韋伯,否則就大局著想,我在美國學到的社會學內容會比較廣比較豐富。我想我雖然「愛」韋伯,但是絕對沒有要「專愛」韋伯,而且英文念了大半輩子到美國念書都累得像條狗,我的德文程度更不如我的英文,就這樣去了德國,恐怕更看不到完成博士學位的一天。後來就安安分分地待在美國,可是我的「韋伯夢」仍然蠢蠢欲動。
1982年暑假,我終於可以從繁重的課業壓力中喘息幾個月,當時想著是否可以「一兼二顧」,又讀書求知,又翻譯賺錢,就打聽到哥大一些學長和當時專門從事翻譯西方經典的「新橋譯叢」有點關係。於是毛遂自薦翻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學長們很客氣地以「翻譯者必須是博士學科考試通過的人才能勝任」為由回絕了我。
1985年在經過修課以及三門學科考試的「驚濤駭浪」都「逢凶化吉」之後,深深感到那幾年修課都在「應付寫報告」,沒能好好靜下心來扎扎實實念些書,所以又繼續做起我的「韋伯大夢」。
當時友人杜念中主編《知識份子》,要辦一期「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的專題。為此他已經邀約各學門在美專家撰稿,社會學部分尚缺人選,於是就向我邀稿。我花了半年多時間,像考學科考一般認真地閱讀了相關二手文獻,發現文獻中對於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了解差異甚大。於是回歸到一個最原初的問題──「韋伯到底是怎麼說的?」我從原典英譯本逐字逐句看去,找出韋伯的主要論旨,再對照德文原典,發現了幾個版本和譯本所造成的問題。然後我再以用同樣的方法去看英譯本《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最後寫成了一篇〈從新教倫理到儒家倫理〉的長文。我的這篇「年少得意之作」後來申請國科會獎勵,沒有任何評語就被拒,讓我再也不跟這樣「無理」的單位發生任何關係。
1987年我回臺大任教,社會學理論是由我和其他同仁輪流擔綱的課程。每次上課,我都自己製作講義,而每個社會學家的講義都由四個部分組成:生平與著作、思想脈絡、著作脈絡,以及主要概念。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研究社會學理論的四個重要方向。
1996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平日不甚相熟的友人來電,邀請參加一個名為「重讀中文」的研討會。平常我並不愛參加「言不盡意」的學術研討會,可是主辦人告訴我,這個研討會雖然也要求發表論文,但是每位報告者有一個鐘頭的時間發表,而且沒有大會安排的評論人。我對這樣的創意十分欣賞,就寫了一篇〈重讀(韋伯)中文〉的論文,將我教授理論的四個方向用來談論韋伯的文本和中譯本的現況與問題。這個立意良善的研討會在國家圖書館舉行,但參加者十分稀少,讓偌大的會議廳顯然十分冷清。事後,主辦單位希望將論文結集於未來新成立的刊物上發表,希望大家不要將文章轉投其他刊物。沒想到後來期刊一直沒有出版,我的這篇文章也就變成了履歷表上唯一的「未出版論文」。這篇論文曾經送給當時正在海外寫論文而訪問我的林錚,後來我遍尋不得原始檔案,還是透過他的保存才將這篇論文留存下來。
之後有一年暑假,我一直認為韋伯的〈新教教派和資本主義精神〉沒有中譯本是件憾事,就想著透過對照英譯本和德文原典來翻譯。忙了一個星期,一開始就發現文本和譯本幾乎是兩回事,自己語文能力也還不行,遂急流勇退。翻譯韋伯真不是「常人」能做的事,必也「超人」乎!這是我對嚴謹譯者的最高敬意。那些拿人家稿子再來加工製造的,上得了我的書架,卻還是得不到我的尊敬。
2008年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舉辦的「經典論壇(IV)」,主題是「諸神爭戰?Max Weber的〈中間考察〉」,我也應邀發表了一場「〈中間考察〉的中興考察」的初稿(其實只有大綱)。在準備那篇文章的半年中,我發現〈中間考察〉的文本位置很奇怪,而且內容有些和之前的《儒教與道教》以及之後的《印度教與佛教》好像都沒關係,反而和韋伯死後才拼湊而成的《經濟與社會》的〈宗教社會學〉部分多所雷同。更妙的是,兩處類似的討論往往都是《經濟與社會》的文本較為勝出。可是這需要更詳細的比對,當時我並沒有做這方面的努力。所以當時的結論只能提出懷疑:「〈中間考察〉其實是個錯置的文本」。也正是那次會議,林錚提醒我施路赫特教授的一篇文章早已經說明過這個文本的考證。參加學術會議能從同行中受益,這是難得又難忘的一次。
2012年,我的同事,同時也是韋伯專家的林端,找我和香港浸信會大學的傑克.巴巴萊(Jack Barbalet)教授夫妻見面,討論籌辦韋伯《儒教與道教》出版一百週年的學術研討會。我這個幾乎三、四十年不願意參加學術研討會的人,終於盼到一場可以發表我累積幾十年的努力成果,並向世界級專家請益的機會。而且這正是我本來就要進行的計畫,於是就更增加了寫這本書的動力。
有趣的是,幾十年來有關《儒教與道教》的相關文獻增加的並不多,如果不算上「挾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來演繹自己的儒家倫理或經濟發展」的文獻,海峽兩岸以及英語世界的文獻中專門討論這本書的專著還是只有1988年簡惠美的碩士論文《韋伯論中國:〈中國的宗教〉初探》。取得相關文獻的管道也比以前容易得多,所以我就一以貫之地從我最近幾年幾本小書的「路數」來重新探訪這個我關懷已久的主題。我先上網買到德文韋伯全集中精裝本的版本,也很幸運地託友人在日本買齊了現有的三個日譯本,以及歷年來不斷收集到的各版中譯本。因為資料不少,我就先以此為題寫了一篇〈百年來的美麗與哀愁:韋伯《儒教與道教》中譯本〉作為大會論文。
在開會的前幾天,林端邀請了他在海德堡的指導教授,堪稱「韋伯學泰斗」的施路赫特教授來本系作專題演講。我在會前趁機向他提起1981年紐約請益的往事,他雖然無所記憶,但是對於我是否悔不當初十分好奇。我回答「了無遺憾」,惹來他開懷大笑。在他演講之後,我也趁機整理了歷年來讀韋伯的一些問題,一口氣在會中提問七個問題。他都給了讓我很滿意的答案。其實,在準備這次會議論文之前,我才在圖書館找到他1989年出版的《理性主義、宗教和宰制:韋伯觀點》(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一書,也發現他早就提出了文本脈絡的重要性。開完會後不久,我就花了大錢在二手書網站上買下這本書。後來我想,也許多年來我都不自覺地接受著他當初在紐約那一門課上的研究路數。後來在會中又得益於他的論文與評論、甚至晚宴上的精闢見解。綜合歷年來,從他的求學忠告,到閱讀他的專書,到後來的開會見聞,都讓我心懷感恩,所以在本書尚未開始之際就已經告知他本人,希望能將我的研究成果致獻給他,以表達我深深的謝意。
當天演講會後,林端邀請我和施路赫特教授夫婦,以及他們賢伉儷與他的得力助手蔡博方一起在「鼎泰豐」午餐餐敘。席間,林端意氣風發地提及將到美國休假進修並要每日參訪一座宗教禮拜場所的計畫。這一切都還言猶在耳、歷歷在目,沒想到兩天後他在陪同施路赫特教授前往佛光大學演講的旅次中猝然長逝。讓聽聞者都錯愕不已。雖然後來會議如期舉行,但總是有著這麼一個令人難以釋懷的惋惜與遺憾。
如果按照韋伯的著作脈絡來看,我應該先寫計畫中有關「新教倫理」的那一本。可是,因為這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打亂了我原本計畫的寫作順序,既然我已經做了不少功課,就以這本《儒教與道教》為先,以後再回頭去討論韋伯的「新教研究二論」──〈基督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基督新教教派和資本主義精神〉。
我寫這本書倒也不是為了配合「韋伯出書百年紀念」這樣的儀式。我在前述那場國際學術會議上就說過「慶祝百年」其實是個有爭議的說法,因為不管百年的起算點到底是1915年的〈儒教〉,還是1920年的〈儒教與道教〉,現在都不是百年,除非算上審查和印刷等等外在因素。其次,也不是因為「身為中華文化的後人,不能不為祖先說點話來反駁洋人的謬論」(時髦的說法大概就是「西方中心主義」或是「西方文化殖民」之類的話);我認為政治意識型態或文化民族主義絕對不能當成研究的指導綱領,或是「未審先判」的「定見」。
一如往昔的幾本小書,我踏著自己不變的步伐,從作者的生平、著作、思想發展等脈絡的觀照之下,來檢視我所謂「四本」(版本、譯本、文本、所本)之間的關聯,以及對我們中文讀者的影響。仍然是「書小志大」,一如往昔。
最後恐怕還是要交代一下(其實我認為讀者,或是最後會讀的人,應該讀著讀著就會懂得,至於不讀的人,又與他何干?),書名中的「二世一生」其實很簡單:我以1920年版的〈儒教與道教〉為「今生」,追溯到他的1915年版的〈儒教〉為「前世」,並以英譯本和中譯本,以及後來根據韋伯論旨而自我發揮的文章當成它的「轉世」,這是影響我們大多數人閱讀的版本。細心的讀者可能會問:那「來世」呢?這本書的「來世」呢?我因為不相信「來世」,所以不是「存而不論」,而是根本就「不論」了。留待「信者」或「來者」去解答吧!
這本書的基本想法和做法都和前幾本小書類似,雖然自己才德各方面都遠不如孔老夫子,可是勉強也可以忝稱為「一以貫之」吧?大家見笑了!這本書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個暑假,雖然我力求前後一貫,但恐怕還是有疏漏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教。
準備好就開始囉!
第一章:韋伯的時代和生平
本書主要是研究韋伯的〈儒教(與道教)〉。
我運用最近幾年一貫的做法,從韋伯的幾個「脈絡」和「四本」的角度出發,其中的「脈絡」包括大我脈絡、小我脈絡、思想脈絡和出版脈絡;「四本」則是指韋伯〈儒教(與道教)〉的版本、文本、譯本和所本。
因為韋伯詳細的大我脈絡和小我脈絡都不是本書的重點,所以讀者可以參看附錄一,略窺一下這方面的全貌。我的重點就放在本書作者能力所及的幾個部分。
以下我就借用現代人申請工作的「履歷表」概念來重新整理韋伯的生平、著作等相關資料,讓讀者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看出一個比較立體的韋伯。
一、誕生、家世、家庭和重要關係人(significant others)
韋伯於1864年4月21日誕生於當時還是普魯士的小城艾爾福特(Erfurt)。他有一個很長的全名馬克西米利安.卡爾.艾米爾.韋伯(Maximilian Carl Emil Weber)現在大家都習慣稱呼他的名字為馬克斯(Max),其實這只是簡稱,這個名字的全名是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這跟他父親的名字一模一樣,可是後來他的父親沒有這個兒子有名,所以基本上大家講到馬克斯.韋伯時,指的是這個兒子。有時為了區分方便,在英文脈絡下提到父親的名字就在後面加個Sr.(Senior的簡稱),在兒子的名字後面則相應地加上Jr.(Junior的簡稱)。
父親老馬克斯.韋伯(1836-1897)祖上從事紡織業,後來從政,曾經擔任過普魯士國會和帝國議會中國家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代表。他熱衷於政治,喜於享樂,對於宗教和慈善事務興趣缺缺。青年韋伯原來是以父親為榜樣,希望走上父親走過的道路:在大學修習法律,並在畢業後準備律師考試,成為國家公務人員。可是後來他和父親疏遠,轉而同情母親的境遇,因此對父親有了矛盾的情感。再加上,他一直仰賴家裡提供經濟資源,讓他對雙親都心生糾結。壓死韋伯這個心結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1897年7月14日他和父親的一場大吵。不到一個月,父子還沒和解,父親就過世了。這個事件讓韋伯精神崩潰,甚至嚴重到讓他無法繼續原先的教職,只得四處遊歷休養。看來前途似錦、青年得志的韋伯,一下子從天堂落入了地獄。不過,這並不是一場萬劫不復的事件。從事後的發展來看,這場精神崩潰似乎只影響到他的教學,沒有影響到他的寫作,以及對學術和社會實踐的熱情。
母親海倫妮.韋伯(Helene Weber, 1844-1919),原來娘家姓法倫斯坦(Fallenstein),祖上出自顯赫的Souchays豪門。但是她的生活並不奢華,而且關心社會事務,特別是因為身為喀爾文教徒的關係而熱衷於慈善事業。16歲(1860年)時就和大他8歲的老馬克斯訂婚。後來20年的婚姻裡和老馬克斯一共生了八個小孩,其中一位夭折,所以有的書只寫生了七個。強勢的母親,對韋伯的一生有很深的影響。
韋伯長時間和父母親同住。29歲(1893年)之前都住在柏林的夏洛登堡(Charlottenburg, Berlin),後來搬到海德堡,住的也是外祖父留下的房子。
他在家中八個小孩裡排行老大。
繼他之後的安娜(Anna),出生不久就夭折。
接下來是大弟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 1868-1958),後來在「文化社會學」領域上也有卓越的貢獻。但是兩人一直處於緊張關係。
然後是二弟卡爾.韋伯(Karl Weber, 1870-1915)。
之後是和母親同名,可是卻也在童年夭折的次女海倫妮(Helene Weber, 1872-1876)。
三女克拉拉(Klara Weber, 1875-1953)是他最鍾愛的妹妹,於1896年嫁給著名羅馬史專家毛姆森(Theodor Mommsen)的兒子恩斯特(Ernst)。
然後是三弟亞瑟.韋伯(Arthur Weber, 1877-1952)。
最後出生的是小妹莉莉(Lili Weber, 1880-1920),後來嫁給謝弗勒(Schfere)。莉莉在1920年4月自殺身亡,韋伯夫婦因此收養了她的四個小孩。
後來成為韋伯夫人的瑪莉安娜(Marianne Schnitzger, 1870-1954)小他6歲。她的祖父卡爾.大衛.韋伯(Carl David Weber, 1824-1907),是韋伯的伯父(Radkau, 2009: 561)。所以,韋伯其實是妻子的父執輩,也就是說,他是和小他一輩的親戚結婚。瑪莉安娜對於韋伯的崇敬可說是數十年如一日。早期韋伯到海德堡教書,瑪莉安娜就去旁聽;韋伯死後,這種崇敬之情還在她所撰寫的《韋伯傳》(Max Weber: Ein Lebensbild)中流露無遺。
瑪莉安娜於1892年春季到韋伯家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兩人的關係才逐漸深化。第二年(1893年)的3月,在韋伯探訪初戀表妹艾美.包嘉登(Emmy Baumgarten, 1865-1946)的半年後,她和韋伯兩人訂婚。
韋伯和妻子膝下無子,在加上韋伯後來的兩次外遇,讓這段婚姻增添了不少八卦。後來因為妹妹的過世,才將妹妹的四個小孩過繼成為兩人的小孩。
小他一歲的表妹艾美是韋伯的初戀〔即母親的姊姊伊達.法倫斯坦(Ida Fallenstein)和姨丈赫爾曼.包嘉登(Hermann Baumgarten)的女兒〕。他於1883年因為在史特拉斯堡當兵,所以和姨母家關係深厚。除了和表哥奧托.包嘉登(Otto Baumgarten, 1858-1934)有許多知性方面的交流,與表妹艾美也過從甚密,特別是1886年之後,兩人魚雁往返更加頻繁。在韋伯的《青年書簡》(Jugendbriefe)中,艾美被暱稱為「Emmerling」和「darling」,兩人通信有八年之久(Kaelber, 2003b: 38)。卡爾柏從兩人的往返書信中發現,韋伯對艾美的感情轉向親情,從情人轉向兄妹。但關於這段感情,也有不太一樣的敘述。根據瑪莉安娜(瑪麗安妮.韋伯,2010:129;1926:99;1975:93)事後的描述,1887年韋伯的阿姨怕兩人感情過深,就將艾美送去瓦爾德基爾希(Waldkirch)和哥哥奧托同住。但韋伯知道後還是追去,兩人雖然相對無語,但覺感情更加篤堅,深陷情海而不可自拔。然而,這次一別,兩人直到五年後的1892年才再度見面,卻已人事全非。這時艾美正因法倫斯坦家族遺傳的精神耗弱而易地休養,韋伯只能到療養院去探訪初戀情人。她一直認為自己是韋伯的未婚妻,可是兩人從未訂過婚。在探視完艾美之後,韋伯自知無法照顧艾美一輩子,就斬斷情絲,而且很迅速地在半年後(1893年3月)與瑪莉安娜訂婚。韋伯在撰寫博士論文階段就是為這段情所困。瑪莉安娜對整件事情顯然了解透澈,所以在後來的韋伯傳記中也沒避諱(瑪麗安妮.韋伯,2010:129-130;Marianne Weber, 1926: 99-100; 1975: 93-94)
艾爾賽(Else von Richthofen, 1874-1973)比韋伯小10歲,是韋伯在海德堡教書時的第一位女學生,和當時在丈夫課堂上聽課的瑪莉安娜是好朋友。當時有機會進大學的女子很少,艾爾賽最初的志向也只是要當一位工廠檢查員(Fabrikinspektorin)。後來經過韋伯的推薦,她如願以償地成為該職位的第一位女性官員。她28歲(1902年)時和當時36歲的雅飛(Edgar Jaff, 1866-1921)結婚。
托伯勒(Mina Tobler, 1880-1967)是一位音樂家,也是韋伯晚年認識的「紅粉知己」,瑪莉安娜的《韋伯傳》中提及她曾陪伴韋伯夫婦參加拜魯特音樂節的事(瑪麗安妮.韋伯,2014: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