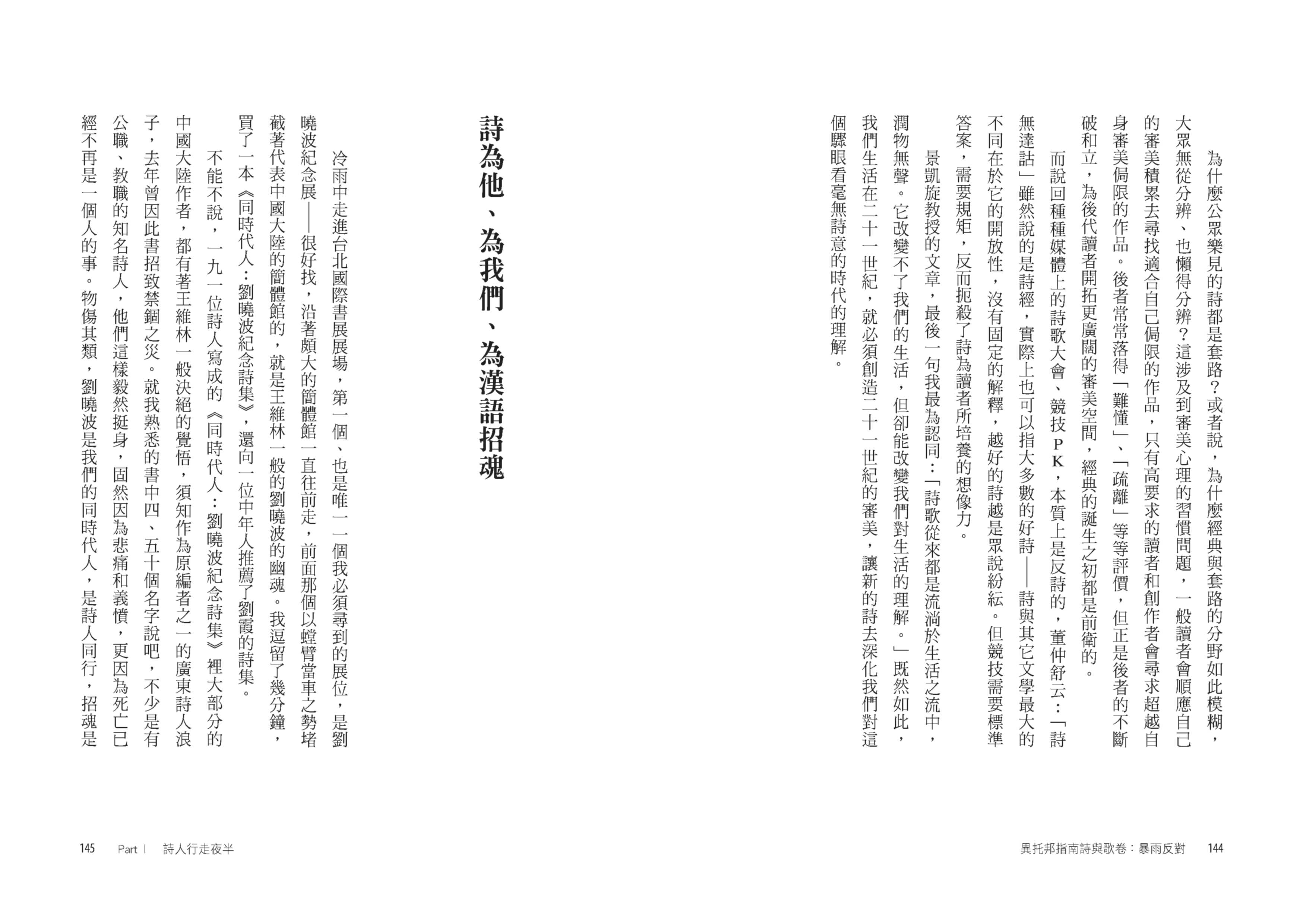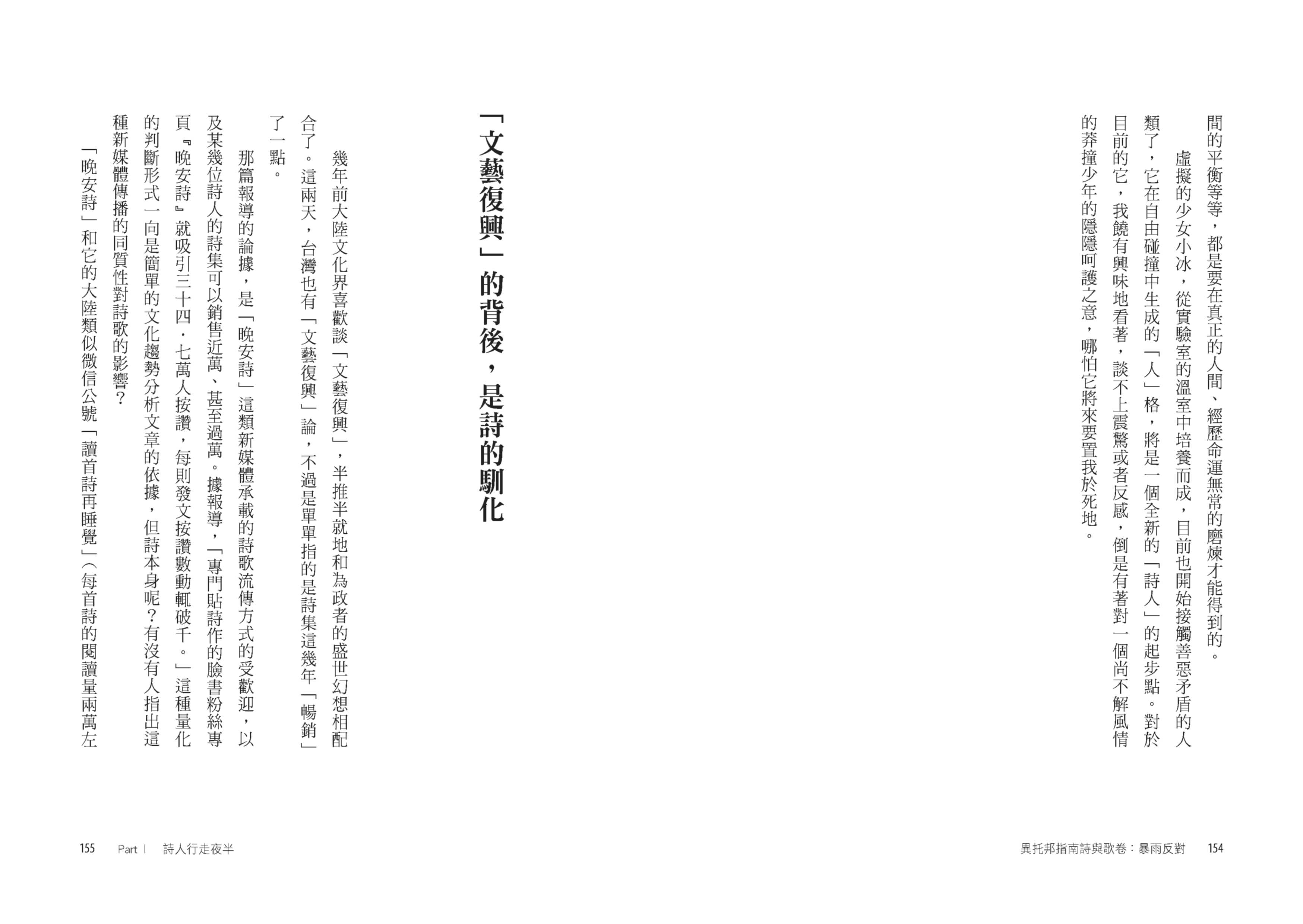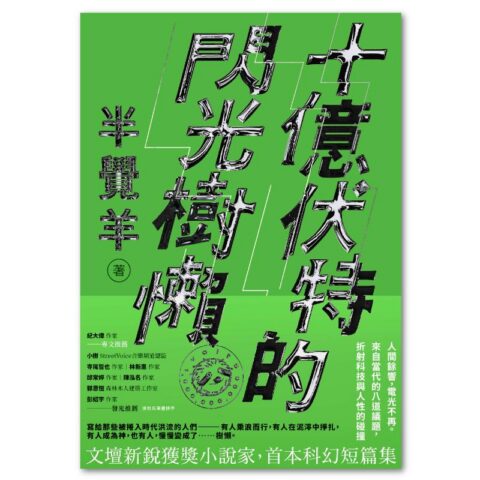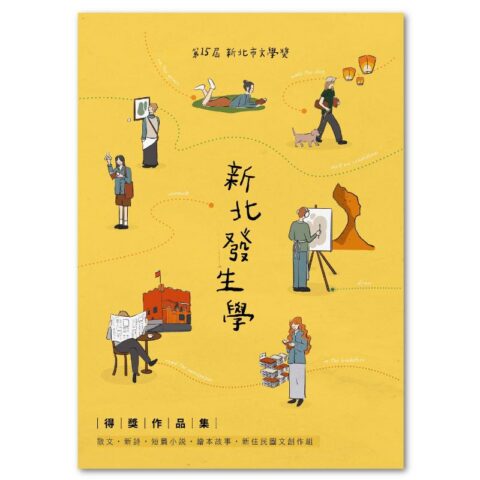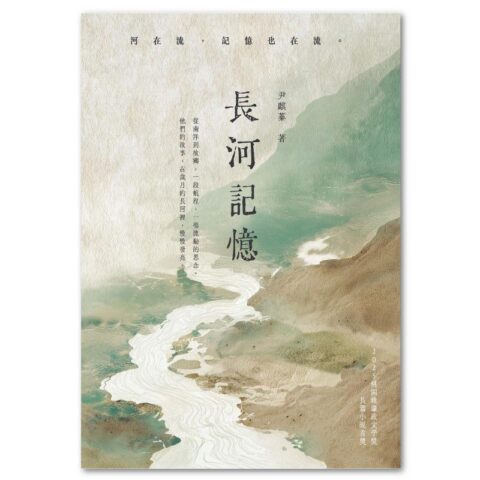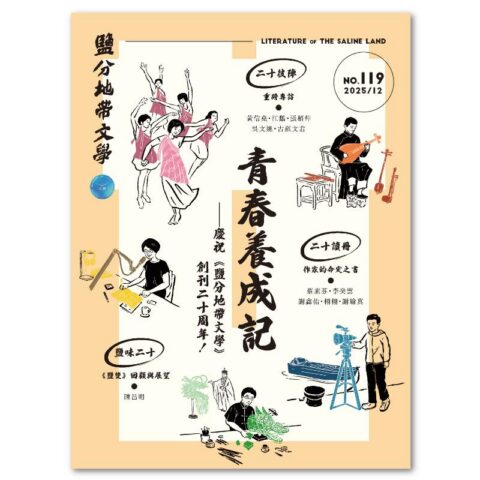異托邦指南 /詩與歌卷:暴雨反對
出版日期:2020-03-17
作者:廖偉棠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2.1cm
EAN:9789570854855
系列:當代名家‧廖偉棠作品集
尚有庫存
讓我們自己成為暴雨,攜帶著雷與電,去反對這個時代的沉默、
反對這個時代的喧譁、反對這個時代的乾涸。
如果世界充滿對假象的阿諛,反對就是詩人與音樂人的義務。
時代浪潮下誕生的詩與歌,是創作者不斷與思想鬥爭的作品。
每一個年代的憤怒與情感,在詩與歌中再次燃燒!
廖偉棠以詩人之性、樂迷之心、評論家之筆
在歷代的激昂文字中尋找詩與音樂的烙印
詩和歌都應該有一個更漂亮的姿勢承擔這個時代的重量。「更行、更遠、還生」,此時重讀,竟也有樂觀的想像,關於藝術和現實的互相牽引如風箏乘風之力。
──廖偉棠
《異托邦指南》系列繼卷一《閱讀卷:魅與祛魅》、 卷二《電影卷:影的告白》, 迎來卷三《詩與歌卷:暴雨反對》。
本書分為兩輯:
輯一「詩人行走夜半」,從歷史的徬徨過往,召喚古往今來險峻時代中,回應社會百態的詩人包括:挑戰佛教和詩的清規的一休宗純、英美著名詩人W‧H‧奧登、日本國民詩人宮澤賢治、俳句大師松尾芭蕉與種田山頭火、回望深淵的瘂弦、以詩叩問生命底蘊魔狂的洛夫、詩作澄明而悟道的周夢蝶、獨立堅毅的劉霞到古典的杜甫、李白、美國底層人民的桂冠詩人查理‧布考斯基、勇於寫不是詩的詩的鴻鴻、聆聽香港雷聲與蟬鳴的梁秉鈞、漢語詩人導演邱剛健等等。
輯二「過於孤獨的喧囂」,盤點東西方各曲風之歌者、跨界樂手甚至樂團:從傳奇音樂人巴布‧狄倫、跨界歌者烏蒂‧蘭普、靈光乍現的李歐納‧柯恩、日本民謠歌手森田童子、超民族音樂大忘杠樂隊、中國近代搖滾詩人崔健、怪誕巫王左小祖咒、飢餓藝術家萬能青年旅店、手風琴爽人樂團五條人、達明一派與「禁色」的黃耀明、滄海一聲笑的黃霑到香港永遠的黃家駒和Beyond……。
時代浪潮下誕生的詩與歌,蘊富駁雜的時代情感,是一代人對藝術崇拜、生命追求所留下的烙印,表面上看似後浪推前浪,但能真正留下的,是保有無窮生長力並不斷地反思,不斷地與思想鬥爭、掙扎的作品,並使蘊育下一代的土壤保持鬆動,讓養分反覆滋潤至下一個太平盛世。
作者:廖偉棠
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二○一二年年度藝術家(文學),現居臺灣。
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散文集《衣錦夜行》、《尋找倉央嘉措》、《有情枝》,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
自序:暴雨為何反對?
PartⅠ 詩人行走夜半
奧登、姜夔或前生
少林門下無知音
旅行青蛙山頭火
斧柄在手,寒山不遠——蓋瑞•施奈德的原點
宮澤賢治:阿修羅的覺醒
瘂弦:深淵,或一條河的意義
蝶的歸來去
在民國的餘光之中
洛夫的得失,我們的得失
劉霞:獨立的詩,獨立的女性
重聽香港的雷聲與蟬鳴
一九八四年的香港詩歌
羅貴祥詩中的家與國
東西南北人、生死愛欲雪——談邱剛健的詩
不是詩,是什麼?
詩不只是安慰,也可以挑釁
為什麼杜甫必須死得戲劇化
失眠的詩歌如何做夢
推崇古詩詞,就要貶低新詩嗎?
詩為他、為我們、為漢語招魂
小冰合是詩人未?
「文藝復興」的背後,是詩的馴化
你的自由是不是你的自由
PartⅡ 過於孤獨的喧囂
重遇巴布‧狄倫Bob Dylan
狄倫反對狄倫
無數狄倫,無數詩與歌的交叉曲徑
在地下
行走的小糖人
迷失探戈
舞舞舞吧,直到生命盡頭
森田童子,或日本「安保世代」的告別
河兩岸,永隔一江水
詩人左小祖咒的憤怒
鳥寫的尋鳥啟事
離魂歷劫之歌
萬能歌謠,不萬能的青年
海豐英雄多奇志
崔健與香港
中國搖滾運動中的扛旗情結
愛人同志,從禁色到彩虹
《一代宗師》裡的香港Blues前傳
時代之曲——說黃霑《滄海一聲笑》
少年香港說
香港曾有家駒和Beyond
黃耀明的另一個中國
俠隱再達明
從獅子山到太平山——黃耀明演唱會中的香港精神蛻變記
民歌四十年和搖滾三十年:距離和答案
爵士樂,或一種民主詩學
暴雨為何反對?
我曾經做夢辦一個詩歌節,為古詩朗讀配上我喜歡的現代音樂:
楚辭五彩斑斕、想像力奇偉洋溢、鬼神出沒,應該配藝術搖滾、華麗搖滾,比如說大衛‧鮑伊(David Bowie)和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漢賦磅礡,只有重金屬搖滾鎮得住;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慷慨激昂,俯仰宇宙蒼涼,應該配太空搖滾、歌劇搖滾,比如說深紅國王樂隊(King Crimson),曹植超然,應該配妮可(Nico)這種洛神級女歌手。
李白作為大唐代表詩人,向他致敬的唐朝樂隊卻未必配得上,後期的披頭四樂隊(The Beatles),恣意飛翔,天馬行空才更像他;杜甫關注現實的苦難、人間的悲喜,周雲蓬配合他老淚縱橫,巴布‧狄倫(Bob Dylan)則與他振奮一笑。李賀奇絕、光怪陸離,德國的Can樂隊、日本的酸母寺樂隊( Acid Mothers Temple)會成為他絕配;李商隱幽深抉祕,一波三折,也許只有地下絲絨(The Velvet Underground)樂隊這種級別的實驗大師能與之共鳴。
宋代蘇東坡與柳永,前者不妨由騰格爾歌唱、圖瓦的恆哈圖樂隊(Huun-Huur-Tu)配樂,後者則王菲、林憶蓮均可。姜夔本身就是一個音樂家,要求要高得多,深邃又清空,流行音樂裡估計只有達明一派、森田童子、竇唯等可以與之唱和……
我且打住,忽略那個詩歌不分家的烏托邦吧,現代詩從「純詩」抽離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在言詞意義上過分講究音樂性的詩不是沒有,而是只可一試不可泛濫,因為當代詩最大的挑戰不再是其純藝術性,而是處理現實與超現實、應對時代的難度。那麼應該講究的是心氣、胸懷的鑄煉,並且從詩的現場傳播、即興創作等角度,找到它與現代音樂的接點,這是一個極具創造性的出路。
因此,編選這本「異托邦指南」的第三部的時候,我自然把詩評與樂評放在一起,意圖使現實之上、文本中的它們也能碰觸出火花——或者,索性是雷電。巴布‧狄倫說的「暴雨將至」,到了這個時代,也許要改變意義了。讓我們自己成為暴雨,攜帶著雷與電,去反對這個時代的沉默、反對這個時代的喧譁、反對這個時代的乾涸。如果世界充滿對假象的阿諛,反對就是詩人與音樂人的義務,無論這假象屬於國族、人情還是世故,還是冠著頹喪的名義對媚俗的縱容。
這首寫給哈薩克樂隊IZ的詩〈夜京空行咒〉,演繹的就是詩與歌聯合的顛覆,可以作為這一次異托邦之旅的前奏,起飛吧,語言的翅膀已經準備好了:
這些星羅棋布為了誰
大地並非墓碑
沉睡已經不能一飲
酒佩著刀,人配不起酒
我馬蒼涼如生宣紙
任這黑汗爬行逶迤
噫!這生生死死為了誰!
如果可以這咒文我不想用漢語
而用那些蝕如馬骨的文字
願這京城寂寂
如暴雨中的哈薩克
願這飛機一時斂翼
棲那巧雲尖兒無何有之枝
願腹中小兒為我打鼓
那個蕩蕩當當輕輕盡盡
的放風箏者竟然是我也
噫!這生生死死為了誰!
口弦蝗蟲陣法
冬不拉橫雨陣法
我思想起我那些黑暗中的姊妹兄弟
那些含著一顆星唱歌
舌頭已經被灼傷的趕路人兮
重遇巴布‧狄倫
1
我聽見有雷炸響一個警告
有浪咆哮要把整個世界淹掉
聽見一百個鼓手雙手在燃燒
聽見一萬個人在耳語但沒人在聽
聽見一個人將死於飢餓,聽見人們對他大笑
我聽到一個在陰溝裡死去的詩人的歌聲
一個小丑在後巷中哭叫
而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而暴雨就要下起——
這是巴布‧狄倫最偉大的一首歌〈暴雨將至〉(Tempest,曹疏影譯),他所唱的也許是當時的美國、古巴、蘇聯,也可以是今天的日本、西亞、北非……一切意象那麼清晰強烈,而咆哮之語又如暴雨迅即混和了大廈將傾之聲,含混而至於擁有超越時代的力量。對於十多年前剛剛接觸他的我來說,他是二戰後最偉大的詩人,因為他的詩不落言詮,卻直指激蕩燃燒著的青年靈魂。
一九九五年第一次聽到巴布‧狄倫的一張完整專輯之前,我已經在詩人袁可嘉編的一本外國現代詩選裡讀過他的歌詞,我記得袁老寫到在美國聽巴布‧狄倫演唱會的盛況,把巴布‧狄倫比喻為柳永,寫得像有井水處就有狄倫歌似的。袁老把巴布‧狄倫的歌詞作為詩翻譯過來,放在那本大師雲集的詩選裡居然毫不遜色,而且另有一股灑脫滌蕩之氣,且神祕、猛銳如春夜之虎。
我曾直接師從他的歌而寫我的新詩,這首先是一種意氣風發的精神,我來了,我看見,我唱出。一個最敏感的心坦然直面最晦澀瘋狂的現實,像美國當代詩歌,擁有一個消化一切的胃,世界於是向他敞開——在我最初的理解中,巴布‧狄倫就是這麼一個魔術師般的吟遊詩人。但是即使是十五年前單純的我,也從巴布‧狄倫處學習了不單純以及批判。坦蕩之氣骨與神祕繁複之意象,是他的兩面,在現代詩中很少有人能綜合之,除了羅卡——由此也可以看出影響巴布‧狄倫的,除了狄倫‧湯瑪斯,還有羅卡和布萊希特。狄倫和他們的敘事歌謠和我們的《詩經》、樂府有同樣珍貴的質量:直接、純樸又婉約、新奇,他們教會我如何以詩歌的形式敘事而不是藉小說、戲劇的形式敘事。
就像一個詩人的詩風發展變化一樣,巴布‧狄倫的歌詞像他的人生、他的音樂一樣變化多多,變化不大的是技巧都是超現實主義的潛意識意象營造為主,但關注主題從由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而來的對美國底層生活的關注,去到六○年代最重要的人民抗爭,他憂時憤世但又冷言調侃,充當的是一個類似莎士比亞戲劇裡小丑的角色——他們是最辛辣的行吟詩人。
但從《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這張專輯開始他開始為自己寫作、走進自己的內心最深處,並且流露出他日後越發突顯的反對姿態:反對聽眾和評論家對他的強行定位、甚至還反對自己。把他的反對姿態與介入時代兩者結合得最好的是隨之而來的兩張插上電吉他、「背叛民謠」的《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和《Highway 61 Revisited》,那裡面句句是內心幻象但又讓人深切地感到時代之痛。此後狄倫還在這樣的路子上若即若離地走了很遠,除了曾經因為成為「再生基督徒」而讓一九八○年前後幾張專輯帶上宗教色彩以外,他的歌詞依然保持一貫的懷疑主義精神,也保持一貫的優秀現代詩水平——因此前些年他不斷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我一點也不吃驚。
巴布‧狄倫還在寫下去,以歌、以詩、以回憶錄甚至小說的方式,他時而回去民謠草莽之根,時而狂奔到蘭波的幻象國度,時而則在摩登都市的霧與人海中浮沉……這些都是他質問自己的方式,他也越來越樂於在自身的深淵裡暢泳,喃喃自語而不管我們是否能聽懂。但就像我十五年前寫的一首獻給他的詩〈六○年代的老巫師〉結尾所說:
緊靠著他一點沙啞的灰燼
遠離六○年代和殘餘的中年肚子
在偏僻的北京或香港
緊靠著,緊靠著他一點破裂的詞語
青年們被吃剩的翅膀骨頭無法入睡。
——被他喚醒的我們,本身將構成他最多義、有無限變奏可能性的一首詩。
2
我生也晚,錯過了那個抗議與愛的時代。第一次聽到巴布‧狄倫的一張早期專輯時,狄倫的聲音讓我吃驚,二十出頭時的嗓音已經老韌如一個飽經江湖的老海盜。聽著那彷佛對這個世界毫不買賬的嬉笑怒罵,你不得不承認,他早已歷經滄桑、熟悉時代的賭局。那時的巴布‧狄倫對我最富有魅力,他既是如他所唱的〈Mr‧ Tambourine Man〉一樣是一個神祕的引領者,又是〈暴雨將至〉中那個與你一起走進黑暗森林的戰友。他的音樂則從俐落直率的木吉他口琴式布魯斯,發展到電流激蕩的民謠搖滾,甚至還帶上六○年代不可缺的迷幻氣味。二十到三十歲之間的巴布‧狄倫,一開口就是風起雲湧。
和其它聽巴布‧狄倫的前輩不一樣,我是同時接觸六○年代激進的他、七○年代反思的他、八○和九○年代「墮落」的他的。但因此我能擁有一個最多面體的巴布‧狄倫。從一九六一年,〈Song To Woody〉的淳樸剛毅;一九六二年,〈Blowin’ In The Wind〉的憤怒哲言;到一九六三年,〈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前瞻號召。到民謠時代結束,電流像更多變的意象和節奏使詩歌涅槃重生,一九六五年的〈Mr‧Tambourine Man〉彷彿彩衣魔笛手開啟了一代人的迅猛幻想;〈It’s Alright, Ma (I ‘m Only Bleeding) 〉的犀利反諷;〈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和〈Like A Rolling Stone〉的虛無和絕望;〈Ballad Of A Thin Man〉一針見血的質問;直到〈Desolation Row〉那史詩式的瘋子方舟受難圖!這個時期的巴布‧狄倫儼然是我最傾慕的冷面騎士。
後面縱還有〈Blonde On Blonde〉的晦澀自辯、〈John Wesley Hardin〉的幽怨與釋然……巴布‧狄倫卻慢慢離我遠去,走回他自己的封閉世界中去了。他最後一次以歌聲打動我,已經是一九九三年那張《World Gone Wrong》和一九九五年那張《MTV Unplugged》,又回到一個人和吉他、口琴的糾纏而生的根源布魯斯,居然還有火氣和血的味道,又有沉澱它們的力道。
但他很快就真正的老去,進入萬馬齊喑的八○年代之後更是銳氣盡失,交功課一樣交出來的一張張新專輯沒有一張能有當年的驚喜。我在一個抽離的時空中同時聽到不同年代的他,漸漸困惑:此Bob仍是彼Bob耶?慢慢我也在聆聽的道路越走越遠,走到實驗音樂與爵士樂的龐大迷宮去了,巴布‧狄倫日漸生疏。轉眼是二○○五年,我在北京一家書店看到一本《認識老年痴呆症》的書,封面竟然是不知從哪裡盜來的老狄倫頭像,我幾乎怒而淚下,你叫我情何以堪!那個時候,我的二十多張巴布‧狄倫專輯已經在舊居塵封許久。
為了迎接「我的鈴鼓手先生」來港演出這一夜,我搬出了我唱片架上放於最顯赫位置的二十三張巴布‧狄倫的各種專輯來重聽。狄倫魔力依舊,沙啞嗓子彷佛依然吞吐著雲彩與大海。十八年前,我第一次在一個澳門電台的午夜節目「另類音樂接觸」聽到巴布‧狄倫,我已然意識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民謠歌手,要聽懂他的歌,需要配備一書庫的二十世紀理想主義兼虛無主義精神讀物作為後盾。下面開列的書單,都是我讀過的書,他們幫助我理解了產生巴布‧狄倫的那個火與愛的時代,也幫助了我理解狄倫。
首選當然是《狄倫‧湯瑪斯詩選》,就是因為傾慕這個二十世紀最天才的威爾斯詩人狄倫‧湯瑪斯(Dylan Thomas),勞勃‧艾倫‧齊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才會改名為巴布‧狄倫並以此揚名後世,巴布‧狄倫從狄倫‧湯瑪斯處學到最深刻的是對死亡的思考以及超現實主義的潛意識幻想戲法,狄倫‧湯瑪斯比巴布‧狄倫濃稠很多也更黑暗,他身上更多二戰的烙印,如此熾熱疼痛以至於詩人在三十九歲便酗酒而亡。
二是《夜幕下的大軍》(The Armies of the Night),六○年代美國反戰運動頂峰——「進軍五角大廈」事件的文學副歌,《裸者與死者》作者諾曼.梅勒以親身經歷加以小說化的「新新聞主義小說」代表作。一代青年的憤怒、迷惘與失落在克制的語言背後悸動。 巴布‧狄倫和瓊‧拜亞(Joan Baez)也參加了遊行,並演唱〈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與〈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這兩首歌曲。
當然少不了回憶錄《搖滾記》,無論我們熱愛、錯愛還是對他因愛成恨,都要聽聽他自己的辯護詞,這是他唯一的回憶錄,呢喃回憶文字如像意識流小說,講述的是時代側面的大霧彌漫,音樂背後的自我拷問與掙扎,是另一種時代的噪音,迷離以至絢爛。
而在格雷爾‧馬庫斯(Greil Marcus)的《地下鮑勃與老美國》裡,巴布‧狄倫彷佛一個老巫師(雖然其時只有二十出頭),敏感地感知了六○年代中「美國夢」的激變,《地下鮑勃與老美國》記載的就是這個特殊時刻,以巴布‧狄倫插上電吉他「放棄」民謠開始,到他祕密地在地下室「回歸」民謠製造出傳奇的《The Basement Tape》為終,《地下鮑勃與老美國》分析的表面是巴布‧狄倫,實際是分析隱藏在人所共知的「美國夢」後面那一個更為複雜甚至黑暗的美國精神。
重遇巴布‧狄倫,我依然相信他日益盤結成幽暗森林的大腦裡面的真誠,縱然這真誠他只對他自己負責。他要來香港,我只猶豫了一下就買了演唱會的票,我不是去看自己的青春,不是去看神話時代的圖騰,也不是去看這群終於有了懷舊本錢的老哥們一起以淚水和吹牛逼來互相取暖,我就是去看這個老得可以上《認識老年痴呆症》封面的老頭,他將如何再一次反對我們所有人,在風暴眼的中心蹲下,用內心的暴雨洗刷屬於他的時代和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