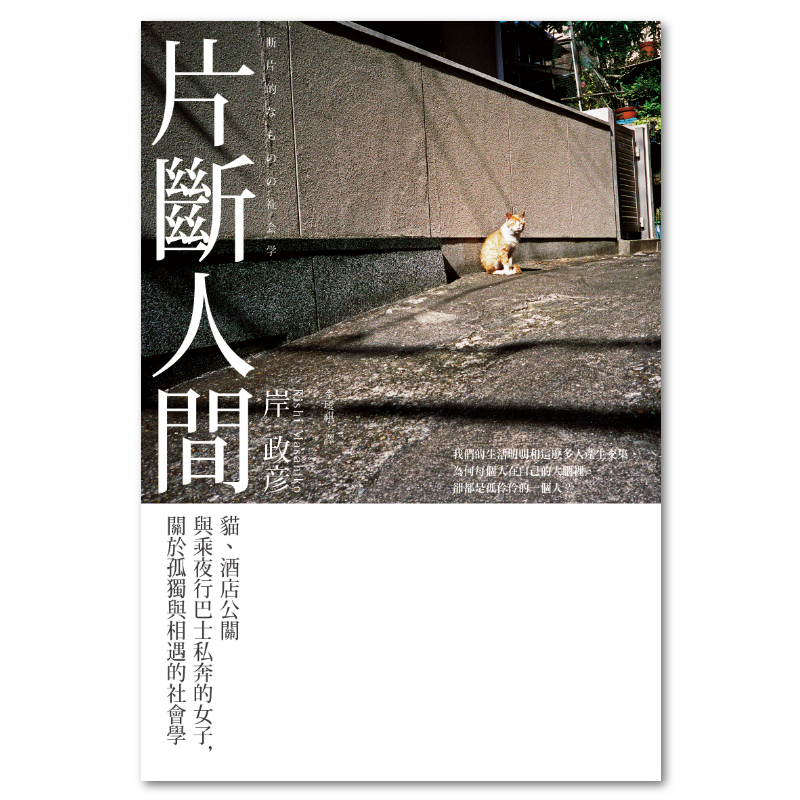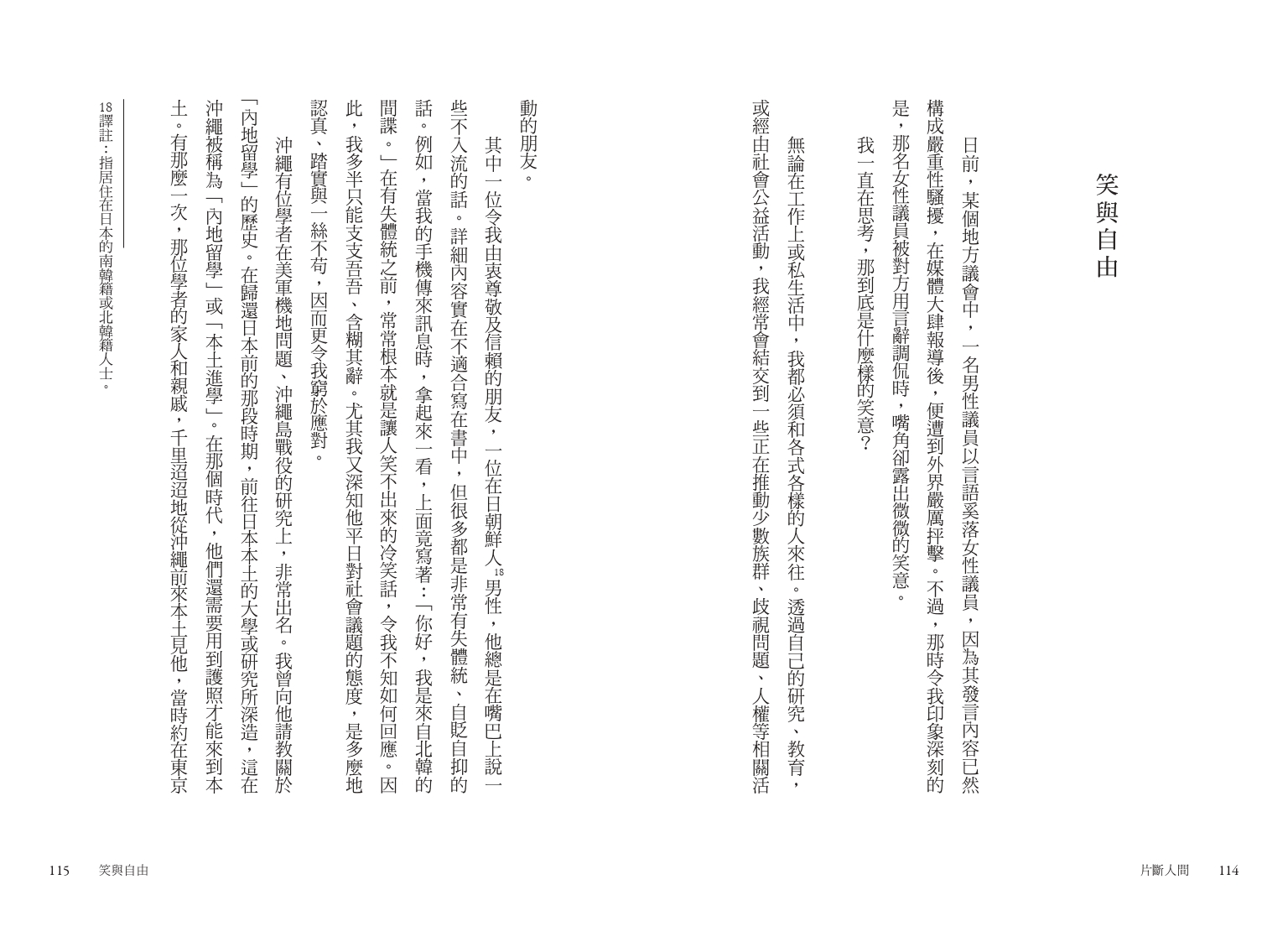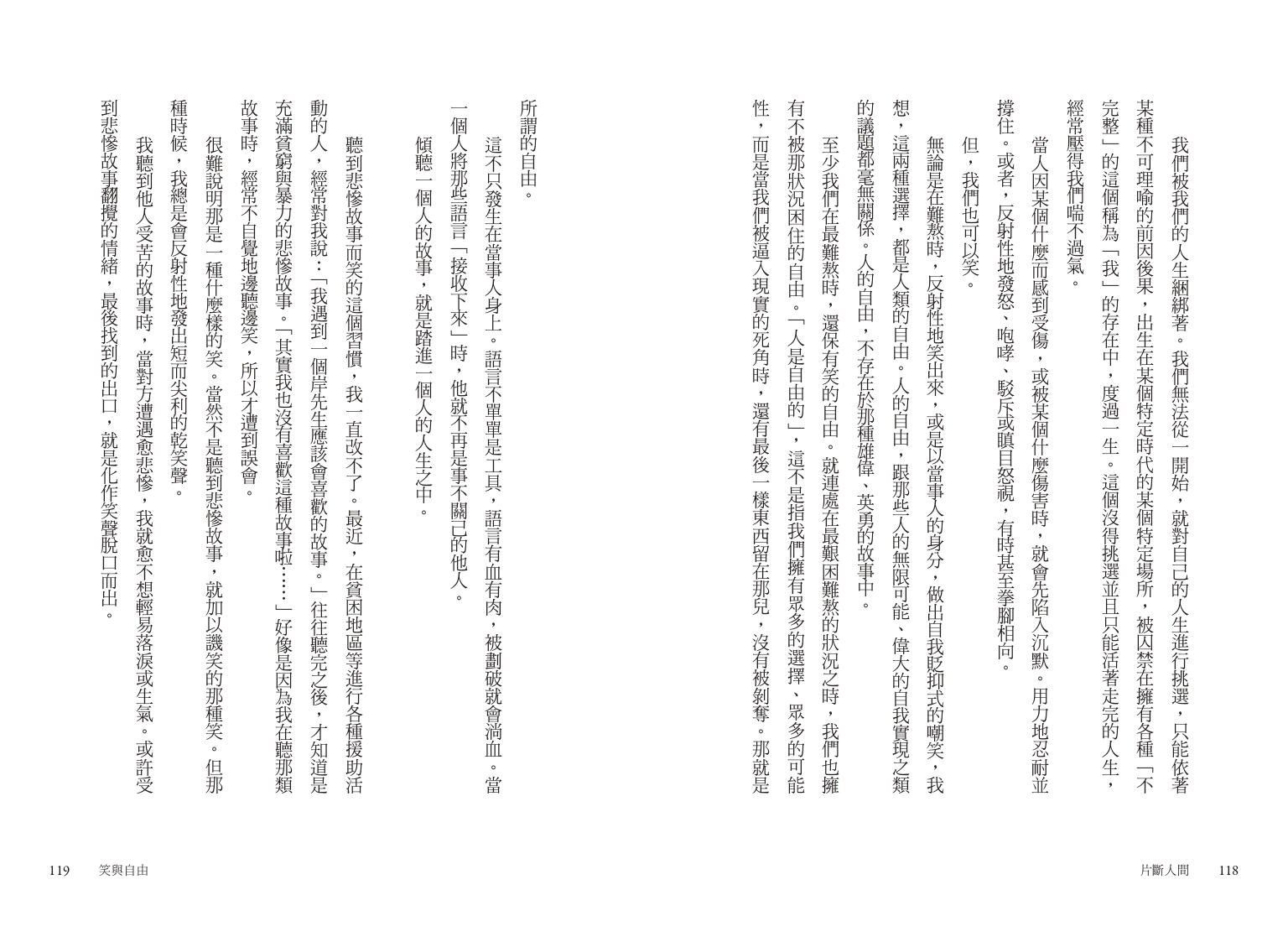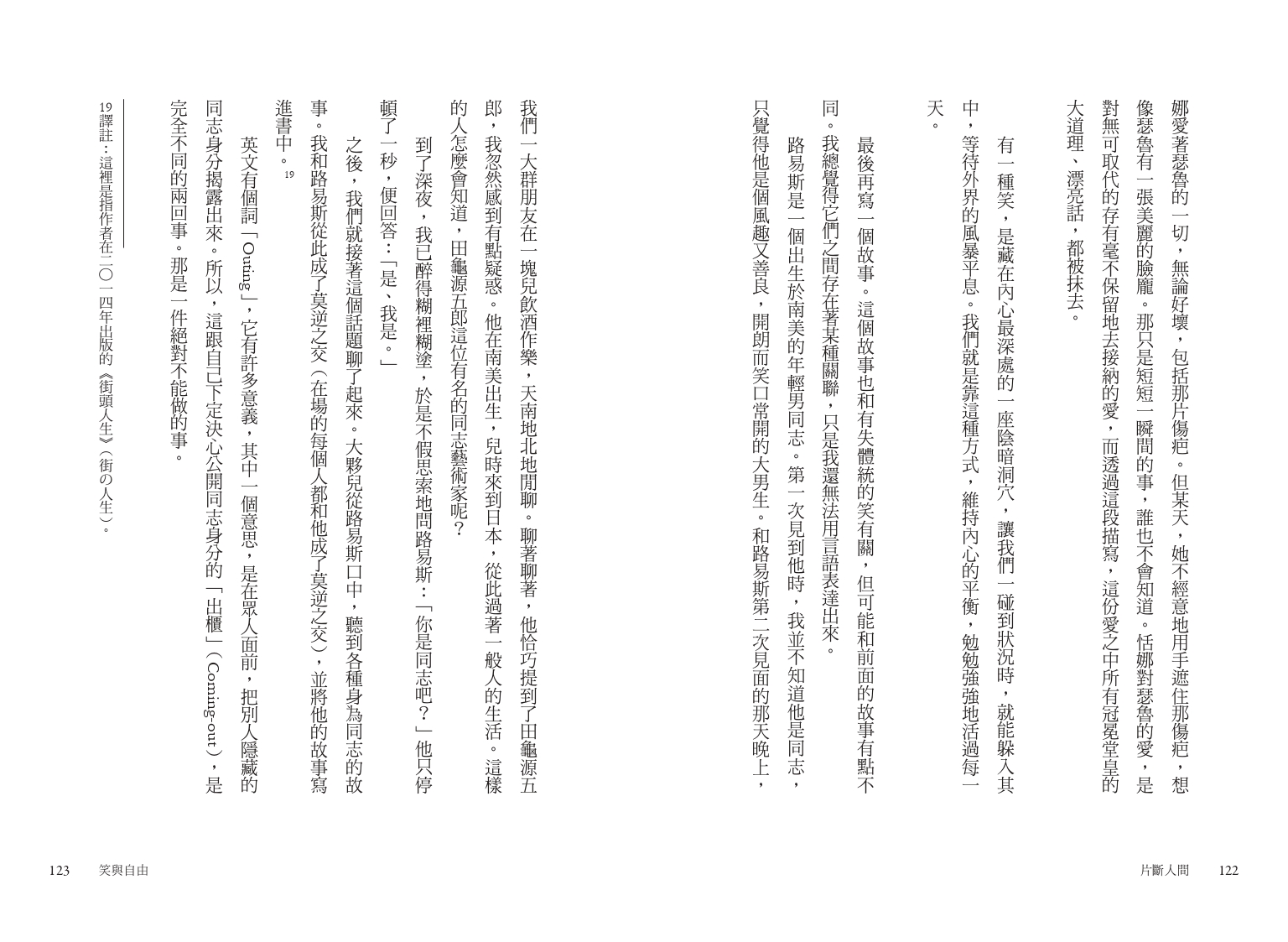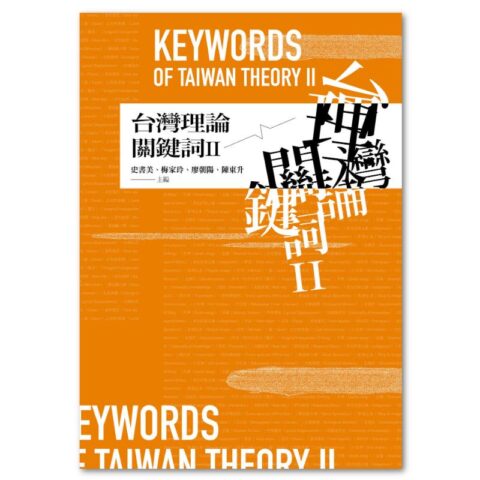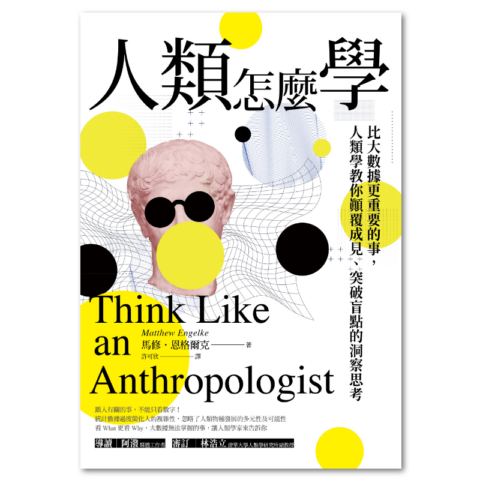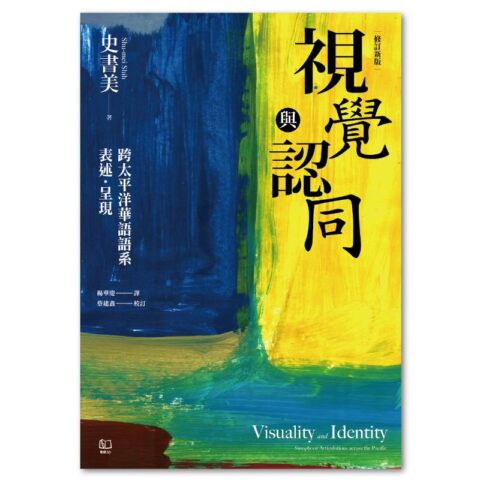片斷人間:貓、酒店公關與乘夜行巴士私奔的女子,關於孤獨與相遇的社會學
原書名:断片的なものの社会学
出版日期:2021-03-11
作者:岸 政彦
譯者:李璦祺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64
開數:32開,長18.8×寬12.8×高1.4
EAN:9789570857122
系列:聯經文庫
尚有庫存
第6回紀伊國屋人文大賞TOP 1!
★入圍芥川獎的社會學家首部田野人生隨筆集★
★一本擁抱「無意義」的生命之書★
很久沒遇到一本,令我這麼捨不得讀完的書了。
──上野千鶴子/社會學家,著有《厭女》、《一個人的老後》
我們的生活明明和這麼多人產生交集,
為何每個人在自己的大腦裡,卻都是孤伶伶的一個人?
隱身於日本社會的沖繩人、部落民與在日朝鮮人;
遺忘於陽光下的黑幫小嘍囉、酒店公關與易妝者;
不斷送盆栽的老奶奶,頭上穿洞的泥巴小貓,乘夜行巴士私奔的女子……
──社會學家與他們實際相遇,撿拾理論也無法分析的片・斷・人・間。
「我們自己與我們的世界,不僅會說故事,更是由故事所構築而成。」
然而,當故事被打斷、撕裂、產生矛盾的時候,
或許才是我們面對自己與這世界最真實模樣的時刻。
岸政彦是一位專長生活史的社會學家,也是一名入圍芥川獎的小說家。他以社會學之眼看書、看電影、閱讀人生百態,並以文學之心,寫下那些散落於日常的「無意義」,寫下那樣的片斷所集結而成的這個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上的我們,正與某個誰所產生的某種連結。
「我們的人生或經驗都是毫無意義的。但即使如此──或說『正因如此』──它們才會如此美麗。我們不用為人生賦予過剩的、陳腔濫調的意義。同時,我們也必須知道,這種無意義本身就是一種美。而且,這樣的人生是錯過不再的,而那裡所流的血也是真真實實的血(而非故事而已)。」──岸 政彦
〈交出人生〉
探頭看看自己的內在到底裝了什麼,就會發現裡面根本沒裝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有的只是,人生至今所搜集的片片斷斷的無用之物,它們之間既無關也沒必然性,甚至沒有任何意義,只是靜靜地散落在那兒。
〈來自海的另一端〉
我們各自禁錮在片斷而不完整的自己當中,自己也不確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卻仍試圖去影響他人及社會。我們沒有把握瓶子能否漂流上岸,被人拾起,卻仍將無窮無盡的字句,塞入瓶中,投向大海。
〈扔掉時鐘,與狗約法三章〉
我們喜歡將各式各樣的事物擬人化。可能是因為,這麼做能讓我們感覺到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是「有連結的」。如果世界完全無法用我們的語言來解釋,那我們就太孤獨了。
各界推薦
千葉雅也/哲學家、小說家
這本書將讀者帶往奇妙的「外側」。這不是一場冒險犯難,是一個由片斷性的場景奇妙地聚合而成的社會,一種瞬間閃過的格格不入感。作者像電影般地加以剪輯串聯,其剪輯技術,高超到甚至令人感到狡猾。美得過頭。
星野智幸/小說家
這本書什麼都不肯告訴我們,有的只是深沉且豐沛的困惑,以及靜靜陪伴在側。正如小石頭與狗那般。而我需要這本書。
高橋源一郎/小說家、文藝評論家
凝神注視社會整體未來的「字字句句」。
阿潑/人類學家、作家
對我自己來說,整本書都值得反覆閱讀,甚至看到了自己──畢竟,連家裡養的狗去世的這個段落都說出了我的心聲──說真的,讀到最後,我感到的是悵然與虛無,但每次看到有想要對話的段落,我都會拍下那個段落傳給不同的朋友。
陳又津/小說家
這個世界存在著無法分析的角落,就像現實社會也沒有明顯的參考文獻和註腳,這些片斷是他與其他人連結的時空,像是一個個微型轉運站,通往許多人內心的道路,路上有一閃而逝的奇異風景。
許瞳/作家
每個人都是一則無人知曉的故事,而生命是一個歪斜中空的圓。當顧著沿線條謹慎行走,當路過這錐心刺骨的人間,岸正彦沉默掇拾靈魂的透明碎片,將那些不必多說的話語、無意義的時間,悄悄補綴為一襲填滿圓心的透明百衲被。
溫又柔/小說家
這整個世界存在於片片斷斷的事物之中。只要培養敬小慎微的眼光,細心觀察與我們共同生活於這個社會的他者,就能更接近這個存在於他者之中的世界,彼此也能更加相互尊重吧。本書為如何通往這樣的世界,指引了一個方向。
蕭詒徽/作家
為了感到幸福,總是不斷替既存於生命中的事物尋找意義,害怕一切沒有理由,因而漸漸搞混了順序——其實,世上大多數事物並不是因為有價值,所以才存在的。岸政彦先生所寫的沒有一篇是勵志故事,卻像從高處掉落之後意外站立著的錢幣一樣,處處令人感到偉大,提醒了我所常常忘記的、對「存在」的敬意。
▍專文推薦
阿潑(人類學家、作家)
陳又津(小說家)
▍相遇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李明璁( 社會學家、作家)
盛浩偉(作家)
許瞳(作家)
溫又柔(小說家)
蕭詒徽(作家)
作者:岸 政彦
1967年生。社會學家。長居大阪,往返沖繩。大阪市立大學研究所文學研究科社會學專攻取得學分肄業、文學博士,立命館大學研究所先端綜合學術研究科教授。研究主題為沖繩、生活史、社會調查方法論。著有《同化と他者化──戦後沖縄の本土就職者たち》、《街の人生》、《はじめての沖縄》等,小說《ビニール傘》入圍芥川獎,《図書室》入圍三島由紀夫獎。
部落格:http://sociologbook.net/
推特:https://twitter.com/sociologbook
譯者:李璦祺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自由譯者。平常是兩貓一兔的媽媽;空閒時喜歡閱讀思考,熱愛參加天文物理、性別研究、社會心理、藝文創作等各式各樣的課程;壓力大時好寫長文抒懷。透過時時刻刻的觀察,讓人生的波函數,塌縮成可測量的量子態。譯有《瀕死經驗的啟示》、《橫尾忠則×9位經典創作者的生命對話》、《成為新人類》等書。
聯絡試譯與譯作賜教:aichih.lee@gmail.com
推薦序1 即使是人生路途中撿拾的小石子,也是獨一無二的 阿潑
推薦序2 創造連結的轉運站 陳又津
中文版序
緒論 未被分析的事物們
人生就是片片斷斷的組合
毫不隱藏,卻無人看見
土偶與盆栽
從故事之外
街頭的卡內基音樂廳
離與歸
笑與自由
掌中的按鈕
他人的手
流過絲蘭的時間
夜行巴士的電話
朝向普通的意志
慶典與躊躇
交出人生
來自海的另一端
扔掉時鐘,與狗約法三章
故事的殘篇
後記
出處一覽
中文版序(節錄)
此次,聽說這本小書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我感到無比開心。台灣和香港皆是我非常喜愛且多次造訪之地,一想到能讓生在這些地方、與我素未謀面的讀者讀到這本書,就由衷感到幸福。
在台北、香港的街頭漫步時,我總想像著:「如果我生長在此地,不知會過著什麼樣的人生?」我想,肯定與我現在的人生截然不同吧。
說不定,某個生長在台北或香港「過著不同人生的另一個我」,也造訪過日本的大阪(我現在所居住的城市)。
初來乍到的另一個我,在大阪這個陌生城市的陌生巷弄裡,說不定也會一邊漫步,一邊想像著:「如果我生長在大阪,不知會過著什麼樣的人生?」
我甚至還曾幻想:「我現在在大阪的這個人生,說不定就是生長在台灣或香港的另一個我來到大阪旅行時,正在想像的人生。」
我以傾聽人們的「生活史」為工作,至今已超過二十個年頭。長期以來,我以居住在沖繩及大阪的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市民為對象,傾聽著他們的成長經歷與人生故事。
生活史的敘述,或者說一個人的人生本身,是由許許多多繁雜的、片斷的故事插曲所組成,這些故事插曲相互矛盾、支離破碎、謬誤百出又模稜兩可。
然而與此同時,也是實際存在的真實人生中的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故事,如果在上面劃一刀,恐怕真的會流出血來。
許多人──甚至是社會學家──主張,應該讓個人訴說的生活史,回歸於純粹的「陳訴」或「故事」。因為他們認為,那些故事與現實毫無連結,既曖昧不明又充滿歧義,只是單純的「趣聞」罷了。這一派說法,如今在現代思潮、哲學、人類學、社會學上,儼然已成為主流,然而從過去到現在,我一直對此說法感到強烈的扞格不入。
我們對這個「自己」出生於何處、身處在哪個時代,毫無選擇權利,但我們又終其一生都不得不與這個「自己」相處下去。即使中途厭倦了這個「自己」的人生,也不可能換另一個人生來過過看。
一方面,個人生活史的敘述是充滿歧義而又流動性的,是模稜兩可而又謬誤百出的。另一方面,即使如此,我們的人生仍是錯過不再的,我們都是被禁錮在自己的人生中,而無法實際體驗他者的生命的。
這本書就是誕生於我思考著這兩件事的過程中。
這裡我想要表達的,並非「上帝藏在細節中」或「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彌足珍貴」之類的大道理。我們的人生或經驗都是毫無意義的。但即使如此──或說「正因如此」──它們才會如此美麗。我們不用為人生賦予過剩的、陳腔濫調的意義。同時,我們也必須知道,這種無意義本身就是一種美。而且,這樣的人生是錯過不再的,而那裡所流的血也是真真實實的血(而非故事而已)。
這就是我想透過這本書表達的。
推薦序1(節錄)/即使是人生路途中撿拾的小石子,也是獨一無二的/阿潑(人類學家、作家)
「我一方面分析那些談話內容,儘量讓我做的調查能歸類在『社會學』的學問範疇中,另一方面,也盡可能地珍視那些,被排除在我的詮釋之外的談話與插曲。不,倒不如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或插曲,反而經常存在於,被我狹隘的理論與理解排除在外的部分。」日本社會學者岸政彦在《片斷人間》緒論中說,自己很受那些發生在眼前的細枝末節本身「無意義性」影響。這顯然更有趣。如同他說的,雖然他的工作是透過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分析統計數據或歷史資料,但他真正喜歡的,「是那些無法分析的事物,是那些單純存在的事物,更是那些暴露在陽光下並逐漸被遺忘的事物。」
因此,我可以理解岸政彦先生何以在自己的研究專注之外,還要寫這麼一本田野之外、理論無法分析且散落在故事之外「斷簡殘篇」的書,而這些反思與採訪過程中的經歷,確實讓人很有感觸與共鳴──例如,岸政彦撿拾石頭的習慣,我也曾經在每個災區現場做過。每到災區,除了拍攝許多遺留物,想像這些物品主人的經歷與故事,我也會撿拾石頭,想像他在這塊土地上的見證,想像它承載的歷史。
這是一篇訴說自己經驗的推薦文,因為這本看似隨筆、短札的書,帶著社會學的意識,也有田野的紀錄思考,故事的訴說,心理與哲學的探索,人際關係與社會偏見的顛覆,乃至於生命意義的扣問,最後落於「生而孤獨」的輕嘆。在每次路途中,我都會取出書稿閱讀,但太多漂亮值得記錄的句子段落,最後幾乎整份書稿都被我畫了線。對我自己來說,整本書都值得反覆閱讀,甚至看到了自己──畢竟,連家裡養的狗去世的這個段落都說出了我的心聲──說真的,讀到最後,我感到的是悵然與虛無,但每次看到有想要對話的段落,我都會拍下那個段落傳給不同的朋友。我想,對於不同讀者來說,都可以從這本書裡找到自己喜歡、有共鳴,且可以與之對話的部分。
推薦序2(節錄)/創造連結的轉運站/陳又津(小說家)
二○一七年,岸政彦五十歲時,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塑膠傘》,入圍芥川賞。兩年後,他再度以《圖書室》入圍三島由紀夫賞。在日本,高齡出道的作家不少,但像岸政彦這樣一直有專書論著發表,卻忽然開始寫小說的人,就十分罕見了。
《片斷人間》於二○一五年出版,岸政彦說,他無法將這些「片斷」放進社會學的論文或報告,卻也無法忘懷這些時刻。連社會學者都無法解釋的困惑,是串連這本書的主旋律。當我們在生活中遇見怪異的陌生人,多半只是得到「那人怪怪的」、「來找麻煩的」這種印象,只求火速逃離。但社會學家必須密集地接觸、分析,持續面對未知的風險。
這本書展開了一場介於田野、研究與虛構的寫作,內容涵括學者對於現象的思索、在田野過程中的困惑與掙扎,也有些像小說才有的奇妙人物。但這些人就存在於我們周遭,只是我們缺乏足夠的好奇心和勇氣去描述這些人──我們怕跟那些怪人產生連結,甚至意識到自己就是那些怪人。在這本書中,岸政彦如此歸納自己的社會學工作:「一直以來我所做的就是,一邊傾聽這些個人生活史,一邊思考『社會』的涵義。」
社會是什麼、人又是什麼?
進入田野之前,研究者心中通常都有個研究目的,像是補充前行研究的不足,或是顛覆既有的理論。但過程總是會聽到出人意表又精神一振的故事,這該怎麼辦呢?這些外人看來沒什麼好寫,甚至是離題的片斷,反而更能顯現研究者自身的特質。不過,因為論文架構的規範以及讀者的期待,這些有趣的地方通常會被刪掉,頂多成為花絮或後記。例如我研究某個題目時,雖然讀了別人寫的文章或意見,但還是會試著詢問當時的筆者,有沒有什麼沒寫的部分?這往往是過去沒機會發揮,這次卻絕對不容錯過的機會。
無論是跑田野或寫小說,我們常常在聽人說話的時候入迷了,在某個當下意識到「這個可以寫」,但動筆敘述之後,卻懷疑自己似乎在虛構,甚至違逆當事人的意願。人一不小心,就會成了故事的容器或俘虜。採訪能拓寬個人認知的界線,無論是幾個小時、幾天的採訪都有類似效果,但身為社會學家的岸政彦也提醒我們:「記錄這種片斷性邂逅中所談到的片斷性人生,然後直接將其普遍性地、整體性地視為對方的人生,或詮釋為對方所屬的族群的命運,這其實是一種暴力。」
笑與自由
日前,某個地方議會中,一名男性議員以言語奚落女性議員,因為其發言內容已然構成嚴重性騷擾,在媒體大肆報導後,便遭到外界嚴厲抨擊。不過,那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名女性議員被對方用言辭調侃時,嘴角卻露出微微的笑意。
我一直在思考,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笑意?
無論在工作上或私生活中,我都必須和各式各樣的人來往。透過自己的研究、教育,或經由社會公益活動,我經常會結交到一些正在推動少數族群、歧視問題、人權等相關活動的朋友。
其中一位令我由衷尊敬及信賴的朋友,一位在日朝鮮人男性,他總是在嘴巴上說一些不入流的話。詳細內容實在不適合寫在書中,但很多都是非常有失體統、自貶自抑的話。例如,當我的手機傳來訊息時,拿起來一看,上面竟寫著:「你好,我是來自北韓的間諜。」在有失體統之前,常常根本就是讓人笑不出來的冷笑話,令我不知如何回應。因此,我多半只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辭。尤其我又深知他平日對社會議題的態度,是多麼地認真、踏實與一絲不苟,因而更令我窮於應對。
沖繩有位學者在美軍機地問題、沖繩島戰役的研究上,非常出名。我曾向他請教關於「內地留學」的歷史。在歸還日本前的那段時期,前往日本本土的大學或研究所深造,這在沖繩被稱為「內地留學」或「本土進學」。在那個時代,他們還需要用到護照才能來到本土。有那麼一次,那位學者的家人和親戚,千里迢迢地從沖繩前來本土見他,當時約在東京的鬧區碰面。他說:「那時,對面走來一群人,一個個臉都跟黑炭一樣,我才在想說,他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土著,結果就是我的家人欸!」語畢,他自己哈哈大笑。我只好擠出模稜兩可、裝傻充愣的笑容,輕輕乾笑兩聲。
內人齋藤直子在做的,是部落民問題的研究。據說,有次她和關西某個被歧視部落的青年會的人,同車前往他處,當車子行經另一個被歧視部落時,青年們一邊說著「好像臭臭的」「哪裡臭臭的」「這裡是部落吧」「這裡就是部落啦」,一邊哈哈大笑。
雖然由於工作因素,我經常接觸到關於部落民或沖繩的故事,但這樣子的笑法,當然並非只有關係到特定歧視問題或社會問題才會發生。這種笑法,真的無論走到哪,都隨處可見。
我是個生不出孩子的人,因為我患了重度的無精子症。還記得某次,內人從醫院帶著檢查報告,哭哭啼啼地回到家中,我一邊聽她解釋一邊走神,漫不經心地想著:「原來我很安全,早知道結婚前應該多玩玩的。」
不,不對,正確來說,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可以拿這件事來跟人開玩笑說:『原來我很安全,早知道結婚前應該多玩玩的。』」那時,閃過我腦海的,是如何把這件事拿來當成一個笑料。
在第一時間,下意識地、瞬間地,把那消息當成笑料看待,才讓我撐過了那件事帶來的打擊。當然,我至今仍找不到方法說服自己「釋懷」。但我們能做到的,便是將人生中怎麼也無法釋懷的事,以嘻嘻哈哈的方式帶過。未必一定要向誰說出來,就算只是在內心自我嘲笑,也能讓我們勉強和那件完全無計可施的事,相安無事,和平共存。
雖然那是一種只限於那個當下,短暫、一瞬間的行為,但唯有透過將這些瞬間,一個個串連起來,人生這場旅程才走得下去。
順帶一提,我偶爾會在上課或演講中,提到自己的私事,也會跟台下的人說:「知道那件事時,我就在心裡想:『原來我很安全,早知道結婚前應該多玩玩的。』」但至今從來沒逗笑過任何人。
我們被我們的人生綑綁著。我們無法從一開始,就對自己的人生進行挑選,只能依著某種不可理喻的前因後果,出生在某個特定時代的某個特定場所,被囚禁在擁有各種「不完整」的這個稱為「我」的存在中,度過一生。這個沒得挑選並且只能活著走完的人生,經常壓得我們喘不過氣。
當人因某個什麼而感到受傷,或被某個什麼傷害時,就會先陷入沉默。用力地忍耐並撐住。或者,反射性地發怒、咆哮、駁斥或瞋目怒視,有時甚至拳腳相向。
但,我們也可以笑。
無論是在難熬時,反射性地笑出來,或是以當事人的身分,做出自我貶抑式的嘲笑,我想,這兩種選擇,都是人類的自由。人的自由,跟那些人的無限可能、偉大的自我實現之類的議題都毫無關係。人的自由,不存在於那種雄偉、英勇的故事中。
至少我們在最難熬時,還保有笑的自由。就連處在最艱困難熬的狀況之時,我們也擁有不被那狀況困住的自由。「人是自由的」,這不是指我們擁有眾多的選擇、眾多的可能性,而是當我們被逼入現實的死角時,還有最後一樣東西留在那兒,沒有被剝奪。那就是所謂的自由。
這不只發生在當事人身上。語言不單單是工具,語言有血有肉,被劃破就會淌血。當一個人將那些語言「接收下來」時,他就不再是事不關己的他人。
傾聽一個人的故事,就是踏進一個人的人生之中。
聽到悲慘故事而笑的這個習慣,我一直改不了。最近,在貧困地區等進行各種援助活動的人,經常對我說:「我遇到一個岸先生應該會喜歡的故事。」往往聽完之後,才知道是充滿貧窮與暴力的悲慘故事。「其實我也沒有喜歡這種故事啦……」好像是因為我在聽那類故事時,經常不自覺地邊聽邊笑,所以才遭到誤會。
很難說明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笑。當然不是聽到悲慘故事,就加以譏笑的那種笑。但那種時候,我總是會反射性地發出短而尖利的乾笑聲。
我聽到他人受苦的故事時,當對方遭遇愈悲慘,我就愈不想輕易落淚或生氣。或許受到悲慘故事翻攪的情緒,最後找到的出口,就是化作笑聲脫口而出。
有一本名為《自殺》的書,出自作家末井昭之筆。末井的母親,年輕時和情夫以炸藥殉情。他的母親被炸成了碎片。有段時間,他一直不敢將這個經歷告訴任何人。但某次他鼓起勇氣,說給作家篠原勝之聽,結果篠原邊笑邊聽他的故事。從此,末井對於說出那件事,就不再感到如此沉重。
我並非想表達我的笑和篠原的笑一樣。我只是在想,那時候篠原勝之如果是「刻意地笑了」,結果又會如何?恐怕是讓末井受到更深的傷,從此再也無法向任何人說出那件事,而那本出色的作品,也不可能誕生了吧!
雖然只是我個人的猜測,但我想,篠原勝之既非嘲笑這個故事,也不是覺得那是個有趣的故事。只是聽到那樣的故事時,不知道除了笑,還能做什麼。
陷入難受的狀況時,我們可以一味地承受痛苦、硬撐、咬牙忍耐。這麼一來,我們就會變得愈來愈像「受害者」。
或者,我們也可以正面迎戰,提出反駁,訴諸各種手段,設法翻轉事態。這時候我們會變成「抗爭者」。
但我們也可以避開這些選擇。在怎麼也逃不出的命運中,不小心洩漏出的有失體統的笑,是一種「人的自由」的象徵性表現。而這種自由,既存在於受害者的痛苦中,也存在於抗爭者的英勇奮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