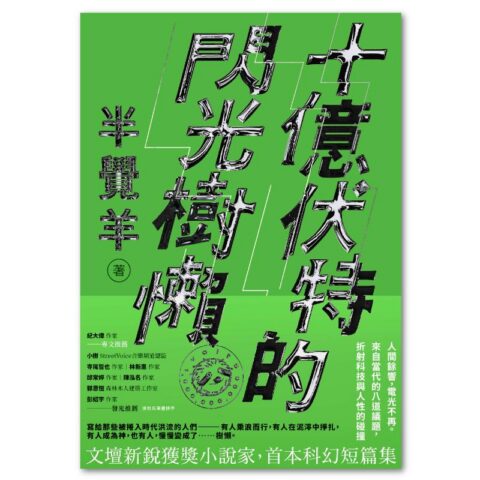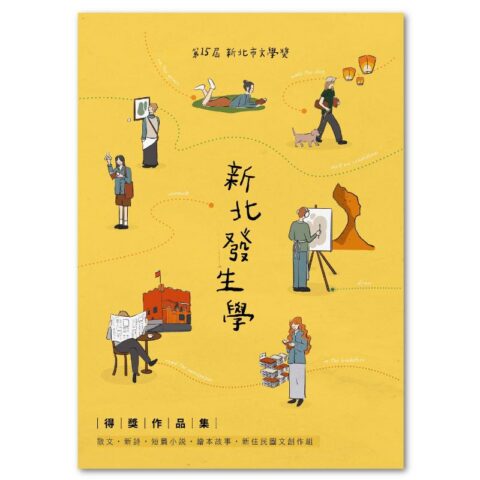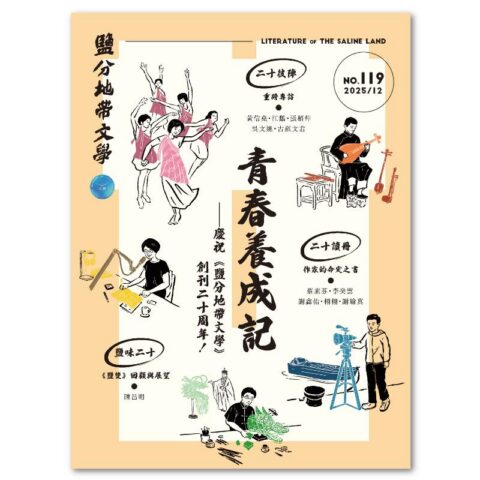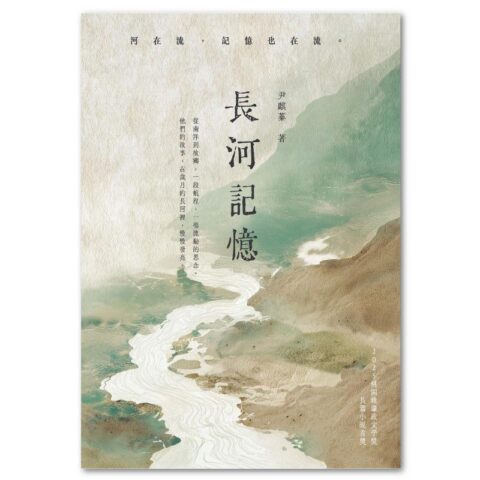冰心玉壺:李一冰文存
出版日期:2022-12-08
作者:李一冰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66100
系列:李一冰作品集
尚有庫存
一窺《蘇東坡新傳》作者的祕密寄託,
了解大時代文人的困頓、掙扎與奮鬥。
他,是「寫傳記的人」。
一生拂逆困窘,卻仍孜孜矻矻,筆耕不輟。
書寫歷史、描摹人物,以故事遙寄自身、映照大時代。
尋找李一冰
1983年,《蘇東坡新傳》出版,成為風靡不墜的中國古典詩人傳記經典,但作者李一冰是誰、生平如何,竟無人知曉。這位像蘇東坡一樣「自喜漸不為人識」的神祕作者,在後人的熱忱追尋下,終於補足這些空白,著作與作者合璧為一,展現了李一冰創作的多重性,也挖掘出他在時代變動中動蕩、甚至遭誣陷下獄的曲折人生。
熱愛歷史,寄情於文
李一冰半生坎坷流連,讀書寫作是他唯一的寄託及慰藉;其執筆所書,已然遠離「研究」,而臻於文學境界。這些文字冊頁留下的雪泥鴻爪,記錄了他一生與命運掙扎奮鬥的心路歷程,書寫的永遠不僅僅是別人的故事。
在人生最困頓的時期中,數不清的暗夜裡,李一冰伏於案前振筆疾書,試著以自己的角度回望歷史,著墨的對象,除了已成專書的蘇東坡與張蒼水外,更遍及王昭君、史可法、陳圓圓、汪水雲……等,可以想見,其與書寫人物的生命是如何連結。
揭開不朽之作 著者的神祕面紗
本書集結了李一冰早年(1950—1960)在臺灣發表過的文章,以及若干尚未刊印的文稿,並收錄其子李東、李雍所撰寫之〈前言〉,書末則附〈李一冰先生自敘家世〉,揭開寫出《蘇東坡新傳》、《張蒼水傳》等不朽名書之作者的神祕面紗。
作者:李一冰
1912-1991,原名李振華,以「一片冰心在玉壺」之意取筆名李一冰,浙江杭州人,原籍為安徽。畢業於浙江私立之江大學經濟系,後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陸續於新文學重要刊物發表白話散文。
民國36年(1947),隨叔叔李辛陽來台,於經濟部物資調節委員會擔任科員。民國40年(1951),不幸捲入弊案成為代罪羔羊,判處八年徒刑定讞,然因未收到拘禁通知而未入監。56歲時遭索賄未果,遂被重提前案,監禁四年後假釋出獄。
獄中四年,李一冰熟讀蘇軾詩作兩千多首,同時整理《東坡事類》、蘇軾年譜等重要書籍,於民國68年(1979)寫成《蘇東坡新傳》,共計七十餘萬字。另著有《南明一孤臣:張蒼水傳》。
前言/李東、李雍
王昭君的悲劇
玄奘出國以前的困學
玄奘曲女城之會
新羅的花郎
蘇東坡的俗語入詩與詩成俗語
罨畫溪
宋人與茶
南宋琴師汪水雲
從衝冠一怒為紅顏說起──為陳圓圓訴不平
史可法與馬士英
民族詩人張蒼水
明末縱橫浙海的張名振
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
前哨金門說魯王
明永曆流亡緬甸記
羅兩峰畫鬼
白石老人的苦學和成名
湖南碩儒葉德輝
附錄
怕太太的故事
臺灣啤酒史
參觀《北宋景祐監本史記》影印記
自敘家世
本書各章出處一覽
前言
先父李一冰先生的名著《蘇東坡新傳》,一九八三年出版於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四十年來,不斷有讀者探詢此書作者之生平及相關著作。透過讀者的回應,讓我們深深感覺到,仍有眾多的讀者賞識此一鴻篇巨著對蘇東坡生平資料的嚴謹考證,並且欣賞此書以古樸典雅的文字,精簡洗練的語言和文采斑斕的風格,表達出令人共鳴的綿密情感。因此之故,我們覺得有必要將先父早年(一九五○-一九六○年)在臺灣發表過的文章,以及若干尚未刊印的文稿,都為一冊,以饗讀者,此即出版這本《冰心玉壺:李一冰文存》的緣起。
先父少時讀書,受明、清之際黃宗羲、全祖望等浙東學派大儒影響,頗注重南明史實。一九四七年因緣際會由大陸杭州遷來臺灣,凜於歷史之不斷重演,遂重讀南明史,隨即陸續發表一些研究成果。這本文存中有多篇文章與南明歷史人物有關,其原因即在此。此後,他又遍讀張蒼水所作詩文及相關史料,撰成《張蒼水傳》,以表彰其人繼承並發揚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毅精神。
此文存所收錄的另四篇文章,就是撰寫蘇傳過程中的即興隨筆。其中〈宋人與茶〉發表於一九七五年四月間的《聯合報》副刊。此文久佚,由臺灣韓棠先生代為尋獲,特此誌謝。日本漢學家楠田觀山先生讀到此文後甚為喜愛,並將它譯為日文,發表在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年)八月號的茶道雜誌《淡交》上。楠田觀山先生與先父兩位老人,雖然從未謀面,但是「雁便」(楠田信中用語)往還無間,老輩的文字之交淡如水,清澈久遠。先父謝世後,楠田先生聞訊,立即來信悼唁。
先父於一九八○年來美依親,定居加州,仍繼續日常讀寫生活。由於他在詩、書、畫三方面都有深厚的興趣和學養,因此選定揚州八怪作為研究對象。其後數年,他不斷搜尋有關揚州八怪的詩文畫作、往來書信,為撰寫揚州八怪的傳記作準備。這本傳記的篇章目錄已於一九九○年擬定,共十六章,一九九一年開筆寫成其中一章,即本書所收錄的〈羅兩峰畫鬼〉。另有一章殘篇,題作〈厲樊榭與金冬心〉。不料這竟是先父一生文字生涯的終筆。是年十月,他即因心臟衰竭去世,享年八十。
文存中還收錄一篇〈臺灣啤酒史〉,原文發表於一九五○年代的《臺灣銀行季刊》(十卷二期)雜誌,這是一本高水準的學術刊物,收錄這篇舊作,是紀念他在日本明治大學主修的專業經濟學。
此書文章大多完成於先父拂逆困窘之時,而文章則大多描述堅忍卓絕之人物。他並非專業作家,也不同於一般世俗定義的學者。但他在憂患勞生之餘,沉浸於讀書寫作之中,並以此安身立命,至老弗退。這些文字書冊留下的雪泥鴻爪,記錄了先父一生與命運掙扎奮鬥的心路歷程。而他晚年精神境界的寫照,正是文天祥〈正氣歌〉的結語: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在這次重校過程中,有幾篇文章,我們附加了一些注釋和後記,若有謬誤之處,是由於我們才疏學淺,並非作者的本意。
李東、李雍 謹記
■ 從衝冠一怒為紅顏說起──為陳圓圓訴不平
一
以吳梅村一句「衝冠一怒為紅顏」而留名千古的陳圓圓,幾百年來遭受著各種不同的曲解和評騭。其實,吳三桂開門揖盜,像這麼嚴重的國家大事,當然應是親受思宗召對平臺、賜莽玉、賜上方的將軍的責任,一個身如漂蓬、愛憎由人的歌姬,如何能夠分擔這宗歷史的罪過?
崇禎末年(一六四四年),天下大亂,待到流寇陷落京師,明朝的局面本自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其時吳三桂雖還手握重兵,防禦北關,但也並非真有什麼旋乾轉坤的回天之力,他如麾兵勤王,難保清兵不躡蹤襲後,做了流寇與滿清夾擊的對象。何況,他又正如明代一般軍閥一樣,際此動亂之秋,本來即是擁兵關外,靜觀時變的動搖分子,哪裡有什麼忠君愛國的抱負!滿清方面對吳三桂的誘約,早於流寇的攻陷京師;清方所派的說客祖大壽,原是吳三桂的舅父,據說這位舅舅曾代表滿清應允外甥,許以事成之後,平分天下。然而,那時候明朝的根本尚未塌垮,三桂本人總還不失是個世家子弟,一時裡他還不敢干冒「夷夏之辨」的大不韙,因此對舅父的勸誘還在逡巡卻顧之中,猶豫未定。
後來,李闖王得了京師,思宗既死社稷,局面大變,於是,三桂為要保全自己的富貴尊榮,非得在此兩大之間,有個趕快的抉擇不可;不過這所謂抉擇,他的趨向,亦屬非闖即清,若不從賊,即須投外,這時候,在他心目之中,本來早已完全沒有大明正統的影子存在了。
他的家被流寇籍沒了,他不怕;他的父親吳勷被闖王拘執了,他不怕,他擁有十萬邊軍的資本,不怕舉大事,爭天下的闖王不來招撫他,他的富貴尊榮依然逃跑不了的。吳三桂的看法果然沒有錯,他父親代闖招降的手書來了,闖王對他軍隊的犒賞四萬金也捧進大門來了,他已率兵入關,行將改幫李家新朝去定鼎中原了。
吳梅村說:衝冠一怒是為了陳圓圓,其實事情斷沒有這樣簡單。吳三桂是個非常容易衝動的人,固是在許多地方可以看得出來的;但這最多不過是他中途變計的一個表面上激發的因素而已,就事實來考察,至多他從圓圓的被據,證實了李自成等到了京師以後,那種打家劫舍、衣冠塗炭的作風,使得含有貴族血液的吳三桂,不得不憬然觸悟過來,他是不值得做闖王麾下的嘍囉的。
於是,他就借著圓圓被擄這一節衝動,突然變計了。這一變本就變得非常具有戲劇性的效果,如明末清初人錢倁軹撰《甲申傳信錄》所述,其人其事,其情其景,都還栩栩如生:
三桂妾圓圓,絕世所希,自成知之,索於勷,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勷從命,闖旋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大喜,忻然受命,入山海關而納款焉。
行已入關,吳妾某氏,素通家人某,闖借其家,家人即掣妾逃,倉皇出都,行數日,竟不暇計南北也。
二人猝遇三桂,計無出,詐曰告變,三桂問曰:吾家無恙乎?曰闖籍之矣。吾父無恙乎?曰闖籍之家並拘執矣。三桂沉吟久之,厲聲問曰:我那人亦無恙?指圓圓也。曰賊奪之。於是三桂大怒,嗔目而呼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顏面?勒馬出關,決意致死於賊。
於是有吳梅村〈圓圓曲〉詩的譏責:
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這都不過是文人的一誇張手法而已,把事變的關鍵放在一個絕色的女人身上,容易動人心目,輕描淡寫之中,把這將軍不忠不孝的面目,十分地烘托出來了。所以,梅村此詩一出,三桂大為狼狽,願酬重幣千金,求取此詩,然而梅村不許。就文字而論,實在通暢淋漓,痛快萬分,縱論事實,吳三桂當時雖然確有「衝冠一怒」的表現,然而,這麼一件變換歷史命運的大事件,其轉變之機,豈真是一個陳圓圓即足以完全左右變更的?大家把一個軍閥對於歌姬的玩好太看重了,三桂當時若沒有另一條「漢奸」的後路可走,還不仍然乖乖地做了闖王的嘍囉。陳圓圓呢,自來美姝名馬,都不過是將軍們的玩物而已。
二
投靠李闖之計中途突變之後,吳三桂的出路,非常自然地由他舅舅搭線,另外扮演了一幕「請清兵」的好戲。吳三桂到底是聰明人,他還揭舉著「借兵復仇」的美名,一副孤臣孽子的扮相。甚至如當時有神童之目的夏允彝,也被他瞞過,《倖存錄》有曰:
三桂即大壽甥也。其父吳勷,向為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所以誘致之者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已破,以殺寇自矢,包胥復楚,三桂無愧焉。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東夷而東夷遂吞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
清兵入關以後,就永遠占據不去,或如夏允彝所言,竟非吳三桂始料之所及,也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但如看到後來南明的弘光政府遣使北上犒謝清兵代逐流寇之勞,同時封贈三桂薊國公,他竟薄此小朝廷的榮典拒不肯受的表現,就可明瞭一切。開門揖盜的奴才,他又興高采烈地做了強盜的先驅,初則追逐闖軍至西蜀,繼則逼迫緬甸交出流亡的帝子─永曆,縊殺於昆明市郊,凡此種種,又豈是為了癖愛陳圓圓,才非如此不可的呢?一個去留不由自主的陳圓圓,不幸適逢時會,便陪著這位白皙通侯的少年梟雄,分擔了他的惡名而已?
自從「衝冠一怒為紅顏」這句話,硬把陳圓圓拉入吳三桂叛國事件中去後,詎料中經三十餘年,久已做了滿清政府詔封的平西王,忽然又要扮演一齣「狐埋狐搰」的好戲,重新撿拾「朱明」的舊行頭,鑼鼓登場了。
吳藩事變的發生,時在康熙十三年癸丑(一六七四年)。按《三聖庵畫像記》說圓圓生於明熹宗天啟三年癸亥(一六二三年),她歸吳三桂時正在二十一、二的盛年,至三桂叛清,她則已是五十老嫗了,而且她到滇南未久,就離開了平西王府,與三桂早已形跡疏遠了。然而名女人逃不開閒是閒非,古今如出一轍,依然不能免於為人攀扯。如陸次雲《圓圓傳》,即曰:
(吳三桂)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塢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
陳圓圓在平西王爺座前,捧觴獻歌,這是她姬妾之身的份內事,像吳三桂那樣一個年少風雲的軍閥,慣以英雄自命,圓圓為歌大風之章以媚之,這也是一個伺人顏色的女人的本分,都可以相信是曾經有過的常事。但是,如要把這些節目統統歸扯到發生於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的吳三桂謀反事件上去,則無論如何會變成非常可笑的說法。
三
吳三桂的叛變,是滿清政府撤藩之議逼出來的,因為撤藩政策一經實行,不但他那滇南王安富尊榮的基礎完全打翻,而異族統治者「飛鳥盡,走狗烹」的命運,尤其可怕,所以,他的叛謀是倉卒而起應付撤藩手段的最後一逞,並非積數十年深謀遠慮的結果。然而,在那時候,陳圓圓已經是五十老嫗,如何能夠想像她還有歌衫舞扇、檀板金樽的魅惑力量?
吳三桂封了藩王,志得意滿,就將明代西平侯沐國公的西平別墅沒收下來,改築野園,窮極侈麗,度著金迷紙醉、醇酒婦人的享樂生涯。
據說,三桂從賊寇中尋回圓圓以後,是帶著她同征西蜀的,但是她到昆明王府時,則已年逾三十了。其時,三桂正妻已死,本來據說是想將圓圓扶正妃位的,然而,圓圓秀外慧中,她有一般女人不易自知的「色衰愛弛」之明,堅辭不受。
縱如圓圓是個絕代佳人,也奈何不得無情的歲月,以色侍人的她,不能沒有遲暮之感。吳三桂續娶張氏,又非常悍妒,而三桂則仍然廣置姬妾,佳麗如雲,有四面觀音、八面觀音、十二面觀音、二十四面觀音等稱謂,以圓圓的聰明,以圓圓在男女關係上所經歷的非比尋常的艱苦,她何必再在少女堆中去爭妍鬥寵;她既辭妃位,沒有再在王府惹人忌妒的必要;加以三桂的為人,我們尤不能想像他能專愛於一個過了中年的婦人,「數十年如一日」。所以,陳圓圓在平西王別邸─野園住了並沒幾年,便無視於滿目繁華,從萬般憂患參透人生,歸於淡泊的她,求為女冠出家去了。
距三藩之變發生前一、二年,久已做了道士的陳圓圓大約早有另一暴風雨丕然將至的預感了,她是個艱危的大浪中翻撲過來的人,時則年已半百,尚又何求?她抱著入山唯恐不深的心情,所以又毅然離開了比較接近世務的道觀,改從玉林禪師在宏覺寺裡剃了頭髮作了女尼。法名寂靜,號玉庵。
陸次雲說她「同夢之謀」時,還在滿清統治之下,這罪名簡直就如誣她共同謀反,對於像陳圓圓這麼一個荏弱而淡泊的女子,實在未免不仁。但後來也有人以為吳三桂的叛清出於她的慫恿,認為圓圓是個頗有民族氣節的女人,特別在對日抗戰期間,曾有好多論客作著如此的禮贊,如一九三九年姚安張根培在傳說中圓圓自殉的蓮花池畔,豎碑留念,碑文裡就有「圓圓身為女子,恥為漢奸妻,是有民族意識者」之類的話,其實這也是無端的揄揚,大可不必。
圓圓出了王府大門以後,雖非絕情而去,但與三桂往來蹤跡之逐漸疏闊,當是事所必然,不難想像的。後來她索性披剃為尼,目的為了全身免禍,自然更加有意的潛蹤韜晦起來,唯其如此,到吳三桂失敗時,縱然陳姬聲名猶豔人口,但以滿清爪牙之銳利,她卻還能保持清磐紅魚的生活,不再遭受這場災禍的牽惹。如鈕玉樵《觚剩》有一則,最接近事實:
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圓圓本姓邢,字畹芬)窺其微,以齒暮請為女道士。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段,戊午,滇南平,借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艫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
據《三聖庵畫像記》,圓圓死於三聖庵,為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一六九五年)七月,享年七十三歲,距三桂之死已十七年。但是另有一個傳說,則她是自投於昆明北郊的蓮花池裡殉難的,兩者孰是,雖還沒有定論,不過清廷抄吳三桂家,籍沒的婦女名單中沒有陳圓圓在,而她是以女尼之身畢命的,似乎已無疑問,蓋美國女作家溫德賽尋求娘娘墳,認為在昆明南郊五里許歸化寺旁的最為確實,墓碑中題「開建三聖堂太戒比丘尼上寂下靜玉庵公老禪師墓」。左右更有聯云:「塵劫中不昧本來朗月生性海;迷陣裡能開覺路青蓮淨孽根。」雖是佛家常語,但用來總結圓圓的生平,真令人有非常恰當之感。
四
通常一個歌伎出身的女人,她的生平,居常完全是表現在男女關係的結合上,陳圓圓自然並不例外。
俗語說,「紅顏薄命」。圓圓也正因其天生麗質,造成她悲劇的一生。她既不幸生為「玉峰歌伎」,又不幸而具有「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的條件,生於明末這麼一個混亂激變的年代,所以一開始她便成了豪紳、皇帝、軍閥甚至流寇大王們爭奪的對象,歷受那些擁有一等權勢的男人們的播弄,還不是一片因風吹舞的飛花?雖然顏色美麗,但是何等的淒涼與漂泊,哪裡能夠自己做得主宰?無非隨著命運支配,去伺候各種不同的面色,來換取微末的生存。
陳圓圓最早的知遇,似是明末四公子之一,江蘇如皋豪紳兼大名士的冒辟疆。冒公子為奔父喪,在歌場邂逅圓圓,驚才詫豔,稱她「蕙心蘭質」,以她的淡雅風華,為跌宕花叢的生平所僅見。據自撰《影梅盦憶語》中說圓圓對他也頗傾心,自此定情;只是因為冒在喪中,不便納姬,所以約期而別。
不料未久,思宗妃父田畹遊江南,一見圓圓,又以為真不愧是國色第一,他抱著政治上競榮固寵的私心,便要收買她來,預備獻給宵旰憂勤的皇帝。事為冒家知悉,自然不肯放棄。明朝末葉,高門華族的紳士橫行鄉里,是具有非常深厚的地方勢力的,並不因田畹是皇親國戚而有所顧忌,所以當圓圓油壁香車被載啟行時,冒府家丁和田皇親的隨從還轟轟烈烈地演出過一場「劫美」的械鬥。結果是冒辟疆被打敗了,圓圓歸於田府。
幸而皇帝求治心切,無意風情,圓圓才得免於入宮。如吳偉業《鹿樵紀聞》所述:
初,上寵田妃,妃殁,上念之不置,戚田畹弘遇欲娛上意,遊吳門,出千金市歌姬陳圓、顧壽,將以進御。上知為青樓婦,卻之。
即此袁嘉谷曲所謂「憶昔掃眉入宮掖,殘香不動君王惜」者是也。而圓圓也就此成了田皇親府中的禁臠。
後來,闖師將迫畿輔,田畹為欲保全身家性命有賴於手握重兵的吳大將軍的庇護,所以不得不忍痛割愛,圓圓也因此再從田家轉手到吳三桂懷裡去了。這一段經過,幾乎無人不知,不必贅述。不過陸次雲的《圓圓傳》說,此事的設計出於圓圓,實在未免渲染過甚,通常,一個私家歌姬是沒有身自為謀的自由的。
京師淪陷,吳家也為李闖王籍沒了,田皇親家也為賊將劉宗敏占據了。於是圓圓的命運又翻上一重驚駭的浪濤。一說在亂城中,圓圓是為賊將劉宗敏所得的,如陳維崧《婦人集》說:「圓圓字畹芬,李自成之亂,為賊將劉宗敏所得。」《鹿樵紀聞》說:「賊據京師,劉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譽二姬色之都,技之絕者,宗敏於是繫勷索圓。」一如陸次雲所說,係李自成從內監口中得知天壤間有此絕色,向吳勷索求圓圓,同時招撫三桂,其中有一段極富趣味的插曲:
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歈,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令群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只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
這是三百年前土包子的大笑話。不過,無論為賊將所得或為闖王所要,在圓圓,都一樣的只是「命薄」而已。
後來,如照通行的說法,吳三桂是為了她才投滿清,做了漢奸的,而她也就重新為吳三桂所得了。
從這個樣子的身世中來看陳圓圓,她只是一片可以憐憫的飛花,美麗然而薄弱、飄零、淒涼地忍受著幾許歷史上大混蛋的蹂躪。歌伎陳圓圓怎麼分擔得起歷史的罪責,而永遠被陷在吳三桂的惡名之內。
自梅村而後,歌詠圓圓的大小詩人不知幾許,但我卻最歡喜近人施蟄存的一首:
宮草宮花寂寞香,美人何與國興亡?商山寺下飛鴻影,猶為將軍舞豔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