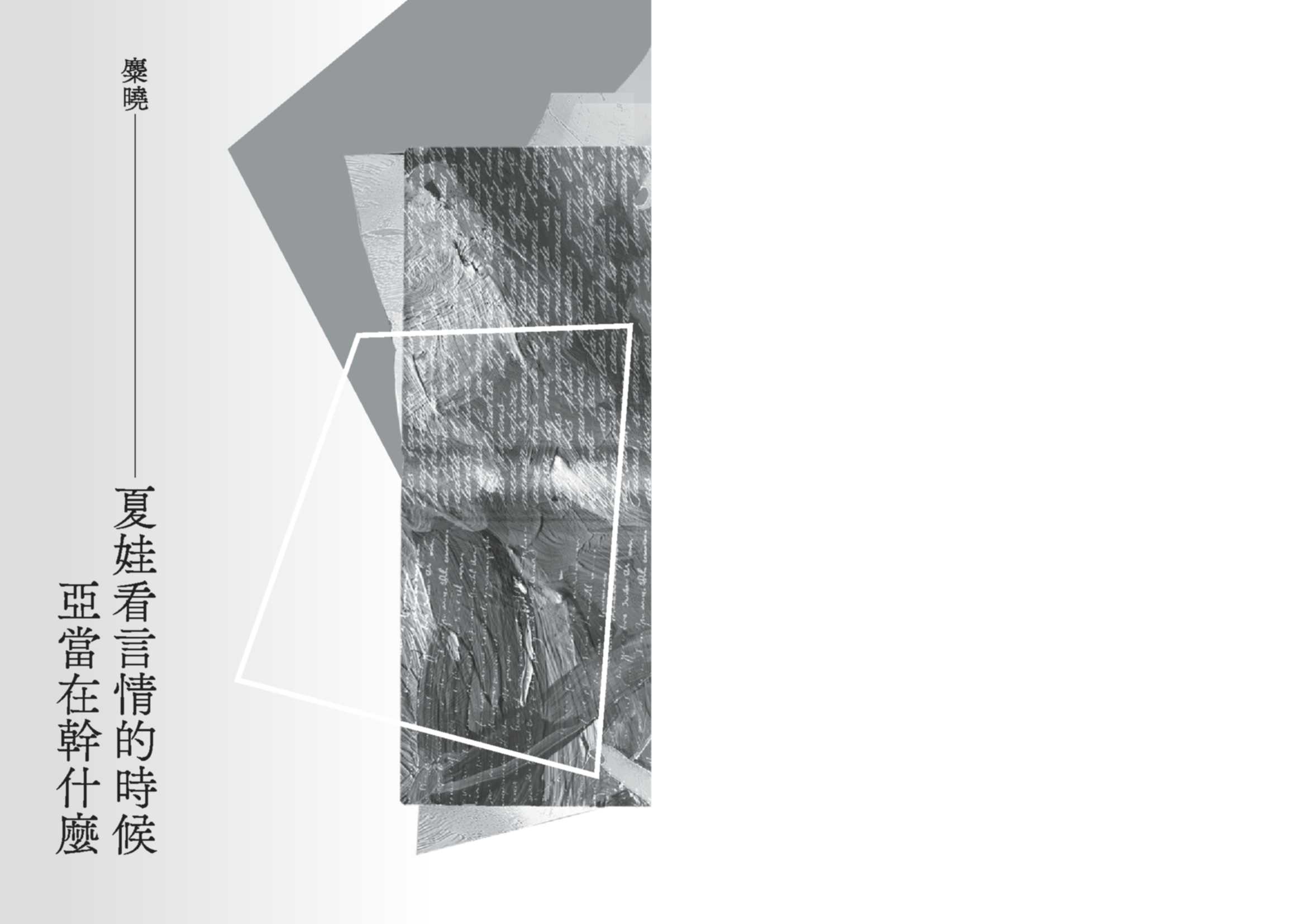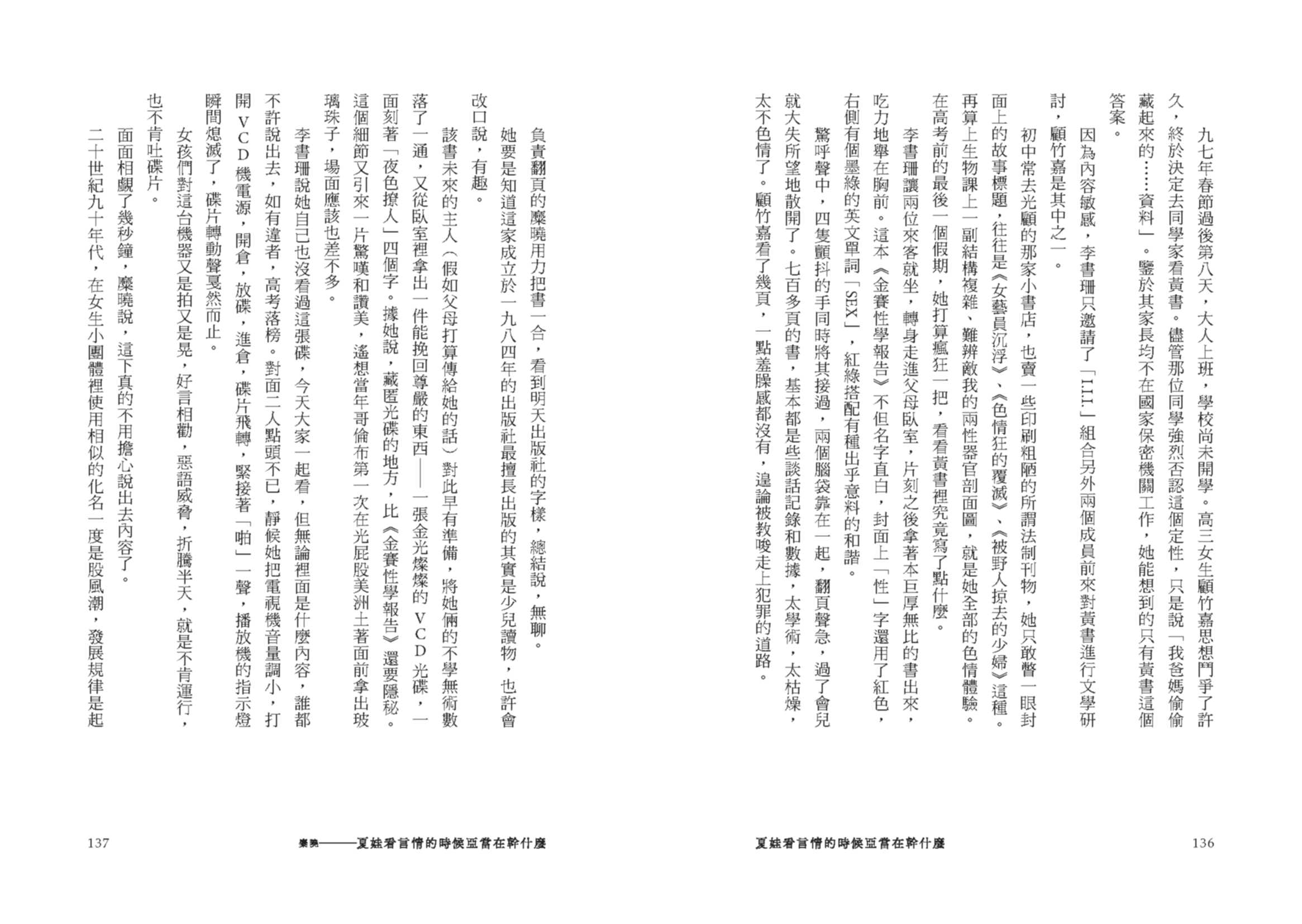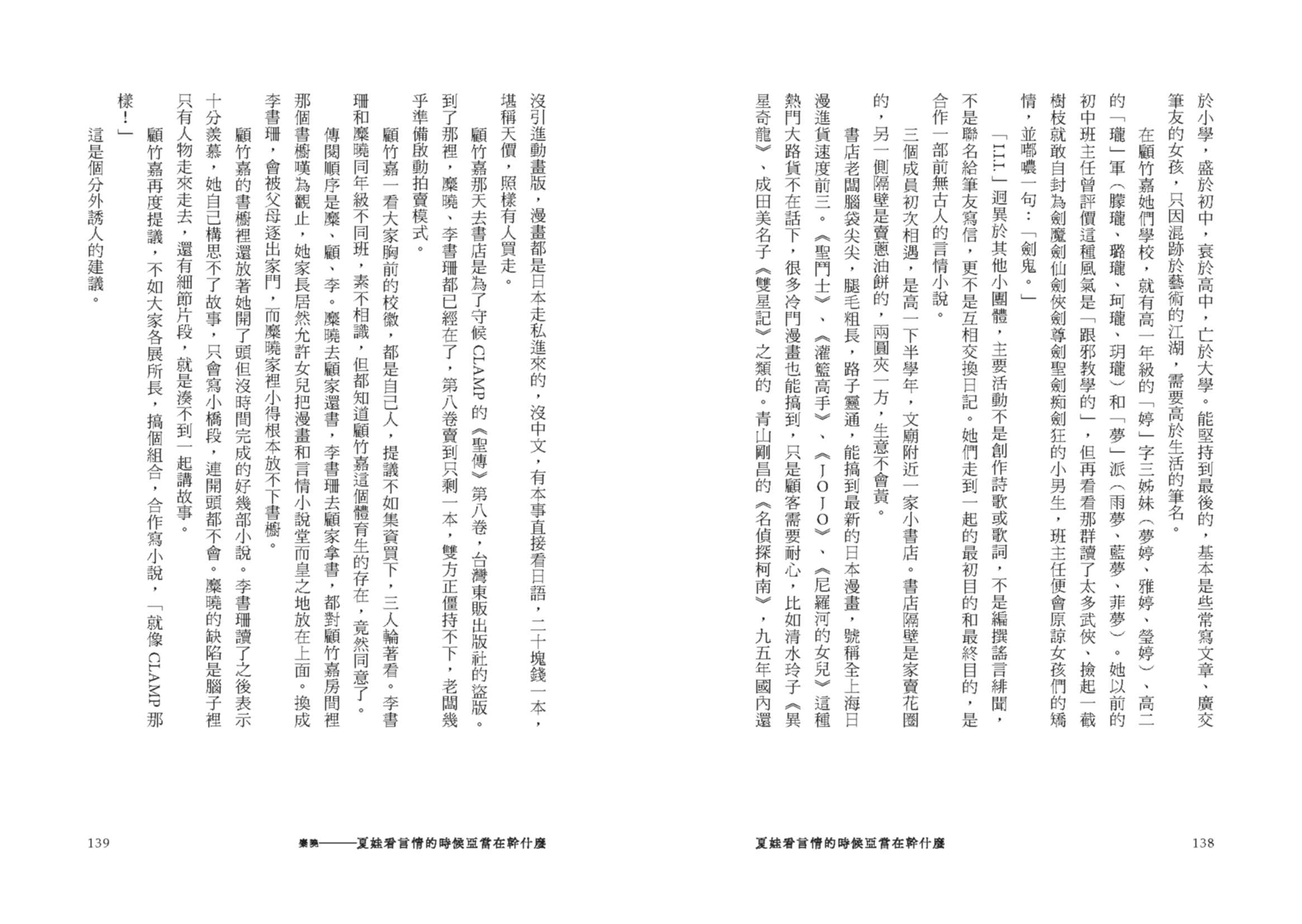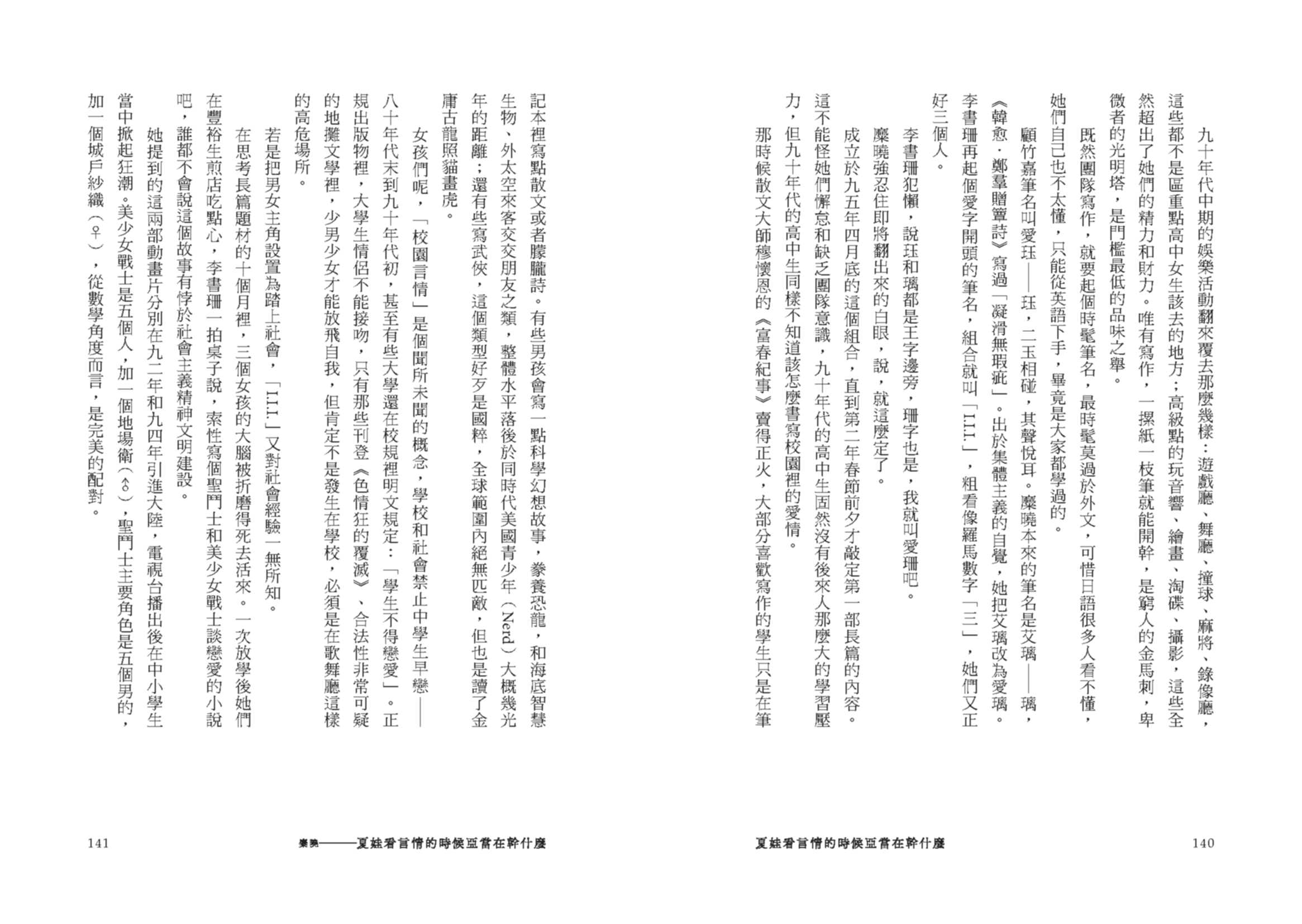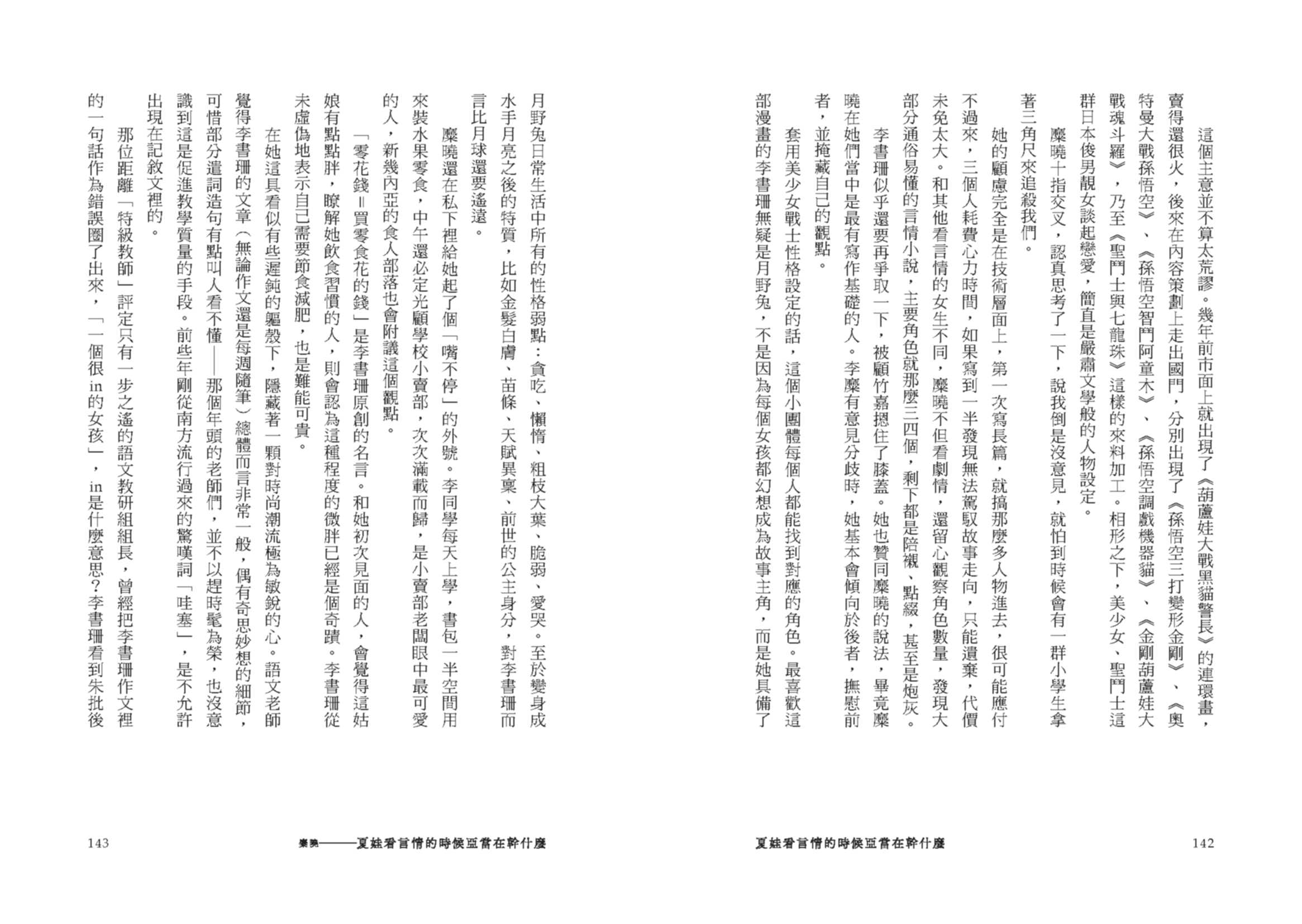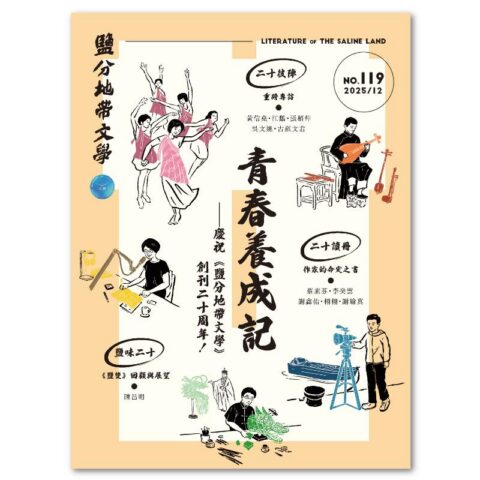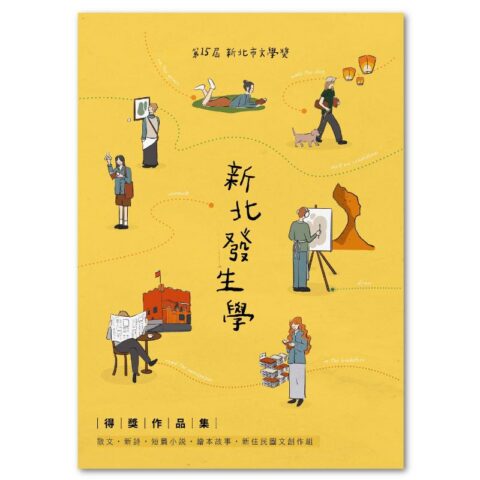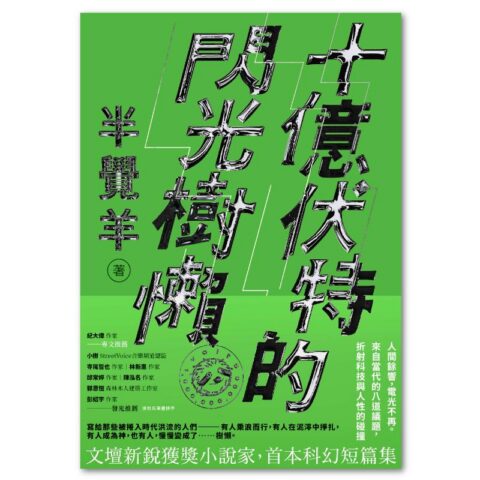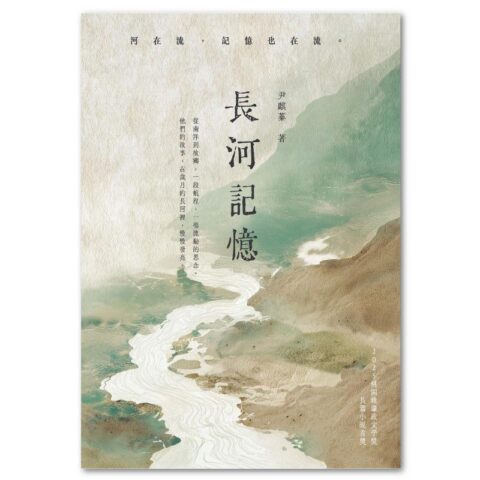夏娃看言情的時候亞當在幹什麼
出版日期:2024-11-14
作者:王若虛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28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1.75cm
EAN:9789570875249
系列:當代名家
尚有庫存
只是「寫作」,卻展現了三百六十度全廣角的書寫盛宴。
平凡而熱烈,這本小說集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文學的原因。
青年寫作者獨有的夢,在這個時代下既赤裸而清晰。這次,不同的夢話可以說給誰聽?
出自書香世家的女孩們是如何藉由寫作在現實中成長?為什麼能在小說中寫性愛是珍貴的一件事,還可以順便報復嚴肅的父親?總是寫不好的男人們,是什麼理由與動機,讓他們非得繼續寫下去,甚至出賣自己只求出書?本書聚焦於文學出版界,並延伸至音樂、繪畫、影視等領域。
以文化產業為主背景,故事中的主角不論男女老少皆擁有一個文學夢,卻並非一味抒情惆悵不得志,王若虛高明的便是幽默犀利同時也能勾起情懷,講寫作是講夢想、講夢想又狠心地戳破美好想像,卻能在幻滅中再度看見那火苗燃起,感受掌心的溫度後,依舊惦記著文學的重要性。
作為短篇小說集,卻以人物作為主軸,聚集數十位性格鮮明的主角們,並透過人物的故事續寫、穿插、倒轉、家庭影響,來串起故事的完整度,像一睹軀體的全面後也能深入窺探骨骼的模樣。
王若虛以此小說,將世紀交錯的文學時代現象濃縮成或重或輕的情節,色彩繽紛,是文學背後一路走來的興衰姿態,也是多數書寫者同樣經歷過的感觸。飽滿的閱讀氛圍,帶領讀者穿越世紀末的文學博覽會。
▌好評推薦
陳莉文│作家
張桓溢│作家
田家綾│專欄作家
作者:王若虛
男,1984年生,畢業於上海大學經濟學專業。《馬賊》、《尾巴》、《限速二十》、《火鍋殺》等7部,中短篇小說集《在逃》、《守書人》等4部。作品見於《收穫》、《人民文學》、《當代》、《青年文學》、《上海文學》、《小說界》、《小說月報》、《芒種》、《萌芽》等雜誌。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九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曾獲第四十一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獎和首屆「澎湃.鏡相」非虛構寫作大賽一等獎。
▍商隱
同小姐
光環
▍糜曉
夏娃看言情的時候亞當在幹什麼
▍王謝
床笫之美
誰要看安部公房
▍鹿原
沒有書的圖書館
▍秦玉璽
腰封無用
前言
可能是在二○○九年冬天,我剛完成了長篇小說《限速二十》的創作,大學交通工具長篇三部曲告一段落(另兩部是《馬賊》和《火鍋殺》),打算寫一個全新的系列,將視角對準八十和九十年代出生的寫作者群體,他們所面對的時代變化,機遇和挑戰,史詩和悲歌。
我深信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裡,中國最年輕的那批寫作者一直身處於史無前例的發展時期,少年作家出書、青春文學興起、電子雜誌、MOOK 主題書、同人寫作、圖片小說、博客連載、火星文體、一百四十字短小說、網路文學、粉絲電影、IP熱、新媒體寫作,還有層出不窮的版權糾紛……幾乎每一兩年就要刷新一次對舊事物的認知。
如果沒有同時代的人用筆描繪這幅波瀾壯闊的圖景,那就太可惜了。這就是為什麼二○一○年十月我發表了第一部該系列的短篇小說〈微生〉,系列名「文字帝國」,來自其中一句對白:
「文字的世界就像個大帝國,從來沒有人能成為帝王,每個作者在這個帝國裡都像一個小小的漢字,也許常用,但絕不是唯一,更不會說它就是最好的。」
我自己也許只是這世界裡的一個邊旁部首,但想做一件前人未曾做過的事情,若干中短篇和長篇小說來勾勒一幅畫卷,即整整一代寫作者的風貌和境遇,無論是他或她是功成名就還是沒沒無聞,是流芳百世還是飽受爭議。
如果讀到這裡你覺得以上表述太正式太複雜,那就請把它理解為《中華小當家》的大宇宙燒麥,或者胖虎大雜燴。
「文字帝國」是無數生活原型的重新排列組合,是虛構作品,每個角色的行為和台詞都經過了分解、轉化和不負責任的胡亂搭配,請讀者朋友們不要做無謂但十分有趣的真相連連看。
本書是該系列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也是我的第三本短篇集,因為版權關係,最早期的〈微生〉和〈瘋女王〉未能收錄其中。用作書名的《夏娃看言情的時候亞當在幹什麼》曾是○八年寫的另一部小說的名字,沒有發表,機緣巧合下用到了文字帝國的短篇裡。
夏娃,亞當,意味著一個開始,長篇《逐鹿》、《八卦賞析》和短篇集《宿敵》在創作中,由於我飄忽不定的寫作速度,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和讀者見面。
在這裡要感謝陳麗麗為〈光環〉提供關於華師大老宿舍樓的資料,〈光環〉中商隱的詩歌均由上師大的錢芝安創作。感謝《萌芽》、《小說界》雜誌長期以來對我的指導和幫助。
最後,將本書獻給我的兩位外公。
鹿原──沒有書的圖書館
老先生每天上午必定要抽的六根香菸,總是被他提前從菸盒裡取出來,在桌角一根根擺好,平頭齊尾,間距相同,像支訓練有素的行刑隊,槍口對外,瞄著一隻廉價的打火機。正式享受之前,菸必須在嘴裡叼一小會兒,再拿下來,捏住尾端輕輕一旋,整個過濾嘴就下來了,菸紙卻絲毫無損。點菸前,他還得用拇指把斷口處的菸草壓壓實,似才放心。老先生習慣鼻子出煙,兩股濃霧在他下巴尖匯成一條白龍。接著就聽輕輕一聲「哱」,沾在舌尖的菸末便不知所蹤了。
坐在屋子另一邊的鹿原總是停下手中的筆,靜靜觀看老先生點菸前後的每一個動作,暗自期待他哪怕有一次不遵循這套流程。鹿原毫不懷疑,十年下來,屋子裡的每一張紙都散發著香菸味兒,尼古丁和菸焦油是這些作品的忠實讀者。作為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允許抽菸的圖書館,它只有一個小缺憾—沒有書。
鹿原第一次聽說這個圖書館的時候,正在北京東城的一間地下室裡靜待發霉。他進京是為了追一筆債,順便感受一下首都的環境。可欠他一萬塊策劃費和五千塊稿費的那王八蛋手機一直關機,出版社說錢我們早就給他了,房東說他早就搬走了,北京幾個圈內朋友說他可能南下了,具體是去深圳還是長沙不太清楚,也有可能回老家了。鹿原毫無頭緒,也不知道接下來該去哪裡。為了省錢,他每天用借來的電磁爐煮掛麵,拌上超市買來的滷肉醬,一天吃兩頓,一頓吃半斤。○三年時的北京,天氣還沒那麼糟糕,白天裡他就蹲在外面曬太陽,邊上躺著斷尾巴缺耳朵但神情安逸的野貓,與他的愁眉苦臉相映成趣。來京之前他躊躇滿志的那部小說,如今也交給小腦去構思了,大腦就負責想接下去該怎麼辦,我自己還欠著別人錢。他兩三天刷一次牙,很久沒洗澡,但這並不可怕,那些和他住在一起的群眾演員、流浪歌手、大學應屆生都這德性。愛乾淨的是那些從全國各地陪孩子來北京上各類藝考培訓班的家長,事兒多,嘈雜,還不好惹。有一天他在公用廁所裡刷牙,看著鏡子裡憔悴又疲憊的自己,更像那幫砸鍋賣鐵也要幫孩子實現明星夢美院夢的玩命家長,心想,我他媽才二十一啊!
就是這個時候三酒從鹿原堂妹那裡知道了他的窘境,打公用電話過來,說要不你來紹興吧,我知道一家私人圖書館,可以讓他們請你去幫忙,包住宿,環境挺安靜,你也可以寫寫東西。三酒在他朋友當中還算靠譜,「能寫東西」這四個字對文學青年鹿原來說也具有足夠大的吸引力,當下就答應了。他事後也沒想到去網上查查看紹興到底有沒有私人圖書館。隔天三酒又來電話說搞定了,你趕緊來吧。鹿原問房東摳回了一點押金,買好了硬座車票。臨走那天他去胡同口的小理髮店剪了頭髮刮了鬍子,到公共小澡堂洗了個澡,在火車站小賣部消費了三袋方便麵、一瓶紅星小二和一盒點八中南海,為狼狽的首都之旅畫上了一個還算體面的句號。一路晃蕩了二十多個小時,他在杭州下了火車,在候車大廳趁機睡了兩小時,再坐長途到紹興,根據紙條上的指示乘坐公交車,終於找到了東小路和五脂巷,然後傻眼了。這是一條太不起眼的巷子,狹窄的路面用碎石板拼成,潮乎乎的,縫隙間能看到青苔的痕跡。兩側舊式民居最高不超過兩層半,黑瓦依舊,白牆已經發黃。巷子裡面彎彎曲曲,看不到幽深的盡頭。仔細觀察巷口,沒有任何標識牌告訴路人這裡面有座圖書館。越往裡走兩步,鹿原的疑惑更重了,此地聞不出書香,倒是從哪戶人家的廚房裡傳來一股油炸臭豆腐的焦香。但紙條上記的地址就是這裡沒錯,五脂巷二號甲二○一。
鹿原正猶豫要不要上去問個明白,樓門裡走出來一個中年男人,臉色黑黃,戴著一副八十年代流行過的那種大鏡片金屬框眼鏡,親切地問:「你是小陸吧?」鹿原趕緊點頭說是是是,您是岑老師?岑老師邊「哎」著邊和他握了握手,但沒有要幫著提行李的意思,說我在二樓窗口看到你走過來的,看樣子就像,來來來,跟我來,當心,這裡有道東西。鹿原跨過防止雨水倒灌的水泥門檻,跟岑老師走在木頭樓梯上。岑老師說我們這樓梯比較老,你抓好扶手,抓好,這樣比較穩。不出所料,台階前後很窄,腳尖踩到底,還有半個腳後跟是完全懸空的。他老覺得屋頂要壓下來,不自覺地矮著身子,怕什麼東西會忽然砸到頭。整棟樓的空氣裡有股叫人無法忽略的糖醋小排的氣息。他還走在半路,岑老師已經拿出鑰匙,開了樓梯盡頭的一扇門,打開燈,說進來進來。
鹿原背著書包、提著行李袋,走三步要找一下重心、調整一下呼吸,覺得自己不是個求職的圖書館管理員而是白色恐怖時期在上海灘尋求庇護所的我黨地下工作者。他好歹走完了這條樓梯,可以好好看看那個傳說中的私人圖書館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老先生抽菸很快,去掉了濾嘴的菸,抽個五六口就得掐掉,不然就要燒到舌頭了。他不用手指縫夾菸,而是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三個指尖攥成個香爐底座,菸身一柱擎天,菸頭直沖天花板。他左胳膊肘又喜歡支在桌面上,菸就和腦門處在了一個水平面,加上低著頭看文章,遠望去,像是個抽菸被抓了現行的學生,正低頭認錯,把作案工具上交老師。菸灰要是飄落到紙上,他絕不用手撣,大概是怕在白紙上留下灰痕,只用嘴吹,偶爾也把整張紙捏起來輕輕抖動。
這裡保存的作品可以說是一文不值,老先生對它們如此愛護,鹿原想,這有什麼意義呢?他瞥了眼屋子裡的三排書架,即使到現在還是沒弄明白,它們是天生就以這種黑鐵的本質示人的,還是曾經刷上過漂亮的油漆,只不過後來被時間慢慢啃食掉了。但至少他已經把它們當成書架看待了,而不是燒焦的遠古怪獸的骨架。他想起自己第一天來到這裡時,被屋子的狹小和書架的稀少給嚇了一跳,頓時有種被三酒騙了的感覺。三酒本人在安排完這件事之後立刻去泰國談生意去了,不知幾時回來。岑老師並未察覺他的詫異,大概以為三酒已經提前給鹿原打了預防針。他拿起桌子上的熱水瓶倒水,說你把行李放那兒吧,來,喝口水。鹿原這時候又不好意思轉身走人,他的體力、他的錢包和他的人際關係也讓他失去了這麼做的資本,只好走過去。
他估計這間「一室戶」不會超過二十五平米,被三個書架一占,大概就剩下五平米了吧?屋頂低矮,日光燈氣血不足,兩張陳舊的書桌分明是學校裡用的那種單人課桌,倒是各配了一盞小台燈。鹿原在其中一張桌子邊坐下,發現桌上有個骯髒的白瓷茶杯,內壁黑得像煤礦坑道,再連繫起空氣中那熟悉的氣息,吃驚道:「這裡能抽菸?」岑老師正在擦桌子上灑出來的熱水,「昂」了聲,手一指。鹿原轉頭看到最近的一個書架的側面貼了張白紙,上面用毛筆寫了六個大字:「此處允許抽菸」。鹿原不懂書法,看不出字的好壞,但這種存心和主流做法對著幹的精神瞬間感染了他。到了這時他才發現一個剛才忽略了的情況—這些書架上沒有一排排豎著擺放的書,全是些紙,一摞一摞堆在那上面,用紅色或白色的塑料繩捆著,乍看上去像等著扔掉的舊考卷。
「那個……」鹿原不自覺地站起身,指著書架問。
「哦,小邱之前沒跟你說麼?這全是我父親收羅的人家的稿子,被退稿的,不能發表的,人家送的,反正都是些沒人要的東西,他就愛這個。」岑老師招呼他再次坐下,「這個是我們家老房子,我父親搬去我那裡以後,就把這裡改成了他的閱覽室,他說叫圖書館,反正他高興就行,這一開也開了好幾年。」岑老師擺手謝絕了鹿原遞過去的菸,說不不不我不抽菸,這個,我父親快八十的人了,但身體還好,他就每天上午會到這裡來,其他時候都需要有人看著,雖然也沒什麼值錢東西,我們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學,沒辦法,只好雇個人,用時髦話說叫兼職,以前找過一個文理學院的學生,但小伙子沒定性,在這裡太冷清,他待不住,就走了。當然,我們給不起很多錢也是個原因。岑老師說到這裡抱歉地笑笑,這個伏筆埋得有點生硬。見鹿原沒有接話,他又趕快轉過風向:「不過你是小邱介紹來的朋友,我是放心的,他說你需要個地方安心寫寫東西,哈哈,我們這裡沒別的好,就是安靜。當然,酬勞也不會虧待你,一個月八百,你看可以吧?」
鹿原一怔,他以為對方最多給個五百了不起,這個開價叫他喜出望外,就差放下矜持起身去握住岑老師的雙手:「可以可以,已經很多了。」這個價格足夠說服他自己,你又不是來當館長的,你就是找個地方過渡一段世界,寫完小說。岑老師說沒事沒事,小邱的朋友嘛。為了確保無誤,他問鹿原能不能拿身分證給他看下。鹿原翻出證件遞了過去,岑老師邊扶著鏡框一側,邊仔細審視,就差把號碼一個個念出來了:「陸篆,這個名字好啊,八二年,喲真年輕,小伙子又那麼帥,啊?哈哈……」鹿原羞赧地撓撓頭,心想無論誰和身分證照片比起來都會顯帥的。岑老師還了證件,又摸出三百塊,說這是預付的錢,你收好,收好。除了問房東要押金,鹿原已經很久沒從陌生人手裡收到這麼多錢了,拿過來正要摺摺好,目光落在岑老師看上去有十年歷史的夾克衫和灰蒙蒙的舊皮鞋上,心裡冒出一個大膽又符合邏輯的猜測。但他沒有多問,把猜測和三張毛主席一起塞進了牛仔褲口袋。
三酒電話裡說的包住,其實就是住在這間屋子裡。行軍床已經備好,就疊放在角落裡,岑老師說邊上的小櫃子裡除了枕頭還有條舊被子,晚上冷的話可以加蓋。喝水有電水壺,就放在桌子上。水龍頭在樓下公共廚房,最靠門口、水管上纏著藍布的那個就是他家的,但水流量有點小。公共廁所要再往巷子裡走五十米,晚上沒燈。「條件艱苦,還請克服一下。」岑老師說。鹿原忽然想起了什麼,小心翼翼地問:「平時……來這裡的人多麼?」
「這個我也不清楚,應該不太多,只有我們家老先生知道啦。」中年男子環顧這間房子,還有那三排最占地方的書架,神情不是剛才的客客氣氣,而是一種無奈。鹿原猜想,要不是父親弄了個詭異的圖書館,這間房子他大概是打算租出去賺點小錢的,也許就專門租給自己這樣的落魄小青年。可他現在卻要付錢給這個小青年,夢想與現實的落差太大。連這個收了錢的小青年也在想,搞這個圖書館,意義何在?不過在岑老師走之前,新上任的管理員還是有點不太放心,畫蛇添足地問了一句:「岑老師,這裡的『書』……我都能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