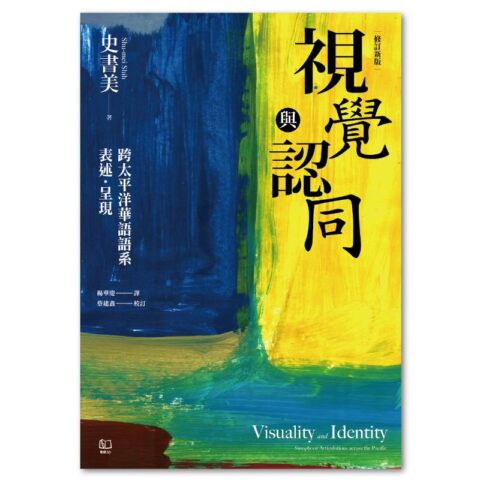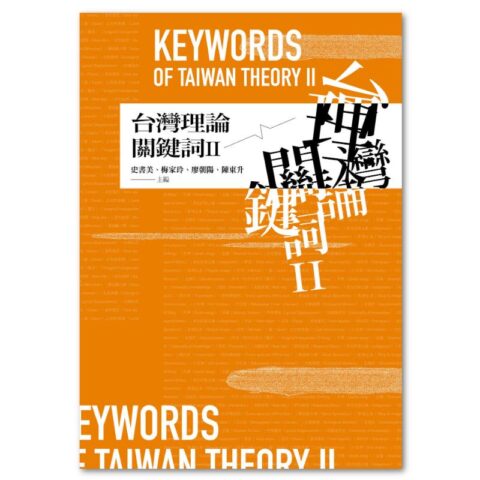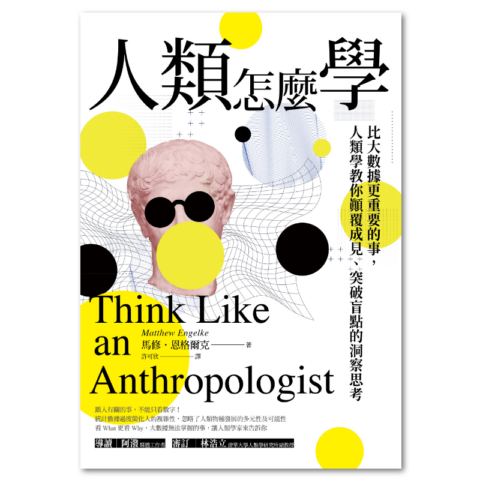憂鬱的熱帶(全新修訂本)
原書名:Tristes Tropiques
出版日期:2015-09-04
作者:克勞德‧李維史陀
譯者:王志明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640
開數:25開(21×14.8 cm)
EAN:9789570845990
系列:聯經經典
尚有庫存
原著問世六十週年,全新中文修訂本
結構主義人類學宗師李維史陀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登上馬托格羅索高原、深入馬查拉河叢林
沿著龍東電報線摸索前進、探查人類學的責任與定位
揭露文明與野蠻之間,其實連一線之隔都不存在。
《憂鬱的熱帶》是結構人類學宗師──克勞德‧李維史陀一生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作品。
李維史陀在求學時代曾經醉心於左翼政治活動,熟讀馬克思作品,同時也受到佛洛伊德潛意識學說和地質學理論之啟發,因此關注於「底層結構」與「表面現象」之間的關聯、斷裂與互動形式。
青年李維史陀於1930年代前往巴西協助建立聖保羅大學,並執教社會學課程。他利用課餘休假期間多次探查印地安人社群,兩度執行大型調查計畫,在叢莽深處的原始部落裡看見人類社會的原初型態,由此展開廣泛深入的思考歷程。
李維史陀採取全新的研究取徑,將這些原始部落放進全球人類發展的脈絡之中,交互參照南亞印度、美洲新世界、歐洲舊大陸等地區的文明發展型態,提出引人入勝的比較印證,兼具開放視野與細膩觀察,反思整部人類學發展史的弔詭荒謬之處,以及人類學家的自我定位難題,使這部作品超越了科學研究的範疇,成為一部融合人類學、歷史學、文學與哲學的不世傑作。
《憂鬱的熱帶》全書長達33萬字,從李維史陀如何成為人類學家談起,兼論當代法國思潮之演變,分析異文明接觸時的衝擊和意義,並詳細描述他先後探訪觀察到的五個南美洲印地安社群,以及人類學家探險歸來之後的反思。全書思想密度之高、批判反省之深刻、行文筆觸之優美,嚴肅之中不失幽默,可說是前所未見,六十年來亦無人能及。
作者:克勞德‧李維史陀
1908-2009,法國人類學家,早歲在巴黎大學主修哲學與法律,1934年受邀赴巴西聖保羅大學教授社會學,並從事巴西土著之田野研究,1939年返回法國。德國入侵法國之後,他設法逃離歐洲,前往美國暫居,開始發展結構主義理論。1948年返法,將研究範圍從親屬關係拓展至宗教及神話學,1959年進入法蘭西學院,1973年獲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為20世紀最偉大人類學家之一,富於哲思,不囿於經驗主義,綜覈各家學理,而多所創發,長於社會與文化之比較研究,於親屬關係、宗教及神話尤有獨得見解,他開創的結構主義理論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對英國、西歐及美國等地的社會科學、哲學、比較宗教、文學及電影均產生重大影響,位若宗師。主要著作有:《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1949)、《憂鬱的熱帶》(1955)、《人類學的結構》(1958)、《圖騰制度》(1962)、《野性的思維》(1962)、《神話學系列》(1964-1972)。
譯者:王志明
台灣高雄人,1949年生,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碩士。農家子弟,為人寡言而勤於筆記,多才,能橡膠版畫,喜歡原始藝術及學習少數民族語言,1987年病逝台北。
第一部 結束旅行
一 出發
二 在船上
三 西印度群島
四 追尋權力
第二部 行腳小註
五 回顧
六 一個人類學家的成長
七 日落
第三部 新世界
八 赤道無風帶
九 瓜納巴拉灣
十 穿越回歸線
十一 聖保羅市
第四部 地球及其居民
十二 城鎮與鄉野
十三 前線地帶
十四 魔毯
十五 人群
十六 市場
第五部 卡都衛歐族
十七 巴拉那州
十八 潘特納爾濕地
十九 首府那力客
二十 一個土著社會及其生活風格
第六部 波洛洛族
二十一 黃金與鑽石
二十二 有美德的野蠻人
二十三 生者與死者
第七部 南比夸拉族
二十四 失去的世界
二十五 在荒野
二十六 沿著電報線
二十七 家庭生活
二十八 一堂書寫課
二十九 男人、女人與酋長
第八部 圖皮─卡瓦希普族
三十 獨木舟之旅
三十一 魯賓遜
三十二 在森林中
三十三 蟋蟀的村落
三十四 賈賓鳥的鬧劇
三十五 亞馬遜流域
三十六 橡膠園
第九部 歸返
三十七 奧古斯都封神記
三十八 一小杯蘭姆酒
三十九 塔克西拉遺址
四十 緬甸佛寺之旅
李維史陀年表
三 西印度群島
對船上同行的旅客而言,他們以前的生活大體平靜無波,現在一下被捲入這種大冒險似的旅程裡面,他們遭受到的那種愚蠢與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種聽都沒聽說過的、非常特別的、極度異常的現象。事實上,他們把這種現象對他們自己產生的切身影響,以及對虐待他們的人的影響,看成似乎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災難。但我自己倒是看過這世界的一些現象,前此幾年也曾親歷過一些不尋常的經驗,因此這種現象對我而言並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當代人類由於人口數量暴增,所要面對的問題也愈來愈複雜,再加上交通與通訊工具快速改進,當代人類的皮膚似乎對愈來愈多的物質與知識交流愈來愈容易過敏,結果就是類似我們早上經歷過的痛苦經驗慢慢地流淌出來。在馬丁尼克這個法國殖民地,戰爭與敗戰所帶來的唯一後果,只是加速推進這種普遍的過程罷了。戰爭與敗戰只是促成一種持久性感染的媒介,而感染本身並不會自地球上消失。某個地方的感染狀況也許會暫時壓下來,但在其他地方會重新出現。一旦社會人群所擁有的空間開始緊縮的時候,愚蠢、怨恨與易於受騙便會像膿瘡一樣地長出來,馬丁尼克島的經驗並不是我所碰到的第一次。
四 追尋權力
有時候會有一幅意象、一種回聲,似乎從過去裡冒出來,在小小幾平方公尺的空間裡短暫停留一兩秒鐘:小街道上的金匠銀匠工作時所發出的清澈聲音,像是有一千隻小手臂的精靈心不在焉地敲擊木琴。穿過這些小巷以後,我馬上又置身於寬廣的大街路網裡。這些大街橫穿過一批五百多年的老房子中間。那些老房子在最近發生的暴亂裡受到極大的破壞,不過那些房子在過去就常常遭到破壞,壞了再修,一次又一次,因此看起來好像是一堆年代古老得不得了、難以形容的破舊建築層層疊疊。我四處觀看這些景象,所做的正是一個空間考古學家的本分工作,鍥而不捨地想從殘片遺物中重現早已不存在的地方色彩,不過這種努力是徒勞無功的。
一旦產生了這種念頭,幻想便開始一步一步地布下它的陷阱。我開始希望我能活在還能夠做「真正的旅行」的時代裡,能夠真正看到還沒被破壞、被汙染、被弄亂的奇觀異景的原始面貌;我希望我自己是伯爾尼爾、是塔維涅、是曼紐西……我希望自己能像他們那樣地旅行,而不是像我現在這樣。這類想法一旦開始出現,便可以無止境地延伸下去:在哪個時代去看印度最好?什麼時侯是研究巴西原始部族的最佳時機、可以得到最單純的滿足、可以看見他們還沒有被汙染破壞以前的景象?到底是在十八世紀與布干維爾同時抵達里約熱內盧比較好呢?還是在十六世紀和列維、特維同行比較好?每提早五年,我就能夠多挽救一種習俗、多了解一項祭儀或一種信仰。但是我很熟悉這些相關的人類學紀錄文獻,我明白,如果我活在一個世紀之前,就無法獲得這許多可用來增進知識的材料與研究方法。因此我便陷入一個圈圈裡,無法逃脫:不同的人類社會之間,愈不容易交流就愈能減少因為接觸而引起的相互汙染,但同時會剝奪了讓不同社會的人相互了解與欣賞對方優點的機會,也就無法了解多樣化的意義。
五 回顧
無論如何,當時我自己也非常無知,便相信了那些可以很方便地納入自己計畫裡面的幻想,特別是連喬治‧杜馬自己對這個問題也並沒有清楚的概念。在土著社會還沒有完全被消滅以前,杜馬曾到過巴西南部,更重要的是,那時候他喜歡和獨裁者、封建地主和文化藝術贊助者廝混,這類人並不能就這個問題給他任何啟示。
因此,當馬格利特帶我去參加午餐會的時候,我大吃一驚。我在餐會上聽到派駐巴黎的巴西大使發表官方觀點:「印第安人?哎啊!親愛的先生,他們在幾年前就全都不見了。這是我國歷史上很悲哀、很可恥的一段。但是十六世紀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一群貪婪殘忍的人。他們具有那個時代常見的野蠻性,這實在也怪不得他們。他們把印第安人捉來,綁在砲口上,然後轟成碎片。印第安人就是這樣不見了。社會學家可以在巴西發現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印第安人嘛,忘掉算了,你一個也看不到……」
現在我回想起這段話,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即使是出自一九三四年的上層統治階級口中,還是不可思議。當時巴西的菁英分子容不得任何人提起印第安人或是巴西內陸的原始情況(令人欣慰的是現在已有所改變了),不過他們倒是肯承認,有時甚至自己說出來,他們的長相之所以會帶些異國情調,是因為他們的曾祖母可能有印第安人血統,不過他們絕對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長相之所以有些奇特是因為滲入黑人的血統。在葡萄牙帝國統治的時代,這些菁英分子的祖先們倒是覺得有黑人血統並不是什麼需要掩飾的事情。以巴西駐法大使蘇沙–丹塔斯來說,他毫無疑問擁有印第安人血統,很可能也以此為傲。但他是旅居海外的巴西人,而且在十幾歲的時候就來到法國,早已忘記他自己國家的真實面貌。在他的記憶裡,真相早已被一種盛行的官方理想化看法所取代。在他還記得的一些細節裡面,我想他喜歡貶薄一下十六世紀的巴西人,以免觸及他父母那一代男人最喜歡的某種娛樂,或許他年輕的時候也還做過那種娛樂活動。那種娛樂是到醫院去收集天花患者的衣服,然後把那些帶有天花病菌的衣物和其他禮物一起掛在印第安人經常走過的小徑上。這種娛樂活動造成相當可觀的成果:一九一八年版地圖上的聖保羅州,面積和法國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的區域被標示為「只住著印第安人的未知地帶」;等到一九三五年我去聖保羅的時候,除了少數幾戶印第安人會在禮拜天跑到桑托斯海灘去賣所謂的特產以外,那附近連一個印第安人也沒有。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一九三五年的聖保羅州幾乎看不到印第安人,但是再往內陸走個三千公里,是還可以找到一些。
六 一個人類學家的成長
我懷疑我會那麼快就決定放棄哲學而改學人類學,可能還有一些更私人性的理由使我對哲學感到厭惡,因而尋求一種逃避之道。我在蒙德馬桑中學愉快地教過一年書,一邊教一邊準備教材,接著我被調到拉昂。到了拉昂之後,學期一開始,我就痛苦地發現,從此以後得一輩子重複教同樣內容的課程。我的心靈組成中有一項特殊的性質──無疑是一種弱點──就是我很難對同一個題目專心兩次。一般說來,中學教師資格鑑定考試被看做是一種非人的試煉,任何人一旦通過了,只要他願意,就可以一輩子安安穩穩過日子。對我而言,情形正好相反。我第一次參加考試就順利通過,是同年考生中年紀最輕的,而且,準備那些原理、理論、假設等等,並沒有使我覺得精疲力盡。我的折磨來得比較慢,教了一年書以後,我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再上台講課,除非每年都讓我教新的課程。當我必須為學生口試的時候,這問題變得更加尷尬:由於題目是隨機抽出的,我完全不能確定考生到底應該怎樣回答才算正確,連最笨的學生似乎都能把該說的答案全都完整說出來。似乎只因為我曾一度用心思考過這些題目,它們就這樣從眼前消失不見了。
我現在時常這麼想,人類學之所以會吸引我,是因為人類學研究的文明和我自己特殊的思考方式之間有一種結構上的共通之處,而我自己(當時)覺察不到。我沒有興趣明智地在同一塊土地上年復一年的耕耘收穫、收穫耕耘,我的智力是新石器時代式的,猶如原始的燒墾農業,不時在未曾探索過的地方放火,使那些土地得到養分,從而收穫一些作物,然後遷移到別的地區去,把燃燒過的大地拋在身後。不過,在那時,我還沒能自我察覺到這種較深層的動機。
八 赤道無風帶
人們經常稱讚里約熱內盧很美,但我卻無法動心。其中原因實在也很不容易說明白。我覺得里約熱內盧這個城市與其周邊環境的比例失衡。糖麵包山、駝背山以及其他備受讚譽的自然景觀,在一位正要進入海灣的旅行者眼中看來,像是一張缺牙少齒的嘴巴裡凌亂凸起的牙根─這些突起的部分經常被厚重的熱帶霧氣籠罩著─這些山太小,跟無比遼闊的地平線一點都不協調。如果想觀賞海灣,最好是從陸地這一側的高處往下看,俯瞰海灣時所見的景觀正好和在紐約給人的感覺相反,在里約熱內盧,大自然本身看起來好像是一片尚未完工的建築工地。
同時,單憑眼睛所能見到的景觀,根本無法看出里約熱內盧海灣有多遼闊。船行的速度緩慢,必須小心避過海灣裡面的大小島嶼,從長滿樹木的山坡上面忽然吹下來的氣息和涼快的感覺,使人早早感到好像已經具體接觸到花卉及岩石,旅行者預先嘗到這片大陸的特性,雖然實際上還看不見它們。這使人又想起哥倫布的描述:「樹很高,好像碰到天頂;如果我沒弄錯的話,這些樹終年不會落葉;我曾在十一月的時候看見這些樹葉新鮮油綠得像是西班牙五月的樹葉;有些樹甚至正在開花,有些則結著果實……只要一轉身,到處都聽得見夜鶯的歌聲,同時有數千種不同的鳥類為牠們伴唱。」這就是美洲;這塊大陸造成一個無法逃避的巨大影響。它的存在,由里約熱內盧海灣霧濛濛的地平線在黃昏時刻生趣盎然的種種活動跡象組合而成;但是,對於一個新來者而言,那些活動、形狀和亮光並不代表某個省分、村莊與城鎮;它們也不代表某座森林、草原、河谷與景觀;它們也不表示生活其中的人們的活動與工作,那些人相互之間是陌生的,因為他們都各自侷限於自己的家族與職業之中。整個景觀構成一個既殊異又綜合的整體,環繞在人四周的,並不是無數的個別生命與事物,而是渾然一體的、令人驚嘆的存在:新世界。
九 瓜納巴拉灣
通常,人都把旅行視為空間的轉換,但是這種觀念還不夠完整。旅行不但在空間中進行,同時也伴隨著時間與社會階層結構的轉變。任何印象,只有同時與這三個座標聯繫起來才顯出意義。不過,空間本身即有三個座標,所以,如果想完整描述任何旅行經驗,必須要同時使用五個座標。我在巴西一上岸,馬上感覺到這一點。我已來到大西洋對岸,在赤道的另一邊,同時非常接近南回歸線。有很多事情都足以說明這一點:天氣恆常溼熱,不必再穿毛衣,房子與街道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我後來發現,這種分界是西方文明的一種常態)。不過我很快就明白,取而代之的是人與叢林的分界;如果是在我們那樣完全人文化了的地理景觀中,人與叢林之間並沒有這樣清楚的分界。此外,還有椰子樹、新品種的花卉、在咖啡館前面成堆的綠色椰子,椰子剖成兩半,內有甜汁,散發隱藏著的新鮮味道。
我同時也注意到其他變化:我以前貧窮,現在變得富有,首先是因為我的收入狀況已經改善,其次則因為當地物產的價格極低。一個鳳梨只賣二十蘇,一把香蕉賣兩法郎;在義大利人開的店裡,一隻烤好的雞才賣四法郎。好像是兒歌裡面的「塔定太太的豪華飯店」。最後,抵達一個新港口時的那種開放心態,那些使人覺得有義務要善加利用的不求自來的機會,形成一種曖昧情況,很容易使人暫時放棄平日的自制,忽然間意氣風發,揮霍為快。當然,也有可能發生恰好相反的狀況。法德停戰後,我抵達紐約,一文不名,就有這種經驗。但是,不論是增加還是減少,不論你的物質狀況改善或變糟,除非是奇蹟發生,否則旅行不可能不在這方面帶來一些變化。旅行不僅僅是把我們帶往遠處,還使我們在社會地位方面上升一些或降低一些。它使我們的身體換到另一個空間,同時,不論是更好或更壞,也使我們脫離自己原來的階級脈絡,唯有親身體驗才會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發生了什麼樣意料之外的變化,這變化了的社會地位決定了我們對眼前環境的觀感。
十 穿越回歸線
侵蝕作用對眼前荒蕪的地貌有重大影響,不過人類必須為其中混亂殘破的景象負主要責任:首先是清理一片土地來種植東西,用了幾年以後,土壤變得貧瘠,被咖啡樹稍落下的雨水沖走,然後轉移地點,到另一塊豐饒的處女地重新種植。在舊世界中,人與土地之間所建立的那層小心翼翼、互相取予的關係,那種經年累月互相調適的關係,從來未曾在新世界出現過。在新世界,土地被虐待,被毀滅。那是一種強取豪奪式的農業,在一塊土地上取走所有可以取走的東西以後,再移到另一塊土地去奪取一些利益。拓荒者抵達、利用的地區被稱為「邊緣」是有道理的。他們幾乎是一清理出一片可種植的土地的同時,也把那塊土地毀了。他們注定只能占有一道不斷遷移的地帶。這種地帶一方面蝕毀原始森林,另一方面留下一片片已喪失價值的土地。像森林火災一樣,這種農業的大火吞沒消化掉它自己賴以存在的東西,這種農業大火在一百年的時間之內燒遍整個聖保羅州。十九世紀中葉的礦工率先點火,他們放棄了枯竭的礦區,由東往西遷移,我稍後就在巴拉那河對岸看見這種大火,正輾過一片混亂的被砍下的樹幹和一些被連根拔起的家庭。
十一 聖保羅市
即使只是扮演知識搧客的角色──當時的法國正逐漸淪落成這種貨色──似乎都幹得很吃力,想到這點不免令人悲從中來。我們法國人探討科學與知識時,似乎仍然是十九世紀延續下來的那種心態的奴隸。十九世紀的時候,每個知識領域的範圍有限,一個具備傳統法國知識分子特質的人──接受博雅教育、思路敏捷清晰有邏輯,加上良好的文字能力──就能夠完全掌握整個知識領域;光憑個人之力的工作,就足以重新檢視整個知識領域,然後提出他自己新的綜合結論。不管喜不喜歡,現代科學與學問不再容許這種手工藝人式的研究方法了。以前可以靠個別的專家替他整個國家贏取榮耀,現在卻得靠整群專家合作才行,這正是我們缺少的。在這個時代,私人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只能收容某些有特殊意義的書籍,但是法國的公立圖書館既狹小又沒聲譽,也沒有研究助理,甚至連給讀者坐的椅子都不夠,不但無助於研究工作,反而阻礙研究。簡而言之,目前的科學與智識創造是一種集體性事業,研究者多半是一些沒沒無聞的人,而對於從事這種研究工作,我們的準備可說是嚴重不足到了極點,我們過分地把注意力放在讚美我們那些老一輩名家輕易獲得的成就。這些老一輩名家的風格令人無從挑剔,可是他們自己在沒有樂譜可以彈奏的情況下,又能相信光憑完美風格還可以再撐多久呢?
比較年輕的一些國家已經得到教訓。以巴西為例,他們以前也曾經有過一些不太多的個人取得的輝煌成就──歐幾里得‧達‧庫尼亞、奧斯瓦爾多‧克魯斯、查加斯和維拉–羅伯斯──一直到最近為止,文化一直是富人的玩藝兒。寡頭執政者覺得有必要培養一種公民的、俗世的公眾意見來制衡教會與軍隊的傳統影響力,他們決定要讓更多民眾可以享受文化,因此創建了聖保羅大學。
十二 城鎮與荒野
在另一方面,有些莊園主人為了宗教的理由,會把土地獻給教區,結果成為教堂財產,受某個聖人保護的鎮區。另外有些鎮區的創建則是基於俗世的理由,有的莊園主決定成為「人口繁衍者」,甚至成為「城鎮栽培者」。在這類例子中,他會用自己的名字為城鎮命名,叫做保羅市或奧蘭迪亞等等;有時候為了政治上的理由,則以名人做為城鎮保護者,取名為普魯登特總統城、科內利烏普羅科皮烏或埃皮塔西奧佩索阿等等……這些城鎮的生命週期雖然短促,仍然不時更改名字,每次改名都代表城鎮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只是有個非正式的名稱:舉例來說,荒野中出產馬鈴薯的地方會被叫做「馬鈴薯」;如果某個地方缺乏燃料用以煮食,或許會叫做「生豆」;有的地方叫做「無鹽」,因為到達那個地方之前可能存貨都已用盡。然後,有一天,某個上校──只要是重要的地主或政治人物都被稱為「上校」──想要在他所掌握的那幾千畝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權威,他就去招募人員,有時候是雇用,有時候則把一些流浪漢捉來,於是「生豆」就變成「萊奧波爾迪納移民鎮」或「費南多市」。隨著時間的消逝,這些由個人野心或一時興起而憑空創造出來的城鎮,可能衰敗、消失:剩下來的只不過是一個名字和幾間小屋,人口愈來愈少,飽受瘧疾和鈎蟲肆虐。不過,有時候這樣建立起來的城鎮會生根,發展出某種集體意識,設法忘掉它起初不過是某位個別人物的玩物或工具而已。
十六 市場
印度的重大失敗可以給我們上一課。當一個社會人口太多的時候,不管其思想家們如何天才,只有使某些人淪為奴隸才能讓這社會存續下去。一旦人類開始覺得他們受到地理、社會與心理習性所壓抑,無法伸展的時候,他們就有被誘採取簡單解決辦法的危險:認定同類的一部分沒有做人的權利。這樣做使其他人獲得多幾十年的時間有些活動空間。然後,就必須再把更多同類摒除在外。從這個觀點去看歐洲過去二十年來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增加一倍的最後結果,那些事情也就不再是什麼某個國家的越軌、某種教條或某群人的異常了。我把那些事情看做是我們已進入一個有限的世界的前兆,就好像南亞早我們一千年或兩千年即已面臨的那樣,除非做些重大的決定,我不認為我們能避開和南亞相同的命運。人有系統的貶低其他人,愈演愈烈,我們如果辯稱近幾年發生的事件只代表一種短暫的汙染,我們就是犯了言行不一和盲目無視的罪惡。
在亞洲,使我害怕的是我們自己未來的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亞洲目前正在經歷的狀況。在印第安人的美洲,我很慶幸他們還活在一個與他們擁有的世界相符的時代,還能享有名符其實的自由的滿足,無論這時代會變得多麼短暫。
十七 巴拉那州
見到他們的時候,分給每一成員戒指、項鍊、廉價胸針等等飾品,有時並不足以建立起想要的友善關係。即使是拿出完全不成比例的一大堆巴西銀幣要跟對方交換一件價值甚低的用具,並不能使該用具的主人心動。他會說他不能沒有那樣用具,如果是他自己製造了那用具的話,他會很樂意地把它交出來,但是那是很久以前他從一位老婦人手裡得來的,而只有她知道怎麼做那種用具,如果他把那用具給我們,那他用什麼來代替?當然無法找到那個老婦人。她去哪裡了呢?他不曉得,同時他會用手隨便朝森林指一指。無論如何,對於一個在瘧疾發作的老人,他離最近一家白人開的商店有一百公里之遠,即使是我們身上所有的巴西銀幣都給他,有什麼用呢?令人覺得深以為恥,居然要從一個這樣的老人身上奪走這樣一件小用具,失去那用具對他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但是常常出現另一個不同的故事。我可能問一個印第安婦人,可不可以把她的鍋子賣一個給我,她會回答可以。不幸的是,鍋子不是她的。那是誰的?一陣沉默。她丈夫的嗎?不。她兄弟的?不,也不是她兄弟的。她兒子的?不是她兒子的。鍋子是她孫女的。孫女總是任何我們想買的東西的擁有者。我們看看孫女,她只有三、四歲,蹲在火堆附近,全神貫注於不久以前我套在她手指上的戒指,因此我們開始和這個小女生進行冗長的談判,她父母完全不置一辭。她對一隻戒指外加五百個巴西銀幣無動於衷,但對一枚胸針加四百銀幣有興趣。
十九 首府那力客
我們也看到小孩玩木雕的小玩偶,都穿著廉價的華衣,這就是他們的娃娃,而另有一些同類的人偶則被幾個老婦人小心翼翼地藏在她們的籃子底部。老婦人藏的偶人,很難說到底是娃娃玩偶呢?是神像呢?還是祖先的雕像?因為她們的偶人可被用來做幾種完全不同的用途,特別是同一偶人有時先用做一種用途,然後又用做另一種用途。有些木偶目前收藏在巴黎的人類博物館,毫無疑問具有宗教意義,其中一個顯然是「雙胞胎之母」,另一個是「小老頭」,這是一位從天上下到人間的神,受到人類惡意對待,於是他對人類施加懲罰,只有一個給了祂居所的家庭沒有受罰。但是,在另一方面,大人會將人偶拿給小孩玩,如果將此視為宗教衰敗的徵象,則又未免過分浮面;現存的這種看起來似乎極難確定的情況,波吉阿尼四十年前就描述過,比他晚了十年的弗里奇也描寫過完全一樣的情形;比我晚十年後有人也做了同樣的觀察。這種存在達五十年之久沒有多少變化的情況,也只能說在某種意義上算是正常情況了。確實是可以看見宗教價值衰退的現象,但其中原因不在於把人偶拿給小孩子玩,而是在於處理神聖的與俗世的兩者之間的關係上面,這兩者之間的共同之處遠比我們所想的為多。神聖的與俗世的兩者之間的對比,既不像有時候人們所斷言的那麼絕對,也沒有那麼恆常。
二十 一個土著社會及其生活風格
貴族展示階級地位的方法是在身體繪圖或是刺青,後者類似貴族的家徽。他們拔除臉上所有的毛,包括眉毛和睫毛在內,他們很鄙夷地稱濃眉的歐洲人為「鴕鳥兄弟」。貴族男女在公共場合出現時,都有奴隸和隨從跟班,這些跟班一聽到他們有所吩咐即刻行動,而且揣測他們心理的欲望。即使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掛滿飾物畫滿圖案的老太婆,她們是最好的設計家,仍然為了不得不放棄她們的藝術創作活動而感到很抱歉,放棄的原因是以前服侍她們的俘虜奴隸(cativas)都不見了。在那力客還有幾個以前的查馬可可奴隸,現在已融入一般社會之中,但其他人對他們仍維持相當尊重的上對下的保護照顧態度。
連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都被這些貴族的高傲態勢嚇住,以貴族頭銜「唐」和「唐那」來稱呼他們。有人說白人婦女如果被姆巴雅人逮捕,一點都不用害怕,沒有一個戰士會玷汙她,因為他怕自己的貴族血液被汙染。有些姆巴雅貴族婦女拒絕和總督夫人見面,她們覺得只有葡萄牙皇后才有資格與她們為伍。另外一個叫做唐那‧卡特琳娜(Doña Caterina)的貴族婦女,拒絕馬托格羅索總督邀她去庫亞巴的邀請,因為她當時正是適婚年齡,她怕去了以後,總督會向她求婚,那時她既不願接受一個不相稱的求婚者,又不願因拒絕而得罪他。
這些印第安人實行一夫一妻制,但青春期少女有時志願跟隨戰士出去打仗,當他們的侍者、跑腿和情婦。貴族婦女有時會有勇士隨從,同時也是她的情人,她丈夫絕對不敢表示任何嫉妒之意,因為他們兩人都會因此而喪失面子。這是一個對我們視之為自然的感情相當厭惡的社會。舉例來說,他們非常不喜歡生育兒女,墮胎和殺嬰幾乎是正常手續,到了這群人的延續是靠收養而非靠生殖的程度,戰士出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搶別人的小孩。在十九世紀初,有人估計某個瓜伊庫魯族群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是原本的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