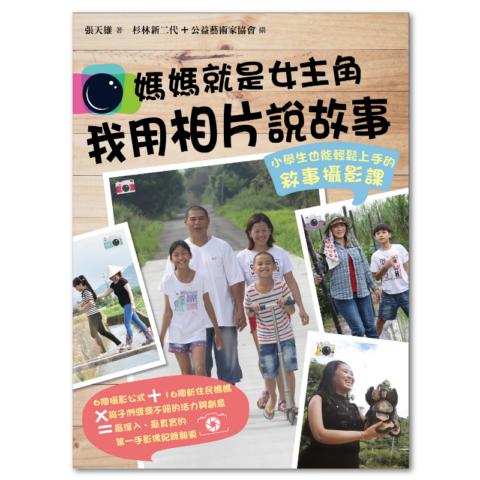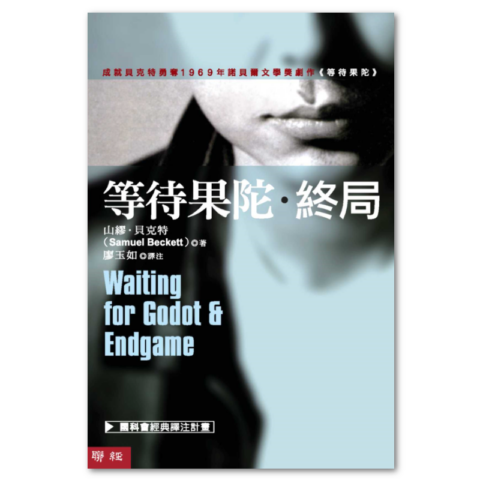心象繪畫:高行健畫集【首刷限量.典藏盒裝親筆簽名版】(回望創作之始,精選又精選的繪畫行跡)
出版日期:2022-08-11
作者:高行健
印刷:彩色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264
開數:長26.3×寬37×高2.8cm
EAN:9789570864175
系列:當代名家‧高行健作品集
尚有庫存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最完整的繪畫行跡
全面呈現1964~2020其對內在與世界的凝神關注
以260餘幅畫作展開「高行健藝術」的紙上展覽
二○一五年,比利時的伊克塞爾美術館與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分別以龐大的規格為高行健舉辦繪畫雙展。其中比利時皇家美術館為高行健的畫作專闢展廳,與魯本斯、林布蘭等西方繪畫大師同列「長久展出、永久收藏」的地位。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高行健,之後以劇作家、詩人、戲劇和電影導演等角色活躍於西方藝壇,至此,他再度以畫家的身分,登上藝術經典的殿堂。
高行健是一個懷疑二元論的靈魂畫家,他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找到一個廣闊的第三空間地帶,以水墨的渲染與光影所造成的朦朧與恍惚,在此展現他的「心象繪畫」。所謂的心象,來自於夢境、幻想、潛意識,將人類與自然間無可捉摸的「靈魂」,訴諸於繪畫的具體手段,卻不明畫身與色,而是虛畫心與空,呈現出一種內心的視像,讓觀者得以抽身靜觀自我的側影,既可不脫離形象,又無細節框限,留給觀眾寬闊的冥想餘地,與多種解答的可能。
本畫冊收錄高行健完整的繪畫行跡,由1964年一路揮灑至2020年,共計260餘幅畫作,可綜觀畫家蛻變、沉思、昇華的心路歷程及思想意境。觀者將發現,脫離文字與言說的框架,訴諸於黑、白、灰與線條、光影的律動,人人具備的深層而混沌的潛意識,都能因此被觸摸與認知。
作者:高行健
國際著名的全方位藝術家,集小說家、劇作家、詩人、戲劇和電影導演、畫家和思想家於一身。一九四○年生於中國江西贛州,一九八八年起定居巴黎,一九九七年取得法國籍,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小說和戲劇關注人類的生存困境,瑞典學院在諾貝爾獎授獎詞中以「普世的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加以表彰。
他的小說已譯成四十種文字,全世界廣為發行。他劇作在歐洲、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亞頻頻演出,多達一百三十多個製作。他的畫作也在歐洲、亞洲和美國的許多美術館、藝術博覽會和畫廊不斷展出,已有上百次展覽,其中多達九十次個展,出版了五十多本畫冊。近十年來,他又拍攝了三部電影詩,融合詩、畫、戲劇、舞蹈和音樂,將電影作成一種完全的藝術。
他亦榮獲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法國文藝復興金質獎章、義大利費羅尼亞文學獎、義大利米蘭藝術節特別致敬獎、義大利羅馬獎、美國終身成就學院金盤獎、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雄獅獎、盧森堡歐洲貢獻金獎。香港中文大學、法國馬賽—普羅旺斯大學、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臺灣大學、臺灣的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和國立師範大學皆授予他榮譽博士。
此外,二○○三年,法國馬賽市為他舉辦大型藝術創作活動「高行健年」。二○○五年,法國愛克斯—普羅旺斯大學舉辦「高行健作品國際學術研討會」。二○○八年,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和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高行健藝術節」。二○一○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辦「高行健的創作思想研討會」。二○一一年,德國紐倫堡—埃爾朗根大學舉辦「高行健:自由、命運與預測」大型國際研討會;同年,韓國首爾高麗大學舉辦「高行健:韓國與海外視角的交叉與溝通」,韓國國立劇場則舉辦「高行健戲劇藝術節」。二○一四年,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舉辦「高行健作品國際研討會」。二○一七年,臺灣國立師範大學舉辦「高行健文學藝術節」。二○一八年,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圖書館設立「高行健研究與資料中心」。二○二○年,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設立「高行健資料中心」。現任臺灣國立師範大學講座教授。
高行健簡介
走向當代世界繪畫的高峰:面對比利時的「高行健繪畫雙展」/劉再復
心象繪畫/高行健
畫作
Part One 1964-1990
Part Two 1991-2000
Part Three 2001-2010
Part Four 2011-2020
高行健年表
高行健著作
畫作索引
走向當代世界繪畫的高峰:面對比利時的「高行健繪畫雙展」/劉再復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追蹤好友高行健的文學腳步,包括他的小說、戲劇、文學理論以及詩歌等,對於他的繪畫藝術,則只是懷著一顆好奇心,不斷去觀察、欣賞、理解,但總是有偏見,以為這不過是他人生創造中的「邊角料」,並未把它列入高行健精神價值創造體系的主流。可是,最近十五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的這十五年,我卻不斷被他的繪畫成就所驚動,不得不對他的繪畫「刮目相看」,並認真對它重新評估。尤其是二○一四年秋天,他到香港科技大學和我進行了幾天的交談之後,才知道,二○一五年比利時將以巨大的規格舉辦他的繪畫雙展:一是在首都布魯塞爾的伊克塞爾美術館(Musée d’Ixelles)舉辦「高行健回顧展」,以展示高行健的繪畫歷史及成就;二是在比利時皇家美術館(Musées Royaux des Beaux-Arts de Belgique)舉辦「高行健:意識的覺醒」巨型新作的專題展。題目是「意識的覺醒」,畫的是人的「潛意識」。剛聽到這一消息,我更是好奇:潛意識也可以成為繪畫題材嗎?高行健是怎樣呈現人的這一片潛在的、混沌的內在世界?因為好奇心太強烈,我不得不要求隨同來港的高行健夫人西零的幫助,希望她能把展出的資訊告訴我,包括圖片和評論。
二○一五年一月返回美國後,儘管我因旅途勞累懸擱了許多工作,但還是關注二月底開始的比利時高行健繪畫雙展。我果然看到,雙展如期隆重地在布魯塞爾兩個藝術館同時舉辦(兩場開幕式僅錯開一天,分兩天舉行),一個藝術奇觀在一個西方國家的首都就這樣出現了。《潛意識》、《幻象》、《衝動》、《內視》、《別處》、《困惑》等本不可捉摸的心象,真的呈現在觀眾面前。展出十天之後,高行健回到巴黎,他打電話告訴我,這是他迄今以來規模最大的繪畫展,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比利時的藝術慧眼會如此重視他的畫,並動用這麼巨大的資源來展示他的藝術。
我明白他說的話。高行健於上個世紀八○年代末來到巴黎,那時正是西方當代藝術最熱鬧的年代。我當時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訪法,到巴黎時在他家住了兩天,傾聽他關於西方當代藝術的有趣評論。我那時就知道,他全然不為時髦所動,正準備在文學和藝術上逕自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但我只相信他的小說、戲劇可以獨闢蹊徑,完全沒想到繪畫。可是,從一九八八年至今,近三十年中,歐洲、亞洲和美國的數十個重要美術館和許多重要的國際藝術博覽會卻頻頻展出他的畫作,為他舉辦了大約八十次個展。而我自己也頻頻收到他的畫冊,至今已有三十多本。每次翻閱他的畫冊,都有一種驚奇感。用手指輕輕撫摸畫面時,竟懷疑自己在作夢。這是我從八○年代初就常常促膝談心的那個高行健所作的畫嗎?那個質樸可親、總是在書寫小說、戲劇的老朋友,也能用水墨畫征服世界,讓西方出版社一本本地為他出版這麼豪華的畫冊嗎?
然而,鐵鑄的事實就在眼前。二○一五年二月布魯塞爾的雙展,比利時皇家藝術館這樣的藝術殿堂,更是慧眼獨到,氣魄雄偉,為他專闢一座展廳,長久展出,永久收藏,這對西方當今的畫家來說也屬罕見。據內行的朋友告訴我,能享受「長久展出、永久收藏」的超級「待遇」的,只能是林布蘭、魯本斯這樣舉世公認的經典畫家(高行健的專題展廳的樓上,正是林布蘭、魯本斯這些西方繪畫大師的展廳)。我多次到巴黎,知道華裔畫家趙無極先生的繪畫曾進入巴黎龐畢度文化中心(Le Centre Pompidou)的展廳,繼趙之後,就是高行健走到這堂皇的藝術尖頂了。這一事實,讓我興奮不已,也讓我再次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總之高行健的繪畫成就,真的超過我這麼一個摯友對他的認知與期待,儘管我比別的朋友更早、更深地認識到他不同凡響的天才,但還是沒有想到,他的繪畫成就能達到與二十世紀現代繪畫大師夏卡爾並肩的程度,高的專題展和夏卡爾的回顧展便在皇家美術館一起舉辦開幕式與新聞發布會。
也是因為好奇心的驅動,所以我又進而想知道,西方藝術評論家與鑒賞家為什麼會如此「看中」高行健?或者說,他們「偏愛」高行健的藝術理由是什麼?我在二○○七年由德國路德維希博物館(Ludwig Museum)舉辦、題為「世界末日」的高行健回顧展中找到了一個回答,該博物館的館長貝亞特.賴芬帥德(Beate Reifenscheid)在回顧展的畫冊序言中寫道:
高行健選擇了一種幾乎傾向於不定型的形式,探究視覺上抽象的可能,不使其成為真正的具象,也不意圖去標示什麼。取而代之的是,他運用感召的潛能,召喚出靈魂中潛意識裡的圖像,那也是在我們人人內心中尋覓和發現得到的景象。高行健運用黑、白、灰各種細微變化的色調,對畫面和色彩而言,也發現了一個全新而豐富的寶庫。(《高行健:世界末日》。德國,科布倫茨:路德維希博物館)
這位館長啟發了我,原來高行健是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找到一個廣闊的第三空間地帶。這個地帶是一個全新而豐富的寶庫。這裡不再是看得見的人與風景,而是看不見且瞬息萬變的「一閃念」。高行健發現了這個地帶,而且「運用感召的潛能,召喚出靈魂中潛意識裡的圖像」——不錯,是潛意識裡的本來無法看見的圖像。如同戲劇把不可視的心象呈現於舞臺,高行健又把不可視的潛意識呈現於畫面,這是人類繪畫史上沒有人做過的事。
太妙了!後來,我才注意到,原來高行健早已「夫子自道」,說明他正是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找到一種具有原創可能性的第三空間,一種可以展示「內心視像」的方式。他說:
在具象與抽象之間,其實有一片廣闊的天地,有待開拓和發現。具象發端於對現實的摹寫,以再現作為繪畫的起點;抽象則出於觀念或情緒的表現。再現與表現,是繪畫的兩種主要手段。我的畫則企圖找尋另一個方向,去喚起聯想,既非描摹外界的景象,也不藉繪畫手段宣洩情感,而是呈現一種內心的視像。這種內心的視像並不脫離形象,而又不去確定細節,給想像留下餘地,令觀眾也產生冥想。意境大於形象,讓畫面變得深遠,喚起的這種心理的空間,使繪畫超越了二度平面,這又不同於傳統繪畫中的透視。(《高行健:具象與抽象之間》序言。美國:聖母大學斯尼特美術館)
除了德國路德維希博物館館長提示我去注意抽象與具象之間外,還有另一位館長的話,也讓我產生深深的共鳴,這是葡萄牙烏爾茨基金會(Würth Portugal)在二○○九年舉辦高行健繪畫回顧展時,會長路諾.第牙斯(Nuno Dias)說的:
如果在幾個世紀之前,高行健無疑會是個文藝復興的藝術家,他繪畫,拍電影,而且寫各種樣式的作品,從小說、詩歌、文論、戲劇乃至歌劇。他的繪畫和文學作品毫無教條,誠如他在他著名的著作中為自己定位,獨自一人,這人不從屬於任何政黨、任何主義、任何潮流,遠離政治、社會生活和群體的思潮,在藝術中則充分地展示他獨立不移的自由思想。(《高行健:洪荒之後》。El Cobre Ediciones出版社)
這位葡萄牙藝術評論家真不簡單。他說高行健「毫無教條」、「獨立不移」,字字都切入核心。高行健從藝術策略上說,他找到具象與抽象之間的可原創地帶;從他的精神密碼而言,則完全得益於自身那種獨自一人、不依附任何外部力量的品格。高行健確實以「獨立不移」為自己的精神宗旨,以「獨立不移」為自救之路。他不依附任何政黨、任何主義、任何潮流,也不重複任何已有的哲學和已有的藝術方式。他從八○年代我初識他開始,就一直懷疑二元論,質疑兩極對立,質疑「否定之否定」等時興的辯證法。他一再說,他看重禪宗的「不二法門」,相信老子的「三生萬物」,他確信「三」比「二」重要。唯有「三」的哲學,才能打破固化的「二」的兩端(即死於「二」的兩端)。「三」包括兩極又不落入兩極,這才是康莊大道。他的繪畫,就行走在這個康莊大道上。前人沒有走過,他偏要走;前人未敢行,他偏大步行。前人視為異道而迴避,他偏視為常道而大膽探索。高行健的自由哲學與自由思想幫助他走出自己的路,無論是小說、戲劇、繪畫,他都走出一條前人未曾走過的路。
在「好奇」地尋找西方藝術評論家的審視眼睛時,我意外發現有一個「關鍵字」與我久蓄於心中的思路相逢,讓我高興得幾乎要叫喊出來。法國文學與藝術史家兼畫家丹尼爾.貝格茲(Daniel Bergez)在二○一三年巴黎索伊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的論著,竟以「高行健:靈魂的畫家」(Gao Xingjian: Peintre de l’âme )為題目——是的,高行健是靈魂畫家,他畫物,但不是「物的畫家」;他畫人,但不是「人的畫家」。高行健筆下的人,不是人的肖像,而是人的靈魂,所以我說高行健畫的不是「色」,而是「空」;不是「身」,而是「心」。靈魂包括意識與潛意識,靈魂難以歸類,靈魂在抽象與具象之間,靈魂實在又神秘。法國這位多才多藝的畫家與評論家,還在專著的序言中如此說:
高行健無法歸類、極為獨特的創作,延續而又顛覆了它得以滋養的兩個泉源。他把同書法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文人畫的傳統加以轉向,又引入抽象;超越文學之源,同時又把所謂「現代」藝術的粗製濫造和老套子廢除掉。他的畫作讓人觀審,不如說訴諸觀者的內心世界。誠如所有偉大的創作,他的畫自有訣竅和奧秘,而且坦誠毫不掩飾其奧秘,也因為這作品的存在就構成了謎。本書不過是對看畫作一些引導,以利讀者進入這無限幽深而豐富的畫作。(《高行健:靈魂的畫家》。巴黎:索伊出版社。獲二○一四年法國藝術科學院獎)
丹尼爾.貝格茲講得多麼好,高行健延續又顛覆了它得到滋養的兩個泉源,即中國文人畫傳統與西方的現代藝術傳統。高行健努力吸收傳統的資源,但又揚棄傳統寫夢的象徵手法,直接訴諸潛意識。讀了貝格茲之後,又意外地發現另一則精彩的評述。法國藝術評論家法蘭索瓦—夏邦(François Chapon)對高行健的畫讚揚道:
你的繪畫如此自由揮灑,獨具一格,與任何流派、任何既有的技法迥然不同,這偉大的藝術突破了空間的規則,也不囿於時間的限制,在人類意識中尚未形成的影子裡發現了調節宇宙運動及其反映的和諧。我欽佩你不墨守各種信條、定義、教義以及秘訣等陳規,從既得的知識沼澤中躍出,朝原始本質的淨區攀登。(《高行健:畫布上的水墨》序言。巴黎:克洛德.貝爾納畫廊)
「從既得的知識沼澤中躍出,朝原始本質的淨區攀登」——這話講得何等好,何等有見解又何等有文采!我正是從這裡出發,去瞭解高行健返回文學初衷與藝術初衷的思路。無論是德國、葡萄牙評論家,都不約而同地說出高行健繪畫最根本的成功秘訣,這就是自由揮灑,獨創一格,獨樹一幟,獨造一局。高行健無論走到哪裡,原創性就跟到哪裡。
近十幾年,對高行健繪畫的「好奇」、「注視」,使得我逐步向高行健的水墨畫世界靠近,因此,此次他的比利時繪畫雙展便格外引起我的興趣。從二月開始,我就遠遠地望著西歐,遠遠地望著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和它的展品及評論。
西零沒有忘記我的委託,她把譯好的許多有趣評論發來給我,讓我真是大開眼界,並深深地佩服比利時那些不為時髦所動、卻為真正的新鮮藝術吶喊開道的美學家。評述太多,我找幾則給朋友們看看。
比利時伊克塞爾美術館的網站介紹他的大型回顧展:
這個展覽令人們發現一位當代獨特的藝術家他那強勁而有詩意的作品。他藉水墨在紙上的渲染來展示意識的自由流動,藝術家以其內心的活動向我們顯示了一派既有表現力又富有人性的普世性作品。現今這莫名其妙的時代,「高行健回顧展」卻透過對絕美的追求,啟示我們從內心去充實自己。他的文學和藝術作品既非政治化,無傾向性,更無知識分子腔,從而普世相通。雖然圍繞著自我抒發感受和激情,高行健卻從內心出發,提煉出絕然非個人超越時代本源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又追求純粹的審美。
比利時皇家美術館網站進而介紹高行健的專題展廳「高行健:意識的覺醒」:
藝術家以其意識的覺醒,邀請觀者悠遊於水墨之上、畫面之間,去感受生存赤裸的狀態,博物館從而變成了凝神沉思之地。高行健是東西方世界的一位擺渡者,以東方作為基石,叩問西方的現代性觀念。他的作品同時也溝通繪畫與文字書寫。藝術家的哲學令這場所超越展廳,比利時皇家美術館把這個大廳變成一個真正的精神醒覺之處。
此次高行健雙展的策展人、比利時皇家美術館館長米歇爾.達蓋(Michel Draguet),也是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VUB)的教授,他在《精神自由學報》(Esprit libre)上撰文寫道:
高行健的繪畫有其中國文化的淵源,同時又覺悟到得擺脫西方當代藝術的時髦和教條。對他來說,當代藝術在西方已經成為思想的桎梏,觀念藝術、社會學藝術,凡此種種,現今已成了膚淺而乾澀的智力教條主義。
又說:
然而他深深植根東方的這些畫,卻不對西方關門,不僅吸收西方藝術,而且悠遊其間。高的圖像有雙重含意:既組合構成一定的形象,又隨著視線的遊移而分解,無限展開。高行健說,繪畫便是化解言說。繪畫對高來說,便是置身於忘言。他投身於音樂喚起的忘我境界。旅程由此開始,每一張畫呈現靈山的一幅景象,而這靈山總遙遙在望。既非他者,又排除集體,一意融合在自然之中。這種主旨的移位從墨海到雪意,通過汙泥的吞蝕,又被太陽消融,畫家由此找尋其生存的依據。這裡尋求的並非是系統的實證,卻出之於顯然易見。魔法只來自視像,這展覽希冀的正是這視像帶來的片刻充盈與寧靜。
米歇爾.達蓋為這場雙展還寫了一部洋洋大觀的專著,這本由巴黎的哈贊出版社(Editions Hazan)出版的畫冊《高行健:墨趣》(Gao Xingjian: Le Goût de l’encre)序言中特別寫道:
他維護傳統卻毫不保守,並非要死守中國的傳統繪畫。相反的,他從古老的宣紙和水墨中,找到了強而有力的表現手段,來表達我們現代人複雜的情感和感受。他的探索全然是當代的:一方面,他把人的生存條件和身分作為中心課題;另一方面,他把小說、戲劇、音樂、詩與歌劇所有的表現手段都動用起來,用來回答這些課題,而這解答既是獨特的,又是統一的。
書寫與繪畫中,他特別看重這種把感受和哲思聯繫在一起的流動思想。二○○○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揮灑得更為自由,而且從未放棄圖像,這些光與影的顯示,不僅體現在新的領域如歌劇之中,也是他戲劇思想的延伸和總結;在電影中,對圖像的運用同樣達到了極致。
比利時皇家美術館貝漢廳陳列的高行健專門為此創作的紀念碑式的系列,展示了一派精神的空間。言詞的音樂和音響的言說彼此呼應,繪畫因而變成了他思考的結晶,戲劇、歌劇與電影可說盡在其中。這種延伸使得他的繪畫構成一番精神層面。圖像在他這裡,既變成依據於感覺的一種思想,又是一個銀幕,超越其表象,令人深思的赤裸存在。(《高行健:墨趣》。巴黎:哈贊出版社)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歐洲的藝評家和學者都從歐洲繪畫史的視角來評述高行健。他們不僅對高行健的繪畫表達高度評價,還注意到他在藝術史上獨到的美術見解。他確實超越二十世紀流行的美學框架和藝術史觀,反對藝術家從政,不以社會判斷、政治判斷或倫理判斷來代替審美判斷,而且還提供了繪畫的新方向。
最後,我們不妨用高行健早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另一種美學》中即概說過的話,來思索他為什麼在繪畫上也能走向高峰:
回到繪畫,在不可畫之處作畫,在畫完了的地方重新開始畫;⋯⋯回到繪畫,在藝術的內部去找尋藝術表現的新可能,在藝術的極限處去找尋無限。⋯⋯回到繪畫,從空洞的言說中解脫出來,把觀念還給語言,從不可言說處作畫,從說完了的地方開始畫。(《另一種美學》。臺灣:聯經出版公司)
十五、六年前高行健已形成的繪畫觀——即「回到繪畫」的繪畫觀——已在西方宣示,而且得到西方藝術思想家的共鳴與不斷引證,而我卻有所忽略。二○一五年上半年,我在關注高行健的繪畫雙展之後,重新閱讀他原先的畫論、美學論著,讓身為高行健一個三十年的老朋友的我,真是感慨萬千。他的繪畫給世界提供了前人所無的心象、幻象和靈魂意象,也給所有精神價值創造者提示:只要有心、有智慧,創造奇觀的可能是永遠存在的。
二○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於美國科羅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