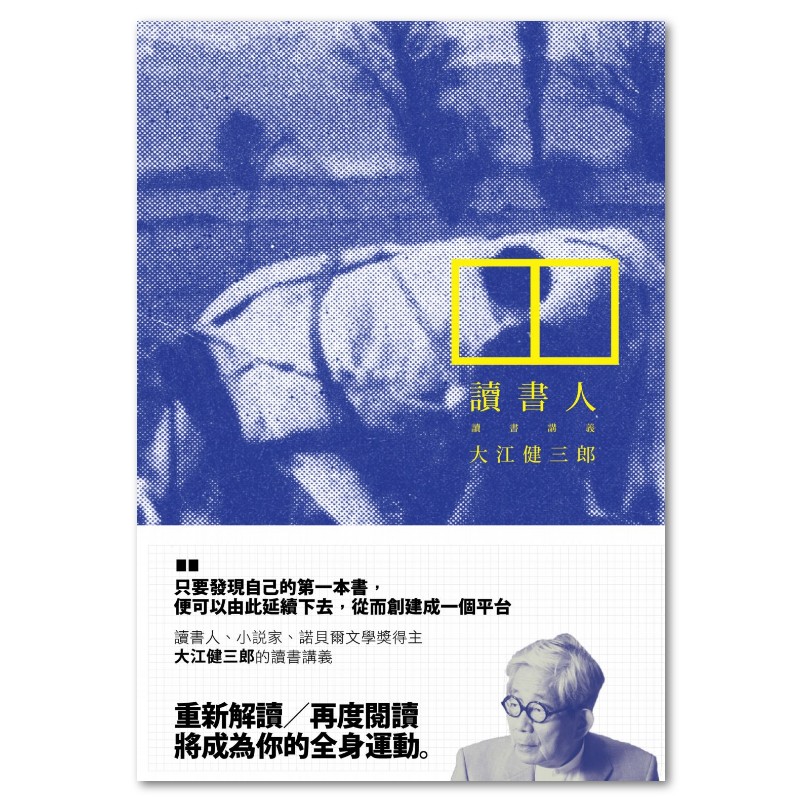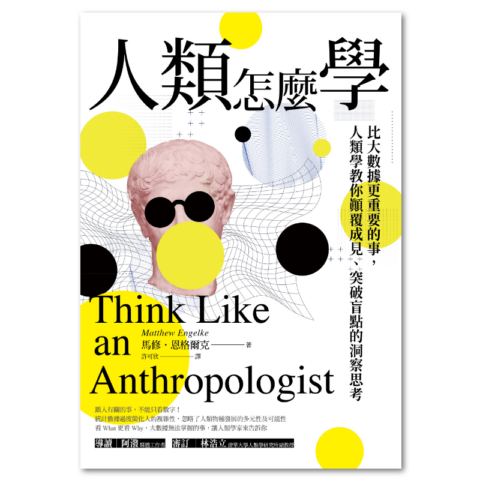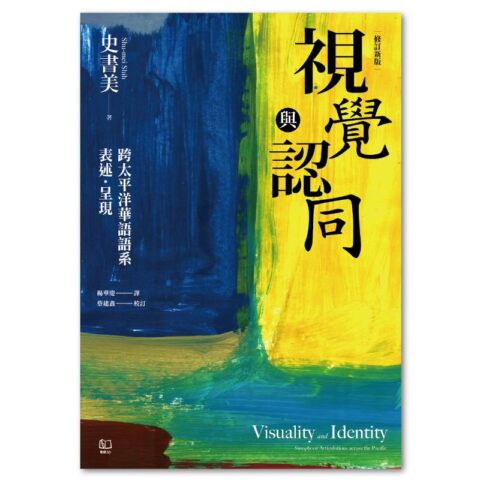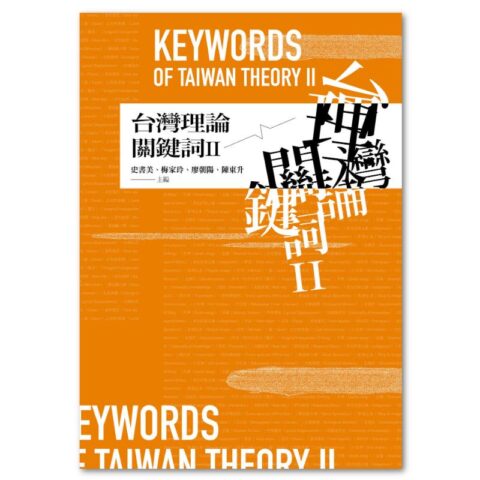讀書人:讀書講義
原書名:読む人間
出版日期:2010-08-03
作者:大江健三郎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64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6486
系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已售完
只要發現自己的第一本書
便可以由此延續下去,從而創建成一個平台
讀書人、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大江健三郎的讀書講義
重新解讀/再度閱讀:大江健三郎的讀書講義!
一半是寫作人,一半是讀書人,生活與讀書是如何連結起來的?
度過只是寫作的人生,只是讀書的人生,
世界的小說家大江健三郎,有著全部愛書人共同的「癮頭」。
好奇圖書館另一頭的那個人正在讀哪本書,趁隙跑去記下打開來頁面上的那句詩;
害怕忘記今天讀了什麼,筆記一本寫完一本,至今仍不間斷;
他讀過的書,紅筆藍筆、紙頁上畫滿重點,讀起字典更不輸看小說的瘋迷;
背誦所有喜歡的句子,希望跟自己喜歡上的書的作者成為朋友。
大江健三郎讀書、寫作一輩子的箇中滋味,盡在這本──讀書講義。
因著發現這些書,與這些書邂逅相遇,我覺得寫出自己所發現的這些書的那些人,都是自己真正的老師。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運。──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薩依德 一生的閱讀,一世的朋友
特別收錄《論晚期風格》之思想──全面閱讀薩依德
大江健三郎的讀書筆記──
閱讀某一本翻譯作品。
◎用紅藍兩色鉛筆將書中自認為確實精采的部分以及不太理解的部分一一畫上線條,如果是稍長一些的段落,則用線條圈起來,這就是我的作法。至於畫線的鉛筆,我之所以覺得至少須要兩種,是因為要用其中一種顏色的鉛筆,將感佩之處以及興趣濃厚之處畫上線條,這是一種肯定的行為。
我並不是「非常自然地開始寫小說」那種類型。
◎我總是首先閱讀外國的小說以及論文,在此過程中對其文體產生興趣。尤其是每當閱讀外國詩歌時,我總會萌發這樣的念頭,於是絞盡腦汁創造出自己的日語體,因而我的文章被人說為疙裡疙瘩、難以閱讀。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即便現在,我們這些純文學小說家的日子過得也不算輕鬆啊。
◎尤其那些青年作家就更不容易了,似乎大家都甘願忍受那種痛苦、忍受著那一切而生活而寫作小說,以這種態勢設法向社會推出自己。然後,便寫出一本幾乎沒有暢銷前景的作品。至於我,尤其在這種時候,首先就會閱讀威廉.布萊克的作品。於是,我便開始思考如何才能對應這一切。
所謂讀書,並不是被提供資訊這種層面的活動。
◎通過讀書可以讓我們知道,寫出那書的人的精神是在如何活動,一個人的思考又將使其精神如何發揮作用。讀者將借此發現這一切,感覺到現在的自己遇見了怎樣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也將能夠遇見真正的自己。
延伸閱讀
論晚期風格,薩依德,麥田出版
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阿多諾,聯經出版
音樂的極境:薩依德音樂評論集,薩依德,太陽社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大江健三郎,聯經出版
沖繩札記,大江健三郎,聯經出版
目次
中文版序 爲《讀書人》中文版面世而喜悅
第一部 生活.讀書
一 別了,我的書!
二 被驅離出故鄉
三 解讀文體,創造文體
四 始自於接受布萊克
五 書中的「令人眷念之年」
六 但丁與「令人眷念之年」
七 沒辦法!我必須埋葬自己的想像力和回憶!
第二部 《論晚期風格》之思想 ─ 全面閱讀薩依德
我作為「讀書人」而生活 — 寫在或是最後一次讀書講義之後
譯後記 感謝大江先生爲我們帶來的「最大樂趣」
序
後記
我作為「讀書人」而生活——寫在或是最後一次讀書講義之後
1
如同在這個連續講座中所說的那樣,我是一個讀書之人。這次雖說是講座,卻並不是面對在固定期間內前來聽講的學生諸君,只需專注於準備這項工作,幸福地上好每一天的課,從而實現長年以來的夢想。是的,我並沒有那樣。我的終身職業是小說家,除了摸索寫作方法外,不曾從事過專業研究,這一輩子也沒能得到大學裡的專職工作。現在,我終於得出「這樣挺好」的結論,意識到這個講座同樣不夠完整,就像我所曾做過的幾乎所有事情一樣!不過,我姑且先繼續講述我作為「讀書人」的經歷。
我是森林深處的孩子,有時,我會從小山包的山頂眺望圍擁著我們村落的、無邊無際的森林,頭腦裡在想,這個世界有著比這整座森林的樹木還要多的書!我沒有忘卻因那種體驗而帶來的暈眩般喜悅、恐懼和寂寥。在那之後,我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作為「讀書之人」,一直在逐一體驗著那種喜悅、恐懼和寂寥。也就是說,我認為半個世紀前的「預言」(儘管那只是微小的規模)得以實現了。
如果說,自己是作為「讀書之人」生活至今的,我的講座中或許會有聽眾質詢道:“不過,你不是把寫小說作為終生的工作了嗎?”
對此,我將這樣回答:寫小說是我終生的工作,而且此前已經寫了很多小說,不過,寫小說時我也是那第一個讀者。尤其在改寫和推敲 之時,我身體內的寫作人和讀書人各占一半。
倘若有人問及我在生活中作為「讀書之人」的比率,正寫著這篇後記的我的日常生活則是這樣的:早晨七點以前起床(因為現在正寫著作為自己「晚期工作”的、理應會成為最晚期之作品的小說),去寫每天確定了進度的定量草稿。從大學剛畢業那段時期開始,我便每三年選擇一位詩人、小說家或思想家,每天下午就持續閱讀其作品和有關他(她)的研究論著。這已經是將近五十年的習慣了。不過,假如郵件於下午早些時候送到(如果是用快件寄來的話,便要從早晨開始),其中大致會裝著一、兩冊新出版的書,我無法不讓自己打開那郵袋來看一看。於是,就這樣從一周前剛讀的那本書開始寫下去。
2
那是比我遠為年輕的優秀研究者採訪了我這二十多年間所敬愛的文化、政治思想家三好將夫之後出版的書。大約半年之前,我收到一封信函,說是三好將來東京,我便在他東京之行的第一天造訪了他應該會投宿的飯店,卻被取消了預約。幾天後,從他的新伴侶處發來一份傳真,說是因為急病而中止了旅行。由於已經是我們這個年齡了,我聞之不禁心緒黯然。然而,在我急急閱讀寄送來的那本書的過程中,卻猜想到至少是他中止旅行的另一個緣由,那就是他失去了與我會面並進行對話的興趣,我由此而體驗到另一種黯然心緒。在那本書裡,印有他的下列話語:
可是,我所感到的困難,是無論怎樣努力,也難以維持與身在日本的那些人展開對話。這確實是個嚴重問題。我認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與大江先生維持著一種對話關係。然而,現在我卻開始覺得那是我的錯誤。他並不進行會話。他喜歡說話,而且也很擅長。不過,他似乎並不聽別人說話。或許,他認為自己這就是在聽著了。
我現在的心情並不明朗,卻不會因此而向三好解釋,也不想設法恢復關係。他不是那樣的夥伴。毋寧說,我體驗到一種爽快,意識到自己人生中的一個終結。我只想對大家說,我承認,就像每次與三好見面時的那種表現那樣,我發現了有關自己的正確診斷,情況確實就是這樣,而且,這已經是難以治癒的痼疾了。
其實,我意識到這也是從孩子時代便留下的、自己的一個根本性欠缺(以及與此相應的困苦),而且,這也是因為我的決心所致,那就是模仿哈克貝利•費恩的口吻說出的「那麼好吧,我就作為這樣的人生活下去吧!」。
我曾邂逅諸多敬愛的朋友甚或師長,我真摯地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幸福。我曾有幸得到與諸如法國文學研究者渡邊一夫和作曲家武滿徹那樣的、確實可以稱為師長的那些人親密交往的時間,然而,即便在與他們說話時,對於就在自己面前的敬愛之人,我覺得自己也曾有過全然沒在聽講的瞬間。
當然,我很注意儘量正確聽取眼前的對話夥伴所說的話語。然而,會話開始後不久,我的頭腦裡便會接連浮現、湧出這位元對話夥伴所寫之書中的各種文章以及完成作曲的音樂之實體。我彷彿一面聽取他們的話語,同時總會引用在那些話語周圍擴展開來的他們的思想,像是在傾聽、注視著這一切。及至到了一定年齡,儘管自己的智力處於一般水準,記憶力卻很突出(比如較之於哲學類、科學類的認知能力)。這便是我曾對自己做過的評價。
也就是說,在現實中與他人說話(先前已經說過,寫小說時同樣如此)之際也是這樣,我是一個「讀書之人」,發自內心地從現在的對話中學習,為自己與那位元對話夥伴所共有的事物而喜悅,有時卻會較之於眼前的本人,我更關注那人寫下的著述,便會圍繞自己所知道的其著述整體,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展開對話。如果有人在長年真誠交往之後,終於對我難以忍受,這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若問及我當時是否對眼前的對話夥伴所講述的內容充耳不聞,我的結論則是否定的。如果與這些令我敬之愛之的人對話,或是聽其講座,抑或共同參加專題研討會,大致說來,從當天晚間直至翌日,我都會在筆記本上復原會議上的發言。在那之後,於我來說,這冊筆記本便成了他們著述的一部分。
話雖如此,及至讀了剛才那本書裡所顯示的針對我的批評後,我懊悔地意識到,自己(以及與我對話的師長們、我所敬愛的人們中的這人和那人某一位)沒能在規定的那段時間內,將相互間的對話展開為真正的對話、提升至討論式新高度和深度,我倒是滿意了,可是對於我的對話夥伴來說,所花費的時間可就是一段貧乏的時間了。然而,作為早已決定「那麼好吧,我就作為這樣的(讀書)人生活下去吧!”之人,我一直是如此生活過來的,而且在今後不會很長久的時間內,也打算這樣生活下去。實際上,存活於現世的、可以被稱為對話夥伴的那些人已經很少了……
3
我想要再度強調,「讀書之人」便是「引用之人」。戰爭失敗之際我十歲時,新憲法得以實施、新制中學出現在村子裡時我十二歲,在其後的三年間,我開始了作為「讀書之人」的人生。
在這三年間形成並一直延續至今的我的習慣,便是圍繞所讀之書「製作卡片」。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讀書卡片為何物,即便是筆記本,也是學校配給的東西,不能根據自己的喜好任意使用。當時,戰爭時期的物資匱乏仍在延續。剛開始時,我把家裡那些舊帳簿和書籍上餘有空白的地方剪切下來存放在箱子裡備用。讀書時,每當遇有自認為有趣或重要的處所時,便用鉛筆抄寫下來,移放在另一個箱子裡。我還記得開始這樣做的緣起。那時,我前往村裡建起的公民館的圖書室讀書(並不是收購來的新書,而是村裡各家湊在一起的舊書,排列在空落落大廳的一個角落處),吃晚飯的時候就會說起今天讀了這本書那本書,於是母親就問道「那書裡都寫著什麼呀?」,見我回答不上來,便顯出一副失望的模樣。父親去世後,是母親在獨自承擔著生活的辛勞,這是時她還不高興地說道:「你是為了忘卻才去讀書的嗎?」
於是,我便把面對母親沒能回答出的、有關讀書的問題寫了下來,後來這成了我的習慣。早在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自己能夠買得起的書還很少(我曾用也是母親教會的郵匯方法,郵購了岩波文庫版的《罪與罰》,我還有一個也是在那時形成的習慣,那就是將興趣未至而暫緩閱讀的書先收藏在盒子裡,當時便把《罪與罰》也放在了那個盒子裡面),我在自己前往書店選購書籍(並非我的錢有了富餘,因而只能每天前去精心選擇一冊)的那家大書店所在城市的高中讀二年級之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藏書。直至現在,我還保存著當年在那裡購買的創元選書叢書版的《蘭波詩集》、《坡詩集》和《中原中也詩集》,還有渡邊一夫《法國文藝復興斷章》(惟有那本書在持續閱讀過程中散開破損了,及至從渡邊夫人那裡得到同為岩波新書版的書後,便換下了那本破損書)。此外,我還往來於這個城市裡的美國文化中心,閱讀了從中學一年級便借助岩波文庫幾乎背誦下來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英語原版書。
我就這樣打下了作為「讀書人」的基礎,而且為受教於前面列舉過的一本書的作者而上了大學……回顧自己的一生,從那時起,就再沒改變過這條根本性的道路,度過著單純的人生。在這漫長期間內,一面讀書一面記卡片的習慣從不曾中斷。
自從我本人開始書寫文章並將其集結為書以來,最有效的技術,便是關於與這讀書卡片有關了。在我引用自己記憶中的話語、句節乃至更長的文章時,這些卡片保證了以上引用的正確性(查閱那些卡片之後,便進入書庫查對實際書籍,雖說原意如此,有時卻也會在放置於書櫥前的椅子上一直讀上半天時間)。我經常遭到一種批判,說是我的小說中有很多引用,不僅引用其他作者的書,甚至還引用自己的舊作。這種現象在一年逐年地增加,它原本就紮根於這個習慣之中,那就是首先作為「讀書人」的、然後是作為「引用人」的「人生的習慣」,這個習慣造就了我的文學。
如果說,有什麼具體的人生智慧能夠傳授給今後將大量閱讀書籍、開拓自己獨特工作的那些年輕人的話,那就是「讀書人」必須是正確地「進行引用的人」,因為那是在傳承文化。在這篇文章的開首處,我例舉了被中止長年交往的例子,這使我想起,我感到已經厭於同某人繼續維持關係,主動中止彼此間交往的,是從少年時期直至青年時期,弄丟了從我這裡借去的書也全然無所謂,豈止如此,甚至將那些書賣給舊書店的朋友,是而且在那之後,專門從我說的話語和寫的文章中進行不正確引用的朋友。
2007年4月20日
大江健三郎
作者:大江健三郎
1935年1月31日生於日本四國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3歲時喪父,在大瀨讀完小學、初中,1950年考進愛媛縣立內子高中,後轉松山東高中就讀,因而結識摯友伊丹十三。就學期間嗜讀大量西洋名著與日本古典文學作品。1954年為向法國文學研究者渡邊一夫學習,進入東京大學法國文學系就讀並開始寫作,陸續在校園刊物跟報章發表〈火山〉、〈奇妙的工作〉等作品;1957年的小說〈死者的傲氣〉,進入芥川賞候選名單,並為川端康成讚賞。隔年即以存在主義為形式、呈現社會與個人關係的作品《飼養》獲芥川賞,同時間自東京大學畢業,論文題目為〈沙特小說裡的意象〉。1970年,將文化人類學的理念引進小說創作的《個人的體驗》獲第11屆新潮文學獎,也將其推向國際作家的位置。
1960年,大江健三郎與伊丹十三之妹由里佳結婚。1963年,患有先天性腦疾的長子光出生,同年出版考察廣島核爆事件的《廣島札記》一書,對「生」與「死」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從四國的森林為基地,大江關心的是人類群體的共同課題,認為「倘若連成年人都不相信未來是美好的,卻硬要孩子們相信明天會更好,乃不負責任的態度」;以民主主義為態度,文學創作與參與、研究社會活動為其一生最重要的志業。1967年,以農民武裝抗暴事件為體的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獲第3屆谷崎潤一郎獎。1994年,因作品中「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開闢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文學的新道路」獲諾貝爾文學獎;大江健三郎於領獎時發表「我身於曖昧的日本」得獎辭,他也是繼1968年的川端康成後、第二位獲獎的日本作家。
2004年,參與加藤周一發起的「九條會」,致力於保護戰後成立的日本憲法,尤其針對主張「永久放棄武力與戰爭」的憲法第九條共同發出聲明,引發後續自主性的市民運動。2008年3月,因1970年寫就的作品《沖繩札記》揭發渡嘉敷島七百餘民眾在當時日方駐軍命令下被迫集體自殺一事,引起右翼團體發動「大江健三郎.岩波書店沖繩戰審判案」,受理的大阪地方法院駁回原告控訴。同年10月,大阪高等法院駁回原告上訴,一、二審大江健三郎與出版《沖繩札記》的岩波書店均宣告無罪。
2009年10月,大江健三郎首度訪台,出席「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研討會。同時由聯經出版《沖繩札記》以及最新長篇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中譯本。2012年4月,生涯集大成作品《水死》中文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