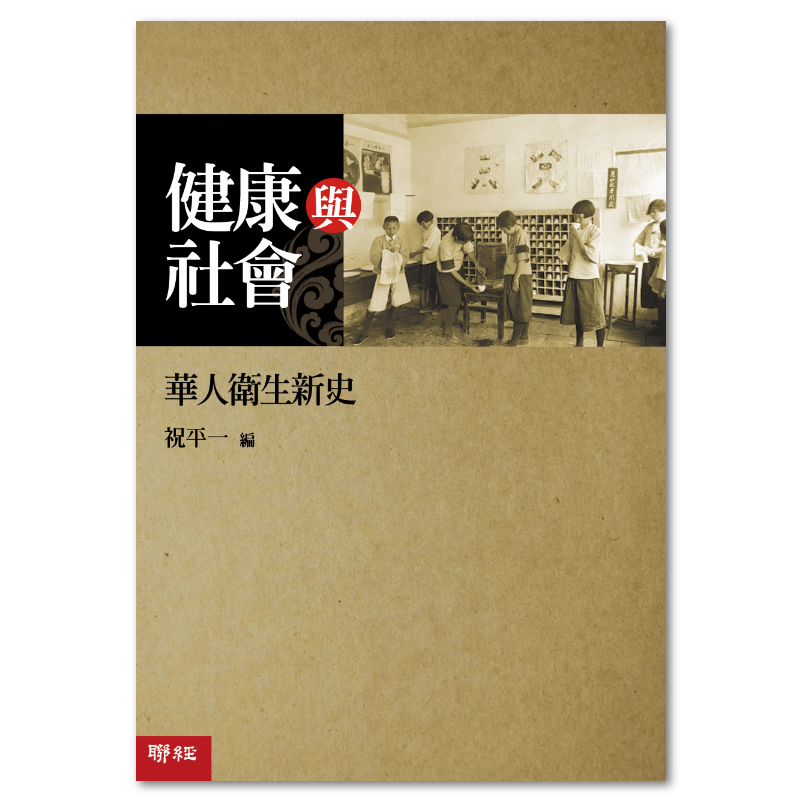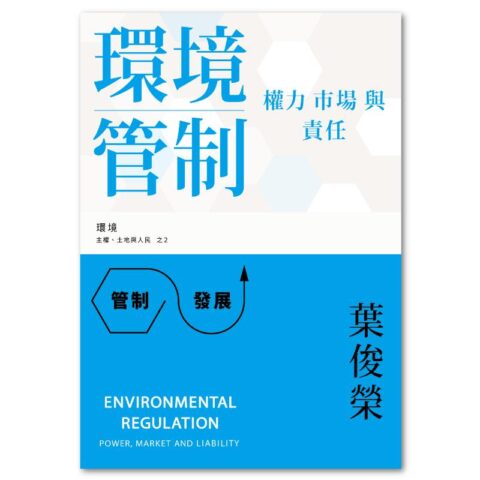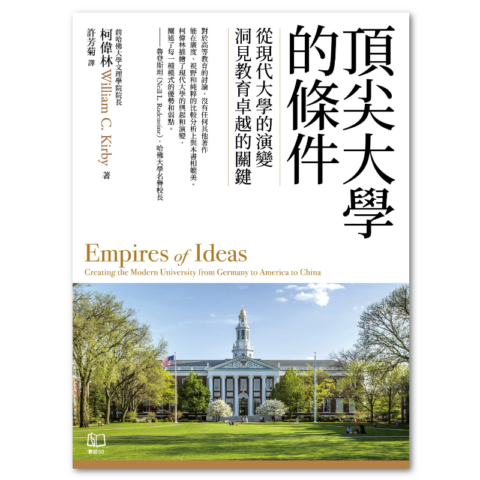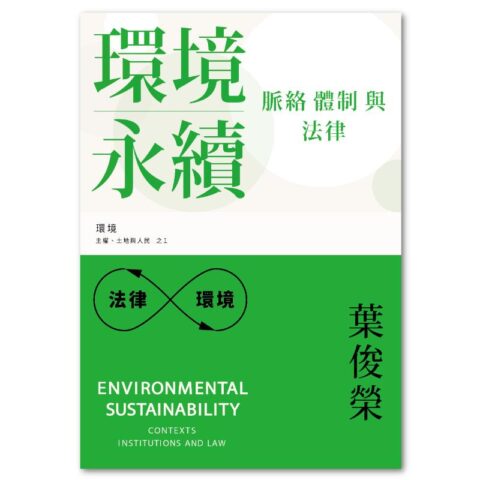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
出版日期:2013-01-29
編者:祝平一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60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41220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祝平一主編,乃華人社會衛生史研究之進階讀物,適於對醫療史或衛生史有興趣的研究生和學者。
《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以個案研究提出華人衛生史研究的可能徑路,以西方公共衛生體制進入華人社會為主軸,探討這一歷史過程中,台灣、香港與中國衛生觀念與實作之變遷。論題含括西方公衛體制輸入後,華人衛生體制的建立與變遷、衛生的實作和概念、操作衛生體制的物質文化、傳染病的防治、衛生體制如何形塑身體與主體、健康不平等與性別等議題。
本書精采內容含括了討論華人社會衛生史上的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近代中國醫院的誕生、19世紀中國通商港埠的衛生狀況、清代的痧症、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檯、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DDT與二次戰後台灣的瘧疾根除、美援下的衛生、民國時期的心理衛生、蘭嶼達悟族的精神醫療變遷與展望、當代中國農村衛生保健典範變遷、中國計畫生育等,皆為一時之重要研究成果。
※ 本書作者群
劉士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暨人文社會科技研究中心)
梁其姿(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劉士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暨人文社會科技研究中心)
林宜平(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蔡友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小濱正子(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授)
(姓名排列按本書目次順序)
編者:祝平一
台灣台南人,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研究興趣:明清的科技醫療與社會、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史。
導讀
第一章 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一個華人社會裡的新興西方觀念(劉士永)
第二章 近代中國醫院的誕生(梁其姿)
第三章 十九世紀中國通商港埠的衛生狀況:海關醫官的觀點(李尚仁)
第四章 瘟疫與社會:以清代的痧症為例(祝平一)
第五章 衛生、身體史、與身分認同: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檯為例(雷祥麟)
第六章 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與特徵(劉士永)
第七章 對蚊子宣戰:DDT與二次戰後臺灣的瘧疾根除(林宜平)
第八章 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郭文華)
第九章 預防、適應與改造:民國時期的心理衛生(王文基)
第十章 巫醫、牧師與醫師:蘭嶼達悟族的精神醫療變遷與展望(蔡友月)
第十一章 當代中國農村衛生保健典範變遷:以合作醫療為例(劉紹華)
第十二章 中國計畫生育的開端──1950-1960年代的上海(小濱正子)
導讀/祝平一、劉士永
本書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成員以個案研究為教材,提出華人衛生史研究的可能性與相關議題。為便閱讀,本書刪去繁瑣的學術性註腳,但在書末開列引用或參考書目,以便讀者查考或更深入探索相關課題。
本書共收文十二篇,以西方醫療與公共衛生體制進入華人社會為主軸,探討這一歷史過程中,各地華人社會的衛生體制、觀念與實作之變遷。時序上涵蓋清末至當代;地域上則包含了臺灣、香港與中國;論題方面則有:一、西方殖民主義與華人衛生體制的建立。二、華人社會如何轉換來自不同西方社會的公衛體制。三、西方公衛體制傳入後,如何引起華人社會衛生實作和概念的轉變。四、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華人社會如何操作其衛生體系。五、傳染病的防治與華人社會的公衛體制的實作。六、操作華人社會衛生體制的物質文化。七、衛生體制如何形塑華人社會中身體與主體的概念。八、華人公衛體系中的健康不平等問題。九、公衛體制中個人的能動性與性別議題。十、研究者如何建構華人社會的衛生史。
劉士永在〈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近代華人社會裡的新興西方觀念〉一文中,簡單扼要地描繪了西方公共衛生傳入華人社會的歷史。雖然,華人社會公衛體制的建立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相繫,但劉士永指出,這段歷史相當複雜。即使當時歐美諸國已分享類似的醫學典範,但各國間的公共衛生理念和執行方式卻相當不同。東亞國家和華人社會利用西方傳入的體制和知識建立自己的公衛體系是個相當曲折的過程,非僅是一成不變的橫向移植。梁其姿以廣州和香港為例,探討近代中國醫院的誕生,為此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證。當時,無論是中式或西式醫院,均是慈善組織與醫療機構的混合體。然而,在西方傳教士的引介下,西式醫療與醫院體制進到了中國,且穗、港地區的華人以開放的態度接受了新的醫療知識與體制。他們相信西醫的外科手術,而且很快地將西醫外科知識與中國傳統醫學結合,解決自身的問題,發展新的知識;他們信任中醫內科的醫療效果勝過西醫,並借用西方的醫院制度,成立以中國傳統醫學為主,或中、西醫結合的醫院。梁其姿並指出,當時穗、港地區的醫院彼此競爭,也積極發展與地方政治、社會、商業精英的密切關係,以取得更多資源與更大發展的空間,而將衛生體制的成立、醫學知識的混合置於更複雜的社會政治網絡中。
19世紀下半葉,在華的傳教士、外國醫生、中國的西醫生等歷史行動者在與殖民帝國相關的海關機構、租界、通商港埠等處,漸次傳入西方醫學與公共衛生的概念與作法。李尚仁以海關醫官為例,呈現西方醫學眼下所見的中國衛生狀態。李文指出,海關醫官「對中國環境衛生的批評,也是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秩序未能符合西方標準的一種反應」。他們所見之港埠華人衛生狀態,亦反映西醫所處的時代性與醫學思考的特徵。李文提醒讀者,不當只以科學進步的角度解讀華人社會的衛生問題。對於衛生的觀點,本身便蘊含了觀察者自身的訓練,甚至於對他者的文化預設;但除了解構歷史行動者外,反身性(reflexivity)的思考亦適用於研究者上。郭文華檢討當前美援醫療的歷史書寫,他贊同美國科學史學者范發迪批評以國家為界線、單線發展的「甬道式國家科學史」(“tunnel history” of national science),提出結合醫療與社會的跨國際書寫取徑(international approach),以開拓美援醫療書寫的新方向。「美援醫療」的跨國際性質,導致衛生史書寫高度的複雜性。然而,這恐非特例,而是華人衛生史的常態,本集中之其他論文也彰顯了相似的書寫問題。
不論西方或東方,近代公衛體制的建立和傳染病的防治息息相關。祝平一以「痧」為例,討論西方公衛體制未入清帝國前,帝國處理瘟疫的方式,以襯映其後基於細菌病原學之現代衛生體制的差異。「痧」在清代的某些醫家中成為疫病的代稱,此亦引發在不同的時空中如何辨識疫病的問題。有趣的是,這個問題並沒有因現代細菌病原學的出現而解決。雷祥麟討論民國時期的肺結核,便是一例。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方及日本,結核病被視為是工業化與都市化引起的疾病,但在中國,卻被認為與中國家庭及在其中所養成的惡習有關。因此,對疾病性質的界定,往往影響了國家和社會應對該疾病的方式。本集中劉士永、郭文華和林宜平所提及臺灣瘧疾也是如此。關於國家、社會與疾病的互動,祝平一、雷祥麟和郭文華不約而同地引用了查爾士‧盧森堡(Charles Rosenberg)「框架疾病」(framing disease)的概念,以處理國家、社會和疾病之間複雜的關係。
公共衛生之推行,有賴體制之建立及施行時所用之物質器具。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與研究特徵〉一文,探討了日本殖民帝國在臺灣建立公衛體制的幾個關鍵問題:如疫病的防治與公醫的建立,並解構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在解釋日治時期衛生與醫學研究上的角色;將日本殖民政治的現代國家特質及其相關之衛生與醫療作為,置於20世紀上半葉現代國家所可能具備之操控特質中,並反思國家的宏觀權力與各種體制交織而成的傅柯(Michel Foucault)式的微權力配置。傅柯式的監控(surveillance)與規訓(discipline)的議題,常出現在有關公共衛生的研究中,如美援時期臺灣衛生所的建立,或是人口控制等。這類反實證主義進步觀的理論觀點,如何在資料上實證,以及其與現代性間的糾葛,乃衛生史中常見且值得關注的理論問題。
微權力的配置最常出現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所使用的器具,透過物質文化,形塑人們的主體性。雷祥麟分析了民國時期新設計的衛生餐檯與個人衛生杯在肺結核防治中,重塑了衛生習慣、身體與「個人」這一概念。國民政府在執行衛生政策的過程中,透過物件為中介,改變習慣,樹立「個人」之存在,並攻擊傳統作為限制「個人」的「集體」──中國家庭──以訓練出合於民國政治想像的新公民。因此,衛生不僅關乎醫療和健康,而和政治、社會與文化纏成一密不可分的整體。林宜平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瘧疾根除的歷史經驗,討論DDT如何成為聯繫WHO、臺灣和美國的科技物,並在冷戰的歷史脈絡、臺灣因戒嚴封鎖以及人員承繼日治時期的知識傳統,而得以克盡全功。然而,臺灣除瘧之成功經驗,不在於DDT的效能,而在於臺灣特殊的歷史與環境,因而難以在其他地方複製。但DDT所帶來的危害及其後的禁用,也說明了在公衛的現代性論述中,往往被忽略的正是所謂進步所付出的代價。
除了物質環境的配置,衛生制度從身體形塑主體的手段尚有心理重建。不論是西方的心理衛生或精神醫學,傳到華人社會後,必須面對在地文化對心靈問題既有的解釋與解決方案;不過,以西方知識處理在地人的心靈問題時,卻也改變了當地社會對精神與心理的觀念。王文基討論1920至1940年間中國心理衛生的推動者如何改變個體與周遭環境,以培育健全的人格。這一自我技術也建立了「青少年」、「青年」等心理知識關照的新範疇。在當時動亂的時代背景下,不論由雜誌或醫療機構所推行的心理衛生運動,也許影響有限,卻呼應著雷祥麟文中家庭作為必須被改變的中國社會核心體制的現象。與此相似,蔡友月探討臺灣蘭嶼的達悟人如何以其傳統文化、基督宗教與現代精神醫學詮釋和對待精神病人。她的論點與一些視現代醫學只是異化和監控「瘋狂」的論點不同,認為雖然「精神病人」的標籤可能帶來污名化的後果,但病人從現代醫學而來的自我理解,與由此所生的「病識感」(insight),自願將自己納入醫療體系的自我鍛鍊,卻也可能是精神失序者解脫之一途。然而,現代精神醫療並不足以處理達悟人社會性的受苦經驗(social suffering)。因此,她提議適合達悟人的公共衛生照顧與心理治療和精神醫療復健模式,應該納入達悟人的特殊技能、部落獨特的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力量。這兩篇有關心理衛生的論文,在在顯示了公共衛生的問題不能僅以醫療技術的方式解決,而必須顧及文化、社會與經濟因素。
蔡友月的論文也描述了臺灣原住民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因為達悟人的精神失序,多源於其邊緣身分、遷移、歧視與經濟上的弱勢。即使在理論上平等的共產社會,健康不平等也是個重要議題。劉紹華透過1949年後中國農村衛生保健制度半世紀以來的變遷,說明公共衛生與政治體系及意識型態間的密切關連。1978年改革開放、醫療市場化後,農村與都市衛生保健服務品質的差距拉大,農村所獲得的資源遠較都市為低,因而乃有2003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之改革,以改善衛生資源的分配。中國農村合作醫療重新回到「平衡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基點,試圖縮短農村與都市間的衛生差距。中國處理農村醫療問題的方式與歐美國家視健康為普世人權,皆是特定意識型態下的產物。在自由經濟體系下,國民的健康問題是經濟勞力成本的一環;而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則試圖平衡發展與平等,以維護市場經濟下共產政權之正當性。她的論文也指出,衛生保健政策不只限於法規與制度面,還與政治、經濟和每個社會的價值取向相關;反之,要理解衛生保健政策、法規與制度,也必須從其社會文化脈絡著手。
一般公衛史的研究多採總體性的分析,多探究公衛體制對人的監控,而較少觸及體制下,個人能動性的問題。小濱正子討論1950至1960年代在中國計畫生育的濫觴期,上海女性便為了各種理由,主動選用避孕措施。不過,上海市的各種機構仍必須作為動員與宣傳的中介,以將相關知識傳遞給婦女。小濱的論文因而又回到了個人能動性與結構間難以切割的現象:女性雖有選擇權,卻也在動員體系下,使國家藉著女性的能動性,而介入控管女性的身體。到了「一胎化政策」實施時,國家介入中國女性的生育,變得更為明顯。
由於時間綿延,空間各異,本書無法賦予華人社會衛生史統一的面貌。但可以確定的是,衛生從來就不只是知識、體制、技術和物質條件的進步問題:它們是操作衛生體制不可或缺的條件,並且和各地的歷史脈絡共同演化,也因而無法孤立分析。再者,西洋的衛生制度,不論在中國或殖民地時期與戰後的臺灣,都曾被視為現代化的指標,成為政府大力推動的政務。但仔細分析之下,華人社會在接受西方衛生制度、建立自己體制的過程中,卻又雜糅了各式各樣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考量,使衛生史的研究益形複雜;且國家與個人、監控與反抗、平等與效益等現代性的問題,不斷以衛生體制為舞台,演出不同的戲碼。
在現今已接受西方公衛體制的華人社會,也和西方社會一樣,成為一個風險社會。衛生問題以許多新的面貌出現,如食品安全、婦幼衛生、以污染呈現的環境衛生、以職災與勞動環境形式出現的勞動衛生等。這些新而跨越學科邊界的議題,正挑戰有志於衛生史的研究者。
第七章 對蚊子宣戰:DDT與二次戰後臺灣的瘧疾根除
林宜平(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二次戰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各國推動以噴灑DDT(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消滅瘧蚊的瘧疾根除計畫。臺灣是戰後全球除瘧行動中,極少數完全根絕瘧疾並且長期維持無本土病例的國家。在衛生署出版的《臺灣撲瘧紀實》中,美援提供的DDT是強而有力的科技物,搭配設計精密的家戶噴射計畫,讓臺灣的瘧疾盛行率急遽下降,終至傳播瘧疾的矮小瘧蚊(An. minimus)銷聲匿跡,也讓臺灣從1965年起宣布根除瘧疾。
不過,DDT在1962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美國環保運動興起之後,在許多國家開始禁用,目前也是聯合國建議管制的十二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一。有趣的是,2005年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慶祝瘧疾根除四十週年,出版紀念特刊《抗瘧實錄》,在第二章〈臺灣根除瘧疾概況〉中,雖然有好幾張當年運送與噴灑DDT的照片,但是在正文中提及DDT的只有六處,許多除瘧細節的描述,都僅以「殺蟲劑」或「噴射」一語帶過。
到底DDT在臺灣根除瘧疾的公共衛生行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當年全面噴灑DDT到底是防治瘧疾?還是撲殺蚊子?本研究回顧瘧疾防治長久以來「對人法」(消滅人體內的瘧原蟲)與「對蚊法」(消滅蚊子)的科技爭議,並且描述臺灣戰後以DDT對瘧蚊宣戰的準備、攻擊、肅清與保全的技術細節,批判檢視瘧蚊的消失和瘧疾死因與盛行率的變化,討論DDT在臺灣除瘧計畫中的角色。
一、蚊、蟲與人:瘧疾防治的科技爭議
瘧疾是非常古老的疾病,瘧蚊與瘧原蟲和人類一起演化。James Webb描述瘧疾的世界史指出:瘧疾源起於兩、三百萬年前的非洲,在10萬年前傳進歐亞,然後在西元前1萬2000年左右,才傳入美洲;而瘧疾的根除,則是在20世紀中,從美洲、歐洲到亞洲,逐漸消退,目前瘧疾主要在貧窮的熱帶國家蔓延,特別是非洲。
瘧疾是一種急性寄生蟲傳染病,瘧原蟲經過中間宿主瘧蚊傳染給人類。相較於其他傳染病,瘧疾的感染性非常強,如果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死亡率非常高,再加上沒有疫苗,因此曾經全球蔓延。瘧疾防治和瘧原蟲、瘧蚊與人類三個物種有關:可以抗瘧藥殺死瘧原蟲;以滅蚊劑殺死瘧蚊;或是以紗窗或蚊帳隔絕人與瘧蚊的接觸。瘧原蟲的生命週期非常複雜,分別在人體內與瘧蚊體內進行有性與無性生殖,治療瘧疾就是消滅人體內的瘧原蟲,除了服用不同的抗瘧藥進行化學治療之外,只能研發疫苗。瘧蚊的生命週期也頗為複雜,和所有的蚊子一樣,瘧蚊是完全變態,必須經過卵、幼蟲(孑孓)、蛹及成蟲四個階段,才能夠完成發育;前三個時期居住在水中,雌成蟲因為吸食動物血液,成為許多寄生蟲的中間宿主,並且透過吸食動物血液,傳播疾病。消滅瘧蚊除了使用化學藥劑殺死水中的蟲卵、孑孓與蛹,或是以噴灑殺蟲劑殺死家戶中的成蟲之外,也可以透過清理沼澤,減少瘧蚊孳生源等環境生態方法,減少瘧蚊。以化學藥物消滅瘧疾最大的問題,就是抗藥性。瘧疾防治有「雙重抗藥性」的問題:瘧原蟲會對抗瘧藥產生抗藥性,瘧蚊也會對滅蚊劑產生抗藥性。
從19世紀的細菌論以來,防治瘧疾到底要採消滅瘧蚊(對蚊法),或是消滅瘧原蟲(對人法),二者有不同的理論與研究證據。例如,最先在瘧蚊的胃裡找到瘧原蟲,證實瘧疾是由瘧蚊傳染的英國軍醫羅斯(Ronald Ross),主張組成「滅蚊部隊」在瘧蚊繁殖的水域噴灑油劑,撲殺瘧蚊幼蟲,並且在英屬西非殖民地獲得初步成效;義大利學者倡導使用蚊帳、紗窗或使用驅蟲劑避免瘧蚊叮咬;而德國細菌學家科霍(Robert Koch)則在德屬新幾內亞進行實驗,對血液中帶有瘧原蟲的患者施予定時定量的奎寧(Chloroquine),撲殺人體內的瘧原蟲,而有很好的成效;科霍防瘧的中心教條是「治療病人,不是對付蚊子」。
由於瘧蚊的孳生與環境息息相關,因此瘧疾蔓延有五個重要因素,包括溫度(攝氏十六度以上)、水、動物、人和房屋。傳播瘧疾的瘧蚊有三、四十種,這些不同種的瘧蚊各有不同的習性:偏好不同的水(或淡或鹹,乾淨與否、是否流動等)、不同的血(牛血、豬血或人血)、不同的棲息地(室內或室外)、不同的作息(白天、傍晚或深夜)、不同的行為模式(一次吸到飽或是分次吸食)等等。調查研究瘧蚊的動物昆蟲學,因而成為預防瘧疾的重要研究領域。有關蚊子習性的科學知識,非常重要的是,蚊子(包括瘧蚊)在飽食動物血液之後,因為體重大幅增加,必須在垂直平面(例如牆面或家具上)暫時停留,消化體內多餘的水分,此一特性後來成為在家戶中噴灑DDT根除瘧疾的重要依據。
(一)日治時代的防瘧技術:對人法與對蚊法
臺灣曾經是不同殖民者眼中瘧疾蔓延的「瘴癘之地」,從清朝以來的漢人移民,到殖民初期遭逢臺灣熱而傷亡慘重的日本人,都視瘧疾為臺灣的「風土病」。直到十九世紀末,研究瘧疾的熱帶醫學在各國殖民地不斷進展,最終證明瘧疾是由蚊子傳染的,殖民國家才開始從傳染病的角度,重新檢視瘧疾。
日本殖民政府從1906年開始,有較大規模的防瘧措施,在甲仙埔採用科霍式的對人法,建議採(樟)腦工人及居民(包括健康者)集體服用奎寧,藉以預防並治療瘧疾。1910年在北投召集全區居民,以原蟲顯微鏡篩檢與脾腫測量診斷瘧疾帶原者,並且強制帶原者服用奎寧錠18天。1911年臺灣的鼠疫已經得到控制,日本殖民政府也開始建立瘧疾特別防治區,擴大防瘧活動,以對人法為主要方針,整頓環境等對蚊法為輔助措施,到1930年共有208個防治區,每年有超過三百萬人接受例行的抽血檢查。范燕秋認為,日本殖民政府瘧疾防治工作的推展進程,主要受科學與技術的影響,例如瘧原蟲檢驗方法、藥物治療,以及攻擊瘧蚊的技術等。
根據丁文惠有關日治時代防瘧的研究,1901年(明治34年)木下嘉七郎發表第一回臺灣肉叉蚊的研究報告,首度發現台北近郊的瘧蚊,到1903年木下嘉七郎和羽鳥重郎已經發現七種臺灣瘧蚊。1927年(昭和2年)森下薰前往印度「中央瘧疾研究所」,進行臺灣、印度與東南亞瘧蚊的比較研究,到1936年總計核定八種臺灣瘧蚊,並且提出十六種臺灣瘧蚊的檢索表。至於瘧原蟲生活史的研究,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大森南三郎,在瘧疾流行區持續進行瘧蚊自然感染率的研究,採集雌性瘧蚊成蟲,調查其帶有瘧原蟲的百分比。
顧雅文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的研究發現,對人法的空間分布一方面凸顯瘧疾與開發間的密切關係,一方面也透露防瘧決策的非科學因素。1919年防瘧政策由對人法轉向對蚊法,但是臺灣的對蚊法僅由受短期訓練的地方官員指派,常出現錯誤判斷或假防瘧之名實施環境美化,不但增加地方居民的無償工作,也很難收到瘧疾防治成效,因此對人法一直是日治防瘧政策的主流。顧雅文認為日治瘧疾防治充分反應殖民醫學的本質:以最容易的方法,確保立即的效益。
根據蔡篤堅的訪談,日治時代的瘧疾防遏所配置技術員與助手負責採血、驗血片與後續的治療,當時一般患者會主動到防遏所驗血,經檢驗員確定為瘧疾後,就可以得到免費的藥物治療。若是爆發大流行,政府也會強制該地區所有居民進行檢查。
從1906年到1942年,臺灣的瘧疾死亡人數逐漸減少,每萬人瘧疾死亡率也開始下降。在1911年之前,瘧疾是臺灣的第一大死因,瘧疾死亡率超過萬分之二十五;雖然從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大戰期間,瘧疾又有一波流行高峰,但是從1912年至1921年,瘧疾開始在第一大死因與第三大死因之間沈浮,和瘧疾競逐第一大死因的,是因為人口往都市集中而開始盛行的肺炎與腹瀉;1925年起,瘧疾下降至四名之後,死亡率也降到萬分之二十以下;到1935年,瘧疾已經成為臺灣的第十大死因,死亡率降到萬分之七點八,該年臺灣死於瘧疾的有3,787人。不過二次大戰期間,瘧疾防遏所的功能逐漸削弱,治療瘧疾的藥物奇貨可居,又掌握在軍方手裡,一般民眾不易取得,再加上空襲期間家家戶戶備水防火,瘧蚊大幅增生,又有大量人口由都市遷往鄉村避難,增加許多對瘧疾缺乏免疫力的易感群,因此二次大戰期間瘧疾的疫情在臺灣再度失控,1942年瘧疾再度成為臺灣的第四大死因,死亡率高達萬分之十點二。
(二)DDT殘餘噴灑:戰後防瘧新技術的誕生
DDT是1873年在奧地利的實驗室裡合成的,但是DDT的殺蟲神效一直到1939年才由任職於嘉基(J.R. Geigy)公司的瑞士化學家穆勒(Paul Müller)實驗發現。DDT殺蟲不但有廣效(什麼蟲都可殺),而且因為具有殘留性,所以效用長久,更重要的是價格非常低廉。DDT於1942年上市,而穆勒也因為這項重要的發現,在1948年獲頒諾貝爾生醫獎。
二次大戰期間英軍與美軍開始大量使用DDT消滅蚊蚤,預防傳染病。從1942年起,美國耗費鉅資,在美國南部每三個月一次,到家戶中以殘餘噴灑(residual spraying)DDT的新技術消滅瘧蚊,預防瘧疾跟隨軍人返鄉而再度盛行。二次大戰之後,DDT在美國廣泛使用,不但噴灑在農田裡、牧場裡,也噴灑在家戶中。當時的科學研究雖然證實DDT具有微毒性,但是美國農業部認為,只要遵照說明書使用,是安全的。如在1947年的廣告中(圖三),雞、狗、牛、馬鈴薯、蘋果與人共舞,齊唱「DDT為我好」。文中宣稱,DDT在1946年已經通過系列科學研究證實,只要妥善使用,可以「造福全人類」。從1950年起,美國每年生產及使用的DDT超過五千萬磅。
除了在美國國內噴灑DDT防治瘧疾之外,美國的洛氏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二次大戰末期的1944年,選在義大利的沙丁尼亞島,進行DDT滅蚊的先驅研究。瘧疾曾經是義大利的「國病」,從中世紀起,瘧疾就是沙丁尼亞島嚴重的地方疾病。在20世紀初防瘧立法、免費施放奎寧以及法西斯政權的環境整治策略下,瘧疾盛行率與死亡率都開始下降。但是在二戰末期,德軍為了阻撓聯軍前進,放水淹沒大片沼澤地,聯軍為恐引發瘧疾大流行,因此從1944年開始進行以DDT根除瘧蚊的田野試驗。主導這項研究的,是羅索(Paul Russell)和索普(Fred Soper)兩位美國公衛專家,不過當時的計畫目標不是根除瘧疾,而是根除當地的瘧蚊。索普等人並且發表研究報告,討論在1944至1945年間,在沙丁尼亞家戶中噴灑DDT,有效減少瘧蚊密度的成果。
二戰結束之後,洛氏基金會補助沙丁尼亞的除瘧計畫。從1946年到1950年之間,除了進行DDT家戶噴射滅絕帶有瘧原蟲的瘧蚊成蟲之外,也在沼澤地噴灑DDT,殺死孑孓。1948年並且動用直昇機與噴射機,從空中噴灑DDT。此一瘧蚊根除計畫其實是失敗的,沙丁尼亞當地的瘧蚊經過DDT陸海空大掃射,並未滅種,但是沙丁尼亞的瘧疾卻根除了,以家戶噴灑DDT阻斷瘧原蟲傳染途徑的除瘧技術,也因此一計畫成果而確定,後來成為全球除瘧標準化的作業程序。索普等人發現,DDT使用在消滅水中的瘧蚊幼蟲,不過是另一種殺蟲劑,沒有什麼太特別,但是應用「DDT殘餘噴射」技術,將DDT噴灑在家戶中的牆壁上,因為DDT具有長效性,瘧蚊吸食血液之後若停留在牆上,接觸到具有神經毒性的DDT會立刻昏厥致死,可以有效阻斷瘧原蟲的傳遞與蔓延。索普認為透過全面DDT殘餘噴射,再加上積極治療受感染的瘧疾患者,不只可以「控制」瘧疾疫情,還可以完全「根除」(eradicate)瘧疾。更重要的是,DDT價格非常便宜,是撲殺蚊蟲、消滅傳染病時最好的「化學武器」。
以DDT殘餘噴射根除瘧疾,建立在非常豐富完整的瘧蚊與瘧原蟲知識上:瘧蚊在叮咬瘧疾患者之後,只要不活過七天,瘧原蟲就無法在瘧蚊體內成長至唾液腺,進而叮咬感染下一個人;而人類如果感染瘧疾,縱使沒有治療,在三年內瘧原蟲也會自動消失,所以只要連續三年全面噴灑DDT,瘧蚊就不會散播瘧原蟲,而瘧原蟲也會在人體內消失。瘧疾是二次大戰期間影響軍力的重要疾病,包括DDT與合成抗瘧藥物氯奎寧,都是美軍在二戰期間發展出來的,而除瘧行動所使用的戰爭隱喻,也符合戰後的主流文化。索普的除瘧方法,仿效現代戰爭:由穿著制服的任務小組,帶著噴槍,進行全面搜索與摧毀任務。1955年索普在美國國會的支持下,獲得鉅額經費補助,並且經過第八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會員國投票通過,以DDT殘餘噴射技術,展開全球根除瘧疾計畫(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全球有六十六個國家參與,並且還有十七個國家候補,不過很特別的是,所謂「全球」除瘧,竟然不包括瘧疾盛行狀況最嚴重的非洲國家。索普滿懷雄心壯志,希望七年內能在世界各地,完全根除瘧疾。
當年美國國會慷慨補助五點二億美元的經費協助全球除瘧,除了人道援助之外,也有經濟與政治效益的考量。根據Andrew Spielman與Michael D’Antonio的說法,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其一是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工。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加工廠,因為勞工為瘧疾所苦,增加成本,等於每年繳交三億美元的「瘧疾稅」,協助發展中國家根除瘧疾後,美國可以在這些國家增加大量健康並有具生產力的勞工。其二則是,當時正值美蘇「冷戰」,美國需要積極與世界各國結盟,與蘇聯對抗。瘧疾蔓延與貧窮息息相關,而貧窮又是共產主義的溫床,根除瘧疾不但可以預防共產主義的擴散,而且在世界各地背著「美國製造」(Made in USA)噴射器的DDT噴灑工,也是散播美國科技與進步的最好宣傳。除了大筆經費支持外,美國總統愛森豪與甘乃迪,都曾經公開對瘧疾宣戰,誓言全面掃蕩(all-out)瘧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