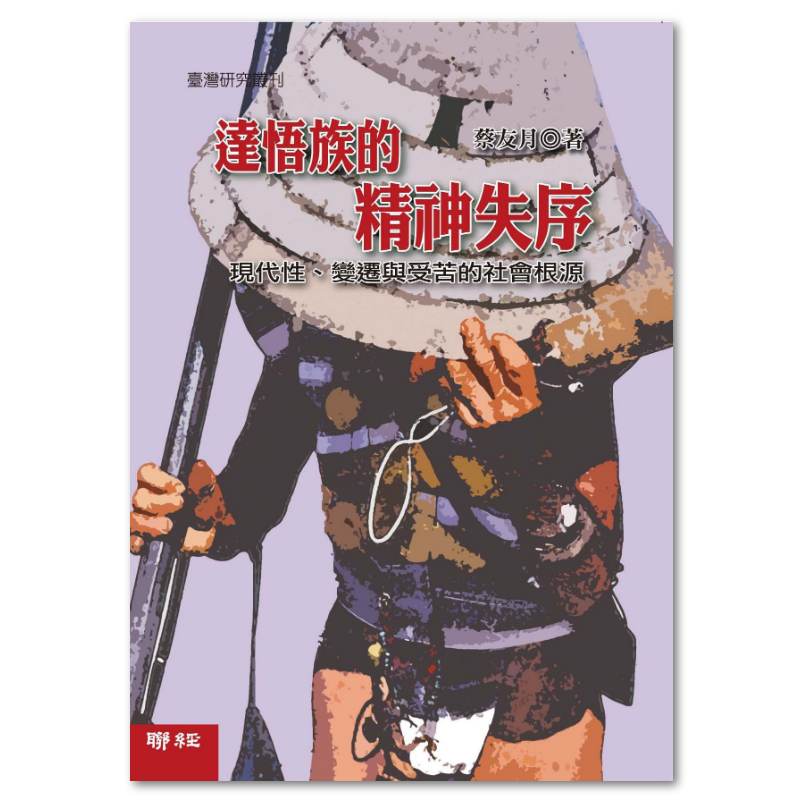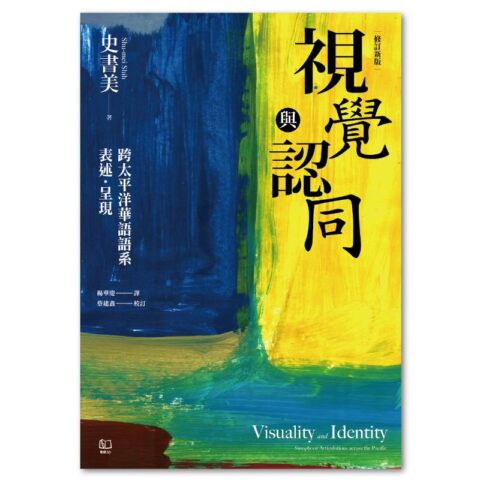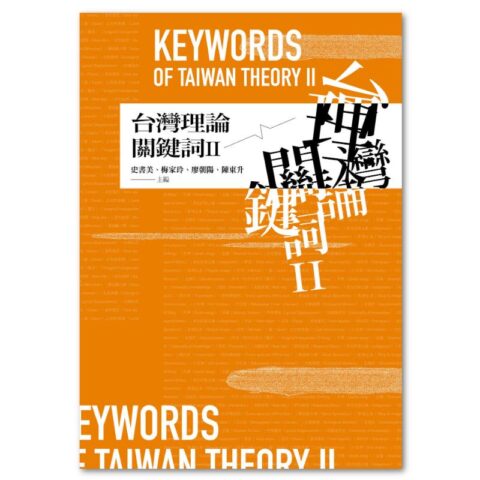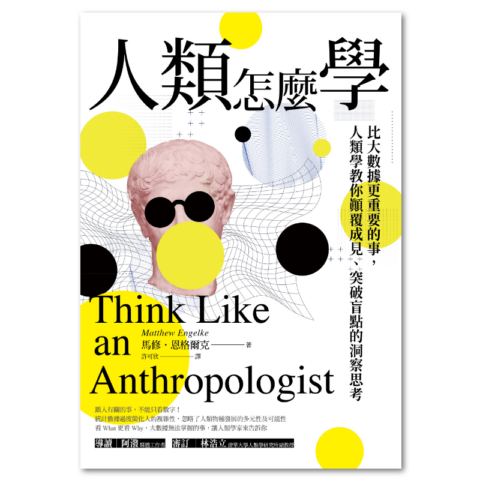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
出版日期:2009-07-17
作者:蔡友月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92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4383
系列:臺灣研究叢刊
尚有庫存
本書探討蘭嶼達悟族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以及精神失序者的疾病歷程、主觀經驗與日常的社會文化處境,主要分析焦點在於社會變遷所形塑的文化建構、現代醫療與疾病受苦的相互關係。
全書分兩個部分,第一部重點是分析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結構根源,並回應生物基因論、環境論、建構論三個對精神失序的研究取徑,對本體的預設、認識論不同的立場,釐清各自的貢獻與限制。全書延續建構論的基本洞見,結合「社會受苦」的概念,避免淪入相對主義,以探究達悟族所面對的快速社會變遷與精神失序的關係。第二部主要是回應既有文獻對文化「本質性」與文化「同質性」的不當假設,進而從社會變遷的分析角度,探討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現代精神醫療在處理精神失序上的可能定位與限制。
作者經過長達八年深入的民族誌田野觀察,接近達悟族人當代的生活世界與受苦經驗,同時輔以各種文獻資料,清楚的分析出達悟族人長久的歷史處境與其當代命運的關連。
作者: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第一章 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一、 導論
二、 問題緣起:晚近青壯世代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
(一) 基因角度的理解
(二) 社會變遷下的家庭解組與社會失序
(三) 精神失序者的社會文化處境
三、 研究方法
(一) 紮根式的民族誌
(二) 田野研究步驟
(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
四、 分析架構
五、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一、 精神失序病因源不同的研究取徑
(一) 生物基因論
(二) 環境論
(三) 建構論
二、 嘗試超越相對主義
(一) 少數族群精神失序的多重受苦形式與「社會受苦」概念
(二) 將精神失序視為一種「現象的實體」
三、 醫療化的限制、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醫學的定位及出路
(一) 精神失序醫療化的限制
(二) 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醫學的交會
第一部 達悟精神失序的社會根源
第三章 現代性、遷移與精神失序
一、 前言
二、 達悟族遷移台灣的歷史特殊性
三、 遷移、世代與認同轉變
四、 升學是向上流動或壓力來源?
五、 求職謀生的挫折
(一) 被迫捲入台灣勞動市場的邊陲
(二) 不斷地在底層勞動市場橫向流動
(三) 家屋改建與過客性來回遷移
(四) 沒辦法存錢?
六、 族群接觸下的憤恨與創傷
七、 傳統親屬連帶的弱化
八、 個人成就與結構困境的雙重束縛
九、 結論
第四章 家庭功能失調與精神失序
一、 前言
二、 傳統達悟文化理想的家
(一) 一個家asa ka vahai
(二) 一個家族 as so inawan
(三) 家屋asa ka vahay
三、 變調的家:十個家庭的現實
四、 變調的家:家庭功能失調的各種面向
(一) 經濟模式改變弱化家庭支持功能
(二) 貧窮、自卑與未完成的家屋
(三) 親密關係的變革
五、 結論
第五章 酒、失業與自我認同混亂
一、 前言
二、 達悟族飲酒的歷史脈絡
三、 酒、失業與社會失序
四、 酗酒、認同混亂與世界觀錯亂
五、 達悟族的「解酒基因」與污名
六、 結論
第二部 精神失序者的社會文化處境與生活經驗
第六章 達悟社會文化與不正常的人
一、 前言
二、 達悟傳統:這不是生病
(一) 達悟傳統的語彙
(二) 巫醫的驅鬼儀式
三、 基督宗教的詮譯系統與處理方式
(一) 西方宗教的傳入
(二) 宗教的治療儀式
四、 現代精神醫學傳入蘭嶼
(一) 現代精神醫學的知識系統
(二) 現代精神醫學的治療模式
五、 三個典範的並存與衝突
(一) 任一典範下都是不正常
(二) 任一典範下都具有污名
(三) 三個典範的交錯
六、 結論
第七章 世代、部落與疾病歷程
一、 前言
二、 去機構化的天然社區
(一) 大自然、非工業化的環境
(二) 生計經濟、貨幣與疾病歷程
(三) 親屬連帶與部落的支持網絡
三、 變遷中的部落
(一) 歧視、偏見與剝削
(二) 生計經濟與自我期許的衝突
四、 轉型中的現代生活與精神醫學
(一) 現代精神診斷下的精神病人
(二) 機構化治療vs.家人照顧的問題
(三) 符合現代生活標準的正常人
五、 結論
第八章 現代性、精神醫學與自我認同的轉變
一、 前言
二、 分裂與異樣的自我
三、 現代性、病識感與自我認同
四、 未來部落的本土療癒機制
(一) 傳統達悟文化
(二) 基督宗教
(三) 現代精神醫學
五、 結論
第九章 結論
一、 發現與論點
(一)理解達悟族精神失序的根源
(二)「精神疾病」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
(三)面對現代性與社會變遷
二、方法與反省
(一)問題意識與資料蒐集的方法與方法論
(二)漢人研究者與原住民被研究者
三、定位與實踐
蘭嶼的迴響
參考文獻
索引
自 序
任何作品的產出都必須置於特定的社會脈絡來理解,因此,讓我在起頭時先簡單的交代我個人所處的田野位置。個人的生命經驗、階級地位、社會文化背景,這些系譜學上多元的位置,不可避免形塑了本書分析上某種認識論的視框,形塑問題的癥結以及企圖解答的謎題。
二十歲五專畢業那年,我開始進入醫院工作,同時插班上東海大學的社會學系。我一邊好奇的學習認識「進入社會」是怎麼一回事,享受獨立與成長,另一邊則開始體驗「社會學」知識帶給我的啟蒙與不安。往後這兩股相互拉扯的力量不斷交戰,刺激我想往更高的知識領域尋求答案。
回顧我護理專業的養成訓練中,長達一年的臨床實習,包括內外科、小兒科、產房、產科病房、嬰兒室、開刀房、公共衛生、精神科等。我對精神科的想像與好奇的程度高過任何一科,那時,天真的以為瘋子的世界,可以忘記一切而沒啥痛苦。進入精神療養院實習後,馬上粉碎了我的幻想。病房內充斥著各式各樣奇怪的人,有人一整天不斷在走廊上緩慢移動,有人可以站在牆角幾小時都不動,有人整天咒罵他人而完全無法閉嘴,也有會把衛生棉塞到衣櫥的女大學生。更諷刺的是,一起實習的同學,在急性病房中遇到她小學時愛戀的班長。總之,我進入精神科實習後,才發現瘋子一樣要面對這個世界的秩序與規範,而且大部分的時候是更為殘酷的壓力。
學生時代一年的臨床實習,與畢業後兩年的加護病房工作經驗,這些身為圈內人的專業角色,提供我自由進出白色巨塔前台、後台的通行證,也讓我對醫院這高度專業化的場域有一手的觀察。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後,我進入台灣某家報社新聞部擔任編輯工作。一年後,又被調至醫療版。媒體的工作擴大了我的觸角,也讓我對醫療事件的生產與傳播有更深一層的反省。我一直嘗試用不同身份,包括醫護人員、媒體工作者、社會學研究者、乃至於紀錄片導演,以多元的視角關注著「醫療」這個豐富而充滿奧秘的研究領域。現在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我以社會學家的角色,經過多年的田野觀察與分析所提出的學術研究,將有其不同於我以往其他角色的貢獻與定位。我期待這本經由學術訓練所生產出來的知識結晶,在歷經時間沖刷後仍能顯現出獨特的價值。但不可否認的,我與醫療交錯且種種逸於學術之外的生命歷程,則是孕育這本書的最堅實的底層土壤。對我而言,對現代醫療論述持續的關注,反映了我個人學術較為宏觀的關懷所在──現代性、科學理性與受苦等生命存在經驗之間的矛盾關係。
本書是根據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作業要點」,由《台灣社會學刊》編委會與兩位匿名評審審查通過,並且再由聯經出版公司的學術叢書編委會審查而同意出版。我要特別謝謝在這一連串審查過程中,《台灣社會學刊》前後任主編黃金麟、蔡瑞明教授、編委會與兩位匿名評審,以及聯經出版公司學術叢書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與編委會,都提供了相當多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聯經學術叢書編輯沙淑芬小姐細心而專業的協助,讓本書能夠更為完善。
本書的部分章節,曾經分別在不同的研討會與學術期刊發表。其中第三章曾以〈遷移、挫折、與現代性:蘭嶼達悟人精神失序受苦的社會根源〉為題,發表於台灣社會學年會(2005年10月,台北大學主辦),修改後刊登於《台灣社會學》( 2007年6月,第13期,頁1-69)。第五章以〈基因vs.社會失序:社會變遷中蘭嶼達悟族的飲酒行為〉為題,收錄於余安邦教授主編的《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倫理化的可能探問》(2008年12月,頁469-530,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第六章曾以〈原住民社會與不正常的人:達悟傳統、基督宗教、現代醫療〉為題,發表於「第三屆台灣本土心理治療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台灣心理治療學會、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協辦)。第六、七、八章又曾濃縮為〈當傳統惡靈遇到現代醫療:蘭嶼達悟族現代精神醫療的變遷〉一文,發表於「近代華人社會公衛史研討會」(2008年12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哈佛燕京學社協辦),並預計收入在中央研究院「衛生史」研究群出版的專書。我非常感謝上述發表過程中的匿名評審或評論人、與會者的建議。在書稿修改過程中,我也曾在清華大學社會所與人類所、政治大學社會所、成大醫學院公衛所、陽明大學護理所、高雄醫學院社會醫學系、台東大學區域政策發展研究所演講,分享本書部分的研究成果,並且聆聽挑戰與回應,有所收穫。
學術的路,大部分時間是讓人感到孤獨的。這本書能夠完成,要感謝很多人的扶持與提攜。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與碩士班的學習,奠定了我社會學知識的基礎。那些年在東海老師們堅實的訓練下,從古典到當代,不同理論典範的激盪,讓我在理論學習上耐心進行蹲馬步的功夫,也讓我明白對知識該有的堅持。我要特別感謝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之一Mark Thelin(練馬可)老師。練老師告訴我,當年他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原有兩個工作選擇,一個是在美國外交部,另一個是教會派他來東海社會系。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會選擇前者,但是他卻努力的在東海奉獻出大半輩子的光陰。他一對一地帶我讀經典,幫我解釋看不懂的英文,釐清書中的意涵。那些年在東海校園老師家中讀書的日子,是我一輩子珍藏的記憶。練老師說:「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藉著我的第一本學術專書,我要感念他對台灣這塊土地四十多年來的無私付出。書中的字裡行間,有著他澆灌給我的養分。這本書的前身,是我的博士論文。我要感謝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張苙雲老師,經過她的訓練才讓我明白如何從事一個紮實嚴謹的研究。她推動台灣醫療改革所呈現的勇敢與擔當,也讓我看到一位成熟的學者在研究與實踐上的結合。我也非常感謝博士論文的五位口試委員。朱元鴻教授在理論與方法上對我的研究的挑戰與啟發,幫助我更釐清自己的立場。張茂桂教授從族群的角度,拓展我的視野。林淑蓉教授當年慷慨的讓我參與她在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讀書會,並且從人類學角度,幫助我對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有更多的反省。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林克明教授,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回應我的研究,讓我思考社會學研究與精神醫學應該如何對話。吳嘉苓教授總不吝嗇的給我各種機會與建議,幫助我在學術的路途慢慢茁壯。在台大博士班求學階段,感謝葉啟政、陳東升、林國明、曾嬿芬、林端教授們在修課過程中的教導。在拍攝紀錄片「病房85033」而做為我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孫中興教授細心地幫我看毛片,並給了許多非常專業的建議。
感謝教育部公費獎學金的資助,讓我在 2004年7月至2005年8月有機會至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社會醫學系參與該系「跨文化精神醫學」的研究計畫,接受為期一年的上課與訓練。我很感謝該系Mary-Jo DelVecchio Good、Byron Good、Arthur Kleinman、Alex Cohen、Leo Eisenberg、Terry O’Nell教授們給我在知識與生活上的幫助。在這個匯集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學者的頂尖學術社群,他們集體努力在醫療領域開闢視野,鼓勵不同學科與領域的對話,探索新的可能性,這也是我未來努力的方向。感謝中華扶輪基金會博士生獎學金(2003至2004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學金(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以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97-2410-H -001-111-MY2)的研究經費補助,提供我必要的物質基礎,讓我能夠進行長時期的田野研究。也謝謝蕭新煌教授所贊助的台灣社會學會雙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的鼓勵。感謝國科會專案擴增留學獎學金,讓我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有機會前往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跨科際科學研究學程(Science Studies Program)與社會學系進行博士後研究。我要謝謝科學研究學程的負責人 Steven Epstein教授以及研究群的成員,這一年對我的啟發與討論。我也要特別謝謝社會系系主任Richard Madsen教授,不斷的聆聽我的發問,並給予我最大的支持與協助。而我多年來的社會學訓練、獎學金、以及紀錄片拍攝計畫,全部來自台灣這塊土地的栽培與資助。台灣社會自由蓬勃的生命力伴隨著我成長,我深深的以這個美麗的小島為榮,這本書也見證了這塊土地給我的營養與動力。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一流研究環境,讓我能夠安靜的修改這本專書。特別是謝國雄教授,他自己清慎自持,卻毫不吝嗇地給予後輩協助。他對知識的堅持與認真,像一盞小小的光,溫暖了我對學術的初衷與熱情。也謝謝祝平一、雷祥麟、丁仁傑、王甫昌、蕭阿勤、黃庭康、汪宏倫、林文源、巫毓荃、王文基、盧孶豔、謝幸燕、陳美霞等在不同時期的鼓勵或建議。我的助理王馨儀、陳靜玉、顏伶伃在本書校對與編排上,都給我很多的協助。
沒有蘭嶼島上的達悟朋友對我的溫暖接納與支持,我不可能進行研究。我要特別感謝Syapen Kazyaz一家人。我多次來往蘭嶼,總是在Syaman Kazyaz與 Syaman Jyalamo家中自由進出。他們全家人待我如同自己的親人一般,無條件的提供我一切的所需。牧師Syaman Ngarai一家人、Si Potaz、目前正就讀清華大學人類學系的Synan Mavivo,以及Sinan Mannik、SiMatong、蘭嶼居家關懷協會的義工們、蘭嶼衛生所、范家璋醫師、婉娟、藍恩基金會、鄉公所的工作人員,還有我無法一一列出大名的Akay、Akes,總是不厭其煩的回答我的詢問,提供我在田野上必要的協助。謝謝最特別的Si Syabokane,我隨著她穿梭於部落,體會到偏遠地區公衛護士的辛勞。我要感謝所有受訪者與他(她)們的家人,謝謝你們接納我的介入。希望我這些年的研究與努力,未來會對島上的達悟朋友有所幫助。我衷心的感謝這一段艱辛的研究旅程。如果不是因此而讓我跨出以往熟悉的生活範圍與研究領域,去經歷一個陌生的世界,我不會這麼快意識到自身的限制與缺點。就像老人家為我取的達悟名字Si Magaga所蘊含的深意一樣,我希望這一段學術的旅程,給我帶來一生的平安喜樂。這些年在小島上的磨練,讓我經歷到神對我的恩典,我相信祂是成就一切的源頭。
最初進行這個研究的前一、兩年,那時候沒有任何經費支援,往往是自己兼課一學期後,存了一點點錢,以最克難的方式前往蘭嶼進行田野。像是走進一個未知卻充滿魅力的森林,我不知何時能夠順利走完全程,也不確定走出森林後,自己會不會因此多明白什麼?卻是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在達悟老人單純相信的眼神、在田野中受訪者面對困頓時的韌性與生命力、在達悟人與大自然和諧互動的身影…,讓我看到沿途中最精采的風景。或許,相較於巨大的結構它顯得渺小的微不足道,卻是這些美好的片段,支撐著我研究往前走的動力。而當我開始有了舒適的研究室、較充足的研究資源後,也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多年以前原初的感動。
小時候同學來家裏玩,看到家裡一大堆藏書,總會問我:「為什麼妳一點都沒有書香世家的氣質?」我一直不肯安份地待在小書房中,生命繞了一大圈,卻又不自覺的回到父親原初對我的期望。我常想如果不是因為戰亂,我的父親這一生應該會有相應於他的才情有更好發展。如果在我遇到挫折與困頓時,還依然有盼望,能夠堅持,懂得相信。那是因為在陪伴我三十年的成長過程中,父親所給予我最無私的愛。我要將所有的成果,獻給摯愛的父親蔡孫積先生、親愛的家人以及一直聆聽我的亞。
來自蘭嶼的聲音
(這是這些年在島上,參與這個研究田野過程的受訪者們,對於這本書出版,他們的一些想法)
我的族人生存在大環境中,面對困境與挫折時的無奈與無力感,其實充份反應了更大的社會現實。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友月,感謝有你陪著我的族人走了一大段路程,完成這本書。對我們而言,你不僅僅是一位研究者更是一位充滿良知的社會關懷家。—Synan Mavivo(現就讀清華大學人類學系,失序者親戚)
這是一本難得深入剖析蘭嶼達悟族精神醫學方面的書,內容詳述了島上的達悟族人變遷到不同生活空間時所面臨到的不平等處境,此書也重新釐清以往學術界對蘭嶼研究的一些論點。謝謝作者呈現了這個主流社會長期來所漠視的區塊,尤其是在精神醫療方面。每當讀到本書裡敘述族人家庭所遇到的困境和故事時,會讓我感同身受到一直流淚不止,因為這正是族人所經歷到的一段受苦的過程。—Syaman Lamuran(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候選人,曾任蘭嶼藍恩基金會執行長)
雖然這本書的觀點和現代精神醫學的理論不盡相同,但是作者對蘭嶼達悟人的關懷和深入的了解,正是重視科學統計與規格化的現代醫療所欠缺的。希望這本書能有助於現代精神醫學反省,不能僅重視「病」而是更應重視病人做為「人」的基本需求,也希望你的作品,能讓更多人來關心我們共同的朋友與這塊土地。
—范家彰(現任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1998年至2007年負責蘭嶼精神科業務共九年)。
和友月認識,就是在這個小島上。為了瞭解蘭嶼達悟族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醫療
、生活問題,她多年來往返台灣—蘭嶼之間,深入各部落研究調查並貼近他們的病痛與家庭,經歷多年奔波終於完成這本書。身為蘭嶼在地護理人員的我,對於友月對蘭嶼這塊土地的關愛深表感佩,願這本書讓讀者更貼近達悟人的真實生活
,特別是這些被忽略的身心障礙者。—Si Syabokane(為蘭嶼居家關懷協會發起人,衛生所護士,曾負責精神科業務,失序者親戚)
恭喜你順利出了這一本書,希望藉著這本書,能讓不了解蘭嶼身心障礙者的人,能有不同的見解,進而能適當的幫助他們。—Si nan Manikend(曾任職衛生所護士,負責精神科業務,現為研究助理)
在蘭嶼,幾乎沒有人會關心這群人,他(她)們被排擠,或有人認為是惡靈附身。在這種環境之下,身心障礙者不但沒有得到好的照顧,家人及家庭也因此受到影響,在此謝謝妳為蘭嶼所做的一切。—Si Potaz(蘭嶼居家關懷協會工作人員,失序者親戚)
希望透過這本書,可以讓社會大眾重視原住民健康議題。也透過這本書,可以讓社會大眾認識蘭嶼有一群弱勢群體需要被關注。—Si dolphie(蘭嶼衛生所護理長)
希望這本書能讓不了解身心障礙者的人,能夠伸出關懷的手幫助他們。—Sinan Matwps(任職衛生所護士,現負責精神科業務)
我和友月是認識很多年的朋友,她每次來蘭嶼時,我常會陪她去部落探訪這些朋友。從她身上我也學習到如何與病患互動,每次在探訪中,她都會記得這些人的需要,下次回來時也一定為他們準備。她為了鼓勵部落中的一個患者,總是固定跟他買半成品的小船。她奔波多年期間付出的心力,我們多看在眼裡。也期望這本書,能對部落裡的患者及家屬有所幫助。也願所有部落裡nimey zow so nakem (辛苦遊盪迷失的靈魂)都能覓得棲息處。—Sinan Naik(部落母語老師,失序者親戚)
謝謝你對我們蘭嶼地區患者及家屬的關心,我希望這本書有助於未來在社區成立復健的機構,協助這些人做些手工藝、而不是讓家屬疲於奔命於台灣與蘭嶼之間。—Sinan Mypwlas (失序者家屬)
希望這本書的貢獻,未來能夠轉換為另一種對蘭嶼的奉獻,祝福你。—Syaman Mypwlas(失序者家屬)
很高興能認識Si Magaga,因為你常常笑,所以我就幫你取Si Magaga。在蘭嶼,妳關心當地人,而且與部落的人相處融洽,妳人緣很好,很讓我感動,最後祝福平安,天主常妳同在。—Sypen Kazyaz(東清部落老人,失序者親戚)
正值達悟文化不斷被踐踏、曲解,台灣主流價值觀不斷衝擊達悟社會之際,希望這本書能公正的替我們代言,消除外界對當地人不當的刻板印象。願神賜福給辛苦撰寫的友月。—Syaman Ngarai(牧師,曾任原民會達悟族代表)
台灣蘭嶼的達悟族,精神失序的比例高過台灣漢人五倍,為什麼?本書從社會變遷與行動者的因應來回答這個問題。面對資本主義、現代國家與基督宗教的普及與深化,達悟的年輕世代經歷了遷徙至台灣以及原鄉中家庭解組的巨變,這是精神失序的歷史與結構起源。本書分析與比較三個定義與回應精神失序的典範(傳統達悟文化、基督宗教與現代精神醫學),區辨出三個世代不同的精神失序經驗,印證了「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藉此挑戰常見的基因論與環境論的解釋,並且提出「修正的建構論」。作者也與社區中的成員分享了她的研究成果,期待透過社會學知識的協助,探索緩解精神失序者痛苦的可能出路。本書同時觸及了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展現了田野工作「四位一體」的潛力。
—謝國雄,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即使到今天,我仍然在台灣許多角落和議題上發現漢人嚴重的不瞭解原住民。這些年來,我們雖然在法政、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上做了不少的工作,但這似乎只觸及到原住民問題的表面,我們彷彿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面的相遇過。透過作者長時間的研究、思考與反省,我們終於有機會接近問題的本質:其實我們都缺乏對原住民受苦經驗的體會,這是整本書最讓我感動的地方!從這裡出發,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連串改變現狀的行動方案。
—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卑南族,曾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山海文化雜誌社總編輯、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弱勢族群何以受苦?面對蘭嶼達悟族人的精神失序,這部力作深刻回應了這個古老的社會學關懷。作者以細緻的田野工作與銳利的分析角度,揭露了台灣社會變遷如何交織出使人深陷苦難的路徑。剖析島間的遷移形式、族群政治、社會歧視與認同危機,才足以明白這些島嶼邊緣的自殺、憂鬱、失落與妄想。蘭嶼的部落巫醫驅魔、牧師帶領禱告、精神科醫師打針開藥,分子生物學研究者尋找易感性的基因,而作者提出對於精神失序的多端緣由,提出整合生物醫學與社會文化的解釋模型,期許更徹底的改造工程。讓這部震撼人的社會學作品,督促我們面對底層社會,更加推進我們反思社會不平等的動力。
—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人們常說,在疾病形成的過程中,先天與後天,基因與社會,都同樣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基因決定論重新成為顯學的今日,我們卻很難得看到一本著作,真正嘗試去說明:是什麼樣的「社會」過程,竟能使各色不同的人們罹患同樣的疾病?本書正是這樣一本具有理論意義的大膽嘗試,它企圖回答:蘭嶼達悟族人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為何竟比台灣漢人高出五倍以上?透過極其廣博的資料收集與鮮活細緻的訪談,作者清楚地描繪出疾病形成的社會過程。由於蘭嶼在最近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劇烈社會變遷,許多達悟族人都曾經歷的極為類似的艱辛處境─遷移至臺、底層工作、家庭崩解、乃至酗酒失業,這種由結構性處境而造成的「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 經驗,終而表現為達悟族人高密度的精神失序。換言之,表面上支持基因決定論的「族群性與家族性精神失序」的現象,其實是源自整個族群被迫經歷的集體受苦經驗。讀畢全書,讀者不僅將得到一個透過社會經驗來理解疾病成因的新穎視野, 更是對於「社會與生物相互形構」的想像與渴望。
—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第一章 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一、導論
本書問題意識的起點,源自我過去研究「死亡」議題所留下的一個問號。我過去的研究,主要是以台灣大型醫院加護病房與安寧病房中的癌症病人為研究對象,探討現代人的垂死歷程被「醫療化」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包括專業權力的濫用、生命倫理的議題、醫療科技的迷思、醫療制度的盲點等等。(蔡友月1998,2004,2008)這些反省更刺激我去想,如果醫院科層化的組織制度與科技理性運作方式,在面對現代人的死亡都有一定的限制,我們是不是能從歷史、社會文化面去尋找面對生、老、病、死的其他力量?
2000年我開始注意到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mental disorder)的特殊現象,並試圖從社會變遷的歷史視野來反省:「精神病是什麼?」簡單地說,我認為那些現代醫學至今也無法控制、治癒的疾病經驗,如死亡、瘋狂,可以激發我們對現代醫學的極限加以省思。「現代醫學」做為現代知識、制度與組織的一環,充分彰顯了現代性發展對人類生命存在所帶來矛盾曖昧的兩面性。在現代社會中,現代醫學在顯著的程度與範圍上都介入了人們的生、老、病、死等經驗。在面對與處理這些生命經驗時,現代醫學有其貢獻,但也帶來了限制與迷思。既有的一些研究指出,在歐美高度現代性的社會對待與處置精神醫學所界定的精神病人都有其不足與限制,相關文獻的討論可參閱本書的第二章。站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刺激我進一步思考,以一個仍處於前現代的部落社會為研究場址,是否有助於我們探究「精神病人」可能的出路,這是我最初的原始謎題(originating puzzle),隨著後來浸淫於田野越久,理論閱讀逐漸深刻,全書的問題意識也開始有所轉向。
2000年我到島上的第一個夜晚,部落的朋友把我安置在牧師家。那幾天,牧師的兒子杉明正從高中放寒假返鄉,他熱心地帶我爬屋頂看海,高興地彈著吉他,和我分享在高中演唱會所唱的歌曲。我怎麼也沒有料到,兩年多後,我再度拜訪他家,牧師卻告訴我:「我的孩子也變成妳的研究個案了,他現在已經從大學休學回家了。妳要不要和他聊一聊?」在往後的田野中,許多令人怵目驚心的生命經驗就這麼尋常地出現在小島上的達悟人身上,失業、酗酒、自我認同混亂、精神失序、自殺等等,這些看似隨機、偶遇的個人不幸,做為一個社會學家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少數族群因族群身份、地理位置、文化傳統等有關社會不平等結構位置帶來的多重受苦。我的問題意識也開始由原先企圖分析現代精神醫學的極限,並從歷史、社會文化面尋求現代醫療之外的療癒機制,逐漸轉向關注:如果進入「現代醫療」的「現代人」仍無法有效緩解生病經驗帶來的磨難,那麼那些缺乏現代醫療知識與處置、做為相對地未充分「現代化」的社會或地區的成員、在政治、社會、文化權力上處於弱勢人群,命運又會是如何?面對疾病、病痛的磨難,「現代醫療」在此的貢獻與限制為何,社會文化又該扮演什麼角色?
人類學家Arther Kleinman以「社會受苦」的概念,指出巨觀結構力量如何作用在行動者的疾病受苦經驗,強調我們必須揭發人類苦難的社會起源,並認為解決的策略不應放在個人的層次(Kleinman1986; Kleinman et al.1997)。延續這樣的關懷,本書關注疾病與病痛受苦經驗的社會文化意義、現代醫療專業在其中的角色等議題,研究對象則是處於三重邊緣化(marginalization)人們的受苦經驗。相對於台灣本島及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蘭嶼達悟族的部落社會是相對地未充分「現代化」的;相對於漢人,達悟人在政治、社會、文化權力上是處於弱勢的;相對於正常人,「精神失序」的達悟人更是主流社會的邊緣人。本書針對那些處於當代台灣社會邊緣的少數族群疾病的受苦經驗,分析重點在於疾病受苦之源、如何受苦、以及自我與社會如何面對這種受苦──亦即精神失序的原因、發病後的境遇,以及現代醫療、傳統文化、基督宗教在原住民部落的角色與作用。在具體的研究問題上,本書試圖分析的是「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特殊現象」,我認為不管在理論對話與經驗分析,這個現象本身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涵,而這樣的特殊性反映在兩方面:
第一,達悟人發病原因的特殊。從精神醫學知識歷史的演進,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精神疾病的病因詮釋,或臨床的治療處置,都越來越向生物模型靠攏。 隨著生物科技的發達,從基因預設來探討原住民日益嚴重的酗酒、憂鬱、精神失序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譬如 2000年一項「達悟族原住民精神分裂症之基因連鎖分析」研究計畫, 即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所產生的學術探討,報告中指出近二、三十年來,蘭嶼達悟族人的精神疾病比例有增高的趨勢;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其比例高於台灣的五倍以上,台灣漢人為0.3%,達悟人為1.6%。在本書的分析中,我並不是要完全駁斥生物醫學知識的進步對人類疾病與社會的貢獻,但在面對「基因(先天)vs.環境(後天)」這延續爭論已久的老問題,我認為社會學的分析可以讓我們對於達悟族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現象提供不一樣的解釋。
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洞見指出,個人是社會的產物,個人行為深受社會、文化脈絡影響。古典社會學家Emile Durkheim,在《自殺論》(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1951〔1897〕)中對自殺的研究,即明顯地呈現了這樣的思維。 Durkheim認為自殺看似個人自我選擇的結果,但卻深受社會文化因素所左右。從這樣基本的社會學想像出發,以社會學知識來理解達悟人特殊的精神失序現象,將可能有不同於現代醫學獨特的貢獻。社會學的分析,如何能有助於我們更恰當地理解少數族群面對精神失序受苦的結構性根源?相較於生物醫學著重基因面向的探討,我將從社會變遷角度分析達悟族精神失序比例增高現象的歷史社會根源,亦即探討該現象與族群身分、當代的文化處境與社會位置的關係。
第二,達悟人對待與詮釋所謂「不正常的人」的特殊性。這部分也涉及了精神失序者病痛歷程、主觀經驗與日常生活社會文化處境的討論。目前交錯在蘭嶼影響達悟精神失序者的三個典範,亦即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與現代精神醫學,「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現代精神醫學」的進展大致相當於Max Weber所指出的現代社會逐漸解除魔咒的理性化過程。晚近達悟人如何理解與處置精神失序者,深受此種變化過程的影響,老、中、青三代經歷不同階段社會變遷的影響與世界觀的轉換,形塑出不同的疾病經驗。究竟面對達悟人或其他類似的原住民文化與社會,現代精神醫學的角色與作用為何?社會學面對達悟族精神失序現象的探討,可能朝向更佳的緩解受苦的方式嗎?
具體而言,達悟族精神失序現象呈現在發病過程與發病後處置的特殊,二者又與一個少數族群經歷快速社會變遷的命運息息相關。這些也都涉及了1960年代中期後,蘭嶼經歷快速社會變遷下,達悟族所處的族群社會位置與文化傳統的特殊性。本書關注近二、三十年蘭嶼達悟族高比例的精神失序現象,在這個尚未充分「現代化」的原住民部落,進行民族誌的田野觀察與歷史文獻分析,並企圖在經驗與理論層次,回答我上述關懷的問題。以下進一步說明本書的問題緣起、問題意識、研究重點、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等等。
二、問題緣起:晚近青壯世代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
(一)基因角度的理解
晚近蘭嶼達悟族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是一個引人注意的議題。高雄醫學院原住民健康中心的葛應欽教授,在1999年曾明白指出當地精神疾病的病人明顯增加。他寫道:
蘭嶼當地由衛生署列管的精神病人有三十餘位,初步估計蘭嶼精神疾病盛行率高達千分之十,而目前台灣精神分裂症病人,保守估計約有千分之三。換句話說,蘭嶼精神疾病的比例高出台灣地區三倍左右!三十餘年前,台大精神科林憲教授曾對一萬多位原住民做過調查,雖然沒有包括蘭嶼的達悟族(舊稱雅美族),但在當時原住民精神疾病盛行率和漢族相似,即使在醫療資源缺乏的蘭嶼也未見較高的盛行率。 (台灣日報1999/4/13)
我們應如何來理解達悟人廣泛而獨特的精神疾病現象?九○年代之後,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達,基因研究在台灣開始盛行,並成為國科會的重點補助項目。因為原住民的獨特族群身分,基因預設也成為近年來探索原住民高比例痛風、酗酒、精神失序等健康議題的重要研究取徑。 科學知識的這種發展,對於理解原住民的健康問題,尤其有特殊的影響。
葛應欽教授2000年在蘭嶼進行的「達悟族原住民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連鎖」醫學研究,也是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下所進行的研究。這項研究的重點包括:
一、蘭嶼精神病患比例高達1.6%,而精神分裂症也達1%,比起台灣其他地區要高出許多,經精神專科醫師訪查蘭嶼全島精神病患,依據DSM-IV診斷標準來鑑定病人,目前共有53位病人,其中3人為非原住民,餘50人為達悟族的原住民。達悟族原住民精神疾病症為1.6%,其中精神分裂症31人,器質性精神疾病8人,情感性精神疾病3人,源自兒童期精神疾病8人。
二、該研究假設達悟族所居住的蘭嶼,孤懸海外,約五、六百年前由菲律賓遷移至此,過去由於種種因素被隔離,幾百年來盛行族內通婚,為一孤立種族的族群。研究者推測由於族內近親通婚的結果容易出現易感性的基因,研究者因此提出基因與高比例精神疾病關連性的假設。
三、由於達悟族精神分裂症病人登記有31人(其中五對為兄弟姊妹),盛行率約達1%,為台灣之3倍。因此,該計畫從31餘位精神分裂病人及其家屬(估計約150-200人)為基礎,並由精神科醫師擴大尋找新病例(預定達40例以上),並重新認識疾病表現型及分類、抽取血液、萃取DNA,並以已知相關基因座當作候選遺傳標記,分析多型性變化,計算其連鎖相關,以提供尋找精神分裂症基因的參考。
四、2000-2001年研究者以31位病人及其一等親家屬為研究對象,對27位病人(4位拒絕)及74位病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等親屬採集血液樣本,共萃取出101個DNA樣品。但研究結果沒有發現顯著的關連,研究者推測也許是樣本過小。
精神疾病的遺傳學研究,過去主要是以領養研究與雙胞胎研究等家族研究為主。一直到分子遺傳學的研究後,才有重大突破,目前這方面的研究被認為是精神醫學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林信男、劉絮愷2002:16)。生物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基因與分子遺傳學的研究,逐漸成為精神醫學解釋疾病成因與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不過,上述基因預設的研究計畫,可能過於簡化,會讓我們忽略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問題癥結,因此有必要先在此加以澄清。
第一,根據前述現有統計與歷史資料,達悟族精神失序比例增高是發生在近二、三十年,九成五以上集中在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基因研究無法提出歷史過程的解釋。
1960年代人類學家李亦園的研究指出,達悟(雅美)傳統的文化結構,維護了該族的基本心理衛生。傳說中的「惡靈」是達悟人社會認可的情緒衝動代替品,達悟人可盡情地恨它、咒它、驅逐它,使得衝動有發洩的管道而不至於危害整個社會的基本安全,維護了成員的心理健康。他還在研究的附註中強調,當時的達悟族,未見有精神病人的報導,「林憲醫師曾函告無精神疾病的紀錄,劉斌雄先生告知,在居留蘭嶼期間,曾發現一可疑精神不正常的達悟男子,但是否為精神病人,尚未能確定」(李亦園,1960:268)。就像葛應欽引用林憲的調查所推測的,三十多年前,達悟族的精神疾病盛行率應該不會比其他原住民或漢人高。1982年公共衛生學者姚克明,在台灣省公共衛生的調查報告,第一次大規模蒐集與達悟族健康有關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的資料。調查的項目包括蘭嶼常見的衛生問題,生產、育兒、口腔衛生、菸酒等,但並未標明「精神疾病」。姚克明並在報告中指出,一些工業社會常見的「文明病」,如高血壓、消化性潰瘍、精神官能症等,在蘭嶼並不常見。他並根據前衛生所廖慶源醫師的報告指出,廖慶源醫師 在蘭嶼服務期間只碰到四個有精神症狀的病人:「第一個全身僵硬、不講話、不吃東西,將他手一提高就停在半空中(疑似僵直型精神分裂症或憂鬱症),第二個是以前住過高雄療養院的病人,有幻聽、失眠、語言不連貫的情形,其他兩個為癲癇病人」(1982:19)。
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劉珣瑛,1992年被派到蘭嶼做定期性精神疾病的診治工作,她是第一位在蘭嶼進行精神醫療的醫生。劉珣瑛等醫師在1993年離島精神醫學研討會,發表了蘭嶼精神醫療概況的研究報告,指出島上精神疾病比例異常增高的現象,「台東衛生所自1992年8月起委託省立台東及馬偕醫院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輪流每個月到該島一次,配合當地醫護人員作診斷與治療。經該島衛生所轉介之病人共28人,初步鑑定結果,精神分裂症9人,非典型精神疾病2人,雙極性情感性疾患6人,憂鬱症合併酒精濫用2人,適應不良症候群2人,智能不足2人,癲癇症2人,非精神疾病之行為問題2人,1人未遇」(劉珣瑛等1993:4)。台灣其他離島區域,如澎湖、金門的精神疾病盛行率,當時則未有如此顯著增高的趨勢。
1990年代隨著原住民運動的風起雲湧,有關原住民人權、教育,以及酗酒與精神疾病等議題,開始成為報章媒體關注的焦點。1995年聯合報一篇有關離島精神醫療的專題報導,也開始注意達悟族高比例的精神疾病現象。該報導以「台灣怎麼偷走蘭嶼孩子的靈魂?」為題,指出許多蘭嶼達悟人的孩子去台灣一趟,再回來時成為眼神呆滯、不認世事的精神疾病患者比例增多。
如果將因癲癇而納入精神科診斷的病人排除在外,回顧醫療紀錄,1960年代達悟族並沒有高比例的精神科個案,1982年當時初步統計精神疾病的病人只有2個,1992年大約有28個,當時就開始有醫師注意到精神病比例增高的現象。根據蘭嶼衛生所的資料,2003-2004年蘭嶼衛生所登記的精神疾病患者約50人,2005年一年內新增8人,這些新增的精神疾病患者全部都是已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2005年底為止,蘭嶼衛生所登記被診斷精神疾病的共58人。2005年之後,青壯世代發病的個案又有增加的趨勢,截至2009年2月本書完稿為止,被納入蘭嶼衛生所精神疾病的個案增加至66位,若加上目前在玉里或其他療養院登記有案的病人,具有精神科疾病診斷的人數,至少超過70人以上。 達悟族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是1.6%以上,和台灣本島0.3%比例相比,比例的確明顯偏高。雖然,我們不能排除過去醫療資源不發達,罹患精神疾病的達悟人數有可能被低估,也無法確認1960、1980、1990年至今,不同的精神科醫師是否採用相同標準的診斷工具,並藉此排除不同診斷工具所造成的誤差。從1996年衛生署針對偏遠醫療的補助計畫下,精神科醫師每月兩次定期到個案家訪視, 在醫師與達悟族護理人員的努力下,全島有精神疾病徵兆的達悟人,都已完成初步的評估與診斷。根據2003年衛生所收案的個案統計,列管約60位被診斷為精神疾病的患者(包括長期住在玉里療養院的患者),95%的失序者集中於25-60歲,為接受過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教育程度大多屬國中、國小,發病年齡大多都很年輕,以未婚的男性居多,且一半以上首度出現不正常徵兆是在台灣。其中只有3位超過60歲(其中1位患者,2004年歿於台灣的精神病院),是屬於在傳統文化下成長的老人,這些老人發病年齡大都在50歲之後。被診斷為精神疾病的達悟人,很明顯是集中在夾雜在傳統與現代文化衝擊下的青壯世代。這些初步的發現,提醒我們必須意識到快速社會變遷對達悟青壯世代的心理衝擊與精神疾病比例增高之間的關連性。
其次,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台灣原住民的健康報告,亦指出二次大戰之後,台灣原住民與漢人的精神疾病比例無重大差異。但是,1960年代之後,台灣原住民酗酒、精神病人比例有大幅增加的趨勢。該份報告合理地推估,台灣地區原住民精神失序的負擔將會有顯著的增加(Cohen 1999:24)。因此,雖然現今有關世界原住民、台灣原住民,以及達悟原住民相關的健康資料都極為匱乏,我們仍可以根據上述的資料,合理地推算達悟族精神疾病比例開始增加,是在這二、三十年的時間,診斷為精神疾病的達悟人,95%高比例集中在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也是一個明顯的表徵。
第二,根據以往人類學的研究,近親通婚的預設並不符合達悟的傳統文化規範。衛惠林、劉斌雄討論達悟族的婚姻禁忌與擇偶條件,清楚指出達悟族的婚姻多數在第三從表外的遠親,在亞世系群單位內有很強的外婚傾向。其中禁忌的範圍包括兩類,第一類是婚姻禁忌”dzikamopasiragpit ta makaniau”,又包括近親禁忌與仇家禁婚。近親禁忌的範圍:(1)居住在一個家宅內的親屬”asa ka Bagai”,不僅是直系血親,並包含同居婚屬與同父異母之異胞兄弟姊妹,乃至遠親屬的寄居者。(2)直系血親”malama”,包括承上繼下的直系三世親屬,及親兄弟姊妹。(3)雙系近親群(ripus),雙系第一從兄弟姊妹及其所出。(4)半兄弟姊妹” kakta no atoy”,同父異母、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及其所出。仇家禁婚”kapusok to Bagai makaniau”指凡兩家曾發生過流血鬥毆、殺人復仇,以及通姦糾紛者為仇家,禁婚。第二類是不受歡迎或可恥的婚姻,包括:(1)夫兄弟婚與妻姊妹婚,(2)叔與姪媳或姪與嬸母相婚,此等婚姻雖然不到完全禁忌的程度,但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可恥的、不榮譽的婚姻。達悟人的社會規範相信近親婚姻必然有兩種結果,生下的嬰兒是瞎眼的,或是子孫不繁,甚至絕嗣(1962:67-77)。早期達悟的神話傳說中,也都明白地指出這些亂倫禁忌的規範。達悟人董森永牧師也強調,達悟人禁止血親婚姻,直到現在也是如此。另外父母的兄弟姊妹之子女,也禁止通婚,直到這些表兄弟姊妹的子女開始,方可通婚(余光弘、董森永1998:4)。
余光弘(1992)重新檢查系譜表示,達悟人的禁婚範圍僅注意父母雙邊的親屬距離,真正的禁婚範圍是父母雙方同胞之子,也就是僅及於雙邊的一從表,雙邊的從表之後即可婚配。陳玉美(1994)提到第二代從表雖然可以婚配,但達悟人覺得還是有點親近,因為第三代從表婚才是當地人最喜歡的婚配。亦即,居住於蘭嶼的達悟人雖有內婚制,但他們的文化與法律規範還是有三等親的禁忌。
第三,回溯更久遠的歷史,基因研究者假設達悟人為一孤立的「種族」,更值得商榷。197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的體質人類學教科書,基本上已經不認為立基於生物差異的種族(race)分類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而質疑種族做為一種實存範疇的合理性(Littlefied, et al., 1982:642)。根據1999美國人類學會宣言:「人類群體不是可以明確、清楚界定、生物上獨特的團體。基因的分析指出,種族團體內部的差異大於種族團體之間彼此的差異。這意味著大部分94%生物上變異在種族團體(racial groups)之內,種族團體之間的差異僅有6%」。 而這種假設某種族、族群與基因脆弱性的研究,近年來在醫學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當某族群的人口在流行病學上被標定為具有風險,往往很容易形塑出一個申請健康資源的通道,在努力尋找某族群的基因脆弱性的背後,醫學也越穩固地建立其科學的地位(Poudrier 2004:25)。當研究上標示特定人群在生物上的缺陷,某種程度也發揮污名化他者與建構特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強化了種族主義等意識形態下的人群分類。
上述基因角度的研究,將原住民族精神失序的受苦經驗,縮小到分子層次來理解。非歷史的取徑並無法解釋精神失序比例大幅增加,是這二、三十年才發生的事,且高比例集中在青壯世代。所謂近親通婚之說,也欠缺對達悟社會文化進一步的考察。這個取徑既不重視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也對失序者的主觀受苦經驗缺乏興趣。除此之外,這方面的研究,對於如何緩解日益增加的精神失序現象,至今為止也少有具體可行的策略。即使如此,如同前面提到的,近年來生物基因角度已成為探究原住民健康議題的重要方向,而產生非意圖的社會效應(見第五章的討論)。此外,沒有深入達悟社會經濟結構歷史轉型的分析,也會讓我們忽略其高比例的貧困家庭、意外死亡、自殺、酗酒、家暴等,所造成明顯的家庭解組與社會失序,而這些問題無可避免地衝擊他們的身心狀態。因此,本研究採取紮根式的民族誌研究,從田野中提煉重要的面向與範疇,輔以歷史文獻分析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核心肇端。
(二)社會變遷下的家庭解組與社會失序
達悟(Tao),為台灣原住民十三族 當中人口較少的一族。蘭嶼島位於台灣東南海峽,東經121度30分8秒至東經121度36分22秒,北緯22度零分6秒至北緯22度5分7秒,面積45.7平方公里。與位於其北方的綠島距離約76公里,與南方菲律賓的巴丹群島(the Batanes Island),距離約110公里,因地理環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不同於台灣其他原住民,形成特殊的海洋文化(見圖1-1、1-2)。
根據2003年蘭嶼衛生所製作了第一份有關精神疾病病因的統計表,有8位是因為酗酒引起病變,3位是車禍腦傷加喝酒所致,有20位是在台工作受挫、生活不適環境因素所致、還有10位被視為遺傳性的親子檔病人。曾負責蘭嶼精神科巡迴醫療多年的范家彰醫師認為,酗酒或環境因素所產生的精神失調,可能是對台灣高消費、高壓力生活不適應所引起的。
2005年2月蘭嶼鄉各村里住戶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蘭嶼島居民3,659人,1,054戶,男性1,969人,女性1,690人,島上居民以達悟族為主。根據1970年代末期人類學家李亦園的實地訪查,東部地區若干平地鄉,以及鄰近平地的山地鄉村落當中,高達八成的年輕原住民(15–34歲)到外地工作。即使是離開台灣本島的蘭嶼,也有四成多的青少年外出,到台灣西部都會區去工作(李亦園1979:5–6)。1970年代之後,這股外移的趨勢,仍有持續上升的傾向,根據2005年2月蘭嶼鄉各村里住戶人口統計,留在島上的人口約一千多人左右,外移的人口已從原先的四成多,增加為六成。
圖1-1蘭嶼全圖
資料來源: 交通部民航局臺東航空站 http://www.tta.gov.tw/ch/chinese6.asp
查閱日期:98年3月18日
圖1-2蘭嶼與台灣關係圖
資料來源:http://home.pchome.com.tw/travel/lowgogai/taiwan.htm
蘭嶼近年來一直是媒體報導的焦點。著名的核廢場設置、國家公園草案、以及海砂屋等事件,使得這個人口僅有三千多人的小島一直具有高度的曝光度。相較於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學者對蘭嶼其他方面的重視, 這些越來越多在台灣生活,擺盪於漢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達悟年輕人,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急速社會變遷下,他們這些青壯世代遷移台灣的經驗,其中夾雜著家庭功能弱化、傳統社會文化規範解組,進而產生精神失序的現象,極少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既有的文獻,也欠缺對近三十年達悟族高比例精神失序的分析討論。 精神科醫師林憲認為,少數族群精神異常比例較高的原因,和他們的社會文化本質及文明化的過程有關(1978:25)。張苙雲(1989)的研究,也發現原住民的心理健康確實有明顯的族群差異。許木柱、鄭泰安(1991)透過泰雅族與阿美族的比較,認為不同族群社會文化的特質,會對成員心理健康有所影響。個人所屬的社會文化特質,對它的成員提供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心理及社會支持,來自不同社會的成員,即使具有相似的個人痛苦經驗與經濟困境,受影響的強度可能會明顯不同,精神症狀也會有不同型態與嚴重程度。上述這些研究提醒我們必須注意到,不同族群的社會型態、文明化的程度、社會文化轉型都影響著精神失序病發的可能性。我認為必須更進一步剖析原住民社會的自殺、酗酒、意外死亡、精神失序等健康議題,與大環境的撞擊的關係,包括現代性對部落社會的影響,族群與遷移所產生的原漢文化差異、認同危機等,所造成社會心理的功能失調與人格的解組。
近二、三十年達悟族精神失序的比例大幅升高,社會與文化意義下的「族群身分」,顯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究竟,達悟族特殊的精神失序現象與其族群身分在面對現代性衝擊的社會文化處境有何關係?達悟族的社會狀況與其他包括台灣在內正經歷快速社會變遷的社會相比,又具有什麼樣的歷史特殊性?本書將分別在第三、四、五章,深入分析以下三個交互的因素。
第一、遷移與精神失序的關係。相較於接受傳統文化與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老年世代,我將探討這些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他們在15、16歲的年紀隻身遷移台灣的生命際遇。是什麼結構的推力與拉力,使得遷移台灣成為接受現代教育的世代共同的命運?他們到台灣後遇到了什麼事?為何將近半數的罹患精神疾病的達悟人是在台灣出現不正常徵兆?究竟,他們到漢人社會求學工作的流離遷徙經驗,與誘發精神失序的關係為何?我分析的面向,包括底層勞動力市場不良的工作情境、文化衝突下的認同危機、缺乏社會網絡支持、在蘭嶼的父母親無法提供孩子在台必要的協助,以及世代的差異所造成的種種心理挫折等等。
第二、家庭功能解組與精神失序的關係。在長期的田野觀察中,我發現這些精神失序者的家庭狀況都有一些共同點:離婚、失業、酗酒、家庭暴力、意外死亡、自殺。顯然這些顛仆不穩定的家庭結構是一股強大的拉力,誘發了個人與集體失序的狀態。我們必須思考什麼樣的轉變,造成傳統家庭無法維持它原先的生活所需的功能。我將溯源到社會變遷的衝擊影響下,傳統家庭走向現代家庭所帶來的改變,包括傳統家庭生計瓦解,使得傳統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逐漸走向貨幣經濟;經濟變遷弱化了傳統家庭功能與支持系統,造成離婚、家庭暴力的問題增多;政府國宅政策的強勢介入,全島家屋的改建帶來家庭的經濟壓力,多數精神失序者生活在全家失業,兄弟姊妹人口眾多的底層貧窮家庭,以及社會階級不平等的浮現。我希望藉此釐清在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中,傳統達悟家庭與親屬關係所提供的社會心理支持力量會逐漸式微?
第三、社會失序下的失業、酗酒與自我認同的危機。我將分析達悟人飲酒問題背後的社會歷史過程,討論酒精是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脈絡中進入部落社會;在快速社會變遷衝擊下,青壯世代勞動的價值、生活型態的改變,乃至於個人生命週期的改變,以及世界觀的錯亂,所帶來生存適應的挫折與認同危機等問題。
上述是由田野觀察中提煉出來的三個重要面向,是本書第一部的問題叢結與研究重點,而分析重點就在於少數族群精神失序現象的可能成因,亦即引發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現象的歷史社會根源。
(三)精神失序者的社會文化處境
本書第二部(第六、七、八章)的問題叢結與研究重點,是以被診斷為精神疾病的達悟人為分析主軸,探討不同世代的失序者在蘭嶼部落的生活世界與病痛歷程。傳統的達悟部落是一個以血緣、姻親等家族連帶關係為主軸的社會,這些被診斷精神疾病的達悟人在其中獲得一定的社會支持。許多人甚至獨居,仍可上山下海,而他人對他(她)們的要求、期望也不高。如果對照台灣精神病人的疾病經驗,蘭嶼部落中這些失序者似乎自由許多,而且不管是失序者或家屬本身,對精神醫學的用藥接受度都很低。家屬普遍缺乏現代醫學知識,也較不重視現代精神醫學所提供的治療方式。根據我的田野資料顯示,處在生存競爭壓力較小的社會情境,或許有助於這些失序者病發後暫時的穩定。但是長期來看,隱藏在部落內的失業、漢文化入侵等結構性的問題,以從所引發的酗酒、文化認同危機等,部落的環境則未必有利於病情的穩定與康復。
蘭嶼一直是現代醫療資源極為匱乏的地區,達悟族節節升高的精神疾病比例,也凸顯了偏遠醫療公衛系統多問題。相較於台灣,現代醫療進入蘭嶼的時間更晚。島內唯一的衛生所成立於1957年,是目前蘭嶼唯一提供現代醫療的所在。島內沒有其他醫療院所,在有限的醫療人力與資源的情況下,一直到1992年以後,才逐漸有精神科醫師抵達島上,給予居民部分的醫療協助。截至2009年為止,只有少數被診斷精神疾病的達悟人是長期安置於花蓮玉里療養院。除此之外,隨著島內精神失序者逐漸增多,一個特殊的情景是:精神失序者自然地遊走於部落中,而部落的族人也習以為常。對照台灣都市化、工業化的生活形態,以及精神病人的處境,達悟精神失序者的這種情形,似乎很難想像。如果從這種蘭嶼達悟部落的特殊現象來反思源自西方的現代精神醫學,又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做為西方現代性一部分而發展的現代醫療知識、制度與組織,充分代表一種「理性化」地控制世界的企圖。事實上,醫療知識一直是人類社會界定「正常」與「非正常」行為重要判準的一部分。當代社會「醫療化」的膨脹,更代表理性化力量的擴大,顯示對「非正常」行為進行醫療認知與處置的擴張。那些自然遊走於部落、其他社會成員卻習以為常,似乎代表醫療化的理性規約控制力量未及之處的某種「自由之身」。目前達悟精神失序者安置於療養院或自然遊走於部落,兩者並存的事實,都顯示現代醫療在某種程度上逐漸地改變了他們對精神失序者的理解與處置方式,但傳統上理解與處置行為「不正常」的方式,仍然存在於部落社會,並且具有相當的角色與作用。
藍忠孚、許木柱針對台灣原住民的健康調查指出:「在過去台灣原住民社會原有的宗教與自然的醫療系統,自成為一特殊的醫病關係。其治療的原因雖然與科學醫學一樣皆產生於有人生病。但治療的主體及重點卻大相逕庭,主要在於病人的社會關係。醫病之關係被延伸為社會規範的約制問題,藉以維持該社會的道德與秩序」(1992:1)。從這種觀察出發,在達悟的個案研究上,我們可以追問:現代醫療進入蘭嶼後,如何改變達悟人原有對精神失序者的認知方式?這樣的改變對那些被診斷為「精神疾病」的患者本身與他人-尤其是周遭的家庭成員等-造成什麼影響?蘭嶼的部落社會普遍看待這些精神失序者的方式,夾雜了超自然認知、基督宗教與精神醫學的詮釋。或許,這有助於我們從社會變遷的歷史角度,反省現代精神醫學專業在當代社會-尤其是在社經地位較低的少數族群中-所扮演的角色。現代精神醫學的出現是否有助於精神疾病患者去除污名、獲得較好的對待與照護?或者它加諸於「病人」更多的污名與進一步的監控?在舒緩社會邊緣的少數族群的精神失序現象上,現代精神醫學的貢獻與限制何在?事實上,在理解與處置精神疾病上,達悟社會的傳統文化與基督宗教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那麼,現代精神醫學夾雜在達悟傳統文化、宗教脈絡中的適當定位為何?
西方歐美國家的精神醫療,曾經從早期「機構化」的處置病人方式,發展到鼓勵病人回歸社區的「去機構化」方案,至今仍存有許多無法突破的問題。那些自然遊走於蘭嶼部落的「不正常人」,能給我們什麼啟示嗎?對於大多數像台灣本島一樣高度現代化、現代醫療資源相對充分,並且相對受到高度理性化控制的社會來說,達悟族對精神疾病的不同理解與對待方式,是否有助於我們反省現代精神醫學的功能與限制?當現代醫療體制成為當代人消解身心之苦的「新宗教」之後,除了就醫看病,期待醫療知識與技術的拯救之外,我們還有其他可能的出路嗎?這些是本書第二部所要探討的問題,分析的重點則在於達悟部落如何面對這些被現代精神醫學診斷為「不正常」的人、不同世代精神失序者的自我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以及傳統達悟文化、基督宗教、現代精神醫學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現代性的社會變遷力量衝擊的達悟原住民,有其獨特的歷史遭遇與命運,它也許是台灣以漢人為主的大社會、甚至是少數民族在更廣大的當代世界的縮影。本書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釐清現代性的衝擊,以及對少數族群的自我認同與心理健康所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