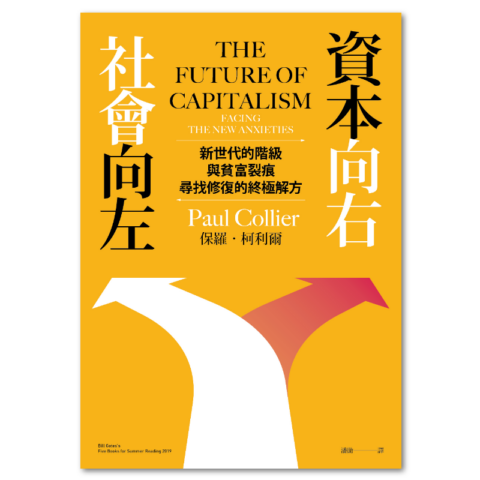共善:引導經濟走向社群、環境、永續發展的未來
原書名: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
出版日期:2014-12-17
作者:赫曼‧達利、約翰‧柯布
譯注者:溫秀英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92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4979
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已售完
生態人道主義者必須創造一個經濟體
在這個經濟體裡
經濟與人口成長是有所節制的
科技是可控制的
而所得不均是可以避免的
1980年代末,經濟學界仍然以所謂的新古典經濟為主流,達利與科布兩位教授出版《共善》,確實相當引人爭議。
在《共善》這本書裡,達利與科布兩位教授針對當時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架構進行深度討論,引用懷海德的「具體性錯置的謬誤」探討當時主流經濟思潮在架構經濟理論時所呈現的與真實情境相差甚多的情況。
兩位作者從哲學研究、邏輯思維、意識形態、經濟歷史觀到新古典經濟學在市場、國民生產毛額計算方法、土地等自然資源的認知等等面向進行分析與批判,並提出為社群而存在之社群經濟學的概念,著重在社群、分配的公義和永續性等方面的探討。藉此思考主流經濟學對經濟活動與人類福祉之間在認知與分析架構上的差距,並且嘗試對此提出對治方法。
達利與科布兩位教授在這本著作中所提出來的一些觀點,與當時主流經濟思潮的意識形態相當不同。不過隨著一些環境經濟學家、生態學家,甚至是生物學家的鼓吹,一些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也慢慢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羅伯特‧梭羅以及肯尼斯‧艾羅就曾分別表達對生態以及經濟體系之間複雜關係的重視,並且呼籲應該慎重審視生態系統在經濟成長分析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透過《共善》,達利與科布兩位教授鞭辟入裡的分析,在當時的學界造成不小的衝擊,如今主流經濟學家與生態經濟學者以及生態科學家之間的看法雖仍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間的對話已然開始,而近幾年生態體系與經濟、社會等體系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已引起愈來愈廣泛的注意與研究。《共善》這本書對於這種思維上的改變,無非是其中很重要的影響來源。
作者:赫曼‧達利
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公共政策學院,在此之前為世界銀行環境部門的資深經濟學家。學術期刊生態經濟學(Ecological Economics)的發起人之一,著作等身。在經濟學相關領域,尤其是在生態經濟學的貢獻,曾經獲得瑞典Honorary Right Livelihood Award、Heineken Prize for Environmental,以及挪威 Sciences and the Sophie Prize等殊榮的肯定。
作者:約翰‧柯布
現任美國加州克萊蒙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名譽教授,曾於1973年在克萊蒙神學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和大衛‧格理芬(David Griffin)創立歷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橫跨宗教、生態、經濟、政治等跨領域研究。
譯注者:溫秀英
任教於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中文導讀
原謝辭
緒論
第一部分:作為學術學科的經濟學
1 經濟學及其他學科之具體性錯置的謬誤
2 具體性的錯置:市場
3 具體性的錯置:衡量經濟上的成功
4 具體性的錯置:經濟人
5 具體性的錯置:土地
第二部分:新的開始
6 從學術學科到服務社群
7 從理財到經綸
8 從個人主義到社群人
9 從世界主義到眾多社群的社群
10 從物質和經濟租到能量和生物圈
第三部分:美國的社群政策
11 自由貿易與社群
12 人口
13 土地使用
14 農業
15 工業
16 勞動
17 所得政策與稅賦
18 從主導世界到國家安全
第四部分:朝向目標
19 可能的步驟
20 宗教性願景
後記:貨幣、債務與財富
附錄:永續經濟福利指標
參考文獻
緒論/自然界的真相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事實真相的呈現已經勝於文字上的修辭,並對思慮欠週的經濟教條進行了批判。不需要辭藻方面的修飾,世界觀察協會(World Watch Institute)一系列的《世界現況》(State of the World),以冷靜平鋪直敍的文字陳述了自然界的事實真相。尤其是其中1987年版,由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以及桑德拉‧波斯特爾(Sandra Postel),發表的一篇名為〈改變的臨界點〉(Thresholds of Change)的文章,更突顯了一些真相的存在。這些事實真相包括:
1. 地球的臭氧(ozone)保護層破了洞。更多的紫外線輻射照射到地球,因而可能增加人類罹患皮膚癌的機率,阻礙穀物的增長,並削弱人類的免疫系統。來自三十一國的代表,史無前例以理智的回應,同意共同降低造成臭氧層破壞主因的氟氯碳化合物(Chlorofluorocarbons)。
2. 證據顯示由二氧化碳引發的溫室效應(CO2-induced greenhouse effect),已經造成全球的暖化。在1983年,當時認為五十年內不會有太明顯的改變,但現在已經證明,1988年發生於中西部的乾旱與暖化之間確實有所關聯。
3.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正在減少中。由於棲息地的減少,尤其是熱帶雨林的破壞,使得物種滅絕的速度增加而減少了生物的多樣性。熱帶雨林只佔了全球7%的土地,但卻供養了全世界一半的物種(Goodland 1987)。
除此之外,酸雨(acid rain)破壞了溫帶森林,並且導致湖泊的酸性提高到讓一些物種無法忍受的程度。因為工業意外,在蘇聯的車諾比(Chernobyl)、巴西的戈亞尼亞(Goiania)、印度的博帕爾(Bhopal)民眾,受到空氣污染、地下水受到有毒廢棄物污染,以及輻射中毒的殘害。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的活動規模相較於地球的生物圈(biosphere)而言,成長的太過了。在過去三十六年間(1950-1986),全球人口成長了一倍(從25億增加到50億)。相同時期,全球的生產以及對石化燃料(fossil fuel)的消費各約成長了四倍。超過現有規模的進一步成長,所造成的成本上的增加,似乎會高過於所能創造的利益。這似乎把我們帶入了一個新的世紀,創造貧窮而不是創造富裕的「非經濟成長」(uneconomic growth)的世紀。這些真相如今還無法找到適切的修辭,來有效地對一般大眾對經濟觀念的麻木僵化進行批判。與凱因斯所說的相反,如今文字修辭上的寬容或是事實,非但不被認為是有助於真相的揭露,甚至被認為是錯誤的。道德上的關懷被認為是「非科學的」,事實的陳述則被認為是「危言聳聽」。
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魯諾(Robert Heilbroner)在其1974年的著作《探索人類的未來》(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裡,提到了人類的經濟活動對生物圈所造成之壓力的可能影響。他特別提到當經濟成長不再可能持續時,我們就必須面臨一些政治上可能造成的傷害。在這本書的1980年修訂版,他建構了一個直到下一世紀初的緩慢持續成長的經濟體模型。而當這個成長終止時,就如同他在1974年版中所提到的,他認為將不可避免需要更集權式的政府來掌控整個經濟體走下坡的轉換過程。(Heilbroner 1980, p.167)。
我們感謝海爾布魯諾以極罕見的意願,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來檢視成長性經濟體與生態系統所面對的物質上之限制,此兩者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本書所關心的主要議題,但我們相信透過思考、願景與想像,可以讓整個轉換過程更為平順。海爾布魯諾認為資本主義(capitalism)與社會主義(socialism),兩者都是支持成長性的經濟體,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的選擇,但我們並不這麼認為。這本書就是要試圖描繪出其他可行的方案。為了構思一個這麼不同的經濟體,迫使我們兩人不僅從經濟學的學科,同時也跨越到生物學、歷史、哲學、物理以及神學的領域。來自事實真相的批判,部分已經觸犯到了現今大學有關知識如何組織(例如知識如何產生、包裹以及交換等)的基本原則。
晦暗不明的經濟成效
如今來自自然界的真相以及與傳統標準的經濟理論之間的衝突,都有相當為人所熟知的過往歷史。過去兩個世紀,經濟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地球的面貌,尤其是人類的生活型態。而這主要是受到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的影響。工業的發展大幅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縱使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大幅增加,但每人可以獲取之商品與服務增加的幅度更大。北大西洋國家與日本大多數民眾的生活,從僅可糊口提增到富裕的水準,而新加坡、香港、台灣與南韓則共享這波經濟繁榮。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的成就。
在此同時,有關經濟的研究也趨於成熟,並邁向一種科學的形態發展。在社會研究領域中,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家所標示的科學有時被視為是同類的,經濟學與物理學以及生物學一樣設置了諾貝爾獎。其他人類社會學科的學生,往往既忌妒又盡力仿傚經濟學家,就如同一些經濟學者仿傚物理學家一樣。
公共政策受到經濟學者的觀點與提議之影響既廣且深,沒有這些幫忙,經濟的發展無法成長到如我們所見的。經濟學家深信,假如政治人物與政府部門能夠更注意他們的討論與建議,則政府的目標可以更有效率的加以實現。他們一再地指出,忽視市場原則的作法將導致資源的無謂浪費。即使是東歐國家的經濟學家也提議應該更仰賴市場的機制,所持的理由與西歐國家的看法相當類似。
不過工業化對於人類的經濟生活也造成了莫大的影響,這種改變到底會對個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早已引起心理學家的關注。凱倫‧霍尼(Karen Horney)在1937年提到了因工業化、高度競爭以及物質化的社會,對美國人所造成的壓力。她指出三種基本價值的衝突已然浮現:「攻擊性格的突顯使得基督教義倡導的兄弟情誼無法與之相互並存;對於物質的強烈欲望導致欲望無法滿足;對不受拘束之自由的強烈欲求,與我們所必須面對的一些限制與責任無法互容。」(Henderson 1978, p.25)。華特‧威斯考夫(Walter Weisskopf 1971)也進行一項有關經濟發展如何對人類的存在與精神方面產生影響的研究,他觀察到這種發展已經對價值的客觀判斷造成負面的影響,並且鼓勵了道德相對論(moral relativism)的看法。除此之外,經濟的發展強調在犧牲別人的情況下求生存,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越來越嚴重。
其他的批評者也指出了因經濟發展對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一位偉大的經濟歷史學家,就以生動的文字,「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來形容伴隨市場興起的社會發展。1944年博蘭尼在他的作品中,開宗明義寫道:「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主要在生產工具上造成幾乎是奇蹟式的躍進,但也伴隨著一般民眾生活上激烈的錯置。」(Polanyi [1944] 1957, p.33)。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對此現象也有同樣的困擾。他觀察到經濟思想成為功利主義哲理(utilitarian philosophy)的一部分,主導著十九世紀:「十九世紀發展出來的這套思維系統,著重的是個人的自我本位(egoism),忽略了所有其他的規範原則……不論是因還是果,事實上這個理論真切地描繪了十九世紀激情而世俗化的,缺乏社會責任的精神。在困惑當中,經濟上的成功又加重了這種在社會與政治上的情勢,而這似乎是一世紀以來的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必然造成的結果」(Schumpeter 1975)。
最近生態學家(ecologist)以及受生態學家所影響的一些人士,將這種經濟體制視為是惡棍一個。他們認為經濟的成長代表的是,從自然環境而來的原物料投入以指數的方式增加,並將產出廢棄於環境之中。他們認為經濟學家在資源消耗與污染等方面的關注太少,認為經濟學家不但忽略了投入因素的來源以及產出的後續處置,而且還鼓勵最大化投入與生產的作法,然而實際上只要生產量能夠支持人類的基本需求就可在這個星球上生存。
大部分的經濟學家忽略了這些批評,他們相信大多數的民眾感興趣的是產品的提供,多過於對心理上或是環境上可能的損失,並且認為那些主張工業化會造成這些苦痛的說法是過於言重了。他們指出工業化國家的財富成長快速,儘管貧富仍然不均,不過創造出來的財富為大多數人所享有。他們並且相信那些擔心未來環境變遷問題的人,同時也低估了一個繁榮經濟體可以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資本與創造力可以帶來科技上的突破,當環境成為關注的議題時,將可引領發明天才等人士來解決這些新的挑戰。
朝向經濟學領域的典範移轉
當一個學科如此成功又同時如此受到批判,或許可以說這個學科的假設與方法可能適用於某些領域而不適用於其他某些情況。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經濟學領域最重要的一些假設與「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觀念有關,也就是如何來瞭解人類的本質。經濟理論建基在認為個人的習性是傾向於極大化自己的利益,這個傾向並且在市場交易以及其他生活領域裡清楚顯現。經濟學家特別指出人類會理性地追求私人利益,而這隱涉了其他行為模式是不理性的,例如利他(other-regarding)行為或是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的一些行為等。
有關理性行為的這種假設,幾乎不包括所有的利他行為,雖然與西方神學在理解人類本質的看法上有所衝突,不過我們卻可在西方神學的看法中找到宗源。神學家曾經認為利他行為是一個倫理上的完美理想,尤其是在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之後,許多人觀察到利己(self-regarding)行為已經成為「墮落」(fallen)情況的主導者。十六至十七世紀天主教會改革運動的宗教改革者以及追隨者,更強調了這種所謂墮落的情形,並且鼓勵一般對新教徒(Protestant)文化聲稱對利他行動真誠性的質疑。在這種文化背景氛圍之下,慈善家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反對基督教義中有關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看法,一點都不令人訝異(Polanyi [1944] 1957, p.128)。追隨聖湯瑪士(St. Thomas)的天主教神學則更相信應從社會關懷與社區營造的面向來看人類的行為。
喀爾文派教義(Calvinism)對於人類的善與教會以及國家的世俗權威(earthly authority)有所關連的看法,抱持質疑的態度。他們認為與上帝的關係應該是直接且具決定性的,認為個人在世俗生活以及宗教事務上皆具有自主性,並且認為政府在干預上應有所節制。在羅馬天主教文化中,對社群的強調則與教會以及社會的統治階級制度息息相關。
現代經濟理論的根源與發展主要來自喀爾文派,兩者皆強調個人的自由,並反對來自世俗權威的干預。他們認為自利(self-interest)的動力,除了在少數的領域之外,幾乎主導了一切。經濟理論與喀爾文派在這方面唯一不同的看法是,前者認為這是理性的行為,後者則認為是有罪的。
喀爾文派雖然認為不應該太輕易相信利他行為的真實性,不過喀爾文派仍鼓勵做為真正的基督信徒應該有利他的行為。天主教義(Catholicism)鼓勵利他行為是人類的基本道德(natural virtue)。當基督教的信仰為主流勢力時,雖然並不阻止自利的行為,不過卻要求需要公開檢視尋求自我利益的行為。然而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檢視自利行為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有害。自利行為是理性的行為,換言之,它會對大多數的人有利。政府的反對或對這些行為的檢驗,所造成的弊會多於利。當這個看法取代了傳統基督教信仰的觀點,當市場原則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多時,在心理層面、社會層面以及生態方面所造成的諸多問題,使得對經濟學家的批評也越趨尖銳。
經濟學對於將個人從階級制度威權中解放,以及提供更多的商品與服務方面,貢獻良多。這個成就是如此之重要,使得很多人認為因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次要的,是為了達到這個重要成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或許是適當的態度與立場。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所謂正面的成就,已經越來越無法得到充分的證明與支持,所造成的負面後果也越來越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該是改變的時候了,而這個改變可能牽涉到透過典範(paradigm)移轉的方式進行。湯瑪士‧孔恩(Thomas Kuhn)在其著作中提到物理學有關典範移轉的重要性,孔恩的說法同樣也可做為思考社會科學領域中有關典範移轉的可能性。
夏羅默‧邁特爾(Shlomo Maital 1982)曾經針對五十所主要大學的經濟系教授進行問卷投票。其中一個問題問到:「是否意識到經濟學已失其所依?」結果三分之二的問答者回答是肯定的(p.17)。邁特爾相信這個學科正面臨危機,「與傳統經濟學看法相左的證據已越來越明顯。」「當不一致的證據浮現並批判了原來深信的觀點,這些學科信奉者將再次把事情導正」(p.262)。對邁特爾而言,這些改變正顯示出典範移轉正在發生。
萊斯特‧梭羅(Lester Thurow 1983)在《危險年代》(Dangerous Currents)提出了類似的結論看法:「經濟學往往需要在簡化的假設之下進行推論,但關鍵在於在對的時間使用對的假設,而這些判斷來自於研究真實世界的實證分析,這些實證分析包括來自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的分析,而不是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p.237)。在該書的其他部分,他提及「心裡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都有其本身的理論,可能導引出與經濟人相當不同的觀念想法。社會化型態、文化與倫理歷史、政治制度以及老派的作風等,在在都影響著我們的看法」(p.226)。梭羅在話語之間點出了新典範的一個方向:「社會並不只是一些個人自願參與交易之統計上的加總,而是涉及到更精緻與複雜的過程。若只是分析個人自身的行為,並不能真正瞭解團體或社群的行為。一個社會大過於其部分的加總,這是無庸置疑的」(pp.222-223)。他根據史蒂芬‧馬格林(Stephen Marglin)的說法,區別了「私自-個人偏好」(private-personal preference)與「個人-社會」(individual-social)的不同,並責怪經濟學家只處理前者的情形。
人類是很複雜的族群,可以從很多的面向來加以研究。每一觀點主要是從具體的現實性擷取而出,並且專注在人類行為的某些特定面向。宗教人(Homo religiosus)將人類視為是具宗教性格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將人類視為是具政治性格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則將人類視為是經濟性的族群。我們這本書主要把重點放在「經濟人」的面向來加以討論,但也不會忘記同樣可以從其他面向,如宗教以及政治的角度來加以觀察。我們企圖依據梭羅的觀念,避免只透過「私自-個人偏好」的說法來解釋經濟人。我們提出經濟人是社群人(person-in-community)的看法,而不是把經濟人視成是純粹的個人而已,這會更符合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以及經濟學家察覺的一些事實。我們並不否認社群中的個人在市場中的行為,與現有經濟理論對經濟人的看法是類似的,只是在對經濟生活的目標之基本討論中應該不單只從這個面向來下結論。博蘭尼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不是社會關係中的部分,而是社會關係被嵌進了經濟體系之中」([1944] 1957, p.57),也因為這種反向的關係,有關社群經濟之說法並不太容易被接受。
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模型完全符合邁特爾對新典範的要求,他曾寫道:「沒有任何科學會丟棄它曾受考驗且正確的原理,即使這些原理變得令人質疑且不正確,除非一個新的且更具說服力的原理出現」(1982, p.262)。我們並沒有提供新的原理原則,如我們會在第2章所建議的,將經濟視為是從原理原則中簡化而得的系統,反而是問題的部分。但我們相信經濟學可以從社群中的個人之觀點來重新實現它的理論,如此做仍舊能夠涵括之前從個人之觀點所得到的洞見。在此不需要「丟棄」它的原理原則,許多的原理仍舊有效,只是需要更能認知到其侷限之所在。這些改變涉及到一些修正與擴展,更傾向於實證與歷史觀的態度,少一些「科學」的矯飾,並且願意將市場視為是附屬的,而不是決定一切的一切。這是我們想要呈現的部分想法。
第一部分 作為學術學科的經濟學
1 經濟學及其他學科之具體性錯置的謬誤
現代的大學,知識是以科學的方式組織而成,並以清楚的基準呈現這些科學的歸屬。依據這些判斷準則,將科學依主題分門別類並建立起每一門學科內部架構的目的。這種組織知識的方式曾經成果輝煌,但它同時也建構在一些限制與危險之上,尤其可能發生艾爾弗雷德.懷海德所稱的「具體性錯置的謬誤」(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知識的組織以科學的方式呈現需要相當程度的抽象概念,而這使得具體情境錯置的謬誤更為嚴重。一個越能成功符合準則需求的科學,抽象程度越高。結果是許多成功發展科學的擁護者,無可避免地在這些抽象的概念中思考社會的種種,並將這些結論應用在這真實的世界而沒有考慮到牽涉的抽象程度有多高。
除了物理科學,似乎沒有其他的學科如經濟學如此滿足學科的理想形式,而由於它的成功,特別容易發生具體性錯置的謬誤。本章將透過對學科理想形式的了解來探討經濟學成功之處,同時探討因之附帶的不可避免的限制。我們將舉一些有名的經濟學作品中,發生具體情境被錯置的例子,而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將以更基本的分析方式來探討這些謬誤所造成的普遍影響。
17與18世紀,物理學的發展極為成功,而現代世界大部分的思想也受到對物理學的尊崇所影響。物理學家發展出對自然界的概念模型,並且導出相當多的預測,而這些經過測試,其中一些證實是正確的,其他實證結果則修正了一些概念或理論。在早期大量的數學應用以發展純粹的理論為目的,而這些理論發展出可以應用於解釋以及預測真實世界的能力。
物理學是可以證實的一門學科,這可從兩個面向來加以說明。首先,有關普世模型的假設,是透過觀察以及實驗所加以提出的。其次,這個模型的有效性,是透過它的可應用性以及檢視是否與觀察到的相互符合來加以驗證。但物理學與其他研究自然界的學科最主要的差別,不在於它的實證元素,而在於它的形式與演繹方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常鼓勵對實證資料的組合以及分門別類的做法,但他並沒有預測到發展複雜演繹系統的可能性。有關生物組織的研究長久以來依循著亞里斯多德學派多過於牛頓學派,不過科學的理想形態為法則的發現,而法則的發現來自於可以藉演繹而得的事實。
當然,以一個較直接的實證直覺來看,觀察到的事實並不一定直接符合這些法則。例如,伽利略(Galileo) 有名的證明,物體向地球墜落的速度並不受到其重量的影響,這些與經驗並不符合,每個人都知道一塊石頭墜落的速度較一片葉子來得快。只有在真空的狀態,這兩者的墜落速度會是一樣的,甚至需要更多的條件才能符合伽利略的說法。以實證的角度來看,月亮並不會朝向地球墜落,因此這個預測只適用於相對於地球為處於定態狀態的物體,或是處於相同的相對運動。再者,該法則只適用於處在地球重力場的物體,而且不被其他重力場所干擾。
這些皆為早期的物理學家所周知,而為了解釋經驗上的現象,必須發展出可以簡化實體的模型,以便能夠描繪出基本的特徵。在簡化的模型裡體現適當的抽象概念,提高了增加分析與預測能力的可能性。
簡化的模型之預測能力與真正的行為之間的差異,讓物理學其他有關力(force)的研究得以有發展的空間。例如,不管地球的重力影響的情況下,月球並不朝向地球墜落的事實,引起了對移動中的物體持續以直線移動傾向的注意。月球的運行實際上是受到兩個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地球的重力拉引以及月球自身的動力。任何脫離受到此兩個因素影響之月球運行,即使差異很小,都會引起是否有其他物理學中有關力之運作的研究。
物理學成功所帶來的讚嘆,促使了兩種不太一樣的有關組織知識體系的觀念。一種觀念是認為應達成一個統一的科學,自然界的任何面向最終都可以被物理法則所解釋。換言之,化學將成為物理學的次領域,而生物學為化學的次領域。
雖然這些看法持續在西方世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對於活生生的生物方面的研究,實在不太可能從多少的物理學的法則之中演繹出生物的行為模式。即使是化學,其呈現出來的複雜多樣也無法歸類隸屬於物理學領域。從實務運用的目的來看,它必須以它自己的方式進行研究,這對生物學的或是社會學的現象更是如此。因此,由物理學所倡議的科學形式可以運作的方式為,讓一些科學擁有相對的自主性,在各自的領域達成各自的目標來建立起類似物理學的科學形式,法則或模型的建立可以用來預測存在的事實。但即使在其他自然科學領域,這個目標仍然未被實現,例如,即使在化學領域,相當多的事實並無法從任何的基礎法則產生推論而得。然而,演繹的概念仍然導引著理論的產生。
儘管物理學家擁有相當高的聲望,仍有一些領域抗拒這種模式,尤其是有關人類的研究領域更是如此。直至最近,絕大部分的歷史研究與自然科學基本上是不同的,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問題是,真實發生的是什麼,而不是意圖從歷史的法則或不變的模型來推論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些人士認為歷史的基本任務是去了解而不是解釋或預測,他們專注於詮釋學(hermeneutics),並以其作為他們特別的研究方法。
19世紀有關知識的組織方式,受到來自物理學界的第二種形態的影響甚深,也就是分類於具有自主性的一些科學領域,這些領域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人類的現象。德國的大學以領導者之姿將知識組織而為「學科」(Wissenschaften),Wissenschaft通常翻譯為科學(science),但因為「science」在英文的意思強烈意指是物理學的模型,而不包括歷史,因此將之翻譯為學科(discipline) 比較妥當。在德國,知識主要以兩種學科形式組織歸類,自然學科以及人類心智或精神的學科。
有關人類社會現象的研究,則從未曾自在地感覺可以鑲進上述兩類形式之中的任何一類。人類社會的研究在這兩類學科組織歸類間拉扯,它們牽涉人本元素,也牽涉一些與自然學科有關的元素,而在美國則有很強烈的傾向認為,它們屬於所謂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要了解科學的學科(scientific disciplines)與人本主義的學科(humanistic disciplines)之間的差異,可從了解前者為著重在什麼是普遍的必須的,而後者著重在什麼是特別的以及或然的差別處開始。當然,科學的普遍性在許多例子中並不是絕對的。古典物理學可以視自然界的架構是絕對的,但生物學只能研究什麼是對生物是具普遍性的,而社會科學只能最多推論什麼是對人類是具普遍性的。甚至,社會科學往往是在探討,什麼對某一特定的社會形態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對能夠普遍適用之模型或法則的追求,而不是努力於釐清與理解真實世界的或然特質,導致這些人類社會的研究方法更加促使它們視自己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