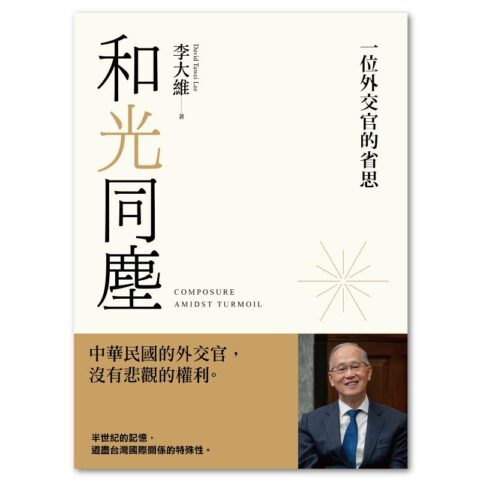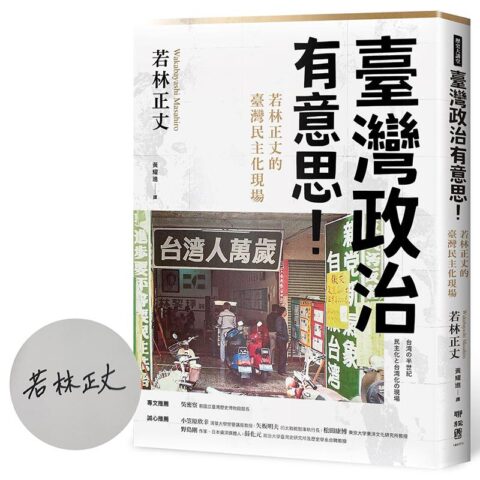當代社會中的理性
原書名:Reason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出版日期:2018-09-23
作者:查爾斯‧泰勒
譯者:蔣馥朵
編者:蕭高彥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144
開數:25開,高21 × 寬14.8c
EAN:9789570851793
系列: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
尚有庫存
「鄧普頓獎」(Templeton Prize)、「京都獎」(Kyoto Prize),以及「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得主查爾斯‧泰勒,以政治哲學角度切入當代議題,並為其論述賦予歷史縱深與未來展望。
2016年「中央研究院講座」邀請到國際知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來台演說。《當代社會中的理性》前兩講是其中央研究院講座稿的譯本,分別探討西方民主的危機以及現代社會中的世俗主義兩個重要議題。
泰勒教授主張唯有將民主重新理解為一種「目的式」過程,降低社會不平等,恢復全體人民自治的古典意涵,方能提升民主的正當性。而在多元分歧的現代社會中,宗教仍為追求超越性的重要管道,政府應該強調寬容,並公平而和諧地管理多元的宗教組織。
第三講為泰勒教授特別提供的手稿,討論西方近代理性以及道德秩序觀念的發展史,以作為其論述民主與世俗化問題時的哲學以及思想史基礎。
作者:查爾斯‧泰勒
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及政治理論家之一。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榮譽退休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曾榮獲「鄧普頓獎」(Templeton Prize)、「京都獎」(Kyoto Prize),以及「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等。2015年獲頒「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為全球人文思想與社會科學的最高學術榮譽。泰勒教授出版超過20本專書,以及500多篇論文,許多著作被譯為多種語文發行全球。其研究興趣廣泛,關懷領域遍及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宗教哲學、哲學史、道德與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多元文化承認論、現代性自我理論)等。
譯者:蔣馥朵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學士、政治學碩士,目前於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攻讀筆譯碩士。
編者:蕭高彥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1993)。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並合聘於中研院政治所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思想史以及當代政治社會理論,核心議題包括共和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現代國家觀念史。著作包括《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榮獲2014 第三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以及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與中英文學術論文數十篇,發表於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Politics、Issues and Studies 以及許多台灣的專業學術期刊。曾獲選為Bradley Foundation Fellow、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並獲得兩次國科會研究獎助傑出獎。學術服務方面,曾擔任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中研院學術諮詢總會副執行秘書、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主編、《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執行編輯、《台灣政治學刊》、《政治科學論叢》與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編輯委員、台灣政治學會執行委員,以及中國政治學會理事。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黃進興)
編者緒論:查爾斯‧泰勒關於「另類現代性」的考察(蕭高彥)
第一講 西方民主的危機?
第二講 西方民主的危機?
第三講 單在理性
序/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是我國最高之學術研究機關,負有指導及獎勵學術研究的任務。除了推選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外,本院實際組織則以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三組,成立研究所及研究中心,延聘優秀學者,從事各領域最為尖端的原創性研究。
在學術研究之外,正如同世界的頂尖大學及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也運用豐富的資源,發揮其獨特的學研角色,扮演學術界與社會大眾知識的橋梁。而「中央研究院講座」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每年邀請全世界最頂尖的學者來院訪問,並發表演講,介紹其專精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展望。
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世界各國重要學者,除了深耕學術研究,往往也在各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扮演極為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甚至在關鍵的歷史時刻,形成民族風尚。他們的演講,往往運用學術理論於經世致用,如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對德國民族的演講,或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關於學術及政治作為志業的演講,均為其中之著例。
2016年「中央研究院講座」來訪的查爾斯‧泰勒教授,多年來在倫理學、政治哲學,以及思想史方面的學術研究,躋身世界一流學者及思想家之列。他近年來關於世俗化的理論,在學界產生重要影響,個人在從事孔廟聖地的分析時,曾有所參照。我也把握了他訪問中研院史語所的機會,與他當面討論在跨文化的脈絡下,神聖性與世俗化對立的不同可能樣態。
多年前個人遠渡重洋到哈佛深造,當時校園內名師雲集,也常有世界級的學者到訪演講,百家齊鳴,交織成一部波瀾壯闊的交響曲。期望未來中研院講座所邀請的大師,能在造訪的當時,對我國學術界產生積極的助益。而陸續刊行「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後,能讓年輕學子及社會大眾有機會了解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發展,並思考這些理論觀點如何與我們所處在地社會文化激盪出新的前瞻性思維。
查爾斯‧泰勒關於「另類現代性」的考察/蕭高彥
2016年度「中央研究院講座」邀請到國際知名的哲學家查爾斯‧泰勒來台演說。泰勒教授是加拿大人,研究所時代負笈英國,在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曾擔任牛津大學Chichele講座教授,並同時任教於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潛心學術研究之餘,泰勒教授極為關懷政治現實,並曾積極參與。在60年代,當他毅然放棄牛津大學講座教授,回到加拿大全職任教後,曾經代表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四度參加眾議員的選舉。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在1965年的選舉中他輸給了當時的政壇新秀,也就是未來總理的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之後泰勒教授雖然沒有繼續參選,但仍持續積極參與魁北克關於語言政策的立法討論,將其政治哲學的思考落實於實踐領域。
泰勒教授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包含了認識論、倫理學、政治哲學,乃至思想史及歷史哲學。他勤於著述,著作等身,計有20餘本學術專書及500多篇學術論文。泰勒教授一以貫之的學術旨趣,在於探討人作為行動者(human agent)在社會及歷史行動中,所展現出獨特的思想及行動樣態,並且嘗試從哲學及思想史的角度,呈現這些人類豐富的歷史經驗。
泰勒教授在取得博士學位後,主要關注的焦點在於批判當時盛行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雖然在英國接受哲學訓練,但他很快地便脫離了分析哲學的主流陣營,並且運用歐陸詮釋學(hermeneutics)的傳統,主張人是創造意義的動物,必須通過每一個人有意義的行動所交織出主體際(intersubjective)的意義網絡,才能適當地理解。泰勒教授之後將構成此意義網絡的思想資源,稱為特定社群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這些社會想像,構成了人們在歷史中持續思考以及行動的脈絡,唯有深入理解詮釋這些資源,才能掌握人類行動的真義,畢竟這無法用外在行為的表徵加以機械式地解釋。
泰勒教授在70年代積極爬梳歐陸的思想史,特別是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及浪漫主義(romanticism)傳統。他的巨著《黑格爾》是英語世界討論黑格爾哲學的分水嶺,讓歐陸以外的讀者,能夠從細緻的歷史背景分析,以及黑格爾理論系統化的兩個面向,掌握其思想之精義,擺脫二戰前後討論黑格爾與國家主義或極權主義關連的窠臼。
在思想史研究的基礎上,泰勒教授建構了其政治哲學的理論體系,其主軸在於探究「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形成。他主張主流的現代性是由市場經濟,以及管理取向的官僚國家所構成,但這絕非如「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主張者的信念,認為這即足以窮盡現代性。對泰勒教授而言,現代性同時發展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及民族(nation)或國民(people)的不同理念,並在主流現代性的框架下,嘗試追求克服社會趨同性帶來的同質化(homogenization)現象,以建構能尊重差異性的社會政治形態。
泰勒教授在這個時期的政治哲學論述中,批判早期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所展現出的康德主義面向,強調程序正義足以推動公平的社會。在這個議題上,泰勒教授和麥肯泰(Alasdair McIntyre)及沈岱爾(Michael Sandel)等思想家共同開啟了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思想風潮,將黑格爾的觀念論及亞里斯多德的實踐哲學,提升為可與康德式普遍主義抗衡的思想資源,帶動了80年代末期政治哲學的重大變遷。同時,也使得羅爾斯從早期的康德主義取向,轉變為90年代以後主張「政治而非形上學」(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在這個時期,泰勒教授除了完成《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這本學術巨著之外,他在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場域所提出的「承認政治論」(politics of recognition),以及他對加拿大法語社群作為獨特的文化群體所提出的民族主義辯護,都成為政治哲學界的討論主題。在90年代中期以來,泰勒教授關注現代社會中的宗教議題,並且對於宗教社群在世俗化的過程中所扮演(以及應當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與啟蒙思想完全不同的論述。
在兩次「中央研究院講座」中,泰勒教授分別探討了西方民主的危機,以及現代社會中的世俗主義兩個議題,綜合了他長期以來的政治思想及歷史哲學反思。在民主議題方面,他指出民主作為「人民主治」的政治形態,其中的「人民」一詞,從希臘以來便具有廣義的全體人民,以及狹義的非菁英之人民兩種可能意涵。民主政府的正當性,廣義而言來自於全體人民,但狹義則意味著政治領袖需要得到平民的支持。泰勒教授強調,「人民」的歧義,在西方形成了一種辯證發展的關係,從而產生了一種「目的式」(telic)的民主觀:在現存的社會中,仍有菁英及平民間權力的不平等,民主社會的目標則是克服此種社會不平等。換言之,民主是一個過程,應當不斷擴充「人民」的影響力,並包含更多的平民。然而,70年代以來的西方民主,因為不平等的持續滋長,導致了政治參與降低,以及對民主信念的流失。泰勒教授主張,唯有將民主重新理解為一種「目的式」過程,方能提升西方民主的正當性。
在第二講之中,泰勒教授區分西方民主社會處理宗教組織的兩種模式。其一為美國模式:在立憲以後,致力創造一個性質中立的聯邦政府,在不同的信仰團體中,尋找某些交疊共識,並且以此作為政治治理的基礎。另一則為法國模式:在法國大革命推翻舊制度之後,共和政府著重於控制組織龐大且長期具有壟斷地位的天主教會。這兩種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現代世俗主義的兩種樣態:前者重視公平而和諧的管理多元性,後者則極力將宗教維持在其特定領域中,不得越界。泰勒教授主張,在多元分歧的現代社會中,美國模式比較能實現包容性的政治治理。
泰勒教授事前已經提供兩份講稿紙本,但在實際演說前,都在會場旁的貴賓室,重新翻閱自己的講稿,潛心專注思考。演講時,他完全不依賴講稿、大綱或投影片,將其主要論點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時間控制得極為完美,令人印象深刻。兩場講座都聚集了滿堂聽眾,在演講結束後,除了踴躍提問之外,更有許多學者及莘莘學子拿著泰勒教授的書籍請他簽名,或繼續討論。
在演講完畢後,經與泰勒教授溝通,他同意除了兩講之外,另外提供一篇他討論西方近代理性及道德秩序觀念發展史的稿件,作為其論述民主與世俗化問題的哲學及思想史的基礎,也就是本書的第三講。而在第二講與第三講手稿中,有小部分重複之處,則由編者重新編輯,以使兩講的主題能夠有所區別。本次講座之文稿有部分內容接近工作中的初稿(work in progress),並不容易翻譯。本書譯者蔣馥朵小姐付出了相當的時間與心力,編者謹致謝忱。
西方民主的危機?
非常感謝翁院長及中央研究院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在「中央研究院講座」討論當代社會幾個關鍵議題。台灣是一座民主活躍的島嶼,非常適合進行這方面的探討。
接下來,我主要想論述的議題是「西方」民主。今日的民主有許多形式,我唯一敢自稱熟悉的,只有西方民主,也就是當前主導北大西洋地區的民主形式。不過,以全球局勢觀之,民主國家其實具有許多面貌,即使排除了名不符實、完全不配「民主」之名的假民主國家(這類國家不勝枚舉),民主的形式還是相當多樣。當然,如果將多少還算合乎民主的政治體放在一起,那麼現有政體的絕大多數都可劃入這個範圍。由此可看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共通假設。事實上,要是你深入探究,會發現每個民主國家都自成一格。
(一)綜評民主
民主的意思是權力歸於人民,由人民來治理。但在實務上,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民主的「治理」與一人獨治(autocracy)的「治理」不同;後者的治理方式很直接,就是由國王或獨裁者下令、任命所有重要官員,並做出所有關鍵決定。
但「人民」的統治不能如此直接。可以說,人民要先讓自己有個共同「意志」(will)。唯有透過複雜的制度與程序,才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意志,而這些制度與程序又要在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ies)中才有意義。主流的社會想像在某些特定時期不懂民主,導致民主失敗,這是常有的事。以當前阿富汗為例,大家還是習慣將各部族參與的支爾格大會(Loya Jirga)視為具有正當性的決策機構,而非替經過普選產生的議會與總統賦予正當性的機構。當然,民主之所以失敗,也或許是因為我們對民主的理解並不適用。比方說,人民選舉出的議員就會遵循人民的意志嗎?鑑於民主過程的複雜度,也由於其中有諸多難以確認的事實,因此常令人懷疑最後的結果究竟是否符合當初的預期。
存在於實際情況中的,是各自有其想像的民主社會。所謂想像,指的是他們對自己身為民主國家的想像,以及他們對應這想像而採取的一系列作為。至於現實,甚至還更為混亂多變,因為各個社會通常有不同的自我構思(auto-conception),各自分歧,並且隨時間而不斷演變。
(二)民主前進?
在今日,西方自由社會普遍相信,無論形式為何,民主確實是正在向前邁進(雖然大家不大清楚各種民主之間的真正差異)。許多人相信,我們正走在一條以全球民主化為終點的道路上。眾所周知,這是條顛簸的道路,民主發展有時突飛猛進,有時節節衰退。民主在1930年代歷經了嚴重衰退:許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場本意是要讓世界更適合民主國家的戰爭)後建立起的新生民主國家反而深受威權統治之害。不過,隨著同盟國在二戰的勝利、殖民主義終結及柏林圍牆倒塌,部分非洲地區出現了令人充滿希望的發展,中東地區也迎來了阿拉伯之春。
但另一方面,仍舊出現嚴重的民主倒退。中國遲遲沒有進展,俄國恢復到一種高度控制的「民主」,而阿拉伯之春過去曾給予人的希望,如今早已煙消雲散。不過西方人大多還是十分樂觀,因為他們認為,有一股力量仍在默默運作。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想法?他們認為,因為這是最穩定的政府形式,所以民主終將取得勝利。甚至可能有人會主張,因為維護民主並不需要時時採取鎮壓手段,所以這是唯一真正穩定的形式。
民主是最穩定的形式?這種見解應該會讓十八世紀的人大吃一驚。美國開國元勛區分了「民主」與「共和」這兩種統治形式,並選擇了後者。不過,這是因為他們採用了另一種民主定義,可上溯古典時期。我之後會回來談這一點。回頭看這種樂觀展望背後的思維,其實民主吸引力的祕密,在於這種制度帶來了「法治」(rule of law)。人們得以平安生活,是因為他們的權利受到尊重,即使權利受到侵害,也可以在法庭上獲得補償。同時,固定舉行的普選也可確保利益(至少是多數人的利益)不會被完全忽視。
因此,民主國家的穩定度是其他政體無法企及的。此外,其他政體必定會承受不斷升高的壓力,因為當代世界有一個普遍的特點,就是教育、傳媒、經濟變化、全球化、消費資本主義等等,會將人們由對權力菁英的忠誠中解放出來,最終使得威權國家航向充滿不穩定性的海洋。引進民主是平穩情勢的唯一可行方式。因此,許多人預測,就算是中國,都有躋身民主國家之列的一天。
這種觀點背後,有一套對民主的理解,我們或可稱為準熊彼得式(quasi- Shumpeterian)理解。人民由平等的個人組成(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人人都有自己的一票;而實際上施行統治的,是專家菁英及自行上位的政治家。當然,人民還是定期投票,選舉也都符合自由與公平的標準。這樣一來,確實有可能替換現任官員,如果現任統治者地位不穩,隨時有其他菁英等著起而代之。
我們姑且稱此為統治的「偶然性」(contingency)特點。這項特點還有其他條件,如自由的媒體、意見交流的公開平台,以及集會權利等等。這些事物有助於選舉的自由與公平,若是沒有這些條件,便無法使不同統治者順利輪替,因此妨礙了偶然性。在西方自由主義式思想中,還存在另一項條件,就是所有人都要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即使是在種族、文化和宗教方面與主流不同的人也一樣。這項條件的目的,就是為了包容(inclusion)。
這個體制讓至少是多數人能夠受到認可,也使局面達到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穩定;可說大大逆轉了古典時期,甚至是十八世紀晚期的情勢,如我之前所述。美國開國元勛對民主的態度十分戒備,這種觀點可上溯到亞里斯多德。既然民主乃是由人民統治,統治者自然不是菁英。如此一來,不但會帶來危險與不穩定,甚至可能會出現掠奪人民財產的狀況,而財產正是繁榮與文明的基礎。不過,這種想法在準熊彼得式觀點中已不復存。自由主義思想將大獲全勝的樂觀預測,背後正是「健全的民主能保持穩定」這個觀點。
這幅圖像有什麼問題?首先,這顯然低估了威權政體可以運用的資源,特別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讓人在面對過去的西方殖民強權時懷有一種歷史的委屈感,甚至是一種在強權手下的屈辱感,並懷疑這些西方強權正在透過助長怠惰、同性戀等等不良風氣,來摧毀其社會結構與宗教,以削弱他們的國力。普丁甚至想建立起「反自由主義國際」(counter-liberal international),發揮團結力量來抵擋文化道德的敗壞。此外,這種樂觀預期也忽略了既有民主國家內部的衰敗與倒退,使得民主國家面對新挑戰時更沒有回應能力。
(三)民主衰退
不過,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參考另一種仍延續著舊有傳統的民主概念形構(conception)。民主不單純是由全體人民施行統治而已,還必須將會對指涉人民的詞語(people、demos和populus)造成影響的模糊與歧義納入考量。在現代歐洲語言中,這個詞彙擺盪於兩種意涵之間:廣義來說,人民包含了社會中的所有成員,至於狹義中的人民,指的則是非菁英階層。後者正是古典定義下的平民(demos),亞里斯多德也因而以「民主」(democracy)來指涉這種由平民統治富人與貴族的階級統治形式。十八世紀晚期的思維,可以說不過是追隨亞里斯多德而已。因此,亞里斯多德的理想政體,是一種不同階級之間的權力平衡,以防出現寡頭或民主這兩種階級力量懸殊的政體。
我在這裡想重新提出的當代概念形構,是熊彼得式概念的替代選擇,但並不只是要回歸古典意義而已,畢竟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沒有這種普世平等主義色調。我要說的是,由廣義的「人民」施行統治,是民主的目的(telos)。然而,在現代社會中,菁英與非菁英之間不但會持續保有懸殊的權力差距,已然消弭的差距都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因此,這樣的社會需要轉型,才能達到或守護這個社會目標。若不保留「人民」一詞的雙重意義,我們無法好好陳述此種民主理解,也無法討論實現民主所需要的條件。
在「人民」的兩種意義之間,其實有著內在的連結。希臘的「階級」(class)概念融入了現代「全面」式(all-englobing)的定義,透過一種末世、宿命的希望,期待第一種定義最終會轉變為第二種。若以烏托邦形式表現,就是「社會主義國際必定實現」(搭著國際歌的旋律)。不過,這的確是民主的一項重要承諾,可以稱為「目的」(telic)式概念形構──當然,這兩種概念構成都是理想型,多數當代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想像其實更為複雜,也不盡然一致。大多數的認知都擺盪在熊彼得式和目的式之間,端看政治脈絡與議題為何。
但就民主理論的層次,我在使用「熊彼得式」的說法時,彷彿認定「目的」已然達成,勢不可逆,我們從此可以忘掉以階級為基礎的狹隘人民定義。當然,的確時常有人呼籲,我們應當忘掉這種定義,而平等政策的支持者也常受到反對者指責,稱前者是在挑起「階級戰爭」。但這種想法和事實實在相去甚遠,無論過去或當代皆然。我們很難相信民主的目的已經獲得實現,不可逆轉。觀察過去兩世紀以來真實世界裡的民主,可以看到情勢不斷在進步與退步之間搖擺。隨著時間變化,菁英與非菁英的區分基礎、社會力量的基礎都不斷在改變。
最早的權力劃分基礎是地產,接著是對工業與鐵路的掌控。隨後,控制者由個人演變為集團,進而成為跨國集團。當代金融機構對我們整體生活的影響力之廣泛,到了不成比例的地步。美國二十世紀初訂定的反托拉斯法案,或二戰結束後的西方福利國家,這些以抗衡或抵銷其影響為目的的手段或安排,不是本身逐漸失去作用,就是在新的國際權力分布中失效。
在追求經濟平等的路上,同樣也是有得有失。工業與商業發展降低了早期因地產而造成的不平等,但工商業發展讓美國迎來「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時代,又嚴重加深不平等。隨著福利國家的建立、貿易聯盟的成長,以及充分就業政策的推動後,先前的嚴重不平等情況在二十世紀中期和緩下來。然而,自1970年代起,前些時候的進展開始穩定倒退,經濟不平等達到歷史新高。因此,將民主視為一個尚待達成的目的,在我們的時代仍有其意義,即便在將來,其重要性也不會有淹沒於歷史中的一天。
我認為,由現代民主史中的另一樁事實,可以看出「目的」式概念形構的重要性。各種議題的支持者在民主場域中角力,而最重要的議題事實上都圍繞著以下疑問:我們究竟是正朝著目的前進,還是漸行漸遠?當人民感受到進步,就是民主政治最有活力的時候。二戰結束後的「輝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榮景、今日的印度,以及民主希望在埃及解放廣場萌芽的時刻,就是人民深切感受到民主活力的時刻。反之,當我們偏離這條路,越來越憤世嫉俗時,公民參與也隨之下降。相較於戰後時期,民主在今日的西方國家裡顯得疲軟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