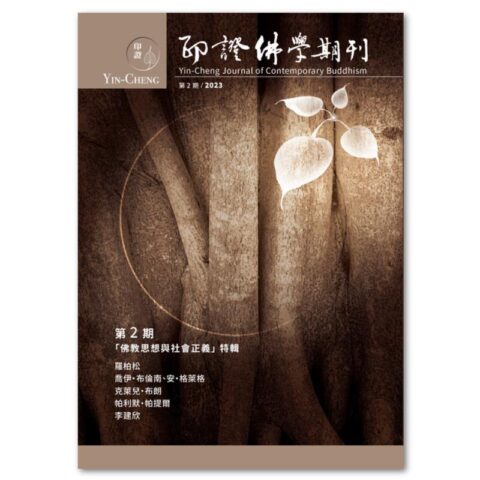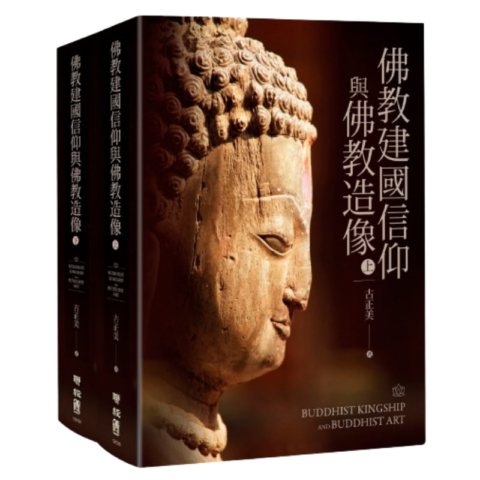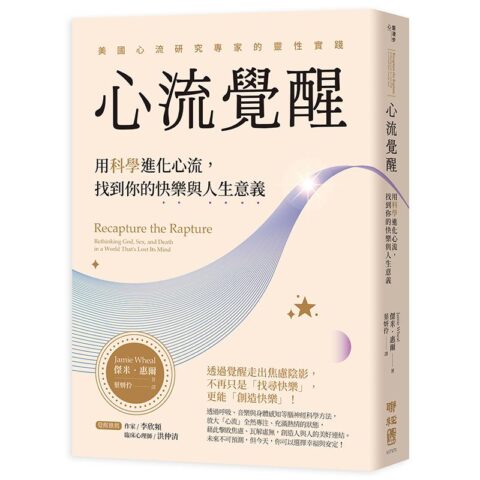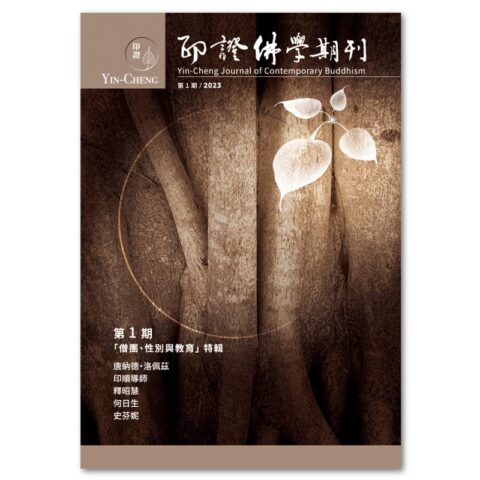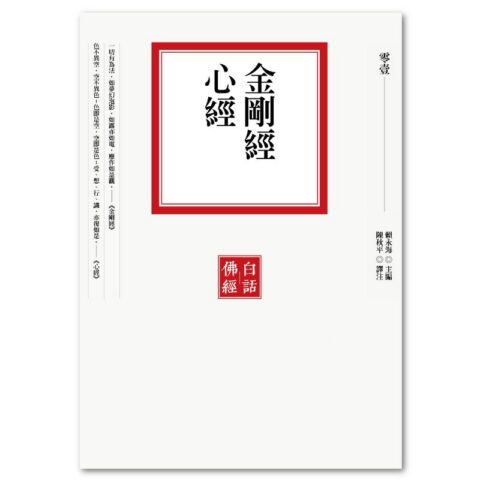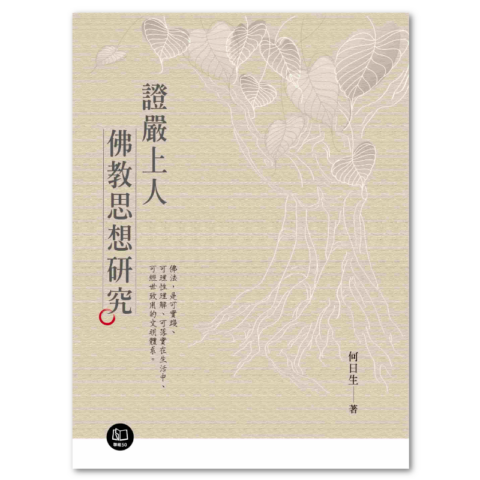宗教是什麼
原書名:宗教とは何か
出版日期:2011-05-20
作者:西谷啟治 (Nishitani Keiji)
譯注者:陳一標、吳翠華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40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8015
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已售完
1961年出版的《宗教是什麼》,被譽為戰後京都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品,立基於「空的立場」,與西方的虛無主義、近代自然科學世界觀、基督宗教做正面對決,透過虛無主義以超克虛無主義。當哲學的虛無主義宣稱上帝已死,自然科學的世界觀認為世界完全是由機械性的自然法則所支配,兩者結合,無神論被提升到用來取代宗教的地位,西方近代文明就走入了虛無主義的困境。西谷認為宗教不是單純對超越次元的信仰與崇拜,而是以主體性的方式對實在的一種實在的自覺,也就是從大疑現前而參禪悟道,透過「空」以克服虛無主義。
第一章〈宗教是什麼〉和第二章〈宗教中的人格性與非人格性〉,說明如何才是探問「宗教是什麼」的正確方法,並分析虛無主義在現實世界會以什麼樣態呈現,從自然科學、哲學、宗教方面做有關其歷史發展的整體考察。第三章〈虛無與空〉提出空的立場,說明其與西方的虛無有何不同,如何能夠克服虛無主義。第四章〈空的立場〉從「有唯有與空為一才是有」來掌握事物的自體性的、非對象性的存在方式,闡明空有的關係,藉此再次凸顯空的立場之特色。第五章〈空與時間〉、第六章〈空與歷史〉則論述空的立場與歷史性的關係,說明時間在空的立場中會以什麼形態出現。
本書並非以既成的宗教現象為基礎,來解析、論述宗教的一般性特質,而是根植於坐禪體驗的西谷哲學,對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菩薩行的深刻洞察與精彩剖析。因為「空」,所以每一個事物自體都可隨處為主,成為世界的中心,但也同時無化它自身,進入到其他事物之本,成為支撐其他事物的力量,絕對的自我否定即是自我肯定,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達到「水清徹地,魚行似魚;空闊透天,鳥飛如鳥」的自在境界。
作者:西谷啟治 (Nishitani Keiji)
西谷啟治(1900-1990)
西谷啟治師承京都學派開創者西田幾多郎,1924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後,留校任教。1937-1939年,赴德國弗萊堡大學研究宗教學,師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深受其哲學影響,並曾於海德堡大學開設宗教哲學課程,在東西對話上頗有貢獻。回國後繼續執教於該哲學科,1947年因戰時涉及為日本民族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之構想建立理論基礎,成為戰爭的幫兇,在占領軍的政策堅持下被迫停職,1952年復職。1963年退休,轉任大谷大學教授。
西谷認為整個西方近代宗教、哲學、科學的問題,即是虛無主義的問題,懷疑神、世界、歷史、自己與他人的存在,西谷窮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標即是「近代的超克」、「虛無主義的超克」,立基於禪的立場、空的哲學,透過虛無主義以超克虛無主義。其貢獻甚廣,遍及文化論、藝術論、科學與技術的問題、社會問題、宗教對話等。主要的著作有《根源的主體性的哲學》(1940)、《世界觀與國家觀》(1941)、《神與絕對無》(1948)、《虛無主義》(1949)、《宗教是什麼》(1961)、《般若與理性》(1979)、〈空與即〉(1982)、《西田幾多郎──其人與思想》(1985)、《禪的立場》(1986)。
譯注者:陳一標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教於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現為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專業領域為佛教唯識哲學、梵文、佛學日文。近年學術著作有〈緣起與業──瑜伽行派對等流種子與異熟種子的詮釋〉(2009)、〈虛無與空──西谷啟治的宗教哲學〉(2007)、〈唯識學「行相」(ākāra)之研究〉(2007)、〈他空說的系譜與內含──論印順法師對唯識空性說的理解〉(2006),譯作有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東大圖書,2002)。
譯注者:吳翠華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專長領域為兒童文學、中日比較文學。近年學術著作有《文學、風土與社會──童謠詩人金子美鈴作品研究》(文津,2009)。
以實踐為優先的西谷哲學(陳榮灼)
西谷啟治的《宗教是什麼》與我的閱讀(林鎮國)
從絕對無到空的哲學──從京都學派內部思想談《宗教是什麼》的成立脈絡與立場(陳一標、吳翠華)
凡例
第一章 宗教是什麼
第二章 宗教中的人格性與非人格性
第三章 虛無與空
第四章 空的立場
第五章 空與時間
第六章 空與歷史
譯者後記
西谷啟治年譜
參考書目
陳一標、吳翠華
從絕對無到空的哲學──從京都學派內部思想談西谷啟治《宗教是什麼》的成立脈絡與立場
《宗教是什麼》於1961年出版,被譽為京都學派戰後最高的代表作。西谷所要面對的三大問題是:一、與虛無主義的對決,二、與近代自然科學世界觀的對決,三、與基督宗教的人格性的意志神以及近代立基於科學、技術的世界觀所產生的非人格性者這兩種想法的對決。歸結來說,即是面對西方虛無主義,如何從虛無主義來超越虛無主義。他所提出來的是根源的主體性哲學亦即空的哲學,主張我們不只要超越意識的場所進到虛無之場所,以超越理性思惟所產生的主客對立,更必須超越意識的場所進到空之場所,以再次肯定在虛無中所被否定的一事物。
內在於京都學派,西谷啟治空的哲學與西田幾多郎絕對無的場所論、田邊元的種的論理有密切的關係,本文擬從探索西田幾多郎的純粹經驗、絕對無的場所等概念成立的脈絡、衍生的問題,後繼者田邊元為何提出種的論理與懺悔道的哲學,以及西谷如何用意識、虛無以及空的場所之不同,來說明他所謂根源的主體性哲學的特色,藉此來鳥瞰《宗教是什麼》成立的脈絡與立場。
一、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無」哲學
(一)《善的研究》的「純粹直觀」
西田幾多郎於1911年出版處女作《善的研究》,在表達其哲學思想的第二編〈實在〉的第一章「考察的出發點」中,開宗明義地說,使人能安身立命的道德宗教的實踐要求,和哲學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有密切的關係,實踐的真理必然就是知識的真理,一個深思、真摯的人必然會追求知識與情感、意志的一致。而在思考什麼才是無法懷疑的直接知識時,他不認同培根所說以一般的經驗作為知識之本,也不認為笛卡爾經由「我思故我在」所推論出來的「自我」是實在的。西田從年輕時代長久的坐禪,所體會到物心合一、主客未分的體驗,而提出「純粹經驗」的概念。他說:
所謂經驗,事實上本身即是知之意。完全捨棄自己的加工,依照事實而知。因為普通所說的經驗實際上是夾雜有某種思想,所以在此所謂的純粹,是指絲毫不加入任何的思慮分別,真正經驗本身的狀態。如見色、聞聲的剎那,還沒有想到這是外物的作用或者有我感知到這些外物,不只如此,甚至於連這色、聲為何的判斷都還未加入,純粹經驗指的就是這些想法、判斷還未加入之前的狀態。因此,純粹經驗和直接經驗是同一的。當下經驗到自己的意識狀態時,既無主也無客,知識與其對象是完全合一的。這是經驗中的最醇者。
西田藉由純粹經驗來說明思惟、意志與知性的直觀,更由此來解釋何謂自然、精神、善、神以及宗教的本質。下村寅太郎曾指出純粹經驗被看成作用時,是主觀;被看成「東西」或「事情」時,是客觀或存在。純粹經驗既是意識作用,也是被意識的事實。下村分析整個純粹經驗含攝的內涵共有12項,清楚地勾勒出它的全貌。簡單來說,純粹經驗是我們最直接的經驗,沒有任何平常所謂識的分別參與其中,然而這主客未分的意識,是一種自覺性的存在,其中本具能見與所見,由此而有一般經驗的產生,而我們之所以最後可以追求善,並且達到善的境界,都是純粹經驗的直接展現。
(二)絕對無的場所論
然而純粹經驗此一西田思想前期的重要概念,隱含了一些問題,如藤田正勝以西田幾多郎《從活動者到能見者》(《働くものから見るものへ》)的序言為線索所指出的,其中最棘手的問題乃是「作為直接所與的經驗與透過判斷所言詮的概念知識之間的關係並不清楚」,也就是說作為主客未分、無意義的事實的純粹經驗,有了自己發展而形成判斷、構成思惟時,依然與最原初的純粹經驗是同一的,但是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說明呢?其次,藤田健治指出純粹經驗這樣的自覺存在,無法說明此世界中個別的存在間的關係。西田在1926年發表的〈場所〉一文中,提出了「場所」作為「辯證法的普遍者」,使他的思想的論理化有了一個端緒。他在1936年《善的研究》新版的序中說道:
純粹經驗的立場到了《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自覚における直観と反省》),透過費希特的事行(譯者按:Tathandlung)立場,進入到絕對意志;進而在《從活動者到能見者》(《働くものから見るものへ》)的後半,透過希臘哲學,一轉而為「場所」的思想。「場所」的想法被具體化為「辯證法的普遍者」;「辯證法的普遍者」的立場被直接化為「行為的直觀」。此書中所謂直接經驗的世界或純粹經驗的世界,現在被認為是歷史的實在的世界。行為直觀的世界、poiēsis(譯者按:製作)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純粹經驗的世界。
如下村寅太郎所指出的,純粹經驗的作用與作用的對象是同一的,能見與所見也是同一的,所以這不外是「自己看見自己自身」。然而這種自覺的意識要能夠成立,必須加上「在自己當中」這樣的場所作為條件,才能夠成立,所以變成是「自己在自己當中看見自己自身」。
二、田邊元的「種的論理」哲學
(一)種的論理
西田的「絕對無」一概念,支配著整個京都學派哲學的發展,學派成員對它有不同的詮釋和發揮。田邊元認為絕對無的場所太偏向於觀想式,他重視有限歷史現實中的實踐,而提出「絕對無的作用」(無即愛)來展開其「種的論理」。
田邊在其〈就教西田老師〉一文中說:「西田老師以自覺為意識的本質,並且認為所謂自覺即是自己在自己當中限定自己,而這種自覺的真義乃是在無自己以觀自己中完成的;失去自己反而才是真正得自己,返回到無而能觀的自己的本然,即是愛自己。老師所主張的這種自愛亦即自己的存在的教說,乃是從老師獨自的體驗中流瀉出來的,我對此無與倫比的高遠深邃的思想只能仰首讚嘆。然而哲學果真能將這種宗教性的自覺加以體系化嗎?」對田邊來說我們是無法直接掌握絕對無的,西田哲學這種基於宗教體驗所得,乃是哲學最後的終點而不是起點,無法作為說明現象世界的基礎。他認為個和類都不是我們能夠直接掌握的,所以主張作為兩者之媒介的種才具有實在性。
有關「種」的概念,乃是基於類(普遍)-種(特殊)-個(個別)的區分,如我們說「鈴木是日本人,日本人是人類」時,鈴木是「個」,人類是「類」,而日本人則是「種」,種是介於個別事物與普遍類別間的一個媒介。相對於西田認定唯有絕對無才是實在時,田邊則重視作為媒介的「種的基體」,承認它的實在性。田邊認為當我們說「鈴木是人」時,雖然表現出鈴木屬於人這個類別,但是這種限定是空泛的,無法具體凸顯鈴木這個人的本質,唯有重視人作為一個社會性的存在,說「鈴木是日本人」時,才能夠適切掌握到每一個體存在的本質。社會不單只是個人的集合,而是與個人屬於不同層次者。種即是在歷史當中具體形成的人的社會,它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與事物,而人就在種當中過生活。
在現實的歷史中,要建立起人類的、理想的國家(普遍),必然要透過民族國家(特殊)此一絕對的媒介才有可能,任何一個個體(個別)的生存必然在國家當中存續,個人要求自由,要求自我的利益,而國家則追求全體國民的自由與最大利益,所以國家是個人的否定對立面。種的論理認為個人唯有在依從於國家的統制,才能有最大的自由與利益,所以依從國家統制的自我犧牲即是個人的自我實現。「統制即自由」、「自我犧牲即自我實現」成為種的論理的基調,賦予國家統制的正當性以哲學理論的基礎。田邊自己也厭惡種的理論被說成國家主義、國民主義、非合理性的全體主義,但是他重視國家、強調個人犧牲的論點,卻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幫兇。
(二)懺悔道的哲學
二次世界大戰後,田邊元不得不承認他太過於高估愛國心驅使下的個體所具有的理性,也太低估作為種的基體的民族性所擁有的非合理性的能量。在幾近絕望的絕境中,他感受到自身的無力與不自由,在深切的懺悔中他發現到懺悔的深刻意義與力量,在1946年出版《懺悔道的哲學》,從親鸞所開創的淨土真宗的絕對他力念佛法門中,提出懺悔道的哲學,作為自己的生命與哲學死而復生的新契機。他說:
這不是以懺悔為對象的「懺悔的哲學」,也不是以既成的哲學方法來解釋懺悔的現象學乃至生命哲學,而是在那一切的哲學立場與方法都變得無力被掃蕩殆盡的廢墟中,再次復興起來的,它就是懺悔道。它是比笛卡爾的方法論的懷疑還更徹底的哲學性掃蕩方法,而且它是可以使我們死而復活的哲學,所以其自身不能被當作既成的哲學來處理。它是使我們進行死而復甦之轉換的行證。自身不懺悔而說懺悔,這不是懺悔道。唯有在他力行中自身行此信此者,才能夠證得、自覺到懺悔。我在此意義下,行證懺悔道,深化懺悔的自覺。
親鸞強調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完全必須依賴阿彌陀佛的本願力,在完全的他力念佛中,深信阿彌陀佛的悲願,即是深信自身是罪惡充滿、無有出離因緣的愚癡凡夫,所以懺悔過去累劫的業障,成為往生淨土行中重要的修行。田邊將此懺悔行轉換成一種立基於實踐的哲學立場,以作為否定原理的個人的原罪、國家的大罪惡為媒介,轉換、發展為懺悔的哲學。
田邊還特別將懺悔道譯作Meta-noetic,以強調它「超越理性直觀」的特色,他說:
懺悔道正含有超越理觀(譯者按:即理性直觀)之意。它就是一種超觀道,這是懺悔道哲學和一般的神秘主義乃至直觀哲學有所區別對立的重要特色。懺悔道不是基於自力的直觀,而是以他力轉換為媒介的行信證。本來是真宗特有概念,我認為對哲學全體有根本重要性的往相與還相兩概念,若容許姑且不論其內容的開展而做一種大意借用的話,相對於一般的神秘主義是一種往相的觀想,懺悔道則是一種還相的行道。
西田所走禪宗的自力聖道門,在直觀絕對無的純粹經驗中,建立起哲學與宗教的基礎,對田邊來說這是往最高目標的往相觀想,但是田邊認為在這過程中我們是無法真正直觀到絕對無,頂多只能觀照到我們內在的罪惡與愚痴,而絕對無也就變成了絕對的他力,變成了愛。「絕對無」在田邊的哲學中,不是積極挺立人的主體性,而毋寧是要完全空去自我,完全依於彌陀的本願,在他力中獲得救贖。回歸到懺悔行此一我們可以掌握的面向,即是還相行道的意義。田邊強調此還相行道乃是一個現實歷史中永恆的歷程。絕對無不能在自力的往相觀想中去尋找,絕對無在現實的歷史中必然是以相對的形式展現的,而懺悔道即是永遠在二元對立的動態展現中,來體證「絕對即相對」。在田邊的哲學中,不管是先前所提到個體會否定利己性的我執,追求社會秩序的普遍性,在人類理想實現的過程中,強調作為絕對媒介的國家的重要性;或者在懺悔道中說個體唯有透過懺悔,體驗絕對無即愛,在一個無限的懺悔行證中,才有真正解脫的可能性,也才有歷史的不斷發展。田邊先前在論述種的論理時所曾說過的一段話,可以說一直都是他思想的中心,他說:
實在必非是主體的否定對立者而且是主體的媒介基體不可。同時若失去此基體的媒介,主體的所謂實存,會墮入單單只是表現解釋的可能存在,或者不外萎縮成只是無內容的自己之決斷這種解釋性的行為主體。
我們看到的是田邊強調具體可以把握的現實歷史,而揚棄西田哲學中抽離了歷史、時間意義的直觀。二元對立下作為主體的否定對立者這樣的媒介基體,雖然說其具體所指有所變化,但其理路可以說完全相同。
三、《宗教是什麼》的問題與論述脈絡
如前所述,西谷啟治承續著西田由上而下、由宗教到哲學的絕對無哲學,以及田邊由下而上、由哲學到宗教的種的論理,企圖對這兩種理路做一番統合與超越,而他所藉以發展自己哲學思想的媒介,則是西方的虛無主義的問題,這是西田與田邊兩人所未正面面對的。整個西谷哲學的核心即是「虛無主義的超克」,藉由虛無主義以超克虛無主義。
西谷認為要對宗教做根源性、主體性的探求,最重要的是提問的方式,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追問宗教為了什麼而存在,從效益、功用的角度探求它的必要性,那麼我們的問題從一開始就閉塞了回答「宗教是什麼」的途徑,因為宗教是每一個人自身的事情,不能從外在來理解。我們在人生中遭遇挫折,開始對人生的意義產生迷惘,懷疑世界、神、歷史乃至自己與他人的存在時,我們自身就成為了一個虛無主義者,孤零零地面對自身的存在,感到那麼孤獨無所憑依。當虛無在自身內在現起,悄悄進入到我們的視域(horizon),吞蝕我們既有一切事物的存在與意義,讓我們無法再藏身於既成的現實幻像時,我們自身成為一個大的疑問號,開始追問「我們自身為了什麼而存在」,這就是禪宗所謂的「大疑現前」。
我們平常所生活的是所謂「意識之場」,亦即「有之場」,在這當中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存在和事物的存在──都被意識表象為一種「有」,當虛無從內在生起時,我們的立場也就轉換為「虛無之場」,但是這還不夠,必須要轉換到「空之場」,才能夠看到事物真正的面貌,透過虛無主義超越虛無主義。
(一)意識之場所的主客對立與實在的遮蔽
西谷將大疑現起,當作是實在可以在我們內在開顯的一個契機,但是他也強調這種大疑與笛卡爾哲學方法論上的懷疑是有不同的。面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此一看似顛簸不破的真理,西谷提示說應該注意那使得我們立基於其上藉以思考「我思」的那個場所是什麼,也就是說雖然因為主體不是來自客觀的事物,所以我思故我在看起來好像相當直接明白,但是我們從生命、物質或神這些場所,就無法導出「我思」的自明性。笛卡爾的懷疑論所推論出來的「自我」,乃是在自己意識的場所中,所被映現出來的自己意識而已,此自明性變成是一種欺瞞、虛偽。為了確保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真理性,有必要從比自己意識更根源性的場所來思考不可,也就是非突破意識之場不可。西谷將意識之場定義如下:
意識之場即是自己的存在與事物的存在產生關聯之場,要言之,意識之場即是唯存在之場,亦即是在存在之根柢的虛無被遮隱蔽之場。在此,自己雖然是主體但卻被以自己意識的方式表象為自己,也就是受到一種客觀化,被當作是一種「存在」來看待。
意識之場即是一種「主」與「客」產生離隔關係的場所,在這當中所建立起來的「自己」乃是一種「自己中心式的存在方式」,「自己」是「主」而其他的事物都只是「從」。不只由此掌握到的「主體」已經受到客觀化,不能如實地見到主體的本來面貌,在意識之場中所見到的事物,也不是事物存在於事物自身的如實樣態,只是事物對我們所顯現的一種受到限定的相貌而已。意識之場始終都是以「存在」來表象自己的存在與事物的存在,也就是說主與客都是一種的「有」,虛無永遠被遮蔽。西谷在另外的場合也用感性之場與理性之場,這都是屬於意識之場的範圍。
(二)虛無之場所的否定作用與實在的現起
對西谷來說,哲學上唯物論與觀念論的主張,同樣都是在意識之場中,在不同的方向上將物質性與觀念表象為超越主客對立者,在透過主客對立之場顯現為「客體」的事物者來思考這一點是相同,而要擺脫唯物論與觀念的糾葛,必定要進到更根源性的虛無之場,在此一般在感性或理性之場所中被認為是存在、實在者,全部都化為在其根柢擁有虛無者,顯現為原本就無根者。虛無之場的特徵就是沒有主客對立,事物的存在與自己的存在都不是被認識的對象,而且不是可以概念性地被把捉、言詮者,所以真正的大疑現起,其中絕不能有能疑和所疑的二元對立,笛卡爾和休姆的懷疑都還是立基於意識之場,沒有能將主客一起無化。
由於在虛無之場中,事物變得不再是對象,所以能夠脫却在意識之場中的表象性格,以一種更接近於實在的方式現起。由於虛無被插入到事物的根柢,事物的存在與自己的存在,在此根柢都化為完全無法把捉者、不知道它是「什麼」的東西,主體與客體化為「無」,看似一種非實在化,但相反地,反而讓原來在意識之場中被遮蔽的虛無,進到我們的自覺當中,海德格所謂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只重視「存在者的存在」,反而形成「對存在的遺忘」,在虛無的自覺中可說有了新的改變。
但是虛無主義的立場還是不免帶有「有」的色彩。也就是說虛無雖然不是「有」,是「有」的無化,它雖然不是意識的對象,但還殘留有以表象性的方式將虛無看作虛無的「事物」之處。換言之,雖然虛無主義已經帶有「空」的內涵,但它還不是徹底的「空」的立場,西谷對沙特、海德格的批評,可以說都與此有關。西谷因此認為虛無之場本質上帶有過渡的性格,是應該「急走過」的地方,他說:
虛無是對一切存在的絕對否定,因此與存在是相對的。虛無的本質在於單純否定的(消極的)否定性(単に否定的な〔消極的な〕否定性,*purely negative[antipodal] negativity)。此立場乃是含有既不停留於存在也不能離開存在的自己矛盾,被其自身撕裂的立場,在這當中,也有其過渡的本質。雖然說是虛無的立場,實際上並不是可以在真正的意義下成立的場所。只不過是應該「急走過」的地方。就這種本質性的過渡性、否定的否定性來說,它始終都是實在的,都是現實的,但其立場本身本質上是無實性的。虛無的立場本身本質上是虛無的。此立場唯有作為這樣的事物,才是虛無的立場。
虛無的立場是一種單純的否定的否定性,否定在意識之場中所掌握到的被客觀化的主體與客體,讓在自己中心的存在方式下的主體,以及只以某種被限定的方式顯現的客體,回到其更根源性的存在方式,更不受限定性地生起,也就是實在的現起。但是在虛無的場所中,所有的事物不再具有其「物質性」、「觀念性」與「實體性」等,呈現出來的是散亂與解體之相,在這當中沒有一般所謂的認識與意義,所以沒有對象及其認識的問題,問題在於實在與以如此方式呈現的事物,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體認與體得。有關實在及其體認,絕不能再從虛無之場回到理性認識的意識之場,再用主客對立的方式來掌握,而是唯有從虛無之場進一步往前,到達事物與自己原本真實地現成的那個場,才成為可能的,這能夠使事物與自己真實現起的場所,就是「空」之場。
(三)空之場所與絕對的肯定
西谷曾經譬喻說,如果意識之場和虛無之場是同一張紙面上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那麼空之場即是整個紙面的180度翻轉,甚至於是360度的翻轉,是和前兩個場表裡一體,而能包含它們的,他說:
意識和虛無之場所都不能離開空之場所而成立。在一切事物被對象化為外在的實在的相之前,而且在它被無化的更本來的相之前,它已經在空當中,在真正地本來性且根源性的相之中。在空當中,事物真正地在事物自身當中。而且,同時在以表象為基礎的對象意識之前,以及在虛無之上的存在性的覺知之前,在作為絕對的此岸的空當中,有真正本來性且根源性的智成立。這就是在可以稱為萬物來證自己、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皆自己本分的場所當中所成立的知,勉強說它是「無知之知」。在這當中,自己是真正在自己自身當中。草木徹於其自身之底是草木自身,瓦石徹頭徹尾是瓦石之時,與此自己同一地,自己徹其底是自己自身。這是無知之知,不外是空之場所。
必須有空之場,一切的事物才能夠成立,西谷將大乘佛教中觀學派龍樹所謂的「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具體展現在西田的場所論中。在意識之場中事物被以主客對立的方式表象為對象前,或者在虛無之場中事物被無化前,它們就已經存在於空之場中,以一種不受意識立場所限定,甚至於不受虛無立場無化的根源性存在方式存在著。在它們如此現成的當下,即有我們如實的會得,這是大乘佛教所謂的空性、真如。空性、真如不是在我們親證之後才如此存在的,它們本來就是一切法的本性。在空之場中,原來在虛無之場中事物所呈現的散亂與解體之相,在此又收攝為一,以一種作為事物自體存在的方式,重新為我們所知,然而此時所謂的知已經不是在意識之場中的理性認知,所以說它是一種無知之知,用大乘唯識學派的話來說,即是一種無分別智,西谷說它是「無分別的分別」。
說到空之場和虛無之場有何不同,西谷啟治認為空之場是「色即是空」而且「空即是色」的立場,或者說是不只「自己是空」而且「空是自己」的立場,在虛無的立場中被否定的事物再次受到肯定,不再是往彼岸超越而是往比此岸還更是此岸的地方超越,三百六十度的翻轉、超越,其實就是零度,這種立場就是「退後一步,照顧腳下」的立場。西谷說:
有作為本來與空為一者而現起,或者說一切的有的事物在空之場所中,在其各自的自體性的存在方式中現成,即是在虛無中現起散亂與解體之相的一切事物又再回復到「有」。一切有的事物又再回歸到那將自身收攝到自身中的收攝力(*power of concentration for gathering itself into itself),回歸到存在的可能性。作為其存在可能性的展示,回復到個別事物所擁有的固有能力、個別自身的「德」。松回復到松之德,竹回復到竹之德,人回復到人之德。在此意義下,相對於虛無是「無化」(Nichtung, *nullification)之場所,空也可說是「有化」(Ichtung, *be-ification)之場所。以尼采的方式來說,此有化之場是可對一切事物說「是」的大肯定之場(*this field of be-ification is the field of the Great Affirmation, where we can say Yes to all things)。
有唯有與空為一才為有,在空的場所中所現起的即是此與空為一的有,這是「看山不是山」之後「看山又是山」時所見的有,所以空的立場是否定即肯定的大肯定,是「有化」的場所。而這種作為絕對的此岸的空,當然不是被表象為「空」這樣的「有」的事物,這種真空不外是作為我們各自的絕對自性而被自覺者,在這當中有一切事物的如實相現起,西谷更說,所謂的空「即是我們當中真自性的自覺或者作為真自覺性的自性,以及在其如實相當中的諸事物自體,同時成立」,西谷也強調說這種自覺不是自己意識,而自性也不是自我或自我的主體性,而所謂事物的實在的如實相,也不是實在論或唯物論意義下的實在。
上述引文中說到,在空之場中「一切有的事物又再回歸到那將自身收攝到自身中的收攝力,回歸到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萬法紛然多端,一切的事物回歸到那使自身回歸自身的收攝力時,一切事物就各自為主,成為中心,以建立其絕對的自主性,那麼諸法不就各自為主,變成完全的混亂了嗎?西谷用「回互相入」來回答這個問題,這是佛教的基本立場「緣起」以及華嚴哲學的「相即相入」在西谷哲學當中的展現。有關「回互相入」,西谷定義如下:
一切事物在其「有」中,互相進入到他者的本,成為不是其自身;而且作為這樣的事物(亦即在空之場中)又始終是其自身,這種回互的關係本身,不外就是使一切事物集中且結合為一的「力」,不外就是使世界成為世界的「力」。空之場即是力之場。世界的任何事物中,都有世界的「力」作為此事物自身的「力」而現成。……世界之「力」或「自然」在松當中現成為松之德,在竹當中現成為竹之德。不管是如何微小的事物,只要它是有的事物,在它的有當中,就有結合萬有的回互相入(*circuminsessional interpenetration)之網現起。或者可以說,在「有」中,世界「成為世界」(世界が「世界して」いる,*world “worlds”)。這樣的存在方式,就是此事物的自體性的存在方式,非對象性的、作為「中」的存在方式,即是此「事物」的自體。
站在佛教緣起的立場,沒有任何一個事物,它的成立和其他的事物沒有任何的關係,不論多麼微小的事物,它的存在在空之場當中都具有一種收攝力,收攝到其自身;同時也將其力量發散到其他的事物,成為讓世界能夠成立的力量。空之場就是一切事物回互地相即相入的力之場,在這當中事物是「有」的同時,也是「空」,是與空為一的有,不再像在意識之場所顯現的某種被限定的相貌而已,所以我們不再只是看到光源所發散出來的光線,只看到它的周圍,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光源,看到那事物的根源性存在方式的「中」。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切事物都是主的同時,也是從;是中心的同時,也不是中心,而是以它者為中心。唯有透過否定所達到的主體性才是真正的主體性。將空的立場放到實踐上,就是不以自己為目的,而要以他人為目的,用大乘菩薩行的話來說,就是要在利他當中完成自利;用基督宗教的話來說,就是要愛鄰人如愛自己。而且在這種宗教的慈悲與愛當中,已經超越了道德中所強調的「人格性」,宗教的愛與慈悲是絕對的自己否定,而不是像康德的自律道德還是停留於對人格性的強調,對西谷來說,還有人格性的立場,就是還不能進到空之場,不能夠完全地自己否定以達到以他人為中心、以他人為目的的境界。西谷由此更說,自由不應單單只是意志的自由,因為它只是被投射到意識之場中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乃是「在空之場中,作為無依處的絕對自主性」;平等也不應單單只是人權與財產權的平等,因為它還是建立在自己中心的存在方式下的權力與欲求主體,真正的平等乃是「自他彼此同時站在互為主從的位置,在相互間絕對不平等的交換中所成立的平等,也就是在愛當中的平等。」
四、結論
在西谷啟治的空的哲學中,一切事物在其自體性的存在方式下,與其他的一切事物是互為主從、回互相入的關係,它不是單純只是一種「有」的存在,而是與空為一的有。每一個事物自體都可以隨處為主,成為世界的中心,但也同時無化它自身,進入到其他事物之本,成為支撐其他事物的力量。所以說空的場所即是隨處為主、到處是中心的立場。在這當中,我們看到西田哲學場所論理的影響,但是「空」比起「絕對無」,更具有此岸的性格,不是我們一時無法直觀的超越次元,而是只要我們「退後一步,照顧腳下」就能夠看到的「水清徹地兮,魚行似魚;空闊透天,鳥飛如鳥」的如實相。而當我們時時以他人為中心,以他人為目的,即是時時自己否定,以他人為否定的媒介,在實踐的過程當中,能有一個具體的、世俗的、水平的道路,這又可避免田邊對西田的批評。
以上我們從西田幾多郎的純粹直觀、絕對無的場所,以及田邊元的種的論理、懺悔道的哲學,來看內在於京都學派的發展,《宗教是什麼》的成立經過了什麼樣的脈絡,但是無法進一步探討西谷對尼采、沙特與海德格思想的繼承、批評與發展。簡單來說,由於西谷重視來自傳統的禪的智慧,讓他的思想在超越虛無主義的努力上,和西方的哲學家有明顯的不同,而這只能留待日後再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