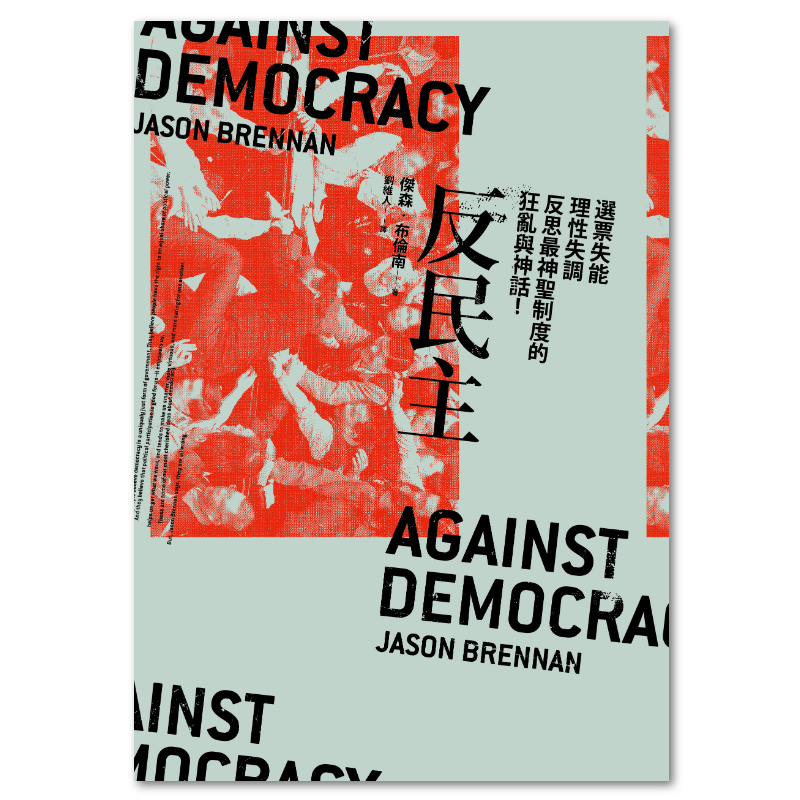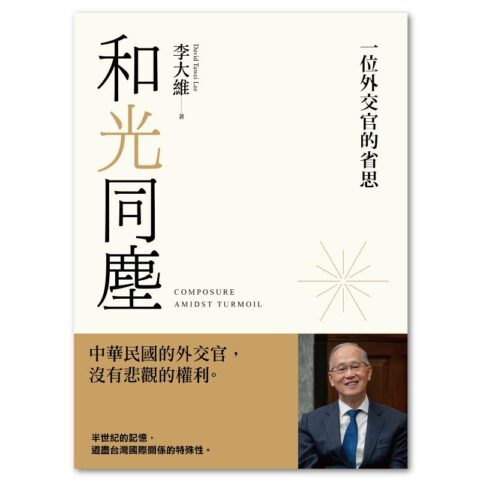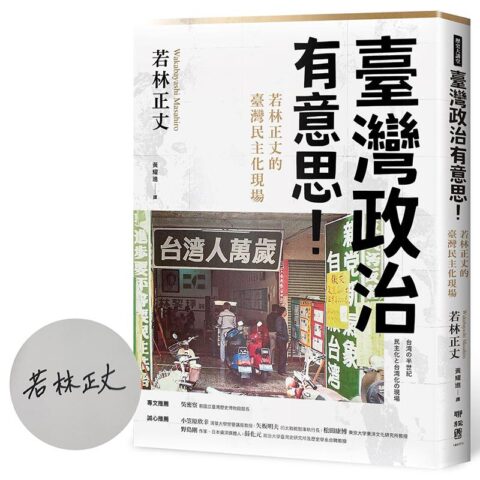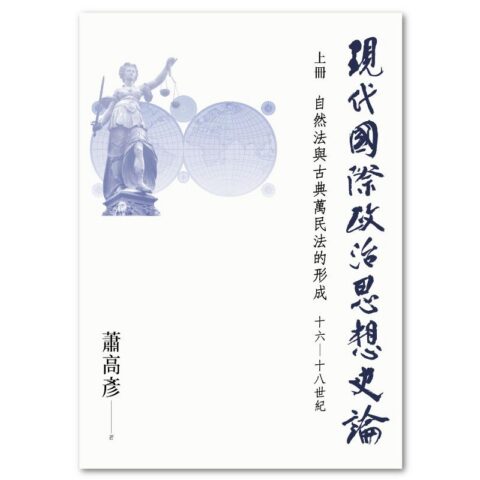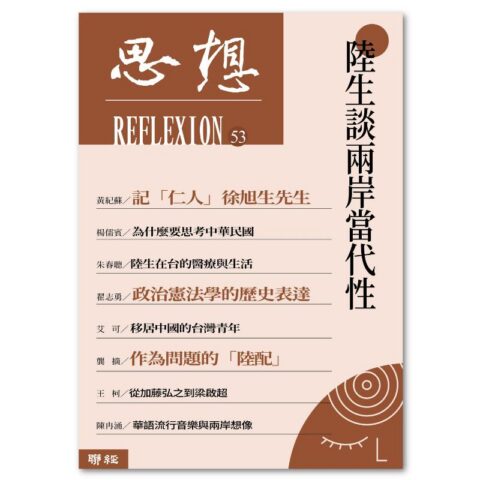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原書名:Against Democracy
出版日期:2018-08-07
作者:傑森‧布倫南
譯者:劉維人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00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51519
系列:Big Ideas
已售完
★本世紀最危險的書,看了會崩潰,不看會後悔
★政治大學教授葉浩老師萬字導讀!
★撼動現代社會的根基、挑戰你我的信仰
★世上最宜居之處大多是民主的。為維繫民主,首先要反對它!
在這價值混亂、制度失衡,民主神話即將破滅的年代
人人都應該要有投下神聖一票的權利,錯了嗎?
民主其實很無能?
民主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政治形式。
我們相信,人人有同等的政治參與權,有權利參與選舉、投下神聖的一票。掌握參與政治的權利則讓每個人擁有權力,決定什麼法案是我們所需,什麼人物非我們所用,而這一再抉擇的過程,會讓公民更成熟、社會更建全,但本書《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作者傑森‧布倫南卻說,我們都錯了!
布倫南指出,就現行實施民主政治的結果來看,這個制度顯然不夠好,而且人人有權參與、決定政治的結果,是社會被無知與非理性的選民牽著走,導致我們往往無法得到對社會來說最好的政治結果。民主,其實是效率低下的制度。
‧你是無知的「哈比人」、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流氓」,還是完美選民「瓦肯人」?
布倫南將選民依資訊掌握度的高低分為三類:
哈比人──無知、資訊掌握量低,容易被煽動並選擇支持對自己並無好處的一方。
*例如:投票給政治承諾會發放高額補助,不知道此舉會拖垮縣預算,造成後續連串問題之人。
政治流氓──資訊掌握量高於哈比人,但支持政策與候選人的根據為個人認同的道理,會罔顧事實與真相,支持與自己意識形態相合的一方。
*例如:舉著認同的道理大旗,四處遊說、參與社運、熱烈表達支持看法,往往看似公正、有憑有據地長篇大論,但選擇忽略不利於個人認同之道理的證據。
瓦肯人──資訊掌握量高,深具社會科學知識,對政策的看法不受個人看法影響,而以客觀的方式選擇結果最良好的一方。
*例如:選舉時仔細衡量各候選人政策,投票時不分黨派、不受候選人個人魅力影響、不計任何鄉里人情壓力,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審慎而公正。
布倫南認為,瓦肯人為最理想、最不受情緒、意識認同影響的政治參與者,但現實的情況卻是無知的哈比人與偏頗的政治流氓當道,整體政治走向被民粹引向歪路。實際的社會科學研究更表明,政治參與以及審議制度會讓公民更加劣化、更無理性、偏見更加嚴重。
‧反對民主,才有修正體制的可能?
面對發展至此陷入僵局的民主制度,布倫南提出一個遭可能萬人撻伐的解決方法:知識菁英制。他認為此時此刻,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新政治體制的可能,不能再毫無限制地讓人們自由參與政治。由知識淵博的理性菁英運行政府、做決策,才是現在我們應該認真考量、實驗是否可行的方法。
民主的缺陷並不足以構成支持權威、走回頭路的理由,為了追求更建全的社會,我們有義務面對迫切待解的民主問題。
布倫南指出了當前社會最重要的難題,來自民主政治的失調。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我們該何去何從?民主這看似現代社會最珍貴的價值,難道真的是過度吹噓的神話嗎?
※ 國內外熱烈討論閱讀
傑森‧布倫南是個奇蹟:他在講道德之前仔細研究了現實情況。在《反民主》一書中,他優雅地導出結論,認為民主參與讓人類忘卻常識與公共行為準則。投票一事並未使我們變高尚;它檢驗的是最佳的美德,並帶出其它最糟的面相。
──布萊恩‧卡普蘭,《理性選民的神話》作者
政治哲學的當中的巨大誘惑在於將政治神聖化,而我們迫切需要能教我們倖免於此的方法。在這本寶貴且強而有力的書中,作者挑戰待在舒適圈中的人們和一般人熟悉的政治生活神話,尤其是關於民主統治。相信大多數讀者會讀到許多自己不認同的觀點──我也是──但同時也會發現布倫南的論點難以抗拒,無法確實地反駁。
──雅各‧T‧列維(Jacob T. Levy),邁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授
布倫南做了診斷,也開了處方,並要求我們立即切除普選制度的毒瘤。不過,畢竟茲事體大,是否該貿然以身試藥,也許還得再考慮一下……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本書同時適合自由民主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來讀。對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來說,本書的許多論點都是很好的練習題,我們可以去思考民主政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各種民主理論背後的假設和推論過程是否都應該再思量,以及更重要的,去思考該怎麼樣修正現狀下的問題。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鳴人堂專欄作家
人人都該有投票權,過去黑人和女人不能投票,那是因為過去我們錯了。在現代,全民民主理所當然到你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反民主》裡,哲學家布倫南(Jason Brennan)主張這種看法才是錯的,而且它會讓民主更糟。你有理由看看布倫南的說法,因為如果他是對的,我們麻煩就大了。
──朱家安,「哲學哲學雞蛋糕」部落格格主、自由寫作者
作者:傑森‧布倫南
專業領域為政治、哲學與經濟。著述豐富,目前已出版十本書,包括《投票的倫理》(The Ethics of Voting)、《為什麼不是資本主義?》(Why Not Capitalism?)和《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無限制的市場、義務投票和自由主義的簡短歷史》(Market without Limits, Compulsory Voting, and a Brief History of Liberty)一書的共同作者。
譯者:劉維人
自由譯者,不專業的冷知識宅宅。喜歡英美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桌遊、酒。譯有《超級英雄是這樣煉成的》、《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被誤讀的哲學家》、《反民主》、《品味這件事》等。
導論 布倫南對民主制度的診斷與處方,以及欠我們的一份病理報告/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台灣版序
2017年版序
前言暨誌謝
第一章 哈比人與政治流氓
第二章 國家主義者的無知、不理性與資訊錯誤
第三章 政治參與讓人墮落
第四章 政治不會讓你我更有力量
第五章 政治非詩
第六章 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
第七章 民主有足夠的能力嗎?
第八章 知者治之
第九章 彼此為敵
布倫南對民主制度的診斷與處方,以及欠我們的一份病理報告/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讀者手上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幾本書的總結,雖然出版於二○一六年,但稍早於英國脫歐公投,是時,川普也尚未當選美國總統。也正因如此,布倫南隨後聲名大噪並被支持者奉為先知,並成為媒體競相追逐的訪問對象,聲勢直逼受邀去日本職棒開球的哈佛公知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作為總結布倫南先前想法的本書,提出了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度的主張。其核心論旨是:民主制度的良序運作,需要每一位投票者都具備關於選舉爭議的足夠的知識,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反之,真正影響人民生活(例如:稅制、工時與基本工資、醫療保險給付比率)乃至國家前途的重大議題(像是移民、外交和能源政策),必須交付到知識菁英的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才安全。
畢竟,民主政治不該是讓這些欠缺知識,甚至連自己的無知都意識不到的愚民來實習的情境;據此,鑲嵌於民主制度的「平等」價值與「票票等值」原則,不但違背了人的天生智力與後天知識皆存在巨大差異的根本事實,強行落實的結果只會讓原本可以替社會做出最好、最正確決定的少數人,喪失了投票的意願,淪為知識菁英與無知庶民的雙輸局面。
欲防範這樣的政治悲劇,唯有提高投票資格的門檻才行,而具體的方式就是讓所有人進行相關的測驗,過濾掉那些缺乏社會與科學知識的人,如此一來既能確保選舉結果的品質,亦可杜絕劣幣逐良幣的蔓延!
如此看似簡單的主張,其實包含了相當多的預設與判斷,值得我們駐足推敲一番。不過,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述外另一個反民主並倡議知識菁英制的哲學家。這位哲人當然是古希臘大哲柏拉圖。作為知識菁英制的鼻祖,他的《理想國》是批判民主的經典之作,當中的許多概念至今仍深遠地影響西方的政治思考,而最重要的莫過於「治國猶如海上行船」的比喻:唯有專業技術才能勝任,具備任何其他特質(例如:取悅大部分的人、受到眾人愛戴)都是不適切的考量,其道理不過像人病了就該找醫生那樣簡單。
事實上,柏拉圖還真的把安定的國家類比為健康的個人。就個人而言,根據他的理解,人的心靈或說靈魂乃底下三要素所組成:理智、激情,以及慾望。一個性格穩定的人,必然由三者其一所主導,也因此有真正適合他的工作。一個社會上,慾望主導的人必然最多,而適合他們的工作就是從事生產,並藉此賺錢,畢竟,他們圖的不過是享樂。激情主導的人則應該擔任保家衛國的工作,且由國家供養,但不支薪,因為榮耀才是他的唯一追求,錢財只可能讓他腐化。作為社會的少數族群,孩子共養、女人共享的共產制度適合他們。至於那些追求真理而衣帶漸寬卻始終不悔的少數中之少數,才適合擔任治國的工作。一來,唯有他們懂得真理、何謂正義,以及值得打造的理想國度;二來,如此理解的他們,不僅視錢財如糞土、榮耀如浮雲,更理解政治權力落入烏合之眾手上的危險,大則有亡國之虞而覆巢之下無完卵,小則哲人本身的性命可能不保,正如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例子告訴我們的。
是故,唯有讓握有真知灼見的哲學家掌權,成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視榮耀如生命的人則擔任衛國士,而其他眾人去拼命工作、生產以換取金錢,才是對所有人都好的分工合作。人人獲取他想得以及應得的事物,當然也是個理想且正義的國度。反之,無知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則是集各種弊病與不義於一身的政治體制。
實施民主的雅典城邦,讓人民按照正當法律程序將蘇格拉底判處死刑,是鐵錚錚的事實。這是民主留給柏拉圖的創傷,也是政治哲學的起點。逃離納粹政權來到美國的猶太哲人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甚至據此認為,政治哲學的首要大哉問乃是:懂哲學的人與不懂哲學的人,如何共存於一個社會?更抽象地說,以批判傳統、質疑已知為職志的哲學,如何存在政治社群當中?
民主制度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不是嗎?
台灣版序(節錄)
中華民國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舉行了第一次完全自由的立委選舉。詭異的是,雖然德國統一及前蘇聯各國自由與民主化的電視新聞,至今依然在我腦中栩栩如生,我卻記不得台灣這件事情在美國曾引起多少新聞媒體報導。很快地搜尋一下谷歌之後,我發現自己的記憶似乎沒錯:我所能找到當時記載每個主要歐洲國家選舉的英語文章數量,遠比記載台灣立院選舉的更多。
為什麼呢?我猜是因為西方世界雖然有著許多好聽的說詞,但依然把民主制度視為西方的東西吧。
中華民國在過去二十年內,已經發展成一個正常、穩定的民主國家。政治權力在對立的政黨之間和平轉移,與我們在美國看到的狀況大體相同。
當然,台灣目前的狀況依然異於常態。國民黨是一個國家主義的保守黨,最適合描述民進黨的詞彙則是市場自由主義(market liberal)或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政黨,而那些能夠被歐洲與北美認定為「左派」的政黨,在台灣沒有任何重要力量。此外,我們可以說台灣和新加坡很像,它的存在還一直處於真實的威脅中。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一直在重申自己的國家主義與威權主義,因此儘管在二○一○年經歷了改革並簽署了雙邊協定,我們依然擔心它會不會在某一天吞併台灣。
《經濟學人》每年都會發布一份廣受引用的「民主指數」報告(Democracy Index),根據每個國家實現某些民主理念的程度高低,給予零分至十分的評分。台灣在二○一七年獲得七‧七三分,在報告的標準中屬於「有缺陷的民主國家」(flawed democracy)。順帶一提,美國、南韓、日本、葡萄牙、比利時也被《經濟學人》評為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得到和台灣相當接近的分數。因此台灣的得分在近一百七十個國家中,排於第三十三名。
雖然是「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台灣在選舉流程與選舉制度上幾乎得了滿分,這表示《經濟學人》的研究人員認為該國的基本民主制度是真正自由公平的。此外,台灣在保護公民自由以及政府運作上的得分也極佳(沒錯,表現比美國好很多,雖然這大概稱不上什麼成就)。在這些評分項目中,台灣被打低分的則是政治參與度低,以及政治文化被認為有缺陷。
不過這兩個項目比較有爭議。一個優秀民主制度的投票率一定要很高嗎?此外,為什麼我們和《經濟學人》不能認為,人民對領導者與體制抱有一定程度懷疑但並非不信任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優秀的政治文化呢?
我在前一本書《投票倫理學》(The Ethics of Vo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提到,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尤其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科學家、哲學家、政客,經常抱持一種過於狹隘的公民觀。在這些人眼中,每位優秀的公民都既是素人政治科學家,又是兼職的社會運動者(activist)。換句話說,我們這些政治科學家與哲學家很容易以為自己是優秀公民的榜樣;其他普通人最好變得更像我們一點。
我的看法與此相反。我主張一般的汽車修理師傅因修車而對國家做出的貢獻,遠比一般選民因投票的貢獻,或一般的社運人士因為從事罷工糾察(picketing)或發起抵制而對國家做出的貢獻高出許多。由於《反民主》這本書,如今我被認為是一個菁英主義者(elitist)。但儘管我對人民政治能力的看法屬於菁英主義,我對公民德行(civic virtue)的看法卻是民粹主義的(populist)。在我看來,大部分公民彼此幫助的方式並非透過政治參與,而是透過日常生活的活動。
每年我都會開一堂概論課程,討論政治、經濟、哲學之間的關係。我們會花大量時間探究,為什麼某些國家富有,某些國家卻貧窮?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一般民眾,經常假設富裕國家一定佔有地利、擁有資源,或從窮人那掠奪了財富。
但相反地,主流的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中大多數人卻認為,優秀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才是確保經濟長久發展的主因。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乃是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或更正式地說,乃是形塑人類互動方式的人為限制條件」。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在解釋經濟成長以及國家貧富原因時,「制度的優劣勝過其他所有因子」。
哪些制度會促進經濟成長呢?由「穩定而包容的政府」實施「法治」,保護「健全的私有財產制度」與「開放市場」的國家,比欠缺這些制度的國家,更可能出現可持續的重要經濟發展。
台灣並非十全十美,但已經是一個令人驚嘆的範例(是我在課堂上引用的範例之一),顯示制度的改善會對各種事情產生多大的正面影響。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廣受引用的歷史資料,台灣在一九五○年的人均GDP低於一九九一年的一千美元(經濟學家討論GDP時,經常以一九九一年的美元作為標準,藉此避免通膨的影響),這表示台灣一九五○年的生活水準還不到一七五○年的二倍。但到了二○○八年,台灣的人均GDP與生活水準卻至少增加了二十倍。台灣在極短的時間內,從「貧窮」國家翻身為真正的富有國家,而且收入分布相對平均,超越了加拿大與大部份歐洲國家的成就。
這是個奇蹟。美國左派民眾不斷表示我們需要消滅全世界的貧窮,但許多人卻似乎對台灣、南韓、日本、新加坡的故事沒有興趣—這些故事都告訴我們,消滅貧窮的並非救濟,而是良好的制度與貿易(不過這句話並不表示我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的一切所作所為)。
如果台灣變得更民主,會不會因此獲益?我不知道。如果台灣開始採用某種知識菁英政治,例如第八章提到的「模擬神喻使政府」,會不會因此獲益?也許有可能。但至少就我看來,台灣目前並沒有歐洲或美國出現的那些政治倦怠、政府失能、管理不當的問題。
我認為造成差異的原因,和主流政黨支持怎樣的政策有關。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對市場經濟與經濟自由主義抱持友好態度,沒有人想要殺雞取卵。而且至少到目前為止,台灣民眾也記得過去的歷史,明白不能把當下的富足視為理所當然。也許那些好幾代之前就富起來的古老民主國家之所以出現問題,就是因為再也沒有人記得貧窮的樣子,沒有人記得擺脫貧困需要什麼。如果上述這個假說沒錯,那麼我對於台灣未來三十年的政治都相當樂觀。但隨著民主發展的時間更長久,當不再有祖父母一輩能夠記得那段苦日子時,中華民國可能也會面對如今美國,英國、或其他國面對的威脅。
2017年版序(節錄)
二○一六年是民主灰暗的一年,不過對民主評論家來說卻收穫頗豐。下列即是見證:
‧我寫了約十九篇指出民主缺陷的專欄與雜誌邀稿。人們對這議題的關注和二○一四或二○一二年我書寫這主題時截然不同。
‧我也在廣播節目上討論我對一些選民不該去投票的論點。聽眾Call-in說:「你說的我都懂!我們能怎麼辦?」一年前,我在同一個節目討論同一個主題,當時Call-in聽眾質問的是:「你竟敢這樣說!」
‧十月至十二月,我每天都獲數個媒體的詢問邀約。
‧《反民主》一書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愛爾蘭、法國、瑞典、挪威、瑞士、荷蘭等地享獲媒體關注。至今已有六國語言的翻譯版本。
上述的成就並非吹牛(但不得不承認也許真有些吹牛的成分)。不如說,這是在陳述事實。自二○○九年起,我持續書寫文章與書籍,挑戰我們對政治參與這事最神聖的、不可侵的想法。然而到了二○一六年,人們對這主題有了不尋常的高度關注傾向。他們也許不認同,但已經更願意思考這個問題了。
英國脫歐公投中,脫歐的票數以些微差距險勝。公投前一個月,巿調機構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發現英國民眾系統性地錯誤理解公投相關的事實。舉例來說,投脫歐的選民相信來自歐洲的移民占英國總人口數的二十%,而投留歐的民眾則認為有十%。雖然他們都錯了,但投脫歐者錯得更離譜:真正歐盟移民在英國的人口數約為總人口數的五%。大體上而言,贊成脫歐與留歐者都高估了英國政府支付他國兒童福利津貼,高估幅度從四十到一百%。兩方選民也都嚴重低估來自歐盟的外資金額,並高估了中國挹注的資金量。當然,這並不代表留歐是正確的選擇。不過在這件事上,一個人對相關事實認知的錯誤越多,的確就越有可能投脫歐一票。
美國也跳了支愚蠢之舞。我懷疑川普會不會像我那些被焦慮支配的同事想的那樣,成為一場災難。不過最初支持川普的支持力量,的確是一群資訊掌握度低得不尋常的選民。他之所以能夠獲得提名,是因為共和黨分裂了資訊掌握度高的投票者。一旦川普成了推定的候選人,我在本書第二和第三章描述的黨派的黨性便會接管一切;讓許多原本「封殺川普」的共和黨員轉而投他一票。
[……]
有些書評指出,《反民主》這本書裡沒有論及川普或脫歐公投。這是因為當我完成這本書時,雖然川普的支持度正在攀升,但尚未成為提名候選人,而英國脫歐一事也尚未成為公投議題。我並未預料到這兩件事的後續發展。
雖然川普與英國脫歐公投闡明了我的擔憂,不過《反民主》一書並非對此兩件事的回應。我對民主的評析是基於長期、系統性的實證研究。約六十五年前,我們就已經開始計算選民對資訊的掌握度如何,當時結果讓人失望,現在也是如此。自有研究以來,位於統計平均數、眾數、中位數的選民,對於基本政治資訊都相當無知或錯誤;在較為深入的社會科學知識上則更為欠缺。他們在無知與資訊錯誤之下,支持了一些如果能夠更正確周詳地掌握資訊,便不會去支持的候選人。我們因此得到次好的,甚至有時是差勁的政治結果。正如我在本書第四與第五章的論述所言,民主和平等投票權沒有內在價值,因此我們應該保持開放的態度,實驗其他形態的政治形式。只有在實證顯示「一人一票」制度造成的實質良善政治結果,比其他制度更多時,它才是行使正義的不二法門。
我批評民主,同時景仰之。關於「民主與自由」的議題,我在《牛津讀本之自由》(Oxford Handbook of Freedom)中論證指出,民主制度事實上與許多重要結果正相關,而且兩者之間似乎不僅有相關性,還有因果關係。民主比非民主制度來得更能保護經濟與公民自由。現在,這世界上最宜居之地大多是民主的。不過,有鑑於我們知道民主有系統性的破綻,就該持開放的態度去調查並實驗其他可能性。
在《反民主》一書中,我認為我們應該實驗一個多數人最為反感的制度: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知識菁英制保留大部分共和代議民主制的特徵;政治權力會分給許多人,而非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會有權力分立,也會有權力制衡。不過,在法律上,知識菁英政治並不會將基本政治權力平分給每個人;而是透過某些方式,讓能力更佳或知識更淵博的公民,比其他人的政治權力更多一點。
[……]
民主是工具,僅此而已。如果我們找到更好的工具,就該自由地使用。事實上我在第六章指出,我們有責任使用更好的工具。正義的事情終究是正義的。糟糕決策不會因為擁有法律地位,就變得比較不糟糕。政治決策的風險都很高。怎麼有人敢在能力不足的狀態下做出決定呢?
導論(節錄)
我曾想把這本書取名為《反對政治參與》(Against Politics),不過這個標題會讓人誤解(在過去其他著作影響下,更會加深這種誤解)。本書中的論證有三點:首先,政治參與通常不會增進民眾的心智或德行,反而會讓我們墮落;其次,政治參與和政治自由,幾乎沒有什麼工具性價值或內在價值;最後,如果將民主制改為某種形式的知識菁英制,可能會讓政治的結果變得更為正義。
不過,我並不打算論證政府的規模—也就是政府監督或監管的事務範圍—是否應縮小。某些當代作者,例如:法學家伊爾亞‧索明,認為讓政治無知的傷害留在限制範圍內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政府的權力縮得更小。索明可能是對的(或錯的),不過我對此問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看法。
我認為大部分民眾都不擅長政治,而且政治對大部分人來說都不好;但我並未因此聲稱政府的管轄範圍應該縮小(或擴大)。我要說的是,如果引述的事實無誤,我們就不應該讓那麼多人有權參與政治。如果你相信社會民主主義,我建議你改成社會知識菁英主義。如果相信的是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改成知識菁英制的社會主義。如果你是保守的共和黨員,變成保守的知識菁英論者應該不錯。如果你是自由意志論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或者左派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我會說雖然無政府主義更好,不過知識菁英制至少勝過目前的民主。
哲學家很愛區分「理想」(ideal)與「非理想」(nonideal)的政治理論。大體來說,「理想」的理論想知道每個人都是完人,道德德行與正義理念都完美無瑕時,怎樣的政治體制最好。「非理想」的理論,則想知道真實世界中—尤其當人民的德行會因政治體制而變動時—怎樣的體制最佳。本書所說的就是非理想的理論。我不想告訴你一個完全正義的社會是什麼模樣,而是想討論在一個倫理缺陷與邪惡行徑相當普遍、民眾正義感相當薄弱的真實社會中,我們應該以何種方式來思考政治參與。
各章概述
第二章〈國家主義者的無知、不理性與資訊錯誤〉,整理了投票者行為的相關研究。大部分民主社會裡的公民與投票者,都是缺乏知識、不理性、擁有錯誤資訊的國家主義者。我會說明民眾政治知識的中位數、平均數、眾數低到何等地步;投票民眾在重要的經濟或政治科學基本問題上會犯下怎樣的系統性錯誤;投票者多麼容易陷入偏見與不理性的狀態。我會列出證據,證明大部分的公民都是哈比人,剩下的幾乎都是政治流氓。
第三章〈政治參與讓人墮落〉將解釋政治參與為何令人變壞,而非變好。許多民主主義者認為,審議式民主(公民經常有組織地討論政治的民主體制)會修復我們大部分的瑕疵;但我的意見相反。證據顯示,政治審議讓人變笨、腐化人心、引人墮落而非向善。根據實證證據,我甚至認為現實比人們想的還糟糕。許多支持審議式民主的人表示,這些證據表示公民沒有以正確的方式討論政治,但我認為這種回應並未解決民主讓人愚蠢墮落的問題。
第四章〈政治不會讓你我更有力量〉將反駁一系列以賦權(Empowerment)為由,認為政治參與和投票權對人有益,或對於正義不可或缺的論述。我認為這些論證全都不健全。*9其中一種論述認為每個人都必須有同等投票權,以及同等任公職權利,否則就無法建立符合正義的良好生活觀。許多追隨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哲學家都相信此論述。但該論述其實無法滿足羅爾斯信眾的要求。
第五章〈政治非詩〉將批評另一系列論證。這些論證根據政治活動所表達的意義,認為民主體制、投票權、政治參與將符合善良與正義。它們主張政治參與具有表達性價值(expressive value),要讓民眾表達政治意見或者擁有自尊,就必須擁有平等投票權。我認為這類基於象徵價值或者自尊的論證無法成立,甚至完全無法告訴我們民主有什麼真實價值。它們無法合理說明民主為何優於知識菁英制。
我認為自己在第五章結尾,完成了過程論無法支持民主優於知識菁英制的論述。雖然目前有成千上萬的書籍與論文利用過程論來為民主辯護,但我不會逐一回應這些文獻。我要反駁的,只有某些最重要的過程論論證。
第六章〈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將提出一個「適任原則」(competence principle):我認為高風險的政治決策,如果決策不完全、奠基於錯誤信念,或由不適合做決策的主體決定,就會因此缺乏正義性、合理性以及威信。根據第二章與第三章的實證證據,整個民主系統似乎都違反這個「適任原則」。然而在選舉過後,民主系統不適任的頻率可能就會降低(因為選民能力不足,但是民主國家大部分的公務員卻沒那麼糟)。我認為,這個現象足以讓我們假設知識菁英制優於民主制。
第七章〈民主有足夠的能力嗎?〉將處理民主支持者的某些可能回應。某些民主理論學家會根據幾種不同的數學理論,認為民主社會中雖然大部分投票者都相當無知,但集合起來時,整個主體依然容易做出有用的決策。我認為這些數學理論都無法為民主辯護。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這些理論無法套用到現實世界。
然而,實證導向的民主理論學家依然認為,除了讓選民表達偏好或投票之外,民主還有其他功能。我同意這種看法。基於許多原因,民主政府在許多議題上都較易做出有用的決策,即使選民出現了系統性的能力不足也無所謂。民主系統內建大量「間接影響因子」(mediating factor),讓選民無法直接心想事成。
但即使如此,我仍認為每一個政府的高風險決策,都應該符合上述的「適任原則」。在非選舉期間,政府公僕的表現經常符合標準;然而選民的表現在大部分選舉期間都無法達標。根據適任原則,我認為這裡有個兩難問題:如果選舉屬於高風險決策,我們就應該假設知識菁英制優於民主制;但如果選舉不算是高風險決策,知識菁英制與民主制就一樣好。由於過程論無法為民主做出妥善辯護,我認為在第二種狀況中,我們僅需選出效能較佳的系統即可。
第八章〈知者治之〉將勾勒出一些知識菁英政治可能實行的方法。我會在該章討論不同形式的知識菁英制分別有哪些潛在利益與風險,並對其餘一部分的反駁理由做出回應。
第九章〈彼此為敵〉是一則簡短後記。我認為政治可惜之處,就是讓我們彼此為敵。政治的問題不只是讓我們充滿偏見、進入部落戰爭、討厭所有反對者而已。政治真正的缺點,是會讓我們陷入真正的敵對關係。此外,因為大部分人的意見都互相衝突,政治還會讓我們因為彼此的態度而互相交惡。總體說來,我認為我們應該拓展公民社會的活動項目並縮小政治的領域。我們應該努力實現約翰‧亞當斯的願望。這不只是因為一個完美的社會不需要政治,更因為政治會讓我們擁有彼此厭惡的理由。
美國革命英雄/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曾言:「我必須學習政治與軍事,讓我的兒子有機會學習數學與哲學。他們必須學習數學、哲學、自然史、造船術、航海、商務、農業,才能讓他們的孩子有權利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刻、編織和陶藝。」亞當斯本身是個政治動物(如果當時有這種人的話),但他希望未來的世代可以活進更高的層次。
這本書會告訴你,我們為何應該努力實現這種願望。
政治參與會喚起高貴情操,抑或腐化人心?彌爾與熊彼得的看法
十九世紀的偉大倫理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我們應該選擇有用的政府形式,使其導向最佳結果。他建議我們思考所有選擇的後果。也就是說,在選擇君主制、貴族制、代議制或其他政府制度時,我們不該只看顯而易見的面向(例如:維護自由權利、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果),也應該思考政府形式對於人民智力與道德的影響。某些政府形式可能讓人民愚蠢而被動,某些則可能讓我們鍛鍊出鋒芒,變得積極。
彌爾認為,參與政治會讓人民更聰明,更關心公眾利益、有知識,情操更高貴。他希望讓工廠工人思考政治,認為這就像讓魚兒看見比海洋更廣闊的世界。他期待政治參與能讓我們的心靈更堅強,而非軟弱。他冀望政治活動讓我們超越眼下的短視近利,以長遠廣闊的視野思考事務。
彌爾很有科學頭腦。在他的年代,世上沒有幾個國家採用代議制,而且即使在那些國家,也只有少數菁英擁有投票權,無法代表人民利益。政治參與在彌爾的時代,通常是讀書紳士的特權。另一方面,彌爾也沒有那麼多支持論述所需的證據,所以大體來說,他的說法算是一種合理但未經驗證的假說。
一百五十多年後,驗證假說的時刻來了。這點之後會提到,實驗結果大體來說是無效的,而且我認為彌爾會同意該結論。大部分常見的政治參與形式,不但並未讓我們更有智識、更為高貴,反而讓我們愚蠢而墮落。這與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看法相當接近:「一般民眾一旦進入政治領域,智力表現就滑落一個層級。面對真實利益,他們分析事情與討論的方式立刻有如嬰兒一般。在政治裡,大家都變回原始人了。」
如果事實偏向熊彼得,而非彌爾,我們就得提出下一個更難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民眾參與政治多深?甚至,政治事務中能讓民眾參與的比率有多高?
民主衰落的光明面
許多民主和公民參與的書籍,都抱怨公民參與程度下降。它們指出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大型選舉的投票率介於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如今即使是總統大選,投票率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六十。中期選舉、州選舉以及地方選舉,更是落到百分之四十。比較完這些數字,作者就開始咬牙切齒,說美國民主的包容性愈來愈高,讓更多民眾坐上政治談判桌,但願意出席的人卻愈來愈少。這些作者認為,現在的公民不再認真看待政治自治的責任。
我的看法不一樣:政治參與度下降是好的開始,但之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甚至應該希望參與度變得更低,而非更高。完美的狀態下,政治只會吸引一小撮普通民眾的注意;大部分的人生命中則是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刻、編織、陶藝,也許再加上足球、NASCAR賽車、拖拉機競賽、閒話家常,或者去Applebee’s連鎖餐廳吃東西。在完美世界中,大部分民眾根本不會在意政治才對。
然而某些政治理論家,卻希望政治能觸及生活中的更多層面。他們希望增加政治討論,認為政治會孕育高貴情操,民主可以讓小市民擁有權力,掌握自己的人生。在這些「公民人文主義者」眼中,民主本身就是美好人生的一環,至少也算是一種高尚的願景。
至於兩種解釋何者較接近真實,則部分取決於人性的特質、民主參與對我們的影響、以及大型政治參與可以解決什麼問題——或者產生什麼問題。
民主公民的三種面貌
如今我們不需再像彌爾那樣猜測政治的影響。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早已投注六十年以上的心血,研究民眾思考、應對、決策政治的方式。專家們調查民眾已知與未知的資訊、信念內容與信念強度,以及改變意見所需的條件。除此之外,還研究民眾的頑固程度、彼此結盟的原因與方式、讓人參與政治或採取行動的原因。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一一細述這些研究結果。目前且先容我簡括結論。
民眾在政治意見強度上有所差異。有些人對信念的忠誠有如宗教信仰,有些人則相當薄弱。某些人的意識形態多年如一,某些人換立場只需要一瞬間。
民眾的政治意見一致性也各有不同。有些人擁有整套融貫一致的意見,有些人則會相信彼此矛盾的事情。
民眾心中的政治意見其數量也不同。有些人對每件事都有意見,有些人則幾乎一點看法都沒有。
民眾心中的政治信念,背後的支持證據數量也不同。某些人會用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作為強力證據,有些人只會看新聞。某些人對於政治幾乎一無所知,心中雖有某些信念,但幾乎(或完全)沒有任何支持證據。
對於自己不同意的意見,民眾的在意程度與回應方式也各自不同。某些人認為反對者就像妖魔,有些人認為對方只是搞錯了什麼。有些人相信反方陣營裡至少有幾個人可以理性溝通,有些人則認為反對者都是愚蠢之人。
民眾參與政治的程度與方式也各不相同。某些人對政治的狂熱,與其他人陷入戀愛時的行為如出一轍。有些人會投票,有些當政治志工,有些人參加競選活動,另外一些人則捐錢。不過也有人從未參與政治活動,甚至永遠不會參與。如果國家剝奪了這些人的政治權力,他們也不在乎,或根本不會發現。
上述每一個變項,民眾都各自站在光譜的不同位置;但在本書論述中可以適度簡化。在此,我要把民主社會中的人粗分為三類,分別將其稱為「哈比人」(hobbits)、「政治流氓」(hooligans)、「瓦肯人」(vulcans)。
‧哈比人:絕大多數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在大部分事情上,他們都欠缺固定而有力的觀點,甚至經常毫無任何觀點。他們幾乎不具備社會科學知識。對當下事件渾沌無覺,也沒讀過判斷/理解事件所需的社科理論或社科資料。對世界相關資訊與國家的歷史,他們只有粗淺的認識。這些人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不想花太多腦筋思考政治。美國大部分不投票的人,就是哈比人。
‧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擁有強烈且大半既定的世界觀。這些人可以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但解釋其他立場時卻無法讓異議者滿意。他們帶著偏見吞吃政治資訊,努力尋找證據支持心中的政治定見;碰到與自己信念衝突的資訊或反面證據,就刻意無視、避開,或直接反駁。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信任社會科學,但大多片面擷取資訊,且通常只看支持自己立場的報告。這些人無論對自己的能力或知識都過度自信。政治觀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加入政治團體會讓他們自豪。在他們心中,在美國選擇民主黨/共和黨,在英國選擇工黨/保守黨,或在德國選擇社民黨/基民黨,對自我形象的影響就宛如信神的人選擇基督或伊斯蘭一樣。這些人經常蔑視反對者,堅稱其他的世界觀愚蠢、邪惡、自私,或至少受到嚴重誤導。大部分經常投票的選民、熱心政治的民眾、社運參與者、黨員、政客,都屬於政治流氓類。
‧瓦肯人:對於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他們的政治意見幾乎全都奠基於社會科學與哲學。這些人會自我反思,證據不足的部分不敢隨便斷言。他們可以用讓異議者滿意的方式解釋自己反對的意見。這種人對政治有興趣,但卻欠缺熱情,原因部分來自他們努力避免偏見,不讓自己喪失理性。這類人不會認為所有反對者都很蠢、邪惡或自私。
這三種形象都是理想化或概念化的原型,每個人符合的程度各自不同。我們多多少少都有偏見,沒有人能真正成為瓦肯人,但可惜的是,許多民眾的形象卻與哈比人或政治流氓相當吻合。大部分的美國人都屬於這兩者之一,或位於兩者之間。
請注意,我沒有用政治意見的極端程度來分類這三種人。政治流氓未必都是極端人士,瓦肯人的意見也未必折衷。某些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就是瓦肯人,大部分的溫和民眾則可能是哈比人或政治流氓。
大體來說,意識形態也與這些原型沒有必然關係。以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ism)為例,其中就有一部分哈比人。這類哈比人會傾向自由意志主義,或者說容易認同該派的結論,但本身並不思考或不大關心政治,通常也不會認為自己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許多(或大部分)自由意志主義者則屬於政治流氓,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身分是他們自我認同中最大的一塊。這種人的臉書頭像是黑金二色的無政府旗,約會對象一定也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只讀被視為異端的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經濟學,以及安‧蘭德(Ayn Rand)的小說。但除了這兩種人,自由意志主義者之中也有不少瓦肯。
彌爾假設,讓民眾參與政治便能啟蒙他們。我們可以說,彌爾認為代議制政治的討論過程和政治參與可以讓哈比人變成瓦肯。熊彼得的假設則相反,他認為政治參與會讓人固執己見,讓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
在之後的章節裡,我會檢視各種認為政治自由與政治參與對我們有利的論述,並一一加以反駁。我堅信政治自由與政治參與對大部分人的整體影響都是負面的。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哈比人或政治流氓,而且哈比人通常都是潛在的政治流氓。遠離政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