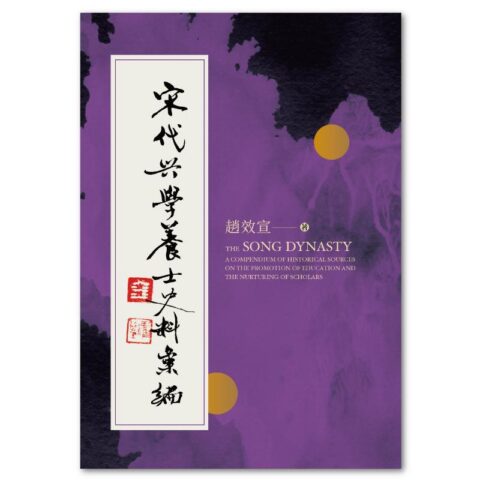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竊盜案件的多元分析
出版日期:2024-09-12
作者:巫仁恕、吳景傑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408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2.8 cm
EAN:9789570874181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以四川巴縣檔案為主要史料,深入探討十八至十九世紀中國地方的竊盜犯罪史,為清代社會史研究開闢新視野。作者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結合法制史、法律社會史、歷史犯罪學、物質與消費文化研究,以及城市史與都市社會學等多元視角,全面剖析清代竊盜犯罪的複雜面向。
在宏觀層面,本書關注同治朝巴縣竊盜案件與重大歷史事件及社會變遷的關聯;在微觀層面,則呈現了犯罪動機的多樣性,挑戰了「貧窮即犯罪」的觀點。此外,也詳細考察清代竊盜相關法令、竊賊身分與行竊類型、案件審理流程及機制,並透過分析被盜物品,揭示了當時的物質消費情況和城鄉差異。
經由對日常犯罪的探討,書中的論述在史料、方法與觀點上均有所突破,開拓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作者意在喚起對犯罪史的重視,尤其是注意犯罪者的能動性,且藉司法檔案來探析社會結構的變化,對於研究清代社會史、法律史、犯罪史的學者而言,本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
作者:巫仁恕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分別曾兼任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並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合聘副教授。曾受邀訪學日本、美國、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法國與以色列等重要學術機構。110年度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獲獎人。
作者:吳景傑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法律史與社會史。
自 序
導 論
第一節 《巴縣檔案》及其研究成果
第二節 竊盜犯罪史的多元研究方法
第三節 本書各章概要
第一章 清代竊盜法律的規範與懲罰
第一節 竊盜律的基本架構
第二節 竊盜相關的律例規範
第三節 竊案的審理與判決:以官箴書為例
小結
第二章 竊案處理流程與知縣斷案的考量
第一節 從案發到報官
第二節 調查、追緝、審訊與結案
第三節 州縣官的斷案考量
小結
第三章 同治朝巴縣竊案發生的背景因素
第一節 同治元年太平軍的擾動
第二節 同治二年重慶教案
第三節 同治三年的米價陡漲
第四節 城市化的速度
小結
第四章 竊嫌身分與犯罪動機的分析
第一節 竊嫌身分的分析
第二節 犯罪動機與行為的發生
小結
第五章 行竊的類型與犯罪的過程
第一節 偷竊的型態
第二節 特殊的時節
第三節 銷贓與接贓的管道
第四節 窩戶:竊賊背後的黑手
小結
第六章 被竊事主的身分與報案選擇
第一節 被竊事主的身分統計
第二節 被竊事主與中人之家
第三節 被害事主的報案選擇
小結
第七章 從贓物來看地方的物質消費
第一節 贓物失單的真實性
第二節 失竊物品的類別變化
第三節 失竊主流物品的介紹
第四節 失竊的特殊物品分析
第五節 物品擁有與社會階層化
小結
第八章 犯罪與城市:城市竊案的分析
第一節 城市內竊盜案件的空間分布
第二節 城市建築與竊盜犯罪之關聯性
第三節 城市被竊標的物之特徵
第四節 城廂防治竊盜犯罪的機制
小結
結 論
徵引書目
論文發表資訊
自序
偷竊,是古老而日常的犯罪行為,其實在歷史長河中,小偷的真實面目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我們對於歷史上的竊賊印象,往往來自於通俗文化中塑造的「義賊」形象,例如在台灣有著名的廖添丁,在明代則有俠盜一枝梅。明末文人凌濛初在他的作品《二刻拍案驚奇》中,對一枝梅的行為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述。然而,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其實是一個拼湊出來的故事。根據我的考證,「一枝梅」在明代的歷史中確實存在,並非虛構的小說人物。然而,真實的一枝梅其實是活躍在明代中葉湖南永州府一帶的江湖大盜,當時的地方官員花了大量的精力才將他捉拿到手。儘管明清以來,許多筆記小說都曾提及小偷,但所描述的多是像一枝梅這樣的特殊案例。之所以過去的歷史學家對小偷的形象和犯罪的討論不多,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史料的缺乏。近年來隨著史料的開發,清代許多州縣的地方檔案逐漸被史學界所知曉和應用,《巴縣檔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不過筆者開始接觸《巴縣檔案》,並利用之作為分析的歷史材料,原來的主要目的並非是研究竊盜犯罪的歷史,而是想要探析清代的物質消費文化。這樣的研究取徑來自於一次非常有趣的對談。還記得多年前剛開始從事物質與消費文化研究的時候,曾嘗試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所開設一門相關的課程。當時修課的學生中有一位博士生吳奇浩,他上課時非常認真,尤其是課表中所列的外文二手文獻,他都非常認真的閱讀完。之後他也決定以台灣史上的物質消費作為他博士論文的主要領域,並且以臺灣的服飾歷史作為博士論文主題。在一次討論過程中,我們思考如何利用新的歷史材料來分析物質消費,我舉出了西方學者常利用遺產清冊上的記錄來分析物質消費,而我認為透過清代的抄家檔案與徽州的分家文書這類文獻,也可以探討社會上層與商人階層的物質消費。吳奇浩則別出心裁,他覺得清代臺灣的《淡新檔案》中有竊盜與贓物的清單,應該也可以作為分析的史料。我非常贊同,但是我問他數量多寡,他則不敢肯定。
日後吳奇浩完成了博士論文《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我也是他口考的委員,這本論文相當優異,有部分已經發表在《新史學》與《台灣史研究》等重要期刊。只可惜他英年早逝,作為老師的我也是萬分的感慨與遺憾。即使如此,奇浩已留下非常重要的學術遺產。除了他的博士論文與著作之外,他是想到利用竊盜案件中失物與贓物清單的第一人。而《巴縣檔案》是我較熟悉的州縣檔案史料,我很肯定的是這樣的分析方式絕對可以應用在《巴縣檔案》。而研究的成果也發表在本書的第七章,該章中分析從乾隆到同治時期地方上物質消費的變化趨勢,這就是我最初的研究動機。
在我靈光一閃,想到利用《巴縣檔案》中的失物與贓物清單來研究物質文化的同時,剛好在暨南大學有一位碩士生王大綱在尋找研究題目。他在修習我的課程後,希望能得到我對他碩士論文的指導。於是,我與他達成了一個協議,我為他指定了研究題目,希望他能利用乾隆朝的《巴縣檔案》來深入探討竊盜問題,並且每完成一章就將其交給我審閱。他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將論文完成,每一章我都仔細審閱並修改了至少兩次。最終,他完成的碩士論文的水準超乎我們的期待,這大概是我在指導學生過程中最奇妙的經歷。因為我自己從碩士班到博士班都是在台灣大學就學,接觸的學生也都是台灣大學的學生。許多老師都有同樣的經驗,指導台灣大學的學生可說是事半功倍,因為他們的學術基礎和學術資質都非常出色,所以指導老師所需要花的力氣相對較少。然而,對於次一級學校的碩士生來說,如果想要達到高水準的論文,指導老師則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王大綱的論文雖然是我花最多力氣指導的成果,但至今仍然是我指導過的學生中最讓我滿意的碩士論文之一,這本論文為我帶來了深深的成就感,我對他的努力和成果感到非常驕傲。
關於《巴縣檔案》的收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館擁有乾隆、嘉慶兩朝的珍貴微卷。這些寶貴的資料,都是本所的賴惠敏教授多年來不懈的努力成果,她曾經申請國科會計畫,並用經費購入這兩套微卷,為後人留下了無價的學術遺產。我原本計畫探討乾隆、嘉慶兩朝的物質收藏與消費的變化,但卻發現本所的嘉慶朝《巴縣檔案》竟然缺少了盜竊類的案卷,讓我不得不改弦易轍,變更我的研究方向。就在這時,我得知京都大學的夫馬進教授利用日本的學術經費,購得了同治朝的《巴縣檔案》,並積極推動相關的研究。於是我透過日本的友人,與他取得聯繫,希望能夠前往京都大學,借閱同治朝《巴縣檔案》盜竊類的微卷。
我準備好後,就去京都拜訪夫馬進教授。他是日本中國史學界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與他討論中國史,無論在書房或料亭,都是一場知識盛宴。夫馬教授退休後,仍持續學術研究。每次見他,都能聽到他最新發現的史料和關注的問題。他的研究成果總有令人驚豔的新見解和新觀點,讓我敬佩不已。例如他在沒有全文資料庫和檢索工具的情況下,從數千件《巴縣檔案》中找出訟師何輝山的線索。更感人的是他慷慨地借我《巴縣檔案》竊盜類的微卷。這些微卷是他退休前用研究經費購買的,因版權問題,京都大學圖書館無法收藏。夫馬教授為了促進研究,對前來借閱的國內外學者都十分大方,這種精神令人敬佩。這本書能完成,多虧了夫馬進教授。沒有他,這本書是無法面世的。
我與日本京都大學的關係,實在是一段充滿奇遇與緣分的故事。我首次踏足的日本學術機構,就是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當時我還是初至近史所的助研究員,感謝陳慈玉老師的熱心介紹,讓我有機會認識了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村上衛教授。此外臺灣大學歷史所的學弟廖述英與嚴雅美夫婦當時也在京都大學留學,他們提供給我許多寶貴的資訊。因此,我也有幸認識了夫馬進老師的得意門生山崎岳教授,他也曾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擔任助手。他們都是我學術路上的良師益友,也是我一生的摯友。有他們的陪伴,讓我在學術的道路上從未感到孤單。2017年,村上衛教授邀請我到京都大學人文研訪問三個月,能夠在這所著名的學府訪學,並在我認為全世界最美麗的城市生活,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冬季與春季在京都欣賞雪景與櫻花的美景,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在京大的這三個月,也是我能夠專心閱讀《巴縣檔案》的絕佳時機。同時,我也有機會參加京都大學的學術活動,與我敬佩的岩井茂樹、石川禎浩等教授討論學術,感受這個著名學府的學術氣氛。非常巧的是,原來在廣島任教的好友太田出教授也轉到京都大學任職,我正巧帶著他的大作《中国近世の罪と罰:犯罪.警察.監獄の社会史》與慶應大學山本英史老師的專書《赴任する知県:清代の地方行政官とその人間環境》,這兩本書都是我非常喜歡的,從這兩本書裡我獲益良多。
在這段時間裡,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巴縣檔案》盜竊類的閱讀中,然而,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短短的三個月裡,我竟然只讀完了一年的分量。這與我最初的計劃和想像有著相當大的落差,我沒有預料到同治朝的案卷竟然如此龐大,這讓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儘管隨著閱讀經驗的累積,我的閱讀速度有所提升,但研究計劃的完成仍然遙遙無期。我開始逐漸轉移研究目標,但同時也因為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而陷入停滯。這是一段充滿挑戰和探索的旅程,每一步都充滿了未知和期待。
《巴縣檔案》是一本藏寶圖,每一次翻閱都能發現新的驚喜。最初,我只是想從中探索清代的物質消費文化,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對竊盜犯罪的奧秘越發著迷。我發現,這些州縣的司法案件不僅記錄了物品的流動,還揭示了犯罪行為的種種動機和影響。於是,我決定轉向犯罪歷史的研究,這也與我個人的興趣和經歷有關。首先,我是一個美劇「CSI犯罪現場」的忠實粉絲,多年來,我跟隨著劇中的偵探們,一起解開一個又一個的謎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可以直接把電視劇的情節套用到歷史研究上。我還需要學習一些犯罪學的基本知識,其中一本由湯姆.蓋許(Tom Gash)所撰的《被誤解的犯罪學》(Criminal: The Truth about Why People Do Bad Things)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他揭露了許多關於犯罪動機的迷思,包括偷竊犯罪,這也讓我開始用犯罪學的視角來看待歷史上的犯罪案件。此外我還閱讀了一些犯罪學的教科書,學習了一些分析犯罪的方法。我嘗試著把犯罪學和歷史學的方法結合起來,來重構竊盜犯罪的歷史。這樣的方法讓我發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事實,也顛覆了我們對犯罪史的一些固有的刻板印象。
我回國後開始思考轉向探索犯罪史這個課題。我的研究助理,也就是本書的共同作者吳景傑教授,當時是台大歷史所的博士生,正為博士論文的選擇與方向而苦惱。他已決定研究法律史,但尚未確定具體的主題。我便建議他嘗試運用《巴縣檔案》來探討竊盜的法律面向,他也欣然接受了這個挑戰,並順利完成了博士論文〈法律、犯罪、社會:清代後期重慶竊盜案件的官員思考模式〉。這篇論文以法律史為主,但也融合了法律社會史的視角。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在本所擔任博士後研究,我們也因此有機會經常交流,討論如何合作改寫論文與撰寫專書。他的博士論文是這本書的重要基石,他在這本書的貢獻與我不相上下。他的努力與成果也受到學界的肯定,在本所博士後期滿後,即受聘於淡江大學歷史系任教。
這本書之所以完成,國科會學術專書寫作計畫所提供的經費助益甚大,計畫編號109-2410-H-001-079,特別在此致上感謝之意。我還要感謝許多曾提供本書意見的師友,除了上述提到的師友之外,還包括葉文心、王國斌、劉錚雲、伍躍、賴惠敏、邱澎生、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林文凱、陸康(Luca Gabbiani)、梅凌寒(Frédéric Constant)、孫慧敏、城地孝、Kim Hanbark、謝歆哲等多位師友。最後還要感謝我的超級助理陳重方,他當時是清大歷史研究所的博士生,也是法律史學界的明日之星,已經出版幾篇重要的論文,頗受學界期待。因為有他幫忙,讓我在身兼行政職務的同時仍然遊刃有餘。
有次和家父談起我正在進行的研究主題,他聽了後很感興趣。他還回憶起小時候看到老家的叔叔家,家後面是養牛的牛圈,有一天夜裡牛圈的牆就被挖了一個洞,叔叔的牛就這樣被偷走了,這與本書中提到歷史上發生的案件如出一轍。最後,期待這本書出版後的小小心願,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夠將歷史犯罪學這一新興的研究領域逐漸推廣,讓更多年輕的歷史研究者投入相關的研究,進而豐富我們對歷史的瞭解。
導論(節錄)
竊盜犯罪毫無疑問是人類社會中最傳統的犯罪類型,至今仍是世界各國在防制犯罪上最困擾的問題之一。竊盜犯罪不僅可能造成民眾財產上之巨額損失,在心理上也造成人民的恐懼感與生活的不安全感,嚴重的影響到社會的治安與人們的心理。竊盜犯罪案件的增多,不但成了治安的一大隱憂,加深社會的不安全感,從現代犯罪學的角度來看,竊盜犯罪還涉及微觀個人的人格心理與家庭背景,同時也反映宏觀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變遷。
竊盜犯罪既然是最傳統的犯罪類型,過去歷史學界對這類犯罪類型的探討,就顯得不夠充分。放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清代中晚期,因為川楚白蓮教與太平天國運動等大規模的動亂,吸引了大多數史家的目光,從而忽略了其他小型像是竊盜這類日常犯罪事件。除此之外,竊盜犯罪被史學家忽視的另一原因,史料的缺乏也是重要的因素。雖然在筆記小說中不乏偷竊的故事,但資料不夠全面,且小說家之言有誇大之嫌。再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局限,導致竊盜犯罪的歷史分析不夠深入。
本書的撰寫得利於清代地方州縣衙門檔案的發掘,即利用四川省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以下簡稱《巴縣檔案》)以彌補史料上的缺憾。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將嘗試從法制史、法律社會史、歷史犯罪學、物質與消費文化,以及城市史與都市社會學等多元的角度來分析竊盜犯罪的現象,同時又注意到從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葉的變化,由此呈現朝代興衰、社會變動與犯罪發生的複雜交錯。
第一節 《巴縣檔案》及其研究成果
這幾十年來,因為不少清代州縣地方政府的檔案被發現,開拓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視野,《巴縣檔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巴縣檔案》自1953年被發現以來,已歷六十餘年,中外各國學者使用頻繁,實因其時代跨度長,內容豐富,相對於內閣大庫檔案更是貼近社會實態的第一手史料。早期因為史料比較難以得見,所以有許多研究是根據四川省檔案館所整理好的《巴縣檔案》史料匯編,主要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檔案匯編,近年來四川省檔案館又出版了咸豐朝的檔案選編,並陸續整理出版乾嘉道三朝的司法檔案。
過去利用《巴縣檔案》的研究成果,有從法制史到法律社會史的趨勢。《巴縣檔案》不僅被充分利用來探討法制史的司法審判與訴訟制度,特別是到二十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後,利用《巴縣檔案》來研究社會經濟史的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程度的發展,諸如婚姻與婦女的地位、行幫與商人團體、民間糾紛的調解、工商業經營制度、基層社會組織與市場管理等議題。如此的發展一方面可以被視為是社會史的研究朝向中國古代法律議題的延伸和擴展,同時也因為受到國外知名學者的社會史研究成果所影響,例如黃宗智與夫馬進的研究。
學者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是最早接觸《巴縣檔案》並著手研究的西方學者,在其任教UCLA時也指導出多位博士以《巴縣檔案》為研究塑材,並出版多本優秀的專著。近年來隨著檔案開放與利用的發展,不少學者開始提倡清代巴縣中晚期的歷史研究,例如日本學者夫馬進便提倡利用同治朝的《巴縣檔案》,同時帶領一批學者投入研究。
先就法制史的面相而言,由於史料性質偏重於法律文書,《巴縣檔案》多被用以反映州縣層級司法審判的實態,以及州縣衙門行政與基層組織的運作。例如廖斌、蔣鐵初的專書即利用《巴縣檔案》來觀察清代四川地區刑事司法制度,包括刑事司法主體、刑事訴訟制度(訴訟的過程、逮捕、保釋、監獄等制度)、刑事的證據制度與審判制度。該書以制度為討論核心,而不涉及刑事案件本身的問題。
夫馬進的研究則指出從訴訟與審判的方式,可以看出同治時期的巴縣,與乾隆、嘉慶時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異。乾隆、嘉慶時期在審判中,地方官的控制十分有效,鄉約和地鄰也服從地方官的權威,協助其進行案情調查,原告也順服地方官的權威而具結。這些方面到同治時期則截然不同。同治年間地方官所下的判決中,在很多情況下很難分清原告或被告何方勝訴,即使能夠分清,在很多案件中其意義有時也令人費解。在當時無論是類似現代刑事案的「命盜重案」,或是涉及「戶婚田土」類似民事的糾紛,都得當事人告官投狀再經過訴訟的過程來解決。夫馬進統計同治十三年間,平均每年訴訟件案數為1000件到1400件左右;若以當地戶口數來推算,每40戶或60戶中就有一戶提起新的訴訟並被接受立案,由此呈現其所謂之「訴訟社會」的特徵,傳統文獻稱此現象為「健訟」。吳佩林利用南部縣與巴縣等檔案探索清代縣域民事糾紛與法律秩序,發現民間到衙門訴訟必須付出多種費用,顯示訴訟的成本相當高。尤陳俊在過去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認為「訟費高昂」雖然確實反映出訴訟費用與陋規的問題,但官員一方面試圖解決,同時又與士大夫不斷地宣傳這件事情,其目的為使民眾打消進入訴訟的念頭,以減輕健訟風氣與行政壓力。既然如此,人們在報官投狀時應該會多加考慮,為何還有健訟的現象呢?
在官方與傳統的士大夫的語境中,唆使人們健訟的惡源是訟師,另一個則是衙門裡的書吏、差役為了藉此自肥。然而美國學者白德瑞(Bradly W. Reed)透過對十九世紀《巴縣檔案》的觀察,認為這類批評是士大夫的一種話語表述,其實衙門吏役收取訴訟規費的行為看似非法,卻有其非正式的正當性,也是補充衙門經費以適應十九世紀官府財政缺陷的一種方法。再者吏役收取規費的行為逐漸標準化,且規費額度並不高,並不會影響百姓訴訟的意願。伍躍從《巴縣檔案》的案例看到官吏主動鼓勵訴訟之實例,說明地方州縣衙門的組織結構及其畸形的薪俸制度,促使吏役必須倚靠陋規收入,甚至州縣官也會暗示鼓勵投狀,這也是導致訴訟社會形成的原因之一。由是,衙門裡的書吏、差役的形象與事實之間,仍有許多待討論的空間。
黃宗智利用《巴縣檔案》研究清代的民事訴訟案件,強調民事糾紛的解決,常是使用「民間調解」與「法庭審判」兩者互補與互動的模式同時進行的,或有稱之為「第三領域」,這些「第三領域」的角色係半官半民性質,作為官府和社會間的關鍵中介人物。黃氏之說成為法律社會史的研究範式,也帶動研究民間糾紛的調解問題,且又涉及到基層社會組織負責人的性質探討。
《巴縣檔案》裡保存了許多基層社會組織負責人的資料,是研究基層社會的絕佳範例。梁勇的研究指出巴縣的保甲長、客長、團正等制度的形成,在早期與巴縣的移民社會密切相關,客長制度就是因此而出現,繼之被納入了保甲制度。太平天國運動之後,軍事化的團練組織漸趨重要,且到了同治年間逐漸在地化,客長制遂退出了歷史舞臺。夫馬進與凌鵬的研究也都指出同治年間的團首監正的職能也擴及民間糾紛的「裁判式調解」,故《巴縣檔案》中常有「憑團理剖」一詞。伍躍關於巴縣鄉約的研究,指出鄉約的職能到清代晚期,已由教化百姓轉變為催辦公務為主,成了縣衙任命的「在民之役」,並非「鄉村自治」或是「第三領域」的成員。這類基層社會的調解形式不僅是民事糾紛,巴縣的竊盜案也多有竊賊被捕後經調解後結案的實例。
此外,巴縣因為是重慶城的所在地,重慶工商業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漸趨繁盛,工商業團體組織也如雨後春筍地出現。關於商人團體、交易糾紛與市場秩序等面相通常都會相互涉及,關鍵的問題在於工商業者團體的角色與作用。邱澎生以乾嘉時期重慶的船運業為例,探討行幫的幫規與官府法律之間的互動而造成制度的變遷,包括乾隆二十五年(1760)取消既有徵調船行與埠頭制度、船幫與八省會館等團體組織介入業者糾紛的調解等等。付春楊也認為清代工商業糾紛裁判是循傳統公平的原則下,官府與工商業者互動的結果。張渝則認為雖然清代有商人制定行規以維繫市場交易的秩序,但這些規範都是在國家制定的法律規範下的註釋或理解,而且商人不是最重要推動的主體,他們沒有獨立維持商業秩序的能力,而是得靠官府的支持才有權威性。令人好奇的是以竊案為例,在訴訟的過程中工商業者若以行規擺脫責任,縣官是否承認其效用呢?本書將有實例可以說明。
第一章 清代竊盜法律的規範與懲罰
竊盜既然是歷史悠久的傳統犯罪型態,相關法律規範也早已形成。到了清代涉及竊盜的相關法律規範雖然有相當部分是繼承明朝,但仍有其時代的特色。清代各種不同形式的法律規範之中,「律」與「例」有其不同的功能。律文提供規範的基本原則,且不輕易變動。條例做為附於律文之後的規範,能夠及時因應社會的變遷,以補充律文未能擴及的範圍,並且在制度的保障之下能夠定期修訂。此外,同一個犯罪行為亦無法在單一律例之中完全涵括,而是散見於其他律例之中,竊盜的相關律例規範亦是如此。過去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日本學者森田成滿從財產權的角度來分析竊盜罪的法律,是少見的研究成果。本章第一、二節透過整理〈竊盜律〉、〈竊盜例〉,以及與竊盜行為相關的其他律例,以理解清代法律對於竊盜行為的整體規範。
雖然法律規範提供了一些準則,但明清官員在面對竊盜案件時在審訊與調查時,又有什麼是法律規範所難以參酌,而是需要實際經驗來解決的問題呢?關於此問題,明清官員留下大量的官箴書,提供了審訊經驗與教導斷案的技巧。本章最後一節擬對照官箴書在實際審判時著重的問題,以說明官員處理竊案時所關心的重點與考量的原則。
第一節 竊盜律的基本架構
〈竊盜律〉在《大清律》之中是被編排在刑律的賊盜門,律文繼承自《大明律》,並更動三處,分別是增加律文小註、刪去「軍人為盜」、改「貫」為「兩」。清朝立國之初,即沿用《大明律》,並加上小註闡明律意。原本《大明律》將〈竊盜律〉分為「已行而不得財」、「已行而但得財」、「初犯、再犯、三犯」、「掏摸」、「軍人為盜」等五節,律例館於雍正三年建議「今兵丁犯竊盜,俱行刺字,『軍人為盜』一節刪」,便成為清代通行的〈竊盜律〉。至於計贓論罪的條文,明初制律時已經發行「大明寶鈔」,計贓時便以「貫」為單位。清代修律時,由於大明寶鈔停用已久,清政府便改用「兩」為單位。
以下將分述清代〈竊盜律〉的重點與特色,並根據學者對於律文的註解說明之。
犯罪行為的定義
所謂「竊盜」,指的是「隱面潛形之謂『竊』,穿窬之類皆是也」,或「乘人所不知而暗取之曰『竊』」,即在事主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取事主擁有的物品,就是竊盜行為。〈竊盜律〉規定「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笞五十,免刺」,即指無論得財與否都算是犯罪行為,但是得財與否在量刑上是有差別。分辨是否「得財」的標準,為事主在這個行為之中是否「失財」,也就是犯人取得事主物品即為得財,即使是「賊人棄財途中而去,被他人拾得」,也算是得財;除非是由「事主拾回」,才算是不得財,因為事主原本被竊去的「贓」已為事主持有。而所謂「已行而不得財」,除了上述犯人已經得財卻又放棄的情況之外,也有「已至盜所,或已穿壁踰牆,為事主覺而逐,雖不得財,業已行竊矣」,即犯人已經進入事主家中,尚未得財就已事發逃走,便符合法律上所稱的「已行而不得財」。
〈竊盜律〉又規定「掏摸者罪同」,說明與竊盜類似的行為還包括所謂「掏摸」,即「擇便取物曰『掏』,以手取物曰『摸』,如今白撞、剪綹之類,乘間潛取,與竊盜無異」,類似今日所謂的「扒竊」。在《巴縣檔案》裡也常見有「綹竊」一詞,即屬此類行為。清律學者即云:「掏摸與竊盜併論三犯次數,以其罪相同也」,在計算累犯次數時,掏摸可以列入竊盜次數,反之亦然。正因為掏摸與竊盜行為相似,故以下論竊犯刑罰時的累犯與計贓的原則,都相同運用在掏摸者。
聚眾首從之別
聚眾多人集體行竊案件,在論刑時有首從之別,〈竊盜律〉規定:
但得財,不論分贓、不分贓。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指上得財、不得財言,減一等。「以一主為重」,謂如盜得二家財物,從一家贓多者科罪。「併贓論」,謂如十人共盜得一家財物,計贓四十兩,雖各分得四兩,通算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兩之罪。造意者為首,該杖一百。餘人為從,各減一等,止杖九十之類。餘條准此。
在不得財的情況下,由於並未取得任何「贓」,因此僅處以笞刑。如果已行且得財的話,其刑責還要視犯人是否為聚眾的主謀或是從犯而定。若是聚眾行竊,主謀將依據以上的刑罰治罪,而從犯是罪減一等。減一等是多少呢?笞杖刑的級距是十下,從律文小字的舉例說明主謀若該杖一百,從犯減一等,即是杖九十。
初犯與累犯之別
除了初犯之外,累犯者的刑罰會加重。〈竊盜律〉規定「初犯,並於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絞監候。以曾經刺字為坐。」《大清律集解附例》概括〈竊盜律〉的律義為「於贓重、屢犯者更加嚴也」,對於累犯的刑責是隨著逮捕次數而逐漸增加。分辨犯人逮捕次數的依據,即以其手臂上是否刺字為準,也就是明人王肯堂(1549-1638)所稱「所犯次數,以兩臂曾經刺字為坐」。但如果發現犯人雙臂皆已刺字,則是「怙惡不悛之亂民矣,故即坐絞」,即試圖以重刑遏止累犯的產生。由是累犯的認定方式,是以竊犯被逮捕的次數而定,第一次(初犯)與第二次(再犯)被逮捕的刑責相同,只有刺字部位的差別,一旦第三次被逮捕(三犯),則是判處死刑。
計贓論刑
〈竊盜律〉的一大特色,即是量刑時依行竊贓物的價值高低而定。這項計贓定罪的標準是附在律文的最後,其規定為:
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以上至一十兩,杖七十;二十兩,杖八十;三十兩,杖九十;四十兩,杖一百;五十兩,杖六十,徒一年;七十兩,杖八十,徒二年;八十兩,杖九十,徒二年半;九十兩,杖一百,徒三年;一百兩,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一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三犯,不論贓數,絞監候。
說明在初犯與再犯的情況下,自一兩以上,每增加十兩為一個等級,其刑責就從杖刑開始加等,五十兩以上處以徒刑,一百兩以上處以流刑,一直加到一百二十兩以上,則是死刑的絞監候;而三犯的情況,則是不必計算贓物價值,一律處以〈竊盜律〉的最重刑責絞監候。
明初因為通行貨幣為大明寶鈔,因此計贓定罪的規定是「一貫以下,杖六十」,後來大明寶鈔廢止,白銀取而代之成為通貨,計贓的「貫」就得換算成「兩」。根據明末佘自強的說法,當時「每鈔一貫,止值銀一分二厘五毫」,如果以〈監守自盜倉庫錢糧律〉「四十貫,斬」的規定,「四十貫止值銀五錢耳」,於法太重。清代以兩計贓,反而使情罪平衡。
計贓論刑又涉及到兩種情況,一是行竊多家財物,另一是聚眾偷竊分贓,此二狀況下如何計贓論罪?在上述〈竊盜律〉小註沿用《明律》的內容,對於行竊多家財物的論刑原則係所謂「以一主為重」,即指如果是竊盜多家財物,則以贓物價值最高者來計贓論罪。因為「將各主通算全科,則失之太重」,如果將犯人所竊的每家贓物合併計算的話,原本也許每家贓物甚低,分開計算都只有杖刑的輕罪,但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會到流刑,甚至死刑,「恐死有餘辜,失之於重」。如果因此判處死刑,雖然符合法律計贓的規定,但實際上卻是比犯人所犯的罪還要重的刑責。
至於「併贓論」的原則根據上述〈竊盜律〉的小註,係指聚眾偷竊分贓時,雖然所有人共同竊取同一家之後每個人皆分得部分贓物,但計贓的方式卻無法分開計算,而是要合併計算後按照主謀與從犯區分刑責,因為「(贓物)在彼雖分,而在失主則失去若干物」,「皆此共盜之人所取,故追贓則照入己,論罪則必併贓也」。從失主的角度,案中失去的贓物價值不會因為聚眾人數之多寡而增減,聚眾者無論各自參與的比例有多少,犯罪的程度都是一樣,只是主謀與從犯的差別而已,因此「贓可分而罪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