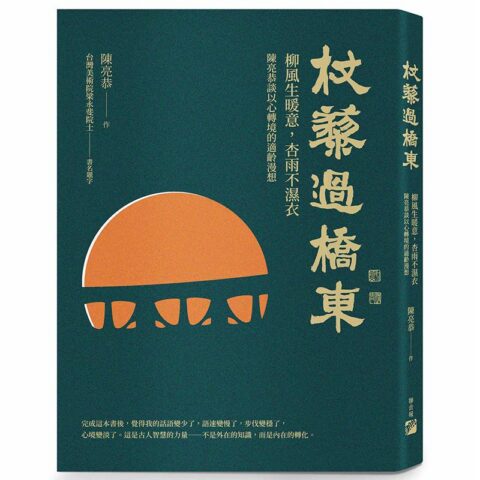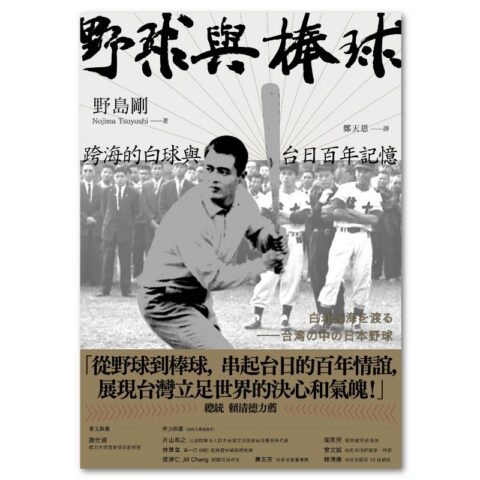純旅行快樂宣言
原書名:The Idle Traveller: The Art of Slow Travel
出版日期:2014-09-11
作者:丹‧基蘭
譯者:莊安祺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72
開數:32開(寬12.8×高18.8)
EAN:9789570844542
系列:聯經文庫
已售完
我之所以照我的方式旅遊,
真正的原因只是因為這樣更有趣,更享受。
丹‧基蘭是唯一一位寧可選擇緩慢的交通工具,也不搭飛機的旅遊作家。
他寫作並主編過十本書,包括暢銷的《爛城市》、《爛工作》,和《爛假期》……並與朋友合著《三個男人和牛奶車》,記錄他駕著電動牛奶車在英格蘭慢遊的故事。
在這本擁護慢遊、漫遊或閒遊的純旅行宣言裡,他呼籲我們重新省思:
究竟我們出發,是為了要尋覓什麼?又如何知道自己真正的抵達了目的地?
他認為我們應該擺脫現代人的度假心態,
對我們自己的好奇抱持信心,沉浸在讓自己脫胎換骨的真正旅遊之中。
並告訴我們如何透過最偉大旅遊作家的視野來看世界,放慢腳步的哲學,
讓每一段旅遊的經驗,不論多麼短暫,都有所價值。
作者:丹‧基蘭
2000至2010年,擔任《閒人》(The Idler)雜誌副總編輯,其後專業寫作,並為英國《泰晤士報》、《衛報》、《每日電訊報》,和《觀察家報》撰寫有關慢遊的文章。他是唯一一位不搭飛機的旅遊作家,寧可選擇速度慢很多的交通工具,這一點使他聲名遠播,為人津津樂道。他寫作並主編過十本書,包括暢銷的《爛城市》(Crap Towns)、《爛工作》(Crap Jobs),和《爛假期》(Crap Holidays),以及《對抗法律》(I Fought The Law),並合著《三個男人和牛奶車》(Three Men In A Float),記錄他駕著電動牛奶車在英格蘭慢遊的故事。他還在2011年與朋友共同創辦了「鬆綁」(Unbound)集資出書網站unbound.co.uk,並擔任執行長。
譯者:莊安祺
臺大外文系畢業,印第安那大學英美文學碩士,譯有《西藏的故事》、《托爾金傳》、《翁山蘇姬》、《創作者的日常生活》、《香料共和國》、《森林癒》、《她們的創作日常》等書。
前言(丹‧基蘭)
導言(湯姆‧霍金森)
1.旅遊不只是抵達而已
我自得其樂,從容的花時間走過這城市的外緣,穿過所有的公園,把倫敦這一部分的結尾和那一部分的開頭串在一起;我發現在這其中似乎為人所遺忘的角落和陰暗的街道,我甚至也拼湊出城市所擅長隱藏的輪廓。
2.留在家裡
不論你人在哪裡,旅行其實是在你的大腦之中進行,因此把旅人的心態運用在你所住的地方,是思索度假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有趣方式。
3.當你自己的導遊
但我對這些旅遊書主要的不滿在於,它們讓你的大腦透過旅遊經驗,走上狹隘的小徑──沒有留下多少讓你自己可以做的事。
4.擁抱災難
但說到旅遊以及愛和創造力──失去控制,超越你自己想像力的理解,才是一切的源頭。我認為這也是查特文在他的名言中所要表達的,他告訴我們:「人真正的家不是房子,而是道路,人生本身是一段必須要用腳去走的旅途。」
5.跟隨你的本能
我一向都不喜歡「名勝風景」,因此我們盡力避開我們所接近的任何景點。我們找到的是另一種風景,是以不可預期的方式移動,因此你不可能為了要見到它們而規劃行程的景觀。我們不是由導遊書或觀光手冊上發現它們,而是跟從我們自己的直覺和好奇心。
6.放下理智
人們說:「你去過這裡或那裡嗎?」「有啊,我幾年前就去過了。」彷彿光是人在那裡花幾個小時,就足夠徹底地瞭解它。為什麼我們以征服和終結的口氣來描述我們的旅遊經驗?
7.雄心壯志
我們全都是自己經驗的作者,因此偶爾停步四顧才這麼重要。如果你容許自己被塞進一系列「依樣畫葫蘆」的經驗之中,勾選一個又一個的欄位格子,那麼人生很快就流逝。
尾聲
謝辭
前言
丹‧基蘭
本書是獻給我的兩個孩子,奧莉芙和韋爾夫。在我寫作本文之時,奧莉芙年方一歲半,只要一有機會,她就愛帶我出門散步。她要我幫她穿上鞋子,為她穿上外套,然後她走到前門,用手指頭敲門。「達!」她說,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後我們手牽著手,出門去探索世界。有時我們會待在離前門幾公尺的地方,玩弄長在牆上的青苔,有時她掙脫我向前奔跑,一路尖叫跑到路的盡頭。有一回我們倆在百貨公司的電扶梯上上下下,來回了十五次。不過我總讓她在前領路,半小時的時間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
和幼兒一起散步,總不免會有一些既教我困惑,卻又啟發我的事物。一方面,你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何方,教人煩惱,因為看起來你是漫無目的迂迴前進,但很快的,你學會放輕鬆,並且在這樣的經驗中找出了意義。你毋需回答任何回題,它完全沒有目的,你會因為被迫停止日常生活的匆忙,而湧出驕矜傲慢的憤怒,然而一旦你經過了這段歷程,它卻教導你面對自己的真貌,而這是你原先根本不知道你會想要知道的真理。
慢遊者就像那幼兒一樣──他們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從容的緩步出發,走入世界,追尋意義,一路上遵循激發他們冒險感的火花。
導言/湯姆‧霍金森
閒散和旅行,表面上看來,這兩者似乎並非天作之合。閒人的本性就是宅男宅女,窩在火爐邊虛度光陰,他們或許較喜歡藉著地圖和書本的媒介臥遊古蹟,而懶得費心花力氣真正去旅行。法國哲人帕斯卡(Pascal Pascal,1623-1662)曾有雋語:「人的煩惱全都來自於他無法安靜的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只要一離開房間,你的問題就來了。據說英文的travel這個字,就源自於一個意思是「三根尖叉的酷刑工具」的拉丁字。
然而,然而……雖然旅遊得面對諸多明顯的不便,但閒散的人卻依舊會受慫恿而離開他的房間。閒人也是漫遊者,漫無目的的四處走動,是人生的觀察者,最偉大的閒人也是最偉大的旅人,和旅行作家。我腦海裡浮現的是生性怠惰的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 LL.D.,1709-1784,英國著名文人),他每天都躺在床上,直到日上三竿,但有時卻會在年輕的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約翰生傳》作者)陪伴下,神采奕奕的到地勢有時非常陡峭的蘇格蘭高地一遊。另一個例子是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蘇格蘭小說家、旅遊作家,著有《金銀島》),他在二十六歲時曾寫過一篇優美的文章,稱頌遊手好閒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是旅行高手,他的《驢背旅程》(Travels with a Donkey)是文壇傑作,而他可能也是對當代最偉大旅遊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1941年生)影響最深遠的作者。
因此旅行和閒散的關係可能比你想像的更密切。或許該說,閒人對於如今把旅遊包裝起來當成商品出售的形式,有強烈的反感,我指的是度假。我們並不是要批評觀光業本身──畢竟,能漫無目的地徜徉在義大利城邦之間,或者躺在水濱湖畔,還是滿教人心曠神怡的,只是光是陽光下的假期,恐怕還是讓人有不足之感,就如很久以前「性手槍」(Sex Pistols)搖滾樂團指出的,這是一種綺想,而且還是很花銀子的綺想。這是奴隸的報償,是陷身乏味工作的人所得到的安慰獎。
對於已經被濫用的那個詞「體驗」,我們也可以有同樣的看法。我們並沒有展開好好生活這困難的任務,反而選擇以無聊的工作打發我們的人生,其中穿插著列在表單上,等待你去經歷的強烈「體驗」。大家都在雜誌上看過如「死前要做的一百件事」之類的文章:開法拉利、參加名流雲集的英國皇家雅士谷賽馬盛會(Royal Ascot)、在達卡大賽車(Dakar rally)中一試身手、赴阿姆斯特丹參加十一月的大麻杯(Cannabis Cup)盛會,諸如此類教人膩煩的活動。可惜的是,開風氣之先的戴夫‧弗里曼(Dave Freeman,1961-2008,1999年出版《臨終前要做的一百件事》)才不過四十七歲,就英年早逝了。
當初我認識丹‧基蘭,是因為他闖進了當時還在肯頓市集(Camden Town,又稱龐克街,位於倫敦北邊,是龐克族大本營)的《閒人》雜誌辦公室。我們給這性情開朗的小夥子一份工作去做,而他後來也一再回來幫忙。逐漸地,他越來越投入《閒人》,多年來都擔任副總編輯。我們在辦公室樂趣無窮,也經常有許多饒富哲思的討論;我沾沾自喜,認為丹在《閒人》的這些年促使他醞釀出本書所抱持的哲學態度。
丹在本書中想要嘗試要勾勒出一種特別的旅遊哲學,讓旅行成為個人自己的療癒過程,而不只是逃避世俗的桃花源。因此我們可以說閒遊並不表示是舒適或輕鬆的旅遊,而且實際上,丹對於美輪美奐的旅館抑制靈魂的效果,還尤其抱著一股憤怒之情。閒遊也未必是慢遊,因為實際的動作步調是相對而言的──搭火車旅行,在一四五○年佛羅倫斯的藥劑師看來,已經是不可思議地快了。閒遊和現代人所謂的「樂」毫無關係,因為樂指的是暫時逃離我們的問題。不,它和態度有更多的關係,或許說「深度」旅遊比較貼切。
就如一點工作可以作為其後無聊乏味的調味品一樣,歷經千辛萬苦的艱難旅程也會使到達目的地時的趣味更加甜美。我認為在對輕鬆舒適的喜愛之外,也必須要有接納行路困難的泰然。我記得自己在二十出頭時,曾由德國北部搭火車要前往一個希臘島嶼,旅程十分艱苦而孤寂。途中我坐在一個小小的港口,對於該如何抵達目的地一無所知,雖然我四處詢問,但所有的人都搖頭回答。我放棄了,一屁股坐在我的袋子上,把頭埋在雙手之間,喪失了所有的希望。就在那一刻,一個小男孩走了過來:「先生,先生,往萊夫卡斯(Lefkas)的巴士再二十分鐘就要開了。」我上了巴士,抵達了我的目的地,在海邊一個叫作「天堂」的咖啡館。咖啡館的主人為我送上了一瓶啤酒。我坐下來,盯著水面,滿心難以言喻的歡喜。閒散永遠是甜美的,而當它是煞費苦心才得到之時,更甜美無比。
或許閒遊最偉大的形式,是孤獨的漫步。在這裡你可以用極低的價錢發現真正的自由,並且縱情那早已為人忘懷的消遣:思考。當今太多的旅行都是刻意設計要防止你思考。機場不能讓你平靜的思索,它們的建築醜陋枯燥,卻以各種顯示幕、商店和廣播讓你心神渙散,無法思想。你永遠不能真正的放鬆,或者活在當下。而另一方面,步行卻讓你回歸自我。威廉‧哈斯列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國作家)的珠璣散文《論旅行》(On Going A Journey)提到下面這段話:
給我在我頭上蔚藍的晴空,和我腳下碧綠的草地,眼前一條蜿蜒的道路,和晚餐前三小時的時光──然後讓我去思想!我很難在這人煙稀少的荒野中不作一些遊戲。我歡笑,我奔跑,我跳躍,我因歡喜而歌唱。
散步就是一種自由,而要順帶一提的是,這樣的步行未必要在鄉下才能進行。我們偉大的城市也很適合步行。我每次赴倫敦,總會花一小時由貝斯瓦特(Bayswater,位於倫敦市中心)走到皮姆利科地區(Pimlico),漫步穿過海德公園(Hyde Park),沿著蛇形藝廊(Serpentine),穿過斯隆廣場(Sloane Square)。我看到的是多麼豐富的景象,並且做了多少的思考。我邊走,邊愛把自己想成flâneur(漫遊者),那種愛以蝸牛般的速度在十九世紀巴黎信步閒逛的詩人。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國哲學家)曾談到flâneurs,說他們喜愛以龜速漫遊,因為這種愛沉思生物的速度才是正確的速度。史蒂文森則主張獨自散步最好:
如果要適度的享受樂趣,步行之旅就必須獨自進行。如果有人陪伴,甚至雙雙對對,那麼散步就只剩下名義上如此;它已經化為其他的活動,而且其本質更像野餐。
唔,雖然野餐也不是壞事,但這並非重點。
火車已經遭到手機、筆電和螢幕的入侵,實在可惜。因為原本火車旅行是一種快樂的假期,擺脫工作和使人心煩意亂的雜務,如今你可以把你的公事帶上火車,或者在車上看電視,但原本你只有兩種選擇:閱讀,或者凝視窗外,兩者都是閒適的樂趣。抱歉,當然還有第三種樂趣:打瞌睡。火車和汽車不同,它鼓勵瞌睡。當然在火車上切斷一切機器設備,而且或許我們也該自我規範,關上手機,把筆電留在行李架上。
你即將要讀的這本書是丹‧基蘭基於二十年的閒遊所獲的心得,他緩慢的旅遊歷險乃是因為他對搭飛機的恐懼而來,逼使他不得不去尋找其他的方式,而那卻恰恰好讓他瞭解了旅行的真諦。如今他十分感謝他的恐懼,因為若非如此,他永遠也不會發現慢遊之樂。這當然並沒有使他的生活變得比較輕鬆。(而且我們也該再次強調,「閒」和「輕鬆」或「舒適」絕非同義詞。其實追求閒散,或者可說是自由的欲望,往往使人生變得十分艱難。)丹的朋友們可以輕鬆登上飛機,前往波蘭參加婚禮,他卻得搭火車往返。他的旅程或許艱鉅,但至少他在旅途中感覺是活生生的,至少他會邂逅人們,聽到他們的故事,看到搭機的旅客所看不到的風光。
是的,丹的確是知行合一。他最偉大的一次慢遊冒險,是在本書中有所著墨,他和兩名朋友乘著電動送牛奶車長達一個月的遊歷,而這次旅行真正的重點,是他和其他人因此建立了聯繫。你在機場能有多少邂逅某人而能攀談的機會?這次的經驗讓丹不再與社會疏離:他發現的事實和報紙讓你相信的正好相反,這個國家到處都是樂於助人的人,社群絕對沒有死亡。
本書最重要的主旨,應是歌誦未經計劃,徹底放手的旅遊。現代旅行,尤其是現代的假期,往往都需要精心規劃,按照時刻表行事。每一天都有特定的活動。我們有行程表、要搭巴士旅遊、是觀光行程。即使花了銀子抵達度假勝地的人,也免不了開玩笑說他們好像在戰俘營裡。但就如約翰生博士所說的:「再沒有比歡樂的計劃更掃興的事了。」計劃中的樂趣往往達不到事前的預期,而丹又很容易感受到觀光計劃不如預期時所產生的大失所望。或許兒童會喜歡這樣的假期,因為在水邊湖畔之類的地方可以享受到很多「樂趣」,這類的假期對家庭可能有其用處:丹並沒有提到,除了閒遊之外,他也熱中於中央公園(Center Parcs,1987年開始經營的度假公司,在英國共有4個大型度假村)度假村。不過我們並不能說這樣的假期和旅行有什麼關係,它們充其量只是休息一下而已。
不,在外玩樂最好的夜晚,和最好的旅行「經驗」,往往都未經事先的籌劃:偶然的邂逅、陌生人的親切、意外的發現。
如我所說,從沒有人說閒遊是輕鬆的事。本書中收錄了許多慘痛經驗的感人敘述,尤其刻骨銘心的是丹與兒子韋爾夫在布達佩斯冷得刺骨的公共浴池裡,莫名其妙犯下的失禮行為。丹的解決方法是他手上一定要有一本好書,不是傳統的指南,而是和他所赴之處相關的文獻或者傳記。如此一來,旅行對於丹就融入了文學和哲學性質的延伸思索,因而閒遊反而成為逃避的相反──它是內在的本質,如果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探究內心深處思想的強烈字眼,那就是“inscape”。
我們也可以說,閒遊和老式的朝聖之旅有更多的共同點,而不像現代假期這般暫停勞務,只顧追求逸樂。不論是像《天路歷程》(A Pilgrim’s Progress)中的「基督徒」那般獨自上路,或者像《坎特伯利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書中的故事真是有史以來最精彩逗人的假期)中成群結隊的朝聖者,這都是性靈的旅程。朝聖之旅是為了協助身為人的你成長,讓你重新與自己和他人建立聯結,治癒你自己的傷害。簡言之,這是一種療癒。
這正是丹的文學偶像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所讚美的旅遊。生於一八八一年的褚威格記得的世界,是把速度這種現代神祇當作是卑俗粗劣的世界。因此閒散才能讓我們再度躋身崇高之境,把我們由機器的插頭上拔下來,讓我們浸浴在混沌和自然之中。本書最美的篇章是丹敘述他去追尋獵鷹,和金鵰共處之際。丹主張,閒遊可以讓我們與曠野重新建立起關係,而那些地方正是布爾喬亞的世界一心想要關閉之處。
而最重要的是,閒遊,或許該說是「真正的」旅遊,喚醒了我們內心的詩人和哲人。我們全都是哲學家,只是現代生活眾多的憂慮讓我們忘卻了這個事實,我們追求讓我們分心的事物以擺脫痛苦,而不敢正面迎上前去。如我的朋友潘尼所說的,你吃了止痛藥,疼痛依舊在,只是你感覺不到。我們全都以酒精、藥物、情愛、紙牌、不同的癮頭、假日、奢華的飯店和旅行「經驗」,在我們的痛處敷上石膏,為的是讓我們承受它。可是閒遊者卻拒絕使用這樣的狗皮膏藥,而展開探索靈魂的旅程,就算他在旅程裡看到地獄,他也欣然接受,因為他同樣也會看到天堂。而在漫長而艱難的攀爬之後,景色將會是無與倫比。
第一章
旅遊不只是抵達而已
嘿,老兄,慢點,慢點。
電台司令(Radiohead)合唱團,「旅人」(The Tourist)歌詞
就像大多數人一樣,唯有在我把機場遠遠拋在身後之時,才覺得自己真正在旅行。由我所住的奇切斯特(Chichester,位於英國南部沿海)往倫敦的火車會經過蓋特威克(Gatwick)機場,在我們經過霍舍姆(Horsham)、克勞利(Crawley)和三橋(Three Bridges)這些越來越逼近機場的車站時,一股熟悉的期待之情逐漸醞釀。起先難以分辨我周遭的哪些乘客會在機場下車,接著我開始看到巨大的行李箱,等距離越近,大家也就開始坐立難安。我看著他們一邊咬指甲,一邊焦躁的看著點陣顯示幕上的車站名單。哪些人是商務旅客也越來越明白,他們因為突然有一連串電話,而曝露了自己的身分。他們虛張聲勢的談起自己雄心壯志的旅程,舌粲蓮花的描述明明是在鄉下機場附近經貿園區舉行的沉悶業務會議。掛了電話之後,他們大聲的嘆氣,轉向窗外,失望之情明明白白的凝結在玻璃之上。
在那之後不久,我可以聽到噴射引擎尖細的噪音,它的音量大到讓緊張的度假者都不由得帶著驚嚇與敬畏之情,瞪著中間的距離。穿著西裝的人們大聲呼氣,大家開始抱怨安檢程序,同時再做不知道已經是第幾次的檢查,確定他們的護照就放在隨身包裡。接著是一波波的動作,人人都忙著收拾袋子,拿起行李。
這些乘客臨下車之際,不由得開始激動起來,就像感覺到颶風即將來臨的動物一樣。商務旅客想要表現出見多識廣的模樣,但他們依舊不免不經意的晃動身體,匆匆穿過這場混亂。月台上眾多行李箱爭著要抬上電扶梯,但已經有一行由上一班火車下來的乘客等在那裡。終於最後一個袋子拖了下來,車門發出嗶嗶聲響關閉,車廂開始移動。
人人都上了月台。每一個人,除了我。我從不在機場下車。唯有當蓋特威克機場被遠遠拋在身後之時,我才知道我真正上路了。
* * *
就像每年由英國赴歐洲旅遊的數百萬人一樣,我也要前往西班牙的地中海岸,和那數百萬人不同的是,我要搭夜車去馬貝拉(Marbella)。
二十多年來,我從沒有搭過客機,寧可由陸路或水路前往各地旅行。大家都認為這事太稀奇,因此過去十多年來經各家全國性報紙的度假旅遊版報導多次,《新聞週刊》一度甚至感動得稱我為「慢遊的捍衛者」。
十年來,慢遊歷經流行興衰,幾乎永遠和環保議題扯在一起,我覺得此事倒很奇怪。我的確認為自己尊重地球──我做資源回收,並且盡量不浪費水,但我之所以照我的方式旅遊,真正的原因只是因為這樣更有趣,更享受。此外,如果我不慢遊,總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在旅遊。
顯然有時候到世界某地非得搭機不可,但英國人所作的國外旅遊,有百分之八十目的地都是歐洲,這些旅程竟有這麼多都是採取航空方式,倒教我驚訝萬分。飛機誠然是很了不起的東西,但隨著廉價航空和套裝行程的風行,我心裡難免覺得旅行變成了讓你低聲抱怨的苦差事,或者咬牙忍受的煎熬折磨。這讓我們不得不面對教人不自在的現代度假事實,矛盾就在於,正因為我們能這麼迅速在全世界移動,因此我們大部分人都不再是真正的旅遊──我們只抵達。
在倫敦的維多利亞車站(Victoria Station),我買了一些急救包需要的必需品,然後鑽進一輛黑色的計程車,讓它載我到聖潘克拉斯國際火車站(St Pancras),我要在此搭歐洲之星(Eurostar,連接倫敦、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等地的高鐵)。我訂了當晚由巴黎至馬德里的臥舖車票,次日一早再接另一班火車往馬貝拉。坐在計程車上的我開始覺得有點鬼鬼祟祟,彷彿自己正在逃學似的。所有搭機去的人現在都置身在人造光線照射的候機室裡,裡面滿是酒吧和無聊的精品店。他們得停止旅行,而成為一件貨品,在離境大廳內先經檢查所攜的金錢,然後再經過篩檢、秤重,堆放到飛機上的小小座位裡。他們很快就要搜查全身,看看有沒有槍械、炸彈和刀子,而帶著寶寶的人則得大口大口啜飲奶瓶裡的液體,證明他們擠出來裝在瓶子裡的母奶不含任何硝化甘油。
當然,儘管會發生延誤、得經歷安全檢查,如果他們搭乘的是廉價航空班機,還得要瘋狂搶一陣座位,但許多人還是很樂於接受這樣的運送方式,不過整個旅途上,他們的活動受限,大腦也塞滿了小螢幕上一再重複的熟悉圖像和影片。如此這般,幾個小時之後,他們就會被送到另一個機場。如今整個世界都是風行全球的品牌,一體同化我們生活的法則和觀念。由西方世界的家經由機場/購物中心進入飛機的人,在機上看了他們喜愛的西方電視節目,接著讓飛機在另一個機場把他們放下來,然後由計程車送他們到旅館──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家旅館,是因為它提供了西方食物和休閒娛樂。這樣的過程當然是一種行動,但你不由得開始疑惑:這樣做的人究竟有沒有到什麼不同的地方去。
一式一樣的機場出境班次告示板似乎也在欺騙你,而火車站的站牌卻喚醒我的想像力,教我夢想自己可能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可能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在聖潘克拉斯,我通過了安檢屏幕,二十五分鐘後,我已經在往巴黎滑行。歐洲之星是浪漫冒險擄獲我心的開始之處。我在倫敦住了許多年,總是難以抗拒長距離火車之旅帶來的心醉神馳感受。現在我才明白,這個城市是我開始對「慢」或「閒」遊的態度有所領會,讓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展之處。
* * *
我二十一歲時遷居到倫敦,在那裡待到三十三歲。剛赴倫敦時,在英格蘭鄉下小城長大的我非常緊張。一天,為了要在這貌似難以捉摸的龐大城市中找出我的方位感,我決定避開地鐵,只搭乘巴士。
由甲地到乙地,搭地鐵再快不過,在上下班時,這絕對是很有效率而且十分實用的作法,但如果要明辨方位,那麼地鐵就一點用也沒有。我很快就明白為什麼身為遊客的我會覺得倫敦如此教人肅然起敬。我有一些不同地點的記憶碎片,它們之間卻沒有明顯的連結。倫敦對我只不過是一些明信片圖畫的混合體,各自圍繞著──這裡就是重點,什麼也沒有。新聞報導說它是罪惡的淵藪,教我腦海裡的倫敦在恐怖和觀光客的刻板印象中飛躍。它所有的神奇和歷史,似乎都淹沒在滿面紅光的倫敦塔衛兵、扒手,和辛苦擺了一天姿勢拍照,總算能在硬石餐廳(Hard Rock Café)翹起雙腿休息一下的皇室成員之中。
而巴士之旅中,卻刪除這樣的感受,讓我能以新的方式發現這座城市,不只是實用,而且徹底改變了我在倫敦生活的態度。許多人看到原本可以搭乘超高效率地鐵,迅速融入大都會步調的我,竟然浪費這麼多時間在巴士上,說我簡直是瘋了,但我卻不以為然。我自得其樂,從容的花時間走過這城市的外緣,穿過所有的公園,把倫敦這一部分的結尾和那一部分的開頭串在一起;我發現在這其中似乎為人所遺忘的角落和陰暗的街道,我甚至也拼湊出城市所擅長隱藏的輪廓。
「去弄一份地圖來吧,笨蛋!」我聽到你喊道,但若沒有風景,沒有欣賞它們的方向感,地圖就一點也不實用。過了一年多,我對於地鐵載我去這城市的哪一部分,都覺得放心得多,很快的,我憑本能就瞭解了街道圖,連看也不用看它。這城市──即使如倫敦這麼龐大,這麼駭人,卻依舊成了我的家。
如今不論我到哪裡去旅行,都應用這個原則。只要能夠,我總採取較慢的路程,因為比起飛越海峽抵達目的地──不論那有多麼高效率,它都讓旅程和我所造訪的地方有更大的意義。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慢遊改變了我的心智解譯這世界的方式,而在本書中,我將說明慢遊怎麼讓你也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
第四章 擁抱災難
所謂不便,只不過是錯想的冒險。
GK‧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神學家),《論追帽子》
……
渡輪發出突突的聲音,渡過了廣大的水域,這時一陣強風灌進了莫爾灣。我們接近莫爾島時,滿月照得海面通明,讓我們很快就看到一樣有點教人擔心的事物。我們要去過夜的克萊格努爾和島的南半部一片漆黑,徹底的黑。他們依舊尚未恢復供電。我已經拋諸腦後的風暴這下又一躍回到我的腦海。我摸索著手機,致電給我們已經預訂房間的旅舍,想確定我們可以去住,但依舊沒有訊號。我想起先前我沒搭理的訊息和不熟悉的電話號碼,心裡一陣驚慌。
凱文和我下樓到冷風中,想要討論出該如何是好。要是旅舍停電,恐怕就已經打烊了,我們就沒地方可睡。那裡恐怕一個人也不會有,我們就會進退兩難。我們倆的手機都不通。渡輪當晚會由克萊格努爾再回奧本,因此如果必要,我們可以趕回來,但這就可能會破壞我們第二天看到鷹鳥的機會。我們先前選擇要待在島上人口較少的南部,就是因為那裡離一位當地導遊比較近,我們原本已經安排好讓他第二天早上來接我們。當時才下午五點,但我們步下渡輪時,天色暗得十分深沉而厚實,唯有反射在水面上的月光和來往汽車的車燈,讓我們能夠看到四周的景象。
幸好我們發現旅舍開著──其實是一直開著,看我們會不會現身。一群當地居民歡迎我們步入溫暖的燭光和爐火,一瓶瓶的紐卡索棕色啤酒(Newcastle Brown Ale)和一杯杯的威士忌傳遞過來,大家談起天氣都驚詫連連,一提到風力發電機因為風太大而爆炸,更是笑不可遏。他們認定我們會想住在托本莫瑞(Tobermory),也幫我們找好了房間,坐在吧台旁的人馬上提出讓我們搭便車的提議,但凱文和我覺得待在原處就很滿意,經歷了我們的旅程之後,在偏遠的蘇格蘭島嶼上的一家小旅社就著火光照亮被困在當地人們的對話,正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凱文對我咧嘴一笑說:「丹,這種慢遊的旅行──是不是一直都像這樣?」我們的主人似乎對我們決定留下來有點吃驚,但我們輪流和他們碰了啤酒瓶,讓他們感覺到我們的確打算待下來享受一下樂趣。
屋外,天空已經沒有烏雲,木星發出明亮的光芒,提醒了我們在宇宙間的位置,教我們為滄海一粟的宇宙洪荒而感到震撼。當你在如莫爾島這般的天涯海角仰望穹蒼,必然難以避免天地悠悠的感觸。當你抬頭望著浩瀚夜空中的群星,或者遙遠的恆星,想起宇宙中這樣的星星遠比地球上的沙粒還要多,那麼你把頭埋進雙手之中,因為「存在」的意義荒謬令人困惑而放聲吶喊,也就情有可原。
我總好奇我們人類這個物種究竟有什麼樣的成就。這個教人不安的想法在我們祖先的心裡必然更加重要,因為他們的時代是一旦太陽下山,唯一的光就只有來自火燄。在這種黑暗中過任何一段長時間,都會使你感到不自在,你開始明白你躲藏在那一片人造光中,讓你產生虛假的控制感,以為你既掌握了現實世界,也控制了心靈的天地。這種黑暗的感受,或者在它把你完全吞沒之時,你所覺得的心理威脅,不只是迷信、創造世界的神話、諸神和怪獸的繁殖場。我們或許自以為比南唐斯丘陵銅器時代建造古墓的人更先進,但他們與夜晚和群星依舊有足夠的連結,得以安排這些古墓的方位與夏至當天的太陽一致。我疑惑這個連結是否也讓他們對自己在宇宙間的位置更加誠實,更加正確。
* * *
在酒館裡,鷹鵰很快地已經成了主要的話題,我們的新朋友也七嘴八舌,紛紛對我們賞鷹的機會提出了各種建議,表達不同程度的悲觀態度。他們全都在談論鷹鵰,彷彿他們也是賞鷹族的成員似的。莫爾島上有三千多居民,其中許多似乎都很感謝這些鳥類對當地經濟的貢獻。人人對於該去哪裡看金鵰和海鵰(Sea Eagle)都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旅舍主人艾歷克卻警告他們不要讓我們抱太高的期望。他抱著一貫的沮喪態度:
「有一對夫妻客人每年都來我們這裡待一週,先生是攝影師,所以他喜歡淡季來,觀光客比較少。唉,他們今天早上才走,整週連一隻鵰都沒看到。」
他還強調他的悲觀論說,既然我們已經來了,他就要打烊回家了。雖然時間才七點,教人有點驚訝,不過早點睡覺對我們也沒有壞處。搖曳的燭光就像天然的安眠藥一樣,教人昏昏欲睡。關於鵰的消息雖然不符我們的期望,但到現在為止,光是到達那裡就已經教我們興奮莫名。艾歷克多給了我們兩條毛毯,並且表示希望電力很快就會恢復,一切就會順利多了。
黎明將近,我們依舊沒有電力,因此凱文和我在旅舍裡就著火光吃早餐。我們既激動又緊張,灰色的濛濛細雨落入莫爾灣,也浸濕了在晨光中等待導遊布萊安‧倫斯(Bryan Rains)的我們。他在幾分鐘後乘著白色的小巴士來了,雖然他熱情友善的招呼我們,卻難掩立刻要澆我們冷水的企圖。
「我們今天早上只有很小的機會,幸運的話只有幾小時。中午天氣就要轉壞了,接下來你們會什麼都看不到。」
我打定主意要保持樂觀,因此提到如果看不到鵰類,是不是可以看到其他野生動物。
「唔,最糟的就是抱定想要看某種特定動物的想法,尤其是鵰類,因為你們想看的別種鳥類棲息地在不同的地方。」
我還是不氣餒,因此向他解釋慢遊的觀念,只要你打算從容的運用時間,往往就會得到意外的驚喜。他揚起眉毛,只說了一聲「是」。
我們往克萊格努爾南方的山上走,布萊安說明我們最可能看到目標的地方有三個,因此我們應該直接前往。但我們很快就受到沿途景色的吸引。日出大約是在八點半,在曙光中,我們來到了當地人稱為三峽灣(Three Lochs)的地方,如果我以為從前曾見過阿恩海姆樂園,那麼現在我必然是置身其間。在向南山谷的北面,路略微向上升起,兩旁是莫爾島上兩座較小的的山,我們的右邊是本比伊山(Ben Buie)左邊是克瑞奇-比恩山(Creach-Beinn)。除了由大地、青草和歪歪倒倒的短籬笆柱構成熟悉的棕色斑點之外,眼前的景象是一片白的雪。我們身後的斯瓜班灣(Loch Sguabain)透過「踏腳石」向下進入遠處和眼睛高度相齊的三個水灣。天空飄浮著白和灰色的雲朵,映照著一波波紅色的曙光,你可以看到水的切面經由(Gleann a’Chaiginn Mhoir)到地平線山坡之外的洛赫比伊(Lochbuie)。先前只有在夏天來過莫爾島的凱文對這樣的變化十分吃驚。我們全都有帶望遠鏡,但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把它們拿出來賞鵰。有時候地球似乎會創造一個景物、光線和人的情感合而為一,渾然天成的時刻。
經過幾分鐘心滿意足的沉默,凱文說他好像看到什麼,於是布萊安拿出望遠鏡,他把三角架架好,把克瑞奇-比恩山頂下五十公尺處一小塊凸起的岩層納入鏡頭裡,他馬上輕聲笑了起來。
「那是一隻金鵰──好眼力,凱文。」
我忘情的把布萊安推開,盯著望遠鏡裡遙遠山側那一簇正在忙著的暗棕色羽毛。這鵰心滿意足的坐著,把頭轉來轉去,沒有要移動的意思。布萊安有點輕蔑地笑了。
「那不能算數──你幾乎看不清楚,而且牠也沒有展翼!」
但對凱文已經夠好了,對我也夠好。我直勾勾望著望遠鏡中的金鵰搖晃著身體,踏入空中,滑過山脊,往另一側下去。那是完美大自然的一剎那,遠比我所能想像的一切都要更好──正因為它的真實。
雖然我知道布萊安的努力是工作使然,不過他還是希望要讓我們能有比方才更好的體驗。如今賞鳥的壓力已經解除,我們可以盡情享受這一天。我們在下一個逗留地點沒看到什麼,但沿著葛蘭摩爾(Glen More)再往裡走,我們停下來,用布萊安的望遠竟又看到棲在山上岩石上的另一隻金鵰。我十分激動,但可以看出除非我們看「展翼飛翔」的鷹鳥,否則布萊安還是會認為這是失敗之旅。他眺望了我們周遭的山脊,我問他在找什麼。
「不尋常的現象,真的。如果你眺望地平線,就會看到不尋常的東西,雖然你不確定那是什麼。」
接著他放下雙筒望遠鏡,指著夸瑞岱(Cruach Choireadail)前的山脊正上方,喊著正往另一個方向看的凱文。
「兩隻白尾海鵰,牠們展開了翅膀。」
我可以用肉眼清楚看到牠們,但透過遠鏡可以更清楚體會到要讓這些巨大的鳥兒飛翔,需要多大的力氣。牠們的雙翼實在龐大。
「比你的身高還長的翼幅,可以達到二四○公分。不過這兩隻還是小鷹。」布萊安說。
我終於找到了龐然大物,不過雖然牠們在我的想像中翩翩翱翔,但在這裡牠們的雙翼卻是如此之長,使牠們的動作就像波浪湧現浪峰一樣。其中一隻消失在山脊之後,但另一隻卻拍翼降落在地面上,讓我看到牠白色的尾巴。牠豎起了自己的羽毛,黃喙和灰頭朝我轉來,顯露出小鷹的灰色胸膛。就連布萊安現在也顯得開心起來。
「那是白尾海鵰,是舉世體型最大的鵰。」
我轉向他問道:「你剛才一直都在嘮嘮叨叨說些什麼?這賞鵰是我們閒晃出來的結果!」他笑得直不起腰來。
* * *
置身在莫爾島的群山之中,我不禁覺得愛倫坡的阿恩海姆並非人因禁錮在大自然中,而發揮完美想像力的表現。艾利森的景色是一種譬喻,是在生與死的束縛限制之下,滿足的心靈在人的內在所能創造的世界。在故事前面,敘述者解釋他的朋友把他自己的快樂定義為他所謂四種幸福的條件:在戶外免費運動所得的健康、愛情、對野心的輕蔑,以及有一個「不斷追求的目標」,最後這個目標越是性靈,快樂感就越高。
在「《阿恩海姆樂園》的墜飾──《蘭多的小屋》中,我們更清楚看到這點,這個故事裡,一名旅人在迷人而我們已經熟悉的景色中,要尋覓一間簡樸而完美的房屋:「我可以想……某位優秀的風景畫家用畫筆創造了它。」他在其間找到一對戀愛中的男女,周遭盡是書本、藝術作品,和一瓶瓶各色芬芳的花朵。愛倫坡似乎是要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控制自己對於完美的印象,而逃避不讓我們達到想望的暴虐現實世界。不過我們做到這一點,不是藉著征服我們所存在的世界,而是藉著在我們的心中重新設計生命的重心,而那當然也就是阿恩海姆所在之處。對愛倫坡來說,這可以藉著旅遊美景、陷入熱戀、不為「明日」的雄心所惑,以及一生一世的追求表達自己的創造感。
雖然我很欣賞澤基的研究,以及他嘗試藉著神經科學的研究,由大腦實體深入探索它所能夠創造的天地,但說到旅遊以及愛和創造力─失去控制,超越你自己想像力的理解,才是一切的源頭。我認為這也是查特文在他的名言中所要表達的,他告訴我們:「人真正的家不是房子,而是道路,人生本身是一段必須要用腳去走的旅途。」
凱文、布萊安和我,那天早上又花了幾個小時尋覓莫爾島上的野生動物,布萊安果然說中了天氣的變化。可是到了下午,我們在克萊格努爾灌了幾杯紐卡索棕色啤酒之後,我讓他承認我對於慢遊和會有意外收穫的看法是對的。他沒法解釋我們在那短短不到四小時的時間裡所看到七種不同的鵰:四隻海鵰(包括「展翅」的兩隻)和三隻金鵰。我們也看到一隻母水獺和兩隻小水獺沿著斯克里登灣(Loch Scridain)的邊緣游泳,白嘴潛鳥、交喙鳥和無數的鵟,不過我們看到最精彩的景象就在天氣轉壞,迫使我們停下來之前。在一個我奉命不准透露的地點(但若幸運的話,布萊安可以帶你們去),他終於找到一隻棲在一株橡樹中的金鵰,在他的望遠鏡裡,我連牠眨眼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們甚至用他的望遠鏡和我的iPhone拍了一張照片,雖然我對照片抱著偏見,但現在它卻掛在家裡我書房牆上,那根羽毛的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