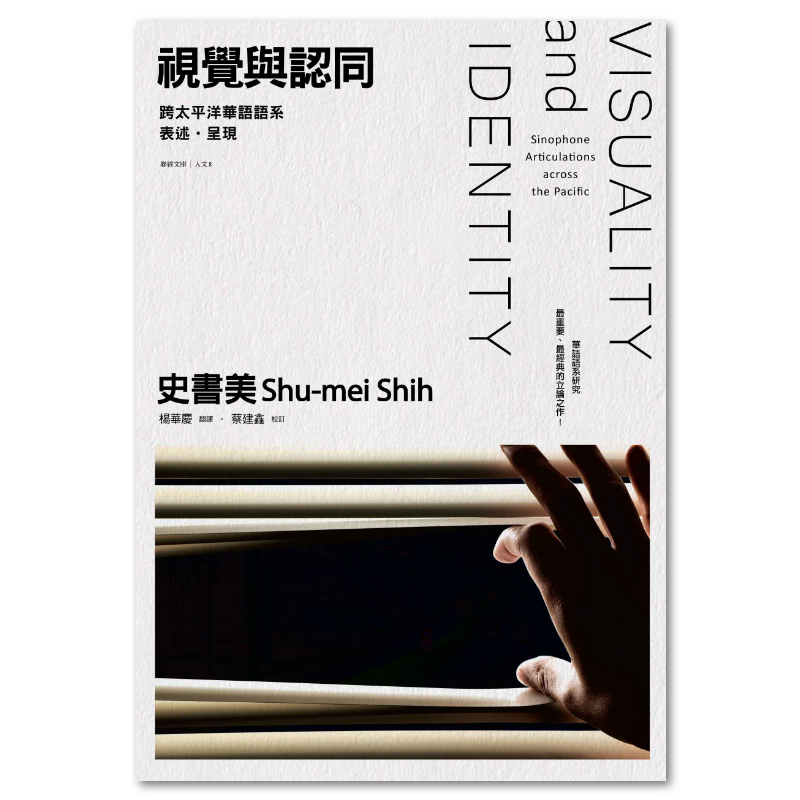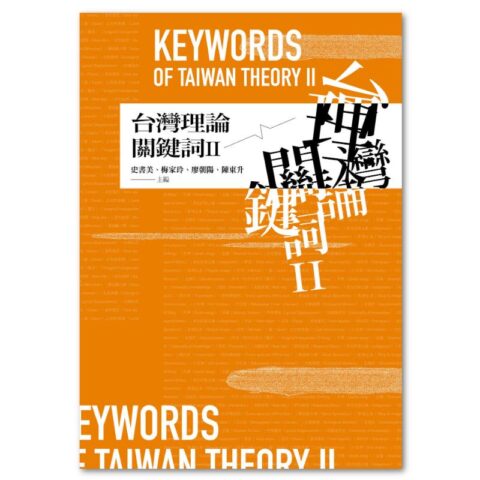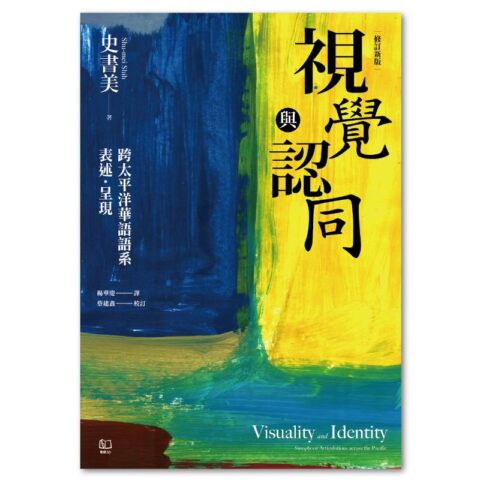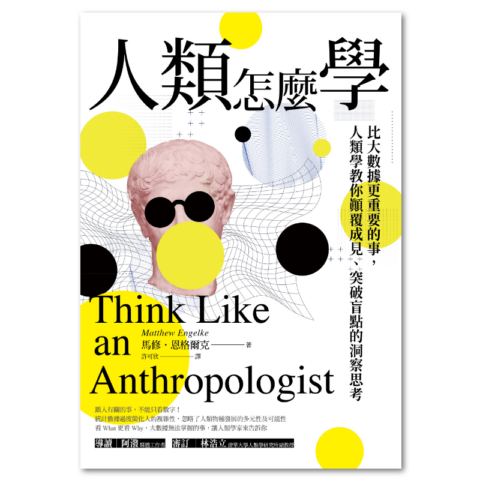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
原書名: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出版日期:2013-04-22
作者:史書美
校訂者:蔡建鑫
譯者:楊華慶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8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41572
系列:聯經文庫
已售完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何依霏(Margaret Hillenbrand)(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院副教授)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周蕾(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Firor Scott講座教授)
林文淇(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教授)
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美國奧瑞岡大學歷史系榮退教授)
梅家玲(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與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賀麥曉(Michel Hockx)(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廖咸浩(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廖炳惠(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台灣研究講座教授)
廖朝陽(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
劉大衛(David Palumbo-Liu)(美國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Louise Hewlett Nixon講座教授)
羅貴祥(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共同推薦(姓氏排列依筆畫順序)
「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中
這是一本最重要、最經典的論著!
漢學家史書美以華語語系概念
深入分析知名台灣導演、奧斯卡最佳導演得主李安的電影「父親三部曲」、《理性與感性》、《臥虎藏龍》
知名香港導演張堅庭的電影《表姐,妳好嘢!》、
陳果的「香港三部曲」(《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細路祥》
以及藝術家劉虹、吳瑪悧等人的藝術作品
作為海外重要華裔漢學家之一,史書美開創的「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乃建基於中國研究、亞美研究、離散研究和跨國研究之間,所進行的一種哲學性文化思考批評。此處所指的華語語系概念,包含了在中國之外使用各種不同漢語語言的各個區域,以及「中國」及「中國性」的邊緣的各場域。本書審視了「跨太平洋華語語系」──使用各種漢語的社群,如中國、台灣、香港和亞美等──的影像,如電影、電視、當代藝術、報紙和新聞的生產與流通等。
在《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一書裡,史書美認為視覺文化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下,調解主體性的主要方式。她在本書中審視了她所稱之為「跨太平洋華語語系」──當中包括使用漢語語言的社群,如中國、台灣、香港和亞美等──的影像,如電影、電視、當代藝術、報紙和新聞的生產與流通等。本書具有開創性地強調了所謂的華人離散研究,應該從漢語文化社群上做出概念化討論,而非拘泥於種族和國族的層面,不僅僅提倡在華語語系族裔的散布研究、族裔研究、區域研究與中國研究之間搭起橋梁,也希望能在法語語系、葡語語系、西語語系,以及英語語系世界中尋求共鳴。
本書共分六章,嘗試在華語語系與中國、亞洲、美國的跨國經濟文化關係和文化表述的互文脈絡裡理解華語語系的內含,檢視各華語語系社族群與中國的關係是如何愈來愈多樣化、愈來愈問題重重;以及此關係為何無法對地方、全球、國家、跨國、移居地及日常生活實踐等多角度、多元價值的脈絡中的華語語系表述和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提出了華語語系這個概念對不同的漢語語言的文學創作來說亦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分類方法。華語語系不但具有也同時包含視覺實踐與文本實踐的廣度,補足過去缺乏描述使用某種漢語語系語言的藝術家之學術語彙的問題。以往華語語系的藝術作品大部分只能以作者的民族出身來定義,而非以作品的地方脈絡和所使用的視覺、聽覺、文本語言來定位。
※ 名家讚譽
本書是全球學界首部有關華語語系研究的專書。
論證豐瞻,視野開闊,關懷深遠,是任何關心華語文學,比較文學,後殖民主義的讀者不容錯過的巨作。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以華語語系太平洋為背景,史書美為少數的文化生產提供了一個令人欽佩的國際視野。她對性別、階級、語言和文化政治的分析,正如她質疑中國中心主義般犀利。這是一個非常傑出的批評成果。
──周蕾(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Firor Scott講座教授)
史書美教授這部重要的著作創造了突破性的研究典範。「華語語系」(Sinophone)挑戰「中國文學」、「海外華人文學」「全球華文文學」、「離散文學」這些概念所隱含的假設和研究方法,提示讀者如何以兼具跨國視野與在地歷史脈絡視角來解析移民和人口流動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現象。
──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透過視覺媒介對「全球華語」(華語語系)的當代生產做出了創新及富啟發性的描述,為中國的文化和離散研究做出了一個重要的附註。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國奧瑞岡大學歷史系榮退教授)
本書由全球資本主義下「視覺性」與「身分認同」間的錯綜性出發,深入地思辨了「華語語系」研究的相關重要議題,層層剖析「中國(China)」、「中華/中文(Chinese)」與「中國性(Chineseness)」之間的盤根錯結,為當前的文學、藝術與文化研究開啟嶄新的思辨面向,發人深省。
──梅家玲(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與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是近十年來漢學、中國研究、亞洲與亞美領域中的重大突破,史書美教授以「華語」表達的新興議題,切入全球華人在世界經濟與文化體系所創出的新視角、新認同位勢,全書對全球化、弱裔論述、跨國性研究、大陸妹、新台灣電影、97年後的香港等課題,均有令人驚豔、眼光一亮的嶄新見解,這本書對文學、文化、電影、藝術研究者均是必讀之作,本人極力推薦。
──廖炳惠(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台灣研究講座教授)
在追溯「華人」主體性於全球傳播的光譜生產上,史書美大膽地拋棄了聯繫華人主體性的地方(種族)和身體(民族),並強調視覺(電影)和言語(語文和語言)才是現代和當代(主體性)歷史形構中最重要的標準。她傑出地完成了這項研究工作。
──劉大衛(David Palumbo-Liu)(美國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Louise Hewlett Nixon講座教授)
作者:史書美
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Irving & Jean Stone人文講座教授、比較文學系、亞洲語言文化系、亞美研究系合聘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文系榮譽講座教授。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陳漢賢伉儷講座教授,美國加大首任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講座教授,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等。華文著作包括《視覺與認同:華語語系呈現,表述》、《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合編《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和《台灣理論關鍵詞》。
校訂者:蔡建鑫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亞洲研究學系助理教授,與高嘉謙合編《現代中國文學》華語語系研究特刊(2013)。
譯者:楊華慶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學部畢業。先後於媒體、獨立藝術空間、文化機構等擔任翻譯、編輯及統籌工作。撰有視覺文化評論數篇,散見於香港文學雜誌《字花》。
謝誌
華譯本謝誌
導論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視覺性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身分認同
華語語系表述
第一章 全球化與弱裔化
理論政變的局限
彈性與節點
彈性和可譯性
第二章 女性主義的跨國性
認同斷片一:女性主義對抗中國父權制度
認同斷片二:自由主義對抗毛主義國家
認同斷片三:少數主體的對抗
認同斷片四:對抗西方凝視
第三章 欲望的地緣政治
腹背受敵的共同體
「大陸妹」的性別化
陰性化「大陸表姐」
性別與公共領域
第四章 曖昧之不可承受之重
「大陸」簡史在台灣
一九九○年代「永恆的中國」
二十一世紀的「親密敵人」
華語語系的艱難處境
第五章 國族寓言之後
寓言時間與城市國家
寓意與平凡
重塑香港性
第六章 帝國夾縫間的世界主義
帝國的年代與其規模
世界主義、多元性、危險
不可譯的倫理性
世界主義合乎倫理嗎?
結論 華語語系的時間與地方
導論(節錄)
我坐在小小的電影院裡和寥寥落落的十多個觀眾一起看著這部票價為二百五十元台幣的電影。電影院裡的座位只有八排,每一排約有十五個座位,可是許多座位卻仍然空空如也。當燈光暗下來,銀幕兩側門上的「出口」標誌燈閃爍著詭異的綠光。就像所有急著模仿台北市大都會腳步的市郊戲院一樣,這間戲院的音量調高到幾乎不能承受的程度。戲院外的街道上擠滿了商店與汽車,市面推銷著混合了求生與享樂的大都會中產生活:進口商品、鄉土小吃、路邊攤及廉價的享樂與服務。如果台北市的戲院為了強化電影的刺激效果,而把音量調到相當大的話,那麼中和戲院裡的音量便更為驚人。中和市的戲院不像台北市的戲院那樣生存得理直氣壯,只能焦急地誇大模仿首都城市的聲響,刺激觀影者的耳朵,以填補正當性的匱乏,同時還得與戲院外的熱鬧喧囂一拚高下。
惡劣的音響品質意外地讓這部電影中演員們所講的官話(Mandarin)的南腔北調顯得清晰無比,致使影像在建構幻象前,已被聲音徹底打破了。而台灣、香港、中國與馬來西亞的不同口音,則凸顯了地緣政治空間(geopolitical spaces)中的差異與張力,讓觀眾難以真正進入這個愛情故事。同時,高度美學化、視地心引力為無物的武打場景以及演員們仿古的念白詞彙與抑揚頓挫,更讓一切顯得格格不入。
所謂的「華語電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特別是武俠片,講述故事的聲音通常是字正腔圓的標準官話。如果演員的官話腔調不夠標準,大多會加以配音,以形成並維持大一統的「中國」整體性幻象。早期的台語電影只能算是一個孤立的個案,而當香港電影進口至其他華語地區時,則必須以官話配音。在《臥虎藏龍》這部影片中,演員們的口音非但沒有統一,反而呈現了許多地方的腔調。觀眾不免猜想:導演李安是否弄錯了什麼,抑或是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為這部片配標準北京話發音?更重要的是,這些南腔北調打破了大一統與整體性的表象。人物角色關係的發展和影片內情節的邏輯,都不能讓人信服。當飾演男主角的周潤發用他港式粵腔的官話喃喃說著情與義的偉大理想時,對說國語/普通話的觀眾來說,這些古典的抒情話語反而顯得彆扭,且不論那些貌似古典抒情的遣詞用字,根本是當代台灣連續劇與愛情小說中常見的語彙。
弔詭的是,不同口音的官話所產生的不和諧聲音,卻與街道中的雜音異響格外相稱。在聲音與噪音的喧譁之間,儘管充斥著不純正性與不一致性,生命卻更加蓬勃發展。中和市或許只是一個模仿,它或許永遠不會成為台北一般的大都會;對中和來說,這無所謂。此外,中和市大部分人口說的是台語,亦即閩南語,而非國語—官話。中和人與說國語為主的台北人不同,他們或許更傾向台灣獨立。
以不純正性與不一致性來描述這部電影與其背景再恰當不過,並且還能揭穿武俠片必定指向一個「永恆的中國」與「本質中國性」(essential Chineseness)的幻象。武俠電影源自於文學中的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則多半運用古典的用字遣詞與語法敘述偽歷史。然而諷刺的是,不論是武俠小說還是武俠電影,實際上皆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發展、乃至更臻完善。雖然武俠片起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但當1960年代與1970年代香港與台灣製作了許多武俠片經典的同時,中國仍是一個孤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弔詭的是,1960年代與1970年代台灣和香港對於所謂傳統中華文化的態度,與日後的數十年間比較,則抱有較少的矛盾情感。就台灣來說,「傳統中華文化」是國民黨用以合理化其在台灣統治的工具。中華民國在台灣(而非共產中國)保存並捍衛了純正的中華文化,也因此,外省人比起本地的台灣人—不論是閩南、客家還是原住民族群—更具有文化優越性。另一方面在香港,英國殖民統治讓香港人對中國產生了鄉愁。正由於中國安穩地鎖在「鐵幕」之後,香港和台灣因而能夠在大眾媒體中重塑傳統中華文化,以宣稱他們具有血統純正的中國性。即使對中國的鄉愁、重塑傳統中華文化與抵抗狹義上的大陸中國中心也許有些許矛盾之處(特別是在反共的議題上),但因政治考慮而被鞏固了的鄉愁論述模式,使武俠片成為傳統中華文化奇幻再現的重要形式。然而《臥虎藏龍》並不遵照再現純正中華文化奇幻的古法來製作電影,因此當電影在戲院播映時,華語地區的觀眾對其離經叛道的方式著實瞠目結舌。沒有任何一部武俠片甘冒得罪觀眾的風險,膽敢在電影中呈現不純正的南腔北調,因為觀眾對武俠片的認知與期待從未與時改變。可以預見的是,《臥虎藏龍》在各個華語地區放映時票房慘淡,直到贏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以後,電影才得以重新上映。好萊塢對《臥虎藏龍》的認可,正表明了中國、台灣與香港之間影像的交流與折衝,是在太平洋兩岸的文化政治領域中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進行。以下,我將討論「語言駁雜」(linguistic dissonance)的重要意義。
《臥虎藏龍》上的語言駁雜,正是華語語系中多種語言的異質性、以及華語人士分布地域多樣化的表徵。其所產生與認可的,正是我所謂的「華語語系」的眾聲喧譁(heteroglossia)。所謂「華語語系」指的是在中國之外、以及處於中國及中國性邊緣的文化生產網絡,數百年來改變並將中國大陸的文化在地化。《臥虎藏龍》所彰顯的是長久以來華語語系社群作為文化生產的重要場域,及其與「中國(China)」、「中華/中文(Chinese)」「中國性(Chineseness)」之間的盤根錯節。
更精確來說,在《臥虎藏龍》中演員們所說的中文是北京官話,亦即普通話,也稱作標準漢語,是中國主要種族—漢族的語言。據官方說法,除漢族外,中國尚有五十五個族裔(ethnicities)存在(中國政府稱之為「民族[nationalities]」),但獨獨漢語被定為標準語言。在《臥虎藏龍》裡,我們聽到四位主要演員所講的漢語口音各有不同。一種標準語言而有多重口音,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實際上在標準語言之外還有許多語言。《臥虎藏龍》直接地再現了現實生活的語言,拒絕掩蓋語言駁雜的真實,此足以推翻以標準語言達成統一的霸權想像。假使《臥虎藏龍》再現了一個時間上無法定義的「中國」以作為電影敘事與行動的舞台,那麼,就像中和市一樣,這部影片其實是由標準性及純正性的碎片所完成的仿擬之作。在此,中國性跨越了地理界線,影片帶領觀眾進入陌生的武俠世界,這個世界就像中和市戲院裡震天價響的音響一樣,喧噪且令人不適。華語語系也許是拙劣的仿冒品,也許青出於藍,但最重要的是,如此再現其實是很難被消費者接受的,因為成功的消費經驗必須是毫無瑕疵地融接單語(monolingual)的普通話(以北京為標準)、一元的中國性、或是大一統的中國與中華文化。華語語系讓過度簡化的縫合作用失效,並且力倡困難、差異與異質性的價值。
此處的重點是,仿擬之作永遠不會成為原作,而是一種翻譯的形式。仿作也許希望成為原作、或者與原作一較長短,但是這樣的期望實際上早已指出仿作與原作之間是有距離的—仿作是獨立的、經過翻譯的個體。翻譯並非甲等於乙的等式,而是在許多仲介/能動者(agents)、多元的本土文化與霸權文化之間發生,翻譯顯示了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有待在特定歷史時空中解讀。就在香港的英國殖民統治接近尾聲(現已完結)、台灣獨立意識抬頭與高漲、中國政經崛起、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以及移民到美國的藝術家與電影人重新形塑他們的中國性的情況愈來愈明顯之際,文化間互通有無與折衝轉圜的空間變得更為不定,華語語系表述也愈來愈清晰可聞。
如果中和市是國際大都會的仿冒品,那麼《臥虎藏龍》則是模仿帝國的失敗之作,因為它正正打破了整體性與一致性的幻象。以仿擬作為再現—亦即過去的模仿理論(mimesis),正好是華語語系文化生產的字面形容。因此,或許更加強烈的後設再現(metarepresentational),更能夠在現今無疆界的世界裡,正視不純正性,這也能解釋為何《臥虎藏龍》在美國如此受歡迎。於是,最主要的張力就此出現:當華語語系的作品勾勒出語言的疆界(此部分我將在〈導論〉後半部分詳細探討),視覺上的華語語系電影與藝術則面向全世界,並且對何謂「中華文化」表達了不同的立場。如此華語語系的視覺實踐無可避免地被置於本土以及全球的脈絡下。
《臥虎藏龍》在美國的接受方式,清楚顯示了語言與視覺之間的張力。對完全不懂北京官話的美國觀眾來說,他們對影片的了解僅能透過好萊塢式華麗的電影風格與英文字幕;此二者各自投射了一個大一統的語言與文化主體。他們分不清什麼是對美國觀眾來說,華語語系對中國性的顛覆,什麼是具有異國情調、優美的中國文化。兩者之間的差異在理解影片與觀賞影片的層次上都消失不見。一旦除去了語言的因素,視覺被當作跨語言、跨社群消費的可能性便自然形成。因此視覺逐漸成為表述認同掙扎的場域與工具,而且是一個廣泛且具感染力的媒介。對李安來說,華語語系之於中國性,正如同其中國性之於其美國性(Americanness):在不同的脈絡中,他的認同掙扎也有所分歧。在《臥虎藏龍》中,華語語系雜音(Sinophonic dissonance)可視作對大一統的中國性的抵抗;但是當面對大一統的美國性時,李安並不挑戰刻板印象中的中國性,反而是緊緊抓住它,這一舉動在《(囍+喜)宴》等影片中得以呈現。當中,再現的跨國政治經濟減低了透過特定的權力邏輯才能彰顯的複雜性與多元性,並將一國的國民(台灣人)變為少數族裔(台裔美國人)。
在再現與翻譯的行為中(從一個媒介到另一個媒介、從中心到邊緣、從中國到華語語系等等),多種脈絡(contexts)均有顯著影響,然而這些脈絡卻在全球層次上輕易地被抹去。全球化的脈絡堅持自己才是最大與最重要的脈絡,因此簡單地抹去華語語系的地緣政治特殊性與區域內的互動性(dynamics)。解讀《臥虎藏龍》之前,我們必須了解其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多元性(multiplicity),然而二者並不是分析與論證的終點(正如許多當代理論一樣)。像異質性這樣抽象的概念,很容易被普遍化而使論者忽略更深入的解析,因而成為全球多元文化(global multiculturalism)中無關緊要的邏輯。若要使用異質性與多元化的概念,我們就必須注意其歷史特性與位置,因為並非所有的異質性都具備相同的差異,也不是所有的多元性都一樣多元。此中的問題關乎內容與結構,而此二者經常隨著本土與全球的多重緣起(包括歷史、政治、文化與經濟等等)而改變。
在這裡採用佛洛依德式的「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oin)概念,是為了凸顯像「原欲/力比多」(libido)與「潛意識」(unconscious)是由許多不同原因造成的結果般,華語語系各地的文化也是由各種不同的因素形成。這些因素「可以組合成不同的意義序列,在特定的解讀中具有其一致性」。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言:「多元決定實際上不過是各種各樣的因素—是各種各樣、而非永無止盡的—進入了所有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而每一個歷史經驗的組成要素,都擁有各種—而非無窮無盡—的功能。」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亦曾將多元決定定義為「由多重因素決定」,以抗衡問題重重的單一經濟主義決定論。如此,多元決定論有助於分析「歷史中的各種狀況以及實踐上的複雜性」。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不同的脈絡中也認識到連續的與不連續的多元性,她以為「即使尚未提出歷史的理解與因果關係的問題,單單認識到時間當中的訊息序列,也足以預知並採取行動」。波娃連結了歷史的理解與主體性結合的可能性,從而使行動變為可能。因此,認識並創造出「華語語系」一詞就是一種實踐與行動,它能在時間與空間兩者之中留下「訊息序列」(intelligent sequences)。
在不同的脈絡中如何分析與理解華語語系的視覺作品,也是華語語系表述在全球化日趨熾烈的世界裡所面臨的挑戰。以視覺實踐作為認同實踐的確相當誘人,但正如李安電影所顯示,它亦有其危險之處。我們所處的現在這個時刻告訴我們:視覺作為認同的主要方式,已攀到前所未見的高峰,甚至可說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第一章 全球化與弱裔化
彈性與節點
若說國族父權的合法場域是第三世界民族國家,而性別化的弱裔化的合法場域是大都會民族國家,那麼同時置身於這兩個場域的人要如何在這兩個節點下運作?電影導演李安的情況是個有趣的例子,讓我們看見既是台灣人又是台裔美國人的他,如何以看似彈性的性別與種族政治實現彈性主體位置。我在下文探討的關鍵問題是:對一個人來說,同時是國家主體又是少數主體意味著什麼?在很大程度上,李安作為一個彈性主體的發生,與數十年來美國主義在台灣的傳播下所形成的美國文化霸權有關。受過台灣教育的台灣人必定具備對美國文化一定的認識。這些認識讓來自台灣的國家主體可以輕易轉變為在美國的少數主體。我在第六章會更詳細地討論美國主義在台灣的霸權地位。
小成本的「父親三部曲」(《推手》,1992;《(囍+喜)宴》,1993;《飲食男女》,1994)讓李安導演功成名就。這三部電影皆由台灣中央電影公司製作,在台灣都非常賣座,《(囍+喜)宴》更創下台灣影史票房紀錄。除了《飲食男女》之外,其餘兩部影片都以美國為背景,也都以文化或世代衝突為開始,以或多或少的和解為結束。在李安之前與之後,有許多移民題材電影的出現(較突出的兩部是羅卓瑤的《愛在他鄉的季節》和張艾嘉的《少女小漁》),但沒有一部獲得如此廣大的迴響和票房成績。李安電影的成功,引出有關意識形態的大範疇問題—文化的、政治的與性別的—而非有關風格與技巧的常見問題。在下文有關意識形態的評論中,我將揭露李安電影吸引台灣觀眾的特點:他對父權體制與父權性別政治的重新建構、對尖銳政治議題的迴避,以及將同性戀收編入異性戀霸權之中。接下來我會檢視這些影片如何另外吸引美國觀眾,並說明李安在他早期橫跨太平洋兩岸的電影裡,彈性再現的具體內容。李安後期的電影更細膩且批判地運用彈性,但是他早期的電影則不然。性別和國家關切的重心和權力不均緊密的關係,建構了一個獨特的文化政治經濟。我們可以李安早期的電影為範例,討論華語語系電影的跨太平洋呈現如何可能受制於這種文化政治經濟。
《推手》中,父親老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暴力抄家時,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在妻子與兒子之間,他那時只能選擇一人保護。作為一個好父親,老朱選擇保護兒子而非妻子,妻子後來死去。老朱對兒子曉生是全心奉獻的,因為他可以說是為了兒子而犧牲了妻子,也因此曉生任何一點忤逆都是不孝,甚至是要命的缺陷。曉生住在紐約,與白人女子瑪莎(Martha)結婚。當老朱來到美國與曉生同住後,他和洋媳婦之間的文化衝突以及不適,立刻成了曉生的不孝。曉生居中調解兩個不同文化,壓力非常沉重。按照故事的邏輯來看,客居異邦的父親永遠是同情的對象,影片也正面描繪其父權與父系定位。生動的例證是:他窺視孫子吉米(Jeremy)的陰莖,並以典型儒家父權口吻說那是傳宗接代的命根子。整部電影中,他與瑪莎的衝突也大多被歸因於瑪莎無法扮演好傳統媳婦的角色。對白人媳婦缺乏同情的呈現,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三部曲中唯有這一部未在美國公開上映。老朱作為美國移民是可悲可憫的,但他的道德正義(為他對曉生無私奉獻所支撐)、高深的太極造詣,以及個人魅力(一位來自台灣的優雅寡婦愛上了他),沖淡了他的可悲。中國(老朱)與台灣(寡婦)之間任何潛在的緊張,都被一種共有的文化中國性的辭令所掩蓋,一股泛中華(pan-Chinese)的同情感反而油然而生。24在這裡,華語語系被誤等於某種泛中華文化主義。相對於白人美國,所有華語語系人口都成了「中國人」。這是三部曲中唯一一部將主體位置與國族主體如此貼近(儘管是放在一個政治上相當可疑的「大中國」之下)。
《(囍+喜)宴》中,同性戀兒子為了取悅從台灣來訪的父母,必須上演一場異性戀婚禮。高偉同的白人愛人賽門(Simon)扮演了父權家庭中媳婦的陰性角色:他為偉同的父母購買禮物、下廚並照料偉同的父母,他亦知道偉同的每樣東西的收放所在,恰如一名好的家庭主婦。而且建議偉同與來自中國、需要取得綠卡的葳葳假結婚,以贏得偉同父母的認可的人也是他。初次與偉同的父母見面時,賽門表現得戰戰兢兢,正符合中國習俗中羞澀新嫁娘的角色。這裡建構的是一段三角戀愛故事,兩個女人(葳葳與賽門)在異性戀欲望經濟中競逐偉同的愛情。影片將同性戀如此收編於異性戀麾下,因此香港影評人劉敏儀便認為《(囍+喜)宴》並未完全顛覆異性戀霸權。想當然耳,這齣喜劇點明父親總是最後的贏家:如果父親一如既往要的是異性戀,那便只有照做。影片最後我們得知父親其實一直都知道偉同與賽門之間的同性戀情,但他在偉同與葳葳圓房前仍假裝不明究理。葳葳懷孕後,父親得其所願,才告訴賽門他接受他與偉同的同性戀情。透過台灣觀眾眼中善意的欺騙,父親的權威獲得確立。影片顯示出父親有能力以彈性手段處理預期之外且違背傳統的挑戰。
《飲食男女》與《(囍+喜)宴》類似。影片看似是一個女性中心的敘事,表面上三個女兒的愛情故事主宰了敘事,但最後仍將女性所處的位置回歸廚房,這一點早有論者指出。鰥居的老父(仍由《推手》與《(囍+喜)宴》中的郎雄飾演)最後以低調的姿態現身為英雄。他的三個女兒在情海浮沉,而他卻默默地與女兒同輩的錦榮滋生愛苗。最後父親出人意料,竟然娶到了錦榮(對父親亦有好感的錦榮母親,梁太太,尤其驚訝)。影片最後幾幕中有一幕是他大腹便便的新婚妻子坐在他們現代化公寓中的一張搖椅上。梁太太對他的好感反倒確認了他浪漫與年輕活力,相形之下梁太太的殷勤則太過歇斯底理,令人喘不過氣。他的三個女兒諸事不順的愛情則突出了他的男性雄風與生育能力。最終,事業心最重、擔任航空公司主管的二女兒家倩回到廚房,透過她的廚藝,讓父親重新尋回先前失去的味覺。三部影片的結局都將榮耀歸於傳統父權體系,在我們看來這個父權似乎更能在必要時刻,透過彈性手段與「善意的」欺騙來壓制挑戰並重新確認其正當性。正如辛西亞‧呂(Cynthia Lew)言簡意賅地定義:這些是有關「起死回生的父親」(resuscitated patriarchs)的故事。
此外,還有其他原因讓這些影片在台灣如此賣座,並且贏得台灣觀眾持續不歇的欣賞與忠誠。儘管李安並未表達過任何有關台灣獨立的本土主義情懷,但李安的成功被視為台灣的國家榮耀。他的名氣被視為台灣在全球文化場域中上升地位的反映。《(囍+喜)宴》和《飲食男女》連續兩年在柏林影展贏得眾家垂涎的金熊獎,他的影片在國際上獲得的注目是台灣影史上前所未見的。更甚者,同性戀是西方先進文明的另一個標誌:觀賞有關同性戀的影片,讓觀者得以躋身全球公民之列,而這個對同性戀的再現也經過重新包裝。事實上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對同志的友善(gay-friendliness)已經成為台北的賣點之一,也構成了台北都市魅力的一部分。對一個亟欲獲得國際社會認可並接納的國家與城市而言,同性戀甚至可能是一種策略,只要它能夠與地方父權體系共存即可,儘管其採取的手段可能非常曖昧。
這些影片因而成為「國家的」再現,是台灣全球化成功的典範,可以幫助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飲食男女》於1994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後,台灣政府發動了廣受媒體注目的推廣活動,包括為數百位好萊塢人士安排盛宴,準備了片中華麗呈現的美食佳肴,而且大廚與原料都從台灣原裝進口。李安本人也助長了這種民族主義胃口,在針對台灣觀眾的訪問中表示很希望能贏得奧斯卡獎,為台灣爭光。到了1996年,《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 1995)未獲最佳導演獎項提名,引來美籍華裔影評人盧燕與非裔美國人領導人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分別指控金像獎委員會種族歧視,李安則對台灣支持者表示極為抱歉。之後他承諾下一部開拍的華語片將贏得金球獎與金像獎最佳外語片,他表示自己「必須為華人電影贏得這項殊榮」。後來他也確實做到,在2001年以《臥虎藏龍》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他曾指出,自己熱切期望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讓父親高興。李安過去未能通過在台灣社會裡被父母用以衡量個人價值的大學聯考,拍攝《推手》前又當了五年家庭主夫,沒有穩定工作或任何工作前景。因此李安渴望獲得父親認可,也渴望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獲得國際認可。在個人的、心理的層面上,我們都可以看到父權體系與國族主義的重疊。
倘若父親三部曲清楚呈現了國家主體的觀點,那麼它同時也顯著地呈現了出自少數主體觀點的文化再現。當中有可消費的異國風情(consumable exotica)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刻板再現:飲宴習俗、外來餐飲、情色與異國女性、太極動作等等。然而,這種軟性多元文化的電影再現所牽涉的,不僅僅是民族文化的弱裔化,也可稱之為台灣的弱裔化(the minoritization of Taiwan)。李安本人顯然也認知到這樣的隱藏意涵。他在《時報周刊》1993年的訪談中提到,今日台灣人的西化程度與美國華人移民一樣,而兩者都希望在西化的同時保留中國的家族主義(familism)與儒家倫理。他指出,「在西化的過程中,台灣人已經做了移民會做的許多努力。雖然他們的身體不在美國,但他們是心理上的移民(psychological immigrants)……住在紐約的法拉盛與住在台北有什麼不同?除了前者對美國認識較多、看到的美國人比較多之外,其實沒有什麼不同。」按照李安的洞見,西化無可避免地將身在本國的台灣人變成了心理移民,所造成的效應就是台灣的弱裔化,因為它必須遵從美國的文化霸權。文化生產與消費日益頻繁的全球交往,不僅使國族文化在美國境內以多元文化之名而淪為弱裔地位,也使美國境外的台灣成為美國的弱裔「區域國家」(region-state)。因此,無怪乎有些台灣人戲謔地稱台灣為美國第五十一州了,畢竟台灣公職人員有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畢業自美國大學。而於1994年7月4日成立的「五一俱樂部」更是認真並有組織地追求這個目標。五一俱樂部的標語是「立足台灣心懷美國」,提倡將台灣變為美國第五十一州,據說這個建議最初是由美國中國歷史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提出。該俱樂部的終極目標是號召台灣就加入美國聯邦一事舉行全民公投,如果獲得多數台灣公民同意,再將提案交付美國國會。
李安影片中將中華文化作為族裔文化(ethnic culture)並將其弱裔化。這個弱裔化的一部分也與中國菜餚的戀物化(fetishization)有關。《飲食男女》開場中,李安用了大約五分鐘的時間來呈現精緻中國美食的準備過程。影片上映後,《紐約時報》刊登了美食作家蘇珊‧哈姆林(Suzanne Hamlin)有關片中食物的兩篇文章,當中附有「炒海瓜子」的食譜,也提示在紐約哪一個中國餐館可以找到影片中的美食。有個例子特別生動:「要享用《飲食男女》中出現的菜餚,請事先預訂。西65街43號的Shun Lee West餐廳,電話(212)595-8895,可以準備影片中十四道菜餚的任何一道,但請提前十二小時預訂。」這段文字捕捉了從外來到本土、從國族到族裔的奇異轉化;這個挪移發生在台灣與美國之間,仲介正是中國菜餚。李安似乎也全心全意支持這個轉化—他自己就去了紐約這家中國餐館,在一整桌豐盛菜餚前為那位美食作家留下了身影。
此中國菜餚的戀物癖在多元文化美國亦遭到了性別化。特別能說明這個狀況的是,在《飲食男女》的台灣電影海報中,讓人肅然起敬的父親出現在前景中(因為重點是父權體系的起死回生),而美國的電影海報則僅呈現三姐妹與一道美麗可口的中國菜—一幅「秀色可餐」的具體寫照。一位影評人指出,「這部電影中的人物幾乎與食物一樣好看。一道接著一道:女性一律窈窕、精巧而活潑;男性都英俊而慵懶,等著被這些女人喚醒。」還有位影評人說:「片中呈現的每頓飯都讓人口齒生津,而三個女兒也同樣讓人垂涎。」將可口、誘人、可享用等食物的隱喻轉移到女性身上,也剛好符合這部影片所屬的情色/飲食類型電影。但更重要的是,影片強調了異國女子的情色化,而情色化就在亞洲女性被性欲化(sexualization)的刻板模式中運作。此事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因此,父親三部曲透過父權體系的起死回生,體現了民族主義者對台灣觀眾的呼籲,體現了台灣對國際聲譽的渴望同時也強調了異國情調以獲得美國觀眾肯定。對台灣觀眾而言,這三部影片是國族的建構,儘管這「國族」有時必須保持模糊,因為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在電影中混沌不明。對於美國觀眾,三部影片代表了國族建構被轉化為可消費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弱裔化過程。表面上,國族主體與弱裔化主體的位置相互矛盾。但細看之下,李安其實聰明地壓抑了可能的矛盾。在三部影片當中,父親角色都處於美國的性別邏輯之外。他們垂垂老矣,他們是其他亞洲女性的愛慕對象,而且他們對支配性的男性化與女性化的結構不會構成任何威脅。唯一有魅力的亞洲男性角色,即《(囍+喜)宴》中的偉同,也適當地被陰性化為男同性戀者,因此不符合規範。因此,令人好奇的是,讓台灣觀眾為之流淚嘆息的父親角色以及他的愁苦,絲毫不會影響美國觀眾偷窺的樂趣。國族主體與少數主體成功融合。更有甚者,有充分證據顯示了透過異國風情與情色,中華文化弱裔化在台灣成為一種趨之若鶩的消費手段,這證實了薩依德(Edward Said)所憂慮的危險和誘惑:被宰制者將文化宰制者的東方主義結構加諸己身。
從台灣與美國雙邊政治關係的角度來看,國族與少數族群的建構,就像台灣的國族命運仰賴美國一樣,兩者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毫無疑問地,台灣—一個不受國際認可的國家、一個非民族國家的國家—就像是美國的殖民地或者是少數族群的一個州,台灣政府與人民對於美國有關台灣的言論無時無刻都保持高度關心與警戒。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於1998年訪問中國時公開宣布支持三不政策—「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也不支持一中一台。並且我們不認為台灣應當參與任何需要國家主權獨立的國際組織」,說明了台灣如何成為中美關係改善下的犧牲品。美國對於台灣命運的主宰力量,以及中國對台灣的圍堵政策,除了是一種新殖民主義之外,還有其他說法嗎?對中國與美國而言,台灣不過是一個應受圍堵的少數弱勢,是在超級強權的權力關係中一個可以任意丟擲的骰子。一方面,美國共和黨政府利用台灣作為反制中國的力量,儼然是冷戰政策的延續,並且與當前崛起的中國威脅論相互結合。另一方面,美國民主黨政府則始終把台灣當作工具,好跟中國有更多接觸。不論是哪一個情況,台灣都是白宮因應需要,用以抵制中國或與中國交好的籌碼。
當李安在父親三部曲獲得成功,開始進軍好萊塢之後,他作為少數主體的位置終究無法避免。他所執導的《理性與感性》受到一致好評,被譽為是大師之作,因為「一個來自台灣的導演」竟然能夠精準地描繪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甚至讓查爾斯王子大嘆,在女王皇宮的皇家首映之前,他實在不知道英格蘭有這麼美。李安利用了許多彈性的策略,透過翻譯隱喻的召喚,來合理化他參與製作這部電影。當面對台灣觀眾的時候,李安告訴他們雖然這是一部英語電影,但是因為他在台灣成長,所以他以華語片的方式來執導。面對西方觀眾時,他則再三強調那些古老的觀念,如禪宗無為、儒家道德、太極(事實上,他在拍攝期間教了凱特‧溫絲蕾[Kate Winslet]太極拳)、「家庭價值」、儒家的仁與禮等等。李安的理由如下:
在珍‧奧斯汀(Jean Austen)的世界裡我覺得很自在。因為現今中國人的社會還處於從封建文化與孝道文化進入現代社會的轉型期。在許多層面上,我認為當代的中國人比現在的英國人更能夠理解十九世紀的英國,因為我們仍然還在那個時代裡。
我試圖在我的電影中融合社會批判與家庭倫理劇(family drama)。我終於注意到我長久以來都是為了拍攝珍‧奧斯汀的故事而做準備。我命中注定要拍珍‧奧斯汀。我只是需要克服文化的障礙。
時間的線性概念把當代「中國性」(Chineseness)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等同起來,這是他在第一段引文中的論點前提。也就是說,中國性等同於過去的、等同於非現代的。在第二段引文,他想到自己跟珍‧奧斯汀的藝術命運相仿;因為他對中國傳統主義的熟稔,他才有了真正憑據,得以拍攝有關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的電影。在個別的訪問中,他視中國女性纏足為殘酷的中國傳統,並暗示了西方現代性的解放意義。同樣地,西方電影評論家也需要合理地詮釋為什麼李安可以把英國的題材處理得如此出色,因此訴諸於象徵性的代表(tokenization)或模範少數民族論述裡,所經常為論者引用的普遍性的概念:李安擅長描寫兩代關係、家庭問題、微妙的人際關係,同時他也「非常理解社會禮儀的壓力」,以上這些都是所有文化的共通之處。因此,一位評論家把《飲食男女》稱之為「奧斯汀的敏銳與中國菜餚」(Austen-like acuity with Chinese food)的完美結合。
兩種可譯文化之間的流暢的結合,究竟可以為我們描畫出什麼性別啟示?可譯性(translatability)有什麼性別位置?換種方式來說,當導演著迷於父權制的復興,並且最終拍製出批評英國父系財產繼承法律,類似半女性主義者(semifeminist)電影時,當中的過程透露了什麼信息?李安電影內有關少數性別的暗示,可以在電影的製作和觀眾反應兩部分中察覺。首先,它排除了李安對影片成功的貢獻。雖然《理性與感性》獲得倫敦影評人協會獎及紐約影評人協會獎,而且橫掃了金球獎最佳編劇和最佳戲劇獎,更在奧斯卡獎獲得七項提名,但是李安最終沒有獲得金球獎最佳導演獎,亦沒有得到奧斯卡最佳導演的提名。我認為這就是彈性的終結。說穿了:種族主義無視李安的彈性策略和他受到大眾的喜愛;這二者在意義生產的關鍵時刻裡無關緊要。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性別和種族弱裔化的行為,正是一個停滯的時刻、是一個節點,是流動的終結。即便不從種族主義觀點出發,李安沒有獲獎一事還是殺傷力強大:這表明了李安不同於那些被提名的(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攝影、最佳服裝設計和最佳音樂)電影共事者,他不過是眾多用來製造機器的螺絲之一,他只不過幸運的被製片人(最佳電影獎的指定接收者)僱用,是製片人而不是他做得好。他僅僅是一個僱員,而不是把電影拼湊在一起的原創藝術家。一個評論家明確地指出,「李安對珍‧奧斯汀從不著迷,在被聘用拍攝愛瑪‧湯普森(Emma Thompson)的劇本前,他從未看過珍‧奧斯汀的書」(黑體字為作者強調)。
我們無須驚訝這個電影評論家,即格拉漢‧福勒(Graham Fuller),在他深具影響力的《視覺和聲音》(Sight and Sound)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說道,湯普森才是影片成功的功臣。我們也無須驚訝觀眾不一定會相信影片結尾「電影由李安拍攝」(A Film by Ang Lee)的功勞鳴謝。在分析了父親形象在電影中缺席的問題後,福勒指出大女兒愛蓮娜(Elinor)承擔了女性被剝奪權利的達斯伍家的「男性地位」和敘事上的「英雄角色」。他延伸了這種說法並得出了一個結論:湯普森是「《理性與感性》的作者(auteur),亦是女權運動者(Suffragette)和英雄的『男性』代理人」。湯普森自己記錄了她與李安在拍攝電影期間的小衝突:她和其他演員在如何拍攝的問題上與李安存在意見分歧,據說李安「深受傷害和困惑」。不同於台灣那種「導演可以隨心所欲」的拍攝方式,或是李安習慣的「有椅子、菸灰缸、濕毛巾、熱茶侍候」的款待,英國演員膽大包天勇於挑戰李安專橫的導演方式。湯普森指出:「和李安一起很容易感到被欺負」;而「休‧葛蘭(Hugh Grant)亦稱他做『狂人』(the Brute)」。李安開始成為東方專橫和東方式寧靜的完美結合物,他獨裁之餘還教攝製隊東方儀式(包括冥想、太極和祈求好運的開拍儀式)—這一切都典型地帶有「東方」色彩,與典型的專制、異國情調和靈性相輔相成。然而影片即將殺青之時,李安不再專橫,而成了一個民主的導演,他不但聽別人意見,而且還購買香檳和中國食品給工作人員。由此看來,李安的好萊塢首作《理性與感性》的拍攝過程及觀眾接收,涉及了馴悍(taming of the shrew)、專制者女性化和國族主體弱裔化(minoritization)的課題。
《冰風暴》(Ice Storm)上映同樣引起話題,李安作為亞洲導演的信譽也再次受到考驗。這部電影的背景是1970年代的美國。隨著《理性與感性》的成功,李安理智超群的指導方式(正如上文所述)相對於他對奧斯汀的鑑賞力而言,毫不遜色。但評者並不認為《冰風暴》跟《理性與感性》一樣兼容並蓄。在1997年的坎城電影節裡,法國評審將《冰風暴》當成好萊塢的商業片,同時美國影評人也認為電影沒有真實再現美國。當李安試圖翻譯的並不是遙遠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而是1973年新英格蘭(New England)的家庭問題之時,美國影評並不樂於給予讚賞。或許,這個距離太近了,令人無法感到自然舒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