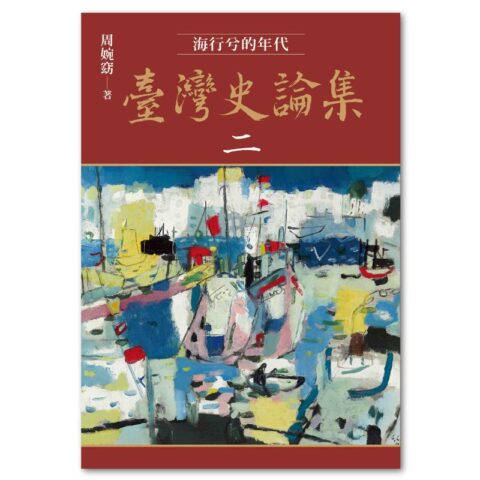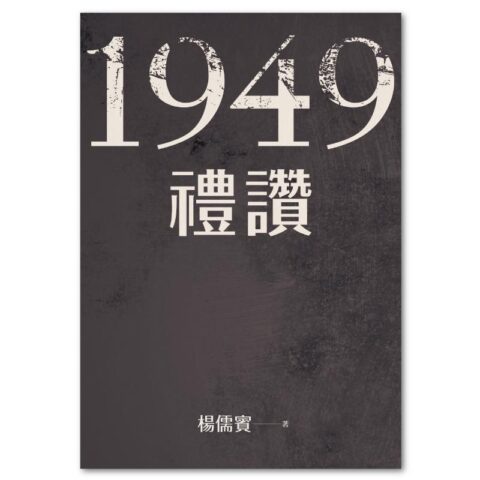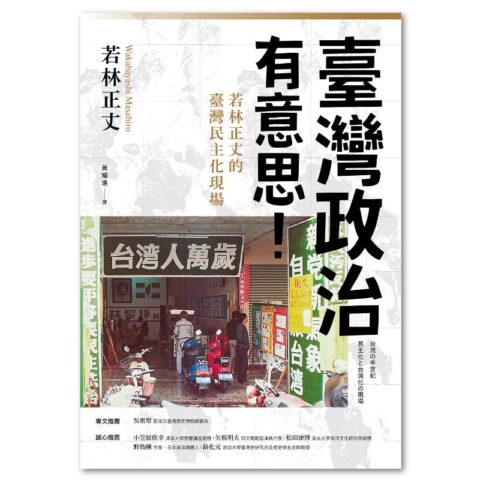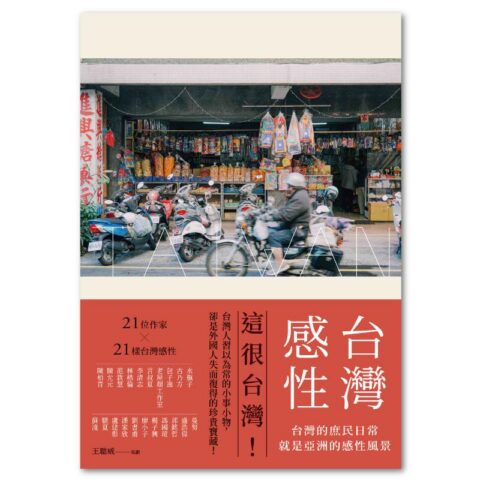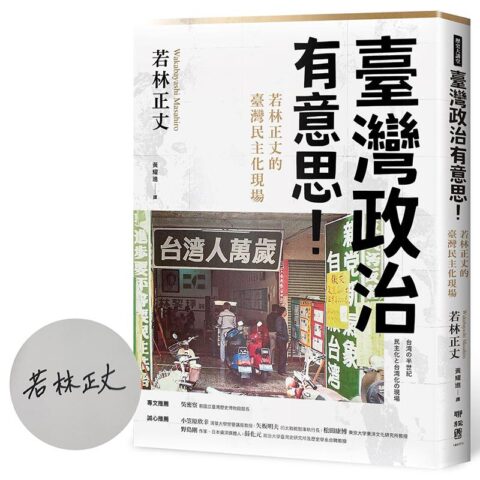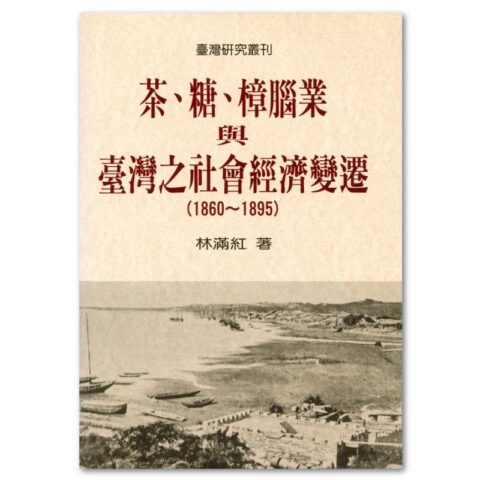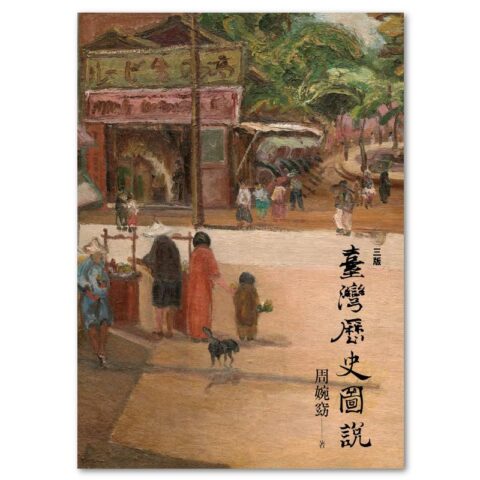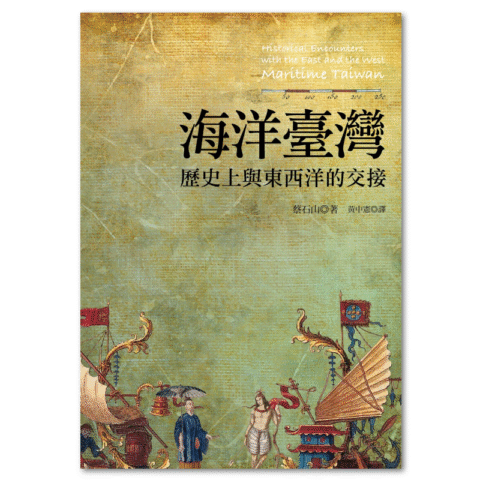台灣史:焦慮與自信(思想16)
出版日期:2010-10-06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6868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本期的專輯「台灣史:焦慮與自信」,有許雪姬的台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探討因論述多於考訂,造成史家失去了應有的技藝,使歷史學成為沒有特色的學門;有莫達明的台灣本土史學的建構與發展 (1972-2004),討論民主轉換與台灣人民自決之嚮往解釋了1980年代由台灣史學所帶起之轉折點,敘事方式漸次擺脫地方史的範疇,逐步地趨向國家歷史的類型。有張隆志的婆娑洋畔、美麗島間:學院台灣史研究札記,探討學院台灣史家面對當代台灣史高度政治化的言論情境,以及國族建構、後殖民差異、轉型正義與全球化等實踐課題,如何超越歷史時空錯置和狹隘地域心態?也有楊照的建立衡量台灣史深度與廣度的標尺,述及台灣史可深可廣,然而我們到現在都尚未真正針對台灣史,建立一套衡量其深度廣度的標尺。本期還有「思想評論」、「思想訪談」、「思想人生」、「思想采風」等多篇精采的文章,提供讀者更多樣的思想風貌。
致讀者
當前臺灣人文學術領域中,論本身的活力、論牽動的人力與資源、論對於社會的移風易俗影響,文化研究與臺灣史乃是最為搶眼的兩個學門。這兩個學科的發展,也與過去二十年來臺灣政治、社會的變動有最密切的關連。沒有解嚴與開禁,文化研究的存在很難想像;不經過本土化雷厲風行,臺灣史也恐怕只會繼續活在陰影之下。但是隨著這兩個新興學門力求學院化與體制化,它們與社會的有機連帶也隨之鬆弛變質。《思想》自許為學院與社會論述的中繼站,繼前一期推出「文化研究:游與疑」專輯之後,本期轉而呈現臺灣史研究的「自我形象」:我們邀請到幾位在臺灣史研究第一線的學者,面對專業之外的讀者,敘述臺灣史學的體制發展與學術成就,更表達他們個人的親身感受,從而呈現臺灣史這個領域的精神氛圍與知識態度。
不無猶豫地,我們用「焦慮與自信」來形容臺灣史家的心路歷程,試圖捕捉這裡所謂的氛圍與態度。從局外人的角度觀察,臺灣史的從業者比起一般史學學者,似乎更在意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正當性、乃至於自己無論有意無意總難擺脫的政治意蘊,於是不免顯得急於辯解。但另一方面,臺灣史學家具有的使命感與承擔感,似乎也比史學其他領域更為濃重,其自負與抱負都很難以狹義的學術意義為界線。當然,歷史研究的意義本來就不會侷限在學院之內;不過,由於臺灣史的新生地位、由於臺灣本身的歷史之曲折、今日處境之曖昧,臺灣史所承載的負擔確實比較沈重。所可喜者殆為,在這種種張力的拉扯之間,高度的自我意識反而正可望帶來益形豐富的歷史智慧,即使必須以焦慮與自信來形容,也仍不失為健康而有益的。
在台灣之外,本期發表高力克、成慶兩位先生的評論,以及許紀霖先生的訪談,多少都聚焦在當前中國大陸上文化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強勁發展趨勢。與中國過去百年的激進、啟蒙思想主流對照,今天左中右各種思潮均匯流於保守價值觀與「中國模式」思路,的確是別開生面的新生事物,值得深入理解與公正的評價。當然,這些發展有其明確的客觀條件,也就是中國崛起這個巨大的歷史現象才是背後的主要動力,不過思想本身的轉折究竟受制於甚麼內在邏輯,也值得分析梳理。針對中國大陸在客觀形勢與思想潮流兩方面的動向,我們都會繼續邀請大陸的知識份子來為文討論,與臺灣的關心者對話、攻錯。
八月間,美國的朱特與中國的謝韜兩位先生先後去世,本期特別邀請朱特的中譯者章樂天先生和謝韜的好友陳子明先生撰文紀念。朱、謝生前並無交集,經歷也沒有相似之處,相提並論似乎有些牽強。但是,晚年的謝韜在中共黨內呼籲恢復從馬克思、恩格斯到社會民主黨的正統,拒絕列寧主義來自「左邊」的篡奪;朱特於去年十月以癱瘓之軀發表最後一篇演講,呼籲大家珍惜社會民主在二十世紀的重大成就,戒慎面對「右翼」對於個人生活保障與社會公平所造成的破壞及其道德後果。東西兩位先生,所面對的問題雖然截然不同,卻都求助於一個共同的傳統。這種巧合,值得我們玩味體會。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哈 金 歷史事件中的個人故事
孫 歌 冷戰初期的「民族」與「民主」
■ 台灣史的反思
莫達明 台灣本土史學的建構與發展 (1972-2004)
許雪姬 台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
張隆志 拾貝於婆娑洋畔、美麗島間:一個學院台灣史研究者的觀察札記
楊 照 建立衡量台灣史深度與廣度的標尺
■ 思想評論
吳乃德 英雄的聖經,政治家的教科書:閱讀普魯塔克
廖 美 交響的會話:大衛‧馬密戲劇的美國切面
高力克 孔夫子的幽靈:新世紀的「三教合流」?
成 慶 當代中國國家本位思潮的興起
■ 思想訪談
陳宜中 崛起中國的十字路口:許紀霖先生訪談錄
■ 思想人生
劉笑敢 學術自述
李懷宇 唐德剛:穿越歷史三峽
■ 思想采風
陳子明 在中國重振社會民主:紀念謝韜
章樂天 托尼‧朱特:未完成的生命依然完美
致讀者
當前臺灣人文學術領域中,論本身的活力、論牽動的人力與資源、論對於社會的移風易俗影響,文化研究與臺灣史乃是最為搶眼的兩個學門。這兩個學科的發展,也與過去二十年來臺灣政治、社會的變動有最密切的關連。沒有解嚴與開禁,文化研究的存在很難想像;不經過本土化雷厲風行,臺灣史也恐怕只會繼續活在陰影之下。但是隨著這兩個新興學門力求學院化與體制化,它們與社會的有機連帶也隨之鬆弛變質。《思想》自許為學院與社會論述的中繼站,繼前一期推出「文化研究:游與疑」專輯之後,本期轉而呈現臺灣史研究的「自我形象」:我們邀請到幾位在臺灣史研究第一線的學者,面對專業之外的讀者,敘述臺灣史學的體制發展與學術成就,更表達他們個人的親身感受,從而呈現臺灣史這個領域的精神氛圍與知識態度。
不無猶豫地,我們用「焦慮與自信」來形容臺灣史家的心路歷程,試圖捕捉這裡所謂的氛圍與態度。從局外人的角度觀察,臺灣史的從業者比起一般史學學者,似乎更在意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正當性、乃至於自己無論有意無意總難擺脫的政治意蘊,於是不免顯得急於辯解。但另一方面,臺灣史學家具有的使命感與承擔感,似乎也比史學其他領域更為濃重,其自負與抱負都很難以狹義的學術意義為界線。當然,歷史研究的意義本來就不會侷限在學院之內;不過,由於臺灣史的新生地位、由於臺灣本身的歷史之曲折、今日處境之曖昧,臺灣史所承載的負擔確實比較沈重。所可喜者殆為,在這種種張力的拉扯之間,高度的自我意識反而正可望帶來益形豐富的歷史智慧,即使必須以焦慮與自信來形容,也仍不失為健康而有益的。
在台灣之外,本期發表高力克、成慶兩位先生的評論,以及許紀霖先生的訪談,多少都聚焦在當前中國大陸上文化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強勁發展趨勢。與中國過去百年的激進、啟蒙思想主流對照,今天左中右各種思潮均匯流於保守價值觀與「中國模式」思路,的確是別開生面的新生事物,值得深入理解與公正的評價。當然,這些發展有其明確的客觀條件,也就是中國崛起這個巨大的歷史現象才是背後的主要動力,不過思想本身的轉折究竟受制於甚麼內在邏輯,也值得分析梳理。針對中國大陸在客觀形勢與思想潮流兩方面的動向,我們都會繼續邀請大陸的知識份子來為文討論,與臺灣的關心者對話、攻錯。
八月間,美國的朱特與中國的謝韜兩位先生先後去世,本期特別邀請朱特的中譯者章樂天先生和謝韜的好友陳子明先生撰文紀念。朱、謝生前並無交集,經歷也沒有相似之處,相提並論似乎有些牽強。但是,晚年的謝韜在中共黨內呼籲恢復從馬克思、恩格斯到社會民主黨的正統,拒絕列寧主義來自「左邊」的篡奪;朱特於去年十月以癱瘓之軀發表最後一篇演講,呼籲大家珍惜社會民主在二十世紀的重大成就,戒慎面對「右翼」對於個人生活保障與社會公平所造成的破壞及其道德後果。東西兩位先生,所面對的問題雖然截然不同,卻都求助於一個共同的傳統。這種巧合,值得我們玩味體會。
托尼‧朱特:未完成的生命依然完美/章樂天
2006年我接下了《責任的重負》一書的翻譯,在托尼‧朱特教授的眾多作品中,這只能算是一本「小」書,甚至英文版的裝幀都不大起眼。然而,譯竣之後我便忍不住去網上尋找朱特教授的其他文字,還產生了作個訪談的想法。他那論辯式的文風帶有驚人的鋒芒,我覺得,他是那種有一點話頭就能展開滔滔雄辯的經典公共知識分子,這在越來越講究容納和承認的今天已經太少見了。
朱特教授是立陶宛猶太拉比的後代,1948年生於英國倫敦東區。1972年,他帶著歷史學博士學位從劍橋大學畢業,轉去著名的巴黎高師,到歐洲大陸的文化中心繼續進修。1970年代末,學術處女作《普羅旺斯的馬克思主義:1871-1914》出版,日後他的著作就再也離不開以法國政治文化為代表的20世紀歐洲歷史這一主題:通過《地中海歐洲的抵抗運動:1939-1948》、《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左派:1830-1982》、《不完美的昔日:1944-1956年間的法國知識分子》等書,朱特教授精密剖析了他所謂的「法蘭西綜合症」——歐洲社會民主左派力量在二戰及戰後的動盪衰落的根源,並以此為抓手,探討了令歐洲人尷尬的一個世紀歷程。1980年代他移居美國、去紐約大學任教後聲譽日隆,各種政論、史論、訪談頻頻見諸報端,並格外細心地回覆各種網上的提問。作為崇尚社會民主的自由主義中左知識分子,朱特教授的活躍讓人無法不將其與愛德華‧薩義德聯繫到一起,兩人都是移民,而且都多年如一日地抨擊美國和以色列政府。
天妒英才,正在創造力鼎盛之年的朱特教授,去年卻罹患與史蒂芬‧霍金一樣的肌肉萎縮症,消息傳出,一片歎息。去年10月,面對紐約大學的700多名聽眾,癱瘓在輪椅上的歷史學家通過呼吸機的支援艱難地喘氣發聲,他的演講主題離不開「失敗」:社會民主的失敗,民族和解的失敗,歐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敗,最終是人類翻過現代史這一頁的努力的失敗——他的演講肯定了社會民主的有益遺產,但結束語卻嚴峻悲觀:「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過去的年代。」這是他患病後的第一次亮相。以頭腦和文字為畢生志業的人,在這一刻,即使置身於掌聲和眼淚的圍繞之間,依然顯得那麼孤獨無助。
過去在延續,我們仍沒有走出來——在「歷史終結」論者眼裡,在滿足於冷戰終結、紅色帝國崩潰的樂觀主義者眼裡,20年來,朱特教授的著作就像一封封無法置之不理的戰書。2005年,朱特教授完成了煌煌大著《戰後歐洲史》,他在這部作品裡火力全開,對白人世界反思二戰歷史的態度及其後果作了冷酷無情的解剖。東歐人的落後情有可原,在蘇聯的嚴密控制下,絕大多數東歐人喪失了正視過去的機會和意識,而一貫自我感覺良好的西歐人,對歷史記憶的玩忽則事關歐洲整體的墮落:包括創造戰後經濟奇蹟的德國人在內,戰後的一代西歐人不敢面對驅猶、屠猶暴行、戰時的通敵行為,還有普遍存在的對納粹主義(及其在德意以外國家的各個變種)的好感。對西歐人來說,「過去」是一道寬廣無垠、潤物無聲的陰影,人們在暗處埋頭活下來,一點點忘卻痛苦,告別過去。
作為一位講究道德良知的公民,朱特教授決不贊同自我麻痹的做法,但作為歷史學家,他又承認選擇性的遺忘對於歐洲戰後的迅速穩定的確大有好處。朱特本人也是戰後出生的一代。對於戰後的記憶,誠如他在一篇訪談中所說,「到10歲左右,我覺得我大多數關於「善與惡」的意識都更多地指向了德國人。」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戰爭電影,基本上表現的都是對德作戰的場景,而對於蘇聯紅軍的態度則比較複雜。事實上,這種有意無意的記憶選擇,從某種程度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冷戰45年間,也就是古巴導彈危機顯得更為危險,而最終,不管是甘迺迪、尼克森還是赫魯雪夫,都忌憚於再次捲入戰爭的慘重代價。
《戰後歐洲史》裡的這些主要論點,以及他那種論辯式而非傳統述史式的文風(全書注釋寥寥,大量的史實被摻雜在推理和判斷之中端給讀者),都透射出托尼‧朱特身上有矛盾的一面。說起來,他的家庭背景就有些奇怪:既信奉馬克思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朱特在其中成長至負笈劍橋時期,初步長成一個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狂熱醉心於以色列基布茲運動。然而,等到終於趁著1967年「六日戰爭」的機會去以色列體驗戰爭的時候,他又恰恰對自己的政治抉擇產生了懷疑。「我懷著這種理想主義的幻覺而去,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國家」,但最終卻發現復國主義左翼和右翼一樣,「對那些被踢出這個國家的人民驚人地無知。」
介入一切的青春狂熱散去,朱特的懷疑主義開始萌芽了,與之伴生的是他對歐洲左翼運動的濃厚興趣。一切意識形態、身分政治都是可疑的,政治投機值得鄙視,但錯置了的理想主義癲狂則更應予痛斥,而正是戰後歐洲的左翼陣營,每每成為誤判和理想錯置的舞臺。1960-70年代,朱特在巴黎高師的學習經歷鞏固了他學術進階的基石,他深度研習了二戰前後法國政治和知識界的歷史,這段經歷日後凝結成了數本專著:《普羅旺斯的社會主義》、《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和阿隆》等等,皆一面提出一種鮮明的、對法國政治文化總體上的批判態度,另一面分析左派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自由立場和道德尊嚴。
人們往往認為,保持客觀公正是歷史學家職業操守的題中應有之義,他們得像考古工作者一樣,不動聲色地梳理過去的事情,排布停當,待讀者自己來評判是非;而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則是一定要有道德判斷的,因為他在更多的場合下得直接面對大眾發言,去影響他們對公共問題的認知。正是從研究法國問題起始,托尼‧朱特嘗試著臧否已發生的事實,甄別個體行為的對錯:法蘭西這個底蘊深厚的優秀民族,為什麼遲遲無法找到通往良性政治的現代之路?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它自二戰以來一再蒙受軍事投降、政局不穩、殖民地叛亂、學生運動等等難堪事實的折磨?
法國集中了朱特教授的多個學術焦點:戰爭遺產的檢討,勞而無功的左翼運動,冷戰政治文化,等等。2006年,我奉三輝出版公司之託著手翻譯《責任的重負》一書,書中研究的萊昂‧布魯姆、阿爾貝‧加繆與雷蒙‧阿隆三人,作為上世紀法國傑出知識分子的代表,因機緣和性格的不一而選擇了不同的事業方向:政治旗手、意見領袖及學術精英。三人各有短長,都在時代的裹挾推撞中犯下了程度不一、方向不同的錯誤。究其癥結,朱特教授展示了一個更大的背景:從第三共和末年到1960、70年代,法國政治界和知識界之所以看似精英輩出,實則你糾我纏,兩敗俱傷,蓋因兩者都向對方輸出了自己有害的一面:政壇上的黨爭滲入知識界,迫使文人們站隊而喪失清白的理性;知識界和媒體的書生之見又每每膨脹,干預了講究效率的政治決策過程。
但是,朱特教授終究不曾忽略三人最大也是最光明的共同點:「勇氣與正直」,他們都在公共生活的腹地確立了自己的位置,表現出這些美德並因此而長期遭人嫉恨。我覺得,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而不只是做些個案分析,仍然與朱特本人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的重負」有關。冷戰思維、黨派之見禁錮了文人的頭腦,讓他們付出了重大的道德代價;現在的世界倒是承認每個人有權信自己所信,然而,假如一味以相對主義的態度包容之,在朱特看來,亦違背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接受 Newsweek 網刊的一次專訪中,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場:知識分子,尤其是像他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不能懼怕從道德的角度說出是非——「道德化」並非禁臠,而是履行使命的必須:
假如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道德化是骯髒的,從而把判斷對錯善惡的權力讓給各式各樣依然使用那種語言的人(天主教徒、穆斯林、其他各種宗教團體——以及政治右翼,他們從不忌諱犧牲別人的利益去搞道德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將無法對關於任何事情——從海外援助到墮胎再到安樂死——的難題給出答案。
是的,我們可以不再使用「道德化」這個詞,只要我們能夠重新樹立「公共倫理」這個曾被古今哲人落落大方地使用的術語的地位。這便是朱特教授的關懷所在,這也是他「叛離」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原因——不管是投身還是脫離某件公共事務,他都要基於具有公共性的道德判斷,而非出於宗教信仰、種族身分、習慣或個人利益的考慮。
作別了歐洲的情感家園,托尼‧朱特來到了美國,1988年接受了紐約大學提供的教席,並在7年之後,協助《西線無戰事》的作者、德國作家埃裡希‧雷馬克的遺孀創立了以雷馬克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此時的他已經是全球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了,而且熱愛演講和辯論,總是極其認真地回覆別人對他網上文章的評論。他對新大陸有不少好感,這裡的人性情開放,精力充沛,也為他提供了在學術界揚名立萬的機會,小布希上臺後,他與所有民主黨人一樣,指著總統的後腦勺罵了整整八年,即使奧巴馬登基,他也沒有輕易改換口吻,只是表示謹慎的樂觀,覺得奧巴馬很可能會在諸如醫療保險和中東問題等一系列大事上妥協。人總在該變通的時候一意孤行,在該堅持的時候腿軟,這種例子,近現代歷史上俯拾皆是。他在給英國友人彼得‧凱爾納寫去的信中談到了這個國家:「我已看到了未來,沒希望的。」
彼得‧凱爾納寫道:對那些不怎麼了解托尼‧朱特的人來說,他是一個眾多矛盾的集合體:一個能尖銳批評那些與他懷有同樣理想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既無限自豪於自己的民族傳統、又被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恨入骨髓的猶太人,一個樂意生活在美國的典型歐洲社會民主派。然而,「在他的朋友們眼裡,這些矛盾都不存在。」因為,托尼‧朱特的性格就是如此,「他所受的教育不是用來服務於任何種族或意識形態利益,而是用以理解和改善身邊的世界的。」他那旺盛奔突的激情鮮明、嚴密而精確;假如他追隨著這些激情進入到昔日觀點的反面,或者冒犯了過去的盟友,都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責任的重負》翻譯過程中,我同朱特教授有過幾次通信。他有一部研究歐洲知識分子向蘇聯「朝聖」的代表作《不完美的過去》(Past Imperfect),我問他,“imperfect”應當翻譯成「不完美的」還是「未完成的」?教授覆函道:你說得對,“Past Imperfect”兼有你提到的兩重涵義,一個未結束、未完成(unfinished or incomplete)的昨天,也是一個道德上、形式上受損(spoiled)的——或用你的話說, 「被玷污」的——不完美的昨天。「中文裡有一個能涵蓋兩種意思的詞嗎?」
我絞盡腦汁,也找不到這樣一個詞,只好老實作答「沒有」。用心讀過《戰後歐洲史》的歐美人士應當受到策動,著手修補他們的記憶和教訓,給「過去」投下的久佇的陰影畫上輪廓,送它遠行。這個世間,一段待述的歷史,一項需耕耘的事業,乃至一段肉體凡胎的生命,如若「未完成」則必定大不完美,但我想,已在九泉的朱特教授是個例外。
章樂天
書評人、翻譯工作者,文章見於各大刊物,譯作兩部:《加繆和薩特:一段傳奇友誼及其崩解》(2005)、《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與法國的20世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