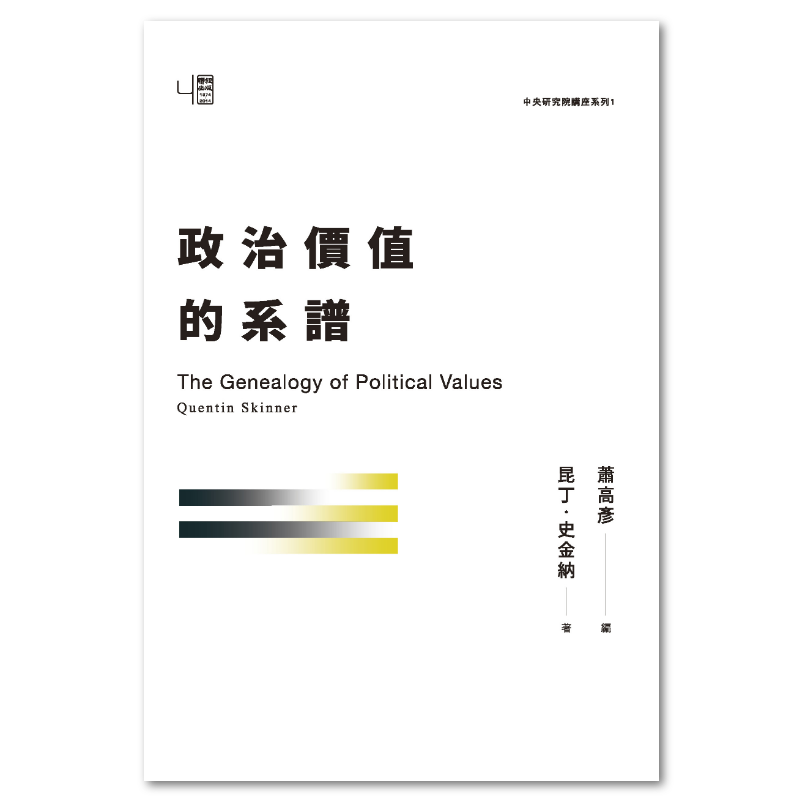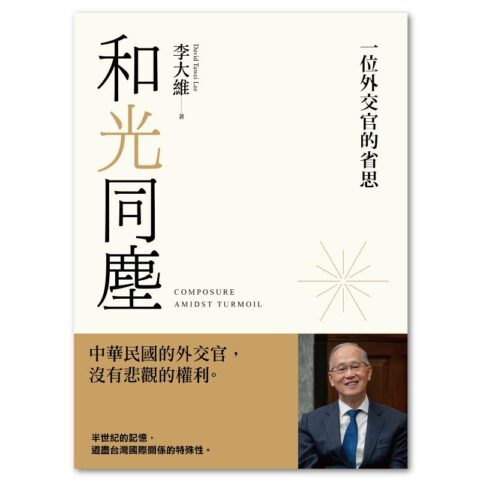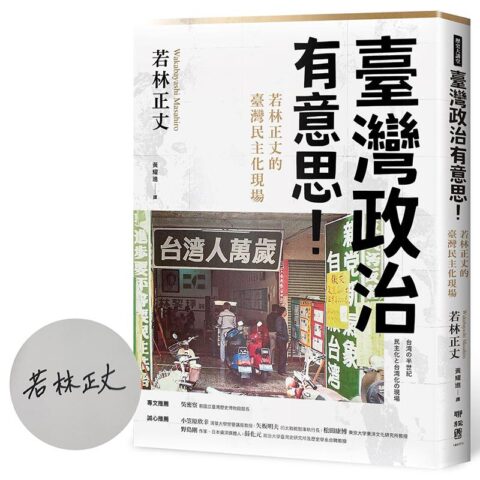政治價值的系譜
原書名:The Genealogy of Political Values
出版日期:2014-08-13
作者:昆丁‧史金納
編者:蕭高彥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120
開數:25開(高21×14.8cm)
EAN:9789570844467
系列: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
已售完
《政治價值的系譜》依據當代政治思想史名家史金納2013年的「中央研究院講座」整理編輯而成。在象徵中央研究院最高榮譽的三次講座中,史金納以大師風範深入淺出地說明史家技藝與現代政治價值的形成,並闡述其學術研究的當代意義。
本書第一講分析「脈絡主義」和「系譜學」如何面對歷史行動者的信念。第二講指出,自由的觀念除了積極與消極之分,更有第三種「共和自由」,對當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參與深具啟發性。第三講則分析人民主權、絕對主義以及「虛擬人格理論」對現代國家概念形成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
王汎森
2008年為中央研究院創立八十週年,除了慶祝八十年來的艱辛與榮耀外,展望未來,在翁啟惠院長的構思下,決定自2009年起設置「中央研究院講座」,不定期邀請世界級學者來院發表演講,期為台灣學術發展注入新活力。「中央研究院講座」定位為本院最崇高的講座,初步由數理、生命組開始規劃,逐步擴及人文社會領域。講座人選以研究領域為考量,打破所或中心的界限,以諾貝爾獎得主或同等級之重要學者為首要邀請對象。
2013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講座,演講人都發表兩次公開演講,並將影音檔存留於本院官方網站。然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與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有所不同,有必要以文字印刷為媒介,讓讀者能夠通過閱讀與反思,理解各個學問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可能取向;並以書籍為基礎,觸類旁通,選擇相關學術著作從事進一步研究。基於上述考量,我們決定請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發表三次演講,並於事後將其講稿翻譯成中文,以「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方式刊行。
在2013年5月,本院邀請劍橋大學前副校長暨皇家講座教授,目前任教於倫敦大學的著名思想史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訪台,進行第一次人文領域的「中央研究院講座」,並將其講稿編輯翻譯成書。
未來隨著時間的累積,相信這個系列能夠很快地在華文世界建立起現代經典的角色,扮演「檀納人文價值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在英語世界中的角色,令讀者迅速跟上各個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重要學者對於未來學術發展潮流或跨越學科藩籬的評估。希望本院這方面的努力可以深植、活化我國的學術傳統。
作者:昆丁‧史金納
現任倫敦大學講座教授,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與皇家歷史學講座教授,是當代「劍橋學派」代表性思想史家,著作超過二十餘本,曾獲巴贊獎(Balzan Prize)、沃夫森歷史獎(Wolfson History Prize)與比勒費爾德科學獎(Bielefelder Wissenschaftspreis)等殊榮。
編者:蕭高彥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1993)。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並合聘於中研院政治所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思想史以及當代政治社會理論,核心議題包括共和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現代國家觀念史。著作包括《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榮獲2014 第三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以及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與中英文學術論文數十篇,發表於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Politics、Issues and Studies 以及許多台灣的專業學術期刊。曾獲選為Bradley Foundation Fellow、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並獲得兩次國科會研究獎助傑出獎。學術服務方面,曾擔任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中研院學術諮詢總會副執行秘書、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主編、《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執行編輯、《台灣政治學刊》、《政治科學論叢》與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編輯委員、台灣政治學會執行委員,以及中國政治學會理事。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王汎森)
編者緒論:歷史與經世:昆丁‧史金納的思想史研究(蕭高彥)
第一講 真理與史家
第二講 自由系譜學
第三講 國家系譜學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王汎森
2008年為中央研究院創立八十週年,除了慶祝八十年來的艱辛與榮耀外,展望未來,在翁啟惠院長的構思下,決定自2009年起設置「中央研究院講座」,不定期邀請世界級學者來院發表演講,期為台灣學術發展注入新活力。「中央研究院講座」定位為本院最崇高的講座,初步由數理、生命組開始規劃,逐步擴及人文社會領域。講座人選以研究領域為考量,打破所或中心的界限,以諾貝爾獎得主或同等級之重要學者為首要邀請對象。
2013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講座,演講人都發表兩次公開演講,並將影音檔存留於本院官方網站。然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與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有所不同,有必要以文字印刷為媒介,讓讀者能夠通過閱讀與反思,理解各個學問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可能取向;並以書籍為基礎,觸類旁通,選擇相關學術著作從事進一步研究。基於上述考量,我們決定請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發表三次演講,並於事後將其講稿翻譯成中文,以「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方式刊行。
在2013年5月,本院邀請劍橋大學前副校長暨皇家講座教授,目前任教於倫敦大學的著名思想史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訪台,進行第一次人文領域的「中央研究院講座」,並將其講稿編輯翻譯成書。
未來隨著時間的累積,相信這個系列能夠很快地在華文世界建立起現代經典的角色,扮演「檀納人文價值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在英語世界中的角色,令讀者迅速跟上各個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重要學者對於未來學術發展潮流或跨越學科藩籬的評估。希望本院這方面的努力可以深植、活化我國的學術傳統。
第一講 真理與史家
首先,這是我第一次造訪台北,真的非常高興。能夠受邀在2013年度中央研究院講座演講,更是倍感榮幸。這是一項極高的榮譽,所以我想誠摯地感謝中研院的各位,邀請我來分享最近的研究。本週一共有三場演講,而我想跟各位在今天的第一場演講裡分享的課題,是對我而言,史學家的任務在本質上究竟為何。另外兩場演講的主題,不只是我近來研究的重點,更一直是現代西方政治理論中的重要課題,也就是「自由」的概念、「國家」的概念,以及公民自由與國家權力間的關係。
從接下來兩場演講的題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探討這些概念時,所採取的是一種我稱為系譜學(genealogy)途徑的方式。目前,在現代西方哲學傳統下,談到「系譜」這個概念,就免不了要提到尼采之名。即便如此,我還是必須澄清,我的系譜學概念並不特別屬於尼采式的系譜學。尼采系譜學的主要主張,與他的權力意志相關連。而他想說明的,就是追根究柢起來,我們的既有認知與評價,事實上在初始時的意涵與目前大相逕庭。換言之,尼采的主張,針對特別的乃是那些否定了其自身源起的信念;而他的目標在於讓我們看到,概念在最初所具有的意涵,與後人的認知間會有多大的歧異。
在應用系譜學的概念時,我並不那麼極端,也限縮了應用範圍。我只是覺得,把探究評價性術語的演變這個工作,看成像是整理族譜,應該滿有幫助的。我之所以認為這有幫助,是因為這會促使我們去思索,究竟目前認知中的「自由」與「國家」等概念,是始終如一,還是在應用時歷經了種種變化與挑戰?
這些承載了自由、國家等概念的術語在意義上是否曾經有所改變?系譜學正好能凸顯這個關鍵問題。我認為,一旦採取了系譜學途徑,就會發現「自由」與「國家」這些術語的意涵,事實上從來沒有獲得過一致的共識。雖然還是有許多人主張,我們可以為這些術語找出一個中立的意涵,並大致上獲得普遍同意,但我認為這種看法並不正確。目前討論的術語,向來就缺乏固定的意義,因此也就無所謂記述其線性概念史(linear history of concept)的可能。反之,系譜學可以讓我們認知到這些概念在本質上的偶然與爭議,並明白我們不可能找出這些概念的本質或自然界線。若狀況如此,採取系譜學途徑更進一步的價值,就是讓我們在寫作時不再用當前常見,但可能是錯誤的方式,來分析概念。這也讓我們不要過於推崇這些概念當前主流的觀點,並把焦點放在這些概念從過去的爭論、辯論中發展出來的程度。我甚至會主張,這能讓我們後退一步,與目前的既有認知拉開距離,重新想想,目前我們看待重要道德與政治概念的方式,是否足以反映出其豐富的內涵。
不必諱言這個途徑也有其限制與困難。在探究這兩個特定政治術語的流變與應用方式時,我將範圍限縮在一特定語言社群裡,這種方式不免稍嫌視野狹隘,對此我也有點自責。不過,這些術語今日的樣貌,是受到意識型態與歷史的力量而形塑出來的;在有限的時間中,我要做的,乃是研究人們談論政治權威的方式;而探討「自由」與「國家」時,我將關注這些語彙在英語世界中的論辯。無論如何,要是這能保證我們在紀錄公共權力本質的各種不同主張時,避免在假設與分類上產生時代錯置的治史問題,那麼這樣的研究就有其價值。在記述這些概念的歷史時,我們應該可以使用更為貼切的詞語,並避免一種常有的錯誤,也就是在渾然不覺的情況下,輕易斷定過去的思維就是目前概念的源起。
在提出系譜學以上各方面的主張時,其實已經開始談到史家——更精確地說是文化、思想史學家——的工作,在我看來應當如何進行。現在,我就要開始談本場演講的主題:史家的任務。
史學家這個稱謂含括形形色色的知識範疇,而這些學者的研究領域則包羅萬象。但在以下我將把討論的範圍限縮在思想與文化史學家—也就是像我自己這樣的史學家。合理來說,史學家主要研究的對象是文本(texts)。在此文本所指涉的不僅只是如小說、新聞、法庭記錄、國會發言、或哲學論文這種顯而易見的類型而已,更廣義地說,畫作、建築與社會行動也能夠當作文本來閱讀。
我將特別提出兩個文化史學家最常對於作為他們研究基礎的文本——廣義來說——所提出的普遍主張。我所要討論的第一個論證是:史學家應該要將他們所研究的文本從本質上當作對於信念(belief)的陳述或肯認來處理。
這是哲學家通常會鼓勵史學家所採取的立場。例如,Mark Bevir在《觀念史的邏輯》一書中極力主張:「當人發表言談(utterance),他們所表達的是理念(ideas)或信念,而正是這些理念和信念構成思想史學家研究的對象。」實踐歷史學家向來樂於支持這個觀點。著名的例子為Keith Thomas在他的經典之作《宗教與巫術的衰落》開頭的評述,他認為自己所研究的是信念的系統(systems of belief),並以文化人類學家的精神來研究。Thomas接着表示,當史學家探討這類過去的信念系統時,他們大抵能夠反映出這些被研究的信念,在今日幾乎都不復獲得認可。 Thomas指出,對於思想或文化史學家來說這反而形成極有趣的挑戰。如Thomas所言,當許多過去被廣泛接受的信念對我們來說是明顯錯誤或甚至毫無根據,無法改變的事實是,在過去許多有智慧之士也視這些信念為真,而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去解釋何以如此。
過去五十多年來,這個挑戰普遍為文化史學家所接受,而現在我想要特別提出兩個在過去被研究近代早期歐洲的史學家傾力細究過的信念系統,我們可稱之為異己信念系統(alien belief systems)。首先,過去已累積許多關於異己的宇宙論信念(the alien cosmological beliefs)的研究。推動這個研究潮流最力的或許是Thomas Kuhn,他在經典之作《哥白尼革命》中的洞見又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被進一步加以概化。其中,Kuhn檢驗Bellarmine樞機主教的觀點,後者在與伽利略的辯論中駁斥哥白尼日心說,堅持是太陽在繞著地球旋轉。
另一個讓近期研究近代早期歐洲的史學家全神貫注研究的異己信念系統則是巫術信念。相關議題的文獻出版依舊蓬勃,而其中至少有三部作品對我來說是大師之作。一部是之前已經提過的:Keith Thomas在1971年發行第一版的《宗教與巫術的衰落》。新近則有Stuart Clark的出色研究《與惡魔一同思考》。但比這兩部作品更早的則是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隆格多克地區的農夫》中分析巫術信念與施術的先驅研究,儘管這本著作一直到1974年才有英文譯本問世。Ladurie不只把焦點放在這個在近代早期歐洲廣泛流傳,而現今看來完全是異己的信念,亦即相信一些人能與魔鬼立約,藉此被賦予傷害他人的能力;他也考慮到當時主張這些巫術施術者會慣常地在夜晚飛翔至與撒旦的聚會,也就是所謂的巫魔會(witches’ sabbats)。
這便是我想討論的第一點:文化歷史學家所關心的是去探討什麼是我們的祖先所相信並認為理所當然的。Bellarmine樞機主教也許錯誤地假設太陽繞日運行,但這顯然是他所相信的。同樣地,惡魔論者(demonologists)也許錯誤地假設人類能和魔鬼締約,但這亦是他們所相信的。文化史學家的任務,我們被告知,就是辨明並解釋這樣的信念。
我接著要檢視的是與第一點緊密相關的第二個主張:身為史學家,當遇到這類異己信念時,必須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信念的異己特性上。這全然是Ladurie在他的《隆格多克地區的農夫》中致力而為的。在關於農民如何看待惡魔附身的分析中,Ladurie開門見山地強調這些信念不僅明顯是錯誤的,而且還成為他稱之為「集體譫妄」(mass delirium)的產物。Norman Cohn在他兩年後所出版關於巫術信念的名著《歐洲內在的魔鬼》中,說了幾乎一樣的話。他認為如果要解釋這些信念,必須首先去認識到這些信念不僅是錯誤的,而且也大抵以「集體幻想」(collective fantasy)的形式出現。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這些史學家的想法,探詢為何他們認為先去考慮那些信念真實或謬誤與否是重要的,這在前述Cohn的段落中已經能找到蛛絲馬跡。Cohn認為錯誤的信念來自推理的失敗(failures of reasoning),因而需要不同於處理真實信念的方式來進行解釋。同樣的論述到Ladurie這邊則更加清楚。Ladurie主張,如果想了解為何巫術信念在當時如此廣泛被接受,我們需要找出是什麼引致這個正常推理過程崩潰(such a breakdown in normal processes of reasoning)。如他所言,謎題就在於找出是什麼阻礙農民認識到他們信念的謬誤,找出是什麼造成了這種「蒙昧主義的高漲」(“upsurge of obscurantism”)。
這個研究途徑不只為Ladurie與Cohn這樣的實踐史學家所採用;許多研究解釋的邏輯的哲學家也推崇這個途徑,包括Steven Lukes, Philip Pettit和 Charles Taylor這些在近代英美傳統學界的領導人物。引述Pettit的話來看,他的說法顯然是在回應Ladurie,認為我們必須去考慮是什麼樣的「社會功能或心理壓力」(social function or psychological pressure)可能使得人民無法認識到他們信念的「錯誤的本質」(the mistaken nature)。
我的興趣並不在於討論Ladurie等史學家對巫術信念所提出的具體解釋。但值得觀察的是Ladurie對於是什麼導致近代早期的法國有如此多人懷抱這類幻想,提出兩個主要的解釋方案。第一是,隨著宗教改革的推展,農民開始害怕失去他們過去所信奉的心靈領導。遠離他們的神父,這些農民發現他們面臨自己「原始的恐懼」並因此「自我放棄而轉向撒旦」。他的另一個而且是主要的假設則是,宗教改革早期階段所推動的社會改革最後卻徒勞無功,這讓農民感到挫折。Ladurie指出,隨著社會改革的失敗,農民想要改善生活的期望延續下來,披上了「神話的外衣」,而被迫藉由「巫魔會荒誕妄想的暴亂,以惡魔的形態來逃避的意圖」這個方式表現。
如前所述,主要讓我感興趣的並非Ladurie所提出的具體解釋,而是他認為,在著手解釋這些異己信念之前,需要做的正是我方才引用的哲學家所建議的:亦即把焦點放在這些異己信念的謬誤,並自問什麼樣的原因壓力可能會導致人們對這些幻想深信不疑。
對於歷史考證的討論到此告一段落。現在我將對我所挑出的這兩個互相關聯的主張進行評論。且讓我們先回到第一個主張:思想與文化史學家所研究的文本應該被當做對信念的陳述或肯認。在此我要提出兩個例子來討論,首先是文學文本。當論及在處理文學文本時,我們是否應該將其本質上當作信念的表述,且讓我們聚焦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上,這個我所能想到最著名而眾所皆知的例子。如果參考近期研究莎士比亞劇作的文獻,就會發現許多文獻認為莎士比亞的劇本表現了(或至少包括)他對於一些具體議題的信念的陳述。舉例來說,Andrew Hadfield於2005年出版的書中聲稱要展現莎士比亞,至少在某段時期,對共和政體表示支持。Robin Wells則在他2005年出版,關於莎士比亞人文主義精神的研究中,舉出他認為是莎士比亞對於社會正義本質的信念。Catherine Canino在她2007年出版的書中,則聲稱要辨明莎士比亞對於貴族的態度。諸如此類的著作還有許多。
這個研究途徑並不令人陌生,但其中確有可議之處。畢竟,莎士比亞所撰寫的是戲劇構作(dramaturgy),常以文藝復興修辭學的專技語言(technical language)來進行寫作,在場景中同時呈現出不同且多半是對立的觀點。舉例來說,在《威尼斯商人》第四幕中,Portia這個角色,當面對猶太商人Shylock請求使他合法契約的債權獲得屢行,宣稱慈悲應該排在正義的前面。在此莎士比亞以戲劇來呈現當時在修辭作家之間關於所謂庭辯修辭(genus iudiciale)爭論不休的問題。他們的問題是要如何期望能在法庭上為在法律上站不住腳的他人辯護。修辭家如Quintilian便警告,這是對於辯護人來說最不利的情況,而唯一的機會就是靠修辭家所謂的共通點(loci communes)。他們建議,辯方所要做的就是訴諸一些廣為接受的道德原則,並期望法官或陪審團會認為這些道德原則比另一方的法律訴求來得更重要且有力。這正是Portia在她的開頭演說所試圖做的,照本宣科地依循修辭學教科書,並確保引經據典的主題選擇(topos)在舊約聖經亦有明文。
這個情節有提供任何證據去證明莎士比亞相信慈悲比正義來得更重要,因此可以說Portia的演說反映了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精神?我們無論如何都沒有立論依據。只能說在這個修辭辯論中,莎士比亞賦予了這個虛構的小說人物某個信念。我甚至要更進一步說我個人不認為所有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有任何道德承諾可以被確信是他自己的信念。
然而,也許有人會反駁說,文學文本是特殊案例,因為它們只處理虛構作品。其他本文開頭所舉的文本類型,如國會演說、哲學論文又如何?如果我們要去理解這些文本,我們不是理當在本質上把它們當作信念的陳述?
我並不如此認為,儘管這顯然是更具爭議性的主張,而且需要花更長的篇幅來闡明。但在以下且讓我試著以著名的政治論著,也就是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為例來說明。馬基維利在《君王論》的第18章中,提出可能是他整本書中最著名的觀察,他主張想要獲得榮譽(honour)與榮耀(glory)的政治領袖必須學著模仿獅子與狐狸。這個段落應該如何詮釋最好?通常得到的答案是,馬基維利在肯認一個信念,亦即政治上的成功靠現實地體認到武力(force)與詭計(fraud)的不可避免,獅子象徵武力,而狐狸象徵詭計。
我並不否認這是馬基維利所相信的。但我有疑問的是用這個方式詮釋這個段落是否夠完善。畢竟,馬基維利的論辯,並非投射向文化的真空;而是當時義大利眾多寫給君王的建言書其中之一,那些作者大都同意榮耀確是君王所要追求的正當目標,而獲得榮耀的手段就是培養德行(virtù)。藉使用德行這個用語,所點出的不僅是道德與政治德行;還將德行作為「人」的界定本質(vir是拉丁文「人」之意)。因此,擁有特別專屬於人的德行便成為成功領袖的界定特質。
相對地,馬基維利所說的是,如果想要取得榮耀,所要培養的不僅是人的本質,也要培養野獸的本質。是故,前述引文中,馬基維利是在反駁這個當時被認為毋庸置疑的人文主義德行論述,亦即人的本質是取得政治成功的關鍵之一。他質疑人文主義對德行的解釋是否足夠完善,並重新定義將德行作為能替君王帶來榮耀的屬性的看法。
而且,馬基維利將這個批判投射向這個文化中討論政治領導最著名且受尊崇的著作,即西塞羅的《論義務》(De Officiis)。在《論義務》的第一書,西塞羅指出有兩種方式可能會造成不正義,一是使用暴力(force),另一則是靠欺騙(fraud)。西塞羅指出,暴力為獅子所用,而欺騙為狡獪的狐狸所用,這兩種手段皆是屬於野獸的特質,所以對人來說並無價值。由此可見,馬基維利於前述引文中,也是在同一主題上引述西塞羅,提醒他的讀者們關於這個議題最受尊崇的權威論述,同時駁斥並反諷了西塞羅的道德誠篤。
我的觀點是,馬基維利在前述引文中不僅是在陳述他顯而易見的信念,亦即認為武力與詭計對政治成功來說不可或缺。他也是在引述西塞羅對德行特質的評論,提醒他的讀者們西塞羅的主張,質疑並且反諷這個主張,藉此反駁當時人文主義政治理論傳統的標準信條,並同時提供對於德行的解釋,而此時德行這個核心概念已被重新定義。上述這一切只用一個句子就完成了。
這顯然給讀者對這段著名論述更為豐富的詮釋。但對我而言重要的是,用這種方式處理與詮釋馬基維利的文本時,並非全然將其作為信念的表述。不如說,是將文本作為對其當時的政治辯論一種特定且相當複雜的介入(intervention)。我們不是在問馬基維利在肯認什麼;而是在問,在前述引文中他在做什麼;甚至可說我們所問的是在說出這段話時,他所打算(up to)的是什麼。
若概化這個論點,我指出的是,最適合文本詮釋的語彙是在討論行動(actions)時所用的,而不是信念。我認為進行詮釋不應只聚焦在人們在說什麼,而應更加關注他們在做什麼,什麼可能是他們在說這些話時的潛在目的。用現下流行的用語來說,我主張應該要把焦點放在文本的表現性(the performativity of texts)。
讓我用兩個我認為對文化相關學門(cultural disciplines)來說非常重要的意涵,來完成我的論述的第一部分。在此我必須謹慎。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說,學者精神崩潰的徵兆,就是當他們開始跟你說他們的研究非常重要。然而,有兩個和我前面的論述相關的意涵對我來說確實值得討論。
首先,如果說任何發表于某個文化的文本都無可避免地對該文化產生「介入」,那麼在文學或哲學,以及意識形態之間就無法存在明確的區分辨別。換句話說,那將永遠值得去探究那些即使是最抽象的文本的意識形態傾向。寫作者時常提出看來單純是信念的肯認的主張,但在此之外還有潛在的意識形態目的,有時具有可觀的與隱藏的複雜性。我要指出的是,如果目的是要去解釋事件進行的全貌,我們就須致力使潛在的目的浮現出來。若問這要如何達成,正如我所試圖闡明的,答案就在於靠跨文本比較來揭露文本、脈絡、與其他文本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觀察到的另一個意涵是,如果將文本本質上當作社會行動來看待,一個我認為有益的結果是會從根本上去中心化(decentre)各個作者。所有的作者們,無論如何傑出,會開始從本質上對開拓論述與辯論傳統的視野有所貢獻。因此,我所訴求的文史研究,其目標並非在提供個別文本的詮釋,而是呈現一個自我辯證的文化的光景。我認為,這是所有與詮釋相關的學門應該要為自己立下的首要任務。
這便是我的第一個主張,但我要小心不言過其實。即使如我所述,文本應該被當作社會行動來處理,我當然不是在否認文本也包含信念的表述。Bellarmine樞機主教在他與伽利略的爭論終究是在肯認日心說為真。這是他所相信的。同樣地,Le Roy Ladurie與Stuart Clark所研究的魔鬼論者也是在肯認人能與魔鬼結盟這件事為真。這亦是他們所深信不疑的。
既然如此,就不能迴避另一個我開頭承諾要討論的命題。 亦即,當我們遇到如此深刻的異己信念時,應該首先將重點放在它們的異己特性,放在這些信念對我們來說明顯為錯的這個事實上。之所以用這個方式來處理,如Ladurie所主張,是因為需要被解釋的是什麼機制介入,而阻礙我們的研究對象發現他們信念的謬誤。
該怎麼看待這個主張?讓我在此提出自己的答案。雖然,如前所述,這個研究途徑一直以來被許多優秀的哲學家所推崇,並被許多傑出的史學家所採用,但我認為採取這個研究途徑對好的歷史實踐來說卻是致命的。何以如此?因為這個研究途徑假設,當一個史學家遇到一個對他/她來說是錯誤的信念,他/她解釋的任務都將在找出是什麼使研究對象的推理出了差錯。但這樣一來就把「抱持理性信念」這件事等同於「抱持被這個史學家判斷為真的信念」。而這是在將「即使是現今來看明顯為錯的信念,在當時信其以為真卻是於理有據」的這個可能性給排除。
換句話說,對我而言文化史學家需要在真理(truth)與合理性(rationality)之間去操作一個非常強力的區隔。當我們試圖去解釋那些被我們評價為非理性的信念,那麼的確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如何最好地去解釋它們。我們因而需要去探究是什麼情況阻礙行動者(agent)去遵從那些公認的證據與論述的規範,或是什麼情況提供行動者動機去挑戰那些規範。
然而,極有可能是,儘管依循在行動者的社會中最佳可得有關論述的規範來形成與檢驗信念,到頭來卻還是得到錯誤的信念。我敢肯定我們都這麼做過。因此,把「抱持對我們來說為錯的信念」等同於「合理性的缺失」,是在還沒認識到這是否適當前,就去排除某種解釋而偏廢其他解釋的可能。
為闡明這個主張,讓我們回到Ladurie關於近代早期隆格多克地區的農民對於女巫的信念的解釋。Ladurie不僅開頭就點出這些信念有誤;他還假設這些信念的謬誤足以顯示他們是不理性下的產物。 他對解釋的探究因此變成去探詢為什麼這麼多人成為幻覺的俘虜。但Ladurie這麼一來就沒有為自己留出空間去考慮其他解釋的可能性。他無法想到農民之所以相信女巫的存在,可能是因為將其它信念視以為真,而從那些信念推導出將巫術信念信以為真是合理的。
只考慮最簡單的可能性的話,假設農民也將其他信念視以為真,且這個信念在近代早期歐洲被公認是理性且不容置疑的,亦即,聖經就是神的話語。如果這是他們信以為真的信念之一,而且對他們來說那是理性的,那麼對他們來說去懷疑女巫的存在反而是不理性的。因為舊約聖經的申命記(Deuteronomy)與出埃及記(Exodus),不僅告訴我們女巫存在,還說巫術是憎惡之物(abomination)且女巫不應苟活。聲稱女巫的存在是不可信的等於對神的話語的可信度表示懷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不理性的?
Ladurie預先排除了那些相信女巫存在的人也有可能是因為依循諸如此類的推理連鎖。但這不僅代表他因此提出一個盡他所知的關於巫術信念的解釋,卻完全不切題。也代表他忽略了諸多關於農民精神世界的問題,而如果要去充分理解他們的信念與行為,探究這些問題是絕對必要的。
這個問題當然已被一些新近的史學家提出。的確,現今的潮流是,如Stuart Clark在《與惡魔一同思考》中所主張,我們的目標應該是盡可能地去理解我們祖先的異己精神世界,如果可以的話,使它們盡可能地理性。因此我接著要來評論這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
我認為,對好的歷史實踐來說,這個相對的研究途徑並不會比較安全。首先,我驚訝於這派的史學家對於人對信念執著的可能性這個問題漠不關心。他們通常寫得好像人必定相信女巫或必定不相信。但當我們對所持的某些信念或多或少感到肯定,對所抱持的其他信念的承諾就會較低,而顯然我們並不對所持的所有信念一視同仁。因此,如果我們要試著去評估如巫術信念這樣的信念理性與否,我們理當需要盡可能地清楚意識到這些信念有多堅不可摧,或隨時會被放棄。
現今關於異己信念的討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對所謂「這個信念是被理性地抱持」這句話的解釋常有所欠缺。有時他們似乎囿於混淆「相信什麼是理性的」和單純實踐理性,也就是「去做什麼是理性的」。舉Paul Veyne的著名文章《希臘人相信希臘神話嗎?》為例,概括來說,Veyne的答案是,對於希臘人來說,去相信神話為真是否理性這個問題幾乎不會被強力提出,但對他們來說不去提出並非是不理性的。這裡的主張可能是指信念體系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就足以讓他們視以為真。然而,如果說這裡的主張是指對希臘人來說,不去提出這個關於信念真實與否的問題在實踐上是理性的——可能因為普遍接受這些神話帶來許多好處,那麼這樣一來就使得「如果希臘人是真的相信他們的神話,對他們來說這理性與否」這個問題沒有確定答案。而且讓人懷疑在多數情況下,答案會是否定的。
然而,我在現今關於異己信念系統理性與否的討論中發現的主要問題,是他們有時在具體化「是什麼使得抱持這個信念為理性」的觀點時太過廣泛。例如,Stuart Clark主張,既然可以展現近代早期惡魔論者的巫術信念和他們的其他信念在內在邏輯具有一致性,那麼就足以去說他們將惡魔論的信念視以為真是理性的。我同意如果信念要是理性的,就有必要去關心這些信念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但我看不出為何那樣就足夠了。同樣必要的是,只有在對於信念形成的過程也具有這種態度時,才能採用這些信念。一個人無法說是理性地持有信念,除非他關心那些能提供基礎去推斷其信念的主張為合理的證據。換句話說,我不認為一旦揭露一個信念系統的內在邏輯可接受性,就肯定能夠說支持這個信念系統是理性的。
這個質疑確是不合時宜的。今日時常聽聞,我所主張的這類堅持牽涉到將我們以今鑑古相對優越的理性所導致時空錯置且屈尊的觀點,代入到對於過去的研究。但這對我來說完全是誤會。身為一個史學家,如果要譴責我所研究的某些信念為非理性,只需要主張我已經揭露在該社群中,公認關於信念的取得與合理化的規範,而這些被宣稱非理性的信念並非依循,而是對抗那些規範而被抱持。我不需要主張這些信念之所以不理性是根據我自己對理性的標準,更非根據某些理性的標準,無論那是什麼。我只是在主張所研究的歷史行動者無法達到一些在當時社會所公認的理性的標準。
然而,在給自己這些限制之後,我必須澄清,我全心支持文化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去盡可能公正地處理那些異己精神世界內在理性的觀點,例如Bellarmine樞機主教或是近代早期隆格多克地區的農民。重點是,如Thomas Kuhn過去論及伽利略與Bellarmine的辯論時所述,要找出任何確切的時間點來指控Bellarmine信念的非理性並非易事。然而當然,這絕非在說Bellarmine所有反駁日心說的話都為真。這只是在說,相信地心說為真對他來說是理性的,即使那對我們來說是明顯錯誤的。
因此,基本上我所要主張的是,當文化史學家試圖去解釋在過去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思想系統時,他們甚至應該避免去問他們所研究的這些信念是真實還是錯誤。他們唯一要提起關於真實的概念的時候,是去問是否我們的祖先有足夠的基礎去相信他們所信仰的是真實的。
這便是我的基本主張。但我已經能預期到,任何人採用這個立場,遲早會被抨擊為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因此,在本文最後,需要就我是否真的採取相對主義的立場這個問題進行討論。表面看來,我的主張顯然是相對主義的。我相對化了把某個信念「信以為真」的觀點。我指出對隆格多克地區的農民來說,去相信女巫和惡魔訂約為真的這個信念是理性的,就算在現代視同樣信念為真是不理性的。除此之外,我主張身為文化史學家我們有必要在這個層次上當一個相對主義者。我們需要提醒自己,以徹底的理性去相信一個錯誤的信念這種事是有可能發生的。
然而,這不代表支持前述立場的文化史學家也欣然支持概念相對主義理論(conceptual relativism)。概念相對主義是關於真理的本質的理論:最接近真理的只不過是理性的可接受性(rational acceptability)。舉例來說,Richard Rorty在他的著作《哲學和自然之鏡》中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概念相對主義者。當他在討論伽利略與Bellarmine的辯論時,他堅持Bellarmine對日心說的反駁和伽利略對日心說的肯定一樣客觀,持反對看法的只是在支持Rorty所謂的「現代科學的修辭」。
這完全不是我所要主張的。我認為,在前例中事實如此,而說Bellarmine的信念是錯的並沒有什麼毛病。但這也不是我的主張。身為史學家,我不希望去探究Bellarmine關於日心說的信念,或農民對女巫的信念,是真實還是錯誤。我根本不希望史學家用這種方式去討論真實。
以此作為我的基本堅持,我的討論甚至不牽涉到概念相對主義理論。我當然不是在說過去女巫和魔鬼結盟這件事曾是真實的。我只是主張,在過去視此事為真是理性的,即使那是錯誤的。總的來說,我只是指出「視什麼為真是理性的」這個問題將隨我們信念的整全性而改變。但我並不是在主張真實本身也會隨著改變,這是完全不同的主張。如果我是這個意思,那麼我所說的話應該是明顯邏輯不連貫的,因為這麼一來我會是在宣稱世上不存在普世真理(universal truth)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普世真理。
然而,我承認,我指出史學家不應該考慮真理,對於許多人,特別是哲學家來說,是非常奇怪的。他們會質疑,我當然希望我說的是真實的?當我說,為了要理解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就必須認識到這本著作某種程度上是對西塞羅的反諷,對我來說這個主張是真的當然是重要的?在此我對Richard Rorty對於這類修辭的駁斥深有同感。如果我們主張所說為真,而且如果我們指的是某些更甚於理性可接受的,那麼我們必定是在說我們的主張反映了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無疑如此。現在,身為歷史學家,我們當然嘗試去追尋在這個意義上的真實。但是的確,無論是人文學還是科學,最多只能理智地期盼,我們的主張,對那些處在進行評斷最佳位置的人來說是理性可接受的。這確是我所極力主張,而且應當銘記於心的是,到目前為止,不斷被取代是歷史和科學解釋的共同命運。
這即是我想用來做為結尾的主張:即「事實性」(factuality)應該要和「真理」有所區隔。不過每個故事都應該要有一個道德教訓,而我想要以這個故事的道德教訓來總結這個演講。在我們的個人與研究生涯會面臨許多信念對我們而言為真,其它則否。然而在面臨這些考量時,我們未必應處理得宜,去過度強烈地堅持那些甚至是我們最珍視的信念的真實。我相信我們應該能處理得更好,如果能承認即使是我們的核心信念無論何時都保有調整改變的開放性。去堅持我們自身信念的真實,等於是在說那些信念無法妥協。我們應小心避免這樣主張。換句話說,我所擔憂的,是對於真實的要求為寬容設下極大的限制。然而,我認為,更多程度的寬容是我們所迫切需要的。試著理性已經相當困難,也許我們應當滿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