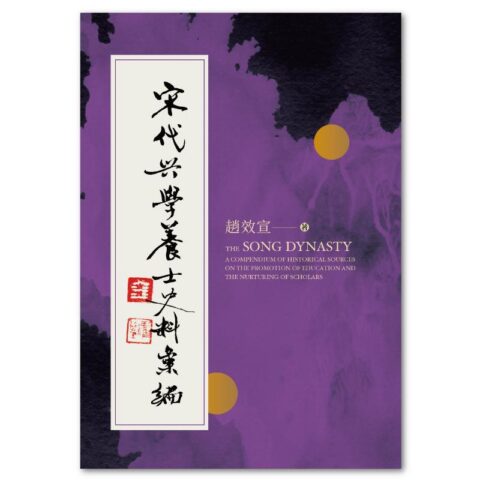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出版日期:2023-06-15
作者:勞榦
裝訂:精裝
EAN:9789570869484
尚有庫存
收錄勞榦教授自1951年1988年所著論文46篇
書末並附錄任長正先生編輯之「勞榦教授著作目錄」一篇
本書收錄作者勞榦教授的學術論文46篇,範圍涵蓋「歷史與政治」、「制度」、「思想史」、「社會史」、「地理與邊疆史」、「歷法」、「考古學及文字學」、「文學」、「典籍」等九個部分,以時代論,則以秦漢及古代史為最大宗。漢武帝是一個多彩多姿的君主,而且在位的時間比較長,因而在政治上形成了許多的變化。尚書官權力的樹立,由於武帝;內朝的建立,由於武帝;對策辦法的出現進而影響到選舉制度,由於武帝;開彊闢土,新設郡縣,創立刺史制度及以東移函谷關來形成畿內與關東交界,由於武帝;改革幣制,始鑄五銖錢,由於武帝;以至於把五月歲首改為正月歲首,亦由於武帝。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的確相當複雜。這一位對於政策和制度關係相當複雜的皇帝,在其一生中也被「宮廷陰謀」包圍著,而「宮廷陰謀」中,最重要的就是「巫蠱之禍」。
本書的內容就以漢武帝為中心,探討漢朝的政治及制度發展、邊塞組織與軍制、豪彊勢族及土地等諸多問題;往上延伸,從金文月相、《尚書》裡的〈召誥〉、〈洛誥〉來探討商周的年代,及《殷歷譜》的修正,提出新的見解;往下則討論到北朝都邑、中韓關係、「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以至佛教對於將來世界的適應等問題,在專業的鑽研之餘,展現了廣博的觀照。
本書初版於2006年,此為新版。
作者:勞榦
勞榦,號貞一,湖南省長沙人。1907年出生於陝西省商縣,1930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並兼任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教授。195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至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授,1975年從加州大學退休後為榮譽教授,1982年被聘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2003年8月30日病逝於美國洛杉磯。
他的研究範圍以漢代為中心,上及上古,下及北魏晉南北朝。對於漢代前後的研究,主要以制度方面為主,做了不少有關秦漢的政治制度研究,從中央官制到地方官制都有所論列。如〈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既找出了漢代中央機構決定權所在,又找出了漢代宦官和外戚所以能夠掌權的關鍵。如〈秦漢九卿考〉,說明了秦漢九卿制的演變。睡虎地秦簡發現以後,證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專著有《居延漢簡考釋》、《漢晉西陲木簡新考》、《秦漢史》、《敦煌藝術》、《成廬詩稿》、《勞幹學術論文集》、《魏晉南北朝史》等。學術論文主要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央研究院院刊》、《清華學報》等刊物。
自序
一、歷史與政治
中國歷史的週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
秦漢時期的中國文化
從儒家地位看漢代政治
戰國七雄及其他小國
秦的統一與其覆亡
漢代尚書的職任及其與內朝的關係
關於「關東」及「關西」的討論
霍光當政時的政治問題
對於〈巫蠱之禍的政治意義〉的看法
論齊國的始封和遷徙及其相關問題
二、制度
與嚴歸田教授論秦漢郡吏制度書
再論漢代的亭制
漢代的軍用車騎和非軍用車騎
釋漢簡中的「烽」
論「家人言」與「司空城旦書」
三、思想史
《鹽鐵論》所表現的儒家及法家思想之一斑
釋《莊子‧天下篇》惠施及辯者之言
記張君勱先生並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影響
論儒道兩家對於科學發展的關係
評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
論佛教對於將來世界的適應問題
四、社會史
漢代的豪彊及其政治上的關係
戰國秦漢的土地問題及其對策
簡牘中所見的布帛
中國古代的民間信仰
五、地理與邊疆史
從歷史和地理看過去的新疆
秦郡的建置及其與漢郡之比較
中國歷史地理──戰國篇
論北朝的都邑
中韓關係論略
六、歷法
金文月相辨釋
商周年代的新估計
論周初年代和〈召誥〉〈洛誥〉的新證明
修正殷歷譜的根據及其修訂
七、考古學及文字學
釋築
漢代的「史書」與「尺牘」
中國文字之特質及其發展
釋武王征商簋與大豐簋
秥蟬神祠碑的研究
The early use of tally in China
On the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s
八、文學
古詩十九首與其對於文學史的關係
崑崙山的傳說
說拗體詩
九、典籍
古書重印問題
《中國古代書史》後序
附錄:勞榦教授著作目錄(任長正編輯)
自序
當六十五年十月,我的論文集出版,現在又十四年了。在出版論文集時,已有未能找到的論文,到了現在,又有不少新作的論文。為了要搜集起來,來顯示近年工作的大概,實在還有再出一部文集的必要。因為各篇論文是彼此相關的,只有集合起來,才可以互相補充和互相比較,來現出一些問題中比較完整的形貌。在這裡除去做了分類的工作以外,在這些論文中,也還有再加詮釋的重要性。只因為篇幅有限,在這自序中,也只能根據幾個重點,加以申說。
首先要說明的是治亂週期與朝代週期的問題。宇宙中許多事物都有其週期性,四時代謝是人所共知的,常見的例如日食週期、地震週期以至噴泉週期,尤其商業的景氣週期,是國民經濟上一件大事。治亂週期就是綜合了若干小的週期而形成了若干大週期。這個看法的基點是根據李四光用戰爭次數,而統計出來治亂週期。若再深入研究來尋求解釋,就知道和朝代週期相關性相當密切。而社會組織的週期也有相當的影響。朝代週期無疑的是和君主世代的能力漸減性有密切關係,但統治的士大夫階級如其各家族長久的繼續下去,即使朝代已換,仍然保存前朝社會組織,也可能將前朝許多因素沿襲下去,而與前朝仍在同一的治亂週期以內。但是人類的社會是不斷進展的,科技的應用也是不斷進步的。治亂週期所含因素本來非常複雜,再加上時代的進展,後一週期自然和前一週期不同。只是對中國來說,中國數千年一直是家族統治的專制政體,所以一個朝代最長不過二三百年,到了朝代結束,就可能即是天下大亂、人民痛苦之時。今後也只有脫離家族影響之後,才會突破原有朝代式的轉移,而開創民族未來新的形式。只是舊的痕路,刻畫很深,解脫出來,當然也是相當費事的。
關於〈漢代尚書的職任及其與內朝的關係〉這一篇是繼續以前所作〈漢代的內朝與外朝〉那一篇而來。所謂「內朝」,是指天子的文學侍從之臣,特別提出來的九卿大夫再加上天子親近的將軍而形成了一個親近顧問的團體。外朝是指丞相以下的朝官,各有所司而不能時常接近天子的。在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時期都沒有這麼重要,到武帝時期,卻養了一群的「天子賓客」,形成一種「智囊團」,做成了一個政策制定的中心,而使丞相只能負執行的任務。其中加官(把一個特殊名義加到公卿大夫等朝官上去)如散騎、左右曹、給事中、諸吏;專任的如侍中、常侍;從外面調來,不必再加上名義的,如將軍;都是屬於內朝的各種官職。但內朝只是顧問的團體,雖然成了決策的源頭,卻還要天子的詔書,才能發生效力,因而尚書一職,就變成了發號施令的關鍵部分。至於尚書官署應當算到內朝,還是應當算做外朝?以尚書的機能來說,無疑的,應當算內朝的一部分。因為侍中、給事中,應當算內朝的「委員」,而尚書卻是內朝的「秘書」,再由天子裁斷諸事。不錯,在外朝議事時,尚書令也出席,所以就機能方面言,他是天子的秘書,而不是丞相的部屬。不能因為尚書出席外朝,而認為是外朝之職,這是事實演變的結果。以後就使尚書令成為真正的宰相,而原來稱為「宰相」的司徒和司空變成只是一個尊貴的虛名了。
內朝這個機構既已成立,霍光當政就是利用大將軍的內朝地位,憑著武帝遺詔,控制尚書機構而來掌權的。到了後來的當政大臣,就更加上領尚書事、錄尚書事、平尚書事等等正式名義。東漢時期,當政的外戚也都是以大將軍或車騎將軍輔政而加上領尚書事或錄尚書事的職銜。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所有權臣也都沿用這種名義。
漢武帝是一個多采多姿的君主,而且在位的時間比較長,這就形成了政治上許多變化。尚書官權力的樹立,由於武帝;內機構的建立,由於武帝;對策辦法的出現而影響到選舉制度,由於武帝;開闢疆土,新設郡縣,創立刺史制度以及東移函谷關來形成畿內與關東交界,由於武帝;改革幣制,始鑄五銖錢,由於武帝;以至於把十月歲首,改為正月歲首亦由武帝。其中影響的確相當複雜。這一個對於政策和制度關係相當複雜的皇帝,在其一生中也當然會被「宮廷陰謀」包圍著,而「宮廷陰謀」當中,幅度最大的,要數「巫蠱之禍」。
巫蠱之禍的起因也是相當複雜的。第一,是武帝的健康狀況和情緒問題。第二,是武帝內寵和內寵間黨羽的爭鬥。第三,是漢代的民俗禁忌也深深的攙入政爭禍亂之中,而使關係更為複雜。第四,司馬遷的《史記》也牽涉到這個風波之中,而《漢書‧司馬遷傳》又收入了號稱司馬遷作的〈報任安書〉,使司馬遷和《史記》也多少和武帝晚年政局有點關係。因而巫蠱之禍更加深了其中的歷史意義。
這是討論《史記》是否「謗書」的一個關鍵。在《史記》中除去〈景紀〉、〈武紀〉遺失以外,只有〈平準書〉和〈封禪書〉對武帝略有諷刺,但這些諷刺的語句還可能認為是被人添加的。刪掉以後,可以無傷敘述的本文。所以《史記》全書應該是司馬遷在巫蠱之禍時,為避免牽連,把涉及武帝較多的景武二紀毀掉,在謹慎中保存下的著作。其被稱為「謗書」的,不是關於《史記》的本身,而是這一篇〈報任安書〉。因為〈報任安書〉的諷刺,是這封信中的本旨,不是附加部分。《史記》認做「謗書」既被人認定之外,後來蔡邕曾因董卓黨的嫌疑,請求續修漢史以贖罪。就因為不能再有謗書的理由,而被拒絕。由於名滿天下的蔡邕尚不能免罪,也就使賈詡為了自保,唆使董卓殘部李傕、郭氾等叛變,以致洛陽覆沒,東漢政權也毀了。
其實〈報任安書〉文章好,並且還有內容,作者對於司馬遷的思想,了解得相當深刻,從來就沒人懷疑過。但是這封信的本身卻有很深的矛盾,影響到是否可以合理存在的問題。此書中「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表示寫的時候是正在巫蠱之禍以後,漢武帝的大整肅時期,當時天下囂然,人人自危。司馬遷當時未被巫蠱之禍牽入,自保還來不及,怎樣可能寫這封激切的信給當時重罪的囚犯?如其說這是一封寫好未發的信,那司馬遷連〈景紀〉和〈武紀〉都不敢保留,又怎敢家藏這篇激切的信,來作牽連入罪的證據?試看一看《昭明文選》卷四十一中有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接著就是楊惲的〈報孫會宗書〉(惲文出《漢書》本傳)。這兩封信都是氣勢雄肆的好文章,比較之下很有相似之處。如其〈報任安書〉為一篇仿作,而非司馬遷的親筆,應當只有楊惲才有此資格。
在〈再論漢代亭制〉、〈釋簡中的「烽」〉以及〈與嚴歸田教授論秦漢郡吏制度書〉幾篇文字,都是根據漢簡討論漢代地方制度中的幾個問題。漢承秦制,採用的是「郡縣制度」,而郡縣制度實可溯及更早。《左傳》哀公二年,晉趙鞅所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一直成為問題,實際上郡縣制度距此稍後,就可證明早已秦漢相同,所以上下二字實是鈔寫的錯誤,當作「下大夫受縣,上大夫受郡」。也就是郡縣制度在春秋晚年,已在晉國開始了。
漢代的邊塞組織,是屬於地方性質的。所以從漢簡中整理出來的新證據,也是主要的和郡縣制度相關。郡吏和縣吏的組織,是郡縣制度中一個重要部分,縣以下的鄉亭和鄉里的組織,又是另外的一個重要部分。鄉是縣以下的分區。鄉以下又分為兩種不同的管理。「鄉里」是以居民的人口為主的,里是戶籍的基本單位。另外,「鄉亭」是以道路的遠近為標準的,亭是其中的基本單位。在邊塞上,亭的防禦性更加強一些。在漢簡中也叫作隧。隧除防禦性以外,又是一些通信的據點。其通信的種種方法,是烽煙、烽表以及苣火。隨著塞外情勢嚴重的程度,而加以區別。不過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時調整的。這是根據敦煌漢簡、居延漢簡和居延新出漢簡所得的結論。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疑問。亭既然只是一種治安或防禦單位,而不是一種戶籍單位,為什麼東漢以後,列侯的等級可以分做縣侯、鄉侯、亭侯三等。這個亭侯的亭,顯然是代表區域的。對於這種事實的解釋,是:漢代封侯的標準,是以戶口(稅收)為代表。受封亭侯的,所畫的區域,往往需要小於鄉而大於里;恰恰亭的巡邏區域,正好大致和這相符。這就變成了亭是受封區域,實際上亭的任務和戶口登記並不相干的。
關於古代地理問題,首先要討論的,是齊國的東進事項。這就是〈論齊國的始封和遷徙及其相關問題〉,這篇是一個政治問題,所以列入「歷史與政治」一類中。不過有關地理問題,也應當討論一下。齊的始封,雖然號稱始於太公。不過按照周初一般情形,第一個國君應當不是太公而是齊侯呂伋。當然太公也可能到過營邱,不過也應當和周公、召公一樣,並未自己就國,而他自己仍長駐鎬京。周公是比較清楚,並未長期居魯,召公也並未長期居燕。太公雖可能到過營邱,他在京師任職,卻未能長期居留下去。在齊、魯、燕三國中,始封時應當是同級的大國。但後來齊、燕都有超越的發展,而魯國卻衰弱下去。傳說中齊國尊賢,而魯國尊親,以致情況相殊,這只是以成敗來推論的,最重要的還在於有無敵國外患。魯國接近中原,有宋衛等國支援,邊疆問題不嚴重。齊國接近邊陲,一定要自行解決邊疆問題,而和萊人就有不能並容之勢。東進的必需,就成為齊國進取的契機。
因為齊國是逐漸向東發展的,齊國的始封按地理形勢,是在漢代濟南郡治所在東平陵附近,亦即現在章邱縣附近。傳說中太公始封的營邱就在臨淄,是絕對錯誤的。齊侯不取萊,臨淄是不可能作都城的。城子崖的古城是考古發現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古代遺址,只有認為在營邱的齊國故址,這個歷史的空白才可能把它填補上。當發掘城子崖時,時期太早,並無齊國東進的觀念,無意中把臨淄當作營邱,以致全盤擾亂,現在是糾正的時候了。 〈秦郡的建置及其與漢郡的比較〉是一篇對於秦時郡制的研究。漢郡是從秦郡沿襲而來,其中頗有因革。《漢書‧地理志》中對於各郡頗有注明;但其中忽略的地方太多,而且還有明顯的錯誤。歷來各家討論秦郡的人很多,但不知為了什麼,大家一致都有這個大疏忽,一直沒有人看出來。這就是漏了河內郡。
此郡從戰國到漢一直不可能取消掉,可是從來討論秦郡的學人,都把河內郡忘掉了。從戰國開始,河內的鄴一直是魏國的重要城邑。孟子見魏惠王,魏惠王說「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河內及河東,正是魏國兩個重要的郡。漢代河內、河東及河南,稱為三河,兩漢時期,都是全國的重要據點。這就是河內地理位置(商代舊都,而且南北朝時,亦屢建都邑),戶口和財富,都一定要被重視。自來講秦制的學者把河內畫入東郡,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秦併六國,設置郡縣,其郡界還是依照六國時的舊界。為的是各國有各國的賦稅制度,而且各郡的文籍檔案,各自集中到郡治,沿襲舊界,比較方便。河內屬魏,東郡屬齊,兩國舊制不同,更無把肥饒的河內取銷,勉強歸入東郡之理。所以秦代一定有河內郡的。因為新的設想加入了河內郡,其他郡數也就要斟酌更改了。
有關歷法一項,這是一個相當複雜而困擾的問題。歷法本身已經夠複雜的了,再加上中國古代歷法問題,更具有許多難於解決的疑點。自從甲骨發現以後,殷歷的排定,是研究甲骨文當前需要的事項。當時群言龐雜,有種種不同的設計,最後是董作賓先生認為殷代用的還是四分歷,總算把原則問題歸於底定。董先生的《殷歷譜》也是一個精心排比下的不朽之作。只是董先生所採用的武王伐紂的定點,用的是唐代僧一行算出的前1111年,而僧一行又是據劉歆的算法而改訂出來的。在國際間通用的武王伐紂年代卻是前1027年,這是據《古本竹書紀年》定出來的,劉歆未能看到《竹書紀年》,所以無法採用這個年代,而自行臆斷採用了另一個年代,國際間的學者都認為證據不足,不予採用。因而董先生的《殷歷譜》也就在國際間甲骨文研究中被擱置。
要想把殷歷譜和國際間認可周初年代搭上橋樑,就得把殷歷譜加以設計,使其適合於被認可的年代,通過了種種的準備工作以後,得到的結論,是武王伐紂,也就是周代的開始應當在前1025年,比國際通用的前1027年後了二年。不過這也是可以解釋的,因為《竹書紀年》用的是建寅歷,而周代官方用的是建子歷,武王伐紂正在建寅歷的年尾,建子歷的年初,所以要差一年。再加上周代各王還可能有未逾年改元的,這就再差一年,也很容易。
若照前1025年為周代開始,算起來周初諸王的在位年數和年壽有一些出人意表的差異。其中大致的估計,是:
文王在位五十年,年壽約為六十五歲。(《禮記》按傳聞文王壽九十七,武王壽九十三,與真實歷史矛盾,不可信據。)
武王在伐紂以前在位十三年,伐紂以後在位四年,共計在位十七年,年歲當為五十六、七歲。
成王在位二十一年,約為十三歲即位,其中周公攝政七年,二十歲親政,年歲約為三十三歲。
康王在位十九年,約為十六歲即位,年歲約為三十四歲。
這個數目因為成康令主壽命如此的短,令人驚異,不過比較兩漢的君王,就不覺到不合理了。西漢除高帝和武帝以外,沒有一人到過五十的。東漢更為清楚,除去光武年過六十以外,明帝四十八,章帝三十三,和帝二十七,安帝三十二,順帝三十,桓帝三十六,靈帝三十四。比較下來,成康兩代的年壽只有三十多,不算稀罕。只是倘若真的如此,就不免使人失望罷了。據《文選》三十五,漢武帝〈賢良詔〉李善注引《竹書紀年》「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也指實成康兩代,總計確為四十年。但是成康兩代年數不夠多,總使人不服氣。我也查到了前1051年干支與前1025年略同,希望能找到這一年。但是對這一年,什麼有力的證據也找不到,就只好放棄了。
以上除去大致談了一些歷史問題以外,主要說的是有關於官制、地理和歷法的問題。因為這三項是會被人認為煩瑣的學問,但是歷史與文化的許多關鍵問題,又需要這三項的結論來解決,所以盡量避免繁複,就其重要的中心點來重新敘述。
為了還有許多方面上文未曾討論到,現在以〈漢代豪彊及其政治關係〉為主,就社會和文化方面,再來討論一下。首先要問的是:什麼是「豪彊」。就史料來看,豪彊指的是一個家族,而不一定屬於個人。《漢書‧王莽傳》「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這裡所謂豪民,當然指豪富的人們。《史記‧呂不韋傳》:「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這裡所謂豪家,當然指財富之家。子楚夫人也就是秦莊襄王王后,秦始皇的母親,其家得為豪家,究竟原來就有錢,或者由於呂不韋替他們經營出來,這不關重要,所要認定的就是豪家的條件是財富。
秦始皇的外家既然屬於財富家族,所以在統一六國之後,對於私人的財富,是加以承認的。在《史記‧貨殖傳》中看到的,只是非常少數的選樣,卻顯然可以看出來秦始皇對於私人財產表示的態度。張良是反秦的健將,他的能夠活動,還不是靠他的財產來支援。甚至項氏叔姪,他們能夠起來,也還是倚賴私人財富的力量。從春秋晚期以後,已經出現了財富集中的情況,戰國時代從都市的發展來看,更是豪富競起的有利時期。戰國時代的戰爭,除去損失兵員,耗減勞動力以外,對於發展中的都市,並未曾有大的破壞。到秦始皇吞併六國,許多國家抵抗不大,尤其是財富的齊國,幾乎只是去接收。楚漢之間的戰爭破壞性大些,但戰國時的豪門大姓,依舊還是豪氏大姓,這就形成了漢初豪彊勢力增長的情況。再加上幾種來源:第一是漢初的封國,成為新貴族,也就是新的豪家。第二是憑種種方法,新進的高級官僚,也會把他們家族變成豪家。第三是漢代領土的新開發,這些中原移民,也更有新的機會來增加財富。這些種種不同來源的豪家,也可能代替了舊日豪家因為種種原因變成了的「破落戶」,他們已經失去了豪家地位後所有社會上的舊有地位。
從戰國以來,許多客觀條件鼓盪之下,使封建的國家形成了官僚的帝國。這些大小的官僚,需要有人候補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文官制度,自然應運而生。戰國時期百家之學紛紛傳授也不過是為了補充職業的官僚。秦始皇晚年,李斯建議焚書,禁詩書及百家語,「有欲學者,以吏為師」,所謂「以吏為師」是要吏員帶門徒,而《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就是準備著應用的教科書,當然,這是不夠用的,等到漢代開始,雖然最先「挾書之律」還未除去,但自由傳授也就進行起來,也就等於把學校傳習,和文官制度聯結起來。東漢左雄建議的「諸生試家法,文吏議章奏」雖然是較晚時期的事,但不論「諸生」或「文吏」都是官僚的候選者,從漢初已經是這樣的。
照《鹽鐵論》中桑弘羊所說的「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這是表示著文官制度雖然在西漢中期已經樹立了安定的軌道;但不論是學校,或者是郡吏,一定是豪門要占些便宜。《後漢書‧馬武傳》說「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可掾、功曹。」這就是表示著漢代郡吏的升遷,要靠幾個條件:學力能力是一個條件,品行是一個條件,而家庭關係也算一個重要條件。這裡光武說「卿鄧氏子」,就可見到在升遷中,家庭在當地的地位,非常重要。這種情形,就會使豪門的優勢,更容易延續下去。
漢代朝廷命官不外幾個來源:郎署、太學、孝廉、上計吏,再加兩種特殊的情況,由功臣或列侯出任,以及由郡吏得著特殊機會逐漸升遷。這些管道看來,還是對於豪家占便宜些。其中清貧卓行力學之士誠然也有,只是機會少些。兩漢書中,誠然有不少出身清寒的人士,但卻不可以把此與貴戚豪門列名的人來做數字統計的。因為出身寒微的人,能夠冒出來,一定有特殊能力,而憑家世財富出來的人,反而多屬庸碌一流。所以清寒出身在正史列傳中所占的比例和清寒出身在當時官吏總數中所占的比例,一定不能相同,也就難以統計了。
自從隋唐實行科舉以後,雖然使清寒的人出路稍寬一點。但因為科舉的標準受到種種限制,所取的不免多數是「帖括之士」,還是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論者不免回想到兩漢的舊辦法,認為這一種「鄉舉里選」,比較上應為更公平的辦法。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號稱屬於「鄉舉里選」的孝廉推薦,除去少數的特例以外,推薦候選人的郡太守,被貴戚、豪彊的「關說」壓迫之下,是無法公平處置的。在《後漢書‧种暠傳》有一段感人的事實,說:
始為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能相違,欲得一名士,以報國家。」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守,暠對辭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這裡敘述到的田歆,當然是一個賢的長官,但也不能不敷衍關說的人,勉強擠出一個位置來推薦人才。那就可知在當時的文官制度下,人才與非人才的比例了。左思〈詠史〉詩:「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這些世胄以及豪彊,在政治及社會上有特殊優惠的機會,在任何一種少數人控制的政權下,都是一樣的。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確實少許有些補救,但取不了真正的人才,也是無可如何的。
貴戚在功能上亦是豪彊,而貴戚以外的地方豪彊,亦所在皆然。雖然不論貴戚或地方勢力,對於中央的政令,都是衝突的。依照法家思想,在一個政權之下,只能馴服在一個來源,所以不論貴戚或者地方大姓,都不能對於天子的絕對威權加以妨害。漢武帝設置刺吏,以六條察郡國,制止豪家大姓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目的。不過不論是怎樣有力的中央,對於豪家大姓,也只能加以抑制,而不能加以消滅。不論何處,還是大姓占了上風。敦煌一處,唐末到宋初的史料還存在了一些,其中張、曹、李、索四姓,可以遠溯漢晉,其中李姓則為隴西成紀李姓世族的後人,這就可以看出大姓傳統也延長了時間不少。魏晉南北朝世族掌政的局面,實際上也是源遠流長的。
這本論文集牽涉的方面比較多,稍加解釋補充,已經費了不少的文字。為了節省篇幅,就此作一個小結束。對於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惠予出版,非常感荷,謹志深厚的謝意。
勞 榦
一、歷史與政治
中國歷史的週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
凡是一種延長下去的進展都有它的週期性,不論生物或無生物都是一樣。生物的個體是非常顯著的,具有它的幼壯老死。無生物也是一樣,一年的四季,一日的朝暮當然是週期,即是就宇宙全部而言,也一樣的含有週期性,只是這些週期性不完全都被人類測得罷了。
中國歷史當然不會屬於一個例外。所不同的是中國因為特殊地理形勢的關係,和世界其他部分被高山、大海以及大沙漠隔絕著。在鴉片戰爭以前,所有對外的交通都在半封閉狀況之下。雖然間或受點外來文化上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始終未成為主流。因而中國歷史的週期,在過去的時候始終是在幾個類似情形之下,複合了上一個週期的升降。
週期,當然不就是一種簡單的週期。週期的形成決不屬一個簡單的原因,而是複雜的因素湊合而成的。並且週期之內還包括了許多小週期,週期之外還要彙合其他週期造成更大的週期。所以對於人類歷史來說,最大週期是什麼樣的週期,還不是現在的人所能解答。
中國的朝代本身是一個週期,這一種的週期代表了興衰和治亂。就一般情形來說,除去特殊短命的朝代不算,一般典型的朝代,大致是二百年至三百年。形成這個期限當然不是一些簡單的問題,不過就其主要方面的原因來說,至少以下各項,是其中比較顯著的。
一、君主家族的興衰與朝代的興衰
不僅一個帝王家,一般凡庶閭里人家也是一樣有興衰的週期。俗語所謂「千年房地八百主」,就是對於人家盛衰無常的一個通常看法。尤其對於帝王家,他們的子弟都是封閉而隔絕的,過著非正常的生活,那就破敗更為容易。之所以能夠維持,是靠著君臣的「名分」,等到腐爛已極,君臣名分不再能發生作用時,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這是比較容易解釋的,凡是君王專制的政府都是全國的官吏最後向君主一個人負責。君主的權力和責任是非常重大、無限制的。尤其東方型國家,並無和君主對抗的教會,那就君主的地位更為超過了一切。人究竟是人,一個智慧很高、精力很強的人,也不可能處處精神貫注。在全國的萬幾寄託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也決不可能幾十年如一日,絲毫不發生變態,也不發生厭倦。所以創業帝王在開始創業制度的時候已經會時常照顧不周,而且更會照顧的方面越多,後來發生的弊病更大。這些創業時的定制經過時候越久,越會和後來的情勢不能適應。到了祖制成為進步的嚴重阻礙的時候,就是這個朝代壽命終結的時候。
其次,一個朝代的興衰完全和一個家族的興衰合而為一,這對於朝代方面來說是更為不利的。就普通一個家族說來,越是大家庭,越容易崩潰。因為大家庭中的子弟,差不多都是不學而依賴,不能抵擋住外界的風波。所以一個富貴之家傳了幾代之後,子弟們多半會一代不如一代,最後歸到總崩潰的路上去。至於帝王家中的情況,比普通富貴之家情況更為嚴重。皇子皇孫往往都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與民間社會毫無接觸,成為一點世故人情也不懂的人。不但如此,這種教養下的子弟不僅知識薄弱,甚至身體也一代不如一代,最後甚至缺乏子嗣。缺乏子嗣的情形,是從記載上看出的,如同西漢、東漢、唐、宋、明、清,都有這種事實。至於身體的衰弱,不僅從記載上可以看出,畫像也可看得非常明顯。現在歷代帝王的寫真畫像,是從宋代開始的。宋元明三代保存在故宮博物院,清代保存在北平的大高殿。這些畫像並且都有影印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上幾代相貌比較正常,到了快亡國的時候,那就逐漸的瘦削下去,表顯著體質上的退步。試問對廣圓萬里的大國,把一切的生命寄託在一個身體衰弱不堪而又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手裡,這個國家那有不亡的道理。朝代的政權代表著安定的力量,等到這一個安定力量瓦解時,一個大的混亂就會產生了。
二、政治組織中積弊的加深與朝代的覆亡
在一個君主專制政府之下,主要的是靠「人治」,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表面的。因為制度也是「法」,法可以限制官吏,限制平民,卻不能限制天子。倘若任何法律制度被天子感覺著不便,就會被天子改訂,而使法律制度變成破碎。況且天子高居於九重之上,具有一個孤立的形勢。做天子的人自己覺著孤危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天子最怕的事一是大臣擅權,一是小臣結黨,同時也盡量想打開近臣的蒙蔽。所以開國的君主以及前幾代的君主,會把法屢次改動或者加上許多附加的辦法,或者再在政府機構中加上些駢枝的機關,使法律制度失掉了原形。到了後幾代的君主就更會明白的違法,使法律制度失掉了效用,以至於國家不能維持。以下是政治制度中幾個最著名的例子:
宰相制度發生的問題與其演變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進行,最有效率的辦法,是選擇一個有能力的人,使他專負宰相的責任。這樣就和君主立憲國家的內閣比較接近。西漢武帝以前的丞相,就是這樣一種任務。漢武帝是一個英明而猜忌的人,他對於這種專責丞相制度不滿意。首先他不用他祖母的姪子竇嬰而用他母親的同母兄弟田蚡做宰相,後來又不滿意田蚡的專斷,而說:「君署吏竟未?吾亦欲署吏。」這種話。所以在他在位的時期,他是極力摧毀宰相的權力的。他的特殊創作是:
甲、用內朝來代替宰相。內朝是天子周圍一班顧問,以天子的私人秘書組成的一個小團體,天子有他們的幫助,就可以處置許多政務,命令宰相去執行,減輕了宰相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宰相府從一個決策機關變成一個承轉的機關。
乙、用平民做宰相,打破了漢代以貴族來做宰相的傳統。並且大量的把有爵位的貴族降為平民。這樣就使得宰相的地位無形降低。
丙、嚴格控制宰相,並且嚴厲的懲罰宰相,使得宰相畏罪,不敢發表意見,而結果成為「伴食宰相」。
自從漢武帝嚴重的打擊宰相以後,君主削弱宰相的權,不僅成為漢代的傳統,也成為中國君主的傳統。這種進行的路徑是:(1)從獨相制度變為多相制。(2)各朝開始時照例用近臣來奪宰相的權柄,等到近臣變為實際上的宰相時,又再以另外的近臣來取代,成為循環不已的現象。而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明太祖廢除宰相,而採用六部分司制,實際總其成的,是翰林院的大學士及內廷的司禮監。後來大學士成為實際的宰相而司禮監卻成為超級的宰相。因而明代宦官的禍患就一天比一天深,而終於無法救藥。
天子始終是猜忌宰相的,宰相的權伸張了一點就被壓制下去。因為每一代的天子都要把朝廷中官吏變成互相監視互相牽制的局面,所受到影響的,自然是官與官之間都是敷衍,誰能敷衍的就名利亨通,誰不能敷衍的,往往得咎。這種局面一代一代的傳下去,自然任何一處的積弊日深,以至亡國而後已。
不僅中央官吏是互相牽制的局面,無法做事,地方政區也是一樣。郡縣制度本來系統非常簡單,可是各朝也是逐漸變成複雜。在各朝開始時期稍整頓一下,但各朝的演變也總是變得複雜而決不會再變簡單,因而地方政區的效率,以及政風,也是越來越不如以前。
三、士大夫家族的問題化與朝代的覆亡
士大夫家族在各朝的演進中,他們對於政治上的活動,還有激烈的競爭,不是像君主那樣世襲的,所以比較皇家,衰敗的要略為緩慢一點。不過就全士大夫團體來說,各朝的晚期較之各朝初期,其中的問題也是漸次增加的。等到問題惡化之時,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存在性。因此加深了一個朝代的崩潰。
競爭之激烈化,以及競爭失敗者的冒險──在一個一統帝國成立之後,如果君主成為唯一的力量,沒有別的力量可以抗衡時,那君主將會打擊其他可能發生的社會力量以便於統治。中國歷代的賤商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商人是被法家認為一種亂世之民的,為的是所有的榮譽都得出於君主之授予,然後權力之運用才可以方便。倘若做商人可以得到鉅量的貲財,而鉅量的貲財可以購買到社會上的榮譽時,那就君主運用的最大工具「刑」「賞」中的「賞」,可以不必經君主的同意而自由取得。所以各個朝代有的是公開的賤商,有的是法律上暗中賤商。
歷代賤商大致說來是成功的。君主雖然未消滅商人(當然也不可能消滅商人),可是剝奪了商人的社會地位,使得天下士子覺得只有為皇帝服務才是天下最光榮的道路。這就是只有做官才算榮譽,凡找榮譽的人只有想法去做官才可以。在一個朝代初建之時,政治尚未安定,百姓比較貧窮,為著起碼生活而忙,想做官的人還少些。到了政治越安定,社會越富足,需要做官的也就越來越多。國家的官有限而請求做官的人無窮,競爭自然越來越激烈,而成為造亂之因。至於商人被壓制的情形,可以分為下列三個時期來說。
(一)察舉時代:這是指兩漢時代而言。西漢初年一切簡樸,郎官是可以從貲財選拔出來的。這就暗示捐錢還是一條間接求光榮之路。所以社會還較為安定。到了西漢中葉以後,太學生的數目日漸增加,雖然表示文化進展,可是太學生的出路只為了做官,就不免有競爭淘汰的現象。這些競爭失敗者並不能「歸田」的,自然還得想法子活下去。王莽時頌功德的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當然都是職業的頌德者,這就形成了西漢改朝換代的原因之一。
東漢建立,教育更為發達。可是到了東漢晚年,太學竟成為游談之所,是非之場。黨錮之禍固然是士大夫的不幸,而三國初年的紛爭割據,實際上割據的軍閥也無一處不有士大夫作為謀士,東漢也就改朝換代了。在東漢晚年較為安定之時不難想像到許多的讀書人殘酷的受到職業上的限制,一點出路也沒有。這些人為榮譽起見不能做商人,受體力的限制不能做農人,甚至由於缺乏寺院的組織而不能做和尚!倘若說三國初年的動亂與士大夫職業無因果的關係,是不大可能的事。
(二)大姓壟斷時代:魏晉以後察舉的名義仍然存在,不過另外還有九品中正制度,對於朝廷已有地位的人士,更為方便,並且還有許多最有地位的子弟,不必經過一些考核就可以為「黃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這種大姓壟斷的情形,到了東晉和南朝,更為顯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不過就政治的安定方面來說,卻也有其功用:(1)寒微的家族對於高官已經無望,就不妨去做商人,反而有益社會的安定。(2)君主以外大姓具有政治上的相當力量,可以使君主變而政府的機構不變。但其壞處則為這一些大姓成為統治階級已久,其子弟生來就有富貴,以致多數人是不中用的,不能應付突然的事變。所以梁武帝晚期成為自然崩潰之局。陳朝雖然用了一點新人,卻仍不能抵抗隋師的南進。
(三)科舉時代:這是從隋代到清朝晚期一個長的時期,占了十三個世紀,對於中國近代社會及政治的影響至為深厚。科舉制度自有其優點,因為科舉取士從來未曾計及到世族寒門的區別,這就比較公平,不僅矯正了大姓壟斷時代的過失,並且比察舉制度也公平一些。察舉制度雖然號稱察舉賢才,但到東漢時期早已由世族把持了。科舉卻未曾被把持,尤其到宋代彌封卷制採用以後,更是完全看卷不看人,給從前寒微之族一個比較公平的出路。
不過科舉制度就其對社會安定的貢獻而言,卻是功過相參,並非完全都在正的方面。科舉取士的標準,不論其為辭賦,為策論,為經義,為八股文,都是按文章的好壞來定去取;而文章好壞的絕對標準,卻是沒有的,只憑主試的好惡甚至憑主試臨時的好惡來決斷。「文章自古無憑據,惟見朱衣暗點頭。」已成為應試的口頭語,所以應試的人多少要帶一點投機或賭博的心理。試問把全國的人引誘入賭博之途,這種政治如何可以走到正確的路線上去?
唐代進士很少,而應試的士子甚多,所以在唐代詩文之中,時常看到落第之事。宋代進士雖然名額增加,可是應試的人也增加。明代把舉人也算成資格,可是舉人在明清時代也不易取中,甚至於只要能在府學縣學做一學生(當時叫做秀才),也可以具有鄉紳的資格。這就使全國人的精神才智都集中到科舉上去。不論科舉考試的內容是什麼(宋代的人已感覺辭賦的無用,明代承經義而改的八股更壞),都是束縛人心,妨礙學問進展的絆腳石。妨礙學問的進展表面上雖然和政治的安定與否無關,但仔細分析一下,卻不這樣簡單。因為科舉把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限制在這一條路上,必需真能使多數得到滿足,才是安定政局的好辦法。但科舉制度並不能做到多數的滿足,只能使人存一個賭博式的希望。尤其不幸的是舉人、進士的名額都是非常有限的,開國時期一經規定以後,就難得再增。舉人、進士的名額已定,而人口的增加是愈後愈多而且愈快,則科舉的效用也會逐漸的減小。歷代民變中的主要分子,如黃巢、洪秀全以及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都是科舉落第的人士。其他一定還有更多不滿意的人,這就表示科舉制度的籠絡人心,在功效上是有個限度的,尤其是到了一個朝代的末期,危險性更為顯著。其中宋代是注意士大夫生活問題的,除去太宗時代曾經一度一榜盡及第以外,並且用種種辦法給予士大夫的恩蔭,讓他們得到了安置,可是這種無限制綏撫的辦法,也拖垮了國家的財政,使宋代在外族侵襲之下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