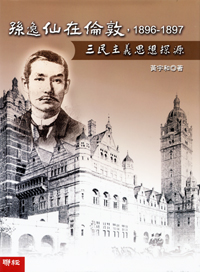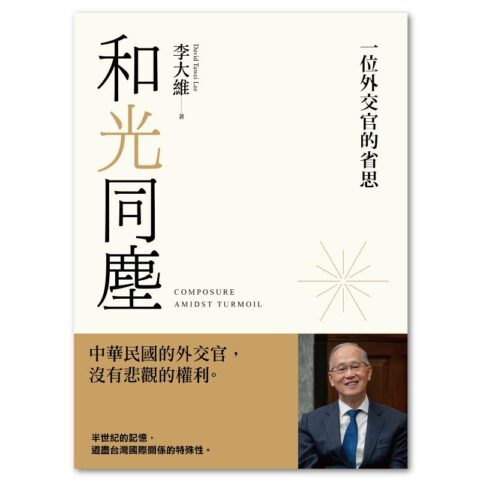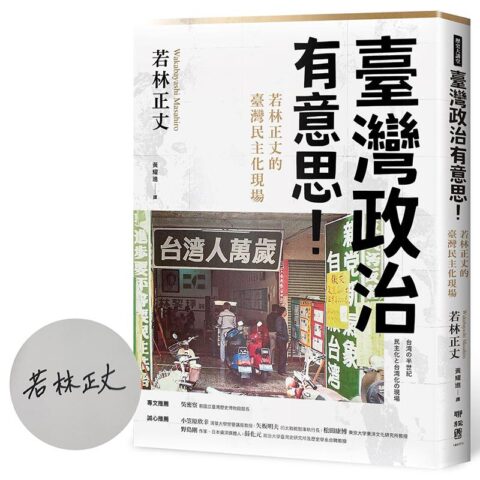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
出版日期:2007-08-10
作者:黃宇和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624
開數:18開
EAN:9789570831382
尚有庫存
國人談三民主義已超過一個世紀,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幾乎所有臺灣的大學都成立了三民主義研究所。有關著作,汗牛充棟,唯獨對三民主義的重要源頭之一──倫敦,探索極少。本書試圖作這種探索。全書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重建歷史,把孫逸仙1896-1897年間在倫敦的活動重建起來,以便鳥瞰其在倫敦時「所見所聞」。第二部份分析歷史,分析三民主義形成的過程內容以及當今之意義。第三部份反思:由於得到兩份高質量的匿名審查報告啟發,作者在出版前再對書稿作全盤檢視並提出回應。
作者:黃宇和
1968年香港大學畢業,即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1971年完成博士論文後留校。1974年起受聘到澳洲雪梨大學任教,2009年遞升至該校近代史講座教授;2014年2月退休,該校遴選其為榮休終身講座教授。1978年英國皇家歷史學院、2001年澳洲國家社會科學院、2012年澳洲國家人文科學院等三院全體院士,先後投票遴選黃宇和為該院院士。欲觀黃宇和院士全部履歷者,請至Google:「Emeritus Professor John Y Wong」,即直達澳洲雪梨大學為黃院士設計、隨時更新的英文網頁。
第一部份:重建歷史
第一章 緒論:三民主義完成於倫敦
第二章 孫逸仙旅英日誌
第三章 孫逸仙旅英圖籙精選
第四章 旅英期間談話、書信、佚文、著作
第二部份:分析歷史
第五章 民族主義思想探源
第六章 民權主義思想探源
第七章 民生主義思想探源
第八章 結論:倫敦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第三部份:反思
第九章 對本書的反思
中英對照
原始文獻
英文參考書目
中日文參考書目
自序
筆者在1968年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研究葉名琛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1974年到澳洲雪梨大學任教。1979/80年度,又從澳洲雪梨大學休假一年,外出研究和講學。先應廣州市中山大學歷史系代主任胡守為教授邀請,到該系講學一個月。再到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當客座研究員一年。在中山大學講學期間,陳錫祺教授勸筆者利用行將再度旅居英國的一年時間,分兵研究孫中山在英國的活動。筆者認為有理,對孫中山的研究自此開始。198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用英語出版了筆者第一本有關著作《孫逸仙英雄形象的來源》。 此後即繼續自費深入研究其“三民主義之所由完成”(中山先生自語) 。待有較紮實的基礎而同時又的確江郎“財”盡之後,即於1996年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申請補助研究經費。承該基金會錯愛,慨助美元25000,至以為感。雪梨大學副校長(Professor Roger Tanner)為了表示敝校的誠意,亦補助美元五千。特致謝意。
1996年底,筆者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所長邀請,到該所當訪問學者,並作學術報告。又由該所的呂芳上研究員介紹,到國史館作學術報告。那一趟臺北之行,讓筆者深刻地體會到,外國人雖然很領略筆者用英語所寫的東西,但總不及黃炎子孫聽筆者用漢語作報告時,有靈魂上的交往。此事引起筆者亟盼用漢語把當時正在研究和構思的《倫敦與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思想探源》,用漢語寫出來,以便直接與漢語的讀者神交。筆者的想法得到國史館當時的潘振球館長暨朱重聖副館長支持,既代筆者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總裁李亦園院士説項,又鼓勵筆者修書向李亦園院士提出此要求。 承李亦園院士俯允, 至以爲感。
1998年,更承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林能士主任盛情邀請,到該系當國科會客座教授。筆者被該系優美的漢語環境深深地吸引住了,於是就愉快地準備本書的撰寫。承國史舘電腦組的朋友們幫忙購進臺灣製造的電腦和軟件,筆者興致勃勃地開始了用漢語寫作的生涯。無奈用拼音輸入法寫作,畢生還是頭一趟。首先打入一個由一組英文字母組織而成的聲音,熒幕屏上即出現九個漢字。若其中有筆者所需的漢字,則上上大吉。若沒有,則把小老鼠移往九個漢字末端的箭頭上一按,熒幕屏上再出現九個漢字,若其中包括有筆者所需的漢字,則上吉。若仍沒有,則必須重新操作。當三番四次操作而仍未找到所需漢字時,眼睛已快掉下來了!匆忙間出現同音異字的情況極多,改不勝改,大大拖慢撰寫速度。
此外,當時筆者用以寫作的美國微軟公司設計的英語系統,只是上面附加美式的漢語輸入法而已。該美式的漢語輸入法,剛剛上市,甚爲粗劣,所用詞彙充滿美國的價值觀。當筆者用聯想方法輸入詞組之如“故事”的漢語拼音詞組時,熒幕屏上總是出現“股市”等字樣。當筆者輸入“藉機”的漢語拼音詞組時,熒幕屏上肯定出現“劫機”等字樣;輸入“鑑於”的漢語拼音詞組時,熒幕屏上老是出現“監獄”等字樣。這種由金錢、暴力與地獄所組成的詞組以及其所代表的價值觀,不斷地互相糾纏不清;絲毫沒有筆者夢寐以求的那種具古雅之風的漢語,反而徒增筆者的寫作困難。結果筆者在政治大學當客座的時間飛快地過去了,而拙著距離完成的階段還是遙遠得很!
筆者帶著失望的心情與疲乏的身軀飛返雪梨大學重執教鞭。由於拙著的插圖特別多,為了配合筆者的寫作計劃,承雪梨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沃特浩思教授(Professor Richard Waterhouse)特別照顧,在1999年向敝校申請到三萬多元澳元,購置一台高級電腦掃描器,讓筆者掃描那些筆者多年以來收集到的珍貴圖片。筆者堅持在課餘時間默默耕耘之際,2001年4月29日即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陳三井先生同月12日來示,囑筆者撰寫《中山先生與英國》一書,作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叢書的《中山先生與世界》系列之一,至以為榮為幸。但是問題馬上來了:筆者正在撰寫中的《倫敦與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思想探源》怎辦?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只好把手頭工作暫時擱下,自費研究和撰寫《中山先生與英國》一書。
經過三年多的日夜奮戰,以及環球飛行追蹤史料,終於在2004年8月5日星期四早上,筆者隨陳三井先生坐計程車到台北市區的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拜會陳志先秘書。筆者把《中山先生與英國》一書的打印件和刻有拙稿全部內容的光碟一張親自交了給陳志先先生,如釋重負。領取了十萬元新臺幣的稿費後,陳三井先生又陪筆者坐計程車到華南商業銀行提款,並全部將之兌換成英鎊,以便筆者在年底重訪英國,為草草寫成的《中山先生與英國》和還未寫完的《倫敦與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思想探源》作補充研究。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感慨萬千。筆者既為《倫敦與中國革命》的寫作中斷了三年多而惋惜,同時又因爲《中山先生與英國》的研究和思考而對中山先生的一生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認識。進而大大減少了筆者過去在撰寫《倫敦與中國革命》時那種局部與拘束的感覺。現在反而有鳥瞰之概了。樂哉!
又是一年過去了,拙稿《倫敦與中國革命》終於在2005年9月18日定稿了。拙稿部份章節曾先後承當時澳洲《自立快報》總編輯潘振良先生、廣州市中山大學的胡守為先生和邱捷教授過目,銘感於心。本書封面,蒙86歲的著名廣州書法家關曉峰先生賜字,並由廣州中山大學外事處的秘書黃小莉小姐就地在穗找人拍照寄給筆者,均誌謝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總編輯林載爵先生,多年來關心筆者對中山先生的研究,首先在1998刊刻了《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漢語本,現在又大力支持本書的出版,特致謝忱。林載爵先生畢生致力於造福學林,公德無量。對於李亦園院士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朋友們的海量汪涵,耐心地等待拙稿的完成,更是感激不盡。
本書稿投聯經出版公司,承該公司編輯委員會評審通過後,交兩位不具名審稿人評審。蒙兩位審稿人推薦出版,不勝雀躍。兩位審稿人又提出極爲寶貴的修改意見,為筆者全盤反思本書所牽涉到的學術問題創造良機,進而提高了本書理論層次,讓筆者增寫了 第九章“反思”,置於書末,佇候教益。
筆者香在港中學時代就讀的九龍華仁書院,為筆者打下了人生基礎。特別要感謝的,有幾位恩師。
蔡師成彭,專職講授數學。筆者之數學根底,皆蔡師所賜。蔡師又是筆者在九龍華仁書院時中一、中二的班主任。他大兒子在同校高我一班,用過的課本贈我,若學校改了課本,蔡師就買新書贈我。他又把大兒子不合穿的校服贈我。蔡師之待我,猶如慈父。在1965年春,擧校華籍老師都誤會我好吃懶做時,只有蔡師成彭,无需我隻字解釋,就清楚瞭解我是朝著更高的目標奮鬥。待我成功地從預科六級跳班考進香港大學時,所有讒言爛語,不攻自破;各方對我的誤會,方始冰釋。只有蔡師,自始至終沒有絲毫懷疑我的誠意。知我者,莫如蔡師。蔡師仙遊之後,我每次做統計時,都情不自禁地淒然下淚,懷念恩師不已。
恩師羅倫士夫人 (Mrs Tessa Laurence),1965年1-4月的課餘期間,義務指導筆者閲讀英國歷史。對筆者的治史方法,邏輯辯證,思維方式,敍事論史,影響既深且遠,可說是筆者西洋史的啓蒙老師。筆者終於能跳班考進香港大學,羅師之功至鉅。1968筆者在香港大學畢業而到英國牛津大學進修,亦是羅師伉儷到機場接機,指點一切。此後筆者重訪英國作科研,必親向羅師請安。
劉師敬之,專職講授中國語文。體恤筆者渴望有系統地學習四書、五經等古籍,退休後逢星期日即整天在其府上免費指點筆者,中飯亦熱情招呼筆者共用。筆者之國學基礎,由此而奠定。畢生受用之餘,對劉師永遠感激。劉師仙遊之後,我每次用漢語寫作,都懷念恩師不已。
江師之鈞,專職講授英國文學,具英國紳士風度,畢生追求完美: 教學時力求盡善,助人時竭力盡美。筆者這窮學生,在九龍華仁書院讀書時,就曾得到江師很大的幫助。當筆者在2006年2月17日,接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電郵擲下本書兩位不具名審稿人推薦出版拙稿時,同日噩耗傳來,江師仙遊!五內欲裂之餘,懷念恩師不已。
特以此書獻給九龍華仁書院各位恩師,以誌筆者感激之情。
第一章
緒論
三民主義完成於倫敦
(一)導言
孫逸仙嘗言:「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交結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一語道破了倫敦與中國革命的淵源。
准此,本書探索的時間和空間,是1896年9月30日至1897年7月1日孫逸仙旅英這段時間。當時他還未採用孫中山這個名字,而自稱為孫逸仙。當時他在外國也是用孫逸仙的音譯──Sun Yat Sen。為了更符合歷史原貌,本書正文全部採用孫逸仙而不用孫中山這名字。
三民主義,在中國近代史上,佔相當重要地位。首先,它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與保皇派交鋒的支柱,歷次舉事的靈魂。後來,在1920年代國共合作時期,孫逸仙所提倡的民族主義被大力宣傳下,凝聚了澎湃的愛國情緒,發揮了無窮力量。北伐戰爭,就是在這種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之下、發動並統一中國的 。儘管1927年後國共分家,但是有學者認為,此後中共所作的一切,都可以解釋為複雜的民族主義理論系統當中、一種特殊表現 。更有學者認為,民族主義推動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發展 。已故的費正清教授曾經說過,「中國民族主義的性質與實況必須搞清楚。」 無可否認,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這種現象,發韌於孫文學說。其次,孫逸仙的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也在近代中國不同的歷史時期,起過不同的作用。因此,探索孫逸仙「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 ,是一個甚有意義的課題。但是,孫逸仙沒有給後人留下任何日記、遊記、甚至簡單的筆記。誰知道他見過什麼、聞過什麼?更遑論探索他心裏想什麼及如何完成其三民主義的腹稿。這問題是多年以來困擾著史學界的焦點之一。這個難題是否永遠沒法解決?
近世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說過:「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陳寅恪先生的話,曾給予筆者很大的啟發。筆者對此話的理解是:「對古人之立說」,是可以高攀到「真瞭解」之境界,而途徑有二。第一,必須「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第二,必須「神遊冥想」,以便明暸其「持論之苦心孤詣」。關於第一點的「真實性」,則古諺有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至於第二點、即「神遊冥想」的重要性,則牛津大學前皇家近代史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核.特瓦若袙(Hugh Trevor-Roper)說得更直接了當。他說:「沒有想像力的人不配治史。」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古代史的大家;特瓦若袙教授是歐洲近代史的權威。可見,無論對古今或是中外的歷史,若要達到「真瞭解」的境界,「神遊冥想」是必經之路。
從研究近代史人物之如孫逸仙及其思想來源的角度來說,上述兩個途徑,在具體實踐起來時,如何走法?竊以為若要達到「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則最好是親臨孫逸仙活動過的地方,體驗生活,觀察環境,浸淫於接近當時的實際條件當中。再結合文物、文獻等,重建當時的各個歷史細節。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神遊冥想」,把各個表面上似乎毫無關連的細節,像積木那樣重新架構起來。所以,在過去的28個寒暑裏,筆者每年都必定重訪倫敦一、兩趟。每趟都一步一腳印地、三番四次地、「跟蹤」孫逸仙走過的地方。在倫敦市區內「跟蹤」孫逸仙,則無論多遠,筆者都是靠兩條腿和一部自行車。市區以外的、當年孫逸仙也要坐火車的,筆者也坐火車。每一次「跟蹤」後所得到的感受,都與前一次不一樣:是一次比一次深刻了。可以說,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發展,感受與認識的深度和廣度與時俱增。重新架構起來的「積木」,越來越比較像樣了。學問功夫是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信焉。
接著,在這個「積木」的基礎上,結合孫逸仙後來見諸文字的理論和行動,作「神遊冥想」,探索其三民主義思想的淵源。
下面比較具體地談談,在實踐過程中,筆者對上述三個途徑──即實地考察、文獻鑽研和神遊冥想──的體會。
(二)實地考察
就以孫逸仙倫敦蒙難這件事情為例吧。孫逸仙最初以為必死無疑。後來竟然又能逃出鬼門關。這種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驗,對他人生觀以至三民主義思想的形成,會有什麼影響?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必須搞清楚他被幽禁的整個過程。而弄清幽禁過程的第一步,又必須查清楚他是如何被綁架的。倫敦這麼大,又人海茫茫,為什麼孫逸仙在到達倫敦的第12天早上,就在公使館的正門被綁架進入公使館?孫逸仙別的地方不走,為什麼偏偏就要走過公使館的正門?公使館的人員,從何得知他們要綁架的這個人,就是孫逸仙?不錯,公使館是僱了一家名叫史雷特的私家偵探社,讓該社派人跟蹤孫逸仙。但是偵探的報告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線索。正如羅家倫教授很早以前已發現的、當孫逸仙被幽禁在公使館後,那飯桶偵探還堅稱、孫逸仙一直足不出戶地留在旅寓睡大覺 !
孫逸仙為什麼偏偏就要走過公使館的正門?如果我們親臨其地,沿著孫逸仙走過的地方,一步一腳印地「跟蹤」他;再結合文獻記載,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就很有幫助。孫逸仙到達倫敦當天,已是深夜,入住旅館後,就沒有再外出活動。第二天早上,他去探望恩師康德黎醫生 。他從旅館到康家是怎麼走的?筆者經過實地考察、比較各種交通工具和路線等,判斷出孫逸仙是徒步去的 。而徒步到康家,則必須由南往北走地經過公使館的正門。正門旁邊有兩道很大的窗戶,通過這兩道大窗,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
同時,該公使館位在缽蘭大街(Portland Place)與娓密夫街(Weymouth Street)交界的西北角。而公使館向南的側面、即面向娓密夫街這一方向的的那部份,每一層樓都有窗戶,讓公使館裏邊的人,有很長的時間,細心觀察由南到北、橫過娓密夫街的行人。而且,公使館每層樓都有三道窗戶、朝著娓密夫街,五層樓共15道窗戶。當孫逸仙沿缽蘭大街西邊、由南往北走而橫過娓密夫街時,公使館裏的眾多人員當中,只要其中有一位從15道窗戶當中的一道窗戶往外望,就會看到孫逸仙。為什麼孫逸仙要在缽蘭大街的西邊走?因為,接著走到下一個街口再往西就拐,是康德黎醫生的寓所。如果孫逸仙早知道公使館的準確位置,他可能會繞道而行。但當時他並不知道。
最後,公使館的華籍員工似乎有個習慣:他們愛在公使館的附近逛街。早在第一任公使郭嵩燾的時代,就有該公使館的華籍員工,因逛街而鬧出事來 。這也難怪,當時的英國與滿清統治下的神州,分別是這麼大!任何稍具好奇心的人,都會經常到街上逛逛。孫逸仙只要在街頭遇上公使館眾多華籍員工中任何一位,都會引起懷疑。因為,當時的缽蘭大街,極少華人涉足。其實,整個倫敦,當時也極少華人。有麼也多數在東倫敦部的碼頭區當工人。孫逸仙的突然出現,肯定馬上引起懷疑。
當孫逸仙到達倫敦第二天(即1896年10月1日)的早上,第一次由南往北走過公使館正門時,公使館的人是否已注意到他?我們不知道。當天稍後,康德黎醫生帶著他,前往康德黎自己過去當大學生時、寄居過的格雷法學院坊,為他找廉宜寓所 。經筆者實地考察,他們所走的路線,也必須從北往南地經過公使館大門。這是孫逸仙第二次在鬼門關 外晃來晃去。
1896年10月4日星期天,孫逸仙早上再訪康家 ,第三次走過公使館正門。過了一會,孫逸仙跟康家大小、一道走路上禮拜堂。康家有固定的禮拜堂,那就是聖馬丁教堂 。經考證,該教堂位於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的東北角,從康家走路去,不遠,但必須路過公使館的正門。如果是坐馬車去,還沒什麼。但是如果徒步去,則一個東方人,在一家洋人當中,還有兩、三個小孩蹦蹦跳跳地 ,走過公使館正門,怎不引起裏邊的人注意?經筆者考證,當時他們是徒步去的!承康德黎醫生的幼子 肯訥夫.康德黎上校(Colonel Kenneth Cantlie)相告,他爸爸從來沒擁有過一部私人的馬車。如果不是有急事或目的地太遠,無論到倫敦任何別的地方都是走路,很少坐出租馬車。他的外婆住在倫敦西南部的班斯區(Barnes),走路去,單程得走上五、六個小時。但是,他媽媽經常都帶著保姆、領著孩子們走路去的。星期六去,星期天回來。聖馬丁教堂近在咫尺,他肯定上教堂時,是走路去的 。
在教堂守過禮拜以後,於回家路上,又是這麼一個東方人,親親熱熱地走在一家洋人當中,更有兩、三個小孩蹦蹦跳跳地,走過公使館正門,裏邊的人還看了沒有?
在康家吃過午餐,暢談過後,孫逸仙在回家途中,第六次走過公使館正門。但這次是單形隻影者,公使館的人,注意了沒有?
1896年10月6日星期二,孫逸仙再訪康家。上午去,下午回 。去時第七次走過公使館正門。回時第八次走過公使館正門。翻查公使館檔案,公使館在當天下午15:00時,就給史雷特私家偵探社發了一封電報,要求該社暗中偷拍孫逸仙一張照片。難道這是偶然的?公使館的目的很明顯。如果偵探成功地偷拍了該偵探所跟蹤的目標的照片,就可以用來對照一下。這樣可以證實,這個從10月1日起突然出現的、此後不斷在公使館面前搖來晃去的陌生人,是否就是前一天(9月30日),在該偵探監視下、於利物浦登岸的孫逸仙。因為,偵探社發給公使館的、有關孫逸仙行蹤的報告中,絕口沒提到過該目標曾走近公使館,也沒有提到他曾多次探訪康家!
可惜,那偵探社回答說:「待天氣好轉再說吧。」 就是不愛想辦法,真沒出息!公使館沒奈何,只好乾焦急。接著,孫逸仙應邀到恩師孟生醫生(Dr Patrick Manson)家裏晚餐;日期方面,據孟生醫生回憶說,要麼是1896年10月8日星期四,要麼是1896年10月9日星期五 。經實地考察,孟家也非常靠近公使館,與公使館和康家大約成品字形。公使館的人,今天又注意了他沒有?1896年10月10日星期六,孫逸仙再訪康家 。讓我們可以肯定他第九、第十次走過公使館正門。其他不能肯定的次數不算。
1896年10月11日星期天清早,當孫逸仙正要作第十一次(我們能肯定的)路過公使館正門時,公使館裏的人終於採取行動,把他誘騙進去。重建當時公使館人員的心思與布局,是很有趣味的。第一,缽蘭大街是使館區,星期天使館人員不辦公,行人極少。儘管有些居民吧,星期天的早上,都睡晚點。清早時份,大家還在夢鄉,外來客就更少。在這個時候採取行動,最適合不過。上個星期天孫逸仙來過一趟,與康家大小上禮拜堂。今天會不會再來?第二,如果再來,預先會有什麼兆頭?承該街一位老居民相告,缽蘭大街南端路中心有一座圓形的教堂,兩旁所有建築物的前部都是半圓形,行人從南到北進入缽蘭大街,必須繞過該教堂。在繞行的過程當中,就會發出回響 。如果有人站在缽蘭大街等候,還未見到來人,早已聽到腳步聲,好作準備。缽蘭大街的星期天清晨,平常是靜悄悄的。1896年10月11日的清早,再一次來了腳步聲,九成是這個陌生的東方人重現了。
如果沒有作實地調查,上述的關鍵情節,筆者就無法知道並作聯想,更無從解決為甚麼孫逸仙會遭到綁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從探索三民主義淵源的角度來看,則跟蹤了孫逸仙10天,收穫同樣豐富。光以孫逸仙在倫敦活動的第一天(1896年10月1日)為例,就發人深省。正如前述,當天早上,他徒步往訪康德黎醫生。通過實地考察,筆者發覺,他沿途見到的,是英國建築業輝煌的成就。甚至可以說是無與倫比,是大英帝國鼎盛的象徵。日不落帝國稱霸全球,到處欺負弱小民族。這些雄偉建築,部份是被剝削民族的血汗。當時的中華民族,就是被踩在地下的民族之一。孫逸仙民族主義的心絃,有沒有被扣住?通過實地考察,又發覺當天康德黎為孫逸仙找到的旅寓,位置就在格雷法學院的邊上,日後孫逸仙多次跑往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叫「南院5號」的,其實就是到該法學院去,與一位唸法律的英國學生討論問題(見第二章「日誌」)。討論甚麼問題?民權的問題?由於實地考察,又發現當天黃昏,孫逸仙參觀了倫敦大學著名的英王書院。教育與民生息息相關 。當時的神州大地,還沒有一所現代化的高等學府!
若嫌參觀大學的例子,還不夠直接了當地、顯示出它與民生的關係,則第二天,孫逸仙在霍爾本區(Holborn)活動。該區既有輝煌的格雷法學院,也有查里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描述的貧民窟。孫逸仙見了沒有?第三天,他跑到老遠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花了一整天參觀由英國皇家園藝協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所舉辦的全國水果展覽(見本章第七節「本書脈絡」)。第四天(1896年10月4日星期天),同樣通過實地考察,筆者發覺,孫逸仙與康德黎一家步出教堂時,目睹英國罷工工人示威的盛大、動人場面(見本章第五節「神遊冥想」)。這全都與民生有關(後者當然與民權也有密切關係)。
在短短的四天之內,有關三民主義的例子,就通過實地考察,排山倒海而來。
關於實地考察對三民主義探源的關鍵性,讓筆者再舉一個例子。偵探報告說,孫逸仙逃出生天後,即在「查靈十字的稅氏酒肆接受記者採訪」 。這不是一般的記者會,而是轟動世界的「宣言」。這「宣言」,讓孫逸仙從一個落荒而逃的反叛者、搖身一變而成為「當世大英雄」(the hero of the great generation of the day) 。它把孫逸仙推上世界性的政治舞台,充實了他的使命感。而作為一位世界性的政治人物,不能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光有行動,沒有理論,是不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對孫逸仙來說,這是一種嶄新的體會。他本來打算在英國逗留10天左右,就赴法國 ,繼續其環球旅行。但後來又改變了主意,決定暫時留在英國多多學習,終於「完成」了他的三民主義 。他之所以改變主意,很可能就是因為有了上述那種嶄新的體會。因此,發掘當時他談話的內容固然要緊(筆者覓到了,見第四章),但是找出記者會舉行的地方──稅氏酒肆──的具體方位,考察它的外型,研究它的內部佈置,則同樣為重要。因為,以孫逸仙當時的政治素養來說,作沒有準備的倉促談話,不可能談出甚麼政治理論。倒是他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人生第一次地、面對甚有學問的記者輪番發問時,深刻地體會到有政治主張的必要,儘管當時他在這方面不多說(見本書第四章)。
但是,稅氏酒肆在哪兒?現代倫敦的街道圖,卻沒有查靈十字,只有查靈十字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現代的倫敦電話簿,同樣可惡,根本沒列上「稅氏酒肆」這名字(偵探報告所用的具地名字是Shades Public House) 。1979/80年度,筆者休假整整一年,在倫敦做研究,沿查靈十字路反反複複地、走了不知多少遍,都屬徒勞。
後承英國大律師協會的唐林先生(Mr A.J.Tomlin)相告,《倫敦郵政便覽》(Kelly’s London Post Office Directory)可供參考 。筆者追查該《便覽》,則證實1896年的倫敦,的確有查靈十字這個地方。而稅氏酒肆,就位於查靈十字27–28號 。因此,1983年5月,筆者興沖沖地又跑回倫敦,在《便覽》提及的地區內,即河濱路(Strand)與白廳(Whitehall)大街之間 ,把每條街道、每家招牌都仔細看個遍,仍不得要領。但是,有了一點頭緒:在該區內、某棟高大房子的牆壁上,釘了一道牌子,上邊印了「查靈十字」等字樣。這牌子雖然與現代街道圖相悖,但證明地區是找對了。
後來,探得英國皇家建築設計師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珍藏有稅氏酒肆的銘刻銅片(copperen graving) 。夠格被該協會挑選作銘刻銅片珍藏備考的建築物,肯定非等閒之輩,於是引起筆者更大興趣,決定修書向該協會求助。承其不棄,提供了該銘刻銅片的照片,如獲至寶 。結果,1987年1月,又興沖沖地再飛倫敦,並把搜索範圍擴大到白廳大街。從北往南地,在白廳大街的東邊慢慢走。一邊走,一邊把馬路對面、即白廳大街西邊的建築物,一座一座地、與手中的圖片比較。走到白廳大街南端盡頭,立即橫過馬路。再從南到北地、在白廳大街西邊慢慢走。一邊走,一邊把馬路對面、即白廳大街東邊的建築物,一座一座地、與手中的圖片比較。在快接近特拉法加廣場時,嘿!筆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於是,擦擦眼睛再看。對面呈現的一座建築物,與手中圖片雷同!該建築物掛有一道招牌:「古老稅氏加靈頓」(Old Shades Charrington)。名字雖有增加,但仍保留了稅氏二字 。正由於它加了「古老」(Old)二字在前面,難怪在現代的電話簿中的S部份找不到Shades(稅氏)!
怎麼稅氏酒肆從查靈十字跑到白廳大街了?房子沒腿,跑不動的。很可能白廳大街的北部,過去原叫查靈十字:且看附近就是查靈十字火車總站和查靈十字醫院。為了證實這種推想,連忙跑到大英博物館,查核有關典籍。結果,找到一本書,是倫敦市政廳出版的,其中有一部份,帶有這個標題:「自1929年8月1日,取消了的街道名稱以及其新名字」。查閱之下,證明查靈十字,已改為白廳大街的一部份 。這種改動,是符合現代化要求的:同是一條大街,為何南轅北轍呢?接著,筆者迫不及待地、函請稅氏酒肆的老闆,准許筆者前往考察及拍照。多年宿願,終於得償!
應該重申,筆者寫本章這一節的目標,是要說明:為了解決有關問題,「實地考察」非常有助於我們「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
(三)文獻鑽研
實地考察,脫離不了文獻鑽研,更代替不了文獻鑽研。應該說,實地考察與文獻鑽研,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不可缺其一。對於這一點,筆者體會是很深的。譬如,偵探報告開頭第一天就說,孫逸仙坐「雄偉」號輪船到達英國,在利物浦的王子碼頭登岸 。這王子碼頭是怎生模樣?這不是一般的問題,因為王子碼頭所給他的,是他對英國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對一個人的總的觀感,有時候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筆者決定親往考察。在1984年,興沖沖地從澳洲再飛回英國。又從倫敦興沖沖地坐火車到利物浦。下了火車,買了利物浦市區的街道圖,按圖找到王子碼頭。好荒涼啊!整個海港沒有一條遠洋船。碼頭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隻。孫逸仙當年登岸的情景,肯定不是這樣。但當年情景往哪兒找?心中一片茫然。惆悵之餘,情不自禁地在碼頭區不斷地踱方步,直到日落西山而不自覺。突然眼前出現一位中年人,對筆者說:「先生,碼頭區入夜不安全,我開車送您回旅寓。」 筆者感激之餘,更深覺出師不利之痛。
退而求其次,第二天查訪所謂railway omnibus。因為,偵探報告說,孫逸仙是從利物浦的王子碼頭、坐railway omnibus,到密德蘭火車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的 。Railway omnibus這個名字好古怪!直譯的話,就變成「火車路公共車」。翻閱前人研究成果,則有把它翻譯成「公共汽車」者 。竊以為這是不準確的。因為,那個時代,還沒有普遍使用汽油和汽車。筆者在起程前,也曾預先函詢利物浦市立檔案館。該館摸不著頭腦,讓筆者轉向英國的國立火車博物館(National Railway Museum)查詢 。筆者照辦,同樣沒有結果。所以,筆者這次親訪,希望多少能找到些頭緒。但是,向當地的專家請教,帶來的都是莫名奇妙的反應。怎麼?在鬧市中架了火車軌道、再用火車頭拉著車箱走?把橫過的馬路通通切斷,不是要天下大亂?筆者本來就覺得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無法之餘,還是明知故問。難怪別人以為筆者瘋了。又是徒勞無功的一天。
第三天,按圖欲找密德蘭火車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因為,偵探報告說,孫逸仙坐「火車路公共車」、到達密德蘭火車站後,就從該站乘火車前往倫敦的 。但是,找了大半天,就是沒有密德蘭火車站這個名字。筆者也曾預先函詢利物浦市立檔案館和摩斯賽區政府(Merseyside County Council)檔案部。前者回信說,密德蘭火車站即中央火車站(Central Station) 。後者回信說,密德蘭火車站即利物浦當今唯一的火車總站──那著名的萊姆街火車總站(Lime Street Station) 。孰是孰非,筆者希望通過這次實地考察,能把問題搞清楚。但是,地圖上沒有密德蘭火車站這個名字,下一步應該怎麼走?筆者決定下午親訪摩斯賽區政府檔案部主任、格頓.李德先生(Mr Gordon Read)。見面寒喧,原來他也是牛津舊生,是筆者的學弟,更好說話。哥弟倆一道翻查1896年的利物浦電話簿,證實密德蘭火車站即中央火車站。那位學弟原先搞錯了:粗心大意,以今況古!筆者安慰了那滿臉通紅的學弟幾句後,就怱怱地趕往中央火車站舊址。好荒涼啊!所有大門窗戶都用木板釘得死死的,牆壁上的污垢黑壓壓的,髒得讓人作嘔。加上時過黃昏,大有鬼影憧憧之慨。惡鬼不足畏,歹徒實堪慮。筆者覺得不宜久留,故拍過照後,就趕快離開。這樣的照片,怎能反映孫逸仙當年看到的景象?又是讓人失望的一天!
窮則變,變則通。鑽研文獻去!經過不斷的探索,多次到利物浦向當地的專家請教,承利物浦各檔案館的眾多好友不厭其煩地幫忙,通過各種途經,找來當年圖片與有關文獻,一步一步地解決了不少疑難:當年王子碼頭的圖片找到了!一看,好熱鬧啊!當年中央火車站的圖片找到了,好帥!當年的街景也找到了,好繁華啊!甚至當年孫逸仙乘坐的、那隻「雄偉」號輪船的圖片也找到了!只有那該死的「火車路公共車」,仍然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筆者也不灰心,以後一有機會就請教高明,十年如一日。終於,在1994年3月某天,與同事沃特教授(Dr John O. Ward)閒談時,承他指引,得閱有關典籍,方知是當年利物浦土話,所指乃有軌馬拉車 。於是又請利物浦市立檔案館的朋友幫忙,找到有關圖片,孫逸仙當年所處的環境、氣氛等等,躍然入目,寧不讓人雀躍?可見,光靠實考察而不作文獻鑽研,是無法重建當年景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