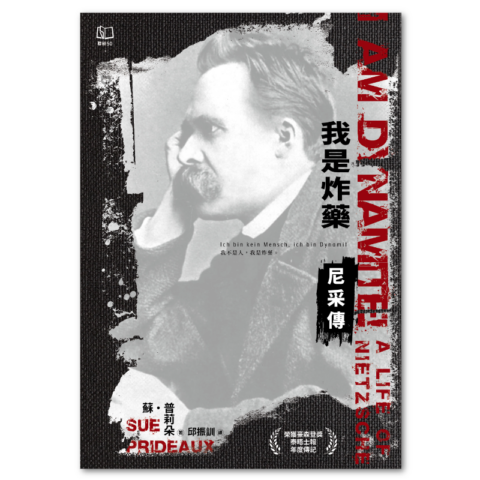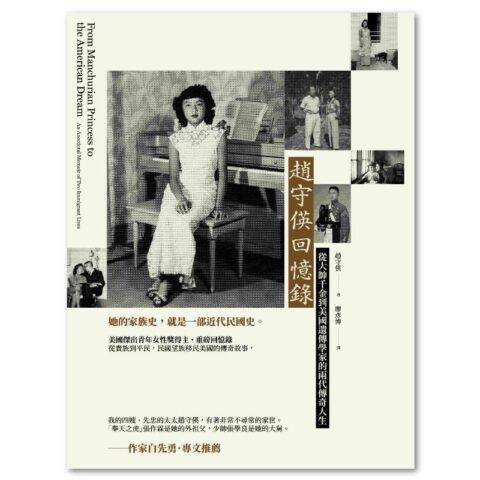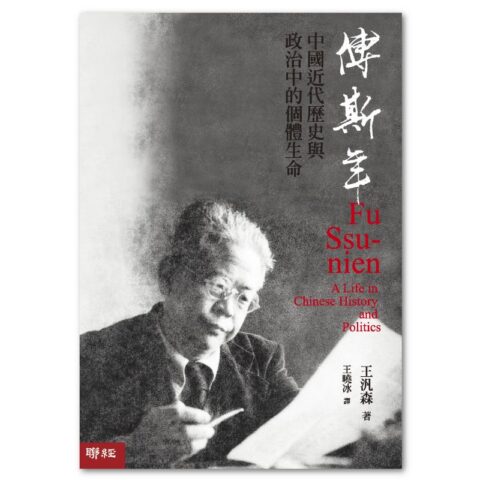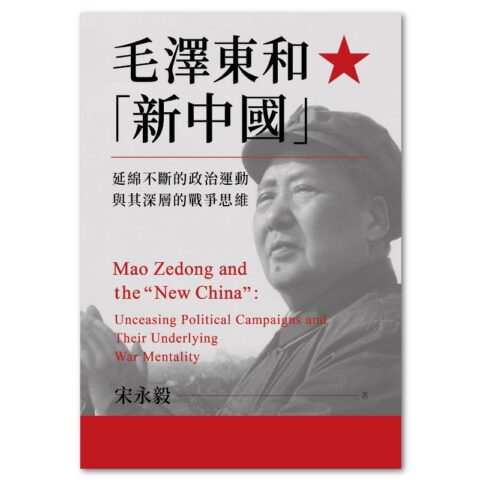1850年到1861年咸豐當了11年的皇帝,卻沒有過一天輕鬆的日子。
歷經太平天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天地會、捻軍等造反,中國歷史由此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咸豐知道很多當皇帝的規範、策略和機謀;知道太多成功與失敗的治國經驗。
他認為,只要按照千年不變的政治教科書闡明的精義、按照已創造出「康雍乾盛世」的法則,必然造出一片輝煌。……
然而,內憂外患使他困惑、棘手、無策。挽救危局的千方百計,換來的只是千絲萬縷的憂慮,看不到一線生機,找不到一條生路。
於是,他帶著無窮無盡的憂慮,去了那個據說沒有憂慮的世界。
作者:茅海建
1954年生於上海,先後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華東大學歷史系(碩士)。曾任軍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1995)、《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1998)、《戊戌變法史事考》(2005)。
導 言
一 皇四子與皇六子
二 良師藎臣杜受田
三 射偏了的箭
四 「上帝」之禍
五 虧得湘人曾國藩
六 新財源:釐金
七 「造反」、「造反」
八 外患又來了
九 公使駐京問題
十 圓明園的硝煙
十一 真正的宰相
十二 京師與熱河之間
十三 笑到最後的人
結 語
後 記
三聯版後記
第三章、射偏了的箭
治清史的同行們有一個共識,即清代的皇帝個個勵精圖治(至於是否能做到當屬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幾個昏君,居然幾年不上朝,放任國運衰敗。
造成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明、清兩代都是皇帝親理政務。雖說天子聖明萬能,但一個人畢竟忙不過來,在實際操作中逐漸形成了輔佐班子。這在明代為內閣,到了清代,除沿襲內閣外,康熙時出現了南書房,雍正時又設置軍機處。
從性質上講,明代內閣、清代軍機處都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工作任務是為皇帝擬旨。明代的內閣大學士、清代的軍機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欽定,不必循官場之例遷轉。但兩者之間最大區別在於,明代各地、各衙門的報告先交內閣,由內閣對此提出處理意見,謂「票擬」,再交皇帝審閱,批准後作為諭旨下達。皇帝若懶得動筆,可由司禮秉筆太監代勞。這就出現一條縫隙,政務可以由內閣、司禮秉筆太監轉化為諭旨。清代不同了,沿襲明代的題本制度(同樣交內閣票擬),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變為奏摺。奏摺由具有奏事權的官員親封,由皇帝親拆,皇帝批閱後下發軍機處,由軍機大臣根據皇帝的硃批或面諭擬旨,再經皇帝批准後下發。在這種體制下,皇帝若不及時發下奏章,政務中樞即梗塞。至於皇帝批閱奏章專用的硃筆,太監誰也動不得,那可是殺頭的罪名。
以一個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閱讀、研究幾萬字的奏摺,立即形成對策下發,還須召見京內外大臣,這確實超出了平常人的極限,近乎於對神的要求。當時人謂天子日理萬機、宵衣旰食,有時也不全是阿諛之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間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間之最。
年輕的奕詝登上皇位時,頗有企圖心。他繼承了祖宗的大業,也極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風範。從《實錄》中看,他此時的工作極為勤奮,每天都有許多諭旨下達,其中不少是親筆寫的硃批、硃諭,不勞軍機大臣動手。他暗暗對自己說道,我一定要守住這一份祖業,我一定要重顯祖宗昔日的榮光。
也因為如此,咸豐帝在上台後的八個月,便主演了一幕眾人拍手叫好的戲——罷免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中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後在詞臣上遷轉。1813年升禮部右侍郎,此後屢降屢升。他的轉機,在於1825年以漕運總督襄辦海運,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後署理工部尚書。1827年旨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1828年任軍機大臣。1837年起,為首席軍機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賴的人。
道光帝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長居政壇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親信曹振鏞,以「多磕頭、少說話」為政治秘訣。穆彰阿位於首輔,幾乎每天都被召見,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詢,必盡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對於道光末年的政治敗壞,應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嚴格地說起來,穆彰阿也是咸豐帝的老師。1836年即奕詝入學時,他即為上書房的總師傅,至1849年初因保舉不當被罷,改為杜受田,可不知為何,道光帝臨死前兩個月,穆又復充上書房的總師傅。對於這位老師,咸豐帝很小便聽到了許多,早就想拿他開刀。
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重要表徵,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豐帝登基後,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很可能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穆彰阿多次充當考官,且長期結交京內外官員,特別喜歡拉攏年輕有才的下級官員,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勢力集團,時人謂之「穆黨」。咸豐帝欲罷免穆彰阿,所下諭旨若由內閣發出,穆是文華殿大學士(即內閣首揆),若由軍機處發出,正好穆是首席軍機,須得事先考慮安排好才行。
僅僅出於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豐帝罷斥穆彰阿,但從咸豐帝後來的諭旨來看,他更加不滿的是穆氏的對外政策,這就牽涉到先前那場鴉片戰爭。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國侵略中國,蹂躪東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雖說戰爭爆發時,咸豐帝只有九歲,不可能理解戰爭的過程和意義,但他的老師杜受田當時曾發表過意見。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國傳統的木簰,火攻突入長江的英國艦隊。這是書生論兵的典型,表現出對前線戰況和近代軍事技術、戰術的無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採納,但他的思想不會不對奕詝發生影響。
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今天看來應當是很清楚的,在於中國政治的腐敗和軍事的落後。但當時的士大夫不承認這一點,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敵區區島夷。他們認為,戰爭的失敗在於忠臣林則徐等人的抵抗主張沒有得以實現,在於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時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歸結起來,就是主張對「逆夷」強硬而不是屈服,而廣州反入城抗爭又使他們誤以為強硬政策獲得了勝利。
由於中英南京條約中英文本的歧義,戰後英國人是否可進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雙方有著分歧。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耆英,在戰爭中被打怕了,竭力維護民夷相安的局面,對外持軟弱態度。他起初因廣州紳民反對,對英人入城問題推諉騰挪,後因歸還舟山而允諾英方有權入城。1847年4月,英軍戰艦再入珠江,陷虎門,逼廣州,耆英見勢不妙,允諾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城。
英人在未入廣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廣州沙面以東大三元酒家一帶的商館,距廣州城西南城牆僅200公尺。廣州紳民在入城問題上的堅決反抗態度,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是沒有認清抵抗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晉文淵閣大學士。繼任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對外持強硬態度。他們不顧耆英先前的承諾,於1849年4月斷然拒絕英人入城,並組織團勇近10萬人,準備與英軍一戰。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戰爭準備,英方宣布將入城一事暫為擱置。也因為翻譯問題,清方以為英方永遠放棄了入城的權利。
就這麼一個小小的勝利(今天看來是否是勝利還很難說),大大鼓舞了主張強硬的官紳士民,認定只要由強硬派掌權,就會改變鴉片戰爭以來屈辱的局面。就連道光帝也為此一振,認為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戰而勝」,封徐廣縉為子爵,封葉名琛為男爵。
廣州反入城抗爭勝利時,咸豐帝已經18歲了,離他當皇帝還不到一年。他已經懂事了。由此,擺在咸豐帝面前的結論,似乎是很明顯的,只要罷斥這批對外軟弱的官員即可,只可惜父皇還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豐帝登基未久,中英關係中又發生了一件事。
1849年英人入廣州城被挫後,英國駐華公使文翰(S. G. Bonham)向國內報告,英國外相巴麥尊(H. J. T. Palmerston)指示文翰繼續交涉,並發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會。文翰因在廣州與強硬的徐廣縉無法打交道,便駕船北上,企圖在中外關係和好的上海打開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達上海,與兩江總督陸建瀛會談,要求轉遞巴麥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會和他本人致耆英照會。陸建瀛先是拒絕,但聽說英國將派船北上天津,態度立即軟了下來。咸豐帝收到陸建瀛的奏摺,下旨:命陸建瀛勸文翰南下,有事只許與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廣縉交涉。諭旨中稱:
若非剴切曉諭,於妄念初萌之際示以限制,勢必以無饜之詞,向在京各衙門紛紛呈投,成何事體!
咸豐帝這時的策略是,不與這些桀驁不馴的「夷」人們打交道,讓善於制「夷」的徐廣縉來辦理此事。同日,他還發給徐廣縉一旨,讓他「堅明約束」,「折其虛憍,破其要脅。」
巴麥尊的照會指責徐廣縉危害中英「和好」關係,並要求在北京進行談判,「商訂其事」。這種直接照會京內大臣的告狀做法,使咸豐帝認定英方在行「反間計」,陷害忠良徐廣縉。而巴麥尊的照會不發給別人,偏偏發給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對此兩人發生懷疑。特別要命的是,文翰給耆英的照會,內中有一段話:
茲以貴大臣本屬貴國大員,熟悉外務事理,眾所共知。更念本國前大臣等素與貴大臣頻恆札商,極敦誼禮,衷懷欣慰,為此乘機備文,照會貴大臣閱悉。
這種來自敵方的對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讚揚,實實在在是幫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這一時候,咸豐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財諸端,持論過偏,傳旨申斥。
也就在這一時候,咸豐帝以英人梗頑,命林則徐進京,聽候簡用。
咸豐帝的意向,已經明顯得不能再明顯了。
文翰沒有罷休。他派翻譯麥華陀(W. H. Medhurst)前往天津投遞文書,當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絕,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動也毫無效果。7月,他只能垂頭喪氣地返回香港。
文翰此次北上交涉,無疾而終。咸豐帝卻從這次對抗中增強了信心。英「夷」也不過如此。然而,他為自己不能趕走這些可惡的「夷」人而遺憾。當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電擊劈時,動感地在臣子的奏摺上硃批道:「敬感之餘,更深慚愧。」
過了不到兩個月,又出一事。
負責北京治安的步軍統領衙門抓住一天主教徒丁光明,手持稟帖到耆英家門前投遞。此事還牽涉到傳教士羅類思。刑部審理後上奏,要求耆英對此事作出解釋(此時刑部尚書為杜受田)。儘管耆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但在咸豐帝心中又留下了耆可能與外人有勾結的陰影。
咸豐帝還沒有行動,又等了幾個月。
1850年12月1日,咸豐帝動手了。這一天,他破例地未向皇太貴妃(即其養母博爾濟錦氏)請安後再辦公,而是首先頒下一道硃諭《罪穆彰阿、耆英詔》。這份文件的分量不亞於一次政變,紫禁城為之震動,空氣也變得凝重起來。雖說這道諭旨長達千言,但咸豐帝寫出了他的真實思想,故全錄於下。讀者在了解咸豐帝的內外政策的同時,也不妨測測他的文字水平和觀念高下:
任賢去邪,誠人君之首務也。去邪不斷,則任賢不專。方今天下因循廢墜,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然獻替可否,匡朕不逮,則二三大臣之職也。
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似此之固寵竊權者,不可枚舉。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誠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無忌。若使聖明早燭其奸,則必立寘重典,斷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縱,始終不悛。
自本年正月(農曆)朕親政之初,(穆)遇事模稜,緘口不言。迨數月後,則漸施其伎倆。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為腹心,以遂其謀,欲使天下群黎復遭荼毒。其心陰險,實不可問。潘世恩等保林則徐,則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及朕派林則徐馳赴粵西,剿辦土匪,穆彰阿又屢言林則徐未知能去否。偽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實在於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無能,殊堪詫異。伊前在廣東時,惟抑民以奉夷,罔顧國家。如進城之說,非明驗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幾至變生不測。賴我皇考炯悉其偽,速令來京,然不即予罷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於召對時,數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應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祿位。是其喪盡天良,愈辯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難知,耆英顯而易著,然貽害國家,厥罪維均。若不立申國法,何以肅綱紀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負皇考付託之重歟?第念穆彰阿係三朝舊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實有不忍,著從寬革職,永不敘用。耆英雖無能已極,然究屬迫於時勢,亦著從寬降為五品頂戴,以六部員外郎候補。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見者,朕不為已甚,姑不深問。
辦理此事,朕熟思審處,計之久矣。實不得已之苦衷,爾諸臣其共諒之。嗣後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務當激發天良,公忠體國,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積習,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難,毋苟安。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諸大端者,直陳勿隱,毋得仍顧師生之誼,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爾位。朕實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
這一篇諭文,讀之頗感氣勢,非積鬱胸臆久矣而不能為之。咸豐帝一吐為快,說出了他多年的心聲。
硃諭頒下後,京內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讀,齊聲讚揚。咸豐帝說出了他們多年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他們於此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的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擯奸,是中國傳統政治學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則,由此在中國傳統歷史學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亂世的基本表徵就是奸臣當道,一旦聖主罷斥群奸,起用忠良,定雲霧重開,萬眾歡騰,王朝也會走向中興。這一套路,經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澆鑄在咸豐帝的心中,他早已決心力行,做一名中興的聖君。
穆彰阿罷斥了,耆英降革了,導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剷除了。一切的好轉,不正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嗎?
在此咸豐帝舒志、臣子們額慶之際,似乎誰也沒有認真想一想,中國的問題僅靠換幾個當權派就會解決嗎?
如果我們仔細地推敲,咸豐帝的上引諭旨尚有不實之處。
除了泛泛的指摘外,穆彰阿的具體罪名有二,一是排斥達洪阿、姚瑩,二是阻撓林則徐的復出。
案達洪阿前為台灣鎮總兵,姚瑩前任台灣道,鴉片戰爭期間兩人負責保衛台灣,竭盡心力。1841年9月,英軍運輸船納爾不達號(Nerbudda)在台灣基隆海面遇險。船上274人有34人乘小艇逃走(多為軍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為台灣守軍生擒,32人被斬首。1842年3月,英另一運輸船阿納號(Ann)亦在台灣中部沿海遇險,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軍活捉。然此兩次事件被達洪阿、姚瑩渲染為擊敗來犯英軍的重大軍事勝利,受到道光帝的褒獎。1842年5月,就在清軍在鴉片戰爭中節節敗退之際,道光帝親自下令,台灣所囚俘虜中除頭目外,其餘「均著即行正法,以紓積忿而快人心。」戰爭結束後,英方要求釋放戰俘。得知台灣戰俘除11人外皆被處死,立即交涉,頗有戰端重起之勢。殺俘是奉旨行事,那是萬萬碰不得的,而開罪了「夷」人,又啟戰火,也是不堪想像之事。在此情勢下,以彈劾琦善私許香港而名揚天下的閩浙總督怡良,赴台親自調查後發現,達洪阿、姚瑩兩次奏報抗英獲勝純屬虛構,請求將兩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後下令將兩人革職,解京送刑部審訊。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參與審訊,事後奏摺中對達、姚兩人尚有回護之意,結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兩人前已革職,後也沒有再起用。由此看來,達洪阿、姚瑩之獄是出自聖裁,與穆彰阿似無關聯。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被革,後發配伊犁。1845年釋回,1846年任陝西巡撫,1847年任雲貴總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開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復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腳。至咸豐帝上台後調林進京,也是林本人稱病不出。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咸豐帝頒下硃諭的前八天,林則徐已經病死在赴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了(關於林病故的奏摺尚未到達北京)。這麼說來,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硃諭中講了兩條:其一是入城一事上過於軟弱,這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其二是咸豐帝登基後,耆英在幾次召對時皆主張對英國「應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強硬手段。實際上,這也是咸豐帝下決心對穆、耆開刀的主因。
對於一個比自己強大國家的咄咄逼人的進迫,應當採取何種策略,從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來看是有區別的。前者強調正義性,後者強調可行性。作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並不為錯,這是他正確分析了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如將國運民生意氣用事,浪於一擲,其意氣雖暢快,但後果不堪設想。耆英的錯誤不在於主和,而在於苟和,沒有利用鴉片戰爭後的和平局面,從事革新,使自己國家變得強大起來。
由此反觀主張對外強硬的官員,他們大多在戰爭期間遠離戰區,沒有直接跟西「夷」打過交道,奏摺制度的機密和各地奏報中的粉飾,使他們無從了解實情真相,偏信那些頗具戲劇性的傳說,前述達洪阿、姚瑩一案的走形變態就是一例。從根本上說,他們的判斷也不是依據敵我力量之對比,而是為了恪守傳統的「夷」夏之道,順昌逆亡。他們相信義理的力量之不可戰勝,認為戰勝逆「夷」的手段不在於器物,而在於人心,「正心」「誠意」即可「平天下」。咸豐帝在杜受田的教導下,飽浸性理名教之義,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這種價值取向,受到了絕大多數官吏和幾乎全部士林學子的歡迎,既是形勢使然,又使然於形勢。
罷免穆彰阿、耆英,咸豐帝表達了其對外新政策:將啟用對外強硬的官員使用強硬的手段來對抗英國等西方國家。他的這種全力保住並盡可能挽回國家權益的意向,無疑應當讚揚,但就實際舉措而言,以為用忠擯奸即可抗「夷」,卻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對外強硬取決於武力的強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種虛張。咸豐帝也明白這個道理。在其聞悉文翰、麥華陀駕舟北上時,便提出這一問題:
至沿海各處防堵,數年以來,想早已有備無患。
這句話說得不那麼自信,底氣不夠充沛。而當麥華陀南下之後,又下旨:
從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帶屢經失事(指鴉片戰爭),追溯前因,能勿早之為計……(各沿海督撫)各就緊要處所,悉心察看,預為籌防,斷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員,總須慎選曉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諂懦弱者概應更換。
此道諭旨頒下後,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福建學政黃贊湯亦先後上奏,提出具體計謀,咸豐帝皆發下,令沿海各省參照執行。
咸豐帝的諭旨,只令籌防,而未言及如何籌防。蔣文慶、周天爵、黃贊湯的計謀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著邊際,與戰時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類似。然而,聖旨又是不能不執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砲台為依託進行抗擊,並在砲台之後路組織團練。對此,他信心十足,宣稱「此臣十載籌防所可深信者,不敢於聖主面前,稍作過量語。」按照這一方法,直隸其實什麼事也不必做(砲台早已建成,團練也已成常設)。
盛京將軍奕興的方法更簡單,根本不必設防,若英軍前來,誘之登岸,堅壁清野,然後以奉天(地域與今遼寧省大體相當)的「勁旅」來剿滅不善擊刺步伐的英軍,「正我兵所長」,沒有什麼問題。按此,奉天也不必籌防,到開戰時再說吧。
兩江總督陸建瀛奏稱,鑒於上海已經開放,「自當另為一議」(實為不設防之議),松江、蘇州一帶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艦船的進軍,另行募勇、火攻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須戰時才可實施,江蘇此時也無事可做。
浙江巡撫常大淳對策有二,一是繼續補造戰船(浙江水師戰船在鴉片戰爭中損失殆盡,尚未補造完竣),二是將團練之法寓於保甲之中。前者是繼續進行正在做的事,後者是以保甲取代團練,實際上一切均無需新張。
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仍宣布採用1849年反入城抗爭的老辦法:一是斷絕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國以貿易為生計,英商挾重資而來,不敢冒商業風險而進攻貿易重埠廣州;一旦開戰,香港英軍僅一兩千人,何抵抗於廣州數萬民眾?且香港巢穴可虞,黃埔船貨可虞,廣州城外英國商館可虞,英人豈無顧惜?他們的結論是英國不敢動手,因此也不必緊張自擾,憑著他們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敵!
最有意思的是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的奏摺。他們與那些表面上大講如何籌防、實際上一件實事也不做的官員不同,公然明白主張不設防。其理由為,一、英國控制了制海權,戰爭無法取勝;二、誘敵深入將導致英軍蹂躪內地,而陸戰必勝的說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寬水深,無險可扼;四、團練戰時不足恃,平時又易流為寇;五、籌防措施會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禍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咸豐帝皇皇數道上諭,換來的就是地方官這些筆頭子上耍功夫、實際無為無作的奏摺。這些地方官老於世故,知道若處處遵旨辦事,聽到風就下雨,那將會怎麼樣也忙不過來,什麼事也辦不成。別的不說,籌防是很花錢的,若真的造砲修船練兵團練,銀子又從何而來,中央財政肯定不給撥款,地方上又從哪兒弄這筆錢呢?
一遇到具體問題,咸豐帝也蒙了向。他本來就是只想制夷而不知如何制夷,對各地的做法結果都予以認可。其中他最欣賞的是徐廣縉、葉名琛,在他們的奏摺上硃批:「卿智深勇著,視國如家,所奏各情甚當。朕聞汝今秋偶有微,此時佳善否?」這裡表現出來的重點,仍是讚揚徐、葉對英國的態度,而不是注意他們的籌防。即便對於劉韻珂、徐繼畬的不設防言論,他也提不出什麼反對意見,而是聯繫其鴉片戰爭後一貫主和的表現,以此時的福州反入城事件為由,將他們一一革職了。
這是一支射得更偏的箭。
花如此之多的筆墨,來介紹新帝罷免老臣的事件,是因為此乃咸豐帝在位11年中唯一的一次振作。此後,他心有餘而力不足了。而我在敘說中又鋪墊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出現了大量的人物。這是因為這些背景反映了那個時代,這些人物大多後面還會出場。我個人筆力不健,只能如實羅陳而不能娓娓道來。還需請讀者原諒的是,我在這裡仍想對各地官員的奏摺和咸豐帝的思想再做分析,幫助今天的人更了解那個時代。
各地官員之所以不肯花力氣整頓海防,除了惜銀惜力(實際上也就是惜民)外,還因為受兩種思想的左右。
其一是英軍船堅砲利,清朝無法組建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與之對抗。前敘周天爵的奏摺中稱:
惟前次失事,皆專事海門,一切船隻砲位,事事效顰。
徐廣縉、葉名琛上奏時也同意這種說法,並裁減廣東水師的戰船。周、徐等氏的意見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不必效法英國等西方國家,在「船隻砲位」上作實際的努力。雖說清朝此時尚無建設近代海軍的能力,但此時是戰後寶貴的和平時期,放棄這種努力就是放棄近代化的嘗試,中國以後也只能用傳統來對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軍不善陸戰。早在鴉片戰爭時,林則徐、裕謙等人就有此類言論,認為英軍雖可橫行海上,但一至陸地,清軍將穩操勝券。戰爭的實踐使道光帝發現此中的謬誤但由於清朝戰後諱敗諱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確地總結教訓。直至此時,英軍不善陸戰的神話仍未破滅,各地疆吏仍將陸戰取勝當作以己之長攻彼之短的制敵良謀。
鴉片戰爭結束已經八年了,當年的前敵主將們紛紛被革退致仕,仍在台上的只有劉韻珂、徐繼畬等數人。戰爭這把客觀的尺子,使他們量清了中英軍事實力的差距。他們兩人的奏議,應當說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為何物的碌碌臣工的言詞,更切合實際。可他們找不到制「夷」的武器,居然放棄了制「夷」的使命。
年輕的咸豐帝,生長在深宮,讀的是聖賢書,他又如何知道制「夷」之法?內外臣工們要麼就是一味強硬,要麼就是一味妥協,誰也說不清「夷」為何物,讓他憑空能想出辦法來嗎?
當時的中國,就沒有人知道正確之途嗎?
也不是。有一個名叫魏源的名士,寫下了一部名為《海國圖志》的著作,初為50卷,後擴至60卷,定稿為100卷。在這本書的敘說中,他提出了一個驚世的命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魏源的思想也是極其有限的。他準備所「師」的西方長技為三個方面:造船、造砲、養兵練兵之法。從今天的角度看來,僅僅「師」這些長技仍是制不了「夷」的。「夷」也不是那麼好制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個方向,朝這個方向走下去,中國就能上軌道。
咸豐帝肯定見到過《海國圖志》一書。據檔案記載,1853年武英殿修書處奉旨將此書修繕貼錦進呈。至於咸豐帝有沒有細讀,讀後又有什麼感受,今人皆無從得知。但是,可以說,到了此時即便他想振作,也已經來不及了。
天下已經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