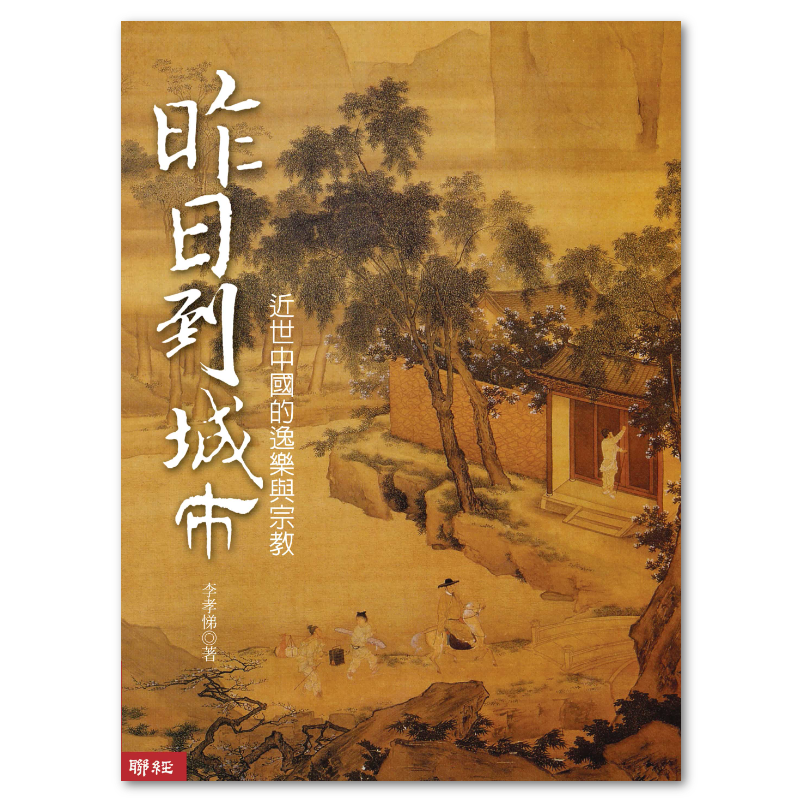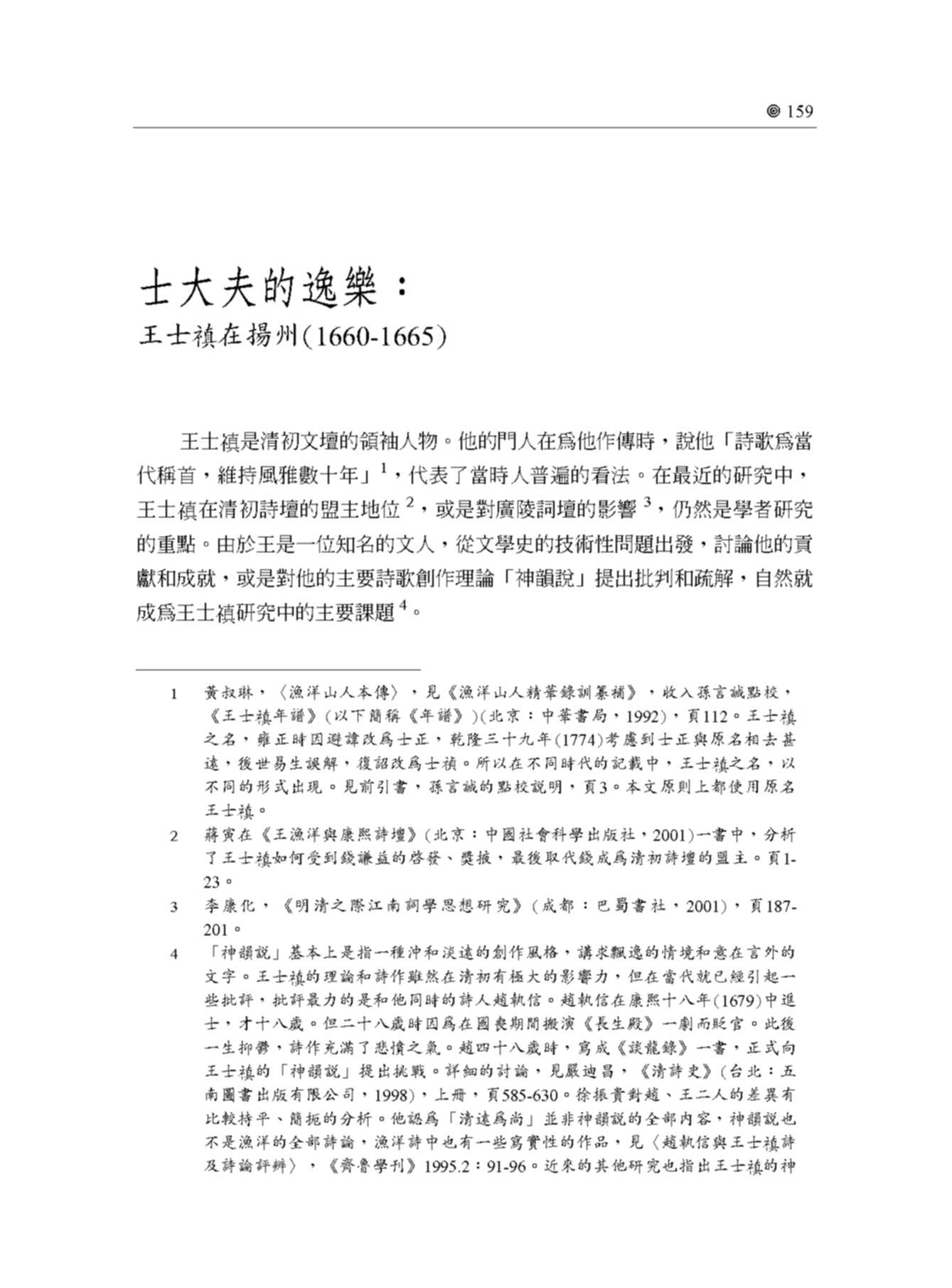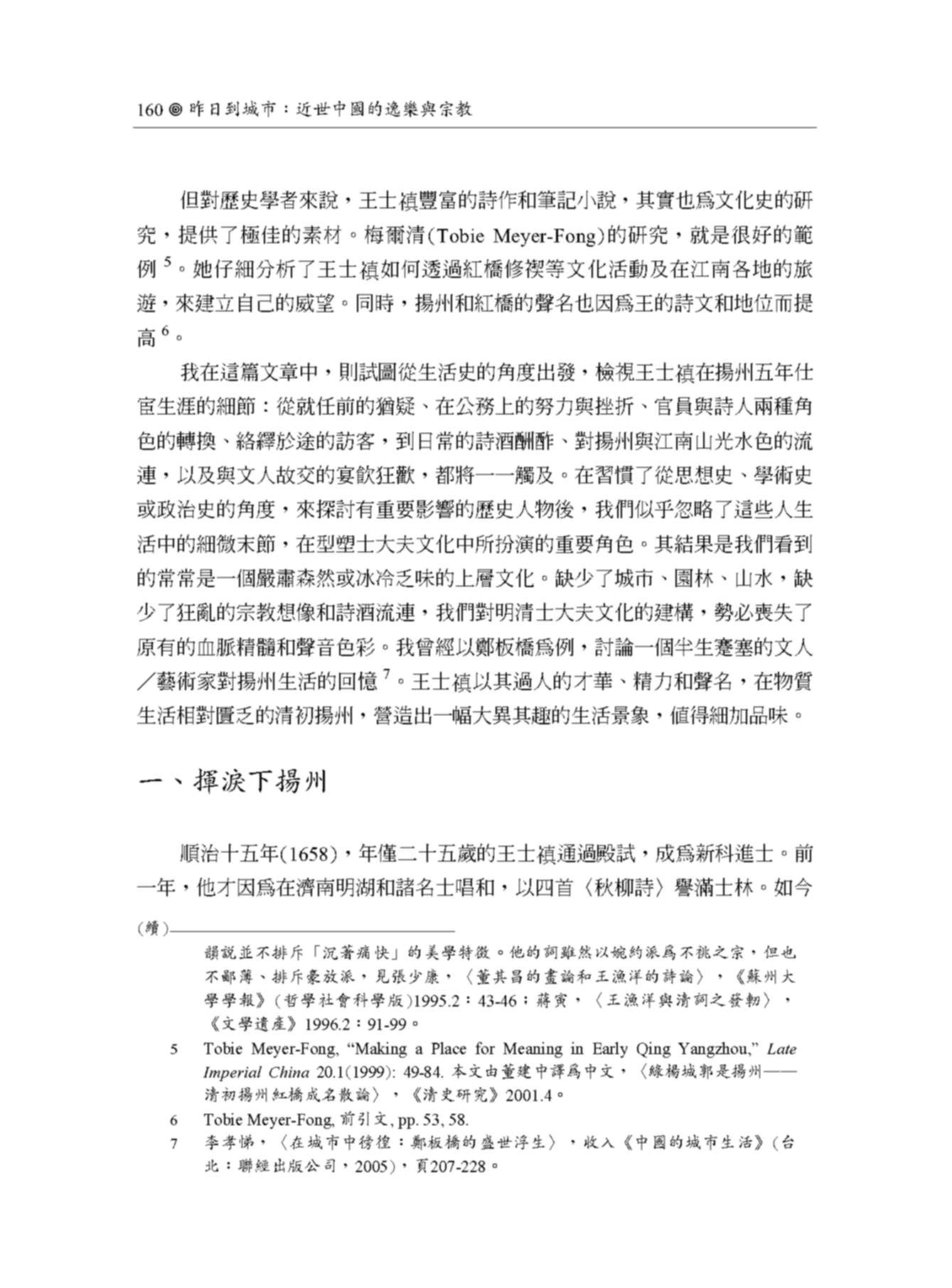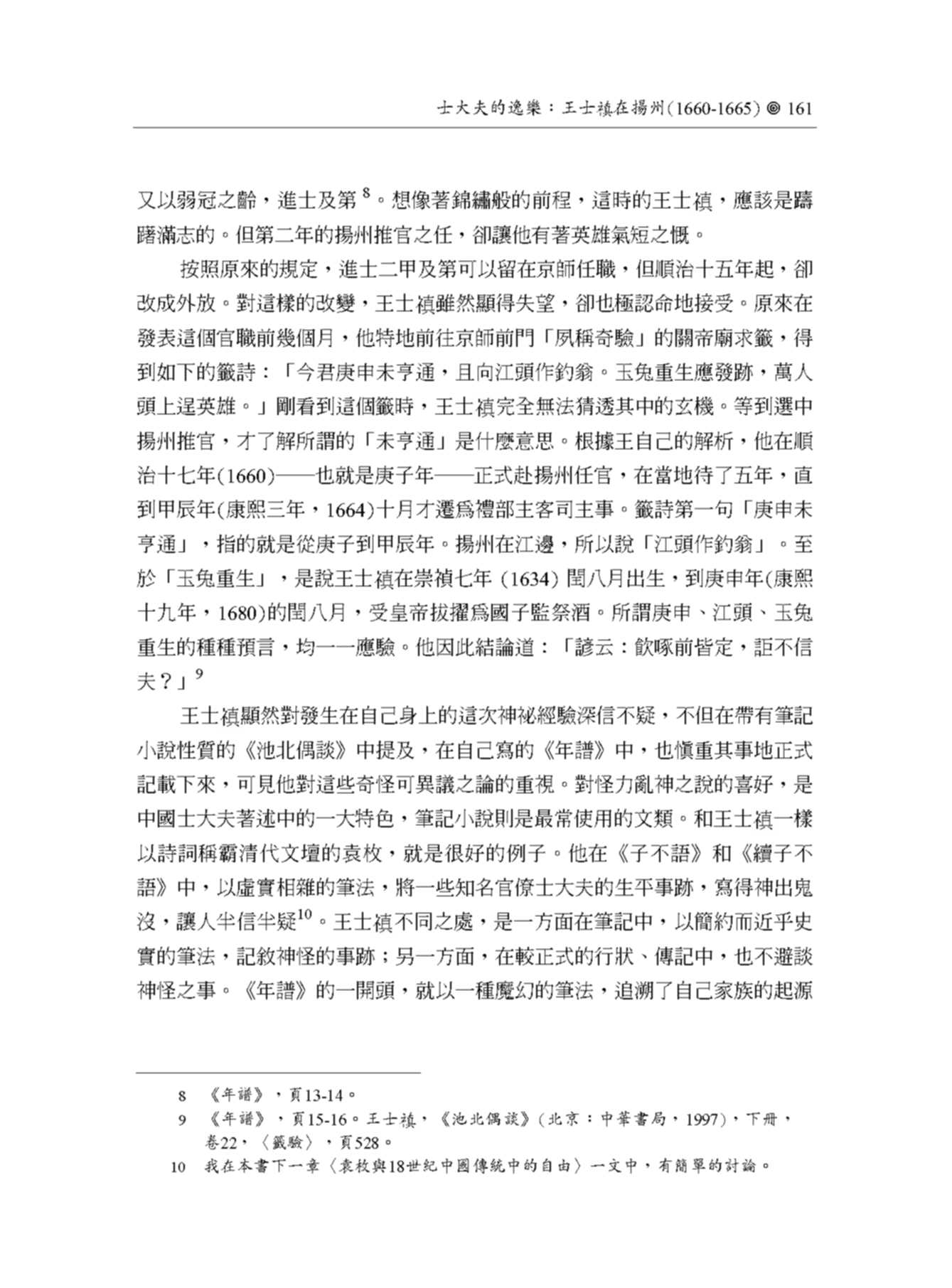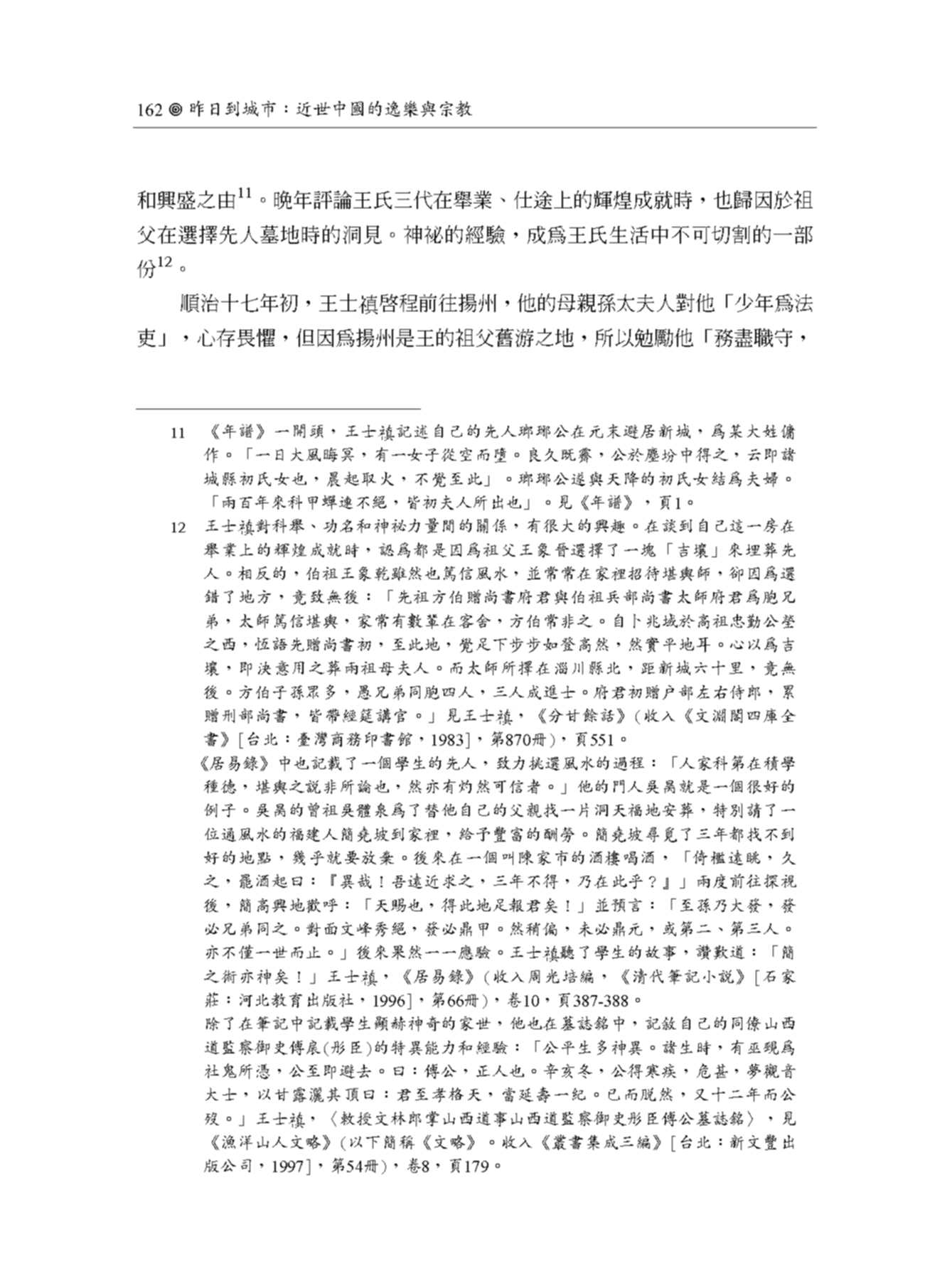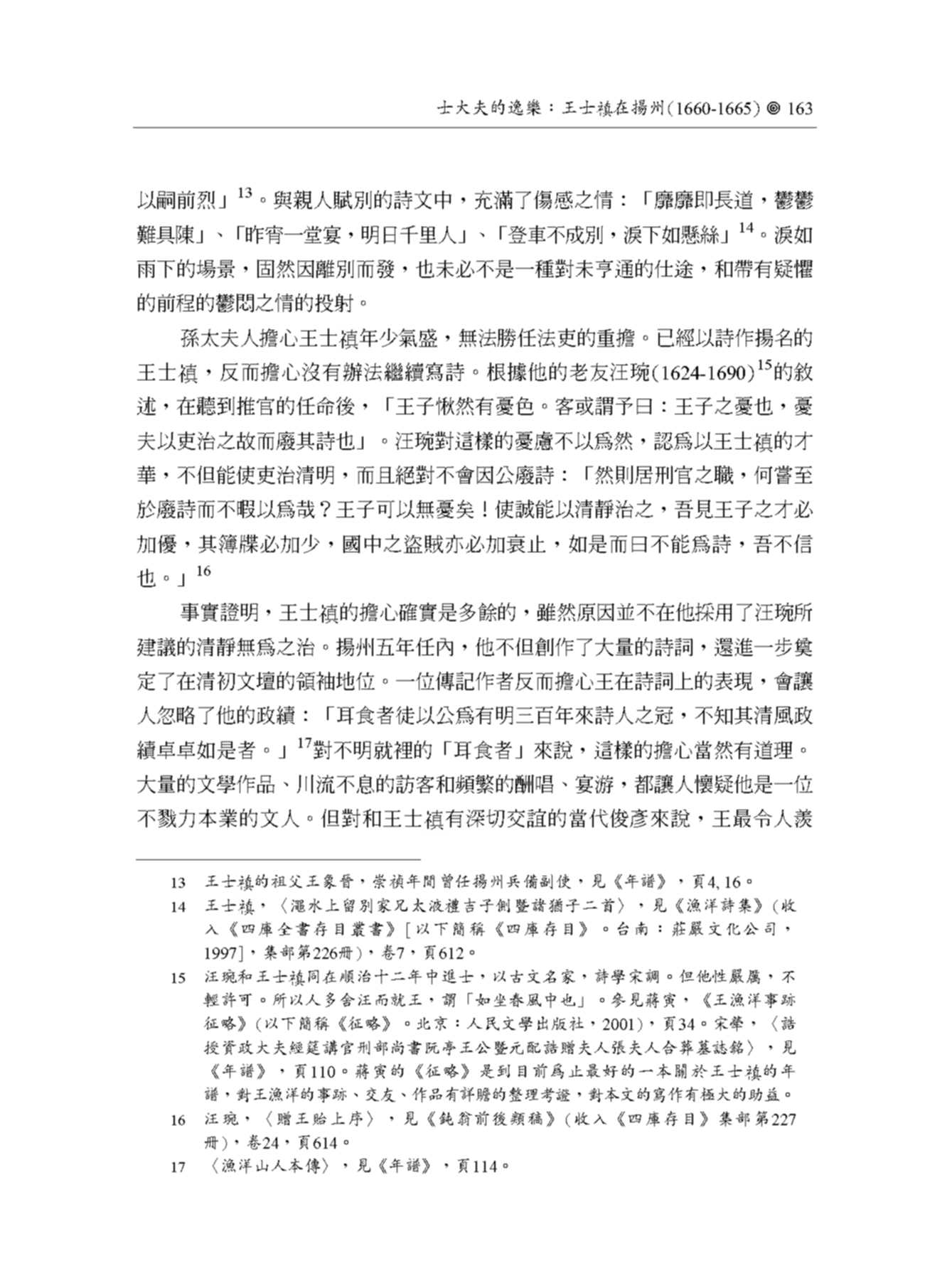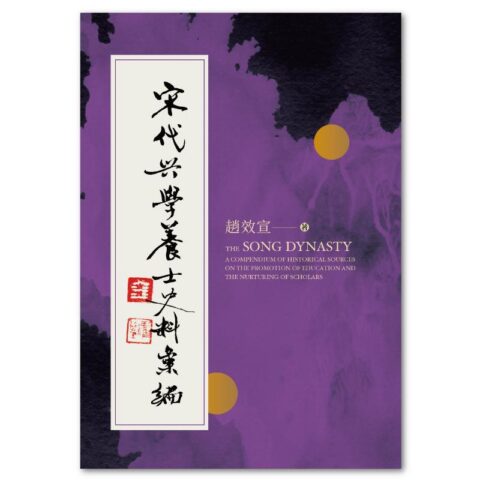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
出版日期:2024-01-18
作者:李孝悌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408
開數:18開,長 23 x 寬 17 x 高 5.7 cm
EAN:9789570872378
尚有庫存
本書共收集九篇文章,處理的主題,包括了城市、逸樂、情欲,以及怪力亂神的宗教想像和實踐。這些課題正好可以作為禮教世界的對立面,以人間樂土的面貌,重新區劃出一塊醒目的疆域,讓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的文化與社會。但不論是20世紀的上海,18世紀的揚州,還是17世紀的南京,經由時空的屏障,卻都像是余懷在回憶中所建構出來的「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一樣,一方面豐富了我們關於城市的想像,一方面卻已成為昨日過眼的繁華。
本書初版於2008年09月出版。
作者:李孝悌
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委員會博士。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及香港城市大學。著作有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
序言
桃花扇底送南朝:斷裂的逸樂
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
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
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 (1660-1665)
袁枚與18世紀中國傳統中的自由
18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
在城市中徬徨:鄭板橋的盛世浮生
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1880-1930)
序言
本書中收錄的,是我在過去五、六年間發表或寫成的文章。其中除了〈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屬於研究回顧一類的文字外,〈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及〈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兩篇文章,是以城市和鄉村的一般民眾為主體,其他六篇都以上層士大夫文化為研究重點。如果和我之前的研究放在一起來看,由近代向傳統,由群眾向士大夫,由大眾文化向精緻文化移動的軌跡確實非常明顯。
這其中除了〈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一文外,轉變的背後其實還是有一定的脈絡可尋。1985年我剛到哈佛讀書時,一方面隨著孔復禮(Philip Kuhn)教授有系統的閱讀清代檔案及民眾叛亂的資料,一方面為了繳交學期報告,在燕京圖書館的書架間毫無目的的翻覽可能作為報告題材的資料。在泛漫無所歸依的搜尋中,我被《白雪遺音》、《霓裳續譜》中質樸的情歌和少女大膽、熱烈的偷情場景所吸引,而以此為題,交了我的第一篇英文報告。這些被五四時代的學者高度評價的俗文學資料,成為我在民眾叛亂的檔案文獻外,另一個進入民眾世界的踏腳石。此後我十幾年的研究興趣,就集中在這個由民眾/社會所衍生出的民眾/文化史的範疇。
我對民眾文化的興趣,在某一個意義上,和我當時所受的社會史訓練有極大的關聯,就是同樣以下層社會和一般人民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而和政治、外交及思想史以上層社會或統治群體為主體的研究,有極大的差別。雖然我後來慢慢了解到,我的第一次「文化」轉向,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其實和社會史也大相逕庭。
這個對民眾文化的興趣,從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的情歌開始,持續了十幾年,中間經過漫長的論文寫作,一直延續到本書中的另一篇文章〈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十八世紀的情歌、檔案中的口供、拳亂民眾的宗教想像或是《五部六卷》中對「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核心觀念的反覆演繹,都不斷以其直接動人的文字、情感、思想和豐富的想像力,對我產生極大的震撼。強烈的程度,和我讀社會史學者從組織、結構的角度分析中國鄉村社會時的感覺,不相上下。
但一方面因為在鄉村和民眾之中逗留的時間已經甚長,一方面因為在寫博士論文《近代中國的戲曲、社會與政治》時,了解到揚州文化在海派文化形成之前的重要位置,和梁啟超對《桃花扇》一劇的高度評價,我決定將研究的重點從近代、民眾轉移到傳統、城市和士大夫文化上。我在寫〈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一文時,受到已故的思想史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對「傳統」與「現代」這組觀念很大的啟發。現在看起來,這篇文章倒頗具象徵意義地,將我的研究從備受西力衝擊而令人厭倦的現代中國,過渡到文化型態迥然不同的傳統世界。
這本論文集中以鄭板橋、袁枚、王士禎為題的三篇文章,都以十七、十八世紀的揚州為主場景,對上層士大夫別具雅趣的生活內容,作了細部的描述。在寫王士禎一文時,我進一步了解到,對許多像冒辟疆一樣的明清之際的士大夫而言,明末金陵才是回憶和歡樂的活水源頭。所以我再次轉移戰場,從二十世紀的上海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揚州,並進而由冒辟疆水繪園所在的揚州府,上溯到明末的南京。
從清代揚州轉到明末南京,與王士禎素有交遊的冒辟疆無疑地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另一方面,從最初透過梁啟超對《桃花扇》一劇的評價而開始細讀劇文起,我就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將劇中的情節和文字寫入論文之中。一路展轉進入南京後,多年的宿願終得實現。〈桃花扇底送南朝〉一文雖然是我另一個以明清南京為題的新研究計畫的起始之作,但我一方面是透過梁啟超這位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史學大師的導引和註解,進入桃花扇的世界;一方面則因為冒襄對明末金陵繁華歲月的追憶,委實過於強烈而鮮明,引發了我同樣強烈的好奇心,一入南京而不可收拾。將這篇文章收入本書中,不論是從傳統與現代的對照,水繪園對明末金陵風華聲教的演繹,或《桃花扇》一作和冒襄的關係而言,應該都不算是過於突兀。既為我從二十世紀上海進入十七世紀中國城市的漫長旅程,找到一個休憩的驛站,也多少有些憑弔告慰前人的意思。
但不管使用的題材是近代上海的城市讀物,十八世紀流傳於城市、鄉村的情歌,還是明清士大夫的詩詞、戲曲創作,這些文章最明顯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逸樂。我在文章中,對逸樂生活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涵,都有比較詳細的討論。這裡要強調的是:耳目聲色之娛當然有可能在有錢、有閑的統治階層或上層社會(包括皇室、官員、士大夫及商人)中佔有比較醒目的位置;對生活在淮北、魯西北、魯西南或川楚交界等土地貧瘠、叛亂頻仍的下層民眾而言,溫飽之不暇,物質感官上的享樂,似乎成了一種遙不可及的反諷。但如果我們把這些西方中國社會史學者作過最好研究的地區放在一邊,而將焦點轉移到十六、十七世紀的江南、華北、長江中、下游或是珠江三角洲的城鎮,我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不一樣的民眾日常生活的景象。
放在這樣的脈絡下來看,我對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和士大夫逸樂的描寫,似乎可以看成是一個重新審視中國人日常生活內容的參照點。我最近信手翻閱大陸學者董新林寫的《墓葬:歷代帝王及百姓死後的家》(台北:五南圖書,2007),深深被大量墓葬圖像中不斷出現的宴飲圖和樂曲演出的散樂圖所震攝。墓葬壁飾在五代達於頂峰,明代之後就很少出現,我們對明清時期民眾日常生活的熱鬧場景的想像,通常是透過《南都繁會圖》《上元燈彩圖》等圖像資料來落實。雖然不管是因死亡或現世生活而觸發的圖像資料,都同樣面臨著「再現」的問題,而在詮釋這本書中的各種墓葬圖像所代表的意涵時,更要將時代、區域、種族和階級等因素考慮在內。但讓我感到訝異不止,乃至興奮不已的卻是:在物質生活繁庶的十六、十七世紀之外,在一個因「死亡」而引發的藝術類別中,逸樂、宴飲和戲曲演出竟佔據了如此醒目的位置。這些壁畫的墓主雖然多半是統治階層,但也不乏一般的民眾:
宋代時期墓葬壁畫中常有「開芳宴」的題材,說明北宋時期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就很講究享樂。此外,單獨的散樂圖或墓主人夫婦對坐宴飲圖的題材更為多見。
也許是出於對現世生活的依戀和不捨,卒至選擇生活中最美好的場景來裝點死後的居所。「逸樂」看起來,確實是我最近所著迷的「文化圖式」(cultural schema)中的一條主軸線吧!
就如同墓室壁畫中居於要角的逸樂與宗教題材一樣,我這些對塵世生活的描述,逸樂之外,宗教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這些宗教題材不僅在現代化的上海製造出鬼魅魍魎和鄉野傳奇的氛圍,在笙歌不斷,「無朝非花、靡夕不月」的水繪園,也像戲曲旋律一樣,縈繞在傳統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再加上袁枚《子不語》中虛實相間的神怪故事,和王士禎對家族起源、興衰的不可思議的玄妙之言,讓我們勢必得重新思考宗教在明清士大夫文化中的位置。過去不論是思想史家對宋明理學的分析,或社會史家所建立的「士紳社會」的典範,都讓我們對中國士大夫文化的內涵和骨架有了最根本的掌握。我從民眾重新回到士紳階層時,採用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冒襄留下的資料正好提供了最佳的素材。就像我在〈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一文中開頭所說的:「更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忠實地扮演現世儒生這個角色的同時,冒辟疆以驚人的細節,展現了他狂亂而超現實的宗教信仰。儒家的道德信念,士紳的現實關懷,超自然的神秘信仰,極耳目聲色之娛的山水、園林、飲食、男女與戲曲,共同構成了冒辟疆生活的整體面貌。」如果我們的文化史研究能在思想史和社會史的學術典範下,作出一些不同的貢獻,或許能稍減我們縱情逸樂的焦慮。
這些文章中第三個明顯的主題是城市。從上海到揚州到南京,城市為民眾的休閑、娛樂和士大夫的精緻品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舞台。〈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一文的主體雖然多半是從各地搜集而來,「鄙俚淫褻」、出諸「里巷婦女」或「村嫗蕩婦」之口的情歌小唱,但不論是唱本的刊行、販賣,茶館、戲園的演出,或是像《馬頭調》之類,經由通都、大邑的碼頭、驛站而流傳的民間小調,都依然和城市有密切的關係。冒襄水繪園所在的揚州府如皋縣,雖然不能和北京、南京、揚州或蘇州之類全國性的城市相比,但卻因為冒本人和南京、揚州的密切關係,提供了我們一個重新思考上層士大夫如何在縣城,乃至鄉鎮,複製大城市的生活經驗和文化型態的機會。
我對文化史的興趣,雖然從1985年交的第一篇學術報告,就可以窺見端倪,但對基層社會和民眾叛亂等社會史的課題,卻始終未能忘情。對許多在哈佛及其他美國大學選修「清代檔案」一課的學生而言,鍾人杰的叛亂案,大概是他們了解清代中國社會最主要的據點。道光二十一年(1841),湖北武昌府崇陽縣因案斥革的秀才鍾人杰,因為包攬錢糧,和縣府胥役憑生釁端,卒至聚眾為亂,攻縣城,殺縣令,並進而「劫庫獄,散倉粟,造幟械」,自封元帥,公然謀反。正為中英鴉片戰爭所困的清政府,大動干戈,才平定了這次發生在叢山之中的內部叛亂。
經由清廷的奏摺、叛亂者的口供、知名士紳/學者的墓誌銘和反映地方觀點的筆記小說資料,我大致體會到Clifford Geertz所謂的「深描」的意涵。經由這些層層交織的細部資料,我不但進入了一個從來不瞭解的中國地方社會,對其複雜的權力生態有所掌握,而且可以由這個切入得既深且廣的個案出發,去衡量整個中國社會運作的模式。換言之,我們可以以這一個小小的個案做參考架構,去尋找中國地方社會中不斷反覆出現的主軸和要素。
我在寫冒襄等幾篇文章時,鍾人杰的叛亂案就像縈繞在水繪園中的戲曲旋律一樣,不時閃過。如果鍾人杰的叛亂案可以讓我們由小窺大,成為了解中國社會的重要據點,王士禎的八首水繪園修褉詩,冒襄作為儒生/文人/地方士紳/風流名士的複雜面相,以及他令人驚異的宗教歷程和水繪園生活中的種種細節,是否也可以為我們了解中國士大夫文化提供一個切入、參照點呢?
我在前面和文章中都提到,西方文化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著社會史而發的一種旗幟鮮明的反抗。Lynn Hunt在1989年主編出版的論文集The New Cultural History駸駸然有篡奪十幾年前才取得霸權地位的社會史的聲勢。 但十年之後,當Victoria Bonnell和Lynn Hunt重新檢討新文化史的走向時,卻已對一些激進的文化史家和後現代主義者必欲將社會史的課題和預設完全抹煞的企圖感到不安:「社會的角色或意義也許有問題,……但沒有它的生活卻證明不可能。」 社會史的各種理論預設和前題,雖然受到新一代文化史家和後現代主義者深刻的檢討、質疑,但社會史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課題和累積的豐富研究成果,卻是文化史家不得不嚴肅以對的資源。
對於如何正視、利用社會史家所留下的學術資源,由計量史、社會史出身,積極參與「文化轉向」,並進而向Lynn Hunt一樣,反省文化史走向的William Sewell在Logics of History一書中有極精彩的闡發。在William Sewell看來,社會史、社會科學和人類學在過去幾十年所累樍的最重要課題之一,就是「結構」(structure)。結構可以有不同的層次和不同的屬性,但Sewell最感興趣的則是結構作為律則、資源與圖式(schemas)所蘊含的意義與限制。
我在過去二十幾年內讀到的美國中國社會史論著中,最具啟發性的就是對民眾叛亂、基層組織、社會結構及非人格因素等課題的研究。Sewell的討論,除了讓我能將這些研究放在更廣大的西方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中來考量,也清楚的顯示出:結構式的分析,其實也可以對感覺上輕薄浮軟──雖然這種感覺多半是一種未經深刻省思的成見和誤解──的文化史研究,帶來極大的助益。我對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鄉野圖像、民眾心態和十八世紀婦女感情世界的探索,似乎正可以歸入文化圖式或心靈結構的範疇。當我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或城市史的研究,不斷面臨宋史或研究其他時代的學者「古已有之」的質疑時,Sewell的分析架構格外顯得有意義。我們過去幾年的文化史研究,在細節和個案的累積上,對一個新開發的領域而言,應該起了發凡奠基的作用。這些細節和個案當然可能只反映了一個特殊的時代,但也極可能是一種反覆出現的主題。如何將這些研究放在特殊的時空背景或文化圖式中來考量,也許是一個值得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十六世紀初葉起,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哲學思想、社會秩序、社會風氣和日常生活的內容等各方面都帶來極大的衝擊。從鄉里到城鎮,從江南到華北,從平民百姓到上層士大夫,生活的富裕在食衣住行和宗教、逸樂各方面所帶來的巨大改變,對那些固守著儒家道德信念的士紳來說,無疑是另一次禮壞樂崩的末世巨變。出生在浙江嘉興青鎮(即今日著名的古鎮烏鎮),以為官清廉著稱的李樂,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進士,萬歷初致仕歸里,正好目睹了發生在各地和他的家鄉的變化。他的二十字短詩:「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鮮明扼要地勾勒出一個被顛倒的世界,以及這個以城市為代表的現實世界和道學家理念間難以跨越的鴻溝。
我在這本書中處理的幾個主題,不論是城市、逸樂、情欲,還是怪力亂神的宗教想像和實踐,正好可以作為逐漸消蝕而為李樂所哀惋的禮教世界的對立面,以另外一種人間樂土的面貌,重新區劃出一塊醒目的疆域,讓我們能從富裕與貧窮、城市與鄉村、情慾與禮教、奢靡與簡樸、逸樂與叛亂、宗教與理性等命題出發,重新審視中國的文化與社會。但不論是二十世紀的上海,十八世紀的揚州,還是十七世紀的南京,經由時空的屏障,卻都像是余懷在回憶中所建構出來的「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一樣,一方面大大豐富了我們關於城市的想像,一方面卻都已成為昨日過眼的繁華。
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
李孝悌
王士禛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禛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或是對廣陵詞的影響,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自然就成為王士禛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禛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美國學者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在本文中,我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以王士禛在揚州五年 (1660-1665) 的仕宦生涯為基礎,探討一位文人/士大夫在清初江南生活的全貌,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詩人角色的轉換,以及與前朝遺民、布衣文人、當朝官員的交游網絡。我也將討論他日常的詩酒酬酢、宴游活動及對揚州與江南景物的流連。和過去習慣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學史、政治史的取徑著手,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不同的是,本文將從生活的細微末節出發,為明清士大夫文化的研究,提供另一個詳細的個案和新的視角。並希望透過士大夫個人豐富的生活經驗,來重建一個和現代世界不同的文化風貌和生活型態。
王士禛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 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禛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 或是對廣陵詞壇的影響, 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或是對他的主要詩歌創作理論「神韻說」提出批判和疏解,自然就成為王士禛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禛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極佳的素材。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很好的範例。 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我在這篇文章中,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檢視王士禛在揚州五年仕宦生涯的細節:從就任前的猶疑、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與詩人兩種角色的轉換、絡繹於途的訪客,到日常的詩酒酬酢、對揚州與江南山光水色的流連,以及與文人故交的宴飲狂歡,都將一一觸及。在習慣了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後,我們似乎忽略了這些人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在型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結果是我們看到的常常是一個嚴肅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層文化。缺少了城市、園林、山水,缺少了狂亂的宗教想像和詩酒流連,我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構,勢必喪失了原有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我曾經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一個半生蹇塞的文人/藝術家對揚州生活的回憶。 王士禛以其過人的才華、精力和聲名,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幅大異其趣的生活景象,值得細加品味。
一、揮淚下揚州
順治十五年 (1658),年僅二十五歲的王士禛通過殿試,成為新科進士。前一年,他才因為在濟南明湖和諸名士唱和,以四首〈秋柳詩〉譽滿士林。如今又以弱冠之齡,進士及第。 想像著錦繡般的前程,這時的王士禛,應該是躊躇滿志的。但第二年的揚州推官之任,卻讓他有著英雄氣短之慨。
按照原來的規定,進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師任職,但順治十五年起,卻改成外放。對這樣的改變,王士禛雖然顯得失望,卻也極認命地接受。原來在發表這個官職前幾個月,他特地前往京師前門「夙稱奇驗」的關帝廟求籤,得到如下的籤詩:「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剛看到這個籤時,王士禛完全無法猜透其中的玄機。等到選中揚州推官,才了解所謂的「未亨通」是什麼意思。根據王自己的解析,他在順治十七年 (1660)──也就是庚子年──正式赴揚州任官,在當地待了五年,直到甲辰年(康熙三年,1664)十月才遷為禮部主客司主事。籤詩第一句「庚申未亨通」,指的就是從庚子到甲辰年。揚州在江邊,所以說「江頭作釣翁」。至於「玉兔重生」,是說王士禛在崇禎七年 (1634) 閏八月出生,到庚申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閏八月,受皇帝拔擢為國子監祭酒。所謂庚申、江頭、玉兔重生的種種預言,均一一應驗。他因此結論道:「諺云:飲啄前皆定,詎不信夫?」
王士禛顯然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次神祕經驗深信不疑,不但在帶有筆記小說性質的《池北偶談》中提及,在自己寫的《年譜》中,也慎重其事地正式記載下來,可見他對這些奇怪可異議之論的重視。對怪力亂神之說的喜好,是中國士大夫著述中的一大特色,筆記小說則是最常使用的文類。和王士禛一樣以詩詞稱霸清代文壇的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子不語》和《續子不語》中,以虛實相雜的筆法,將一些知名官僚士大夫的生平事跡,寫得神出鬼沒,讓人半信半疑。 王士禛不同之處,是一方面在筆記中,以簡約而近乎史實的筆法,記敘神怪的事跡;另一方面,在較正式的行狀、傳記中,也不避談神怪之事。《年譜》的一開頭,就以一種魔幻的筆法,追溯了自己家族的起源和興盛之由。 晚年評論王氏三代在舉業、仕途上的輝煌成就時,也歸因於祖父在選擇先人墓地時的洞見。神祕的經驗,成為王氏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份。
順治十七年初,王士禛啟程前往揚州,他的母親孫太夫人對他「少年為法吏」,心存畏懼,但因為揚州是王的祖父舊游之地,所以勉勵他「務盡職守,以嗣前烈」。 與親人賦別的詩文中,充滿了傷感之情:「靡靡即長道,鬱鬱難具陳」、「昨宵一堂宴,明日千里人」、「登車不成別,淚下如懸絲」。 淚如雨下的場景,固然因離別而發,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未亨通的仕途,和帶有疑懼的前程的鬱悶之情的投射。
孫太夫人擔心王士禛年少氣盛,無法勝任法吏的重擔。已經以詩作揚名的王士禛,反而擔心沒有辦法繼續寫詩。根據他的老友汪琬 (1624-1690) 的敘述,在聽到推官的任命後,「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汪琬對這樣的憂慮不以為然,認為以王士禛的才華,不但能使吏治清明,而且絕對不會因公廢詩:「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為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為詩,吾不信也。」
事實證明,王士禛的擔心確實是多餘的,雖然原因並不在他採用了汪琬所建議的清靜無為之治。揚州五年任內,他不但創作了大量的詩詞,還進一步奠定了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一位傳記作者反而擔心王在詩詞上的表現,會讓人忽略了他的政績:「耳食者徒以公為有明三百年來詩人之冠,不知其清風政績卓卓如是者。」 對不明就裡的「耳食者」來說,這樣的擔心當然有道理。大量的文學作品、川流不息的訪客和頻繁的酬唱、宴游,都讓人懷疑他是一位不戮力本業的文人。但對和王士禛有深切交誼的當代俊彥來說,王最令人羨慕、稱許之處,正是他在刑官與詩人兩種角色間優游裕如的轉換。不過在進入這個主題前,我覺得有必要交待一下王士禛在推官任內的表現和挫折,以便對他生活、情感的各個面向,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先是,順治十六年 (1659),王士禛到任前一年,鄭成功率領的軍隊進犯長江沿岸,直抵鎮江、包圍金陵,東南人士群情振奮。明鄭軍失敗後,清廷開始追查江南各府州縣之迎降鄭成功者,株連極廣。 順治十八年 (1661),清廷派出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官員到江寧負責審理這些通敵的重大案件:「辭所連及,繫者甚眾。監司以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王士禛則以審慎的態度,將沒有證據的官員、人犯釋放,將隨意告訐他人的奸宄之徒下獄,因此活人無算。
王士禛公正不阿的辦案態度,由此可見。這種敢於堅持己見,不怕忤逆上司的作風,雖然在這一次的事件中並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應,卻在第二年招致降級的處分:「山人居官公正嚴肅,不畏強禦。每疑讞重獄,據案立決,牘無留滯。時失出法嚴一事,被部駁輟至鐫級。」對這樣的挫折,《年譜》中只平淡地記敘了孫太夫人的勸勉:「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計也。」王士禛似乎也默默地接受了母親的勸勉,一本良知地平反了許多冤案。
但從他和冒辟疆的往來書信中,我們卻可以猜測這次懲處,讓王士禛感到極度的沮喪。事實上,早在前一年,他就因為一項「極沒要緊事」,被部議罰俸一年,而發出「弟本無宦情,只得浮沉任之耳」。 壬寅年(康熙元年,1662)他被降級處分後,更覺得人生了無生趣:「弟近況益惡,非筆札所能悉其萬一。庾子山云:『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老世翁橋梓愛我最深,何以教之。棧豆寧復可戀,甘作駑駘,豈不可笑。」 同一年冬天的另一封信,說「爾來諸事拂鬱,無復人理」。 短短幾個字,仍然透露出他極端不滿的情緒。同樣的怨懟,在康熙三年又出現了一次:「邇來事事拂逆,告貸無門。殆如少陵所云:心死作寒灰,無復人理。」 此處所說的事事拂逆,可能和長兄士祿作考官時監督不周,因而下獄有關。王士祿是順治九年 (1652) 的進士,康熙二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以磨勘罣吏議,逮下獄」。 士禎因為不能代兄赴京申冤而感到無限的愧疚,這點下文還會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