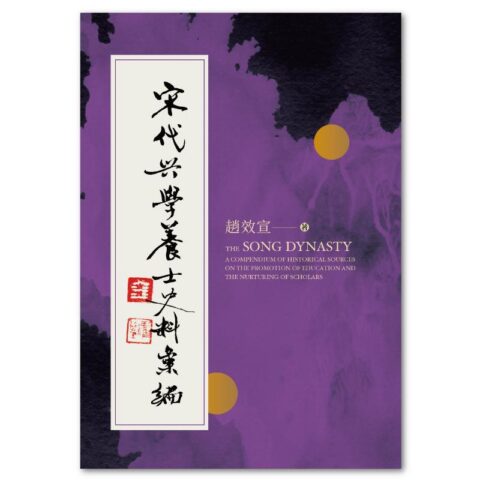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
出版日期:2012-01-18
作者:錢理群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32
開數:18開
EAN:9789570839241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被公認為東亞區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
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當代中國重要知識分子
以獨特觀點,從個人歷史記憶出發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做出最完整的回顧、批判、反思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共八十萬字,醞釀了二十五年,反映了錢理群近期研究與思想的重要結晶,
試圖通過本書建構一個底層(我─錢理群,民間思想者)、高層(毛澤東)、中間層(知識分子)互動的三維敘述空間、結構
此三層之間的互動、反抗、合作、背離
形成一個複雜交錯的歷史過程,
並構成中國今日思想狀況的藍圖。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完整呈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路歷程
堪稱近年來華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回顧與自傳。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提供了讀者看待當代中國問題時不可多得的思想資源,對於當前「中國崛起論」、「中國模式論」的知識熱潮,以及「毛澤東的幽靈」浮現於「後毛澤東時代」的徵象,提出即時有力的回應與批判。
錢理群以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通過本書,對於自己如何走過毛澤東影響下之共和國六十年,做出回顧與反思。共和國六十年的政權迭替,整個國家民族經歷了分裂動盪,在錢理群平靜而從容的敘述調子底下,內蘊著歷史的激情與蒼涼。
「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扎、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錢理群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作為親歷共和國六十年的獨立知識分子,錢理群以其豐厚的歷史經驗與直面現實的批判力度,為讀者打開一扇深入了解1949年至今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民間思想知識狀況與毛澤東思想實踐的窗口。錢理群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本書的敘述框架,指出毛澤東時代的1957年所底定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與後毛澤東時代有著內在的貫串性聯繫,這是批判性理解當下政體的核心關鍵。同時,錢理群致力挖掘中國當代民間思想,力圖在被鎮壓、被抹殺的「民間異端」歷史中,重拾那頑強存在的民間思想,並繪製其知識系譜,以提出一條中國民間版的社會主義思想道路。錢理群以其豐富的史料文本與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參與者的親歷經建,精采地勾勒出中國戰後思想狀況的景貌,並站在民間的立場、從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角度,為讀者漸次打開、進入中國大陸戰後歷史與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達到心的交流。
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裡順著歷史行走順序,將中共建國之後至今六十年的歷史分為建國初期(1949-1955)、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大躍進年代(1958)、大饑荒年代(1959-1961)、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文化大革命年代(1966-1976)、後毛澤東時代(1977-)。在同時考量各歷史時期的國內情況/國際情勢的視角下,他將整段歷史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分野,強調毛澤東與中共在前段時期所奠定的中國共產黨之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如何後遺到「後毛澤東時代」、成為後段時期實行改革開放的基礎,同時提出反右運動前後所奠定的「1957年體制」是「1989年體制」的基石,兩者間有著內在的歷史連續性,如此方能歷史化的理解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體核心。
更重要的是,錢理群考察了自1950年代即出現的校園「右派」(校園民主運動),文革間的民間思考、1980年的民運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並認為它們之間有一脈「社會民主主義」的知識思想連續,亦與1990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知識分子論爭以及當下中國的民間社會運動,有著複雜的內連性質,而這些知識運動與黨內思想的分派彼此扯動,形成上下相互吸收、影響的關係。
錢理群先生將當前中國的思想、知識光譜做了歷史化的考察,並以此回應、分析所謂「毛澤東的幽靈」在「後毛澤東時代」浮現的現象,對於當前「中國崛起熱潮」以及與之相應的知識徵候,提出即時、有力的批判與警醒。
本書《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冊)以前言為始,從起自建國初期(1949-1955年),迄至第九講 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年)(下)。
作者:錢理群
1939年出生於抗戰中的重慶,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1960到1978年先後在貴州省安順地區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目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被公認為東亞區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和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以研究魯迅著名,並曾名列北京大學學生評鑑「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首位。
他不僅對魯迅思想擁有一種理解與把握,早在中國大陸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就在最終決定文學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與「文學」之間發現了「文化」的仲介作用,在1990年代進一步的研究中,試圖把20世紀文學置於本世紀的歷史中心課題──「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現代出版」和「現代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為「文學外部關係的研究」領域上打開一條新的思路。
2002年從北京大學退休後,又重歸中學與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
錢理群的重要性在於,歷經中國文化大革命、七九年民主改革、八九年天安門等重大歷史事件,帶著近五十年中國變動的歷史記憶、政治和社會改革思潮,對中國民主運動發出犀利的批判與反思。
著作甚豐,出版的書近五十種,代表作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1948:天地玄黃》等。最新著作為2007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的《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2008年在台灣出版的《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以及《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等。
前言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二、毛澤東思想、文化的幾個基本特點
三、毛澤東在當代中國
四、毛澤東對世界的影響
第一講 建國初期(1949-1955年)
一、歷史交替時期我和我的家庭
二、知識分子的選擇:以沈從文爲例
三、在治國道路和模式上毛澤東的選擇
第二講 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上)
一、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的反應:尋找中國的發展道路
二、毛澤東的內在矛盾
三、國內外、黨內外的反響和毛澤東的對策
四、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反應、政治形勢瞬息萬變
第三講 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下)
一、青年學生的反應:中國校園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
二、「一切問題都要重新估價」:顧准的思考
三、反右運動中的毛澤東、我和知識分子
四、反右運動以後毛澤東在理論上的修正
五、反右運動以後建立的「五七體制」
第四講 大躍進時代(1958年)(上)
一、「你們難道不願意當聖人嗎?」
二、大躍進:毛澤東的治國宏圖
三、全民大煉鋼鐵、全民圍剿麻雀:大躍進的兩個場景
四、我在大躍進中
第五講 大躍進時代(1958年)(下)
一、人民公社運動: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試驗
二、「全民參與」辨析
第六講 大饑荒年代(1959-1961年)(上)
一、從「天堂」落入「地獄」
二、大躍進怎麽變成大饑荒
三、存不存在糾錯機制
第七講 大饑荒年代(1959-1961年)(下)
一、大躍進、大饑荒的民間觀察與思考
(一)顧準:「社會主義的史前期」批判
(二)《星火》:「國家社會主義」批判
(三)張中曉:毛澤東時代的精神批判
二、如何走出困境
三、我在大饑荒年代形成的毛澤東觀、魯迅觀
第八講 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年)(上)
一、中國農民的呼聲
二、底層和中層幹部的反應
三、高層領導的回應與選擇
四、毛澤東的决策:重啓階級鬥爭的戰車
第九講 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年)(下)
一、從大地起風雷
(一)國內戰場:基層、中層和上層的階級鬥爭演習
(二)國際戰場:中美關係與中蘇大論戰
二、中國校園的地下新思潮
三、社會底層的狀况:文革前我個人的遭遇和預感
前言(摘錄)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大概這是一個歷史巧合;我於1939年1月出生在重慶;而毛澤東1939年春在延安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過去大家誤以為1935年的遵義會議就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中共黨史專家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此順便介紹一本書:何方寫的《黨史筆記》,在香港出版。何方是張聞天的秘書,算是歷史的當事人,根據他很具說服力的研究,1935年的遵義會議,只是確定了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特別是軍事指揮層面,但總書記仍然是張聞天,而並非如後來的人所說是掛名的,至少在1939年以前,張聞天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是有實際領導權的,毛澤東只是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真正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是在1938年下半年,這年7月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對當時在莫斯科準備回國的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下了口頭指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並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並樹立他們的權威。這表明,是共產國際任命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王稼祥在9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這個指示,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政治報告,按中共規矩,做政治報告的多為領袖人物,毛澤東既然做了政治報告,代表他當時已有領袖資格、地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舉起了毛澤東自己的理論旗幟,以後,它不僅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主要是反對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的主要理論武器,而且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對毛澤東個人而言,則是為他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不僅是組織上的領袖,更是思想上的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1939年春,毛澤東已經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此,我們可以說,1939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始進入毛澤東時代,我恰好於此時出生。十年後,1949年,我十歲時,毛澤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毛澤東時代。
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我正是三十七歲。十歲至三十七歲,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黃金歲月,由少年至青年至中年,都生活在毛澤東統治下,我的知識結構、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澤東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確立。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不止國際上,中國內部也有一批毛澤東主義者),這意味著我是主動參加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我與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之處。這反映我們生存時代的特點,我們是在革命年代成長,革命年代能把最普通、最邊緣的人物捲入歷史潮流,這在台灣大概很難體會。文革發生時我在貴州,在最邊緣的農村、最邊緣的山區,在那裡也有革命。我們這一代和歷史運動有著血肉的關係,這些歷史運動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身體、情感、心靈,我們的小我和歷史的大我糾纏在一起,這和我的學生輩以及在座諸位非常不同。我的學生後來讀了我的精神自傳,最大的感慨是,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身外的東西,是需要理解的對象,但對我們來說則不是,歷史就是自身。我們這代人和毛澤東所領導的歷史、革命,有非常糾纏的關係,每個人心裡都有著巨大的困惑,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困惑。革命最大的問題是會擠壓個人的自由空間,許多知識分子感受到此種擠壓,想從此束縛中擺脫出來而不得,就有了困惑。但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同,我是主動要求參加到革命中,而不是想擺脫,但我的苦惱是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像魯迅〈阿Q正傳〉說的那樣:不准革命,或者是只能按照別人指揮、設計的模式去革命,當自己有其他想法、有批判意識,則不被允許,於是就產生很大困惑。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未必和毛澤東一致,空有自己想法,但無法讓其成為現實,進而影響歷史進程。這些困惑,對在座諸位大概都是很陌生的。但正在這種受到排擠、鎮壓的情況下,還是堅持主動投入參加革命,使得自己和毛澤東的時代以及革命歷史,發生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我這樣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面臨了重新認識毛澤東的困惑,如何走出毛澤東,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我和毛澤東時代的複雜關係可分兩點來說。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紮、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當然我這樣的立場不容於後毛澤東時代,也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兩頭不討好。因此我讀魯迅的著作會產生強烈共鳴,魯迅〈影的告別〉裡說:「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沈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我覺得這正是我所處的地位和困境。魯迅當年也困惑於他和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複雜的糾葛。他既是這傳統文化最堅決徹底的批判者,又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這種複雜關係引起我的共鳴。魯迅自稱是傳統中國最後的知識分子,說句大話,我也是毛澤東時代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我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一種痛苦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救贖。我已將自己和魯迅的關係清理,如果能將毛澤東的關係清理,就可以無愧見上帝,交待自己一生。魯迅〈頹敗線的顫動〉裡寫到那位「老女人」:「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也能表達我對毛澤東文化的複雜感情:既「咒詛」又「祝福」,既「決絕」又「眷念」,既「復仇」又「愛撫」。因此我對毛澤東的講述,不可能像許多人那樣快刀斬亂麻式的明快徹底,也不可能是冷靜客觀的批判,我的批判是帶著複雜感情的,這也許是種侷限,但同時也是特點。
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我前面的講述裡反覆用了兩個概念: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化。毛澤東文化所指為何?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第一講 建國初期1949-1955(2009年9月22日講)
今天是正式的第一講,我想完全按照歷史的順序講,所以第一講是建國初期,即1949-1955年。建國初期的問題首先在於,面對政權更替,一般老百姓該怎麼適應這種歷史的大變化,包括個人家庭命運的變化;第二,民眾當中特殊群體──知識分子,又如何適應這樣的變化,找到自己在新社會的位置;第三,執政者掌握政權後,要把中國帶往何處?
為了方便大家進入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從個人經歷說起。
一、歷史交替時期我和我的家庭
1949年,我正好10歲,在上海迎接「解放」。當時我是上海幼兒師範附小五年級的學生。我記得大概在1949年6月23日,前一天晚上槍炮聲不斷,那天早上我和一位好朋友一起準時上學,走在大街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在沿街商鋪屋簷下躺著一排排大兵,這大概就是人們口耳相傳中已經相當神祕的「解放軍」了。解放軍為了不擾民,寧可露宿街頭,這使我這個小學生非常感動,許多上海市民也都是由這件小事認識了解放軍、共產黨和新政權的。對比國民黨的傷兵到處騷擾,我們都覺得這個世界真的變了。這個最初的印象十分深刻,一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
現在想起來,其實,還沒有「解放」,我就已經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了,只是我並不覺察而已。事情說起來還有點曲折。我是1948年從南京逃難到上海,原先預計再逃到台灣,但到了上海,我的外祖父和幾位在銀行供職的舅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產黨的影響,一起勸說我母親不要走,所以我們就了留下來,我也在上海上小學。1949年上半年,那時秩序還算正常,我參加了上海市少年兒童的演講比賽,得了第三名。我記得自己講的是諾貝爾的故事,當時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講的是江亞輪沉船事件:1948年12月3日,上海吳淞港口江亞輪運輸大批人逃往台灣,卻發生沉船,失蹤1,600多人,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個象徵性事件,我後來在寫《1948:天地玄黃》時,就將其視為國民黨時代結束的一個象徵。那次我的演講引起一些成人的關注,上海當時有個少年兒童劇團,就把我吸收進去做業餘演員,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所領導的,我也就在實際上被納入共產黨的體制了。我們排了一幕話劇,我飾演一位報童,在街頭貼標語,撒傳單,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因此,上海一解放,我們就到各處的工廠、部隊、軍營去演出。
後來上海拍電影《三毛流浪記》也找了我。「三毛」是漫畫家張樂平(1910-1992)創造的一個流浪兒形象。這部電影於1948年拍攝,到1949年才拍完,恰好跨越了兩個時代。我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闊少爺」的群眾角色,不知道為什麼在「演員表」上有我的名字,前幾年北大學生發現了,就用電腦技術,把電影上我的一個鏡頭定格了,發表在網上,也發給了我,算是一個紀念吧。這部電影公開放映大約是1950年初,我當時已從上海返回南京讀書。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討論三毛不幸命運的原因為何,我也發了言,認為這是戰爭造成的災難。沒想到我的發言遭到了其他大哥哥大姐姐的批判,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就批評我沒有階級觀點,不區別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就是正義戰爭,是不能反對的。還有位大姐姐說,錢理群看來還需要學習及改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改造」這個詞,一直被要求改造到今天。
但「階級」在當時確實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特別我的家庭正是這場革命的對象。我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到,共和國是一場革命的產物,革命是對原有社會結構、秩序的大顛倒,這導致原有階級、社會、人際關係的大變化。我們在歷史的敘述中都會討論到革命的意義,但很少考察這種大變動具體對每個人、每個家庭帶來的問題,以及他們心理的反應,這些都被歷史敘述所迴避,這樣的歷史是簡單化的。
這裡我想談談我的母親的反應。對於她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她原來是國民黨高官的貴夫人,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家屬、反動官僚的家屬,所有人都用不屑的、敵視的眼光看著她,把她視作不可接觸的賤民。但我的母親卻以驚人的決斷和毅力適應了這樣的變化。她首先做的就是立刻把我父親所有的證件,包括蔣介石給他的勝利勛章,全部交給政府;然後她從此絕口不提和父親有關的任何事情,也絕口不提她過去的生活。既然這段歷史被視為罪惡,那就把住關口,從此不說。但她內心深處還保留著對父親的懷念,有兩件事可以看出,在她的臥房裡還掛著我父親的一幅畫像,過年過節時都要添一副碗筷來表示懷念。但後來連這都不被允許,因為我哥哥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家裡怎麼可以掛著反革命分子的畫像呢?後來這些外在的紀念形式都被取消了,思念也了無痕跡。本來她可以向我們傾訴以減輕精神的重負,但她閉口不言,就這麼沉默幾十年,至死也沒有隻言片語談及父親。她只保留了一張結婚照,並小心、頑固地斷絕和海峽對面的一切聯繫。最初兩邊還是有聯繫的,父親會通過香港的關係寄錢回來,從1949年起延續三、四年,後來大哥從美國回來,這筆錢才沒再寄過來。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我在美國的三哥通過輾轉關係傳話,表示願意接濟,這顯然有父親的意思在內,但母親斷然拒絕。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緩和後,三哥讓他的親戚到南京來探視我們,帶了錄音帶希望母親留幾句話給他,母親還是斷然拒絕。
她又以極其謙和的態度對待周圍所有的人,政府的一切號召,從災民捐贈寒衣,到大躍進獻銅獻鐵,她都極積響應。街道居委會表示希望利用我們家裡的汽車間辦個學習班,我母親欣然同意,並跟著大家一起學唱革命歌曲;後來居委會又提出房子不夠,希望獻出我們樓下的房子,她也毫不猶豫同意,反倒我們通通不同意。接著搬來新鄰居,她也處處禮讓。我那時常責問她為何那麼小心,她默默看著我,不說一句話。
就這樣幾十年風雨都過去了,到文革時,全家都很緊張,以為在劫難逃,但母親仍坐在長年坐著的那張破籐椅上,繼續編織毛衣,比我們所有人都鎮靜。後來出現了奇蹟,我們家對面就是學校,但紅衛兵竟然沒來抄家,據說是居委會幫的忙,他們說這個老太太人非常好,別去打擾她。但母親愈來愈虛弱,終於病倒。我清楚記得,當時從我工作所在地的貴州趕到南京她的病榻前,母親一面喘息一面說,這幾十年來我總算沒有連累你們……,說完不久就去世了。這時我才懂得母親幾十年的堅忍,就是為了保護我們這些孩子,她用柔弱的肩膀獨自承擔一切,默默保護我們每一個人。後來我寫篇文章紀念我母親,說這是「一種堅忍與偉大」。這是一個普通婦女,在面對巨大歷史變局時,所做出的回應。
當然我們家裡也不盡然都是這樣陰暗,也有陽光照耀的時候。我有一個哥哥是共產黨員,一個姐姐是解放軍。姐姐在上海淪陷區加入了新四軍,我那時人在重慶,兩人沒見過面,我們見面是在1949年以後。有天姐姐和姐夫穿著解放軍綠色軍裝來到家裡,我當時覺得他們是從天而降的「神兵」。此後我們家又成了「革命軍人家屬」。我們既是革命軍人家屬,又是反動官僚家屬,歷史變化具體而微地縮影都在我們家裡。此後我們家中永遠只談哥哥、姐姐、姐夫,而不談父親。
儘管家中充滿陰影,但我個人的童年生活還是充滿陽光,我當時就讀的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中學,就是全南京最好的學校。這與毛澤東在解放初期的政策有關。當時他為了政權的穩定,採取兩個措施,一是不「四面出擊」,強調不要樹敵太多,同時強調在歷史「轉變的緊張時期」,「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一些」;二是更加高明的「包下來」的政策,所有國民黨留下來的成員,只要不公然反對共產黨,都給予基本生活、工作保障,用毛澤東的說法,就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均吃」。
在學校裡也有兩項措施。首先是大量吸取底層人民、工農的子弟來讀書,所以我們很多同學是從農村來的。2006年,也就是中學畢業五十週年時,許多同學都寫了回憶文章,一位來自皖南西部偏遠山區的同學,生動地敘述了他百里迢迢來附中上學的情景:「頭一回乘船」,然後「頭一回轉乘長途客車」,再「頭一回乘火車」,最後「頭一回乘市區公共汽車」,才來到學校,「一路上,頭一回看到高樓大廈,看到兩旁種著法國梧桐的林蔭大道,排列成行的路燈和五彩紛呈的霓虹燈……」。這「頭一回」,實在是歷史性的: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引導農民和他們的子弟,進入現代城市,接受現代教育,參加國家建設。在教育方面,除了像這位同學這樣,在正規學校接受教育以外,還辦了許多工農速成中學、夜校、識字班,讓已經成年的工人、農民有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據新華社報導,有4,200多萬農民參加了1951-1952年冬季學校的學習,還有數百萬人參加了其他各種為工人和農民開辦的業餘學校的學習。為工農幹部設立的速成中學在1954-1955學年招收了5萬1,000名學生。應該說,政府在為工農提供教育機會是不遺餘力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也因此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這個「新中國」的主人。
而且在進入城市以後,農民的子弟還受到了特別的照顧:當時國家的教育、衛生、文化、社會福利政策,都是傾向於工農的。這位同學保留了當年的日記,就有這樣的紀錄:
1953年12月14日記:我因一時交不出膳費,就吃「半夥」,只吃早晚兩頓。這受到同學的普遍關心。說這會損害健康。陳重明同學拿出五千元〔錢註: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五角,當時是不小的一筆錢〕硬要我吃午飯,說這是「對祖國負責」。我謝絕了,但極感動。他們這都是社會主義品質啊!
1953年12月21日記:徐易告訴我,余仁老師已把我的伙食問題反映到教導處,決定提高我的助學金〔錢註:後由丙等提到甲等〕。我很感不安,因為我本意是想自己克服困難,不增加國家困難。
這兩則當年的日記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提到「社會主義品質」問題,這也是我們這一代接受的教育:社會主義就是強調「社會平等」和「一人有難,人人相助」,而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依然處於相對貧困的地位,這顯然是一個問題,因此,國家的政策向他們傾斜,給予全額助學金,不但合情合理,也是由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
這位同學日記裡提到的陳重明同學,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兒子,這也透露出一個重要事實:當時的共和國的教育,一方面向工人、農民和底層人民子弟傾斜,另一方面,也讓上層社會的子弟繼續讀書。這和後來(主要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逐漸限制,甚至剝奪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的權利,是大不一樣的。我們學校本來是中央大學的附屬小學,是一所貴族化的學校,同學的組成原先主要是國民黨官員子女,後來則多為大學教授子女,現在則上下階層都有,大家平等地在一起受教育,底層人民的子弟又受到格外的照顧。像陳重明和這位農村來的同學之間的友好關係,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這也可以說是新中國教育在其初期的一個新氣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