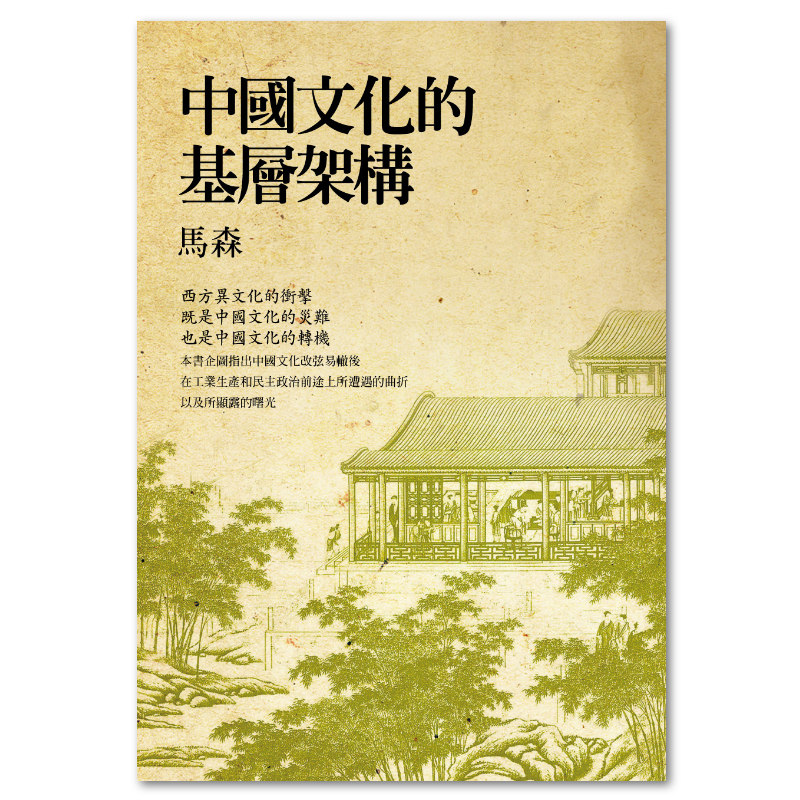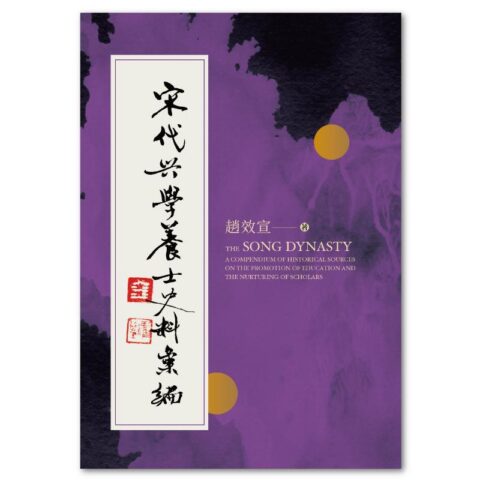中國文化的基層架構
出版日期:2012-03-14
作者:馬森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288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39562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西方異文化的衝擊
既是中國文化的災難
也是中國文化的轉機
本書企圖指出中國文化改弦易轍後
在工業生產和民主政治前途上所遭遇的曲折
以及所顯露的曙光
本書從中國遠古的文化形成與其架構講起,除了參考結構功用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理論,也兼採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神話研究路徑以及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和榮格(Carl G. Jung)所建構的心理分析和文化原型(archetype)的理論,主要討論的是中國文化在歷史發展中的基層架構及其影響。其重點有二:
一、提出「老人文化」做為中國文化基層架構的表徵:虞舜和姜太公的神話反映出古中國以周文化為基礎的「老人文化」的基本特徵,是故代表周文化的儒家在農業經濟、宗法制度的社會中得以一枝獨秀,屹立數千年。但是到了工業社會,老人權力頓失,缺點顯露,反倒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
二、提出「繭式文化」做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模式: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屢蹼屢起,其間晦暗之時,與其若湯恩比(Arnold Toynbee)稱之謂「僵化」(petrifaction),莫若稱之謂「繭化」。任何文化相對於族群都具有雙重作用:一面維繫、保護族群的生存與發展,一面也局限了族群的發展趨向,正如繭之於蛹的關係。中國文化也須經過繭縛與破繭的過程,如果能破繭而出,自將會是另一種面貌。
西方異文化的衝擊,既是中國文化的災難,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轉機,本書也企圖指出中國文化改弦易轍後,在工業生產和民主政治前途上所遭遇的曲折以及所顯露的曙光。
作者:馬森
序言
第一章 文化的意涵
第二章 文明的成長、僵化與覆滅
第三章 人類文化的模式──繭式文化
第四章 周文化的歷史地位
第五章 神話與神話原型
第六章 商周的遞嬗與宗法制度
第七章 家族主義的形成與持續
第八章 周公與孔子
第九章 孟子的光輝與矛盾
第十章 不見容於周文化的墨家
第十一章 道家對周文化的背反
第十二章 儒家的另一面──法家
第十三章 中國文化中的陰陽觀
第十四章 秦文化的興起與消弭
第十五章 周文化的復起與鞏固
第十六章 家族倫理的政治化──釋《孝經》
第十七章 中國文化中的女性地位:《列女傳》的意義
第十八章 中國人心靈中的黑暗海洋
第十九章 中國文化的轉折
第二十章 從傳統到現代
第二十一章 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
第二十二章 結語
參考資料
附錄 馬森著作目錄
索引
生在五四運動後的大變動時代,身經日軍侵華和國共鬩牆的兩大戰亂,目睹國人從傳統向現代蛻變所遭受的種種痛苦,不能不對我國的文化與國運有所反思。從清末義和拳的「扶清滅洋」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陳序經的「全盤西化」,一路走來倍感艱辛,距離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仍然如此遙遠。回首我國的固有文化,既然綿延數千年之久,絕對有其存在及持恆的理由,不能以「封建」一語概括否定。如果沒有遭受到清末以來的西潮東漸,中國文化勢將依循千年的故轍繼續發展,亦會自我完足,不假外求。然而西潮打亂了中國的發展軌跡,對比之下,國人不可能再有任何不假外求自我完足的感受,於是強力扭轉前進的方向,以俾能夠加入世界列強的行列並駕齊驅,此乃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大勢使然。
世人所謂的「四大文明古國」,除巴比倫外均尚生殖繁延於世。尤其是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的顛躓,屢蹼屢起,具有特強的韌性。其間雖有晦暗之時,呈現出湯恩比(Arnold Toynbee)所謂的「僵化」(petrifaction)樣貌,但這是諸文化的常態,非中華文明所獨有的現象。其實對人類的文化而言,與其稱之謂「僵化」,莫若比之於「繭化」,僵化不再具有生機,繭化卻是生機的一種變相。任何文化對習於其中的族群都未免具有雙重的作用,一面維繫、保護族群的生存與發展,另一面也侷限了族群發展的趨向,正如繭之於蛹的關係。世界上的文化有的破繭而出,發揚光大,有的窒息而僵,失去了光輝,甚至斷絕了生機。中國文化也須經過破繭的過程,如果能夠破繭而出,自將會是另一種面貌。這是我對世界各文化發展細心觀察而後的心得。
文化乃人類活動所自然形成者,其間只有差異,沒有優劣,因此我們對文化的探索,切不可陷於個人的主觀情緒,只有以客觀的理性態度釐析其根源、追蹤其發展的脈絡,庶幾掌握此文化之真相。在我長久對中國古史的探索中,也像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鑽研人類學的思路一般,落在神話在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上。雖然我國古史所載多實際而少神話,但仔細讀來,就會發現在對實際的記載中,仍含蘊了不少神話。譬如遠古的虞舜一再為其父瞽叟及其弟象所害,而終不易其孝悌之心,實在顯示了為意識型態包裝而後的結果,正是周以後家族主義的反射。在崇尚宗法制度的家族中,父親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權威象徵,即使如瞽叟之愚之惡,亦不可奪其權勢;即使如舜之智之善,亦不可逾越身為人子的謙卑。又如周初的姜尚,一出現即以老人的姿態來扶佐周文王治國;文王逝後又扶佐武王伐紂,那時已是百餘歲的人瑞,尚能在戰場上衝鋒陷陣,豈非神話而何?這樣的原型一再出現在中國的史策中,不能不成為我們認識中國文化的重要線索。前者毋寧是人子盡孝的典範,後者則是主導數千年人際關係及社會地位的「老人文化」的原型。
我提出「老人文化」一詞,並無貶意,正如前言,任何文化只有異同,而無優劣。在農業生產及家族主義的社會中,掌權者定是父輩老人,其經驗和知識是靠天吃飯的農業生產所仰賴的可貴要件,老人享有權力與受到尊重是自然的事,同時也是必要的事,因而才會形成尚老的「宗法制度」。但是到了工業生產的社會,家族主義解體,老人權力漸失,其滯重難改的積習與對新事物反應的遲緩,反倒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是故老人文化與工業文明形成格格不入的現象,這正是老人文化從優勢轉為劣勢的根本原因。
在農業生產的周文化中所形成的儒家思想,正代表了周文化的核心價值,呈現出老人文化的樣貌,受到東方及中原地帶的族群擁戴。其他如邊陲的秦文化、楚文化,雖都曾鼎盛一時,甚且秦有實力統一了東方諸國,但均無能與周文化抗衡,而逐漸為周文化所吸收消於無形。異於周文化的墨家、道家等學派,自然也一一被排斥到邊緣地帶。黃老思想在漢初曾一度盛行,唯至漢武帝以政治的力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而也無能繼續與儒家抗衡,遂使儒家一枝獨秀,以其所弘揚的盡孝與尚老的宗法制度來規範國人的思想與行為,與農業的生產方式相輔相成,綿延數千年無多大改變,直到五四運動在巨大的西潮衝擊下,儒家的思想才受到嚴厲的檢核與批評。
一個人的生理及心理在成長的過程中,有些基本的性質無法為後天的環境與教育所改變,同理一個民族的靈魂在外來文化的激盪中,不管這外力多麼強烈,也難以徹底改變或消彌。這民族魂,用現代的詞彙來說就是榮格(Carl G. Jung)所謂的「集體無意識」。既是集體的,又是意識不到的領域,就非個人的意願所可左右。也正因為這個緣故,青年人與女性在中國傳統的老人文化的視野中始終處於劣勢,以致限制了活潑的年輕頭腦和族群一半的婦女對文化發展的貢獻,壓縮了文化的生機;沉澱在潛意識中的尚老、慕父的情結,窒礙了開出現代的科學精神與民主、自由的觀念。遠古的神話及其所形成的原型都深深地涵泳在國人無意識的黑暗海洋中,左右著我們的思想與行為。所以首先必須把無意識提升到意識的層面,才會有真正改弦易轍的希望。
第一章 文化的意涵
一、人類是否有創造文化的潛能?
今日來談一國的命脈與發展,有兩個問題立刻來到我們的思緒中:一國的人民,做為一個族群,能否任意地變革與發展?還是受到該國的歷史、文化所限,在變革與發展中會遵循一定的道路?
當然這樣的問題也可以擴大用來詢問人類整體的發展:人類的文化是否為人類進化中生理構造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還是人類先天就具有創造文化的潛能呢?前者意謂著有相當的局限,而後者則似乎敞開了自由發展或不同文化體系間交互影響與適應的可能。
這兩組問題是息息相關的。如果人類的文化是生理構造和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那麼一個族群的原有歷史、文化在其變革發展中,定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人類先天具有一種創製文化的潛能,那麼族群的發展便會更加自如。
人類的起源既然仍是謎一樣的課題,要企圖了解這一類的問題,一定得要先從一個族群具體而實有的文化上來探索才行。
二、文化釋義
我們對「文化」一詞的應用,今日與古代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別。譬如在《辭海》中就有兩種解釋: 一是我國古代的用法,舉《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就上下文義觀之,「文化」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名詞、一動詞。謂以文化之而不改,則以武加誅。又舉南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文化」在此是「文治教化」的意思。二是由西方傳來的意義,也就是相當於英、法文culture一字的含義,謂:「人類社會由野蠻而至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績,表現於各方面者,為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等,其綜合體,則謂之文化。」
我們今天談文化,大概都用的是第二種意義;第一種解釋反成古義,棄而不用了。由此亦可見我們有不少文義,已伴隨著文化的變革發生了變化。本文所欲探討的正是「文化」一詞的含義。
人類對文化之概念的掌握及對文化內涵的諦視與解析,應該說是相當近代的事。雖然不分中外,古代發展較早的學問,如哲學、史學、文字考據之學,都可以視作文化組成的部分,但是那時候並沒有掌握住文化的整體意涵,也沒有明確地把文化與社會的結構和人的行為綰連起來,做為一種探察研究的對象。文化之具有今日的涵義,應該是來自人類「進化」的概念,與「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混融的結果。文化意指人類在超脫野蠻狀態過程中的種種表現,統涵社會中可以承傳的一切。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在《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 1877)一書中和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都曾把人類的進化分作三級,即「原始」(savagery)、野蠻(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 (Margan 1877; Tylor 1871)。「文明」指的是具有豐富的文化時期。「文化」一詞意涵既廣,歧義自多,美國人類學家柯若貝(A. Kroeber)和柯魯孔(C. Kluckhohn)在〈文化──概念與定義評論〉(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文中,列舉了一百六十個對文化的定義,都脫不出文化是使人類的生活和價值超脫動物狀態的種種行為與事物這一個範圍。(Kroeber &Kluckhohn 1952)在地球上,除了人類以外,動物界都沒有人類所創製的文化現象,所以可以說文化是人類社會的特徵,也是唯有人類才具有的特徵。就人類共有的特徵而言,文化泛指一切在社會中獲得,可以繼續傳遞的行為模式和事物。人類的語言、工業、藝術、科學、律法、政治、道德、宗教等固然是文化,就是經由人類的智能所產生的物質,像是建築物、工具、機器以及藝術品等,也都屬於文化的範圍。
三、文化與族群
一接觸到一個族群的文化的具體內容,我們便馬上警惕到一個事實:雖然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共相,但文化的具體內容卻是因族群而異的。中國的文化不同於印度的文化,印度的文化不同於埃及的文化,埃及的文化不同於美洲印地安的文化等等。即使在同一個文化中,仍存在著次級的差別,例如以地區而論,中國中原的文化與邊疆地區的文化不同;以種族而分,漢族的文化與回族的有別,雖然他們可能在同一個地區,而且生息綿延了若干年代。由其相異者觀之,文化具有強韌的傳承性是不容否認的。若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移民是從一種文化遷移到另一種文化,譬如中國移美的華僑,數代後則異於本土的華人。這說明了文化也具有強烈的習染性。因此,一方面使我們了解到傳承性和習染性二者並非彼此排斥,另一方面也開啟了我們探索文化的穩定和變革的門戶。
十九世紀前半期,西方的工業國家,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日漸隆盛,實行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和殖民政策。也正因為這種政經軍事的原因,帶動了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與發展。初期的人類及社會學家,在西方的工業社會之外,所觀察到的其他種族文化,與西方的工業文明有很大的一段距離,難免因此產生西歐種族文化的優越感,「種族決定論」(racial determinism)一度甚囂塵上,認為不同的文化現象決定於種族,而種族則是有優劣之分的。(Gobineau 1853)十九世紀中葉,達爾文的「進化論」發表以後,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理論更助長了「種族決定論」的聲勢(Darwin 1958)。我們知道,德國的黑格爾(Friedrich Hegel)和法國的孔德(Auguste Comte)在當時西方的知識界影響甚大,二人都執有輕視非歐洲種族的態度。(Hegel 1956; Cornte 1954)德國文化史家柯來姆(Gustav Klemm)寫了一部長達十巨冊的《人種文化史》(Allgemeine Cultur-Geschicte derMenscheit, 1843),把人種分成「主動」(active)和「被動」(passive)兩種,蒙古人種(我們中國人在內)、黑人、埃及人、芬蘭人、印度人以及歐洲的下等階層都被派為「被動」一類,只有日耳曼族高踞「主動」一類之首。(Klemm 1852)雖然他追隨黑格爾的歷史階段說,認為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的族類,都會從野蠻狀態奔向文明與自由,但是在每一個階段的最高成就,卻只有主動的族類才可達成。法國的高比諾(Comte J. A. de Gobineau)的極端「種族決定論」更直接影響到後來納粹對猶太人的仇恨與屠殺。
在這樣的氣氛中,英國的社會思想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進化論」,自然也把西方的工業社會擺在人類進化的尖端,其他的社會都注定了步向同一路程(「進化」和「適者生存」等字眼都是斯賓塞在達爾文以前就已使用的),不可避免地也把種族的因素攙入社會進化之中。(Spencer 1896)然而他以違反自然進化原則的口實,非常厭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毋寧預言了今日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其實他與馬克思的觀念互通之處甚多,二人都主張社會的進步是經鬥爭而來,前者主張通過自然經濟的淘汰(自由經濟的先驅),後者則主張必須通過階級鬥爭。馬克思雖然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但也同樣具有種族的成見,「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就帶有十分輕蔑的意味。(Marx 1967)這種種的學說使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社會思想籠罩在帝國主義與種族歧視的迷霧中。
但重要的一點,是「進化」這一觀念由此確立,開啟了現代人對自我的認知,使以後的社會科學家都不能規避或否認人類的文化是日新月異進化不已的。
四、進化與擴散
原則雖然建立,解說仍然分歧。在自然競爭和社會鬥爭中進化以外,「擴散」(diffusion)也被認為是文化發展的一個決定因素。極端的「擴散論」(diffusionism)者甚至倡言所有人類的文明,都是在六千年前源自同一個古代的文化中心──埃及。與「進化論」者最大的區別,則是「擴散論」者認為文化不但可以進化,也可以退化。今日所見的一些原始部落,不一定必然是從更原始的狀態進化而來,也可以是從比較高度的文明退化到原始狀態,例如十九世紀的美洲印地安文化,顯然不及早期的瑪雅(Maya)或印卡(Inca)文化昌明。這種觀念,德國的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的著名的巨構《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West)一書中發揮的淋漓盡致,在他眼目中,中國的文化從戰國以後,已經步上沒落的命運。(Spengler 1922)退化沒落以後,繼之以死亡,一個文化死去了,在地球上又有另一個文明代之而興。這種觀點的實證在人類歷史的演化中屢見不鮮。
那麼人類的文化在生死的鬥爭下,或在交互的影響下,是像斯賓塞所說沿著一條單一的路線進化(unilinean evolution)?還是像後來的人類學家所倡議的「多線進化」(multilinear evolution) ?雖然站在維護各民族固有文化的立場,我們期望人類文化發展應具有多元的面目,但以今日新興的發展國家無不奔向工業化和歐美式的政經結構的情勢而言,則使我們不能不抱有「單線進化」的隱憂。當然,假想伊斯蘭教徒有一日改信基督,或基督教徒歸入伊斯蘭的崇信,未免不切實際。因此,是否單線進化的問題,在今天是無法結論的案例。
我們中國文化在二十世紀,正面臨到何去何從的挑戰。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但我們的文化根柢到底何在?如何保有或是否應該保有我們的文化之根?在走向西方式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我們的局限何在?是否應該毫無保留地擁抱西方的文明?這恐怕都是今日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
如果我們尚無法解答這類的問題,至少我們應該嘗試研討、描繪出中華文化的根基所在,正像一般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學者所努力的一樣。
第一章 文化的意涵
一、人類是否有創造文化的潛能?
今日來談一國的命脈與發展,有兩個問題立刻來到我們的思緒中:一國的人民,做為一個族群,能否任意地變革與發展?還是受到該國的歷史、文化所限,在變革與發展中會遵循一定的道路?
當然這樣的問題也可以擴大用來詢問人類整體的發展:人類的文化是否為人類進化中生理構造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還是人類先天就具有創造文化的潛能呢?前者意謂著有相當的局限,而後者則似乎敞開了自由發展或不同文化體系間交互影響與適應的可能。
這兩組問題是息息相關的。如果人類的文化是生理構造和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那麼一個族群的原有歷史、文化在其變革發展中,定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人類先天具有一種創製文化的潛能,那麼族群的發展便會更加自如。
人類的起源既然仍是謎一樣的課題,要企圖了解這一類的問題,一定得要先從一個族群具體而實有的文化上來探索才行。
二、文化釋義
我們對「文化」一詞的應用,今日與古代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別。譬如在《辭海》中就有兩種解釋: 一是我國古代的用法,舉《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就上下文義觀之,「文化」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名詞、一動詞。謂以文化之而不改,則以武加誅。又舉南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文化」在此是「文治教化」的意思。二是由西方傳來的意義,也就是相當於英、法文culture一字的含義,謂:「人類社會由野蠻而至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績,表現於各方面者,為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等,其綜合體,則謂之文化。」
我們今天談文化,大概都用的是第二種意義;第一種解釋反成古義,棄而不用了。由此亦可見我們有不少文義,已伴隨著文化的變革發生了變化。本文所欲探討的正是「文化」一詞的含義。
人類對文化之概念的掌握及對文化內涵的諦視與解析,應該說是相當近代的事。雖然不分中外,古代發展較早的學問,如哲學、史學、文字考據之學,都可以視作文化組成的部分,但是那時候並沒有掌握住文化的整體意涵,也沒有明確地把文化與社會的結構和人的行為綰連起來,做為一種探察研究的對象。文化之具有今日的涵義,應該是來自人類「進化」的概念,與「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混融的結果。文化意指人類在超脫野蠻狀態過程中的種種表現,統涵社會中可以承傳的一切。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在《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 1877)一書中和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都曾把人類的進化分作三級,即「原始」(savagery)、野蠻(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 (Margan 1877; Tylor 1871)。「文明」指的是具有豐富的文化時期。「文化」一詞意涵既廣,歧義自多,美國人類學家柯若貝(A. Kroeber)和柯魯孔(C. Kluckhohn)在〈文化──概念與定義評論〉(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文中,列舉了一百六十個對文化的定義,都脫不出文化是使人類的生活和價值超脫動物狀態的種種行為與事物這一個範圍。(Kroeber &Kluckhohn 1952)在地球上,除了人類以外,動物界都沒有人類所創製的文化現象,所以可以說文化是人類社會的特徵,也是唯有人類才具有的特徵。就人類共有的特徵而言,文化泛指一切在社會中獲得,可以繼續傳遞的行為模式和事物。人類的語言、工業、藝術、科學、律法、政治、道德、宗教等固然是文化,就是經由人類的智能所產生的物質,像是建築物、工具、機器以及藝術品等,也都屬於文化的範圍。
三、文化與族群
一接觸到一個族群的文化的具體內容,我們便馬上警惕到一個事實:雖然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共相,但文化的具體內容卻是因族群而異的。中國的文化不同於印度的文化,印度的文化不同於埃及的文化,埃及的文化不同於美洲印地安的文化等等。即使在同一個文化中,仍存在著次級的差別,例如以地區而論,中國中原的文化與邊疆地區的文化不同;以種族而分,漢族的文化與回族的有別,雖然他們可能在同一個地區,而且生息綿延了若干年代。由其相異者觀之,文化具有強韌的傳承性是不容否認的。若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移民是從一種文化遷移到另一種文化,譬如中國移美的華僑,數代後則異於本土的華人。這說明了文化也具有強烈的習染性。因此,一方面使我們了解到傳承性和習染性二者並非彼此排斥,另一方面也開啟了我們探索文化的穩定和變革的門戶。
十九世紀前半期,西方的工業國家,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日漸隆盛,實行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和殖民政策。也正因為這種政經軍事的原因,帶動了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與發展。初期的人類及社會學家,在西方的工業社會之外,所觀察到的其他種族文化,與西方的工業文明有很大的一段距離,難免因此產生西歐種族文化的優越感,「種族決定論」(racial determinism)一度甚囂塵上,認為不同的文化現象決定於種族,而種族則是有優劣之分的。(Gobineau 1853)十九世紀中葉,達爾文的「進化論」發表以後,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理論更助長了「種族決定論」的聲勢(Darwin 1958)。我們知道,德國的黑格爾(Friedrich Hegel)和法國的孔德(Auguste Comte)在當時西方的知識界影響甚大,二人都執有輕視非歐洲種族的態度。(Hegel 1956; Cornte 1954)德國文化史家柯來姆(Gustav Klemm)寫了一部長達十巨冊的《人種文化史》(Allgemeine Cultur-Geschicte derMenscheit, 1843),把人種分成「主動」(active)和「被動」(passive)兩種,蒙古人種(我們中國人在內)、黑人、埃及人、芬蘭人、印度人以及歐洲的下等階層都被派為「被動」一類,只有日耳曼族高踞「主動」一類之首。(Klemm 1852)雖然他追隨黑格爾的歷史階段說,認為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的族類,都會從野蠻狀態奔向文明與自由,但是在每一個階段的最高成就,卻只有主動的族類才可達成。法國的高比諾(Comte J. A. de Gobineau)的極端「種族決定論」更直接影響到後來納粹對猶太人的仇恨與屠殺。
在這樣的氣氛中,英國的社會思想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進化論」,自然也把西方的工業社會擺在人類進化的尖端,其他的社會都注定了步向同一路程(「進化」和「適者生存」等字眼都是斯賓塞在達爾文以前就已使用的),不可避免地也把種族的因素攙入社會進化之中。(Spencer 1896)然而他以違反自然進化原則的口實,非常厭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毋寧預言了今日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其實他與馬克思的觀念互通之處甚多,二人都主張社會的進步是經鬥爭而來,前者主張通過自然經濟的淘汰(自由經濟的先驅),後者則主張必須通過階級鬥爭。馬克思雖然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但也同樣具有種族的成見,「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就帶有十分輕蔑的意味。(Marx 1967)這種種的學說使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社會思想籠罩在帝國主義與種族歧視的迷霧中。
但重要的一點,是「進化」這一觀念由此確立,開啟了現代人對自我的認知,使以後的社會科學家都不能規避或否認人類的文化是日新月異進化不已的。
四、進化與擴散
原則雖然建立,解說仍然分歧。在自然競爭和社會鬥爭中進化以外,「擴散」(diffusion)也被認為是文化發展的一個決定因素。極端的「擴散論」(diffusionism)者甚至倡言所有人類的文明,都是在六千年前源自同一個古代的文化中心──埃及。與「進化論」者最大的區別,則是「擴散論」者認為文化不但可以進化,也可以退化。今日所見的一些原始部落,不一定必然是從更原始的狀態進化而來,也可以是從比較高度的文明退化到原始狀態,例如十九世紀的美洲印地安文化,顯然不及早期的瑪雅(Maya)或印卡(Inca)文化昌明。這種觀念,德國的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的著名的巨構《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West)一書中發揮的淋漓盡致,在他眼目中,中國的文化從戰國以後,已經步上沒落的命運。(Spengler 1922)退化沒落以後,繼之以死亡,一個文化死去了,在地球上又有另一個文明代之而興。這種觀點的實證在人類歷史的演化中屢見不鮮。
那麼人類的文化在生死的鬥爭下,或在交互的影響下,是像斯賓塞所說沿著一條單一的路線進化(unilinean evolution)?還是像後來的人類學家所倡議的「多線進化」(multilinear evolution) ?雖然站在維護各民族固有文化的立場,我們期望人類文化發展應具有多元的面目,但以今日新興的發展國家無不奔向工業化和歐美式的政經結構的情勢而言,則使我們不能不抱有「單線進化」的隱憂。當然,假想伊斯蘭教徒有一日改信基督,或基督教徒歸入伊斯蘭的崇信,未免不切實際。因此,是否單線進化的問題,在今天是無法結論的案例。
我們中國文化在二十世紀,正面臨到何去何從的挑戰。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但我們的文化根柢到底何在?如何保有或是否應該保有我們的文化之根?在走向西方式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我們的局限何在?是否應該毫無保留地擁抱西方的文明?這恐怕都是今日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
如果我們尚無法解答這類的問題,至少我們應該嘗試研討、描繪出中華文化的根基所在,正像一般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學者所努力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