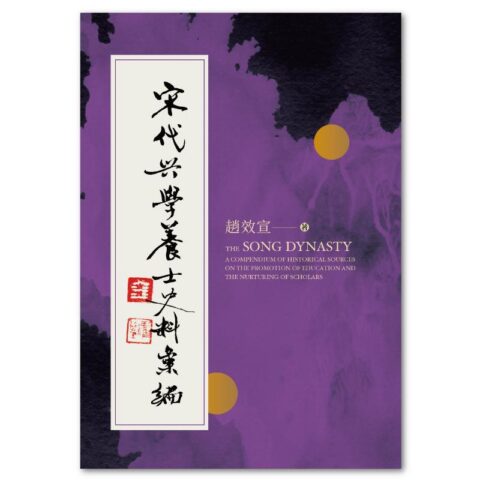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出版日期:2015-06-03
作者:林冠群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12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5716
系列:聯經學術
已售完
關於唐代時期,吐蕃宰相制度的重要研究鉅著!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在於君相之間的委託關係
贊普為吐蕃國家主權的象徵,實際不管事,而將統治權委託給宰相(大論)
宰相因之擁有浩大的權勢,對於國事幾乎無所不統
倘若贊普終止委託關係,則宰相掌握再大的權勢,亦將不戰而潰
吐蕃相制歷經獨相而眾相,由眾相而僧相,由僧相回復至眾相
均隨著客觀情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上述不但具體反映各時期的君臣關係,同時也反映王室與眾家貴族的關係
吐蕃相制近於農業社會體制,與游牧社會有較明顯的差異
更可從吐蕃相制窺探出其與中原文化的淵源。
林冠群最新論著《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指出了吐蕃王朝的大小事務均由宰相一人總其責,後因贊普幼年即位,導致獨相掌握政柄。吐蕃便將獨相,改為多人同時擔任宰相的眾相制。眾相制實施後,贊普王室所信仰的佛教得以立為國教,全面推廣。這種情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佛教的政治地位跟著水漲船高。佛教僧侶也就躋登廟堂之列,位極人臣,形成以僧人擔任宰相的僧相體制。上述相制演變,對吐蕃及其後代影響深遠。西方藏學界在此一領域上,少有鞭辟入裡的論著。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包括緒論與結論,共計六章,都二十六萬言。第一章緒論:深入討論唐代吐蕃政權的屬性與政治文化,以及吐蕃的國家型態。此為歷來學界所說不清楚之處,但卻是瞭解吐蕃的核心。第二章:探討吐蕃宰相制度的由來,從吐蕃地方性的部落組織、吐蕃王朝以前部落與部落聯盟的架構、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的雛型與官員的設置以及吐蕃王朝的建立與宰相制的確立等,瞭解吐蕃體制事實上屬承繼性的發展。第三章:討論吐蕃宰相的官稱與職權、blon che 官銜釋義、blon che之職權以及blon che之任免等,藉此理解吐蕃宰相制度的基本架構。第四章:探索吐蕃由獨相制演進至眾相制的情況、吐蕃眾相制的由來,復以〈吐蕃大事紀年〉所載,試圖具體呈現的吐蕃眾相制,並對吐蕃眾相的銜稱與運作、眾相制對吐蕃政壇生態的影響、世人對吐蕃眾相制的誤解等,作深入且理性的討論。第五章:從吐蕃僧相體制實施的時代背景著手,探討墀德松贊贊普為何會開啓僧相體制,進而討論吐蕃僧相的官銜與職權、僧相體制對吐蕃王朝的衝擊等。第六章結論:總結本文的4章,歸納出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吐蕃宰相制度的意義,以及吐蕃宰相制度對後世的影響,並據以說明吐蕃宰相制度與中原文化之關係。
本書對於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不但修正正史及藏文史料記載的錯誤,提出學界前所未論及者,並從中窺探漢藏在文化上的關連性,貢獻一家之言。
作者:林冠群
1954年出生於台北市。祖籍福建林森。政大東語系土耳其文組學士、政大邊政所碩士、文大史學所博士,美國印地安那大學阿爾泰學系訪問學者。歷任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代理院長。現任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專攻唐代吐蕃史、藏族史、中國民族史、隋唐史。著作有《吐蕃贊普墀松德贊研究》、《唐代吐蕃史論集》、《唐代吐蕃歷史與文化論集》、《唐代吐蕃史研究》以及70餘篇學術論文。曾榮獲教育部第56屆學術獎;大陸第1屆、第3屆漢文專著珠峰獎。
藏文字母與羅馬拚音對音表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
第二節:唐代吐蕃政權的屬性與政治文化
第三節:吐蕃國家型態
第二章 吐蕃宰相制度的由來
第一節:吐蕃地方性的部落組織
第二節:吐蕃王朝成立以前部落與部落聯盟的架構
第三節: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的雛型與官員的設置
第四節:吐蕃王朝的建立與宰相制的確立
第三章 吐蕃宰相的官稱與職權
第一節:blon che 官銜釋義
第二節:blon che之職權
第三節:blon che之任免
第四章 吐蕃宰相制度的演進
第一節:由獨相制演進至眾相制
第二節:吐蕃眾相制的由來
第三節:〈吐蕃大事紀年〉所呈現的吐蕃眾相制
第四節:吐蕃眾相的銜稱與運作
第五節:眾相制對吐蕃政壇生態的影響
第六節:世人對吐蕃眾相制的誤解
第五章 吐蕃僧相體制的實施
第一節:吐蕃僧相體制實施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墀德松贊贊普開啓僧相體制
第三節:吐蕃僧相的官銜與職權
第四節:僧相體制對吐蕃王朝的衝擊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
第二節:吐蕃宰相制度的意義
第三節:吐蕃宰相制度對後世的影響
第四節:吐蕃宰相制度與中原文化之關係
附錄
徵引書目
索引
表圖目次
表1:吐蕃地方勢力一覽表
表2:P.T.1286〈十七小王及家臣表〉
表3:西元705年以前之吐蕃大論世系表
表4:吐蕃歷年眾相任職表
表5:西元701年以後吐蕃大論與眾相名諱一覽表
表6:西元705年以後之吐蕃大論世系表
表7:西元755至763年吐蕃眾相任職表
表8:西元755年至763年吐蕃眾相名諱表
自序
自民國48年,十四輩達賴喇嘛出亡印度達蘭沙拉以後,西藏逐漸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究竟在歷史上,西藏與中原政權的關係為何?西藏究竟是獨立自主,抑或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各方爭論不休。因此西藏歷史的型塑,成為各方為尋求各自立場的有力論證而角力。吾人可依治藏史立場與觀察角度的不同,區分有四,其一,視西藏自古以來即屬獨立自主的國家,具獨特歷史文化,與中國毫無關涉的海外藏人;其二,普遍對達賴有好感,同情並美化西藏,以執學術牛耳的姿態治藏族史的西方學界;其三,稱西藏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馬列主義史觀為綱治藏族史的中國大陸學界;其四,持西藏屬中國之特別行政區,並以中華文化道統立場治藏族史的台灣學者。上述四類又可大致歸納成兩大陣營:海外藏人與西方學界;以及海峽兩岸的學者專家。兩大陣營觀點的最大差異,在於歷史長河中,西藏與歷代中原政權的互動內涵與模式,各持己見,並透過學術會議、期刊雜誌與論著,互相批駁、詰難與撻伐。
如是發展,形成海外藏人與西方學界對於海峽兩岸的藏學研究,不論有心或下意識排斥,抑或有意無意地忽視,在彼等論著之中,甚少或根本不使用海峽兩岸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成因在於彼等以為中文的論著,充滿了「民族偏見」。彼等甚至以為古代的漢史料,也是屬於自讚毁他,天朝觀念作祟下,誇大不實的載記,不值一哂。此種情況使得大陸藏學學者沈衛榮教授,發出不平之鳴以為:「曾經是侵略殖民者的西方人,脫胎換骨成了西藏文化的大救星。而千餘年來和藏族百姓緊鄰相伴,文脈相通的漢人,卻無厘頭地成了摧殘藏族文化的災星。真是豈有此理!」(氏著:《尋找香格里拉》頁203)
這種詭異情況的變化,其中很大的因素,是由於國人把中原漢族以外的歷史都拋棄掉了。以唐代吐蕃史為例,是為國史之中,國人最陌生的一段歷史。治中國中古史者避之唯恐不及,此造因於語言文化的隔閡,所以弄不清楚來龍去脈,容易犯錯,徒留話柄。是以不是點到為止,就是引用國外學者的論著,一來亦可彰顯自己治學廣博,能夠引用國外學者的論著,使自己的論著增加權威性;而讀者也因之認為作者既引用了國外論著,則此論著應具可讀性,繼而對其增進了信賴感。職是之故,國內縱然有出色的中國邊疆史論著,也遭受到冷漠的對待,甚至棄之如敝屣,既不提及,更不用說援引了。這真是令人慨嘆的現象。
但事實上,也不能完全嗔怪國內學界的大小眼。因為在中國邊疆史的研究領域,國內確實要落後國外甚多。其中原因為國史學界偏重於長城以內的歷史,至於長城以外的歷史,則歸之於「虜學」,屬「域外史」,甚少正視。有志於治「虜學」的學子,唯一的途徑,就是到國外求學,受教於國外名師。學成後歸國,卻覓不到一處容身,因為國內學界甚少將「虜學」作為研究重點,頂多就是應應卯,點綴點綴。在如此情況下,要國內虜學研究趕上國外水平,不啻天方夜譚。
然而,一部中國史,沒有了「虜學」,就好像失去了半壁江山,也好似泛黑著半邊臉的美人。因為一部中國史原本就是由華夷交參混融所成,缺一不可。例如唐朝為平唐境內之安史叛眾,引進迴紇援軍,唐迴雙方議定酬勞為收復長安、洛陽後,迴紇可獲二都地面上的所有財物。事成,迴紇欲履約引兵入長安,李唐王儲廣平王為避免因長安遭洗刼而激起洛陽的頑抗,遂不顧李唐太子身份,親拜於迴紇王儲葉護馬前,不但阻止了可預見的悲劇,也為自己博得了「廣平王真華、夷主也」之美譽。此段史事意味著必須涵括華、夷,否則無法整體呈現古代中國之「天下」,更無法展現完整的中國史。不幸的是,東漢班固撰寫了《漢書.匈奴列傳》,內中借用出使匈奴之漢使者所云,諸如「匈奴俗賤老」、「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等語,批判匈奴之文化,並結論以為:「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上述見解影響所及,往後華夏族群均持「夷狄禽獸也」之概念,鄙視與華夏殊異的人群,直至20世紀初葉,凡非華夏族群之族稱用字,一律加上「犭」、「豸」、「虫」等偏旁,例如青海果洛族原用字為「猓狢」,抑或選用污名化的詞彙,如雲南傣族原用字為「歹族」等,由此道盡中原華夏族群的心態。連帶地,也波及了研究中國邊疆史的學者,一併遭到排斥、鄙視,而予以邊緣化。
究竟上述所提及之匈奴婚俗「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所謂的「烝報婚」,真是如漢人所以為有如禽獸般的亂倫?非也!其實施如此婚制的原因在於:游牧民族的生活資源來自於所豢養的牲口,為避免牲口近親繁殖,以致降低了牲口品質,影響毛、奶、肉及小仔的產量與品質,因此在實施族外婚之同時,利用由外部落娶來的婦女所攜帶而來之嫁粧,包括屬於婦女所擁有的牲口,用來與本部落的牲口配種,從而有新血緣的加入,避免了近親繁殖。但當家族中有成家的男性亡故,其配偶勢必因改嫁而帶走她所擁有的牲口,造成家族財產的損失,與生存上的危機。因此其亡故男性的兄弟子侄之一,必須負起責任,接納亡故男性之配偶,以避免牲口流失而危及家族集體的利益與生存的安全。對於彼等而言,這是應盡的義務,也是維護整體家族持續發展的美德;但對於持儒家道德標準的華夏族群而言,卻目之為亂倫,有如「禽獸」,繼而口誅筆伐,歷代相承而形成視夷狄為下等人的傳統。是故,研究「漢學」屬高級學術工作,研究「虜學」,也就是研究夷狄之學,被貶為「偏之又偏」的末流之學。國人因之棄如雞肋,任其腐敗。結果,國外將雞肋視如珍饈,深挖窮治,滋味無窮。接著以所謂「突厥學」、「藏學」、「蒙學」、「滿學」等挑戰「漢學」,沛然大勢,衝擊了許多中國史的成說。「虜學」成了外國人的專利,長城以外的歷史,他們說的算。
曾幾何時,西方的船堅礮利,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也帶來了如下的說法:中國是漢族的中國,說蒙古人、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是中國人是很虛偽奇怪的事,認為凡與漢人異質的民族都不屬於中國,是中國征服來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加殖民主義者。面對如此洶洶情勢,海峽两岸學界匆促應戰,左支右絀。因為所有涉及長城以外歷史的發言權,早已落入外國人的手裡。
筆者有鑑於上述情勢的發展,以為國內不能再如埋首沙中的鴕鳥,任由外國人對歷代中原政權與週邊諸族關係的歷史,以及所謂的「虜學」,說三道四,任意以其成見肆虐。吾人應秉執歷史事實,以吾國之治學方法與觀點,推出具學術水平,而又能平心而論的論著,爭取發言權。
筆者不才,曾於民國100年8月出版《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獲得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張廣達院士的推薦,角逐教育部第56屆學術獎。治西域史成名之張廣達院士推薦以為:
林冠群教授數十年來如一日,鍥而不捨,精耕細作,全面、深入研究吐蕃史。天道酬勤,今天,林教授在數十年間完成了數十篇專題論文的基礎上,集腋成裘, 刊出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部煌煌巨著。近二十年來,國際學術界對吐蕃史的研究明顯不如先前活躍,有如佐藤長、山口瑞鳳、Ch. Beckwith等人那樣的較高水平的吐蕃史著作已較少問世。我們慶賀林冠群教授的《唐代吐蕃史研究》在此時此刻的出版,它的出版改變了吐蕃史學界一時間的蕭條面貌。
林教授的《唐代吐蕃史研究》這部大作是研究吐蕃史的重大貢獻。作者多年堅守這一領域,一點一滴地積累,一步一個脚印地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繼續前進,發前人之未發,糾前人的紕漏。作者深入探討吐蕃氏族制以來的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吐蕃与周邊族群互動史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闡發吐蕃人物生平及其歷史地位和作用。對於大事紀年、史實考核、漢藏文史料的比較,辨析精到,凸顯作者作爲一位歷史學家的審慎和細緻。書中對唐蕃關係的考據、對吐蕃制度的考述和對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毀佛事實的撥亂反正等,均有見地和新意。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對相關漢藏文文獻資料的利用和準確理解,使之不再是日本學者専擅的特權,糾正了山口瑞鳳等權威人物理解和詮釋漢藏文文獻的諸多誤差,顯示出作者扎實的學術功力和嚴肅的學術批判精神。
總之,無論是就學術發展史而言,還是就本書的學術高質量而言,《唐代吐蕃史研究》都極具價值,特此極力推薦。
上述張廣達院士的推薦與筆者的研究成果,獲得教育部第56屆學術獎遴選評審委員會的肯定,並做出以下的評論:
藏學研究在國內一向被視為冷門學術,海外則以大陸、日本為主。在學術研究領域,藏學較其他學門難度更高,除語文之外,尚需熟諳西藏宗教及社會文化歷史,同時也要有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素養;研究資料,除傳統文獻外,尚需精熟敦煌出土文書,尤其藏文資料,所以需要有長期浸潤,始克其功。林冠群教授,向海內外學者專家多方拜師,駕馭語文障礙,而精通土耳其文、藏文、維吾爾文等,經數十年苦研吐蕃史,而今有關藏學著作豐碩,深受國際學界肯定,在國內實是藏學代表之不二人選,不再使外人專美於前。
綜觀林教授之學術成就,主要呈現在釐清諸多文獻誤植史實,理性與批判國際學者的學說,進而建構吐蕃史研究的根本且完整的知識基礎,深化省視唐代中國史的視野。尤其是對吐蕃的崛起過程、吐蕃贊普位之繼承,吐蕃王國體制的特質、唐蕃關係等方面,均有深入且有批判性的討論。如證明藏族家喻戶曉「朗達瑪大滅佛法」的史事係偽史,而能發千古未發之覆,為藏史千古疑案作了澄清。再如過去一般都認為墀祖德贊為吐蕃三大明君之一,實則為加速吐蕃王朝衰微崩解的昏君,藏族史家因崇佞佛教而予以曲筆,林教授的研究還原了墀祖德贊贊普的歷史原貌。又如漢藏史籍缺載藏族史上唯一女性執政者墀瑪蕾,林教授就敦煌文獻作了史料的補闕;另外亦對新舊《唐書‧吐蕃傳》錯誤記載「女子無敢干政」一節,作了修正。凡此研究成果,都是東西方學界少有觸及者。
筆者在張廣達院士與教育部學審會之肯定的激勵下,奮起餘勇,秉持大陸學界對筆者的評論以為:「偏重實證的研究理路」作風,踵繼多年來累積的研究成果,再次獲得國科會專書撰寫計劃的補助,繼續完成《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一書。此書係《唐代吐蕃史研究》在吐蕃政治體制中的宰相制度方面,再加以深入闡發。由於《唐代吐蕃史研究》屬通史性質,限於篇幅,有關唐代吐蕃的許多領域範疇僅能淺嚐,無法暢所欲言,特別是攸關最能呈現吐蕃制度面的特色、最具變化、以及最能反映唐蕃文化交流成果的宰相制度,筆者以為仍需就相關史料與史實,詳為發掘闡述,遂有本書的問世。
筆者以為西方學者強項在於能夠大量使用藏文文獻,不受藏語文的限制與障礙。但其缺點在於忽略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彼等僅能使用經過翻譯成英文的新舊《唐書.吐蕃傳》、資治通鑑等常見的漢史料,除此外,再無法深入或普遍發掘其他文獻如:《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全唐文》以及唐人筆記小說等,甚或除〈吐蕃傳〉以外的新舊《唐書》本紀、列傳等,也一併在其忽視之列。除非兼治漢學的西方學者如法國石泰安氏(R.A.Stein)、戴密微氏(P. Demiville)等,則能兼採漢藏史籍,作出公允持重的論斷,令人感佩。其餘大部份西方學者忽略了漢文史籍的重要性,因為唐蕃互動頻繁,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漢文史籍記載有大量吐蕃訊息。在唐代吐蕃傳世史料闕佚,文獻難徵之際,漢文史料益發突顯其重要性。當然,吐蕃文獻無可諱言地仍居關鍵地位。是以,作為唐代吐蕃史的研究者,對各種史料文獻應採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偏聽,不偏信,就學術論學術。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前言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與吐蕃政教情勢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早期,在贊普都松芒保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 676-704)族滅論欽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大論一族(西元699年)以前,吐蕃實施的是獨相制。即由一人單獨擔任大論(Blon chen po, Blon che),由其實際負責吐蕃政府的運作,大小事務均由其一人總其責。適巧,吐蕃在贊普松贊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649) 於西元649年去世,由其孫芒倫芒贊(Mang slon mang btsan 650-676在位)年幼繼位以後,由大論祿東贊輔政,從此產生了獨相掌握政柄的現象。吐蕃王室為扭轉類此「太阿倒持」的惡局,於是在相制上作了變革,把原由一人單獨任大論的辦法,改變為任命多人同時擔任宰相,組成宰相會議。除保留一人仍任原有的大論(Blon chen po),仍享原有獨相的名位,擔任眾相之首以外,其餘的宰相,賦與「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字義:政事大臣,漢譯:宰相同平章事)或「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字義:政事大臣參議大詔命)的頭銜,躋登眾相之列,以分散相權。於是,吐蕃的決策中心,原由一人掌控的首長制,轉變為多人參與決策的委員制。眾相的任免權,掌握在贊普手中,因此等於贊普控制宰相會議,於是主導政局的大權,回歸於贊普。吐蕃具體實施眾相制的時間,史未明言,然確於贊普墀德祖贊之祖母墀瑪蕾(Khri ma lod?-712)攝政時期所推動。自此以後,眾相制成為吐蕃的定制。
眾相制實施以後,贊普王室的信仰--佛教,不但得以立為國教,且全面推廣。此正意味著吐蕃王室在權力鬥爭上的全面獲勝,贊普能夠充份掌握政權,意志得以暢通無阻。這種情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佛教的政治地位跟著水漲船高。佛教僧侶也就堂而皇之,躋登廟堂之列,甚至位極人臣,形成了吐蕃以僧人充當宰相的僧相體制。
上述吐蕃王朝宰相制度的設計與演進,已屬眾所週知之常識。然而,由獨相演進至眾相,復由眾相轉為僧相主導政局等相關詳情細節,仍有許多疑義與誤解亟待釐清,試舉中外學界之例詳述如下:
西元1991年由白鋼氏所主編之《中國政治制度史》一書,對中國歷朝歷代包括中國周邊族群的政治制度,作鳥瞰式的整理與詮釋,具一般性質的參考作用,為普羅大眾提供初步且概論性質的介紹。該書頗能代表中國大陸學界對歷代及周邊族群政治制度的認知。經查閱該書對唐代吐蕃有關宰相制度的論述如下:
贊普之下,設大相一人,藏語稱「論茝」,又稱「大論」,唐人譯為宰相平章國事;副相一人,藏語稱「論茝扈莽」,又稱「小論」,但副相一職不常設,大相與副相是總管王朝政治事務的大臣,地位最高,權勢極重…由上述贊普以下四部份官員(大相、都護、內大相、整事大相)組成的政治機構,藏語叫做「尚論掣逋突瞿」,意為由王室和貴族掌握著吐蕃王朝的全部政權。
依上引文所載,吾人即知該書之編寫者,雖然並未註明引用資料出處,但仍可確知其引用了《新唐書.吐蕃傳》的材料,以及當時所能蒐到的專文。上引文所顯現對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的認知,很能代表大陸學界對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所得。吾人復舉由專研藏學的陳慶英與高淑芬二氏所主編之《西藏通史》為例,其所載唐代吐蕃宰相制度如下:
中央官員可以劃分為三個系統:(一)貢論系統:即大相論茝(大論),論茝扈莽(小論),悉編掣逋等三人。論茝,即藏文blon che的音譯。初設一人,後則增至數人,以防止專權。論茝扈莽,係藏文blon che vog dpon的音譯,副相或小論。悉編掣逋,即spyan chen po的音譯,一作都護。他們三人受命處理軍國大事,負責軍事征討。…貢論、曩論和喻寒波三大系統中的大、中、小三位首領官,合稱九大尚論,即尚論掣逋突瞿,藏文作zhang blon chen po dgu。
以上引文較諸《中國政治制度史》一書所載之唐代吐蕃宰相制度,除增加幾個專有名詞的藏文原文,以及對由獨相演進至眾相有數語描述外,餘大部雷同。吾人另舉大陸專研唐代吐蕃史的陳楠氏大作為例:於1998年出版之〈吐蕃大相尚結贊考敘-兼論吐蕃宰相制度的變遷〉一文中以為:吐蕃王朝於二百年之間,輔政大臣制度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一,自650至698年為一人擔任大相的制度,使得輔政大臣權力過度集中,形成大相專權局面;其二,自701至798年期間,為免大相權力過度集中,增加大論人數,汲取唐朝典章制度,任命「大尚論掣逋突瞿」即宰相同平章事達9人,但同時又有首席宰相制度,位列首席者,一般都必出身於「尚族」,又稱作「舅臣」,身份地位類同於先前的大相;其三,從798至838年間,開始任用僧人掌政,鉢闡布則為「僧相」 的代名詞,地位高於外族(戚?)和王族諸權貴,由於連續百十年的尚族輪流輔政,形成豪族專權的局面既削弱了王室權力又造成社會矛盾,貴族間爭權奪勢的權力之爭愈演愈烈,為調解各種矛盾,遂起用大僧人為輔政大臣。陳楠氏另於1988年出版之〈吐蕃職官制度考論〉中以為:貢論(dgung blon)為輔佐贊普治理國家的高級執政官,負責議政、判事、主兵等軍國大事;貢論系統包括大相(論茝)、副相(論茝扈莽)、都護(悉編掣逋)各1人,後又增至9人,是以貢論員額有一個從少到多的變化過程。根據〈唐蕃會盟碑〉屬於宰相一級的官員有鉢闡布、兵馬都元帥、兵馬副元帥、貢論掣逋及社稷大臣。宰相職掌與大相差不多,諸如協助贊普制定法令政策,主持盟會,經略地方,出使外邦等。只不過是權力相對分散,各人有所側重罷了。另有一區別是,宰相已逐漸成為文職官員,另設專門統帶軍隊的官吏,以免宰相擁兵自重難以控制。吾人由上述大陸學界概論性質至專論的論著觀之,雖歷經十餘年,在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研究上,可議處不只一端。
在西方藏學界方面,有1990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劍橋早期內陸亞細亞史》一書,其中由霍夫曼氏(Helmut Hoffman)所撰寫之〈早期與中古吐蕃〉(Early and medieval Tibet)一文,文中簡略地介紹了唐代吐蕃的政府,其以為:在贊普之下有附屬小王,諸如吐谷渾之達延(Dar rgyal)、工布、娘布等,此三者地位高於宰相,繼其後為最顯赫的貴族所出任的大論(Great Minister)或衆相(Great Ministers),繼之為內臣(nang blon)及外臣(phyi blon),而內外臣之銜稱係由其於朝中所站的位置而來。上述霍夫曼氏所云者,顯然採用《賢者喜宴》所記載的材料,並受義大利著名藏學家杜奇氏﹝G.Tucci)的影響,而且敘述過於簡略。其間歷十餘年後,於2009年出版了2本有關唐代吐蕃的專著,分別為英國的道特森氏(Brandon B. Dotson)所著之《吐蕃大事紀年──西藏第一部史籍的譯註》(The Old Tibetan Annal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History),以及美國華爾特氏(Micheal L. Walter)所著之《佛教與帝國──早期西藏的政治與宗教文化》(Buddhism and Empire: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arly Tibet)。上述2部專書,可謂為西方藏學界在唐代吐蕃方面新出的研究成果。吾人觀此2書對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不是語焉不詳,就是無片言隻語,好像唐代吐蕃不存有宰相制度似地。特別是道特森氏在其書中,對吐蕃王室的繼承與婚姻;贊普手足與半手足;贊普諸母、祖母、生有子嗣的后妃與小妃等母系與姻親;王朝婚姻與國際關係;贊普宮廷與政務會議;行政管理與行政官員;土地與稅收;徵兵、運輸網與警報系統;政府官員;吐蕃帝國的階層與等級;成為貴族與貴族大臣;親族性、犯罪連坐、交換與繼承;平民、臣屬與奴隸;等級順序與行政管理系統等等,均作了介紹。可謂林林總總,一網打盡吐蕃內部的制度,並解釋了大事紀年中的所有專有名詞。然而,觀其對吐蕃宰相制度的說明,卻有如霧裡看花,竟未列專節介紹,例如其云:「中央會盟(vdun ma)經常由大論召集,是為吐蕃最高政治權力所在,也是在此盟會決定最重要的法令。」若按照上引說法,大論的浩大權力何處去了?又為何會激發墀都松贊普族殺擔任大論的噶爾氏家族?道特森氏對大論的職權竟無隻字片語。又如其譯zhang blon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為「Great ministers participating in the〔deliberation of〕state affairs」(參與商議政務的大臣),譯雖不錯,但未論及由獨相演進至眾相的過程,以及為何如是演進,眾相從何而來,其所謂的「內閣」與其認為「吐蕃最高政治權力所在」的「中央會盟(vdun ma)」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上述重要論題,道特森氏均未觸及,一如啞謎。道特森氏在書中將吐蕃制度網羅幾盡,獨漏最重要的宰相制度,何以哉?又如華爾特氏論及吐蕃的政治與宗教文化時,認為中國主要影響蕃廷之處,在於官僚政治運作方面,然並未顯現出深刻的政治涵義,除此外,通篇全未觸及吐蕃宰輔的層面。但吐蕃政治文化之中,最重要的現象是吐蕃諸氏族競逐蕃廷要職的現象,其中以競逐大論一職為最。因為大論官位最高,權勢最大,這是討論吐蕃政治文化時,首要論及的焦點,捨此,如何侈談吐蕃的政治文化?
另於2011年山姆凡薛克氏(Sam Van Schaik)代表英國藏學界提出最新的研究成果:《西藏歷史》(Tibet: A History),書中以為吐蕃帝國政府的形成由首相(prime minister)居於最高位置,其下有四位首席大臣(the four chief ministers)。未知凡薛克氏上述所云首相之下的四位首席大臣,究竟何所指?凡薛克氏所指似乎與《新唐書.吐蕃傳》所載其官有大相、都護、內大相、整事大相等4類,頗相神似,但又有不同。凡薛克氏此說與大部份漢藏文獻所載有所出入,可惜未作進一步解釋,或提供資料出處,此阻却了讀者循線探索的機會,也未將情況說明清楚。著書如是,倒為少見。亦即西方從早期的杜奇氏(G. Tucci)到中期的霍夫曼氏(Helmut Hoffman),中經2009年上述的2書,以及2011年英國最新的研究成果所顯示,証明西方藏學界在唐代吐蕃的研究領域上,有關吐蕃的中央職官乃至宰相制度的部份,少有鞭辟入裡的論著。究其原因,一則證明西方藏學界無此方面的認知,無法深入討論;再則完全不參考中文寫作的論著,以致有一大部份的吐蕃制度,包括官制、社會階層與等級,在以中文書寫的論著之中,均已曾大量討論,或已成定論者,其仍重覆論述;三則無識於東方的社會文化等等因素,有以促成。由上述可知,國外學界對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尚處於貧乏狀態,此應是彼等之弱項。
按唐代吐蕃為藏族在歷史上,所建立最強大的王朝。唐代吐蕃在藏族史的地位一如國史中的漢唐,其典章制度,多為後世藏族政權所師法。例如在達賴之下的噶廈(bkav shag)政府,由4位噶倫(bkav blon)組成,採合議制。此「噶倫」(bkav blon)官稱,不但源自於唐代吐蕃的官稱:「宰相同平章事」(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且其合議方式避免一人獨攬大權之精神,也是仿自唐代吐蕃。由此可見,唐代吐蕃典章制度的研究,對於藏族史而言,殆屬重要課題。
王師吉林曾云:「研究歷史者,所研究者即為變化。」準此,筆者以為在唐代吐蕃的典章制度之中,以宰相制度最具變化。而且由吐蕃宰相制度的產生、運作及演進當中,看唐代吐蕃的君相關係、中央權力結構、各氏族的發展等問題,則更能掌握住問題的核心,也較能看出其歷史發展的真髓。
學界有關吐蕃相制的研究,大多於吐蕃的官制、政治制度或人物研究之中,一併論述。在國外方面,雖有英人理查遜氏(H.E.Richardson)之「吐蕃王國之大相(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 」,但其重點在探討曾擔任大論的氏族,與其氏族起源等,並未論及宰相制度本身的問題。且其他相關論著不是語焉不詳,多所錯誤,就是有意無意地加以疏略,有如上述。是以筆者不揣固陋,擬針對吐蕃宰相的官稱、宰相如何產生、如何任命、職權為何、相制如何演變、其演變過程所代表的意義等,作一剖析。在取材方面,涉及吐蕃相制的原始史料,最重要的有《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吐蕃贊普世系表〉等,其中尤以〈吐蕃贊普傳記第二〉最為重要。其內容全為吐蕃宰相的記載,應可稱之為〈吐蕃宰相世系表〉(以下簡稱宰相表)。在吐蕃金石銘刻方面,述及吐蕃宰相方面者,有〈唐蕃會盟碑〉、〈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諧拉康碑〉、〈昌都丹瑪摩崖石刻〉等,雖屬零星片斷,但在名銜上,有很重要的記載。在教法史料方面,著名的《賢者喜宴》著錄有2件吐蕃贊普盟誓的誓文,當中有參與盟誓大小臣子的名銜,是為本文重要材料之一。另漢史料在提供較為詳細的情節上,有很大的作用,且與藏文史料作比較時,可發揮相互印証、糾繆及補闕的功效。
由於漢史料包括張說奉敕撰〈撥川郡王碑文〉所載:「論弓仁者,源出於疋末城,吐蕃贊普之王族也…戎言謂宰曰論」、《補國史》所載:「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宦族則曰尚…」、以及《資治通鑑》所載:「吐蕃…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等之記載,造成了學界對吐蕃相制諸多誤解,諸如大陸藏學泰斗王堯氏於解讀青海都蘭吐蕃墓所出土的吐蕃文彙時,以為吐蕃的「論」就是部長一級的長官,可譯為「相」,所謂「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意思是「所有的大尚論」。但事實上,吐蕃早期實施獨相制時,其大論官稱為Blon che,《新唐書‧吐蕃傳》載為「論茝」。另又作Blon chen po或Blon chen pho。至西元705年以後,吐蕃實施眾相制,除「首席宰相」仍保留原有獨相銜外,其餘眾相概稱為: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或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準上,吐蕃宰相官稱應稱為「論茝」或「大論」,更何況「論」係指未與王室聯姻(有例外)的貴族,至蕃廷任職的官員,皆稱為「論」,是以「論」者,皆為官員,但未必就是宰相,〈撥川郡王碑文〉謂宰相曰論的說法,與實際顯有出入。有關此方面將於本書之中,詳細地予以討論。
基於上述的認知,為免於受所謂原始史料之誤導,為辨明吐蕃相制的真義,筆者以為宜有一部專書,針對吐蕃二百年來宰相制度的源起、發展、演變及其影響等,作一通論性的闡發,冀成一家之言,以供學界卓參。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唐代吐蕃的崛起過程,乃由雅魯藏布江沿岸河谷適農地區的氏族部落,彼此相互競逐兼併,最後由雅魯藏布江南岸支流雅礱河谷地區( Yar lung so kha)的悉補野氏(sPu rgyal),以「天神下凡,入主人間」之姿,獲得各氏族的支持,兼併各部,統整雅魯藏布江南北兩岸。進而透過既和親又征戰的兩面手法,征服游牧部族國家羊同(Zhang zhung,約位於今西藏西部地區),並以懷柔政策,說服位於西藏與青海接界處、長江源流區的游牧部族國家蘇毗(Sum pa)內附,而完成了吐蕃的統一。接著,繼續東北進,依序併吞青海諸氐羌部族國家:多彌、党項、白蘭、吐谷渾等,直抵李唐所控疆界。完成了歷史上首度青康藏高原諸氐羌系民族的大一統,迸發出堪稱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強大軍事及政治力,奠下今日青康藏高原族群的分佈與文化基礎。
唐代吐蕃的持續向外發展,先後與李唐、大食競逐西域,控制絲路通道,北逐迴紇,視迴紇如無物;東向犯唐,河西隴右盡陷其手;東南臣服南詔等等,盛極一時,影響所及,不僅阻斷了漢民族向西域的拓墾,改變了亞洲民族爾後的生態與發展,且對唐朝內部產生極大的影響,在外交、政略、財經、軍事、社會等均因吐蕃的壓迫,造成重大的轉變。對吐蕃往後的歷史發展,更屬關鍵。
筆者撰寫本書的目的,在於以本人過去所撰之論文,諸如〈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唐代吐蕃的相制〉、〈唐代吐蕃的僧相體制〉、〈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吐蕃「三尚一論」考疑-吐蕃眾相制度探微〉、〈唐代吐蕃的氏族〉、〈唐代吐蕃曾否加入中國文化圈考辨〉、〈吐蕃贊普墀祖德贊研究〉、《唐代吐蕃的傑琛(rgyal mtshan)》、〈唐代吐蕃的社會結構〉、〈唐代吐蕃眾相制研究〉、〈吐蕃「尚」、「論」與「尚論」-吐蕃的社會身份分類與官僚集團的銜稱〉、〈〝贊普〞釋義–吐蕃統治者稱號意義之商榷〉、〈漢藏文化關係新事例試析〉、〈唐代吐蕃政權屬性與政治文化研究〉、〈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雛型與官員設置研究〉以及〈唐代吐蕃僧相官銜考〉等文為基礎,再進一步廣蒐國內外最新相關研究成果,同時蒐集並爬梳藏文原典史料,予以整理、補闕、修正,以便對於吐蕃君臣關係、氏族生態、政治運作、政局發展、與李唐在文化上與政治制度的關連性等方面,以及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宰相制度,就其制度的完整輪廓、內涵、運作、淵源、設計、原由、任命、職權、演進、影響等,以本人累積三十餘篇論文的研究能量,試圖將之整理撰寫形成有系統的學術性專書,貢獻一家之言。
本書研究方法主要採史學方法,將所蒐集之漢藏文獻資料,經必要的考證、排比、分析、歸納及綜合等,將經過上述方式整理的材料,借用政治學中之制度研究法的概念,加以舖陳。其中尤須注意唐代吐蕃的特性,及其與李唐在文化、制度等方面,因交流所受到的影響等。
按本書所參考的主要文獻,大部為現存吐蕃時期所遺留的文獻,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銘等。但有學者別出心裁,重新檢討碑銘的內容,於碑銘的用詞用語、銘文的語言習慣及其內容等著手,重新考訂諸碑的成立時間,辨其真偽,亦即是否立於事件發生的當口,或是事後所立,或是否由蕃廷所授權,或由功臣後代所立者等。例如,彼等以諧拉康碑中贊普自稱「nga」(我),認為贊普此種自稱,從未見於唐代吐蕃時期的各種文書之中,而且也很難想像類吐蕃贊普至高無上的地位,會使用一般常人所使用的第一人稱「nga」;復由碑銘中使用的「…ring la」(於…期間)用語,在吐蕃時期指的是前朝的贊普,並非指現任的贊普;在用詞方面,例如唐代吐蕃時期的碑銘,其統治者的稱號就是「贊普」(btsan po),吐蕃帝國崩潰以後,統治者不復存在,此時若有碑銘使用了次於btsan po一等的rgyal po(王)一詞時,吾人據此即可確定此碑應立於吐蕃帝國崩潰以後,並不屬於唐代吐蕃時期。類此從卷子與碑銘內容的行文與使用的詞彙等,疑部份屬於吐蕃王朝崩潰以後的產物。意指並非所有的敦煌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銘,都屬於吐蕃時期的文獻,不能目為第一手史料。
但筆者以為,容或某些因素讓部份敦煌古藏文卷子,與部份的吐蕃碑銘等,遭疑非出自吐蕃時期,然而,彼等仍屬最靠近吐蕃時期的文獻,且未遭藏傳佛教後弘期之僧院史觀所汚染。在吐蕃原始史料大部闕佚難尋之時,彼等仍擁有第一手史料的地位,殆無可置疑。
吾人觀敦煌古藏文卷子之中的歷史記載部份,其屬於吐蕃王朝成立以後,吐蕃歷朝歷代陸陸續續累積匯編而成,似非成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之作。持此觀點的理由如下:其一,吐蕃文字的使用,係於松贊干布朝開始,因此,松贊干布朝及其以前時期之紀事,似從口頭傳說或記憶,轉成筆錄,並予潤飾與改造,此促成在追述先人事蹟之際,執筆者可承上意加油添醋;其二,歷史的撰述,原就需蒐集材料,沒有歷朝歷代的紀錄留存,後人無從據以撰著。是以雖有主張《敦煌古藏文卷子》之中的〈吐蕃贊普傳記〉、〈贊普世系表〉等,以及諸如工布碑、噶迥碑等,均為吐蕃王朝崩潰以後方問世的文獻,可能其主張無可挑剔,但事實上,僅拘泥於成書時間而忽略其他事實,並不足取。明乎此,吾人在取材上,就不受所謂是否使用原始史料,而影響全文觀點正確與否之疑慮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