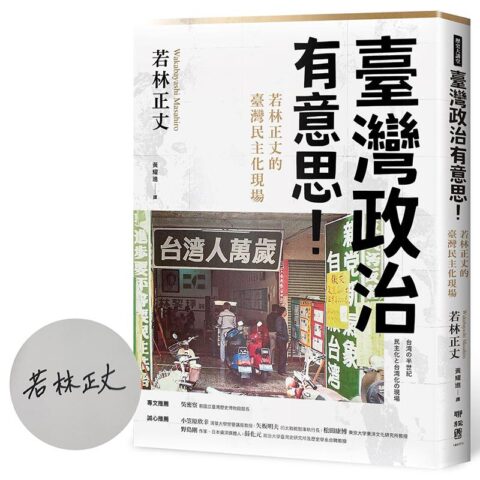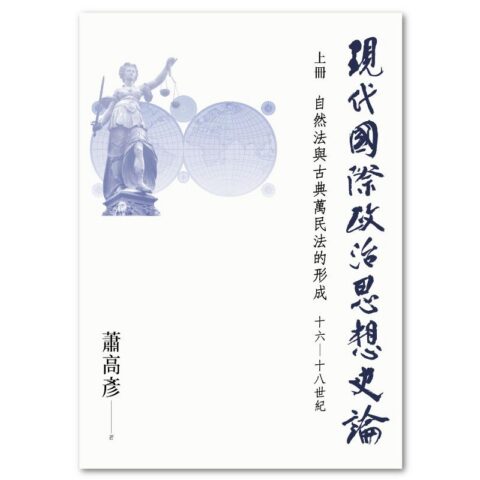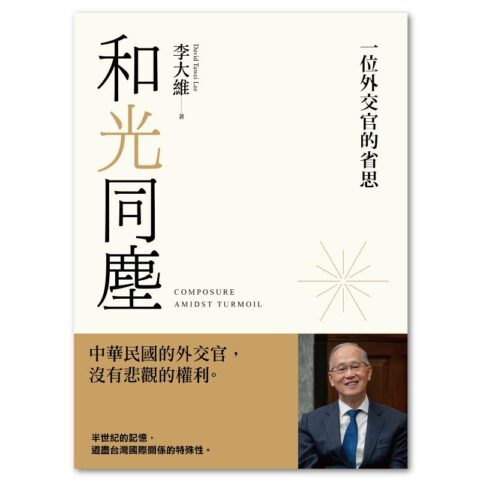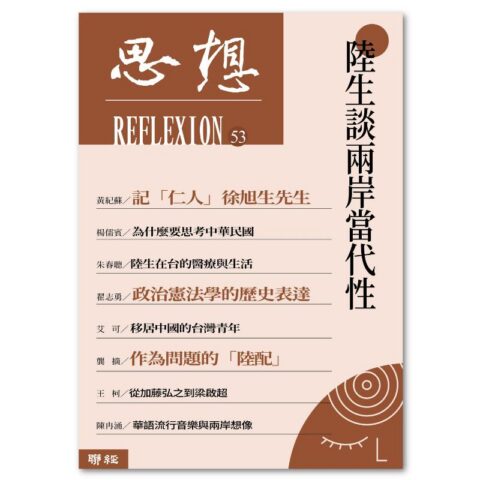從王權、專制到民主: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
出版日期:2015-12-04
作者:蔡英文
印刷:單色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408
開數:25開(14.8 x 21 cm)
EAN:9789570846515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
公民享有了政治自由,
但陷入了良好生活與現實的落差。
政府的失能、社會經濟進展的期望、道德的標榜、
政治的腐化、社會正義的籲求、貧富差距的糾結。
台灣民主要能穩健發展,不致走向自我毀滅,
成為台灣社會民生關切的問題。
《從王權、專制到民主》作者蔡英文關注民主的自我否定,或者甚至自我毀滅的問題,民主難得而易失,懷此關切,試圖從西方民主理念及其實踐的歷史經驗,尋求解釋:上溯民主觀念的起源,下探當代民主的論議,闡述了歐洲如何從古羅馬的皇權帝制及封建的分割性主權體系,轉向現代絕對主權的國家理念,以及人民主權的萌發,進而解釋民主革命所形成的代議民主如何在人民主權的動力與憲政法治之秩序兩者辯證中開展。
本書試圖指出,這種辯證的動態無法讓民主形成如專制王權政體一般的穩定秩序,而是充滿了權力的競逐與衝突,時時陷入失衡的險境。但也因這種民主性格才讓公民享有專制王權的屬民所無法享有的自由與平等的生活條件,以及能有尊嚴之生命的期待。民主的辯證是對未來開放的,而且沒有終點,它是否會走向自我毀滅?這有賴公民德行,及其明智的政治判斷,以及政治責任的承擔,也有賴於公共領域是否能有效地承擔合理性之輿論的媒介,以及政府的治理能力。
作者:蔡英文
1952年6月4日出生於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及研究所畢業,英國約克大學政治學博士,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系及渥爾森學院訪問學人,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主要著作有:《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聯經出版公司)、《當代政治思潮》(三民書局)等。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篇 民主思想的古典脈絡
第二章 古典共和思想中的公民政治共同體──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的解釋
一、引言
二、古雅典城邦的民主與古羅馬共和的貴族政體
三、亞里斯多德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的理念
四、西塞羅的公民社會的概念
第三章 聖奧古斯丁的政治神學的批判
一、引言
二、奧古斯丁的關懷
三、超越性的論證原則
四、上帝之城與俗世之城
五、對古典共和之公民政治共同體的批判
六、結論
第二篇 人民主權與憲政民主
第四章 從君主的威勢到國家主權者權位的轉變
一、引言
二、政治領導者(主權)與民主的問題
三、古羅馬的帝國理念──塞尼嘉的「皇權帝制」的正當性論證與中古封建的「君主制」原則
四、但丁的帝國理念
五、馬基維利的政治領導的理念
六、拉‧波艾西的反君主制原則
七、國家主權理論的轉向
八、結論:在社會契約論下的主權理論的弔詭
第五章 史賓諾莎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蘊含的民主的弔詭
一、引言
二、史賓諾莎之絕對性民主主權的理念與憲政法治的緊張
三、盧梭的人民主權的批判觀點
第六章 革命與民主政治的正當性──鄂蘭與列弗的解釋
一、引言
二、人民主權與民族的絕對主義
三、民主革命的極權政治傾向
四、結論
第七章 革命後的政治思辨──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與龔斯當的自由憲政的觀點
一、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
二、龔斯當的「自由憲政」的理念
第八章 民主憲政國家與人民主權之間的緊張──卡爾‧施密特對議會式民主的批判
一、引言
二、市民法治國的內在矛盾
三、對議會式民主的批判
四、議會民主制裡中立性的問題
五、挽救憲政民主的途徑―國家主權者的政治決斷與「公投」的人民決斷
六、結論
第九章 政治的代表性與自由民主體制──施密特、鄂蘭與列弗論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一、引言
二、施密特的民主的同一性與國家的代表性原則
三、鄂蘭對代議民主制的批判及其共和主義式的民主理念
四、列弗的民主政體理論
五、結論
第三篇 民主社會的實踐議題
第十章 市民社會與自由民主──蓋爾勒的觀點
一、市民社會與人個體性之倫理
二、人之個體性、市民社會,以及現代性文化的關聯
三、人的個體性與單原子之個人
四、市民社會、自由民主與民族主義
五、結論
第十一章 公共領域的倫理與民主政治
一、公共領域的古典意象與現代詮釋
二、現代性之公共空間面臨的問題
三、公共空間的倫理性格
四、結論
第十二章 政治之罪惡與寬恕的可能性──以漢娜‧鄂蘭的解釋為焦點
一、引言
二、納粹極權主義之罪惡的解釋
三、罪惡與思維能力之障蔽
四、公民責任的三個層次
五、結論
第十三章 公平正義的實踐及其困境──比爾‧霍尚維隆的福利國家理論
一、引言
二、歐美福利國家的型態及其面臨的問題
三、保險制與補償助益制的原則──霍尚維隆的福利國家理論
四、福利國家實踐上的限制
五、福利國家的民意──以英國《遠見》雜誌的社會調查為例
六、結論
第十四章 結論
參考書目
導論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公民享有先前沒有的政治自由,但陷入了民主所承諾的良好生活與現實的落差、政府治理的失能與社會經濟進展的期望、道德的標榜與政治的腐化、社會正義的籲求與社會貧富差距的糾結纏繞,姑且不論台灣的主權不完整所帶來的困境。置身這種處境,台灣民主是否能穩健發展,而不致於走向「民主的自我毀滅」的途徑,遂成為關切的問題。
資歷尚淺的台灣民主尚未累積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解釋,致使無法形成「民主的傳承」(inheritance of democracy)),藉之得以緩解民主的困境。民主的理念來自西方,在了解民主的意義上,我們有必要走進西方的經驗世界,探究其民主的傳承。自十九世紀現代民主理論形成以來,有關民主的論述推陳出新。面對浩瀚無窮的論著,任何人皓首窮經皆不可盡。是故本書不能說全面性地闡釋了民主的政治思想史,更不能說有系統地建立了民主的理論。
現代民主源出十八世紀的美法兩國的民主革命;透過暴力與戰爭,這兩個國家以「人民主權」為意識型態,推翻了「舊政制」及其等級身分的社會結構,制訂了以人權與公民權為公法的憲法,設立分權的政府組織以及選舉的代表制,據此形塑了現代的「代議式民主」(或謂「自由憲政民主」)的架構。但民主並非一蹴可及,也非畢其功於一役,經由十九世紀以來的勞工與婦女的抗爭運動,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民主才發展出不分性別與資產資格的「普選制」而走進所謂的「群眾民主」(mass democracy),其間遭遇極權主義與法西斯政權的頓挫,直到1990年代,民主才普遍地被承認為具有正當性的體制,是構成良好政府的基本條件。
現代民主(不論你稱為民主體制或民主體系)在歐美的發展經歷百年,相較於先前人類生活過來的君主專制(monarchy)與帝國的政治體制,其時間委實短暫。就此而言,民主尚且處在動態的發展當中,而沒有所謂「歷史的終點」(如福山所言)。現代民主藉由人為的力量或甚至暴力,裁斷歷史的延續性,顛覆舊有的體制,就這一點來說,民主代表一種歷史的斷裂。另一方面,從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亦可發現民主永遠不會滿足既成的事物,甚至它自己建構的制度;它既是自我批判,也向未來開放,但民主的這種傾向使它在過程中處處是險境,在特殊的境況中,會走向民主自我否定的途徑。舉兩個例子,法國革命在1792年到1794年之間,革命分子羅伯斯比為防禦新建立的民主以免遭到內外敵人的攻擊,以及鞏固民主秩序,而訴諸反民主的恐怖統治。同樣地,德國在1918年從君主專制走向了所謂威瑪的民主共和,這個新建立的民主共和處於政黨林立、相互鬥爭而無法形成一穩定的秩序,加上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一戰的戰爭賠償,將這個新起的民主共和推向危機的境況,在其中醞釀納粹政黨的興起,這個政黨以合法的民主程序掌握了政權。但它以反民主的種族主義為意識型態,並且藉由全面控制的手段,解決了民主的危機,但也埋葬了這個民主共和。法國當代「解構論」的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他的《非法亂紀的國家:理性二論》(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的〈論強權的理性〉中,用「自體免疫」(auto-immunity)作為譬喻來闡釋民主內在的自毀傾向。若不論他如何說明民主內蘊的無可化解的弔詭(aporias, 或譯為「死胡同」),德希達以此概念指出民主的「非確定性」(indetermination)與開放性,這種特性讓民主得以保持其自由與平等的動態擴展,但民主也因這種特性使它遭受內生的反對者或甚至政敵的強勁攻擊。面臨這種危機處境,民主如同生物有機體一樣必須以自己的抗體來對抗這些危機,以防禦自身。但在某種情況下,免疫的抗體在對抗外來的病毒之時,亦可能反向攻擊自身,而造成免疫系統的崩潰,這就形成所謂「自體免疫」的自殺。(Derrida, 2005: 45)
然而,這種民主動態的發展也伴隨著另一種追求穩定性的趨勢。在推翻舊政制之後,民主革命面臨的難題即是如何在廢墟之中重建新的國家體制以及社會秩序。新國家體制的建構必須有其典章憲政,以確立國家治理的公共權威,以及組織政府,建立「權力的布置或機制」(the apparatus of power),並賦予人民享有基本權利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民主的動態必須有其憲政的規約。
本書即以民主的動態與憲政制度這兩個面向,闡述歐洲如何從王權專制走向自由民主的理念。民主是一古老的名詞,它源自古希臘雅典城邦在西元前第六與第五世紀的政治實踐,其意涵表示人民(demo)的力量、做為與自治。作為一種體制(regime),它意指人民以自由與平等的身份共同參與,以及審議與決斷公共事務,並形成憲法(constitution)、組織政府,安排制度(如從公民大會以至法庭等),這種民主體制的形成,就如德國歷史家邁爾(Christian Meier)所稱,乃是史無前例,為古希臘人所獨創(Meier, 1990)。古雅典的民主城邦在西元前第五世紀末因伯羅奔尼薩戰爭(Pelonnesian Wars, 從431 B‧C至404B‧C)逐漸走向衰微,至331B‧C為馬基頓的菲利浦(Philip of Macedon)所征服。在這一段期間,羅馬共和逐漸興起。羅馬共和創建於509B‧C,歷經由三次的「布匿克戰役」(Punic War, 從264B‧C到146B‧C),征服迦太基(Carthage),而成為支配地中海地區的霸權。羅馬共和亦如古雅典民主是一自由城邦,但其體制的構成是以人民權力為基礎,而以貴族所形成的元老院為治理的權威。同時,由於羅馬法頒佈,羅馬共和比古雅典民主更注重公民的法律人格及其權益。在本書的第二章中,我對這兩個政體的差異,做了扼要的說明,以此為背景,闡述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的政治共同體(或謂公民社會)的理論。他們的政治理念一般被稱為古典的共和思想,其論證的主軸在於解釋共同體的構成乃以人民(與公民)共享的公共性的「福祉」(happiness或goodness或謂「共善」)為基礎,此「共善」既是物質性的(如財富、資產,或者滿足個人生存的必需品)也是非物質性的(如和平、安全、正義公理等倫理上的要求)。以此共同體之構成為起點,他們進一步說明憲法及其政府的組織與公民的身分與權益和德行。
第二章 古典共和思想中的公民政治共同體: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的解釋
一、引言
古希臘城邦與羅馬共和雖有體制上的不同(前者是民主城邦,後者是貴族的共和)但在本質上乃是由公民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koinonia politike)也可稱之為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ies)。如我們所熟悉的,亞里斯多德在闡釋此概念時,界定人的本質在於過政治的生活(phusin zoon politikon),並且區分 polis(城邦的公共生活)與 oikos(家業的管理),把政治視為「公共之善」(res publica)的具體落實,以及明確表述「公民之德」。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在古羅馬共和時期,因為「羅馬法」的實踐而有了新的概念內涵。古羅馬共和思想雖然承襲亞里斯多德的「公民的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可是更強調法律的權威;同時,公民身份之認定不只是在於公共事務之參與,更是指稱「法律社會的成員」。這些成員(或所有的公民)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以及受法律的保護。簡言之,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之概念上賦予更明確的法律人(legalis homo)的意義。(J‧ A‧ Pocock,1992/1995: 36-37)
如何較詳細地闡釋古典共和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的概念的轉變?針對這個問題,本章闡述西塞羅的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atis)與共和國(civitas 或 respublica)的觀念,而說明古典共和之「政治共同體」呈現「人民的權益」(res populi)與法治的含意。古典共和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理念是跟當時的民主城邦與貴族共和的實際經驗有關,是故,在闡述他們的理念之前,簡要說明民主城邦與貴族共和的特徵。
二、古雅典城邦的民主與古羅馬共和的貴族政體
古雅典城邦,經歷了索倫(Solon)在西元前594年,以及克萊吉尼斯(Cleisthenes)在508年(或507年)的政治與社會改革,而形成(或者說創造了)民主制。不論其歷史的機緣與這些改革的方案,古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表現下列的特質:民主城邦是由公民所構成的共同體,公民身份是有其限定(譬如婦女與外邦人,奴隸皆不得成為公民)。公民皆有責任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擔任執政官。因此從法律的制訂、司法的審查,城市的公共政策的審議與執行皆由公民承擔。這種民主的城邦,引用卡斯托利亞底斯(Corelius Castoriadis)的話,即是由公民集體構成的自我建制(the self-institution of the collectivity)。這種自我建制呈現動態性格,但這種動態乃受其憲法的主導,也由公民的知識與理念的傳播所支援與推促,就如雅典公民所言,法律既然由我們所制訂,也可以由我們改變(Castoriadis, 1996: 122)
古希臘創造出民主,其概念語詞乃結合「人民」(demos)與「治理」(kratos,也意指力量、智能、意志與作為)。就此而言,民主意指人民的作為、權力與治理。在古希臘的政治中,人民乃指特定疆域(如城邦)的居民,它與「貴族」(aristori,或謂「寡頭」)相對立。除此之外,人民也指實行民主的城邦的所有公民。在此,值得提示的是,民主的概念也跟其他兩個概念語詞相關,一是「表達言論的平等權利」(isegoria),另一則是「參與法律的制訂與接受司法的平等權利」(isonomy),這兩個概念語詞的使用,乃先於「民主」的概念,它意指公民的平等地位(Vidal-Naquet, 1996: 109)。在民主政體中,所謂「政治」乃是指公民集體的參與、審議、判斷與行動,這一切作為的正當性不須援引超越性的論證(如上帝的權能或天意),也非來自一人或少數及獨制的權力(如君主制與寡頭制的權力),而是純粹由人民(公民)本身的作為。因此,如維多‧拿奎德(Pierre Vidal-Naquet)所言,「民主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政治是可能的,而政治就其定義而言,乃是所有公民的事務」。(ibid‧: 111)
相對而言,古羅馬從西元前509年,當貴族推翻王制,至西元前27年屋大維稱帝,其間所形成的「共和制」並非如古雅典城邦的民主制,而是「寡頭制」(oligarchic regime,或可譯為「貴族制」),主導政治的不是平民大眾,而是社會上有名望,且擁有龐大財富與扈從(clients)的家族。這些貴族掌握元老院作為他們治理平民大眾的重要機構,體現政治的權威(autorita)。儘管共和的平民大眾沒有資格參與公共或政治事務的權利,但貴族深知其權威必須來自人民的支持,他們的政治事功,榮耀必須贏取人民的讚許與信賴。因此,羅馬共和的政府,在理念上,乃是「權威在元老院,權力在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貴族與平民雖相互倚賴,但亦彼此衝突,甚至鬥爭。平民欲擠身於公民階層,進入元老院,必須透過顯赫的事功與財富的累積,以及由此得到社會的聲望。在西元前第四世紀公民經由所謂「社會等級的鬥爭」(struggle of the orders),取得抗衡執政權威的權利,而得以自組議會(plebeian assembly),以及自選其行政長官(tribunes)。就此,元老院的權威必須受到人民議會及監察官的制衡。(Rosenstein, 1999: 374)。
然而,古羅馬共和並非民主制,其主要的因素在於政治權力與權威跟社會的名望與財富糾葛一起,無法如古雅典城邦一樣,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公共空間,容許自由公民審議與決斷政治事務。共和雖有公共討論的場所(forum),但是羅馬人民不是透過政治參與的途徑,發揮其影響力,而是運用街頭抗議、騷動,甚至暴亂的方式表達政治的不滿。除此之外,羅馬共和的行政長官雖經由公民的選任,但他們不是人民的代表,因此,沒有責任實現人民的願望(Yakobson, 1999: 391)。共和體制因元老院的權威以及注重法治而得以維繫其穩定性,但由於掌握元老院的貴族來自社會的望族以及財富的累積,致使政治權力、權威的行使與社會的實力相結合,排除了人民的政治參與。除此之外,貴族內部派系的傾軋、鬥爭造成元老院決策權的癱瘓,無法有效地因應內外的問題與危機。因元老院制度的失靈,解決內外的政治與軍事事務而只能循經制度外的途徑,決斷權最後則由軍事強人所掌控,在共和體制喪失其正當性的處境中,從貴族門第出身的軍事強人的干政,以及平民大眾的要求,將共和制推向皇權帝制(principte)。以上述的政治體系為背景,本章試著闡釋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的政治共同體理論。
三、亞里斯多德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的理念
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解釋,任何共同體(koinõnia)的形成必須預設其成員可以共享、溝通與參與的共同事務,以及共同的結合紐帶。就城邦的共同體而言,亞氏基於目的論與自然演化的觀點,闡釋它乃是從家庭、農村公社演化成的,最具廣延性(comprehensive)、自足性(autarky)的結社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說任何結社皆是建立在「善」之目的的條件上,那麼,依照亞氏的觀點,城邦的政治共同體乃是人之「最高善」的實現。
城邦的政治共同體既是一廣延性與自足性的結社型態,那麼,它必然包含各種自發自願結合的結社團體(如農業的、技術工藝的團體),這些結社團體,相對於城邦的政治共同體而言,是部分的,無法成就自足的條件。這種「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取決於一個社群之「善」的本質意義,譬如,大學作為一個追求「知識」之善的目的而形成的共同體,「知識」遂成為此共同體生活的「界線」(a limit),組成此共同體的「部分」(如校務的行政管理)成為達此目的之「輔助性」的設置。城邦政治共同體既然代表「最高善」的實現,那麼,這「最高善」所指為何?
「善」,在個人與結社的層面上,指「良好的生活」與「人的卓越秀異」(human excellence)。從一普遍的意義來說,它可以意指人的實踐(praxis)與構成社群的倫理,如公道、正義,或者是友誼,當然,它亦包含實質性的福祇,如健康、利益與優厚的物質生活狀況等。亞氏在思考政治共同體的「最高善」的意義時,著重於倫理之善的組合關係,其理由在於政治共同體既是一廣延的、整全與自足的社群,它的「至善」必須包容與超越其組成之「部分」的個別與特殊的「善」,而得以滿足此條件的「至善」就必須是倫理性的「善」。這也是為什麼亞氏強調「正義」(不論是數學式的,或幾何學式的分配正義)乃是政治共同體構成的基本條件的理由。
城邦的政治共同體,乃是在一種憲政下由公民所構成的共同體。在界定「公民身分」時,亞氏排除了宗族血緣與地緣的關係;其次,否定從事勞動生產與製造業者(包含外邦人和商人)的公民身分。在這裡不討論古希臘城邦公民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就「公民身分」的理論解釋而言,所謂公民乃指「享有參與政治事務,以及身兼行政與司法職司的權益。依照我們的定義,享有這些權益者才有資格成為城邦之公民。一般而言,一個城邦乃是像這樣具有自足生活的成員所構成。從是觀之,公民是指擁有產業,得以免除勞動與工作,而享有閒暇、具有能力參與城邦公共事務的『統治階級』(politeuma)。他們在上軌道的城邦中,是平等且彼此相似,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同質性的生活方式,能表現公共德行(civic virtue)。他們自由合作,彼此相互治理,能達成一個共同體『共善』之目的。」(1985‧: 1227 b7-16~1332 b12-41)。
政治共同體具有政治的屬性(the political),在此,亞氏所使用的「政治」(politikos)一詞具有如下的含意:政治表示公民(polites)對於城邦公共事務的關心,以及增進公共福祉的作為,這乃是「政治屬性」(politiké)的基本意義。除此之外,政治亦表示「治理」(the ruling)的意涵,它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指城邦的「統治階層」(politeuma)依照法律(通常是指習慣法)的規約,處理城邦的公共事務;另一方面,指公民彼此之間的關係乃是建立在道德倫理的聯繫。再者,「政治體制」(politeia)這個名詞亦含有城邦之憲政構成的意義,以及表示亞氏所說的擷取寡頭政體(oligarchy)與民主制(democracy)的長處而形成的理想政體(polity)。
不論及亞氏對政治體制的類型之論述,他的公民政治實踐的理念,其論證的主題在於公民的政治實踐並非技術性的專家政治──如我們現在所稱的「科技官僚」的行政管理──而是指公民參與政治實務時,言行的具體表達,以及彼此之間言行之溝通、分享。他所關切的是公民「合作共事」(act in concord),以增進與實現城邦的共同福祉。
亞氏在闡述此公民政治實踐的理念時,提示了人的本質或意向的觀點,就如同一般所論的,亞氏肯定人為「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以及「具言說與行動能力的存有」(zoon logos ekon)。相對於現代的「個人主義」,此觀念強調人相互結社的傾向,而非孤立單獨的個體存在。同時,「理性言說」(logos)是指「公民在市集或公共場域」(agora)的言辯、溝通,以及經由此過程,對於公共議題有一種釐清,以鄂蘭的用語,即是「透過言辯,解釋、論述我們生活之共同世界的種種事物」,它所指的不是一種「理性計算」,或者也不是如歐克秀所指的「依照一項不證自明的原理作獨白式(monological)的推論與證明」(Oakefshott, 1991: 84-85),語言的表明與溝通,乃是一種彰顯與釐清。
亞氏以古希臘城邦的政治社會經驗,建立了「政治共同體」 (koinõnia politiké)的理念,在其中,他闡釋公民身份與德行的意義,肯定政治共同體的道德倫理性格;另一方面,他塑造出人的「公共或政治人格」和「理性言辯溝通」的存有,這些均構成了「公民共和主義」思想之濫觴。羅馬共和時期的西塞羅承續了這些理念,提出了政治共同體的構成基礎。筆者依據他的 De Re Publica(《論共和》)與 De Legibus(《論法律》)為本,說明其公民社會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