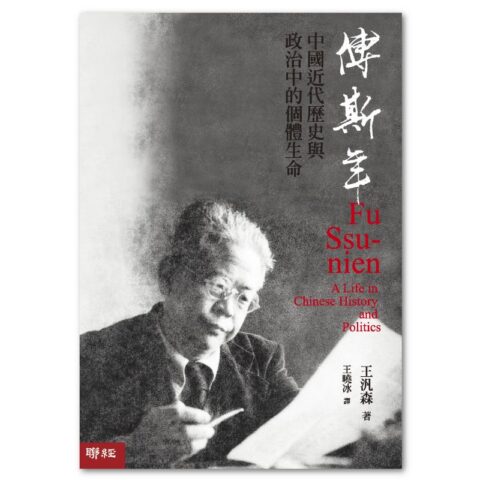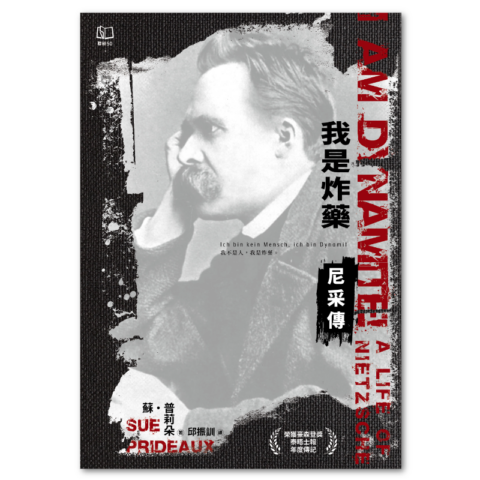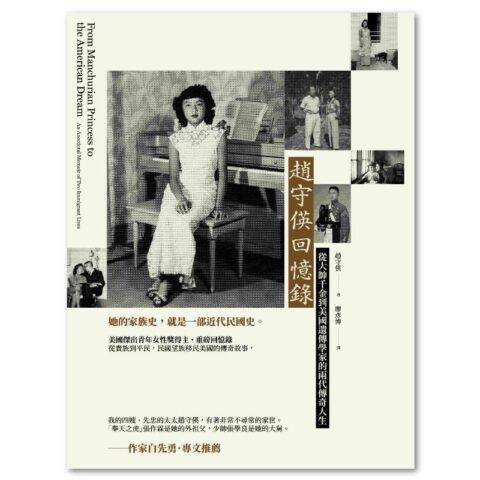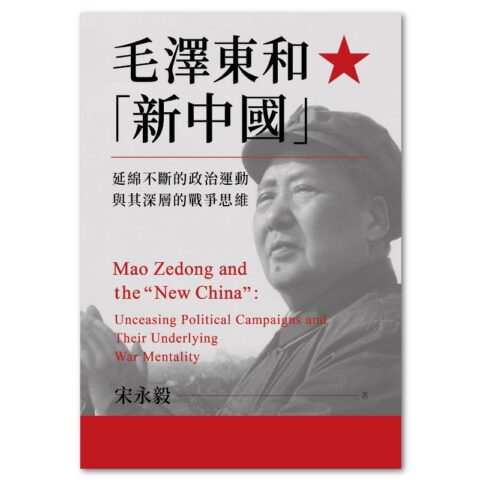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余英時文集06)
出版日期:2023-02-09
作者:余英時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67091
系列:余英時文集
尚有庫存
研究胡適生平,總是存在著大大小小的疑點,余英時先生考據諸線索,提供後世這些疑點的澄清,並盡量還原真相。
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在胡適個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階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他的博士學位問題,他的西洋哲學素養,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隨著《胡適日記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
余英時先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根據《胡適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探討胡適在各個階段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並就上述引起議論的疑點,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讓胡適自己說話,盡量還胡適一個原來面貌。
本書為增訂版,新加一篇〈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考證胡適為什麼轉學到哥倫比亞研究院?以及胡適考過博士口試的新證據。
書系總目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詩存
作者:余英時
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
一、留學時期(1910-1917)
二、「新文化運動」初期(1917-1926)
三、「大革命」時期(1926-1930)
四、侵略陰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
五、出使美國(1937-1946)
六、內戰時期(1946-1949)
七、落日餘暉(1949-1962)
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
前言
一、胡適的出現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二、思想革命的始點
三、長期的精神準備
四、思想革命的兩個領域
五、胡適思想的形成
六、方法論的觀點
七、實驗主義的思想性格
八、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
《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
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
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
聯經出版公司重新編校的《胡適日記全集》是一部最完整、也最合用的新版本。最完整,因為它以曹伯言先生整理的《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為底本,又增加了一些以前未收的新資料;最合用,因為《胡適日記全集》四百萬字,翻檢不易,聯經本附加一冊人名索引,為使用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最近一、二十年來,晚清到民國時期許多重要人物的日記都已相繼出版,為現代史的研究領域增添了很豐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價值而言,《胡適日記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遠非同類作品所能比肩。理由很簡單,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更難得的是,他在日記中保存了大量反對他、批判他、甚至詆毀他的原始文件,這尤其不是一般日記作者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他的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讀完這部四百萬字的日記,便好像重溫了一遍中國現代史,不過具體而微罷了。
聯經出版公司毅然決定出版這樣一部龐大的日記,其原動力只能來自一種純淨的文化理想。因此劉國瑞、林載爵兩先生提議我為本書寫一篇序文時,我在「義不容辭」的直感下便一口答應了。現在開始著手寫序,我卻不免頗為躊躇,因為我不能決定採用什麼方式把《胡適日記全集》的史料價值充分而又系統地呈現出來。21年前我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聯經,1983)寫序時,除了《胡適留學日記》之外,其餘部分尚未刊行。所以我只能從思想方面著眼,寫成了一篇〈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但其中很少談到他個人的事跡。自1990年《胡適日記》影印本(台北:遠流)問世以來,它便成為我經常瀏覽和翻檢的一部史料。在一切涉及20世紀文化、思想、政治動向之類的論著中,我往往先參考《日記》,一方面尋求整體背景的了解,一方面覓取具體證據。日積月累之餘,《日記全集》逐漸引導我進入了胡適的世界,我在20年前的一片空白今天總算勉強填補起來了。反覆考慮之後,我最後決定根據《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把胡適的一生分成幾個階段,並分別點出其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但在每一階段,胡適個人的生命史上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現在由於《日記全集》的出現,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我自然不能在這篇序文中討論所有的疑點,因此下面僅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我相信這也許是使讀者認識《日記全集》的價值與意義的一種最有效的方式。
一、留學時期(1910-1917)
《胡適留學日記》刊布最早,流行也最廣,所以不須多說。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已詳引《留學日記》,說明留美七年是他的「精神準備」時期。1917年6月他啟程回國則象徵了「準備」時期的終結,因為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已發表在《新青年》1月號,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這七年之內,中國學術思想界正處在低潮時期,不少人都在重新探索出路。陳獨秀的《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和章士釗的《甲寅雜誌》都代表了這種探索的努力。胡適個人的「精神準備」和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才造成了他「閉門造車」而竟能「出門合轍」的巧遇。
在這一階段中,胡適生命史上有兩個相關的疑點必須予以澄清:第一是博士學位問題,第二是他的哲學造詣問題。
關於博士學位的問題早在1919年便已出現了。朱經農1919年9月7日給胡適的信中說:
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近來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了一位與足下「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先生的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神氣,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pass」,「老胡這樣那樣」。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沒有關係,只是「冒充」兩字決不能承受的。我本不應該把這無聊的話傳給你聽,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種謠言甚為可惡,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應設法「自衛」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無人相信這種說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現在「口眾我寡」,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了。
「昔為好友,今為讎仇」即指梅光迪。這是當年「謠言」的起源,但朱經農顯然知道關鍵全在胡適的博士論文沒有印出來。1920年8月9日朱經農在致胡適函中附註又說:
又,你的博士論文應當設法刊布,此間對於這件事,鬧的謠言不少,我真聽厭了,請你早早刊布罷。
胡適的論文終於在1922年刊出(見後),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因。現在讓我們根據《日記》,重考這一疑案。《留學日記》1917年5月27日追記〈博士考試〉條說: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中略)此次為口試,計二時半。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二日),口試三時。七年留學生活,於此作一結束,故記之。
此記明言「考過」,本無可疑。胡頌平《年譜長編》在此條之後的「編者按」引唐德剛《胡適雜憶》說:
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讀了兩年(1915-1917)。兩年時間連博士學位研讀過程中的「規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談不到通過一層層的考試了。……所以胡適以兩年時間讀完是不可能的。
《年譜長編》的「編者按」接著說:
照《胡適雜憶》的話,似哥大不應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乃是事實,若非唐君推斷有錯誤,則是哥大辦理博士學位授予的人有錯誤(第一冊,頁285)。
胡頌平先生為胡適辯護,自在情理之中,但唐德剛先生的懷疑是否有根據呢?胡適晚年在《口述自傳》中,是這樣回憶的:
我在1915年9月註冊進哥大哲學系研究部。其後一共讀了兩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過了哲學和哲學史的初級口試和筆試。初試及格,我就可以寫論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學博士]學位了。1917年的夏季,我就考過我論文最後口試。所以兩年的時間——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爾研究院就讀的兩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了。
這和前引《留學日記》一條先後一致。《日記》說他在1915年11月——即入哥大兩個月後——便考過「初試」,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今據《口述自傳》,則知他在康乃爾最後兩年已修了足夠的哲學史和哲學課程,所以他讀博士學位的時間一共是四學年,並不自哥大始。但是胡適在康大畢業是1914年,為什麼他說在康大讀了兩年研究院的課程呢?1914年2月17日〈記本校畢業式〉條解答了這個疑團:
余雖於去年(按:1913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課,惟以大學定例,須八學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學位,今年夏季始與六月卒業者同行畢業式(《留學日記》卷四)。
原來他每年都上暑期學校,到1913年夏天已修足了畢業學分,只因限於校章的規定,延遲到1914年2月才正式取得學位。他最後兩年多修研究院的哲學課程,是無可置疑的;《留學日記》中有很多條劄記可以證明這一事實,讀者不妨自行檢閱。
康乃爾哲學系當時以德國唯心論獨步美國,胡適所師事的克雷敦(James Edwin Creighton)、漢門(W.A. Hammond)、狄理(Frank Thilly)、阿爾貝(Ernst Albee)等人都是望重一時的名家。胡適在康大的哲學訓練已奠定了他在哥大攻讀博士學位的基礎。由於他的思維方式自始便與黑格爾一派的路數不合,他早在1914年1月便露出了接近杜威一派的明顯傾向(見《留學日記》,卷三,第三二、三四兩條劄記);第二年5月他已成為「實效主義」(pragmatism)的信徒(同上,卷九,第五二條)。所以他「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留學日記‧自序》)。有了這樣充分的準備,胡適兩年內在哥大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便絲毫不必詫異了。
但唐德剛在上引《口述自傳》一段文字的註釋中卻又提出了另一相關的疑問,推斷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的結果是「大修通過」(“pass with major revision”),而且必須「補考」,因此遲至1927年他重返哥大,滿足了這兩項要求之後,才取得博士學位。我們都知道,哥大過去有一項規定,頒授博士學位必須在論文出版並繳呈一百本之後。因此在一般的理解中,這是胡適的學位比論文完成遲了十年的唯一原因。但唐先生的疑問也自有他的根據,他認為如果不是「大修通過」,「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離華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親返紐約始拿學位呢?」所以他推測這是因為杜威在華兩年,親見胡適在「學術界的聲勢」,回到哥大後,運用他的「地位」,把「大修通過」改為「小修通過」(“pass with minor revision”)。這是一個「大膽的假設」,然而沒有經過「小心的求證」。因此他感慨地說:「如果杜威遺札尚存,哥大紀錄猶在,『胡適學位問題』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可見他並沒有在「哥大紀錄」或「杜威遺札」中發現任何硬證(hard evidence),可以支持他的「假設」。唐先生似未見前引朱經農的信,但他的懷疑卻與梅光迪不謀而合,甚為有趣。現在《胡適日記》出版了,我們可以試著解答他的疑問了。
胡適1917年回國後立即捲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學革命」,緊接著又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動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簡直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我們只要一查1919-1920〈日程與日記〉殘本(《全編》本,第三冊,頁12-222)。便可見其一斑。這一段時期內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論文、拿學位證書的念頭。那麼他為什麼終於在1922年出版了這篇論文呢?除了與上引朱經農的信有關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動念,願意應哥大之聘,去教一兩年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日程與日記〉1920年9月4日條記:
Greene(按:即顧臨,Roger Greene)來信,托我為Columbia大學覓一中國文學教授,我實在想不出人來,遂決計薦舉我自己。我實在想休息兩年了。今天去吃飯,我把此意告他,他原函本問我能去否,故極贊成我的去意。我去有幾種益處:(1)可以整頓一番,(2)可以自己著書,(3)可以作英譯哲學史,(4)可以替我的文學史打一個稿子,(5)可以替中國及北大做點鼓吹。
可知哥大原來託顧臨探詢他的意向,如果他不能去,則請他另推薦替人。他這時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為三年來太忙了,自覺治學成績下降,有改換環境的必要。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中說:
去年我病中曾有〈三年了〉詩,只成前幾節,第一節云:
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麼事體?
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幾歲年紀!
我想我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
明白了這個背景,我們便不會奇怪他何以忽動遠遊之念了。一年半以後,哥大的聘書果然來了。《日記》1922年2月23日條: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Nicholas Murray Butler正式寫信來,聘我去大學教授兩科,一為中國哲學,一為中國文學。年俸美金四千元。此事頗費躊躇。我已決定明年不教書,以全年著書。若去美國,《哲學史》中下卷必不能成,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學史罷了。擬辭不去。
這時他的心情改變,又猶豫不決了。但成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這應該是他決定將論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學位的最後手續,另一方面也可用為講授中國哲學的教材。不但如此,1923年6月他還有赴美參加教育會議的機會(見《日記》1923年6月4日條)。所以論文不遲不早,就在1922年出版,決不是偶然的。後來這兩個遠行計畫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年才有歐、美之行。
1926年12月26日《日記》上有一句話:
發電給亞東,請他們寄《名學史》一百冊到Dewey處。
這當然是為了取得學位之故,所以這一百冊論文直接寄給杜威。但《日記》中涉及博士學位的僅此一條,唐德剛先生認為「杜威遺札」可以解決胡適學位的問題,《日記》中恰好保存了杜威在1926年9月30日答胡適的一封長信(《日記》1926年10月9日條)。此信主要是答覆胡適所提出的關於「比較哲學」的問題,其次則是一些互相問候的話,沒有半個字提到胡適學位的事。如果真如唐先生所推測,杜威用了大力量使哥大鬆動它的「嚴格校規」,把胡適的論文從「大修」改為「小修」,那麼這封信上至少會有一兩句交代的話。彼此信中全不及此事,恐怕只能表示胡、杜兩人心中根本就沒有「學位」的問題。博士論文「口試」是「最容易的一道關」,這是唐先生也承認的(頁98)。除非「哥大紀錄」中有關於胡適從「大修」改「小修」的明確記載,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考官中有誰故意和杜威過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導的論文。更使人難解的是,哥大富路德教授(Luther C. Goodrich)是1927年的目擊證人,他既出面說明胡適得學位遲了十年完全是由於「論文緩繳」之故,唐先生為什麼不予採信呢?下面是唐先生的話:
夏(志清)、富(路德)二教授認為……別無他因,只是「論文緩繳了」就是了。富老先生在1927年已(是)哥大的中日文系主任。是年胡適自英來美便是他籌款請來的——公開講演六次。胡是三月份正式取得學位,六月初的畢業典禮上,胡公接受「加帶」(hood)和領取文憑時的「儐相」(escort這是那時的制度),便是富先生。據說當胡氏披著無帶道袍應召向前接受加帶時,他1917年的老同學,斯時已是哥大哲學系的資深教授的施納德(Herbert Schneider),曾鼓掌戲弄他,弄得胡博士哭笑不得。
據富氏所知,1927年胡氏並沒有「補考」。(頁99)
這一段描述中有生動的細節,最容易使人感到胡適的學位問題確有不可告人的內幕。胡頌平先生指出胡適在這一年的6月已回到上海,不可能參加哥大的「加帶典禮」,當然是一個無法反駁的事實。但他對於老同學「鼓掌戲弄」一事卻難以應付,只好說是唐先生的「幻想」。這都是因為當時《胡適日記》尚未出版,別無資料可以比勘的緣故。事實上,唐先生此說確是得之於富路德,不過他聽錯了故事,誤將胡適1939年6月在哥大得榮譽法學博士的經過搬移到1927年來了。《日記》1939年6月6日條記:
下午Columbia畢業典禮,我得一個法學博士學位。此為我做大使後得的第一個名譽學位。(今年有五個大學要給我學位,因醫生的訓誡,我只能出門接受兩個。)Prof. Goodrich做我的Escort。
普通得博士學位決無由一位教授作「儐相」之理,唐先生所謂「這是那時的制度」,完全是「想當然耳」。在獲得榮譽博士的場合,老同學「鼓掌戲弄」當然出於善意,這最後一點疑團便渙然冰釋了。
總之,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說,仍然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已在胡適研究的領域中發生了影響。曹伯言、季維龍編著的《胡適年譜》1917年5月22日條(安徽教育出版社,頁119-120)說:
日記中,未說明此次口試是否通過。
這是受唐說影響的明證。我在上面的討論僅僅是澄清事實,以彰顯《胡適日記》的史料作用,並沒有為他「辨冤白謗」的意思。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胡適與哲學的關係。自從金岳霖說過「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這句話以來,中國讀者大致都接受了這一評論。即使胡適本人也從未自稱「哲學家」。他的思想走不上形而上學的路數(所謂“metaphysical turn of mind”),也沒有接觸過羅素以來的數理邏輯,所以金先生的評語是很中肯的。但是他先後修過康大克雷敦和哥大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 Woodbridge)兩大名家的哲學史課程,更因為特別受到杜威講各派邏輯的啟發而決定以「先秦名學史」為論文題目。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胡適回國後事實上已放棄了西方哲學,轉向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研究的道路,他不能算是專業哲學家,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這裡我要介紹一下《日記》中所保存的一篇羅素書評。1923年羅素為美國著名的雜誌 Nation 寫了《先秦名學史》的評論,開始便說:
對於想掌握中國思想的歐洲讀者而言,這本書完全是一個新的開端。歐洲人很難同時是第一流的漢學家,又是合格的(competent)哲學家,這是不足驚異的。……一個人不通中文而想知道中國哲學,面對著這一情況簡直只好絕望。好了,現在我們終於有了胡適博士,他對西方哲學的精熟好像是一個歐洲人,英文寫作之佳則和多數美國的教授沒有分別,至於翻譯古代中國文本的精確可靠,我想任何外國人都很難趕得上。具有這樣獨特的條件,他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引人入勝的,正符合我們的期待。聽說這本書不過是他已出版的一部更大的中文著述的一個綱要,據讀過的人說,原著(按:指《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比本書還要好,這就更使人嚮往了。
可見在羅素眼中,胡適的西方哲學至少是「合格的」。讀了這篇英文書評,我們更難想像他在論文口試中會得到「大修」的結果。
胡適生前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羅素的書評。如果不是他把這篇文字附收在《日記》中,這件事便將根本埋沒了。他在論文的最後一篇中專論「進化論與名學」。羅素在書評中對此持疑,認為從胡適所引的文字看,似乎尚不足成為定論(“inconclusive”)。這個批評對胡適發生了影響,他在1958年所寫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中說:
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裡最脆弱的一章……。我在當時竟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遠流本,頁2-3)
胡適在北大編寫《中國哲學大綱》講義時,「莊子進化論」不但是他的得意之筆,而且舊派學人也有深信不疑的。馬敘倫著《莊子札記》便全襲其說,並因此遭到傅斯年的嚴厲批評。胡適晚年為什麼轉而痛斥自己「年輕人的謬妄議論」呢?我相信這是由於羅素的批評使他重新檢討了原文,終於放棄了早年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