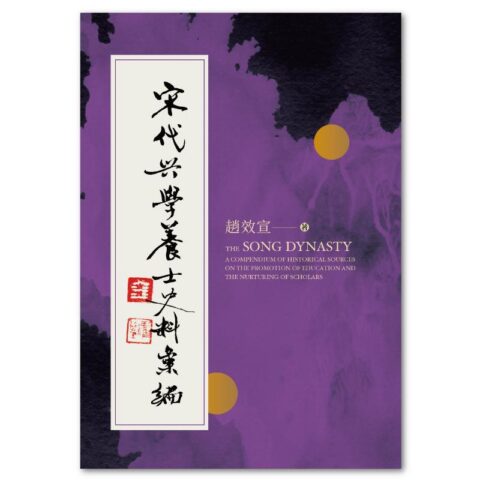中國現代性的黎明
出版日期:2025-01-02
作者:楊儒賓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68
開數:18 開,長 23 × 寬 17 × 高 3.2 cm
EAN:9789570875577
系列:楊儒賓作品集
尚有庫存
中國進入現代,碰到西方文明引發的全球性現代化浪潮,即有現代化轉型的問題,政治現代化是整體現代化方案的重要一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受到十八世紀歐美現代思潮影響甚大,但這個突破帝制中國兩千年的新國體實乃建立在中西兩種現代性思潮混合的基礎上,雙源匯流而成。締造民國的兩大領袖孫中山與梁啟超持的都是中西混合現代性的立場。
本書是《思考中華民國》的先行著作,「中國現代性的黎明」意指中華民國體制所凝聚的中國現代性有傳統文化的養分。本書主張宋明理學,尤其從陽明學到十七、八世紀之交的道體論儒學,它們提供了中國現代民主政治基礎的有力因素:道統與政統分權並具指導地位的架構;良知作為人人皆有的政治主體之基礎;文學思潮植基於兼具個性解放與倫理內涵的情教上;三教論倡導儒教與其他宗教共存共榮。這些現代化議題的前身不見得能「開出」現代的民主政治,這片土地吸收了新的思想。隨著西方現代化思潮的傳入,這些中華文化傳統的元素被喚醒,並與新的思想交匯融合,進一步增強了二十世紀以後中國現代性的發展。兩股思潮匯聚,彼此轉化,終於形成嶄新中華文明之政治體制。
作者:楊儒賓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版《儒家身體觀》、《儒門內的莊子》、《原儒》、《1949禮讚》、《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思考中華民國》、《多少蓬萊舊事》(增訂版)等書,並有譯著及編著學術論文集多種,也編輯出版了多冊與東亞儒家及近現代思潮為主軸的展覽圖錄。目前從事的文化工作以整編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的書畫墨蹟為主,學術工作則嘗試建構理學第三系的系譜。
序 言
導 論 龍場一悟—良知學的登場
一、前言:晚明、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
二、新格致說的出現
三、撒手懸崖,生死一搏
四、氣湧情熱的良知
五、結語:畸人的歷史效應
第一章 當代中國的黎明—晚明儒學的解讀
一、前言:「晚明儒學」概念的出現
二、從「左派王學」到「資本主義萌芽說」
三、近代思維說
四、良知學轉出說
五、歷史的動力:資本萌芽?良知學轉向?
六、結語:納銜接於開出
第二章 良知的良能與不能—王陽明的實踐檔案
一、前言:紛歧的良知學
二、震霆烈曜:良知的體悟
三、「義外」的意義:兩種格致論的爭議
四、在纏良知的陽明家事
五、良知束手的平亂政績
六、結語:呼喚在世存有的客觀精神
第三章 花開散葉—良知學的分化與晚明文化思潮
一、前言:大星殞落後的陽明學世界
二、天泉證道與三教融會
三、良知本體監視下的鄉里實踐
四、庶民王學與師道
五、作用是性與情教
六、結語:從良知學到後良知學
第四章 三教別裁—王學學者的「異人」經驗
一、前言:良知教的秘教訊息
二、鐵柱宮道士及其他異人的出現
三、臨清的恍見一翁事件
四、榮格與智慧老人的遭遇
五、三教論下的智慧老人原型
六、結語:「異人」的啟示
第五章 情歸何處—晚明情思想的解讀
一、前言:一情兩路
二、陽明學的情之解放作用
三、王龍溪與江右學人的超越之情
四、泰州學派與晚明文風
五、李卓吾與情欲論述
六、晚明新興文學中的情論
七、從情論到情教
八、結語:一場幫助教化的情欲革命
第六章 道勢相抗—道統思維的挫折與展開
一、前言:現代化源頭的良知學
二、朱子與道統論
三、龍場之悟:良知學的出現
四、出為帝王師:泰州學派
五、道脈如何斷得:東林學派的抗爭
六、無法突破的死結:君王專制
七、明夷之待:破碎山河後的省思
第七章 反抗原型—明鄭亡後無中國
一、前言:「開臺」的意義
二、明亡於何時
三、亡天下與清學抹殺論
四、最後的「天下」:明鄭二十三年
五、近世第一波的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
六、結語:臺灣的明鄭文化原型
第八章 明清之際儒學的現代性曙光
一、前言: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
二、知識與良知的斷續關係:再參「格物致知」公案
三、物的反思:質測與通幾
四、政道的呼籲:從吏治到政治
五、「明清之際」作為「清民之際」的詮釋學大地
六、結語:明夷、曙光與等待
結 論 現代化工程仍在進行中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序言
中國近世和西方碰觸,很不愉快,常聽到的時代主旋律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此次的中西碰觸之深廣,影響之深遠,用李鴻章的話講,可說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晚清以來,遂有自強運動、變法立憲、武裝革命的救亡圖存之舉,古老的中國面臨文化轉型的巨大考驗。時序進入二十世紀後,危機持續加深,救亡圖存的壓力未曾稍減,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九四九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可視為這樁轉型工程三個極重要的地標。中國一百多年來政治局勢的演變大抵越走越趨激烈,脫離中國原有的道路越來越遠,暴力的成分越來越濃。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性的共產主義革命的一環,也是民國以來反傳統路線發展的高峰。
民國時期的三大革命事件的歷史意義前後相續,左派人物論一九四九共產主義革命的性質時,常將此次的革命視為一九一一辛亥革命及一九一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完成者,甚至視為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歷史發展的目的,這是一種解讀。他們的解讀甚至可將時間往前延伸,直至晚明時期。即使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革命是在馬列主義引導下的徹底反傳統的革命,途徑是那麼地顯著,但它仍須尋求中國社會脈絡的支持。
這種歷史目的論的解讀在文化傳統主義者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但他們將視角轉到自己腳踏的文化大地上,詮釋學的前見(prejudice)是思考問題的起點。如果二十世紀中國的三大革命的意義前後相承的話,它們或許都可視為作為母體的華夏文化在現代化轉型運動中生起的三個環節,環節的轉換或如理或不如理,但前提總有傳統文化作為反應的背景。文化傳統主義者往往將二十世紀新文化轉型工程的源頭溯源至王陽明之後的晚明及明清之際,也就是十六及十七兩個世紀,他們也相信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兩個時段的思潮,前後遙遙相應,民國新文化運動中有中國傳統的基因。文化傳統主義者的解釋自然只是眾說之一,但以中國文明的體量之大及傳承之久,任何新理念要在中國社會生根發展,它需作新舊社會階段的接榫工作,這樣的設想應當是合理的。筆者認為文化傳統主義者銜接現代性與儒家傳統的設想有史實的依據,也有理論的支持,值得嚴肅考慮。
筆者接受中國現代性的晚明源頭說,但也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來自西歐文明引發的現代化的變革,它的格局超出傳統中國文明的視野,需要新的藥方,病情才能見效。本書持的是混合現代性的觀點,也認為清末民初的時代風雲兒梁啟超、孫中山等人也是主張中西現代性的銜接說。但因為作者專業所限,本書會將焦點聚集在王陽明以下儒家思想的發展,主體概念的變遷是本書敘述的一個潛臺詞。本書因為有中國現代性的關懷,所以內容雖以十六、十七兩世紀的思潮演變為核心,卻不能沒有當代的關懷作為支柱。本書實質上採取的是流動性的雙焦點,一強一弱,一明一暗,強焦點在晚明清初,弱焦點在晚清民初,關懷面在學術也在政治。
本書無疑地涉入了儒家現代性方案的解讀,所以有較明確的價值定位,但內容不能局限於儒者哲學思想的析辨,多少要將隱藏的歷史影響的因素帶進論述當中。而在論述思想的發端與作用時,也不能不對一些可敬的大儒指指點點,佛頭著糞,同時呈現他們的思想之特色與不足,以顯現後來者思想的繼承與批判的軌跡。圓滿的人格與圓滿的思想是理型世界的事,現實世界是有個性與歷史的場域,共性要自我坎陷於個性,圓滿要透過缺陷而顯現,就像永恆需要變化的補足一樣。本書的敘述方式和一般的儒學史的呈現方式不一樣,關懷不同故也。
本書的論點基本上延續港臺新儒家及日本戰後「中國近代思維說」的日本學者的觀點而來。「近代思維」或作「近世思維」,中日文翻譯及使用方法不同的緣故,本書沒有強求統一。作者於求學期間,頗受益於港臺新儒家學者的著作,也多有機會向他們執卷請益,但當時對於他們在現實與理念之間所作的哲學整合工作之意義,了解仍不夠深。上世紀末,筆者也有機會拜晤島田虔次與溝口雄三先生,溝口先生在新竹清華大學客座時,筆者更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其人其學。溝口先生左派儒學的取徑和剛解嚴時期風起雲湧的臺灣社會運動,有種奇特的呼應關係,溝口先生當時對臺灣學界的儒學同行應該是有些期待的。但在二十世紀,筆者一點微不足道的現實關懷與同樣青澀的學術專業,兩者不太連得上關係。經過多年的探索,個人的生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時代的氛圍也大不同於解嚴前的臺灣社會,本書嘗試作一點儒學與當代社會連結的工作。本書雖是學術專書,但在心境上,毋寧更該視作一篇遲交的報告,也是對可敬的中日儒學前輩學者的禮敬。
本書的篇章在不同的學術會議場合報告過,也多已分篇發表。二○一八年冬承蒙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雅意,筆者應邀擔任該中心首場講座,講座共五講,名稱為「儒家與當代中國」,較密集地探討了儒家與中國現代轉型的議題,議題從晚明到當代。此次出書,筆者在以往的學術業績以及講座的基礎上,一分為二,出了兩部書。一探討民國思潮,一探討晚明以降的儒學思潮。兩部書是對中國現代性的儒家方案的解讀,兩書內容前後呼應。筆者將包含兩岸關係在內的中國現代性議題放在此在(Dasein)的詮釋學基礎上定位,這是種築基於歷史過程及文化風土上的共在性地緣政治學,它與以權力博奕為核心的脫內在關係的地緣政治學著眼不同。地緣的「緣」可以放在兩集團交鋒處的「邊緣」來理解,也可以從各種歷史與文化因素交集的「緣會」來理解,前者是平面空間性的權力布局之緣,後者是立體時空的相互主體性之緣。一個「緣」字,兩種理解。本書從共在性地緣政治學出發,將焦點集中在華人政治版圖尚未明顯分化的晚明階段,嘗試理清中國現代化轉型的來龍去脈。
從共在性地緣政治學考量,本書收入明鄭的反抗意義的專章,既將它視作明儒道統論運動的尾閭,也將它視作臺灣反抗運動的原型,這是從關係界定本質的一種視角。明鄭是個複雜的概念,鄭成功的歷史形象也有各種折射。但鄭成功的抗爭意圖應該是清清楚楚的,從與鄭成功同代的抗清同志張煌言、黃宗羲眼中看來,明鄭的抗爭主軸當放在傳統所謂的春秋大義下看待,可視為繼承東林、復社反抗運動的一環,而且反抗到天涯海角,山窮水盡,極反抗精神之極致。魯王、寧靖王、鄭成功、陳永華在臺灣、澎湖、金門的奮鬥雖然難挽虞淵之落日,但精爽不滅,不必以成敗論英雄。
感謝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林遠澤主任及中心同仁的邀請與督促,他們多次提供了場所,讓筆者有機會將書中論點攤在不同關懷者的交鋒下,試煉,補強,存活。也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鄭宗義教授讓我有機會在該系先後主辦的學術會議及香港新亞儒學講座上報告此書的內容,在擔任新亞儒學講座前後一週的時間,竟然湊巧地在現場目睹了幾次「反送中」運動的悲壯與挫折。感謝《東亞文明研究集刊》、《清華中文學報》、《中國哲學與文化》、《中正漢學研究》、《現象學與人文科學》、《文與哲》等期刊允許我收錄刊於該期刊上的文章,由於期刊文章的體制與專書的要求不同,本書對這些文章的內容作了詳略不等的修正。但仍難免重疊冗雜,不夠潔淨。最後更要感謝蔡岳璋博後以及蔡錦香助理耐心地幫忙校稿工作及行政事宜,筆者當然要負最後一切的責任。
導論(節錄)
龍場一悟──良知學的登場
一、前言:晚明、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
如果說王陽明是五百年來影響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位儒家學者,這個判斷縱然無法得到學者普遍的同意,但至少王陽明獲選的機會極大,這樣的判斷很可能是可以被接受的。王陽明活在十五世紀末期至十六世紀早期之間,頭尾的年分各占一半,他的後半生穿越了以舉止荒唐著名的明武宗正德十六個年分,又進入了以專斷剛愎著名的明世宗嘉靖的前七年。這段時間並不是對思想友善的歲月,但王陽明的思想因他本人的功業及門生的努力推廣,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的思想的解釋力道,竟深刻地衝擊了晚明的帝國。
王陽明的學問以良知學的名義著稱於世,他的影響不僅止於儒學的範圍,良知學的因素還滲透到晚明的社會及文化上去,並引發明末清初的另類儒學的反動。他的影響也還不僅見於晚明,兩百多年後,良知學在清末民初又是一支重要的思想力量,同時,明末清初思潮也曾活躍於清末民初。「良知學之於晚明思潮」、「晚明及明末清初思潮之於清末民初文化」的現象很明顯,不太需要強調。如果我們關心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我們對「晚明及明末清初思潮在清末民初」這股隔代影響的現象再下一轉語,可以說即是「良知學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如何理解的問題。
本書認為晚明及明末清初的重要文化議題在清末民初再度顯現,也就是在密切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脈絡下返魂重現,關鍵的時間點在甲午(一八九四)、乙未(一八九五)年間。但之前的十九世紀下半葉,也就是鴉片戰爭以後,大清王朝已不能不浸漬在歐風美雨的侵襲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大清王朝大不同於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者,在於代表現代西方文明的歐美政治勢力已及於中國。如何同時回應來自歐亞大陸的帝俄勢力以及海上的歐美資本主義帝國的挑戰,這個新因素已是大清王朝必須面對的政治困局。到了日清甲午戰爭大清大敗,乙未訂立馬關條約大清大輸,大清王朝朝野上下才徹底地翻轉過來,死心塌地地想到變法革新,救亡圖存,刮骨入髓的現代化工程於焉展開。這個新時代帶來重要的新議題,其衝擊之大可以說是秦漢後僅見,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議題不能不推出並擺在歷史的議事臺上。
然而,正是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向歐美敞開大門之際,它同時也向被它滅亡的勝國思潮招手呼喚,清末民初的新議題和再度流行的晚明及明清之際的文化議題交涉重疊,合流競馳,王學及明末清初的儒學思潮事實上介入民國新文化的建構裡面。學界談中國現代化的議題時,不論是新儒家的良知坎陷說模式,或是日本漢學家的中國近代思維模式,遂有將中國現代性上推至王陽明啟動的晚明思潮的論述。這樣的解釋再稍加推衍其內涵,也可以說它意味著中國現代化工程的解釋應該採混和的現代性的提法,亦即十六、十七兩世紀的中國原生現代性碰上清末傳進來的西洋現代性,兩相混合,衍化出現代中國的格局。雖然在混合變遷的過程中,混合現代性的路途並不平坦,對新議題的認識並不清楚,初步的結果也不一定可欲。但工程仍在進行中,排難解紛,批卻導款,現代化的工程總不會一步到位的。演變至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兩種現代性銜接的模子。
從混合現代性的角度著眼,良知學的出現不可能不是關鍵性的因素,而王陽明於正德三年(一五○八)在龍場的那場著名的一悟,則是良知學正式成立的標誌。良知學絕不會只是理學史的概念,它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重要的一環,釐清過去,正是為了正視現在,並看清未來。我們如果釐清王陽明於正德三年那晚在那麼窮困荒蠻的地區發生的精神轉化事件,了解這個事件到底啟發了何等顛覆現實的機制,我們對良知學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或許可以有另類的想法。
二、新格致說的出現
《王陽明年譜》於正德三年戊辰條下,記載王陽明經過曲折的心理掙扎過程後,於當年春天到達了貴州的龍場。龍場當時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鳺舌難語。」這是個活像《山海經》的《大荒經》的世界,也像屈原〈招魂〉裡的異類空間。年譜接著記載對人生命運已有相當了悟的王陽明之心情與行事如下:
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黙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
《五經臆說》今已散佚,王陽明所以作此書,意在表示他所悟的內容並沒有離經叛道,反而與儒典是相合的。年譜是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等人在王陽明逝世三十五年後初步編成的,其時已是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年譜所以有上引這段話,潛臺詞當是當時頗有人認為王陽明體悟的《大學》格致說是新說,未必符合聖人本意。所以王陽明要以《五經》之言印證自己的體證,以示所悟格致新說雖是臆說,卻與聖人本懷若合符契。
龍場一悟帶給王陽明極大的自信,良知學正式成立。年譜記載他隔年即開始暢論「知行合一」的旨趣,而且席山、徐愛、冀元亨、蔣信等著名門生已圍繞著他,開始研習良知學的真諦。王陽明的講學生涯一啟動,即不可遏止,縱然他以後公務倥傯,戎事雲集,而且在惡劣的政治文化氛圍下,無意間即捲入糾纏不清的政治鬥爭中。但他從來不廢講學,良知學隨著他的足跡散布到江南、西南,甚至大明江山各地。他晚年居越,其時隨他學習的門生多到甚至居不能容。錢德洪記載嘉靖二年之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環繞在旁的門生已來了一年多了,姓名竟然還記不全。教學時,王陽明甚至要他的一些及門弟子等人分擔工作,擔任良知學的講師。講會的規模真是不小了,五十而知天命以後的王陽明親眼目睹了良知學流行的榮景。
上述所說,只是越中一地的盛況。良知學之特殊者,在於其學並沒有人亡政息。相反地,王陽明逝世以後,類似的講會還會繼續在各地,尤其是王陽明過化之地,如野草蔓延般地散開。一場講會,甚至可聚集聽眾達四、五萬人。講會之盛,遠邁宋元,開儒學史上未有之新局。萬曆早期,張居正執政,他對書院、講會特多禁忌,不是沒有原因的。一位以嚴厲整肅天下秩序自許的大政治人物,在沒有學術自由理念的背景下,他怎能容忍最有動盪社會潛能的良知學的講會呢?我們如不了解良知學,毫無懸念地,我們即無法了解晚明的社會文化。
關鍵還是要回到正德三年龍場的那個夜晚,王陽明「大悟」,所悟的內容為何?為何窮鄉深夜發生的一場私人性的事件竟能攪動寧靜的大明天下。據年譜所說,其內容當是「格物致知」的道理,但「格物致知」的議題自從經過程伊川與朱子的轉手的解釋,它的解釋變得有名地複雜,成了一潭難以澄清的濁水。哪家的「格物致知」說的提問因此不能不出現,龍場大悟,到底這場和「格物致知」有關的悟覺事件該如何解釋?
第一章 當代中國的黎明──晚明儒學的解讀
一、前言:「晚明儒學」概念的出現
本文探討晚明儒學的定位問題,但背景放在儒學與當代中國的關係下看待。當代學者探討中國現代性的議題時,往往追溯到晚明,但論點頗駁雜參差。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我們反思晚明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的文化問題,學術問題遂得深化,它不只具有歷史的興趣,它與當代中國的文化定向有特別的連結。
論及中國的現代性,我們很容易想到一個與它相關聯的概念「近世」。「近世」這個歷史性的概念指向「北宋」這個時間的斷點,北宋之前是五代唐朝,五代時間短,可視為唐宋兩代之間的過渡地帶,宋代文化的特色乃是在與唐代文化對照下產生的,唐宋文化的對照之解釋模式最著名者當是內藤湖南在一世紀前提出的「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在二十世紀初期提出的唐宋變革說影響甚大,在一九二二年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他提出「人民」的理念、科舉普及化、黨爭政見之爭的性質、君王專制完善化、貨幣流通、學術自由化、文學與藝術更具特色云云,以突顯宋代文化的特色。後來他的學生宮崎市定繼起,踵事發揮,「宋」作為一種中國近世的起源,遂成了有力的假說。
「唐宋變革說」是一個大的歷史命題,此命題有相當豐富的內涵,它在學界引發的影響也相當的大,筆者受益於這個假說匪淺。一個與「宋代」的時間性斷點可以相對照的是中國近世性質源頭的晚明說,晚明說成立的條件是放在陽明後學下論述的,陽明後學主要的思想自然是繼承王陽明而來,陽明之學事實上又是理學的一支,陽明學者問問題的方式以及提供的答案都還是帶有兩宋的理學之風的。本文聚焦晚明最重要的理由當然是這個提問乃是學術史的事實,它是傳播頗廣、影響頗大的公共論述。晚近在日本、中國、海外學界,學者提倡中國的現代性議題時,往往追溯到晚明,筆者稱之為「中國現代性的晚明起源說」。我們順藤摸瓜,容易突顯出焦點。
中國現代性的晚明起源說的提出者不只一個來源,首要者當是二十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從經濟史觀提出的觀點,他們探詢中國社會的性質時,發現晚明是轉變的關鍵期。在儒學史或思想史界,此一論述或可溯源至嵇文甫的《左派王學》,其結論最後集結於侯外廬、范文瀾的「資本主義萌芽說」。由於馬克思主義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極大,回應馬克思史觀的「資本主義萌芽說」的聲勢自然也相當可觀。另一種晚明說則是順著理學的脈絡下來的,這種晚明說強調陽明學本身具足了轉化人生也轉化文化的動力,梁漱溟的論點可為代表。一九四九以後,港臺新儒家提出更完整的觀點,筆者稱之為「良知學轉出說」的模式。「良知學轉出說」是「良知坎陷說」的修正版,它是一種歷史的敘述,而不僅是哲學依據的解釋。這種晚明說強調現代性的內涵在晚明已出現,但其時儒者的理論資源不足,沒辦法在制度上完成儒學的內在要求。港臺新儒家學者追溯中國現代性的起頭可追溯到宋儒,但焦點集中在明末三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身上。此外,日本儒者島田虔次、溝口雄三也都提過晚明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筆者稱之為「近代思維」的模式。島田與溝口兩人的觀點頗有異同,雙方辯論甚為精緻,這條路線無疑地可上溯至內藤湖南提供的「唐宋變革說」,其說與丸山真男約在同一時期發表的巨著《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雖然定位相當不同,但也有交涉。他們的論點與中國學者的晚明說頗可相互發揮,本文雖以「資本主義萌芽說」及「良知學轉出說」作為論述的主軸,但「近代思維說」的論點也將是本文重要的參考架構。
二、從「左派王學」到「資本主義萌芽說」
論及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不能不提王陽明所扮演的角色,近代中國思想的演變與陽明學有密切的關係。陽明學在有清一代,除了明末清初這個階段仍保留晚明的餘暉以外,基本上處於隱伏的狀態。清廷政權穩固以後,基本上以朱子學作為官方的意識型態,清朝的朱子學就像任何成為官方意識型態的思想的命運一樣,都不免在過度保護下,生機斲喪,逐漸枯萎。到了晚清時期,風雲際會,乃有陽明學復興之勢。晚清維新大將康有為、梁啟超都是陽明學的提倡者,同時期的劉師培與康梁學風不同,但同樣宣揚王學不遺餘力。康有為注意陽明學或許與其師朱九江有關,但筆者懷疑與其時日本陽明學的復興可能關係更大。眾所共知,康有為登上中國思想舞臺一個重要的歷史契機乃是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清日簽訂極羞辱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康有為約在京舉人,公車上書,終於引發震動一時的百日維新。甲午戰爭提供的教訓非常深刻,康梁維新,孫黃革命,嚴復以譯事宣揚新的文明理念,可以說都是受到此場戰爭的刺激。清日兩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後,同樣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樣展開過救亡圖存的學習過程,何以日本區區一島國,最後竟能戰勝老大的大清帝國?這是那個時代知識人關心的焦點。日勝清敗,其中一條線索被認為很可能和王學有關—雖然這條線索存不存在或者怎樣的存在?不一定容易講得清楚。
陽明學傳到日本後,在東瀛三島的流傳呈跳島狀,藕斷絲連,不像朱子學那般有較明確的傳承的線索。然而幕末時期,維新志士多受陽明學影響,從佐藤一齋、大鹽平八郎到吉田松蔭,陽明學在他們思想中都占有一定地位。明治維新的功臣當中,頗有受陽明學甚深影響者,如東鄉平八郎,這也是事實。已故日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論及當代士風之不振時,即特別標舉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陽明學的作用,他最後也以自己認定的良知學之義理走上淒美悲愴的櫻花萎絕之路。有關明治時期日本陽明學與維新的關係,以及日本的陽明學是否或是透過了什麼樣的管道反過來影響了清末的陽明學復興思潮,此事有待學者更進一步的研究。但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此事是十九世紀末影響中國極深遠的一件事,此事多少刺激了陽明學在中國的研究之興起,這似乎是條可以接受的理論線索。
筆者所以舉出甲午戰爭和中日陽明學的關係,意指陽明學在近世晚期中國的復興原本就和中國的現代化的工程分隔不開,甲午戰爭乃是仿效近代西方科技的兩大東亞國家的直接對抗,但就象徵而言,也可視為西方現代性的代理人戰爭,這場戰爭直可視為檢驗中日兩國近代化工程成績很好的測試劑。陽明學在當代中國是被歷史逼出來的,它是學術論述,也是政治論述,它在近世遂不能不與「現代化」這個歷史工程綑綁在一起,兩者的內涵息息相關。
然而,陽明學之所以會在當代形成一樁與現代性有關的假說,亦即資本主義萌芽說,其關鍵人物當是嵇文甫與侯外廬對晚明思潮重新解釋的成果。其中嵇文甫的出生與撰文日期都比侯外廬早,他的「左派王學論」在當代的晚明思潮論域中,更居有開風氣之先的地位。左派王學之說不是傳統的學派分類的用語,嵇文甫對此一用語的脈絡沒有解說。此詞語或許取自黑格爾左派、右派之分,黑格爾右派有加布勒(A. Gabler)、欣里希斯(H. Hinrichs)、羅生克蘭茲(K. Rosenkranz)等人,這一批國人不太熟悉他們思想的黑格爾後學,常被歸類為保守派,他們的思想深潛於宗教哲學的土壤中。黑格爾左派哲學家如施特勞斯(D. F. Strauss)、鮑威爾(B. Bauer)、費爾巴哈(L. A. Feuerbach)這些相對年輕的黑格爾後學則重感性,重物質,在政治思想及行動上通常也較具反封建的精神。由於馬克思和左派黑格爾的思想關係匪淺,因此,嵇文甫受到黑格爾學派發展的影響,因而有左右派之分,此事是相當可能的。嵇文甫的用語也可能受到王學「江右學派」一詞的暗示,因為嵇文甫所列出的左派王學,主要的對話對象正好是陽明後學的江右學派中人。江右學派的特色注重良知的致虛內斂,體證心體。學者平日用功所在,對內當收斂精神,對外當恪守倫理,聶雙江、羅念菴、王塘南等等江右學者的學說大體近似。嵇文甫所說的王學左派中人則注重良知的情感與意志的作用,並落實於人倫日用,在紅塵是非中行道。陽明後學的這兩種思想趨勢和黑格爾後學的左、右派對分,倒有幾分近似之處。以彼喻此,作為論述的工具,「左派王學」之說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理論設準。